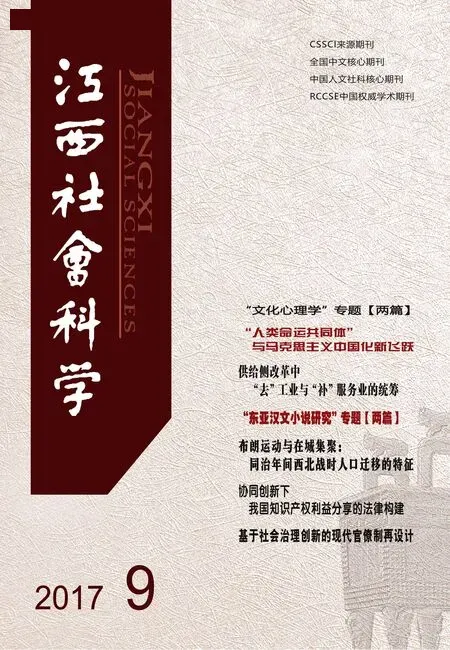胡适对黄庭坚白话诗人身份的确认与阐释
■董 赟
胡适对黄庭坚白话诗人身份的确认与阐释
■董 赟
新文化运动之际,针对当时的文学状况并结合文学革命需求,胡适在“分身法”下以“白话”为标准对黄庭坚诗词进行新阐释:推重流利平易的古诗并大力发掘其律诗中的白话因素,以“做诗如说话”重新指认黄诗特点;在文学史观进化论下,搁置淫邪猥琐及著腔唱诗的部分,以“歌者之词”有意拔高本色当行的山谷词,认定黄庭坚“白话诗人”的身份。胡适的重释意在建构,将现代的思想和眼光带到古代文学研究中,是考察其进行经典重释与传统发明的典型个案,具有批评的翻案及文学经典重构等多方面意义。
胡适;黄庭坚;新诗;白话诗人;宋诗运动
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在《国语文学史》中说“最近几十年来,大家爱谈宋诗,爱学宋诗”[1](P74),是指清末民初流行的宗宋、学宋之风。彼时江西派法席盛行,同光体诗人“大半瓣香黄、陈,而出入于宛陵、荆公”[2](P293),宋诗派的壮大意味着诗文创作领域内复古思潮的显扬,“同光体诗人不过于山谷以外,参以昌黎、半山、后山、简斋等”[3](P359)。随着同光体诗人相继离世、文学革命势起与白话文学发展,宗宋学黄的热潮减退。1922年胡适撰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总结说:“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4](P227)胡适所定义的“宋诗运动”不仅指同光体诗人,亦涵盖“诗界革命”实践者及正如火如荼壮大的新诗白话诗人。将白话诗人纳入“宋诗运动”范畴,把新诗和以文字、议论、才学为特点的宋诗相提并论,正源于胡适彼时对宋诗风格的独特理解和全新阐释:“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4](P227)在新的理解情境下,胡适从山谷诗词接受传统及阐释语境中抽离,从“白话”的角度重释黄庭坚及其代表的宋诗词原型,并建构新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
一、重释:“分身法”下黄诗的“做诗如说话”
在《〈国语文学史〉大要》中,胡适集中论述了他理解、评价黄庭坚诗词的角度和方法:
又如黄庭坚(山谷),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家。他的诗都是古典的,但他做的小词,不但完全用白话,而且常用土话。我们现在用分身法来看黄山谷,把他的古典文学江西派拉去,剩下的完全是高兴的时候,写出来的白话作品,或是做给妓女唱歌的小词小曲,那才是真正的黄山谷的文学哩。[1](P134)
细绎这段话可知,胡适并未因大力鼓吹新文学而彻底抛弃旧文学,相反,在肯定古典文学价值的同时亦认可黄庭坚作为“很重要的文学家”的地位。胡适重释时所用方法即所谓“分身法”,将黄之文学分为“古典文学江西派”“白话作品”和“小词小曲”,并称后二者为“真正的黄山谷的文学”。胡适据此挖掘出黄庭坚那“许多的不同”,同时,通过将这三类文学纳入文学史书写,或贬抑或欣赏,用山谷那“不同的、特别的表现”透露他建构文学史的标准。
“分身法”在《国语文学史》①的论述中被充分实践,胡适严厉批判“古典文学江西派”的文学:“他们常有许多用典的诗,有时还爱用很僻的典故,有时还爱押很险的韵。但这种诗并不是他们的长处。这种诗除了极少部分之外,并没有文学价值,并不配叫做诗只可叫做‘诗玩意儿’,与诗谜诗钟是同样的东西。黄庭坚的诗里,这一类的诗更多。如他的《演雅》《戏书秦少游壁》,同大多数次韵的诗,都是这一类的。”[1](P79)《演雅》以一韵到底的七言古诗铺排四十二种鸟虫情态,并以之比况谗佞,颇有讽喻,胡适称它为“诗玩意儿”,大概因其手法上趋向极致的用事、隐括、以赋为诗,及形式上整齐的句式和工整近于呆板的对仗,使诗的韵味大大削弱;《戏书秦少游壁》及部分次韵诗亦多此类毛病。胡适很反对“‘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一类不通的古典诗”[1](P100),使事用典向为山谷所长,在胡适这里却是很被轻视的“把戏”:“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5](P83)
然而,胡适重写文学史的目的在于建构,重心在发掘古典诗中的白话因素。因此,他以“分身法”重释黄诗:“宋诗到苏黄一派,方才大成。……依我们用文学史的眼光看起来,苏、黄的诗的好处并不在那不调的音节,也不在那偏僻的用典。他们的好处正在我们上文说的‘做诗如说话’。”[1](P79)剔除“古典文学江西派”的作品后,“黄庭坚的好诗却也不少”,这部分“白话作品”是胡适重释山谷诗的目光聚焦处,并且相对于苏诗而言,“黄庭坚的诗,更可以表现这个‘做诗如说话’的意思”[1](P80)。胡适自称最喜欢《题莲花寺》,《国语文学史》引述全诗且加着重号,并阐述:“这虽不全是白话,但这种朴素简洁的白描技术完全是和白话诗一致的。”[1](P80)是否全用白话并非判断白话诗的标准,重要的是诗意明白晓畅,所采用的白描手法与白话诗一致。早在1916年,胡适复信任鸿隽讨论“作诗如作文”时即引用《题莲花寺》,并说“此诸例皆千古名作,试问其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5](P68)以此阐发他要“以质救文之弊”的理想。结合书信内容来看,胡适认为《题莲花寺》没有那“重形式而去精神”“以文(form)胜质(matter)”的病根。1919年,胡适作《尝试集》序时再次引用信中内容并进一步说明:“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6](P139)诗歌的韵味由内容而非形式决定,所以“这诗里的小毛病,如‘马百蹄’,‘不敢谁’也只是因为旧格式的束缚;若打破了这种格式,便没有这种缺点了。”[1](P74)将古典诗的格式视为限制白话诗及其代表的“活文学”正常发展的障碍。因此胡适提倡“诗体大解放”,志在打破旧诗格式来创造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长短整齐不拘,做真正的白话诗。同时,“诗味在骨子里”是胡适对山谷诗“韵胜”特质的现代阐释,与黄庭坚的诗论如出一辙。
此外,《国语文学史》又引《跋子瞻和陶诗》《题伯时画顿尘马》及《戏简朱公武刘邦直田子平》(其五)三首古诗,并言:“这不都是说话吗?”此三诗用“吃饭”“洗袍裤”的俗语,“虽”“乃”“亦”“何如”等虚词,无一僻典,平易浅显,近于说话。“说话”与“白话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简单易懂,“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然而,诗非止于此:“我并不说,明白清楚就是好诗;我只要说,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7](P277)以此三诗为例细析可知,“明白清楚”之外,好诗尚有更深刻的内涵和要求。《跋子瞻和陶诗》以简驭繁,遗貌取神,以简洁的笔法刻画对师友苏轼的悼怀与对未卜命运之忧虑,形成骨子里的诗味。1959年,胡适在书信中评价钱钟书《宋诗选注》时,提及黄庭坚仍忍不住称赏此诗:“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5](P1396)时过境迁,胡适彼时去文学革命的时代和环境远矣,也没必要在私人信件中着意宣传什么理论,而是审美偏好与接受惯性的自然流露。可见,在胡适眼里,《题莲花寺》与《跋子瞻和陶诗》堪为黄诗的代表作,这类“白话作品”正符合胡适的文学审美。同时,在整部《宋诗选注》中胡适尤其以所选山谷诗不具备代表性来证明钱著“选的不好”,说明胡适对黄庭坚文学经典及宋诗特征的认识与钱钟书大相径庭,也正证明其审美趣味与文学史观有极强的个人特点。
后二诗均出以俳谐的手法,幽默的况味。《戏简朱公武刘邦直田子平》,诗题已明言为戏作,整首绝句流畅如叙事,简洁如漫画,简单明白,又兼一丝诙谐意趣。《题伯时画顿尘马》以转折跳脱的笔法将精神从沉闷的文书工作中解脱出来,进入归思的邈远境界,这题画诗已远超出画面之物象与风韵,采用的“打诨出场”章法使全诗形成一种“比喻性结构”,“以其语境的大跨度跳跃和逻辑关系的超乎常规而获得一种‘反常合道’的‘奇趣’,它与宋人追求的审美趣味是一致的。”[8](P462)这种“奇趣”不仅为宋人所好,其旨归亦见纳于胡适,鉴赏诗歌时他非常欣赏奇趣、谐趣、理趣和风趣。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多次表述对陶渊明“诙谐”、杜甫“诙谐风趣”和“俳谐诗”、韩愈“诙谐”、卢仝“滑稽风趣”、杨万里“风趣”等的欣赏,认为文人作的打油诗正是“白话诗的一个来源”,认定“诙谐的风趣同白话诗的密切关系”。[1](P74)以此来看,胡适对文学史的建构以“趣”为宗,而他自己在“实行这主张”时也好作打油诗。可见,这二首诗的内在韵味与胡适对幽默诙谐风味的偏好一致。“趣”本身就有“反常合道”的深刻哲理,是对严肃的主动放弃,对执着的有意超越,从这个角度说,胡适认可黄庭坚所说“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9](P666),也发掘了更为真实的黄庭坚,山谷诗在内容与情感上的真实性和个性化更为凸显。同时,这三首诗均作于山谷中晚年,时诗风已渐趋稳定,平淡简易而诗意充盈。胡适那颇具内涵的“说话”准则竟与黄庭坚晚年所反复申言并积极实践的“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9](P471)及“语气平而意深,理盛其文”[9](P1966)等诗论高度一致。
胡适的解读是,黄庭坚“白话作品”的好处在于“做诗如说话”,“我们读黄庭坚的诗,都应该用这一个观点来读他,方才可以真正领会他的精采之处”[1](P74)。《国语文学史》选《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池口风雨留三日》与《登快阁》三首七律。凡诗中用典、使代字、当句对处,胡适均未加着重号,胡适欣赏的是诗中随感录式的写法,触物兴怀、涉笔成趣,很有点“我手写我口”的意思在,且诗意畅快明白,语言清新平实。至于经典名篇《登快阁》,纪昀言“起句山谷习气”[10](P39),概因不满山谷以夏侯济信中那“痴儿”的口俗语入律诗;张戒《岁寒堂诗话》批评颔联“但以远大、分明之语为新奇,而究其实,乃小儿语也”[11](P457)。而胡适偏赏首联及颔联,正因其口俗语、“小儿语”所带来的天然质感,加之即目所见,没有安排痕迹,音调自然近于说话。因此,只要以“说话”的标准审查,关注“质”而非“文”,即便律诗亦可以是“白话作品”,这是胡适重释经典和建构白话文学史的一个前提。
通过胡适对黄诗的重释可知,“白话诗”内在地包含着明白清楚、不用典、俗语、白描、质胜文、趣、诗体解放等要素,与黄庭坚“韵胜”、平淡论的文艺理想有精神上的一致及理论上的部分重合。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固然与其审美偏好有关,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传统中“文胜质”的主观反叛,也是对当时“文学之腐败极矣”现状的有意纠正。这样的论述已经超越纯粹的文学研究,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一种文化选择。
二、建构:文学史观进化论下黄庭坚的白话诗人身份
“黄庭坚的诗,为江西派的祖师,影响至今不绝。他的诗多用古典,流弊甚大。但他做小词,却流利明显,绝不似他的诗。”[12](P138)“分身法”不仅被用以区分山谷古典江西派的诗和“白话作品”,亦是诗词分界的方法。如果说“真正的黄山谷的文学”“因为旧诗体束缚住了,这个白话的趋势在诗里不能完全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在下文看黄庭坚的白话词,就可以知道他真是一个白话诗人”。[1](P74)随着关注点从诗转到词,黄庭坚在胡适的文学史建构中成为白话诗人,而山谷诗词面貌迥异的原因在于:
山谷作诗还不能打破古典主义的权威,故他的诗只能代表人造的权威,而不能代表历史上自然的倾向;及至他随意作小词时,一切古典主义都不必管了,随便说小儿女的自然语言,便成好词,所以他的词——因为是无意的——代表历史上自唐末以来的一个自然趋势。[13]
所谓“历史上自然的倾向”,是胡适以历史进化的眼光看待诗的变迁,从《诗》到骚,到五七言体、词、曲,再到新诗,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演进来的。因此,包括“从诗变为词”的“最大的解放”在内的中国传统诗体之变化,都成为胡适大力鼓吹“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的历史依据。[14]在这种进化论的诗体观念下,胡适认为“‘白话韵文的自然趋势应该是朝着长短句的方向走的’,长短句的词比那五言七言的诗,更近于说话的自然了”,因此“北宋白话文学最发达的方面是在词的方面”。[1](P92)
在对北宋词史的梳理过程中,胡适依次列举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和秦观的白话词,所选五家尚能得北宋词之大概,然于黄庭坚,胡适评价:“黄庭坚是宋朝第一个白话词人。”[1](P98)鉴于前述胡适之文学观念,他对黄庭坚白话词人身份的认定是一种很高的评价,并且,通过“宋朝第一个”的定语,将历来评价不高的山谷词重新置于研究的聚光灯下。词风放浪近于淫亵的山谷何以担得起北宋白话词之开创者?其词何以代表“自唐末以来的一个自然趋势”?胡适于1924年开始选注《词选》,意在通过选词展示“选择去取的大旨”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通过评点、注释,胡适展示他对山谷词、宋代白话词及白话文学的认识。序言称“山谷,少游都还常给妓人做小词,不失第一时代的风格”,“第一时代”即指前文区分的词史之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中“歌者的词”的阶段,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特征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12](P8)山谷词,尤其是前期词,多半应歌妓演唱需求、为迎合市民口味而作,故题材多男女恋情,内容庸俗放荡,用词俚俗泼辣。所以,山谷“随意”作的小词便是真正代表平民、顺应时代、用自然语言的文学,因此可称黄为“宋朝第一个白话词人”。针对历代对黄庭坚那些格调低俗的艳情词之指责,胡适在新标准下予以纠正并加以新释,提高山谷词的价值和地位。
尽管以“白话”和“民间”为标准,胡适仍剔除“亵浑不可名状”之作,选词要“用的是小儿女的情感,是平民的材料,是小百姓的语言”[1](P99)。《国语文学史》中引的第一首山谷词是《沁园春》,此词采用乐工娼女的视角叙说小女子情绪,用词浅显通俗近于口语,风味颇近民歌。《词选》亦录此词,“玉瘦香肌”下注:“此处用陈套语,最鄙俗可厌。”[12](P148)他强烈反对在词中使用陈套语,推崇自然流畅的词风。《词选》刻意注释山谷词中的“恶灵利”“个里”“则甚知”“斗顿恁”“合下”等,认为乃宋人白话入词。可见胡适发现黄词中大量白话时的兴奋,因为这不仅佐证黄庭坚“白话词人”的身份,也为白话文学史的建构增添材料。这种“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研究方法也被用在《国语文学史》中,胡适引《鼓笛令》(见来便觉情于我),证明山谷的一些白话词“用当时的方言太多了”,“这种词在柳永、秦观的集子里也有,但黄庭坚词里最多”[1](P100),从使用方言俗语的角度肯定黄庭坚的白话词。
《词选》与《国语文学史》中的选词篇目大致吻合,基本都属“歌者的词”。然而,令人颇感惊异的是,《词选》选录《清平乐》(春归何处)、《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望江东》(江水西头隔烟树)三首“意境已近东坡,不是柳永一派了”[12](P139)的词。《望江东》一阙颇受胡适欣赏。1916年5月,胡适在日记中记录“活文学之样本数则”,即抄录此词[15](P389-390);7月,胡适与人通信时举此以证明“宋、元人曾用白话作词曲”[5](P77-78)。三年后,胡适在信中又以此词解释“言近而旨远”的内涵:“譬如山谷的‘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一首,写的是相思,寄托的是‘做官思想’。”[5](P205-206)可见,尽管格调典雅纤秀近于文人词,但因其白话的使用及“言近旨远”,这类作品用民间的情感、材料、语言,仍属“活文学”范畴,与“以诗为词”之作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与胡适对黄诗白话性质的阐释一致。山谷词风格复杂,前后期变化明显,后期出现《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醉蓬莱》(对朝云叆叇)这类用词典雅、不避典故、词风豪迈且多叙述身世怀抱的词,沿着苏轼所开豪迈词风而来,扩大传统艳词意境,所选词牌多含五、七言句式,正是:“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16](P671)造句、内容、情调已近于诗,非歌者当行语,故而并不在胡适所选之列。
总之,胡适欣赏山谷词的准则在于,剔除低俗淫荡、以诗为词之作,选取“知词别是一家”的词手之作。这种眼光并非没有见地,那些具有民间曲子词本色的山谷词在当世也颇有影响。“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17](P309)“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18](P254)这类“山谷词酷似曲”[19](P1400),包孕着散曲的某些特点:“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20](P108)胡适显然已意识到词曲递兴、雅俗分流的逻辑:“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根本上看来,只是逐渐删除词体里所剩下的许多束缚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词体所缺少的一些东西如衬字套数之类。”[14]他用诗体进化论及对山谷词的阐释放大了古已有之的“山谷词酷似曲”的论述,对当时及后世的词曲史建构产生一定影响。
通过文学史和选词,胡适建构了他的宋词,黄庭坚则是这一文体的代表。其思路是:认定词代替诗是文体进化之自然趋势,已知黄庭坚是白话词人,而其诗、词有着“隔世的区别”,因此,通过“看黄庭坚的白话词,就可以知道他真是一个白话诗人”。这样,在文学史观进化论下,借文体概念的偷换,胡适不仅认定黄庭坚是“宋朝第一个白话词人”,也敲定其白话诗人的身份。
以上是胡适评说黄庭坚诗词的主要方面,可借此窥探他阐释古典文学的方法和角度。按胡适标准厘选出的山谷诗词异于鉴赏传统中习见之代表作,但亦清新可读,颇具艺术特色。这是因为,胡适看似只有“白话”这一个标准,实际上,他对于“明白清楚”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具备文学审美性。因此,胡适是在对山谷诗词进行文学审美的基础上挖掘其白话因素。这固然因为胡适浸濡古典文学已久,对文学有敏锐的感知力,也是由于黄庭坚诗词那可供人从不同角度解读的生命力和丰富性。胡适意在“但开风气不为师”,昭示他敏锐的感觉和新颖的面目,同时也标示出一种新的范例。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文艺思潮来看,胡适对白话的大力鼓吹很大程度上是为文学革命张目,因此,他不得不将中国古典旧诗设为假想敌。为了确证白话文学观念之历史合理性,他在建构理论时又只能从古典传统中寻找可资借鉴与转化的思想艺术因素,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追索一条白话文学史的发展线索。依靠这种刻意发掘的白话因素,胡适写出全新的文学史,不仅改造过去,也开启未来,或者说用改造过去来启示一种新范型。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引领的新诗实践以旧诗之道探寻新诗之路,将传统诗歌的创作经验用于新诗理论建设。总之,这是胡适针对当时文学状况、结合文学革命需求、以黄庭坚诗词为个案进行的经典重释和文学史书写。
三、意义:翻案的批评与文学经典的重构
作为学术创新时代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胡适对山谷诗词的阐释带有批评的翻案性质。胡适刻意强调山谷诗流利平易的特质,异调于接受传统中对以才学为诗、拗峭避俗的过分关注;对于山谷词,胡适搁置淫邪猥琐及著腔唱诗的部分,有意拔高本色当行的曲子词;排斥经典篇目的同时大量选录曾鲜为人注目的作品。对具体诗词的评价或有争议,但胡适确实将现代的思想和眼光带到古代文学研究中。他从黄庭坚诗词中看到的是白话的生气、形式的解放、内容的自然和情感的真挚,这不仅给诗词鉴赏提供新角度,丰富对黄庭坚的认识,也让黄庭坚这一宋诗的代言人在新时代白话文学的冲击下不至于被埋没,反而在新眼光下焕发生机。
同时,胡适承认唐宋诗之变,明确提出宋诗对唐诗的革新意义,他对宋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特征的概况也具有开拓价值。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本就承袭“以文为诗”及宋词而来:“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词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21]可以说,胡适是用新的知识和观点,从变化了的角度来审视固定的研究对象,他给“以文为诗”以新解释,在价值评判上建立新标准,形成一种不同于宋诗阐释传统的新路径,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但批评的声音一直同在,胡适在1918年就说:“外面有许多人误会我们的意思,以为我们既提倡白话文学,定然反对学者研究旧文学。于是有许多人便以为我们竟要把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学都抛弃了。”[5](P185)这种误会在今天依然存在。然而,正如郑振铎所说:“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22](P438)胡适这一代新诗先行者不是要割断与文言、旧诗的联系,而是旨在发明传统,将新诗看成一次类似词代替诗、曲更替词的自然的文学革新,为新诗争取文学史的合法地位,他们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本身也展示出古典与现代间的深刻历史联系。同时,他们的学术活动也带着整理国故的意图,重新评价旧文学并改造利用,一定程度上重构文学经典。从宏观层面来看,在中西方思潮激烈碰撞时,胡适等先行者选择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走出了‘西化’与‘化西’的二元对立,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关系中具有方法学的意义”[23]。
据此,如果将新诗看作诗体进化中的一环,视为古典文化传统的一次替代性生长,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五四时期的诗界与北宋诗坛之间相似的文化氛围,新诗之诞生与宋诗的变革、宋词的发展之间也存有内在革命性的一致。这样,胡适的革命之力呼应了山谷的开辟之功,一定程度上讲,二人诗作的才情都被过于自觉的理论淹埋,呈现出多理趣而少性情的特点。
注释:
①胡适原文常加着重号,本文在引述中未予以保留。
[1]胡适.胡适文集(第8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陈衍.石遗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4]胡适.胡适文集(第3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胡适.胡适书信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胡适.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胡适.胡适文集(第9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0](元)方回.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宋)张戒.岁寒堂诗话[A].历代诗话续编[C].丁福保,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胡适.词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
[13]胡适.胡适致顾颉刚信函[J].小说月报,1923,(4).
[14]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N].星期评论,1919-10-10.
[15]胡适.胡适日记全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6](宋)魏庆之.诗人玉屑[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7](宋)陈师道.后山诗话[A].历代诗话[C].(清)何文焕,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宋)李清照.词论[A].苕溪渔隐丛话后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9](清)李调元.雨村词话[A].词话丛编[C].唐圭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1]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J].东方杂志,1934,(1).
[22]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A].郑振铎全集[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23]贺仲明.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6,(9).
【责任编辑:彭民权】
I206.6
A
1004-518X(2017)09-0131-07
董 赟,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四川成都 6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