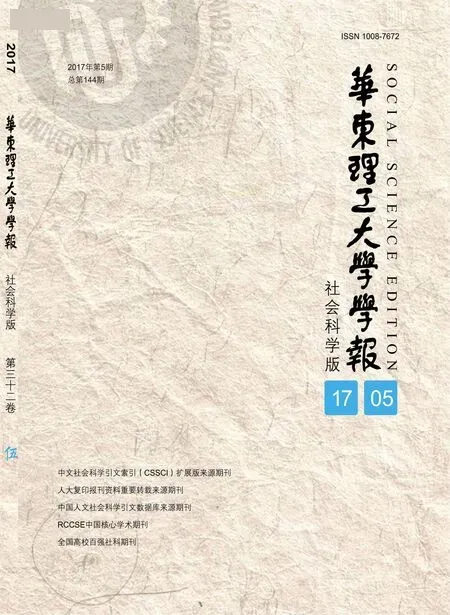文教、制度与大国治理
吴重庆
文教、制度与大国治理
吴重庆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觉得前面曹锦清先生说到的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一个国家在国力衰弱之后,其自己的那套制度也会遭殃,就会被污名化、被抛弃。可是,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从近代以来开始衰弱,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一系列制度所造成的。我在读了有关全球史、世界体系、全球化等主题的书籍之后,觉得中国作为大国在近代的衰弱实际上是由大的格局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扩张造成的,不能单单将其归咎为中国制度的问题。
从近代开始再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基本上都是对制度的污名化,所以曹锦清先生前面的说法是非常有力的。他提出了治体和政体,非常有力地让我们能够在思维的道路上稍稍扭转一下,即不要顺着近代以来的惯有思路一直走下来。我们以前经常说大国治理与小国治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一个小国的治理经验拿到中国这样的大国来套用。像上世纪80和90年代,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热衷组织干部去新加坡学习治理经验,我觉得这不太切合实际,因为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大概只有广州那么大,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去学习它的什么东西呢?以前有人常常把大国污名化,好像大国就一定与封建、专制、保守等东西相联系,殊不知大国能够维持下来是一定有它非常了不起的过人之处的。今天世界上还有几个大国能够像中国这样接续自己的传统资源独立自主地走下来?所以,曹锦清先生前面说,这绝对不是“人治”或者“专制”这两个词可以轻易地将中国政治过程打发掉的,它里面一定是有一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我觉得郡县制这个话题非常有力地回应了上述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作为大国能够走到今天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有一套成熟的制度在内。
曹正汉先生非常详细地分析了我们这套制度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到底这套制度好在哪里。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中国作为大国能够维持下来,除了郡县制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在维系着它?其实我不是很同意只是用“央地关系”来分析传统中国的一套政治过程,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国家概念去想象王朝,也不能以今天的交通及行政的可达性去想象数百年前的治理空间。在王朝时期,比“央地关系”更有弹性的是“天下”概念。
“天下”概念之所以能够流行,蕴含在其背后的内容是什么?这里面一定有文教也就是儒家文化。就是说,是儒家文化制度化的存在才使得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治理能够一直维系下来,因为我觉得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教化的载体,它非常有效地降低了大国治理的维持成本,或者说是行政成本。在古代那种技术条件下,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发挥这方面作用的话,光靠郡县制也不一定能支撑得住。所以这就联系到我对曹正汉先生观点的探讨,曹正汉先生提出的“强政权、弱国家”概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当时为什么是弱国家?首先,可能当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没有国家的形态存在,再一个就是文教发达。文教发达使得国家不需要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是弱国家、强文化。还有就是曹正汉先生提出的代理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问题。我觉得这两种风险的燃点和爆发程度是不一样的。可能代理风险比较容易出现危险、出现问题。异姓也好、同姓也好,利益稍微不均衡就有可能闹事,它的燃点是比较高的。但是社会风险,就是底层民众的叛乱、造反、起义、革命,其燃点我觉得是会比较低的。如果把这两种风险拿在一起分析的话,也许是需要适当作出区分的。我几年前到江西的兴国去做中央苏区的调查,当时也访问了当地的一些老人家,包括向他们采集区域内的历史传说。他们说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在江西那一带杀人无数、血流成河。我就问为什么这么厉害、杀这么多人?老人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老百姓不愿意向他们交粮、纳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们只认皇帝,只认清朝,人们不认太平天国的军队,人们宁愿被砍头也不向太平军交粮,所以导致太平军滥杀无辜。这背后就反映出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心中对正统的认同是非常深的,所以你让他们起来造反是不太容易的。我们知道历代民众的起义造反,往往是民众碰到灾害之年生活过不下去,并且要有领袖,但是同时还需要有另一套文化的配合,赋予造反行为的正当性,这就是所谓的“千年王国论”。利用某一种宗教的信念及组织网络,在许诺给人们美好愿景的同时,快速地跨区域组织大批群众参与集体行动,可见教化的力量是非常厉害的。因而我们要来分析行政成本、代理成本或者治理绩效、治理风险,都需要把这个维度考虑进去。我们在考虑大国的治理经验时是不应该遗漏掉文教的。
今天我们的国家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为什么越来越强调集权?按这个郡县制的历史来看,应该是国家会结束集权。可是今天国家这么强大了,权力为什么还要收到国家那里去,这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这里面是因为治理技术在变化,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它可以实行集权。以前可能是技术不匹配的时候,它用文教输出,那么今天技术跟上了,也就意味着它可以不需要文教的输出。我想,在中国崛起、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治理,有了成熟的治理技术,在国家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我们还需不需要文教?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的文教是什么?如果没有文教的输出,仅靠技术的治理手段(例如今天在城市中流行的、将技术手段用到极致的所谓“网格化管理”),我认为那是走不到“善治”、“良治”的地步的。这套文教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在助力一个大国的治理,同时也关系到推动人民主体性的形成。文教不仅仅是在治理技术不足情况下可以发挥弥补的作用,同时也应该在治理技术过度发达情况下发挥纠偏的功能。在今天,我们是否需要倡导文教以及需要怎么样的文教,这是值得人文学者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