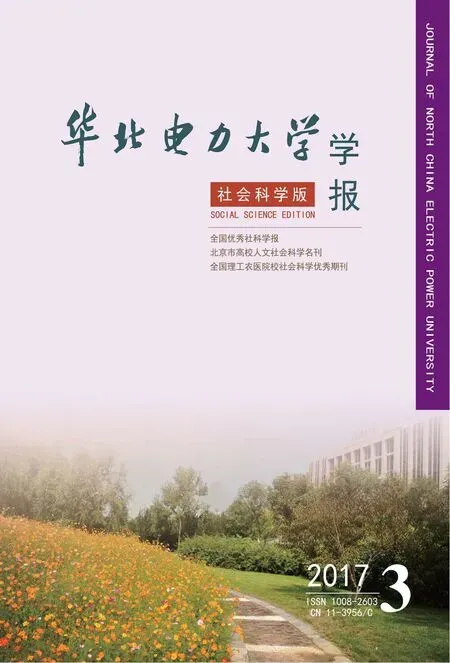消弭界限与回归真实
——以《自由的恶作剧者》为例
韩娟娟, 李雪梅
(1.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2.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433)
消弭界限与回归真实
——以《自由的恶作剧者》为例
韩娟娟1, 李雪梅2
(1.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2.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433)
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印第安作家杰拉德·维兹诺刻画了一群不循规蹈矩的恶作剧者家族群像,他们在部落保留地和都市之间穿梭。维兹诺认为,美国政府从立法上设立保留地的行为不仅限制了印第安人的物理行动,而且是封闭他们的精神桎梏;恶作剧者消弭了地理边界,打破了文化之界限,重构真实的民族身份,赢得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杰拉德·维兹诺; 边界; 身份构建; 生存空间
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1934-)是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最多产、风格最多样化的作家之一,曾获得美国土著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众多重要奖项,被同时代的著名印第安作家莫马迪称为“最好的讽刺家”[1]。作为印第安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维兹诺作品众多,艺术风格多样。他融合了欧裔美国文学传统和印第安口述文化,形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况且,他的文本大都具有开放式的结局和意义,因此引起了评论家广泛的关注和热议。相比较于其他作品,评论界对《自由的恶作剧者》并未多加关注。就国外而言,仅有克斯汀·斯密特(Kerstin Schmidt)探讨了维兹诺如何将后现代主义中的颠覆和解构概念应用于小说《自由的恶作剧者》中[2]。而国内尚无对《自由的恶作剧者》这部作品的引介和评论。综合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自由的恶作剧者》这部小说的关注度不够充分,对其的少量研究也多是将其与其他作品并置,对维兹诺写作的整体性进行分析。
一、 跨越地理边界
著名美国作家安扎尔朵(Cloria Anzaldúa)在《边界》(Borderlands/LaFrontera:TheNewMestiza)一书中指出:“边界的设立是不仅为了区分安全与非安全地带,同时也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3]。安扎尔朵也指出边界不仅是划分物理疆域的存在,同时可扩展为文化意义上的“软边界”,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的状态伴随着社会更迭与权力更替而变化。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边界作为一种场所,“不仅体现了时间上的联结”,而且还构建了不同的身份,此外,“作为文化混杂的动荡区域,开启了新的篇章”[4]。霍米巴巴认为居住在边陲地带的人被赋予了一种权力,甘之如饴地参与地区事务,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为不可控的杂糅性,却常常偏离正轨。换句话说,霍米巴巴强调了边界的动态性,和边界写作中跨界的可能性。
保留地时代的开启使得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形成了一条隐形的边界。美国政府通过建立保留地,不仅打破了部落的生活方式,部落里的印第安人被“圈禁”在严格的地域范围内,同时白人则堂而皇之地拿走了更多的土地。更有甚者,1887年联邦政府颁布的《道斯法案》规定印第安人必须通过交个人税才能“合法”使用原本属于保留地的土地,然而大部分印第安人无法承担高额的租金,这就使得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紧缩。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维兹诺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拉斯特·布朗(Luster Browne)取得保留地土地的过程:“1868年,身穿燕尾服的干瘪白人命名了这个保留地”[5]。维兹诺用“干瘪”和“燕尾服”两个词赋予了白人道貌岸然的特性,而且讽刺了白人给印第安人划定疆域的行为。而作为最后一位去领取土地的印第安人,拉斯特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歧视:“助理理直气壮地坐在椅子上,椅子前面是一条铺着军用毛毯的长凳,当他念出授权书上的名字时,蔑视地看着这个顽强的混血儿”,同时他将一片沼泽地分给了拉斯特,形容这片沼泽地“就像以总统之名赋予的贵族头衔一样无用”[5],暗示着拉斯特被政府赋予的部落男爵(The Baron of Patronia)的名分只是一种安抚手段,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保留地被划分给印第安人的同时,美国政府就希望印第安人蜗居在日益萎缩的地理空间中,保持远离主流社会的状况。
然而,面对美国政府划出保留地这个生活范围的不利境地,印第安人并没有蜷缩在“受害者”的身份中,而是主动地穿越保留地的地理界限,参与都市生活。正如罗斯·卡斯特洛诺所说:“穿越边界是一种充满力量的颠覆行为”[6]。保留地恶作剧者在穿越边界的同时,不仅打破了地域上的限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部世界的感官。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恶作剧者家族从来没有囿于保留地的地理空间,他们总是打破静止的生存状态,来往于保留地和城市,在旅行中构建自己的传奇故事。小说第二章中,维兹诺刻意将恶作剧者后裔乔伊娜·布朗(China Browne)与美国白人夫妇和中国老妇人三个种族代表人物的相遇设置在中国天津火车站。通过对车站候车室脏乱差环境的简短描述,维兹诺暗示了白人夫妇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不仅认为中国人会随时偷走他们的行李箱,而且一直追问乔伊娜名字的暗含意义,随意驱使其拿行李箱,似乎驱使印第安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之相反,乔伊娜主动“靠近中国老妇人,转过头来微笑”[5],对于陌生人释放出善意。虽然保守的中国老妇人对于乔伊娜的善意表示怀疑,叫喊着:“洋鬼子,洋鬼子”,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受到伤害,“乔伊娜会打破不信任和怀疑,带着部落恶作剧回到保留地”[5]。在随后进入车站的过程中,中国老妇人不慎跌入河流中,却无人注意,乔伊娜不计前嫌迅速帮助了老妇人,赢得了老妇人的尊重,“这两位女性沉默着看着彼此,一个微笑着,另外一位随后也笑了”[5],微笑代表着她们之间的隐形边界被跨越,隔膜被消融。同时,中国老妇人为了表示感谢,将自己的五角星帽子和中国草药制成的香包送给了身为印第安人的乔伊娜,物品的交换暗示着她们关系的重大转变。维兹诺笔下的印第安人作为旅行者和边界穿越者,消融边界进入别的空间,不仅在不同种族之间建立了交流的机会,而且通过交流成功地改变了他者口中的印第安人形象。
小说中的恶作剧者不仅通过走出保留地的方式打破了地域边界的限制,而且邀请保留地之外的人进入,反向消融界限,为保留地注入勃勃生机,形成从内至外的生命力。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恶作剧者金森·布朗从祖母那里学得了在荒野中寻找大蒜和野生人参的能力,意图与外界进行人参贸易以协助保留地的经济发展。面对恶作剧者试图走出经济困境的举动,白人却多加阻挠。白人邮差在听到中国人与保留地建立了商业联系的时候,甚至宣称:“已经够了,你们有了庇护所、国际机场,而现在共产党的威胁也来到了我们的背后”,“我不会递送他们的信件的”[5]。正如布雷瑟所说:“美国白人把印第安人禁锢在他们被赋予的角色中:为了保卫白人的权力地位,印第安人必须保持现状”[7]。白人政府将印第安人限制在保留地的行为可以看做是种族隔离,希望印第安人保持现状,而不是寻求发展,同时也可以说是希望其顺其自然湮灭在历史进程中。随着人参贸易的进行,金森受到了法庭的传讯,他们的经济贸易也被迫停止,法官宣称他们违反了野生植物保护法。金森布朗随即在法庭上证明了人参本来就是属于印第安人的财产,它们之前就一直被用于传统的印第安典仪中。并且“在口述故事中,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达成了协议,同意部落拥有渔猎和收集人参等自然植物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被法令所保护的”[5]。最终恶作剧者获得了交易人参种子的权利,因为法官错误地认为人参只有根须是有用的。印第安人和外界之间经济贸易的顺利进行,成功地打破了白人试图封锁保留地的目的,在交流中实现了保留地的发展。
二、 消弭文化界限
著名印第安文学批评家欧文斯在其著作《他者的命运》(OtherDestinies)一书中指出:“通过重新安置政策,美国政府试图淡化印第安部落的传统生活方式,并且鼓励同化”[9]。文化作为民族之根,是一个民族立足之本。白人政府秉承着印第安传统文化不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的态度,试图同化印第安人,促使其放弃传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为了打破这种思想,维兹诺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还原了印第安文化真实的状态。其所刻画的恶作剧者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传统印第安民族观念,而且保持着开放交流的想法,愿意消融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学习白人的科学技术。
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自由的恶作剧者》中,恶作剧家族十分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拉斯特口述恶作剧者传奇和创世故事,而且教他的孩子们在精神动荡时朝‘恐慌洞’(Panic Holes)里嚎叫以平缓心情”[5]。口述故事在印第安民族文化至关重要,在白人到达所谓的“新大陆”之前,印第安民族通过口述方式传承历史,在讲故事中民族的渊源得以延续。“恐慌洞”的存在也是印第安民族文化特有的部分,他们用其缓解精神上的压力,倾述自己的烦恼,并且还能通过它与人交流。这无疑成为他们拟构虚幻的自由空间——独立于真实世界,不受外部力量操控。乔伊娜·布朗与中国老妇人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后,向她讲述保留地的故事,但是由于语言上的限制,她们之间无法沟通。乔伊娜选择“向一个恐慌洞嚎叫,然后老妇人就理解了”[5]。虽然维兹诺将赋予“恐慌洞”童话般的神奇特质,却表达了他希望不同文化之间能通过这一媒介进行交流的意愿。除此之外,恶作剧者尊重自然,爱护动物的传统文化也在小说中得到了赞扬。金森在进行贸易时,没有为了眼前的短暂利益将人参拔地而起,而是尊重自然,选择拔掉人参的几根根须而已。同时,小说中恶作剧者还继承了印第安文化中人和动物平等相处的和谐自然观。恶作剧者多次充当解救动物的角色,并设立治愈动物的医院。印第安人认为他们能从自然和动物中汲取赖以生存的能量,继承传统文化是印第安民族持续发展和保持民族独特性的必经之路。
恶作剧者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愿意走出保留地学习白人先进的科学文化。如果要拯救单个文化免于灭亡,文化之间必须彼此发生联系[10]。纵观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封闭的文化必然是不长久的文化。只有打破文化隔离,相互借鉴,才能源远流长。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恶作剧者不仅尊重本土文化,而且愿意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为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注入活力。斯莱布特·布朗(Slyboots Browne)作为保留地里最聪明的恶作剧者,是一个精通鸟类知识的梦想者,“想象一个没有束缚的自由世界”[5]。他选择接受白人的教育,先后从私立学校和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并且学会了驾驶飞机。学业有成回到保留地后,斯莱布特将他所学的驾驶知识应用到现实中,试图在保留地建立一个飞机场,以建立保留地和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他还在城市里设立了动物医院救助受伤的鸟类,当记者问到他的目的时,他回答道:“因为城市里的白人也需要向我们学习,不仅是部落里的人,而且还有鸟类和城市里树下孤单的阴影”[5](126)。斯莱布特作为吸收了印第安传统文化和白人先进科学技术的典型代表,传达了维兹诺意在打破文化界限的意旨,暗示了只有互相交融才是未来文化的正确走向。
希克斯在《边界写作》(BorderWriting)一书中指出:“如果边界是一种机器,那么它就是混合了两种文化的走私者”[11](xxxi)。正如希克斯所说,边疆地带本身就是文化混合的场所。而维兹诺正是在这种混杂的文化状态中,意图打破主流文化或同化或消弭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目的,解构霸权主义的主流话语。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边界持续流动,恶作剧者不断移动,文化则始终在改变。维兹诺挑战了固定的印第安身份的概念——植根于过去,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塑造了集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于一身的恶作剧者,在植根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指出这才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 构建真实身份
边界产生自我身份,一方构建另一方导致了身份异同[10]。换句话说,边界两边身份的不同是由于一方不仅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构建了另一方的身份。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印第安人的身份正是由保留地外部的白人构建的。由于边界的限制,主流社会的大部分人对于印第安人的认知大都通过主流话语所限定的方式单方面呈现,因此带有固有的局限性。而维兹诺塑造的不循规蹈矩、游走于保留地和外部世界的恶作剧者,通过自己的亲身力行弱化白人口中“茹毛饮血的野兽”的印第安人形象,并且努力构建属于自己的真实身份。
主流话语从单方面塑造印第安人形象,因此带有极强的片面性。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玛丽·吉·海尔姆(Marie Gee Hailme)作为学校的老师,在最后的演讲中告解了自己的错误行为:“我在教室里教授给学生的部落价值观不仅错误百出,而且有失偏颇”[5]。实际上,玛丽是一个孤儿,在教会的寄宿学校长大,对真实的印第安人所知甚少,但是由于她是在主流社会中长大,白人自然而然对她的描述深信不疑。“我意识到我是在描述一个完全杜撰的部落”[5],玛丽虽然知道自己的错误言行,但是为了顺应主流社会的价值要求,她却将错就错地继续传播了虚假的印第安人形象。此外,书中的荷马(Homer)作为一名颇负盛名的作家,同样靠消费印第安人在社会上取得了自己的声望。由此可见,主流社会中关于印第安人的刻板形象大都不是对真实印第安人的客观描述,而是处于保留地边界之外的主流话语的虚假刻画。这种带有主观目的的恶意抹黑无疑使印第安人深受打击,造成了他们在走出保留地之后受到了不怀好意的揣测。
面对刻板形象的恶意塑造,印第安人通过亲力亲为的方式拟构真实的民族身份。乔伊娜在天津火车站通过自己对中国老妇人的帮助,改变了其之前大呼“洋鬼子”的惧怕心理,通过赠与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五角星帽子和香草表达了她对乔伊娜的感谢。金发碧眼的银行家为了调查混血儿事业家和保留地经济,采访了在保留地发展航天事业的斯莱布特。在采访过程中,他意识到了身为印第安人的斯莱布特的好学、勤奋和聪明,评价到:“你跟我们在书本上阅读到的保留地贫困潦倒的印第安人截然不同”[5]。
恶作剧者在来往于保留地和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成功塑造了真实的民族身份。鲁弗认为:“个体处于边界一方的社会与文化氛围拟构自我,以希望被社会大众认知的方式表现自己的身份,结果就造成了身份的碎片化”[12]。换句话说,从边界的一方出发构建身份只能构建部分的自我,而不能形成完整的身份。原因是处于边界一面的话语通常只能出于自身的角度塑造自己以及他者的身份,因而带有极强的主观性。但是,边界穿越者既是“自我”也是“他者”[11]。作为边界穿越者的恶作剧者出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重构自我,跨界同时意味着去疆域化,“自我”和“他者”的区别不复存在,个体是不同空间的“主体”,而主体意识的提高也是正确构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1] Momaday, N Scott. The Native Voice, in E. Elliott,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15.
[2] Schmidt, Kerstin. Subverting the Dominant Paradigm: Gerald Vizenor’s Trickster Discourse[J].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1995(7): 65.
[3] Anzaldúa, Cloria. Borderlands/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M].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2007: 3.
[4] Bhabha, H.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M]. 1994: 7.
[5] Vizenor, Gerald. The Trickster of Libert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6] Castronovo, Russ. Compromised Narratives along the Border: The Mason-Dixon Line, Resistance, and Hegemony.BorderTheory:TheLimitsofCulturalPolitic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7: 202.
[7] Blaeser, Kimberly.GeraldVizenor:WritingintheOralTradition[M].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6: 43.
[8] Keating, Ann Louise. Myth Smashers, Myth Makers: (Re)Visionary Techniques in the Works of Paula Gunn Allen, Gloria Anzaldua, and Audre Lorde. Critical Essays: Gay and Lesbian Writers of Color, 1993(26): 73.
[9] Owens, Louis. Other Destinies: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30.
[10] Johnson, David E., and Scott Michaelsen.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7:132.
[11] Hicks, D. Emily. Border Wri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Text[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12] Roover, Megan De. Internalizing Borderlands: the Performance of Borderlands Identity[D]. Guelph: The University of Guelph, 2012: 1.
(责任编辑:王 荻)
Breaking Borders and Getting Realities——TakingTheTricksterofLibertyas an Example
HAN Juan-juan1, LI Xue-mei2
(1.School of English,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InTheTrciksterofLiberty, Native American writer Gerald Vizenor describes a band of tricksters who do not follow the rules, and they shuttl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reservation and urban cities. Vizenor holds that American government′s behavior to legally set up reservation not only imposes restrictions on Native American′s physical activities, but also confines their spiritual freedom. The tricksters not only eliminate the geographical border, but also break the cultural border, and reconstruct authentic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contributes to broader survival space.
gerald vizenor; bord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survival space
2017-03-1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2016M601480);辽宁省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L16BWW005);2015大连外国语大学创新团队(2015CXTD02)。
韩娟娟,女,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李雪梅,女,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在站博士后。
I126
A
1008-2603(2017)03-01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