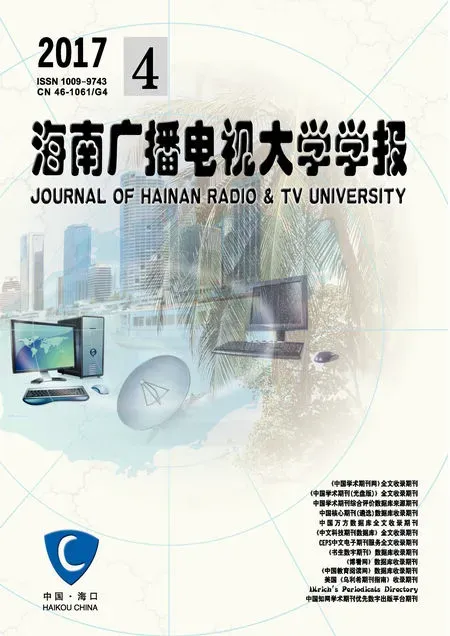审判中心视野下印证模式完善刍议
——结合刑事错案分析
陈晴燕,吴 斌
(1.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2.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海南 文昌 571300)
审判中心视野下印证模式完善刍议
——结合刑事错案分析
陈晴燕1,吴 斌2
(1.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2.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海南 文昌 571300)
厘清印证模式与印证标准关系,扩展印证模式研究范围。通过解析刑事错案如何生成,深层次探究印证模式失灵原因,侦查机关封闭的取证方式,公检法相互协作关系,单一证据来源渠道,未明确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关系,可见印证标准只是错案形成的外因,不正当的程序设计(印证模式)才是内因。最后提出,强化律师在侦查环节权利,削弱侦查权并实现淡化三机关相互配合关系,完善证据规则与庭审实质化的完善措施。
印证模式;刑事错案;侦查中心主义
一、质疑:印证模式为何频频失灵
2016年12月2日,最高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聂树斌案终于尘埃落定,案件判决结果下来后,人们好奇于事实裁判者是依据怎样的标准认定案件?证据之间逻辑关系能否支撑判决依据?这些疑问实质上系对我国证明模式的些许质疑,其为何未能防范错案的发生?解答上述问题,首先,应了解我国刑事证明体采用何种标准。早在2004年*此后针对我国证明模式的不同学说相继出现,主要有法定证据主义模式,新法定主义证明模式等。但是学术界基本上认同将证明模式评价为印证模式的观点,本文采用学术界主流观点。,龙宗智教授指出我国诉讼证明标准为印证标准,强调证据间相互支持、互相印证,也正是过于注重证据外部的客观性,致使司法证明的机械化。其次,面对不断曝光的冤假错案,立法界逐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2012年新修订《刑事诉讼法》新增“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证明标准,学界不少学者*蔡元培:《论印证与心证之融合——印证模式的漏洞及其弥补》,载《法律科学》,2016 年第3 期;张文娟:《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相互印证”与“自由心证”之辩——相互印证弊端之实证分析》,载《证据学论坛》2007年第2期;帅清华,郭小亮:《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提出裁判者审理案件时片面倚重证据证明力漠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主张在印证模式中加入心证来增强法官根据个人经验法则审理案件的能力。
大部分学者观点集中在如何保障法官正确采信证据,要求印证标准添加心证要素,虽增加主观要件的印证标准固然能缓解法官盲目采信非法证据问题,但是我国刑事制度素来重视实体真实,且司法机关和侦查机关作为国家公职机关,负有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职责,职能的同向性使得三机关之间互相配合程度大于互相制约程度,这些因素决定刑事错案不完全由于法官未正确采信证据产生,还与整个证据生成的刑事诉讼结构息息相关。学者们对印证模式的完善局限在审判阶段证明评价上,主要是将证明模式等同于证明标准,而证据证明模式系更为宏观的概念,从证明标准层面定义证明模式略显单薄,证明模式内涵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关证明主体的证明权利配置,以及证据方法和证明标准等规则设计的结构和样式*通过对证明模式的解读,印证证明模式包括印证证明标准、公检法三机关关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活动、法官审查认定证据证明力与证据能力的相关规定。王守安,韩成军:《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重塑》,《政法论丛》2016 年第5期,第84-91页。。基于此,印证模式的研究范围无须拘泥于审判环节,把研究重点延伸至证据的产生,才能够更加全面看待印证模式,为完善印证模式提供独特的视角。
二、再现:刑事错案在印证模式下如何生成
作为承担收集证据责任一方的侦查机关,素来以印证标准要求自己的侦查行为,其制作的证据链条通常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口供为中心;二是沿用“由证到供”办案方式。先证后供必须依赖于保障私权利的正当程序的有效建立,然缺乏控制的公权力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利益和实体公正。
(一)刑事证据生成程序缺乏规范
受到印证模式外部客观性影响,侦查人员在所有证据类型中更青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聂树斌案一审判决的做出是以聂树斌对奸杀康某的犯罪经过的供述为中心*参见:《聂树斌案一审判决书》。;有学者指出聂树斌的口供符合犯罪现场、受害者外部特征,增加审判的可信度,倘若未出现真凶王书金,原案一度难以取得可资翻案的条件*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3-11页。。
为做好防范刑讯逼供工作,“零口供”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范措施被写入相关法律法规,但是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远未匿影藏形,口供对刑事侦查工作依然起着举足轻重作用,据某学者调研显示,80%以上案件依靠被告人口供定案*李训虎:《口供治理与中国刑事司法裁判》,《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19-205页。。但是司法实务中超高认罪率与人性自我保护本能相悖,即犯罪嫌疑人首次审讯通常否认罪行,可以想见,这其中定会存在侦查人员为尽快获取供认笔录而不注重审讯方式的行为,采用肉刑或疲劳询问等变相肉刑方式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认其罪。此外,一份完整的询问笔录还需要搭配讯问人员的指供才能完成,而从未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自然不了解具体犯罪细节。“为了不挨打,不仅要按照审讯者的要求说,而且尽可能揣摩他们的意图。”从杜培武案的当事人关于案件的叙述可见一斑。且侦查机关制作的其他类型证据存在瑕疵,起到增强某些证据证明力的指认、辨认笔录制作程序不规范,辨认笔录只写结论未附有辨认、指认物品或图片,难以有效说明其合法来源,也未指定见证人。侦查人员干扰鉴定人鉴定活动,影响鉴定人中立性换取前后衔接上的证据链条。这种证据生成模式实际是侦查机关依职权进行的侦查活动,这保证证据符合审判标准,却缺乏合法性,侦查权凌驾于程序正当性之上,证明标准的适用也失去价值。
(二)侦查阶段犯罪律师辩护权的缺位
印证标准要求侦查主体提供大量证据保障证据确实、充分,可证据数量的多寡根本无法管控侦查权,反而是失去控制的公权力在侦破案件的需要下扭曲变形,人为制造或者选择符合印证标准的证据,杜培武案的告破是真凶亲口承认自己杀害被害人,杜才得以解脱杀人凶手的嫌疑,可见,杜供述中的骗枪杀人情节,明显是受到侦查机关逼供所做的伪证。
至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使律师辩护权完善化,但是侦辩二者工作性质的冲突性天然造成侦查权对律师辩护权的排斥,办案机关曲意解读限制律师会见权的“三类案件”适用范围;看守所不及时安排律师会见,或者要求律师提供“三证”之外附加其他会见手续*“三证”指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三类案件”指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给律师会见增加难度。同时辩护律师关于案件知情权和表达辩护意见权未受到应有重视,辩护律师难以发挥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作用。其次侦查环节辩护律师在对办案机关取证行为的监督集中在犯罪嫌疑人方面,办案人员获取其他类型证据的行为基本不受辩护律师的监督。我国取证形式采取单轨制模式,侦查机关兼顾案件侦破和证据收集,法庭上的证据几乎滥觞于侦查机关,当然辩护律师可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相关进展,但是侦查机关究竟能否据实相告还存有疑问,此外辩护人可在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行使阅卷权,不过,部分检察院非法限制律师采用复印、拍照方式获取案卷内容,更有甚者存在随意刁难律师现象,有的地方拒绝律师复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一定程度制约律师对案件的了解*韩旭:《〈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法学论坛》2015年第3期,第134-141页。。
(三)庭审流于形式
印证标准通过多个证据相互吻合的低概率事件强化证据链条的客观化外衣,减少证据结构上的逻辑漏洞以避免个别偶然发生的事件造成误判,然而欠缺主观色彩的印证标准事实上成为滋生书面审理的温床,且客观层面上公诉方倾向于书面证据中心主义,证人过低的出庭率影响着法庭质证的开展、法官据以断案的自由心证,遂法官不需要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靠审阅案卷材料确保证据链条相互印证即可做出判决书。部分法官甚至无故打断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发言,抑或无视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合理辩解,无端斥责被告人,庭审流于形式*孙长永,王彪:《论刑事庭审实质化的理念、制度和技术》,《现代法学》2017年第2期,第123-145页。。实践中,律师为被告人刑事辩护的效果不容乐观,同时辩护律师全国的平均辩护率在30% 低位波动*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65-85页。,表明仍然有大量被告人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法庭审判,无力为自己辩驳。此外法官通过庭前审阅案件卷宗资料虽可快速获悉案件情况,但法官提前形成案件的主观预判可能会动摇其中立的庭审定位,庭审中辩护律师的慷慨陈词难以改观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印象,书面审理顺应印证标准需求倾轧和代替以庭审为中心的审理方式。
三、反思:印证模式缘何走入误区
在“侦查中心主义”和印证主体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工作机制下,通过违法行为获取的证据未止步于审判阶段,有时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实施不法行为的证据,可见印证标准仅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印证模式的瘫痪不能仅考虑证明标准这一因素。
(一)侦查权缺乏制约机制规范
侦查机关的刑事执法行为需要正当程序加以规制,否则易出现侦查权力滥用问题,造成大量违法证据进入庭审,进而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结构。犹言如此,侦查环节违法取证行为仍屡见不鲜。侦查人员为确保案件破案率,出现围绕被告人口供“制造”符合要求的证据,其可能制作新的证据保证证据间印证结构的完整性,呈递给法庭的证据导向同一证明结论,但是单个证据的合法性有待商榷,那么事实结论也成“无根之水”,难以保证由它推导的案件事实属实。刑事错案中证据链条的达成可能深受侦查人员有意选择的证据影响,以牺牲被害人利益为代价,律师未在第一时刻矫正已经严重走形的证据链条,证据流入审判阶段后,只关注印证程度高低的审判者未必能承担起调整证据走向的重任,且印证标准中证据间相互印证的外部客观性很好掩盖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因此保障被告人防御司法权力侵犯的措施应当提前到侦查阶段,迫使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被告人的证据。
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与证据链条的证明有效性息息相关,律师在场权的增设正基于此而设置,然迄今为止,侦查权仍主导着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有效适用缺乏相应制度支撑,作为保障辩护权实施后盾的救济制度未建立起来,检察机关虽然肩负法律监督职能,但其与侦查机关利益的同向性,以及法律指导意见的监督形式难以监督侦查权,同时侦查阶段的程序规范不在审判机关管辖范围,审判者中立、超然的角色定位只限于审判阶段,尽管法律加大律师辩护权范围,侦查取证的封闭性仍未被辩护律师打破。庭审阶段“毒树”和“毒树之果”仰赖自身较强的证明价值被法官采信,立法未明确规定证据准入法庭资格,未建立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适用效果不显著,法庭庭审职能未充分发挥,导致不遵守规定的取证行为未受到追究。证据法设置的目的不仅为查清犯罪事实,制裁罪恶之徒,还应是私权利制约和控制司法人员滥用公权力的有力武器;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系早在证据成形时确立好,处于流水线末端的裁判者满足于确保证明逻辑结构严密,审判结论是否唯一性,漠视内心是否形成确信。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会有效对抗侦查权专断,律师可摆脱侦查人员对证据来源的垄断,自发搜寻相关证据,法官能够听取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两相比较控辩双方的证据,重点关注疑点较大的证据,让办案机关违法取得的证据无处遁形。
(二)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工作关系
仔细剖析侦查机关依据印证标准制作的证据链条,发现证据结构表面上符合证明标准,实际上证据间逻辑结构函矢相攻。譬如聂树斌的口供一边承认犯罪,一边貌似回忆不起自己作案经过,多处细节难以做出确定描述,作案时间分别有被车间主任批评后的第二天、当天等说法*参见:http://news.sina.com.cn/c/nd/2016-12-02/doc-ifxyiayr8829409.shtml.;办案人员一味追求主要证据环环相扣,忽视证据是否依据正当程序生成,些许证据存在由于非法取证形成的逻辑漏洞,发生无法融入闭合的印证结构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为确保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公检法三机关建立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关系,然而实践中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那些程序违法的证据未被法官排除掉,非法证据可以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司法审判的天平倾向于控方,控辩平等的司法构造成为空话,律师在庭审上再出色的表现也无法回转败局,审判阶段沦为侦查行为的最后确认环节,只是对侦查这一阶段工作的查缺补漏,相当于把承担查明案件的重担转移到侦查机关头上。侦查机关权力的强大反衬裁判权的式微,因此建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必须把侦查权放进制度的牢笼,强化三机关相互制约、监督关系,不仅为进入审理环节的证据链条正本清源,亦使法官免受法律之外因素的干扰,真正做到公正审判。
侦查机关在追求实体真实的证明理论下收集证据,漠视程序合法性,受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紧闭”外界监督大门,阻碍辩护律师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同时法院和侦检两方通力协作的工作关系,以及来源单一的证据通力造成庭审审理方式的萎缩,证据能力不足的证据继续发挥事实证明的效用,作用于判决结论的走向。我国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制度,公权力机关代表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国民安全,遂刑事诉讼制度注重规定司法机关的刑罚权,侦查机关自主的取证方式,公检法分工合作、相互协作的关系,即无论适用哪种证明标准,法官中立的地位都会发生偏移。
(三)未厘清证明力与证据能力的关系
聂树斌案中其口供多处关键事实有数种说法,不能确定其供述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应认定聂树斌的供述不具有证据能力而丧失证明案件事实的资格,但是在聂树斌案最终的判决书中法官仅认定被告人供述证明力较低,这反映出印证标准自身存在轻证据能力审查,重证据间关联性的弊端。
首先漠视证据能力审查 我国奉行职权主义,事实裁判者对程序的控制和证据的取舍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法律为保障法官查明案件的权威,较少规定证据能力规则,转而采用印证模式限制证据证明力。但是法官采信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证明力与证据能力,割裂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以证明力认定代替证据能力的审查无法保障证据对待证据事实的可信度,侦查机关的口供情结源于口供证明力较强,相比口供证明价值,获取口供的审讯工作的合法性显得无关紧要。且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依靠印证标准采信缺失证据能力的证据可能造成审查认定的事实与案件事实大相径庭。
其次,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程度越大,则该证据证明力越大以印证程度弥补证据证明力自身的缺陷,片面审查证据间外部逻辑紧密程度,易使证据实质证明力的审查成为裁判者审判案件的真空地带,增加错案发生的风险。证明标准的理论过于狭隘,证明力的判断不限定在证据关联性,还包括证据可靠性、真实性,证据间印证程度的高低不与单个证据证明力相挂钩,司法改革基于证明标准客观性较强问题,引入主观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然而职权式侦查模式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合作关系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两大痼疾,经改革后的“证明标准”也难逃这两大问题的影响而收效甚微。
四、重塑:印证证明模式的完善路径
印证模式的失灵需规范侦查取证程序,加强律师辩护权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作用,加强三机关相互制约关系,借助“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风潮完成庭审实质化,保障事实裁判者独立审判权,实现庭审实质化内部结构和保障以审判为中心的外部环境相互配合的局面。
(一)加大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权力范围
侦查虽肩负探明事实真相的重任,但其属于行政行为,表明侦查机关与被告方的辩护人地位不对等性。辩护人参与侦查的首要职能是监督权,其次才是调查取证权,这决定律师基本不能单独提供证据,因此可在区分控方证据与辩方证据基础上,明确辩方证据在事实认定中处于基础信息地位。立法上应当充分保障辩方举证权,鼓励辩方积极举证*左为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2016 年第1期,第162-176页。。解决取证主体单一造成证据片面化倾向问题,让进入法官视野的证据之果客观全面,侦查一方有失偏颇的证据无法控制案件审判。并且多部法律要求建立律师值班制度,及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建议》。。
(二)强化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关系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依职权行为应当受到积极有效监督,以帮助实现审判机关独立,审判者独立,做到公正司法和实体正义的统一,兼顾严格惩处罪犯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价值。2017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突出强化三机关相互监督的职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其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并制定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约束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进一步完善庭前会议对非法证据的处理机制,通过审前阶段对非法证据核查工作,有助于弱化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工作关系。
(三)实现庭审实质化
1.确立合理的证明力规则
法律预先规定好的证明力规则难于适应客观需要,还可能与诉讼中寻求真实的目标南辕北辙,即使每个法官的证明力判断不尽相同,也不必担心这种主观判断千差万别,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差别不大,生活经历积累下来的经验法则和逻辑也相似。在《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审判责任范围”依然是“其他故意违背……证据规则和法律明确规定违法审判的。”显示证明力是法官事实判断所要考虑因素,“排除合理怀疑”在中国适用的基本环境仍不尽人意。不管审判结果是否符合事实真相,只要违背证明力规则,法官必须承担司法责任。对司法责任的追究要有限度,在“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司法运行机制实施的条件下司法审判的错误率可能增加,应当减低追责标准,将追责范围限定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判断证明力大小的权力须回归法官多年生活、工作自发形成的经验规则中,不限于立法规定的字面意思范围,制定适合不同类型案件的弹性法则规定。
2.完善证据规则
一是强化直接言词制度。鉴于立法未取消证人不出庭情况下书面证言的效力,且在证人出庭问题上法官超强的职权裁断,使得书面审理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善。立法应当强化直接言词原则,明确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需以口头形式向法官呈现出来,否则不予采纳证据。二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冻、饿、晒、烤等恶劣手段”“体罚虐待”等法律术语的认定标准,同时赋予法官证据排除方面更多的裁量权,便于法官排除制约审判公正的非法证据,并适当扩大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范围。
[1] 佀化强.事实认定“难题”与法官独立审判责任落实[J]中国法学,2015(6):282-300.
[2] 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J]中外法学,2015(4):846-860.
DiscussiononthePerfectionofConfirmationModelintheViewofJudicialCenter——Combined with Criminal Misjudged Case Analysis
CHEN Qing-yan1,WU Bin2
(1.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2. Wenchang Municipal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Hainan Province,Wenchang,571300,China)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ification model and the verification standard,and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verification model. By generating and analyzing the Criminal Misjudged Case,to explore the deep-seated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the investigation organ verification mode,closed forensics methods,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cooperation,evidence sources,fuzzy evidence and proof,proof standard for misjudged cases just visible form,the program design is the internal cause of unfair.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 of trial procedure,namely to strengthen the lawyer's right in the investigation stage,weaken the power of investigation and implement three desalination authorities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improve the rules of evidence and the essence of the trial.
confirmation model; Criminal Misjudged Case; investigation centralism
D925.2
A
1009-9743(2017)04-0110-06
2017-06-20
1.陈晴燕,女,汉族,海南三亚人。海南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2.吴斌,男,汉族,河南舞阳人。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7.04.020
张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