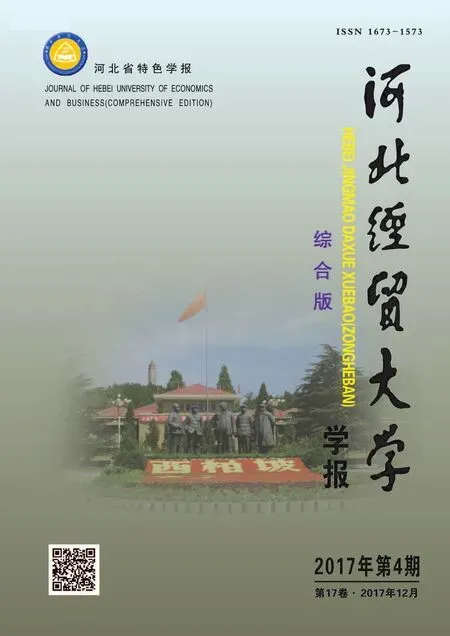“违约不担责”的误读与澄清
——某地行政机关与法院会商资讯评析
辜 岸,杨志敏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违约不担责”的误读与澄清
——某地行政机关与法院会商资讯评析
辜 岸,杨志敏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行政部门与法院会商可能发生纠纷的裁判,虽然对政府工作会有所帮助,对于纠纷化解有一定作用,但其蕴藏的法律问题更加突出。每个案件都具有特殊性,事先就某些事项预设法律适用方案本身存在极大的风险;行政部门与法院会商有违国家机构的权限划分,妨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因而害及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之公信力,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多有抵牾。
情势变更;法律适用;权力边界;司法权威;房地产新政;违约不担责;楼市调控
媒体2017年4月27日从北京市住建委官方微信公众号获悉,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三部门召开会议,研究“3·17新政”实施后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履约纠纷裁判等有关问题,明确对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按揭贷款方式付款,且买受人能够举证确因调控政策出台导致首付款比例提高、无法支付首付款项,因而无履约能力的,以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返还收受的购房款或者定金的,法院可以支持。①这则报道透露的信息显示,第一,北京“3·17新政”后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因调控政策出台导致无履约能力的,可以解除合同,用媒体报道的语言表述,即买方可以“违约不担责”;第二,这个处理方案是由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三部门会商后确定的,确乎具有一定权威性。毋庸置疑,此次会商对于解决因北京市住建委等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后产生的房屋买卖纠纷有一定作用。②但是,对于这次会商的作用和意义的解读,笔者认为并不是用“违约不担责”式“人文关怀”可以概括的。就法理而言,下列问题似乎应该高度重视:因房地产市场“新政”缔约后无力履约解除合同的依据何在?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许还在于,行政部门是否可以与法院会商确定对某类案件的裁判方式?笔者不揣简陋,拟对此进行简要分析与澄清,并以此就教方家。
一、房地产“新政”是否构成解约事由
(一)合同解除事由之情势变更的中国语境
作为合同效力终止事由之一的合同解除,通常包括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1]合同的法定解除须有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约事由为前提,当事人方可行使解除权。《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若干法定解约事由,但对学界一直呼吁应作为合同变更或解除事由的情势变更原则,《合同法》并未规定。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该规定被普遍解读为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司法确认,可作为合同法定解除的依据之一。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之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影响,在该解释出台之前,人们就已经关注和探讨。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调控政策属于情势变更而非不可抗力,因商品房调控政策导致合同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无法履行的,可以解除合同。[2]该司法解释出台之后,法院基本认可调控政策为“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客观上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事由,而认同合同解除之效果。④但是,近年来屡屡实施的房地产“新政”措施是否真的如论者所言构成合同解除事由之情势变更?似乎不无考察的必要。如果构成情势变更,当事人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当无疑义,否则,解除合同则缺乏依据。
对情事变更原则的构成,大陆法系通说认为须符合下列条件:即须有作为缔约基础的环境的客观的异常变化;异常变化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变化具有不可预见性;变化的结果使维持原合同的效力显失公平。[3]⑤承前述司法解释的表述,笔者认为,在我国现实语境中,情势变更须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且因此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后果。
(二)房地产“新政”与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
如果以此为据进行考察,我国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导致的当事人之间情势变化,是否符合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笔者认为应当审慎斟酌。
1.楼市调控并不一定导致“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后果。目前各地所采取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无非是限购、限贷、提高首付比例以及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税收政策等。如果银行依据调控政策而提高购房首付比例或者拒绝贷款等,虽然当事人可以有多种方式筹款和解决资金缺口,但的确可能比向银行申请贷款增添更多困难,就此而言,出现缔约基础的“重大变化”是有道理的。⑥但是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否达到“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严重程度,则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据笔者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来看,不少购房者并非必须向银行高额贷款方能解决购房资金,只不过向银行贷款可能更有利于资产的优化组合,并以此规避货币贬值导致的财产价值损失,换言之,不少人选择贷款购房,仅仅只是出于商业利益或家庭资产优化配置的考虑而已。
其次,即使对于确因资金短缺而贷款的购房人而言,因银行限贷或拒贷并非一定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融资,或融资导致的负担达到对当事人“明显不公”的程度。从各地调控措施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政策走向,即对第一套住房的首付比例并未显著提高,因此,调控对于那些所谓真正“刚需”的购房者影响并不大。北京市政府“3·17”调控《通知》所针对的主要是第二套以上房屋的购房者,⑦而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住房价格之高虽远超人们先前的预期,但已然成为现实,而在如此高房价情况下还能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者显然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即使现金实力不济,卖掉原来的房屋支付首付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或许会有这样的看法,即面对北京等地高企的房价,哪怕提高5%~10%的首付比例,对购房人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面对已经高企的房价,早有筹划的购房人不可能不知道购房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即使不提高比例,原有的“首付”也不是小数目,并且购房后的“月供”不低。与即将开始的不可忽视的月供相比,提高幅度并不十分明显的首付比例,又能对购房人带来多么大不了的负担呢?即使增加部分负担,亦断不至于导致“明显不公”或履行不能。
再次,至于那些动辄购买若干套房屋“囤房”和“炒房”者已不是一般意义的购房者,他们不但有较为殷实的资产,而且对楼市的风吹草动有着比普通购房者更为敏感的嗅觉,他们通常会对此早有应对预案。何况这类商品房“炒作”行为恰是政府倾力整肃的对象,无需对其施以“援手”。基于此,笔者认为,政府调控给购房者带来的“增量”负担并非到了对当事人“明显不公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程度。
2.楼市调控并非完全“不可预见”。即便楼市“新政”导致“重大变化”,可能给一方当事人造成一定的损失或加重其负担,在结果上与订约初衷不尽一致,但是,政府采取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是否为毫无征兆的突然之举,而使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呢?这可能是认识“新政”措施是否构成情势变更更为关键的因素。
如果我们对中国楼市有大致了解,对此应该有明确答案。回顾我国房地产市场二十来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房地产市场已初具雏形,但产生的纠结与问题似乎不应忽视,尤其是不断上涨的房价让不少人始料不及。曾几何时,从中央到地方出台强力调控政策,但是,调控效果并不明显。本届中央政府任初曾希望通过加快保障房建设以缓解市场的紧张状况。但是,实际情况似乎并不乐观,⑧在第一届任期尚未届满之时“调控模式”已在各地开启。2016年3月25日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所谓“沪九条”)即开始从严执行限购政策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2016年7月以后,部分城市房价开始升温,甚或渐次“发烧”,多地开始集中推地平抑房价,媒体推测或有可能重启限购。[4]2016年8月9日住建部在其官网发布的贯彻《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之实施方案指出,完善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坚持分类调控,因城施策。“分类调控”仍然是调控,换言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尽管调控收效欠佳,但在市场开始“发烧”而无其他措施可以应对的情况下,仍不得不调控。就在住建部发文的同时,针对中国二线城市房价“高烧”不止的情况,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各地的楼市调控大潮即将来临。[5]2016年国庆期间,全国21个城市密集出台调控措施,在完善差别化信贷政策的同时,再次祭出了限购的“撒手锏”。尽管对此不无质疑之声,[6]但是多地的调控措施仍然不期而至,不仅限购限贷,而且限售,调控措施可谓空前严厉。换言之,在中央政府提出的“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行政色彩浓烈的限制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楼市困局,但仍旧“无奈”地一再为之。迄今为止全国已有数十个城市实行了包括限购、提高首付比例、限贷等调控措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不难发现,每一次的政府调控都非空穴来风。在政府相关意图明显,甚至三令五申,媒体报道汹涌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的购房者,不可能对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控措施无动于衷,甚或一无所知。
综上所述,购房者抑或售房者,对于订立合同时已经或即将采取的调控措施不是“不可预见”,大多是不愿预见,甚或不做预见。尤其是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楼市定位已然明确并已体现出对“过快增长”的房价严重关注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各种可供利用的政策工具抑制房地产泡沫,防止出现市场大起大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所谓“不可预见”者,如果说其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漠不关心可能过于尖刻,但心存侥幸则是非常可能的。由此之故,笔者认为,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并非“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相反,恰是我国政府在市场活跃之时屡试不爽的“常规之举”,预见其发生并非不能。
(三)房地产“新政”难以确定构成解约事由
承前文之分析进路,笔者认为,楼市“新政”能否构成解约事由非确定之论,即使发生纠纷,不同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也有特殊性,因此,对因楼市调控导致的履约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纷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把握,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因限购导致购房者丧失购房资格,⑨并因此“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学者言之因调控导致“合同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无法履行”者,解除合同似无不可。但此仅为履行不能之障碍解除合同而已,并不因此免除其他合同责任。倘仅因银行提高首付比例而使购房者负担增加即可解除合同,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当然,这可能会面临如下诘问,即会商意见并非支持对所有“新政”后的购房合同予以解除,而仅限于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按揭贷款方式付款,且买受人能够举证确因调控政策出台导致首付款比例提高、无法支付首付款项,因而无履约能力的,方可以情势变更为由解除合同,会商意见有何不妥?对此诘问,笔者想指出的是,基于前文的分析,不但将“新政”措施之影响确定的界定为重大情势变更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即便客观情况的确发生“变更”亦非当事人完全不可预见,因此,会商意见的适用余地极为有限。而且,即便因限购导致购房者丧失购房资格而在客观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者可以解除合同,既然非因“不可预见”的事由所致,作为购房者很难说全无过错,如果要求出卖人返还收受的购房款或者定金法院予以支持,而全然不考虑对方当事人可能受到的损失,其合理性也值得怀疑。由此之故,房地产“新政”难谓确定的构成解约事由。
还需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号)要求,“对于上述解释条文,⑩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专门下发“通知”固然是基于彼时经济状况的不乐观而致纠纷增加的情况有关,但是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是没有道理的。换言之,不能因价格变化,或政策调整动辄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调处而害及合同的严肃性。由此,我们认为,如果前述相关部门会商确定因楼市“新政”影响商品住房交易,法院可依据双方举证即判定解除合同之报道属实,那么,此举并不见得妥当。如果仅提高首付比例就以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不仅可能给投机者更多的可乘之机,动摇合同“严守”的基本规则,而且鉴于我国目前信用水平不堪之现状,以一些人所谓“中国式聪明”,⑪更有可能让社会公众规则意识的养成遥遥无期。所以,对于因房地产市场“新政”而提高首付比例即将其确定为情势变更,并以此为由解除合同,要么是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误解,要么是放宽了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都不见得妥当。至于媒体所谓“违约不担责”之说则纯属无稽之谈。即便如报道所言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合同既已解除,何来违约,遑论违约责任?如果法院裁判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有效而予以维持,当事人即应按约履行,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者均须承担违约责任,更无“违约不担责”之可能。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媒体从业者应当提高法律修养,不要误导读者或观众,更不能为了增加发行量或提高收视率而以“标题党”手法哗众取宠。
二、法院与行政部门“会商”纠纷裁判是否恰当
如果仅就调控措施是否属于情势变更而变更或解除合同存在争议,在笔者看来只不过是法律适用中通常存在的“技术性”问题,法院完全能够独立判断并依法裁判。但是,行政机关与法院会商确定对某类纠纷的裁判,或者协调案件的处理,则可能涉及政府与法院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力的边界,以及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约束和良好运行的重大问题。兹事体大,且与此类似情形者早有见诸有关地方的官方文件,⑫倘若非依法理深入辨析,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认识误区,甚或可能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这个认识和做法。长此以往,必将贻害无穷。基于此,笔者以为对其略作辨识决非无谓之举。
(一)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其应依法“各行其是”
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作了明确界定。依照宪法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作为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解决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因此,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与肩负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无论法律定位还是职责分工均不相同,应各司其职共同维护国家权力体系的良好运行。换言之,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各行其是”是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法院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仅是我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特色,而且符合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分离这一现代国家的普遍做法,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基本制度保障。试想,如果法院与政府就相关事宜协调处理意见,而不是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进行裁判,那么,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如果产生偏差,尤其是在行政行为中产生纷争,何以得到监督与纠正?相对人的权益又何以能够得到保障?因此,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裁判各类案件不仅是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而且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基本保障,是实现案件公正裁判和维护社会正义的基本制度安排,人民法院依法履职进行案件审判不但无需与行政机关协调,行政机关也无权干预。我们观察发现,在党和国家强调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司法的情况显然已有所好转,但是,通过会商和协调案件处理之类做法,在本质上与直接干预异曲同工,将可能害及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权之行使。总之,政府与法院协调处理案件背离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分工的宪法原则。
(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实现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的基本要求
不能否认,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的利益纠葛与冲突难以避免,更有甚者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因此,我们不仅要及时化解纠纷,维护社会和谐,而且政府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出发依法采取必要的“维稳”措施是其职责所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有些地方政府片面理解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动辄以法院工作应服务大局为由要求法院服务甚或服从于政府的具体工作,这就非常值得商榷了。
大局者,事物之整体或其发展之基本规律也。准确把握大局,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自觉服务大局更是各国家机关工作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或可曰,依法治国既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保障,同时也是“中国梦”本身应有之义。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通过严格、公正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为此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法律的严格执行,既需要行政机关严格公正的执行法律,更需要人民法院作为调处纠纷的最后防线予以保障,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经验和世界各国法律实践的不变教条。实际上,只有将行政与司法适当分离,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才能真正做到对行政权力恣意的防范,支持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活动,以及为不服行政执法机关行政行为的当事人提供可能的公开的司法救济的渠道。反之,则可能使行政措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判断成为泡影,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规制,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倘如此,行政权力将成为无所约束的“下山猛虎”。因此,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严格司法,是实现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要求法院工作与政府行为协调,尤其是法院如何对个案进行裁判,更是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与政府行政并无直接关联。
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法院与政府机关的“不协调”多有发生。在英美国家,在涉及政府的案件中,有时法官的裁决可能导致行政机关的不满,甚至被政府认为是与其“对着干”,虽然法官们在意识到自己的裁决所引发的法官与政府的紧张关系时,通常会尽量考虑如何在严格依法裁判案件的同时,处理好自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些尽职的法官却总是认为法治、程序正义是不可忽视的。法院不是要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而是要审查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7]所以,在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今天,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裁判争议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司法原则。否则,法院与政府的不同定位以及其职能划分将变得毫无意义。法院独立地位之不存,独立行使审判权将无从谈起,更谈不上以司法权力有效制约行政权力。倘若此,那些制约行政权力的“笼子”将形同虚设,其后果之严重可以想象。因此,我们坚定地认为,法院相对于政府而言的超然地位,是保证法律良好运行,从根本上服务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的必要保障,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三)坚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重塑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因为诸如财政预算与经费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形成了司法机关对地方党政的依赖,[8]并由此使得地方权力构架中行政权力的“任性”,甚至一些基层政府甚至将法院作为贯彻政府意图和解决棘手问题的工具。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从长远和全局来看,不但不利于政府工作的推进,而且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与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极不协调。为纠正此风,最高人民法院下文规范并明确要求“人民法庭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不得超越审判职权参与行政执法活动、地方经济事务和其他与审判无关的事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曾经指出,有些地方乡镇的领导把人民法庭看作其下属的一个部门,擅自指挥人民法庭工作,任意借用人民法庭工作人员,借用政法部门的强制手段来推行乡镇的行政工作,这与国家机关活动的法治原则是不相符的,与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背道而驰的。把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捏在一起,去从事不符合司法机关性质的一些活动是违法的。[9]以各方关注的房屋拆迁工作为例,因拆迁涉及多方利益而具有一定难度,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借助法院之力强制推进拆迁工作,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影响了法院的形象。对此情形,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曾在全国高级法院会议上强调“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参与拆迁”。[10]问题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有的地方政府无视法院的独立地位,对法院工作指手画脚无疑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各国的法治实践早已证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保有权威,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
201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11]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不该也不能成为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更不能沦为行政机构的下属部门,而应具有高度的权威,享有解决一切法律争议的终局权力,其裁判结果应该得到普遍尊重和遵从。
由此以观,法院的独立审判地位不应仅仅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必须得到切实的落实和强力保障。只有这样,法院的权威才可能得以重塑。各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应该也不允许以各种借口干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有当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力得到了尊重和有效行使,司法的权威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此时的司法机关才能真正成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无论是行政直接干预法院司法甚或裹挟司法的问题,⑬还是以维护社会稳定或协调处理争议为名,政府与法院就纠纷解决联合下文⑭而“隐形”或间接干预司法都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应该坚决予以纠正。
(四)对“会商”现象的简要评析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容和制度安排。⑮我们以此反观某市住建委、人民法院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三部门召开会议,研究“新政”实施后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履约纠纷裁定等有关问题,表面上看政府部门并未对司法机关下达“指示”,更没有直接干预司法机关的工作,但是,三部门会议就争议处理所形成的一致意见显然会对法院审判产生影响,甚至在个案裁判时,法官极有可能按预先会商的意见进行处理并做出裁判。如此这般,审判仅仅就是一个查明事实的问题,而且在查明事实问题时,先前的会商结果也极有可能会对法官产生不当影响。法院的审判极有可能在事实上沦为形式和“过场”。这样的审判与法院应坚持的审判规则明显不符,其实际效果将因此而大打折扣。由此之故,我们可以符合逻辑地推断,如果司法机关按照与行政机关会商的既定方案处理纠纷,那么,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亦将因此而被极大地消弭。或可一言以蔽之曰,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应该在执政为民的理念指导下审视自己的行政和服务行为是否符合法治的要求,而不是与法院会商裁判事宜;作为享有国家赋予的审判权的法院也应该有高度的“独立审判”的角色意识,抵制和拒绝在具体法律事务中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当然,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我们强调政府依法行政,法院独立审判,并非一概要求政府与法院的绝对“绝缘”。如果在行政过程中,政府部门本身无法确定某个或某类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向法院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咨询,那么,法院就法律规范本身可能的含义进行必要的释疑并无不可。但是,这类咨询性释疑需明确界限,在笔者看来应仅限于法律文本本身的规制意义,而不能就具体纠纷事宜或政府即将进行的行政行为涉及纷争的裁判规则或处置方案进行解答。而且,为了尽可能避免“瓜田李下”嫌疑,政府与法院即便因咨询性问题的接触也应尽量避免,因为这项工作完全可以由政府法律顾问予以解决。
三、结语
笔者上文的分析,很容易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是否过分的强调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而忽略了实际司法工作的困难?的确,司法审判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并不完善的制度体系下的司法裁判,将现实的纠纷处理与政府当前工作协调,可能更有利于法院开展工作。笔者也深信,尽可能使各方利益得到兼顾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按照“会商”精神处理案件,会不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偏差?而且这样的“会商”会不会害及法院独立审判?这正是笔者所关注和担心的事情。如果因调控而导致履约不能应该依法解除合同,那是法院本身应该而且可以做出的裁判,何需“会商”?既然无需“会商”,那又何必“会商”?就此而言,笔者认为,与其抽象地谈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在具体工作中排除可能各种有害独立审判权行使的具体事项,即便是善意但的确可能害及独立审判的具体事项。如果政府与法院各守其准则,严格依法办事,这不就体现了“具体法治”吗?法治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应该体现为一套严密的制度体系和运行良好的机制,并落实在具体纠纷调处之中。只有“具体法治”得到实现,才可能真正体现国家全面的法治,依法治国才是现实的,法治国家的建设方可期待。
就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而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实现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基于此,笔者虽在本文分析政府与法院的会商问题,但并不愿意仅仅就事论事,停留于此会商而大谈会商本身有多么的不堪。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指出,现代科学兴起的根本前提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即每个细微复杂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确切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体现出一般原则”。[12]笔者正是想通过对本次“会商”这一看似细小之事,揭示司法机关独立办案以及中国法治宏大主题的一般原则,这应该成为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
注释:
①新浪财经转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报道:《北京住建委等三部门明确:受“3·17新政”影响交易违约不担责》,载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7-04-28/doc-ifyetxec6850528.shtml,2017年 4月 28日。
②“通知”第二条明确“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无住房且无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执行现行首套房政策,即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5%,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40%(自住型商品住房、两限房等政策性住房除外)。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已拥有1套住房,以及在本市无住房但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中新经纬以《北京“3·17”新政后,买卖合同纠纷终于有办法解决了》为题报道,该报道载http://jhcb.net/anhuinews/c824b0f6c19e 67afb816bda9e0cf9a22aba42d62f508e7.html,2017年4月28日。
③对于合同法为何不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学界有不同的解读。《合同法》颁行后,学者认为,即使该原则在法律上未作规定,但适用该原则仍为可行,其路径选择可考虑在处理涉外合同时可采国际惯例,而在处理国内合同关系有具体规定时适用规定,在无具体规定时,可以依照公平原则处理。参见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0页。
④这类判决颇多,尤其在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房屋买卖纠纷适用法律时基本持此观点。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13046号判决书、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4民初11227号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2201号判决书,等。
⑤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条件虽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表述不尽一致,但其精神大体一致。基于此,笔者不对此条件一一分析,仅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表述作分析。
⑥对此,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当事人因银行拒贷或提高贷款比例导致当事人履约困难,但此困难并非“不能克服”,因而,此情势的变化不属于不可抗力。
⑦2016年北京“9·30新政”已调高购房首付: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5%,对拥有1套住房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无论有无贷款记录,首付款比例均不低于5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70%。与此相比较,“3·17新政”并未提高首套房的首付比例。
⑧2014年12月5日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5年经济工作,没有专门讨论和研究房地产问题;2015年12月14日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但是,市场似乎并没有回应中央的预期。2016年7月以来,多地住房市场又回暖上涨迎来本轮周期的高点,全年成交规模创历史新高,城市分化态势延续,1—11月百城住宅价格累计上涨17.83%。国庆节前后,各地政府密集出台调控政策,直至四季度市场走势才渐趋平稳。关于2016年的房地产形势,参见会计网资讯:《中国指数研究院:2016年房价走势总结与2017房价趋势预测》,载 http://www.kuaiji.com/weixin/3350272,2017年1月6日。
⑨尽管对地方政府限购政策的合法性,学者不无质疑。参见陈承堂:《宏观调控的合法性研究——以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为视角》,载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史以贤:《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法治思考——以限购令法律问题为视角》,载刘云生主编:《中国不动产法》(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对此暂不置评。
⑩此处所指“解释条文”,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26条。
⑪媒体所谓“中国式聪明”是指那些精明圆滑之人利用他人善良或某些规则之漏洞占尽便利者,或不守规则获利者。参见搜狐财经文章:《中国式聪明》,http://www.sohu.com/a/122554836_115362。笔者对此称谓并不赞同,而且这样行事风格的人可能不仅存在于中国或仅是中国人,在一个诚信缺失或规则意识淡泊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存在。此处只是借用这一说法以表达当下我国总体来说信用环境不佳和人们的规则意识不强的状况。
⑫早些时候就有地方政府和法院为了化解争议而联合发文处理相关案件和事件的情形。如莆政综[2007]150号文《莆田市人民政府、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协调处理机制的意见》,即要求辖区内的各级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信息共享和重大事项的协调。这虽与本文所说的会商处理案件不尽相同,但其实质无二致。对此已有作者严正指出,此举不仅违背我国宪法之制度设计,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且最终害及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参见李忠义:《试论行政审判中的司法独立——兼评地方政府与法院就解决行政争议联合下文现象》,载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⑬在基层司法实务中政府干预法院裁判的事件亦不鲜见,地方行政部门以公函形式要求法院按政府意图裁判,甚至“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者亦偶有所见。参见潘洪其:《政府“警告”法院 法治为之蒙羞》,载于《公民与法治》2010年第8期(下)。
⑭如上文提及的莆政综[2007]150号《莆田市人民政府、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协调处理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信息共享和重大事项的协调。关于该文件的具体落实情况可参见《福建莆田市人民政府2009年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情况》,载国务院法制办官网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dfxx/dffzxx/fj/201002/20100200194809.shtml。《莆田市人民政府、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司法建议办理工作的规定》则对司法建议的范围和程序作了规定,而且要求各县(区)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市直有关单位遵照执行。参见《莆田市人民政府、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司法建议办理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⑮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笔者看来本应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尤其是各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干部更应对此有高度的自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学者认为,党“支持司法”是党在处理与司法权关系时的最新表述,用“支持”而不用“领导”,意在落实宪法中保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原则。参见徐显明在第十二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上的演讲。该演讲载于“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众平台,亦可查询相 关 网 站 , 如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822/13/45568883_681212679.shtml。
[1]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628.
[2]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46.
[3]李永军.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61.
[4]朱开云.多城集中推地平抑楼市 厦门等二线城市或重启限购[N].北京青年报,2016-08-27.
[5]夏宾.中国住建部谈楼市调控:坚持分类因城施策[EB/OL].http://www.chinanews.com/house/2016/09-06/7996214.shtml,2016-09-06.
[6]李赓南.中国楼市怎一个限字了得?[EB/OL].http://fi nance.sina.com.cn/zl/bank/2016-10-07/zl-ifxwrhpm2491207.shtml?cre=sinapc&mod=g&loc=31&r=15&doct=0&rfunc=52&tj=none,2016-10-07.
[7]葛峰.英国法院在敏感案件中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N].南方周末,2012-06-03.
[8]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研究[J].中国法学,2014(2).
[9]佚名.最高法院:法庭不得参与拆迁等行政执法活动[EB/OL].http://www.lawtime.cn/info/fangdichan/chaiqian chengxu/20110118130797.html,2011-01-18.
[10]王琳.中国经济时报:法院不应成为拆迁的马前卒[N].http://news.sina.com.cn/c/2004-12-21/14085287105.shtml,2004-12-21.
[11]佚名.中国的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N].人民日报,2014-01-22.
[12]【美】弗朗西斯·奥克利.自然法、自然法则、自然权利——观念史中的连续与中断[M].王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Misunderstanding and Clarification of Bearing no Liability on Breach of Contract
Gu An,Yang Zhimin
(Law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207,China)
There is no doubt assistance on government work if the people's court consults information with administrative organs,which is possible to creat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n resolving dispute,but the hidden legal problems are more prominent.Each case has particular conditions,there are estimated risks if enacting law application precept in advance;consulting case information between courts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s violates power division rules among State organs,prevents the independent exercise of its judicial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stipulations of law by the people's court,which will produce harmful effect on judicial authority and judicial credibility,and conflicts with the order of rule of law.
change of circumstances,law application,power boundary,judicial authority,new deal of real estate,bearing no liability on breach of contract,real estate marke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D916.2
A
1673-1573(2017)04-0051-08
2017-09-26
辜岸(1992-),男,四川仁寿人,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杨志敏(1957-),男,四川眉山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竞争法及民法。
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