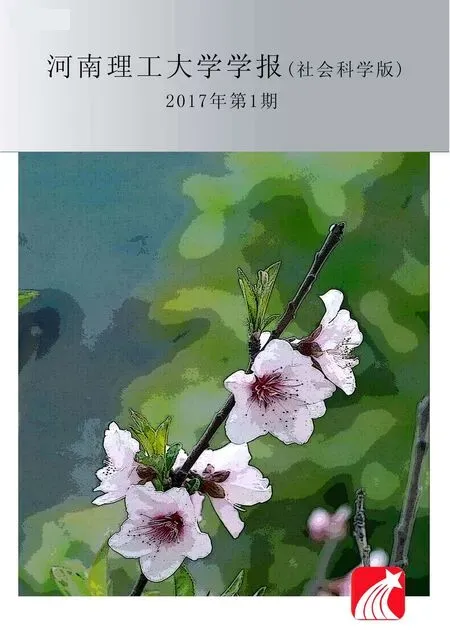《欺骗》中女主人公成长困境研究
王化菊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欺骗》中女主人公成长困境研究
王化菊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布鲁克纳的小说《欺骗》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在实现心理成熟和精神顿悟时已年过半百,这种成长的滞后性使该作品成为一部特殊的成长小说。文章结合传统成长小说模式和主人公安娜的性别、阶级和时代特征分析其成长延迟的原因,发现她在成长空间、引路人、寻找职业和走进婚姻几个成长关键点上陷入困境,困境背后是传统社会观念对女性成长的种种束缚和英国20世纪下半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给人们造成的道德模糊和价值体系混乱。安娜最后的精神突破得益于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反思和自我认同能力。主人公安娜的特殊成长历程颠覆和改写了传统成长小说的模式,丰富了成长小说的内涵,给当下女性成长以警醒和启迪。
欺骗;成长延迟;成长困境;认同
传统上,以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为典范的成长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关于年轻人成长发展故事的小说。例如,刘半九先生在给《绿衣亨利》的译本作序时曾指出,成长小说 “往往以一个所谓‘白纸状态’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与别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能力、道德和精神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成熟过程”[1]1-2。莫迪凯·马科斯对成长小说的界定为:“年轻主人公在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2]5-6这两个定义都提到了成长主人公是年轻人。然而,这种年龄限定并不是该类型小说的本质要求。戈尔曼研究成长小说时强调“成长小说主人公的目标是自我实现”[3]243;巴赫金对成长小说论述的核心是“主人公的性格变化具有情节意义”[4]230。至于主人公成长所发生的年龄段,二者都没有限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表现形式的复杂化,作品主人公的年龄和心理在很多时候并不构成正比。尤其是当主人公是女性时,她的主体性构建成功往往要滞后很多,比如沃尔夫《向外航行》和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在真正实现精神成长时都已不再是青少年。安妮塔·布鲁克纳*布鲁克纳被誉为“英国现代最受尊敬的小说家之一”,她是1984年英国布克奖得主、1997年《卫报》评出的最佳英语小说作者之一、2010年布莱克纪念奖短名单入围者,从1981年至今已出版25部小说。笔下的女性人物成长延迟更多,但不能因此把她的小说排除在成长小说类别之外。相反,其小说作为成长小说的特殊性值得深究。
一、《欺骗》是一部特殊的成长小说
《欺骗》(Fraud)是布鲁克纳的第12部作品。该小说讲述了五十多岁的安娜·杜兰特在母亲去世后不断反思和探索,最终走出幽闭生活和传统期待、实现自我精神解放的故事。小说以描述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性格转变为主要情节,具有成长小说的基本特征。英国学者乌桑迪萨加对《欺骗》的成长小说性质明确认定[5],国内王守仁等学者也表示认同[6]。然而以五十多岁的女性为成长小说的主人公确实罕见,难免引发质疑:为什么有人要年过半百才真正成长起来?书写这样的成长小说有何意义?“现在我终于长大了,对于有些人来说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你知道吗?”[7]223小说尾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安娜向费利佩提出的,也是布鲁克纳向读者提出的。通过提出这个问题,作者引导读者关注这部小说作为成长小说的特殊性。安娜的成长为什么延迟如此之久?她遇到了什么样的成长困境?她是如何走出来的?她的特殊成长经历有何启示?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安娜的成长困境
苏珊娜·豪曾把英国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总结为:“青少年主人公启程上路闯世界,通常由于自身的气质原因遭遇挫折,偶遇引路人和指导者,在选择朋友、妻子*这里只说了“妻子”没有提及“丈夫”,反映出传统英国成长小说以男性为主导。和谋生的职业方面开始会犯许多错误,最后通过找到他可以在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活动领域使自己以某种方式适应他的时代和环境的要求。”[8]4对照这种情节模式,可以发现安娜的个人成长经历与之十分不符:在外出闯荡世界、遇到引路人、寻找合适职业以及走进婚姻这几个成长关键点上安娜都遇到了重重困难。为什么?答案应该从安娜的个人情况和她所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中寻找。
(一)安娜的性别、阶级身份及时代背景局限了她的成长空间
除了短期游学巴黎以外,安娜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座幽僻的古宅里,没有离开家门真正踏上人生旅途。由于身为女性,她没能像威廉·麦斯特那样出门料理家族生意、广交朋友,而是长期在家照顾母亲。这一点与安娜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中的劳伦斯·哈乐迪和尼克·马什。他们和安娜一样都有孀居的母亲,但他们一个从乡村来到大城市从医,另一个往返于纽约和伦敦之间从事金融业。相对于同时期的中产阶级女性而言,他们的广阔活动空间得益于他们的男性性别。由于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安娜没有必要像德伯家的苔丝那样为生活出门奔波,经历艰难困苦,自然也就缺少了在生活中历练的机会。优越的经济条件在个人成长方面可以是台阶也可以是围墙。在这一点上,小说中出生下层社会但处事练达的钟点工佩吉·杜肯和主人公形成了鲜明对比,佩吉·杜肯的贫穷推动她广泛接触社会。由于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安娜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并不能给她带来一份体面的社会工作,而只是富家女的一种身份装饰。当时英国第二次妇女运动聚焦于女性在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和社会性别角色问题,恰恰说明女性在社会上可以获取的角色还十分有限。安娜和小说中其他几位女性大学毕业后回家而不是走上工作岗位正是这种社会现状的反映。
沃尔夫曾呼吁女性的发展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继承了沃尔夫很多写作特点的布鲁克纳在《欺骗》中给她的女主人公安娜安排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可惜的是安娜的这间屋子仍然在父辈的领地里,遵守的是大写的父亲的规则。安娜在这间屋子里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母亲,将自己的梦想和才华搁置一旁。她不是主动选择了这间屋子,而是无奈地留守。肖尔瓦特早就看到,沃尔夫为女性搭建的这间小屋“可能是避难所,也可能是监狱,甚至是坟墓”[9]264。对于安娜来说,小屋的监狱色彩更重一些。“越狱”之前的安娜患有厌食症,身体日渐消瘦。她的身体空间的缩小或许可以看作是成长空间有限的隐喻。总之,安娜的性别、阶级和时代境遇限制了她的成长空间,把她像鸟儿一样囚禁在家这个狭小的牢笼里,限制了她的人生阅历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使其个人成长长期搁浅。
(二)性别、阶级和时代境遇同样致使安娜的成长缺乏引路人
个人的成长往往离不开他人的指引,在很多成长小说中都能发现精神导师这样的角色,比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雅诺和竖琴老人,《简·爱》中的海伦和邓波儿小姐等。然而,《欺骗》中安娜却缺乏适合充当她引路人的人物。
一般而言,最有责任引导女儿成长的应该是母亲,然而安娜的母亲艾米不仅没有给她有用的指引,反而是她成长困境的直接制造者:艾米过久地将安娜留在家中照顾自己,致使安娜身体被困;艾米用消极被动的人生观教导女儿,致使她精神被困。艾米常常告诉女儿:“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值得等待的,到时候你自然就会幸福快乐。”[7]222正如安娜后来意识到的,母亲教给她的这句话是她人生中最大的谎言。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到处都是欺骗,这个谎言的欺骗性最隐蔽,后果最严重。听信母亲话的安娜像城堡里的睡美人一样一直默默地等待王子来拯救,一直等到人老珠黄。艾米为什么要这么教导女儿呢?一方面是因为艾米确实相信如此,否则她本人不会从三十岁左右守寡到近七十岁。也就是说,艾米是父权文化的盲从者,深信女性就应该被动等待。另一方面是因为艾米身体虚弱,只好留安娜在家陪伴和照顾她,否则艾米觉得自己无法生存下去。然而据薇拉观察,艾米的身体虚弱甚至是后来的死亡,都是她自己的心理作用。艾米柔弱退缩的心理还是传统父权文化的产物。从根本上而言,艾米是传统性别观念的传承者,安娜的女性性别身份让母亲理所当然地想把自己的人生观念传递给她,全然不知这些观念对于安娜的主体构建和精神独立起着负面作用。
艾米死后接替她的角色的是薇拉·马什。薇拉·马什对自己的这个责任有着清楚的认识,但她以年事已高为借口加以推卸。事实上,薇拉也没有能力做安娜的精神导师。据薇拉自己回忆,薇拉和丈夫的婚姻是别人安排好的。在薇拉年轻时,上流社会女孩不可以谈论自己的感情。薇拉和丈夫门当户对,但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在为丈夫服丧期间,薇拉发现“窗台上的盆景在和煦的春光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7]49。这种自由舒畅的感觉出现在丈夫去世以后,暗示薇拉在之前的婚姻生活中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经历了这种表面美满实则沉闷的婚姻,薇拉充满困顿,对于安排安娜的出路和指导她的人生,她并没有把握。
除了精神困顿外,薇拉的道德立场也不明晰。薇拉发现安娜像极了狄更斯小说中的小多莉特,一个自愿在监狱里照顾父亲的孝女。然而,薇拉提到安娜的孝顺品质时语气却很复杂,同情、揶揄、挖苦多于赞美。作为安娜美德的受益者,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因为薇拉知道这种品格在这个时代已经过时。她曾感慨:“那种男人喜欢女人温顺、被动,只会夸奖取悦他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7]19布鲁克纳作品颇具现实主义特点。《欺骗》的背景是20世纪下半期的伦敦,当时英国早已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推进,女性开始作为劳动力进入市场竞争,社会对女性的性格期待不再是温顺贤良,而是积极进取。安娜养成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性格,她生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伦敦自然是不适应的,即薇拉所说的“时代错置”。薇拉知道安娜善良孝顺,但薇拉态度矛盾,在传统美德和现实要求之间摇摆不定。薇拉一会儿想把安娜介绍给儿子做配偶,一会儿又觉得那简直是侮辱儿子。相对于被传统观念淹没的艾米来说,薇拉向现代女性自强精神迈了一步,但她被卡在了传统和现实中间。艾米看不清安娜的困境所在,薇拉虽能看清却束手无策。薇拉自身的失败和困顿决定了她也没有能力引导安娜走出成长困境。
除了艾米和薇拉的无力以外,作者还描写了安娜身边一系列迷茫的女性:菲莉丝·马丁因为丈夫的不忠而变得神经质;玛丽安因丈夫的粗俗而无语;费丽帕因做已婚男人的情人而纠结;就连成功征服劳伦斯的维吉也生活得紧张兮兮,怕丈夫被别的女人抢走。佩吉曾说:“除非嫁一个好男人,否则所有的女人都是受害者。”[7]56这位钟点工的话正是对这群中产阶级女性命运的总结。布鲁克纳刻画的这幅不幸女性的群像图解释了安娜引路人缺失的必然性——生为女性,她周围找不到合适的身份认同对象。同时,这副群像图也粉碎了传统成长小说构建的“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温馨神话,揭示出“她们从此过上了不幸的生活”冷酷现实[9]301。
在安娜认识的所有女性中,有一位活得有滋有味的女人,那就是佩吉·杜肯。通过薇拉的眼睛,我们看到佩吉衣着美丽时尚、言谈自信风趣、家庭幸福圆满。尤其令薇拉羡慕的是,佩吉有着明确的生活目标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这与来自上层社会的薇拉和安娜的空虚困顿形成鲜明对比,令她们相形见绌。为什么和佩吉认识良久,安娜没有能够从她那里获益呢?原因在于她们之间没有交流。她们之间隔阂的主要原因在于阶级差异,这点可以从薇拉与佩吉聊天后产生的羞耻感得到证明。虽然佩吉不以自己清洁工身份为耻,并骄傲地把自己当成专业人士,但薇拉骨子里却把她看成仆人。不与仆人闲话是英国富家小姐们从小接受的一个行为准则。和薇拉同一阶层的安娜也有类似的偏见——她几乎不和佩吉说话,甚至总是故意避开她。薇拉和安娜在经济条件方面优越于佩吉,她们靠固有资产投资收益就可衣食无忧;但在精神方面,她们二人才是需要学习和提升的。可惜阶级鸿沟阻断了佩吉做她们导师的可能性。除了佩吉,小说中另一个生活相对幸福的女人是劳伦斯的妈妈梅。梅有一个体贴的儿子,还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好姐妹,因此不像其他孀居女人那样孤单。梅是乡村小镇上的一个小店主,也属于劳动阶层。布鲁克纳用这两个劳动阶层女人的幸福来映衬英国中产阶级女人的悲凉,颇具讽刺意味。或许这也是她对自身所属阶层女人的无奈调侃。
找到合适的职业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是传统成长小说常有的结尾,然而安娜在这一点上同样陷入困境。“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女人,这点我知道,并对此感到羞耻,我从来没有工作,从来没有生育孩子”[7]162,安娜向劳伦斯坦承。当被问及原因时,安娜说得很简单:因为妈妈需要她。照顾母亲是安娜未能拥有职业的直接原因,然而根本原因是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玛丽父亲身体硬朗,绝非体弱多病,玛丽也同样被迫在家照顾父亲,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玛丽父亲直接用父亲的权威限制女儿的自由,专制到不允许她接电话,像极了《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那个堵在门口不让别人接近女儿的美国南方佬。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一再上演,是因为在传统父权文化中,女人的天职就是在家照顾人,照顾的对象包括父母、弟妹、丈夫和孩子等。作为未能适时出阁的独生女,安娜几十年来唯一的工作就是照顾母亲。即使结了婚,她的工作也是多一个照顾对象而已,就像她的好朋友玛丽那样。肖瓦尔特调查发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不习惯去选择职业,因为女性本身就是一种职业。”[9]21安娜骨子里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梅生病住院都没有告知在外面当医生的儿子,直到病逝;八十多岁的薇拉悉心照顾发烧的儿子,后来自己生病却又找来安娜和女儿照顾儿子。女性和男性照顾与被照顾的角色分配不公平一目了然。
为什么安娜在照顾老人这份工作中收获的不是成就感和荣誉感却是失败感呢?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照顾他人的工作没有经济回报,但有道德肯定。奥斯丁笔下的爱玛对老父亲不离不弃被众人称道;狄更斯笔下的小多利特甘愿在监狱照顾父亲而成为道德楷模。但是到了安娜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趋势下,传统的道德标杆开始束缚劳动力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于是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应运而生,结果传统道德被经济发展颠覆,“孝”变成了“愚”,这是安娜道德困境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照顾老人并没有发展成一种社会职业,安娜的付出也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值。“她当时做的事情现在被叫作‘护工’,那时这种工作无名无分”[7]114,叙述者回忆道。由于越来越多的女儿(和儿媳)离开了专门照顾父母的这个“岗位”,留下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护工后来很快发展成为一种行业。安娜处在社会对照顾父母的行为从道德嘉奖到市场回报的过渡期。因此,她既没有得到传统孝女的好名声和高尚感,又没有得到职业护工的市场回报和工作成就感。可见像安娜这样的中产阶级女性在当时要通过做传统工作融入现代社会是极其困难的。
即使安娜有勇气挣脱家庭牢笼及时走上社会,她在社会上找到合适职业的可能性也不大。纵观她身边的同龄女性,费利佩加入了一种艺术欣赏班,类似于老年大学,不能算作工作。维吉婚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售房中介,婚后迅速转向家庭主妇,并为此自鸣得意,说明销售当时对于女性来说不是体面的工作。萨拉·金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新时代的职业女性,她以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姿态勇敢地闯进医生行业,完全抛弃了传统女性的性格和角色,成为时代先驱。但萨拉·金出场时间滞后且极其短暂,说明作者对这种女性发展方向十分顾虑。安娜最后从事的工作是服装设计,但她还仅仅是在帮玛丽设计婚礼服装,能否真正走向市场尚未可知。再加上安娜年龄偏大,人脉缺乏,在创业方面毫无经验,她的职业前景不容乐观。
(三)安娜的个人条件和时代变化让她在走进婚姻方面遇到了巨大挫折
父亲的早逝是安娜成婚的第一个不利条件:“在婴儿期后就没有见过父亲的安娜永远学不会两性间互相吸引的规则。”[7]19在安娜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母亲给安娜描述的父亲形象近乎完美但不现实。安娜于是天真地等待一个母亲口中的父亲那样“安静、深刻、含情脉脉的男人”[7]63,但从来没有遇到过。此外,沉默被动的传统女性性格让安娜在婚姻市场中也没有竞争力,她结婚的机会掌握在别人手中。劳伦斯是唯一被安娜的静默深深吸引的男性,安娜也钟情劳伦斯,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因为乡下出生的劳伦斯一直有种自卑感,他努力摆脱乡音说明他想掩饰自己的原来身份。安娜处处端庄礼貌的行为方式不断提醒劳伦斯她来自上层社会,这令他产生沉重的压抑感。劳伦斯的自卑和压抑让他本能地选择逃离,再加上维吉对他大胆色诱,他注定留下安娜独自坐在蛋糕前,幻想里面藏着婚戒。尼克和安娜来自同一阶层,当母亲安排他和安娜约会时,他为什么毫无兴趣呢?因为安娜的善良和拘谨让玩世不恭的尼克反感,被妻子出轨所伤害的他不再相信这个时代的女人还具有传统美德。同时,不断有女人主动追求尼克,让他不屑于再费力地去取悦女性。对于尼克来说,女人不值得追求也不需要追求。尼克是现代女性观念解放的受害者,也是对女性的施害者。他常常用吻别的方式和他的女性朋友撇清关系,传统故事中的一吻定情被他改为一吻断交。他用这种方式嘲讽女性,揶揄世风。尼克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男性,他们的爱情观念在当时已被颠覆,对于城堡里的睡美人已经失去兴趣,何况安娜也不具有神话故事中公主的美貌。概括地说,安娜的上层社会单亲家庭出身、拘谨的性格和当时男性自身普遍存在的心理困境让她婚姻无望。虽然步入婚姻不一定会促进安娜的精神觉醒,但被迫单身的她无法及时转变社会身份,结果被剥夺了社交机会,给她的个人成长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总之,安娜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重重困难,她没有广阔的成长空间,没有称职的引路人,没有畅通的职业道路,也没有适合的结婚对象,她的性别阶级属性使她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被严重边缘化,其成长因此滞后。安娜的成长困境反映出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在女性名义上相对解放的新时代仍然受到歧视和压制。她们表面高贵却内心悲凉,表面坚韧内心彷徨,面对未来看不清方向。这种现状比传统女性受压迫的情况更加隐匿、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应对。这个特定群体的成长出路在哪里?巴特勒指出:“女性成长小说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为一个经济和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10]55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独生女的安娜在经济独立方面没有困难,那么她是如何实现精神独立的呢?
三、安娜的精神飞跃
关于成长小说中主人公获得自我认知的主要方式,芮渝萍做了这样的总结:“一个比他们年长或在某方面更有经验的人从旁观者的角度,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潜质;另一种重要途径是通过反思获得自我认识;第三种则是在与他人的冲突中发现自我;第四种是通过认同或崇拜某些特殊的人,从而主动接受影响,效仿其行为和思想。”[11]79对照安娜的成长经历,我们发现第一种途径行不通,因为她压根没有这样的引路人。由于冲突也可以是反思的素材,不妨把第二种、第三种途径合并为一种,这种途径正是安娜的主要精神成长方式。最后一种途径中认同可以扩展为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认同。简言之,反思和认同是安娜精神成熟的两个关键词。
母亲去世直接给安娜的成长松了绑,在母亲去世之后安娜一边鼓起勇气主动接触他人,一边深刻地反思自己的人生。她主动探望薇拉、参加社区圣诞派对、拜访邻居和卡特女士、去劳伦斯诊所、赴巴黎为玛丽庆祝生日以及去劳伦斯家里做客。然而这些交往带给安娜的都是失望和打击,她的友好善良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嘲讽和冷落。这是安娜成长路上必经的历练。安娜在默默忍受苦涩的同时也细细反思其中的原因。
首先,周围人对安娜的冷漠和敌意,安娜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他们。薇拉对自己既友好又反感是因为她自身困顿;尼克对自己的敌意是由于他自尊心受过伤;维吉对自己的无礼是由于他自己肤浅等。安娜透过他们的表面看到了更深的内因,她在彷徨之后决定坚持自己的友善。“如果她(马什夫人)需要,我还会再次照顾她”[7]221,被多次冷落的安娜最后向费利佩声明,虽然她知道这样并换不来别人对她的感激和爱。在道德模糊的社会里,道德高尚的人是落寞的,甚至偶尔会羡慕那些没有道德原则的人。然后,在这一点上安娜选择了坚守道德。“布鲁克纳的小说让读者思考和怀疑她的笔下的人物或者布鲁克纳自己真的认为同情、忠诚、和善良毫无价值。”[12]21在《欺骗》中,作者的道德倾向相对明显。安娜的道德坚守体现出她对自身过去的经历由否定到肯定,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由怀疑到认同,对未来方向由迷茫到明确。这种自我认同感“是一种自然增长的信心,既相信自己保持内在一致性和连续系的能力(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这种信心是与对别人保持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相协调的”[13]797。经过理性反思和道德抉择之后,安娜再次去照顾薇拉时不再忐忑不安,而是沉着淡定,甚至还给薇拉一种威严感,可见她自信心的增长和自我认同感的增强,以及她对自己和他人保持一致性能力的提高。
在道德立场方面坚持自我的同时,安娜在精神成长方面的另一个突破在于她对自由的追求。一方面,她看清了母亲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对她的期待是一种欺骗。“欺骗是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期待,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自己的需要来打造我。在这种意义上而已,欺骗其实惊人的普遍。它也不仅仅存在于两性之间。”[7]221安娜对欺骗的阐释很深刻,其中最特别的一点是她指出父辈以爱的名义对子女的利用和束缚。虽然安娜自称并不因为照顾母亲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而后悔,但这番言论说明安娜对母亲最终还是否定的。安娜把象征母亲身份的那件大衣送人折射出她最终对母亲的不认同。否定母亲就是否定母亲代表的那些束缚她个性发展的价值观。这种否定是安娜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为她走向精神自由排除了内在阻力。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女性,安娜内心早已埋藏下渴望自由的种子。母亲去世、劳伦斯成婚、玛丽失联、周围人对她避之唯恐不及的境遇使得亲情、爱情、友情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安娜而言都不可得,她的人生一时降到了谷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静思人生,安娜心中回响起法国诗人瓦莱莉关于追求自由的诗句,这让她兴奋不已,心中自由的种子瞬间破土而出。在圣诞节这个象征着新生的日子里,安娜终于实现了精神顿悟。因为这个心理突破,孤单和困难不再可怕。顿悟是成长小说常见的情节。这时安娜的精神导师不是身边的朋友长辈,而是有名的诗人,这是她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特点。在诗人自由精神的引领下,安娜在圣诞节当天五次想象去南方追求明媚阳光下的新生,由此开始了对自由的积极追求。她不再静静地待在古宅里,而是去充满流动性的巴黎选择不固定的住所;她不再默默等待,而是立刻行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服装设计中去;她向费利佩确定是劳伦斯报警寻找她,预示着她要给自己的爱情一个交代;她还劝说玛丽和费利佩果断做出选择,不再隐忍等待幸福;她心中自由的种子不仅发芽长大,还向周围女性心中播撒。
认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对自我和他人的认同过程中,安娜选择了善良和自由,摈弃了母亲的宿命论。认同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对个体过去生活的印证和引申,同时还是对未知之将来的规划和设计”[14]21。在小说结尾处,安娜的自我主体建构还远远没有结束,她的未来还不够明朗,但在自由精神的推动下,她的事业和爱情有了方向。虽然前景并不乐观,但有了一种成熟的精神内核,安娜就可以坚定地走下去,就像她最后坚定地走进川流不息的巴黎大街所预示的那样。
四、结 语
成长最终意味着在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生为女性,安娜自幼内化了被动等待的传统女性思想,长期扮演照顾他人的传统女性角色。这种思想和角色在观念更迭、道德模糊的现代英国社会得不到认可,安娜和社会之间的距离一度拉大。中产阶级出生带给安娜高等教育和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同时在她和社会现实之间拉起一道围墙。活动空间受限、精神引路人缺失、事业爱情皆无望的主人公在个体成长道路上深陷困境。通过在困境中苦苦反思,安娜最终否定了被动等待思想,肯定了宽容友善的精神,在坚持自我认同的同时努力主动融入社会。在此过程中,主人公从知识中汲取成长能量、感知成长方向,显示出知识女性的成长特点。《欺骗》是布鲁克纳对中产阶级知识女性成长困境的探索,是对身处这种困境中的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辩白,也是对她们的命运和未来发展做出的思考。在批评社会的同时,该作品通过安娜的成长启迪同时代的女性走出困境,走向内心的坚定和强大。
[1] 刘半九.绿衣亨利·译本序[M]//凯乐.绿衣亨利.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SUSAN A G. Starting over: the task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contemporary bildungsroman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0.
[4]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历史中的意义[C]//巴赫金.巴赫金著作集.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ARANZAZU U.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at the fin de siècle: the utopia imperative in Anita Brookner’sAClosedEyeandFraud[J].Critique,1998, 39(4): 325-340.
[6] 王守仁,何宁.构建单身知识女性的世界——论布鲁克纳的小说创作[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33-39.
[7] BROOKNER A. Fraud [M]. London: Penguin, 1992.
[8] HOWE S. Wilhelm and his English kinsman: apprentices to lif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0.
[9] SHOWALTER 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10]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1] 芮渝萍,范谊.成长的风景——当代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2] NORTON A V. Anitar Brookner reads Edith Warton and Henry James: the problem of moral imagination[J]. Tulsa studies of women’s literature,2010,29(1):19-33.
[13] 埃里克森.统一性与统一性扩散[M]//莫雷.20世纪心理学名家名著.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4]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责任编辑 位雪燕]
On the heroine’s growth predicaments inFraud
WANG Huaju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Huainan232001,Anhui,China)
The psychological maturity and spiritual breakthrough of the heroine inFraudby Anitar Brookner were not achieved until she was over fifty. The delay of growing up makes it a special Bildungsroman. Taking the gender, class and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roine Anna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edicaments in light of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Bildungsroman. It is discovered that she was stuck in space, mentor-ship, career as well as marriage because of the mutiple bondage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on women’s development and the moral ambiguity and value confus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Britain. The final metamorphosis of Anna results from her self-reflection and self-identification as an intellect. Anna’s special growing up process subverts and rewrites the pattern of tradtional Bildungsroman, enriches the concept of this genre, and enligthens the inner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omen in a sense.
Fravd; growth delay; growth predicament; identification
王化菊(1983—),女,安徽淮南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圣经文学研究。 E-mail:xbwangdog@163.com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1.012
2016-11-23 项目基金: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QN201351)。
I207
A
1673-9779(2017)01-0066-07
王化菊.《欺骗》中女主人公成长困境研究[J].2017,18(1):066-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