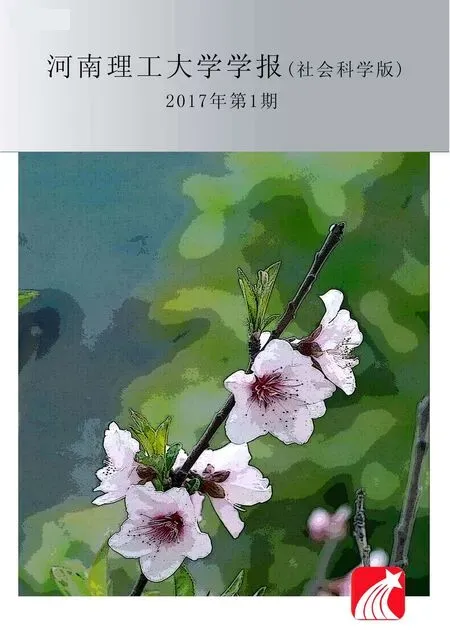论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怀旧情结
韩利敏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论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怀旧情结
韩利敏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著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中表现出对未来极权社会的巨大恐惧和对人类被独裁奴役命运的深深忧虑,因此,奥威尔的小说似乎总是放眼未来、预言未来的。然而, 纵观奥威尔的小说世界,可以发现他在小说中,对人类未来表现出极大关注的同时,也处处流露出对美好旧世界的无限缅怀,即怀旧情结。奥威尔以自己对生态乌托邦的积极建构、对童年回忆叙事的青睐和对田园世界的眷念与向往来完成自己的文学怀旧之旅,折射出怀旧者背后的“文学怀旧”传统和“向后看”的民族心理。怀旧与前瞻相辅并存,共同完成了奥威尔作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的政治体察与历史审视,对奥威尔小说中怀旧情结的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伟大作家,把握他时代良心的脉搏。
乔治·奥威尔;怀旧情结;生态乌托邦;童年叙事;田园世界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著名小说家之一,他的两部惊世骇俗之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把奥威尔带进了财富与声誉之堂,同时也给他贴上了诸多标签,如“人类责任和道德选择之伟大传统的主要捍卫者[1]”“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代人冷峻的良心[2]”等。然而,由于历史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奥威尔也被划入“反苏反共作家”“人民的公敌”和“资产阶级反动作家”的黑名单中。由此可见,奥威尔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议不断的“问题”作家。抛开评论界的是非争执和标签之争,考察奥威尔真实的生活经历与思想发展,可以发现奥威尔是个多元矛盾集一身的“矛盾体”: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却被打上“反共作家”的标签;拥护社会主义,却看不到革命的希望,极其悲观;憎恨资本主义社会,却格外推崇它所带来的自由民主;他是大英殖民帝国的子民,却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来自英国上层阶级,却对殖民地无产阶级充满了同情;他坚信无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力量,却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丑化。重重对立集中体现了奥威尔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复杂性。在笔者看来,奥威尔的矛盾性并不仅仅如上所述那样简单,深入他的小说世界,可以发现奥威尔身上体现出的另一对矛盾:对未来人类生存的极度焦虑和对美好往昔的无限缅怀,即奥威尔的未来忧思与怀旧情结的对立。对奥威尔小说中怀旧情结的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伟大作家,理解奥威尔在政治立场上的矛盾性。
一、文学怀旧与乔治·奥威尔
“怀旧”( nostalgia ) 一词源于希腊语,是由两个词根“nostos”( 意为“回家”) 和“algos”( 意为“伤痛”)组合而成 ,最初“怀旧”属于一个病理学概念,意指古代战场上士兵经历的一种近乎致命的强烈思乡病,它是较为常见的,也是可以治愈的,这种思乡病随着患者返回故乡而自动得以救治。 到了19世纪, “怀旧”一词在语义上逐渐变化,演变成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对家乡、对失去的美好的无限追思;20世纪中后期,“怀旧”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正式确立下来,内涵也从对“家乡”这一空间概念的思念变为对过去这一时间概念的“怀旧”[3], 此时它变成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心理状态, 因为时光不能倒转,怀旧注定是对一个“失去的天堂”无尽又无望的期盼。从时间维度来看,怀旧是人类借助“失去的天堂”来审视不堪的现实世界,借助对一个和谐、宁静、单纯而美好世界的构想来试图逃避、调节和缓解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冲突;从空间维度来看, 怀旧就是一场“寻根”之旅,回到最初的家园, 一种“叶落归根”的心灵追求,“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成为人生中简单、纯粹和自然时刻的象征,对家的追思回望代表着人类对曾经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与追求。
怀旧是文学家常用的一种策略,文学中的怀旧现象在西方早已有之,并贯穿始终。古希腊神话中的人们对于“黄金时代”的怀古忧思与无限缅怀开启了文学怀旧的先河。自此,怀旧情愫便一直绵延不绝,《圣经·旧约》中伊甸园的诗意构建和人类对“痛失乐园”的无限惆怅体现了人类对原始纯真时代的留恋,面对尘世的荆棘和现世的烦恼时,总会萌生出“复乐园”的模式化怀旧冲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对古罗马和希腊神话中“旧世界”的憧憬,向往古希腊阿卡迪亚地区宁静的牧民生活,借助田园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来抒发对宁静现世生活的憧憬, 对人间纯美爱情的渴望和对尘世纷争的逃遁,于是带有浓烈怀旧情愫的田园诗歌迅速复苏并繁荣起来;滥觞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掀起了返回传统农耕社会、田园生活的高潮,华兹华斯对自然生灵的细致观察和细腻刻画流露出对自然的顶礼膜拜,对原始自然生活的怀念和对现实工业文明的诗意逃遁,后来的雪莱、拜伦和济慈也纷纷继承了复古主义,把怀旧进行到底;20世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狂热推崇,以及对传统社会的人文理性进行的空前“祛魅”,促使功利主义盛行、经济利益当道、生态危机恶化、人类异化、价值崩溃、道德沦丧,面对如此种种不堪的混乱世界,人类对远古纯真年代的迷恋之情达到了巅峰,文学中处处弥漫着复古怀旧、思家恋旧的情绪,不过此时文学中的怀旧策略已经撕去早期怀旧文学和浪漫主义那种诗意回归的温情面纱,表现出对当下政治危机、价值危机和生态危机更直白、更尖锐和更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再次体现出文学家对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深层忧患和悲悯情怀。
乔治·奥威尔短暂的一生亲历了大英帝国无可挽回的衰落、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战争和各种杀戮。奥威尔出生于英属殖民地——印度,一个家道中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家族光荣但家境贫寒,童年在印度的见闻使他意识到殖民主义的罪行,对大英帝国的邪恶殖民扩张心生反感,对帝国的仇恨也油然而生。少年时期的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公学,但贫寒的家庭背景让他受尽了歧视与奚落,使他对英国存在的阶级等级制度深恶痛绝。在伊顿公学毕业后,奥威尔开始在缅甸做英国殖民警察,缅甸岁月使他认识到人性中残暴的一面。西班牙内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所受的遭遇和迫害使奥威尔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发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极权主义倾向,使其对强权政治和个人独裁的严重威胁深感不安。人到中年的奥威尔,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世界变得满目疮痍,法西斯主义肆虐猖獗,独裁统治、极权主义盛行,人类自由被破坏,人性被压制;战后两大阵营冷战对峙,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战争乌云四处弥漫,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梦想彻底破灭。面对如此破碎、阴暗的世界,对人类充满忧患和悲悯情怀的奥威尔不自觉地缅怀过去,流露出一种伤感怀旧的颓废情绪,用这种怀旧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积极批判、重建或消极逃避。纵观奥威尔的小说世界,可以发现作者无处不在的怀旧情结,集中体现在他对政治乌托邦的极端失望和对生态乌托邦的积极建构;奥威尔对童年回忆的青睐表现出他对美好旧世界的缅怀;奥威尔在小说中抒发了对田园世界的眷念与向往,透出浓浓的怀旧情愫和乌托邦倾向。
二、奥威尔对生态乌托邦的构建
“乌托邦”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代表着人类对古朴纯真生活的美好向往,托马斯·莫尔开启了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先河,他的《乌托邦》在表现手法、审美特征和创作规律等方面奠定了现代乌托邦小说的写作范式。生态乌托邦指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都处于一种完美和谐与统一的存在状态,强调人的“诗意的栖居”必须建立在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基础之上,强调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社会精神发展的协调一致。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家之一,奥威尔在其小说中早已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尖锐地指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表达了构建生态乌托邦的诉求与愿望,体现出他忧思怀古、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情怀。但他的怀旧忧患不丧失信仰,悲观中不放弃探寻,体现了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思想勇士之斗志。
奥威尔的生态乌托邦构想与他对自然的兴趣密不可分,奥威尔是一个狂热的自然主义者,痴迷于探求自然生物的生存之谜,对水生动物的兴趣尤其浓厚,酷爱垂钓。奥威尔对垂钓的热爱可以在他的小说《上来透口气》中主人公保灵对钓鱼的痴迷中窥见一斑,“想到钓鱼,我就如痴如狂,激动得难以自抑”[4]42。对于挣扎于喧嚣嘈杂的现代都市的保灵来说, 钓鱼是一种精神愉悦的活动,因为钓鱼时他能坐在一个宁静的池塘,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宁静、平和。在保灵看来,“钓鱼就是平和”,钓鱼就是战争的反面,钓鱼对童年的保灵无异于一场天堂之旅, 奇幻无比,令人神往。垂钓时的那份宁静,那样的绿水,那种悠闲、悠然和惬意的感觉让他不再匆忙奔波,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疲于奔命,给他一种真实的存在感。保灵特别梦想回到儿时的故乡下宾菲尔德钓鱼,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下宾菲尔德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村民生活淳朴、心态平和、关系融洽,那里遍地山楂树篱,栗子树的花在盛放,野薄荷绿意盎然;河水清澈,泉水叮咚,岸上是郁郁葱葱的植物,鱼儿在水中欢快地跳跃[4]86,这就是保灵儿时的故乡。童年记忆中的故乡湖畔垂钓代表着和谐、美丽和纯真的田园生活,代表着保灵对故乡、童年和古朴生活的怀旧,更代表了作者奥威尔对构建生态乌托邦的美好愿望,表达了他强烈的生态意识。
奥威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环境之上,只有在生态环境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的纯真,人才能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才能建立政治上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关系,消除等级差别,消除种族歧视,即只有先建立生态乌托邦才有实现政治乌托邦的可能,这一理念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得以完美地体现。主人公温斯顿生活在一个反面乌托邦的世界——大洋国,这是一个充满着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寓言操控、历史篡改、人性压制和自由极度受限的黑暗未来世界,温斯顿反叛党的寡头政治和独裁统治,大胆地追求个人自由与思想自由,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来推翻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在他追求自由的种种尝试中,他多次幻想并苦苦寻觅的一个地方就是“黄金乡”或“黄金原野”“他醒来的时候想到这个地方就叫它黄金乡,这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掉的草地,中间有一条足迹踩踏出来的小径,到处有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簇簇树叶微微颤动……却有一条清澈的缓慢的溪流,有小鲤鱼在柳树下的水潭中游弋”[5]28, 这是温斯顿心灵深处的“乐园”和“净土”,这里没有思想警察的监视,没有“老大哥”的目光逼视,有的是风轻云淡,有的是鸟语花香,在这里,他行动、言语自由,欢畅地享受爱情与友情,这就是温斯顿心向往之的“故乡”,这个生态乐园是他精神困顿的疗养所和心灵的归宿地。“黄金乡”的幽静、沉寂和缓慢给他压抑的人性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和一束和煦的冬日暖阳,借着这束微弱的希望之光,他可以对抗那个荒诞的世界,对原始生态家园的守望让他坚定了推翻极权、独裁统治的决心和信仰。
在奥威尔看来,人类最大的幸福在于保持简单、自然的生活。人只有大量地保留简单的生活才不会异化,而许多现代文明,特别是电影、广播和飞机,将会削弱人的意识,钝化人的求知欲,使人越来越像动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威尔对农耕文明时代简单生活的怀旧与缅怀,主张建立一个珍爱自然、以一种温柔和关怀的方式改善自然的社会,他对现代生态危机的关注和对工业文明的排斥体现出他对表面繁荣、实则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的忧虑;奥威尔对生态乌托邦社会的积极构建表达出他面对风雨飘摇中大英帝国的衰落而表达出的无限惆怅与怀旧。
三、奥威尔对童年回忆叙事的青睐
从“怀旧”的两个词根“nostos”和“algos”来看,怀旧充满了伤感与无奈,那么,怀旧缘何感伤?因为故乡仍在,而童年已逝;因为家乡可回,而时光难倒流。因此,乡愁、童年和往昔便成为“怀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纵观中外古今文学可以发现,“童年”是一个充满童趣、纯真、美好的典型怀旧伤感母题,因此追忆童年的美好、缅怀儿时的快乐几乎是每个作家都有过的写作经历,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高尔基,他的《童年》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追忆童年之力作;还有鲁迅对童年“三味书屋”的回忆也不时引发读者的怀旧惆怅之情。同样,作为一个对人类生存现状极度担忧的作家,奥威尔也往往通过作品中的童年回忆叙事来认清现实的生存困境,借昔日“童年”世界的唯美来比对今日成人世界的混乱;通过向往回归返璞归真的自然世界、童年时代,来抒发对当今自然、社会状态的忧虑与反感。
奥威尔的童年回忆叙事最典型地体现在小说《上来透口气》(ComingUpforAir,1939)中,这部小说远离了作者一贯的政治锋芒与极权批判,无关宏大叙事,无关现实指涉,讲述了生活于喧嚣嘈杂的英国工业文明下的一个小人物——乔治·保灵,讲述了他的一次“出逃”,一次想“上来透口气”的寻根之旅,他逃往何处?重返家乡,寻找田园诗般的童年时光,他的返乡之旅和童年追忆是对庸俗日常生活洪流的反抗,是反思现代文明与个人价值的尝试。童年中有他那可爱的家乡,珍贵的宁静氛围和平和心态,保灵说:“你要是愿意,就叫它和平好了,但是我说‘和平’的时候不是指没有战争,我指的是平和,那是你在心底里所感到的”[4]452;童年记忆中有慢节奏的生活,愉悦放松的精神,按部就班的从容;童年记忆中还有一个宁静的池塘,那儿鱼儿成群、自在游弋;童年还有母亲手工做的糕点、手工劳动的氛围。这一系列童年记忆的美好画面成了保灵的精神寄托,是他个体得以滋养的土壤,是他在机器轰鸣、枯燥乏味的都市生活中存活下来的精神动力。然而,保灵想象中的家园和童年记忆在现实面前破碎不堪,真正的家乡已面目全非:人口激增,高楼林立,工厂遍地,机器轰鸣,对保灵来说,家乡变“异地”,熟悉又陌生,故国变“他乡”,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以至于他在自己的家门口竟迷了路。保灵的故乡之旅是一次幻灭之旅,让他发现上来根本无气可透,“现在是没有空气了,我们身处其中的垃圾箱高出了平流层”[4]454,童年梦境的惊醒再次凸显了他身处现实世界无处可逃的窘态,平添了童年怀旧的悲凉之感和徒劳之感。
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庄》中,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农庄德高望重的公猪老梅杰有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很久以前的事,那时他还是只小猪崽,妈妈和其他母猪常常唱一首老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英国动物》,这首歌描述了暴虐的人类被推翻之后的一幅“动物天堂”之景,“英国果实累累的田野,将只有动物在上面迈步……马衔和马刺将永远锈迹斑斑,残酷的辫子将不再挥舞……水将会更加洁净,习习微风也将更加清澈”[6]6,这一革命性的宣言成为动物们推翻人类“暴政”的号角。在这一纲领的鼓舞和引导下,动物们的夺权之战才可能胜利,而这一重要的革命纲领正是老梅杰童年记忆的结果,代表着整个动物界童年时期的共同愿景与追求。同样,在《一九八四》中,温斯顿一直怀念资本主义的“过去”,经常梦见自己儿时的生活,他的母亲和妹妹,“在那个时代里,一家人都相互支援,不用问个为什么”,但“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和痛苦,却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切复杂的悲痛”[5]28。在街上闻到纯正咖啡的香味和吃到浓郁的巧克力时,他马上又回到了那将遗忘过半的童年,感觉浓烈的香味好像是他孩提时代发出的一样[5]127。他还时常梦见自己童年时期的“黄金乡”的美妙,“有一条小溪,在那边那块田野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你可以看到它们在柳树下面的水潭里浮沉,摆动着尾巴”[5]111。这就是温斯顿的童年回忆,他用回望童年的怀旧方式为自己在“大洋国”自由感和价值感的丧失做了一次精神补偿,用童年那永恒的美好回忆来医治他当下锥心的痛。
回忆是一种回归,重温童年的质朴纯真、朴素纯洁成为作家当仁不让的重要怀旧形式,失去的天堂才是真正的天堂,无法返回的童年也许恰恰正是人类最陶醉的岁月。对此,美国学者戴维斯给出了更为理性的解释,“怀旧隐匿和包含了没有被检验的信念,认为过去比现在更好、更美、更健康,它泰然自若地宣称‘美好的过去和毫无吸引力的现在’,尽管过去也经历了一些磨难,但总有一种内在的感情和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7]。
四、奥威尔对田园世界的眷念
作家对田园世界的想象源于人类对古希腊黄金时代的怀旧,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城市生活的逃遁,在田园世界里自然被描绘成一幅如诗的画卷:幽静的花园,祥和的乡村,和煦的阳光,永远看不到荆棘丛生、毒蛇猛兽,远离了地震山洪。社会被想象为一个人间的“大同世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自由博爱,共享财产。古希腊时代人们就有对“黄金时代”和“阿卡迪亚”等理想田园社会的向往,2000多年前的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中描述了一个人人平等、自给自足的完美世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人人平等、财产公有、和谐统一的田园世界;孔子在《礼记》中也描绘出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中国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的惬意与闲适。由此可见,田园世界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产物,是文人寄托个人理想、发泄社会不满和怀旧寻求心理慰藉的产物。作家乔治·奥威尔见证了20世纪初、中期人类所遭受的种种浩劫,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人道主义者,不免胸中悲愤难抑,在奥威尔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医治尝试中,对田园社会的怀旧与向往不能不算做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人与人之间的博爱与平等是田园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思想内容,在奥威尔的文学创作中体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和谐相处,诗意地栖息在田园牧歌般的家园中,对这一精神家园的探索在温斯顿的一个梦中得以体现,“在这段时间内他梦得很多,而且总是快活的梦,他梦见了自己在黄金乡,坐在阳光映照下的一大片废墟中间,同他的母亲、裘利亚、奥勃良在一起,什么事情也不干,只是坐在阳光下,谈着家常”[5]251。在温斯顿的田园设想中,他在美好的阳光下尽情享受着亲情、爱情和友情,没有了斗争与压迫,死敌奥勃良也变成了可以亲切交谈的友人,交流顺畅,心灵相通,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和谐,这是奥威尔文学创作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样,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RoadtoWiganPier,1937)中,奥威尔描绘了英国北部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威根是位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的一个小城,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在此奥威尔为矿工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超强忍耐力而深深打动,他们的劳动强度超大,工资收入少得可怜,但他们仍然能用这点工资来糊口度日,他们的住所面积实在狭小,但他们仍能“过度拥挤”地蜗居在一起,生活亦能“其乐融融”[8],奥威尔在为工人阶级贫苦的生活状态深表同情之时,又唏嘘感慨,矿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身心健康的法宝正是在于他们缩减自己的物质需求、降低物质消费的欲望;在农耕文明时代,没有机器大生产,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财富没有现在丰富,但人们依然悠然自得,原因正是如此。通过对矿工生活的同情,奥威尔也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田园生活祥和、宁静的理解,他深入社会底层去体验黎民百姓的生活,节衣缩食,穿着朴素,生活简易,显现出他的平民意识和对田园生活本质的身体力行。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逐渐从一个农耕文明社会发展成一个机器文明和科技文明社会,因此奥威尔带着对人类从古至今对田园生活的留恋,带着对当时政治紧张局势的焦虑创作出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它不仅仅是人们所理解的一部政治讽喻之作,还是一部充满田园情结的怀旧之作。首先,故事是在广阔的田园背景上展开的,一个生活着众多动物的农庄,动物们通过革命暴力的手段建立起属于动物自己的王国,推翻了人类的暴政与剥削。更为重要的是,动物们在老猪梅杰精神领袖的指引下颁布了动物王国的“宪法”《七戒》: “1. 无论如何,两条腿的都是敌人;2. 无论如何,两条腿的,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3. 动物不准穿衣服;4. 动物不准睡在床上;5. 动物不准喝酒;6. 动物不准杀害动物;7. 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6]15。这部“宪法”规划了动物王国美好的蓝图,描绘了一个美丽的田园生活画面:生活简单、纯朴,反对奢侈消费,主张节约勤俭;人际关系融洽,反对等级划分,反对同类相残。奥威尔始终认为人类恬静、简单的生活方式在维护人类自由、建立平等和谐人际关系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种田园精神也代表了奥威尔对人类传统生活方式的珍视和维护。
五、结 语
乔治·奥威尔凭借其小说《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而享誉世界文坛,文学创作中的反极权主义思想和政治讽喻几乎“垄断”了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领域, “一代知识分子的冷峻良知”作为一个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也把奥威尔的思维模式化和定型化。然而,作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奥威尔有其多面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是一个充满悲悯情怀和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着眼于人类未来世界的政治危机和价值危机,以反乌托邦文学的形式向人,作品体现出超前于时代的前瞻性与洞见性;另一方面,处于危机四伏、喧嚣混乱的社会巨变中,奥威尔又以古老的文学怀旧传统来审视当今世界,缅怀失去的天堂,试图以对人类文明童年时期的怀旧来医治当下千疮百孔的世界,他以对生态乌托邦的积极建构、对童年回忆叙事的书写和对田园世界的眷念来完成了自己的文学怀旧之旅,折射出怀旧者背后的“文学怀旧”传统和“向后看”的民族心理,作品又体现出重访历史、重温田园的怀旧性。在奥威尔的小说中,前瞻未来与重温过去并存,极权社会与田园世界交织。怀旧与前瞻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了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的政治体察与历史审视,怀旧与前瞻平分秋色,共同构筑起一位冷峻知识分子对抗强权、追求真理的良知之桥。
在转瞬即逝、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人们难以在浮光掠影的生活背后寻找到意义、价值和信念的归宿,怀旧作为一种“反速度”或“倒速度”的原始冲动应运而生,体现出现代人在迅疾飞逝的岁月中想抓住什么或留住什么的愿望。诚然,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消费主义盛行、全球一体化袭来和生态危机加重的当今世界,人类何尝不可乘怀旧之舟徜徉在“黄金时代”的宁静里呢?何尝不可在慢慢长夜中做个美丽的梦呢?
[1] CALDER J. Open guide to literature:AnimalFarmandNineteenEighty-four[M]. Milton Keennes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87.
[2] 杰弗里·迈耶斯. 奥威尔传[M].孙仲旭,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52.
[3] JOHN D L.The ancients’ironic nostalgia[J].Paragraph, 2006,29(1):94-107.
[4]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M].孙忠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M]. 李美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7] DEVIS F.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M].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9:19.
[8] 乔治·奥威尔.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M].郑梵,胡萌琦,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82.
[责任编辑 王晓雪]
The research on nostalgia writing in George Orwell’s novels
HAN Limin
(ForeignLanguageDepartment,AnhuiPolytechnicUniversity,Wuhu241000,Anhui,China)
The great British writer George Orwell expressed his deep concern and anxiety about the arrival of totalitarian society and people’s being enslaved by dictatorial government in the future in his masterpiecesAnimalFarmand 1984. Therefore, it seems that Orwell is a future-oriented writer, focusing on future in his writing. However,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ading of his novels, it can be discovered that apart from his great concern over people’s future life, Orwell also presents strong nostalgic feelings for the good old past. His nostalgia writing is undertaken through the following ways: active appeal for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utopia, wide use of childhood recollecting narration and strong yearns for a pastoral or picturesque world. Orwell’s nostalgia writing carries on the great literary tradition of nostalgia and reflects a “looking back” psychological tendency of the British nation. Looking-backward and looking-forward, combined together, help to express Orwell’s concern over politics and history as a humanist writer. The research on nostalgia writing in George Orwell’s novels is helpful for furthering and widening George Orwell research in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way, which in turn, helps to grasp his pulse of conscience as an intellectual and humanist.
George Orwell; nostalgia writing; ecological utopia; childhood recollecting narration; pastoral world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1.011
2016-10-13
安徽省教育厅科研项目(TSSK2015B37)。
韩利敏(1982—),女,河南濮阳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E-mail:zhudongbei2016@aliyun.com
I106.2
A
1673-9779(2017)01-0060-06
韩利敏.论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怀旧情结[J].2017,18(1):06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