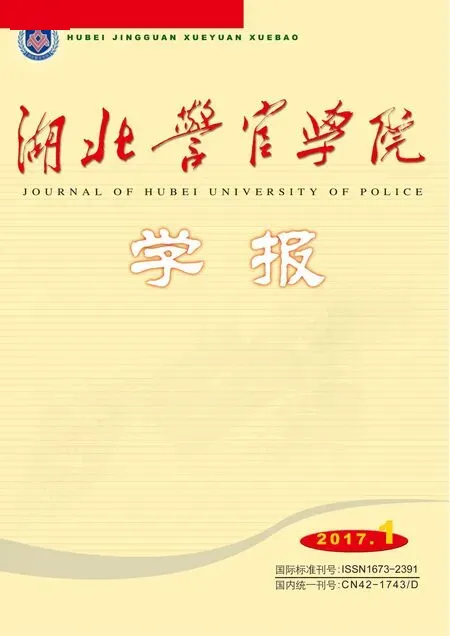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与本土化思考
马丽亚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88)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与本土化思考
马丽亚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88)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核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集各国司法实践之经验为司法转处提供了基本指导和标准:转处依据的多样性且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且尽早进行转处,决定主体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且自由裁量权较大,转处方案的多样性且适当进行干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现状,剖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发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本土化难以避免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控制和影响,公安机关无须过于积极地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社区功能的发挥非常有限,应当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国际准则;本土化
“转处(diversion)”一词就字面而言即“分流,转向”的意思。国内学者的探讨主要分为“司法分流”①参见张鸿巍:《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分流制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6期。和“转处”②参见盛长富:《总论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河北法学》2014年第12期;林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理念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两种说法。前者更尊重本意,直白易懂;后者取意于域外该项制度的丰富内涵,又区分为“转向处分”③参见沈银和:《中德少年刑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7页。沈银和认为,“转向处分,简言之,即对于轻微犯罪之少年,不予审判,更不予处罚,而代以教育性之辅助措施。”和“转向处遇”④“转向处遇”即一些学者文章中提及的“转处”的全称。两派,故认为该项制度由“转向”和“处分或处遇”两部分组成。然而,“司法分流”在刑事诉讼法领域内常有“程序分流”、“案件分流”的含义,并不能突显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转处”则较多用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故以下采“转处”的说法。鉴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规定的内容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现状,转处的适用对象即涉罪未成年人,因此文章探讨的是涉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转处衔接问题(简称“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以此为切入点探索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标准和应然状态,从而为梳理分析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提供参照对象,讨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本土化的可能性。
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问题的缘起
(一)从实践到理念
1899年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使得未成年人脱离正式的对抗制特征明显的成年人法庭,无人照管、疏于管教以及被指控犯罪的少年可以在独立的少年法院接受审理。“富有同情心的法官可以适用个别化处遇方法对少年进行矫治,以促进其康复和再社会化,从而取代以往对他们采取的单纯的惩罚方法。”①[美]戴维·S.坦嫩豪斯:《20世纪初少年法院的演化——超越完美建构的神话》,载[美]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伯纳德·多恩著,《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0页。实际上,少年法院的创设即是对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是司法历史上首次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审判时分离,由专门的少年法院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处遇。与成年人法院相比,少年法院对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能够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向未成年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保护。
其实,少年法院创立之初就有两种为其提供理论支撑的理论,即“干涉主义”和“转处理念”。②干涉主义强调由儿童福利专家实施的新计划所带来的积极优点,干涉论者认为建立以儿童为中心的少年法院是设定一种积极规划的良机,这种规划既能防卫社会又能治愈那些犯了罪的儿童;转处理念所采取的方式希望避免刑事法院对少年的伤害。伴随少年法院的发展,前者提倡的正当化理由与法院的现实功能和合法原则及均衡原则均发生冲突,当这种冲突逐渐加剧时,转处理念作为少年法院创设与持续发展的正当化理由,就以一种少年法院独立运行的核心解释原则而出现。少年司法的转处理念原则不仅符合青少年成长的现代理论,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相契合,也与作为青少年罪错回应的程序公正及均衡原则相适应,遵循了少年司法的规律。③Zirmring,Franklin E.(2000).The Common Thread:Diversion in Juvenile Justice.California Law Review,88(6),P.2480.
从转出层面而言,司法转处即指将未成年人从刑事司法程序中分离开来,使未成年人避免遭受正式的刑事司法的负面影响。少年法院的创设是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司法实践表明,正式的刑事司法程序中的羁押、审判、服刑等措施,并不关注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更无暇顾及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背后的家庭监护和教育等问题,难以实现刑罚目的,甚至适得其反。支持少年法院的改革者们认为,刑罚是一种不必要的严酷,羁押场所变成了犯罪的学校,纯洁的人被腐蚀,可挽救的人在慢性的犯罪道路上变得不能回头。本·林赛法官认为刑事法院就是一种“对儿童的迫害”。④Ben B.Lindsey,Colorado's Contribution to the Juvenile Court,in THE CHILD,THE CLINIC,AND THE COURT 274,(Jane Addams ed.,1925).威廉·斯特德谈到警察局时指出:因为犯罪而被拘留的10-12岁的儿童们发现警察局就是他们奔赴监狱的学前班。⑤WILLIAM T,STEAD,IF CHRIST CAME TO CHICAGO(Chicago Historical Bookworks 1990)(1894).
从转入层面而言,司法转处摒弃正式刑事司法善用的审判、监禁等方案,强调家庭和社区对改造未成年人的重要意义,从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出发,对其采用适当的处遇措施。家庭教育是影响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方式。⑥张远煌主编:《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未成年人身心和人格的发展依赖于家庭教育以及与父母的关系,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脱离原生家庭监护和影响的能力。尽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其家庭监护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但是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遇,仍然首先要考虑让其回归家庭的监管教育中。良好的家庭监护条件是治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防止再犯的根本性举措。在家庭环境之外,社会组织和团体也非常关注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尝试理解其行为背后所表达的需求,并集社会优势资源帮助和解决未成年人的需求。社会力量的支持既能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等帮助,也能提供就学、就业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二)从理念到制度
作为少年法院创立之初的基础理念之一,转处理念逐渐成为主导理念,并成为指导少年刑事立法、少年法院改革和少年司法程序变革的重要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由理念演变为制度的过程中,其在减少司法系统压力、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尊重未成年人利益和帮助未成年人成功回归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中,故其实质内涵和制度边界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少年法院独立于正式的刑事诉讼司法程序,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司法转处意味着不让未成年人案件进入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即不由法院处理;从延伸意义上而言,未成年人案件可以在任何一个诉讼阶段转处,故也包括在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对未成年人案件作出转处决定,即采“大转处”①“大转处”是指转处既包括将未成年人案件从审判程序前进行分流,也包括将未成人案件从审判阶段中和执行阶段中进行分流。概念,这也是有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采用的涵义。
以上两种司法转处在制度落实方面均需从对象、主体、条件、程序和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第一,在适用对象方面,不同意义层面的司法转处适用对象范围是不同的,对同一意义层面的司法转处的适用对象也应科学划定,依据标准可能有未成年人行为的不良程度、行为时的年龄和成长背景等。第二,在适用主体方面,两种意义层面的司法转处制度,拥有决定司法转处权力的主体范围必然不同,不同主体的权力范围和制约因素也不尽相同。第三,在适用条件方面,不仅要考虑司法转处自身涉及的主体和对象,也要考虑司法转处项目中第三方主体的主观情况和社区等机构的承受能力。第四,在适用程序方面,主要探讨的是对非释放和非劝导警告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转处,对未成年人案件司法转处前的调查报告是必然要求,司法转处适用对象的权利和义务,司法转处对适用对象的监督、考察和帮教,最后司法转处项目的中止和终止,这些程序根据未成年人行为的不良程度可能有有无和繁简之分。第五,在适用效果方面,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司法转处后评估其效果有助于针对性地调整转处项目,完善现有转处项目,为以后的司法转处项目提供经验教训,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好的司法处遇路径和回归社会的支持。
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的司法转处
为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提供明确依据和标准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以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最具代表性,辅之以相关的国际准则的规定,基本上能为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勾勒出一个较为周延的体系,故下文将从四个方面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的司法转处进行描述和剖析。
(一)转处依据的多样性且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
根据《北京规则》中第五条第一款②“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犯作出的任何反应均应与罪犯和违法行为情况相称。”,第十条第三款③“应设法安排执法机构与少年犯的接触,以便在充分考虑到案件情况的条件下,尊重少年的法律地位,促进少年的福利,避免对其造成伤害。”和第十七条④“主管当局的处理应遵循:(a)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d)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作为主导因素。”的规定,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时,需要考虑的依据有三个方面:未成年人的行为、未成年人和社会。首先,未成年人的行为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情况和严重程度,这是对行为本身的事实判断。其次,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情况是对个案更深刻的考量,与此相关的规定还有1990年《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二十八条。⑤“拘留少年的环境条件必须根据他们的年龄、个性、性别、犯罪类别以及身心健康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具体需要、身份和特殊要求,确保他们免受有害的影响和不致碰到危险情况。将被剥夺自由的各类少年实行分开管理的主要标准是提供最适合有关个人特殊需要的管教方式,保护其身心道德和福祉。”同理,对未成年人的转处必须根据其身份、年龄、性格、成长环境、具体需要和特殊要求等情况科学合理地作出。最后,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应当考虑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不仅包括整个社会的需要,还包括未成年人所处社区的需要。从价值层面上而言,未成人犯罪实质上也是对社会安定秩序的一种侵害,但是由于未成年人各方面的特殊性,在权衡二者轻重的时候,决定主体更倾向于优先考虑未成人的需要而让社会的整体利益作出适当的让步。从操作层面上而言,适当的让步表现为社区在可接受范围内的配合,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具体方案很多情况下依赖于社区的支持和帮助,故考虑社区的条件和意愿对于保证司法转处的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北京规则》多次提到要将“未成年人的福祉”视作对其进行转处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且《公约》第四十条第四款再次提到“儿童的福祉”。“未成年人的福祉”即《公约》第三条第一款⑥“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确定的“儿童的最大利益”,这意味着进行转处前或者转处过程中都应当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增进少年的福利。①宋英辉,何挺,王贞会:《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观护办法,即便是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对未成年人的综合情况进行考量后如果需要也应当进行转处,这使得转处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更具积极意义。
(二)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且尽早进行转处
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与转处依据的多样性密不可分,未成年人的福祉是进行司法转处的核心依据,因此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应当是基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考量,尽可能尽早地让其脱离正式的司法程序,这意味着不论未成年人处于何种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转处。1997年《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行动指南》第十五条的规定,②“应对现有的程序进行一次审查,如可能应制定转送教改或其他替代传统刑事司法系统的措施,以避免对受到犯罪指控的青少年实行刑事司法制度。应采取适当的步骤,在逮捕前、审判前、审判和审判后阶段全程范围都可采用广泛的各种替代和教育措施,以防止重犯并促进儿童罪犯在社会中改过自新。”是国际准则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转处阶段的全程性。审前阶段可能包含对未成年人造成严重影响的逮捕和羁押措施,因此国际准则要求将逮捕作为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的一个重要的程序节点,即未成年人一经逮捕,依据《北京规则》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官或其他主管人员或主管机关应不加拖延地考虑释放问题。”《北京规则》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了审前起诉机关拥有“随时撤销诉讼的权力”,尽可能地避免未成年人遭受法院的审判,尽可能避免使未成年人成为罪犯、被判处监禁刑的可能性。同时该规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关当局应尽最大可能并尽早采用从监禁机关假释的办法”,为审判后进入执行阶段的未成年人提供了及时转向的路径。从措施上来看,虽然对成年人也有撤诉和假释的规定,但是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要求都是“尽最大可能”、“尽早”且“随时”。
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将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及执行等程序阶段纳入转处的适用范围,③钟勇,高维俭:《少年司法制度新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每个阶段均有不同主体作出相应的转处决定,这反映出转处完善的静态体系,更反映出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是基于对其福祉的关怀、对其最大利益的考量,因此一直对未成年人的情况保持动态关注。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从形式上来看,是为未成年人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设置了环环相扣的拦截线;从实质上来看,是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严密紧实的保护网。
(三)决定主体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且自由裁量权较大
根据国际准则的规定,对作出未成年人转处决定主体的首要标准即是专业化和专门化。根据《公约》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的当局或机构必须是专门建立的。《北京规则》第六条第三款④“行使处理权的人应具有特别资历或经过特别训练,能够根据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明智地行使这种处理权。”和第十二条第一款⑤“为了圆满地履行其职责,经常或专门同少年打交道的警官或主要从事防止少年犯罪的警官应接受专门指导和训练。在大城市里,应为此目的设立特种警察小组。”对从事少年司法的执法人员的专业化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执法机构第一次接触涉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对社会的看法。而且,任何进一步的干预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初步接触。而警察又是与进入少年司法领域的未成年人进行接触的第一类主体,因此具备专业的处理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知识和素养是非常必要的。决定主体的专门化和专业化是保障转处效果的基本条件。
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的主体,还有检察机关、法院、仲裁庭、委员会或理事会等其他机构,这在《北京规则》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得以体现。⑥“应授权处理少年犯案件的警察、检察机关或其他机构按照各法律系统为此目的规定的标准以及本规则所载的原则自行处置这种案件。”同时该条规定的“自行处置案件无需依靠正式审讯”这一点表明决定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的主体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对其有一定的约束,即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应征得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且方案在执行前需经主管当局审查,但前者通常会同意,后者通常会审查通过,故决定主体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不论从实体还是程序层面来看都是相当大的。
(四)转处方案的多样性且适当进行干预
具体的处遇方案在《北京规则》第十八条第一款中有明确规定,⑦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有些可以结合起来适用的这类措施包括:(a)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intermediatetreatment)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这些方案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已经施行且证实有效,但并未提及更多的实施细节,故国际准则既鼓励以上方案的推广和发展,也不排斥各国根据国情进行探索。该规则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①“为便利自行处置少年案件,应致力提供各种社会方案诸如短期监督和指导对受害者的赔偿和补偿等等。”也表明目前实践中的转处方案大多依赖于社区执行监外教养的办法,因此社区在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些转处方案不仅是审判前的转处方案,而且是审判后对未成年人进行假释、释放之后根据其情况和需要施行的转处方案。
转处方案的成功施行不仅立足于决定主体或主管当局对未成年人自身和行为的综合考量,而且立足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自愿配合,②“《北京规则》第11条第3款规定的“任何涉及把少年犯安排到适当社区或其他部门观护的办法应征得少年、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但此种安排决定在执行前需经主管当局审查。”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只有同意和接受转处方案,方案才能顺利开展并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转处方案的实施应取得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真正同意,而非迫于没有更多办法的无奈选择。本规则第十八条第二款再次强调了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转处方案的配合。③“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此外,转处方案施行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主管当局可以根据掌握的每一个未成年人的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完成转处的目标,未成年人得以成功教养且回归社会,终止对未成年人的任何干预。
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本土化思考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现状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主要由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这三个阶段构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也应当在这三个阶段进行。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因有限的自由裁量权难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而且,未成年人警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公安机关的相应探索难以展开。我国第一支未成年人检察队伍和第一个少年法庭建立之时,便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进行着不懈尝试和探索,因此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主要由检察院和法院进行。检察院对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标志性举措便是附条件不起诉,2012年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中有明确规定。
相较于检察院,法院对未成人施行的司法转处方案更加灵活丰富。最高法于2014年发布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典型案例98例,④《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1月24日发布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典型案例98例》,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3447.html,2016年4月8日。包含62例刑事案件,其中未成年人涉罪的案件54例。每一个案件通过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和案例评析较全面地描述了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细节,梳理这54例案件,基本上能够勾勒出法院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的全貌。
第一,在这54例案件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无一例外均宣告缓刑,这是我国法院最常用的司法转处方案,法院在宣告缓刑时,根据情况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案中的未成年人通常会宣告进入特定场所的禁止令或接触特定人的禁止令。第二,赔礼道歉或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也是每一例案件中必然出现的方案,但在“方某某等抢劫案”中也出现过“向国家预缴罚金”的方案。第三,监管帮教也是法院最常用且最重要的一类司法转处方案。监管帮教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五类:家庭监管帮教、学校监管帮教、社区监管帮教、矫正机构监管帮教和工厂、企业等监管帮教。家庭监管帮教即法院责成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对未成年人进行管教,在“马某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北京海淀区法院还监督马某某的父母在规定时间内接受法院提供的亲职教育。学校监管帮教大多是指未成年人的原学校愿意接受其返校,通常学校会建立监管组织或专人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管帮教。社区监管帮教是由社区中的邻里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督帮助和教育,包含义务劳动等内容。矫正机构的监管帮教由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开展集中教育、心理矫正,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帮扶。工厂、企业等监管帮教较为典型的是上海闸北法院与上海市宝山区政法委、检察院、社区矫正部门共同设立的“未成年人成长之家”和广东深圳市宝安区法院于东莞某文具厂设立的“青少年教育基地”,工厂、企业为未成年人提供食宿和劳动技能培训,法官对未成年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听取未成年人的思想报告,与工厂、企业的负责人访谈等,关注其表现,工厂、企业也可以与矫正未成年人达成就业协议,为其提供就业岗位。此外,有一定的专业人员和机制对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加以辅助。例如,广东省顺德市法院在判处未成年人刑罚之后及时安排有多年帮教经验的护航志愿者对其进行跟踪帮教;广东省湛江市矫正部门对未成年人建立通讯监管措施。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本土化思考
以上所述的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典型案例,呈现出来的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背景下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的最高标准。与国际准则相比,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从实质上而言,这些差距是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中存在的本源性问题,以及补足差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1.转处依据:以未成年人福祉为中心与以成年人司法制约为中心
国际准则要求在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处时,未成年人的利益优先于其他因素。这一点在域外诸多国家均依托于较为独立且完整的少年司法体系而得以实现,从警方阶段、检方阶段到法院阶段和执行阶段,均以未成年人的福祉为中心。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直至2014年11月底,全国共设立少年法庭2253个,合议庭1246个,少年刑事审判庭405个,综合审判庭598个,共有7200多名法官专门从事少年法庭审判工作。①《最高法:各地都要建少年法庭》,新京报数字版,2014年11月26日第A16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11/26/content_549040.htm?div=-1,2016年4月10日。目前我国最高法院对于少年法院或少年刑事法院的改革思路并不明朗,导致地方持观望态度,加之各地未成年人案件数量显著下降,部分地方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各类法庭不同程度地萎缩或消失。因此,在成年人案件量如此之大的形势下,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人员或调离或兼办成年人案件。
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成立我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至去年12月底,已有12个省级检察院和960多个市级检察院、基层检察院成立了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此外,安徽、河南、辽宁等地的一些市级检察院,将辖区内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统一指定一个基层检察院办理。”②《最高人民检察院设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新华网,http://www.bj.xinhuanet.com/hbpd/fz/yw/2015-12/24/c_1117568621.htm,2016年4月10日。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建设的情况要优于少年法院专门机构建设,但是各地尚处于专门机构的初步建立阶段,机构内办案人员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和执法方式有待于提高。
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虽然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但其主要补充了“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诸如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没有的制度,在刑事诉讼环节的推进部分,仅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此外没有更多特殊内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主要是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而逐步推进的,从批捕到起诉到审判和执行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的严重性和人身危险性都是决定的主要因素,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然而,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更多的应该考虑未成年人的福祉,其行为并非首要考虑因素,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更应该秉持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尽可能尽快施行,不必囿于成年人刑事程序的限制。但是,我国目前置于成年人为主导的刑事诉讼框架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显然无法摆脱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控制和影响,这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面临的最根本性的障碍和挑战。
2.转处主体、阶段:在司法转处中公安机关得以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我国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的决定主体和阶段与国际准则的要求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差距和缺陷,即公安机关和侦查阶段的缺位。就域外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进入司法领域的未成年人涉罪行为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案件量占比较大的身份罪是重要的部分。身份罪意味着实施行为被视为不合法仅因为行为人是未成年人,即儿童在他们的未成年时期拥有这样一种身份,且因此而被加以诸多特殊限制。行为违反了那些特殊限制规定就构成身份罪。③[美]李·泰特尔鲍姆:《身份罪与身份犯》,载[美]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伯纳德·多恩著:《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76页。“身份罪行为要求违反了如下几类规则。第一类包含了仅针对青年人的禁止性规则(‘不得为’,诸如此类),例如法律禁止那些特定年龄以下的人饮酒或某一时间后在街上逗留。第二类包括要求对象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的命令性规则,例如儿童应服从他们父母或监护人的命令。违反此类规则可能显示出儿童是‘顽愚不化的’或‘桀骜不驯的’。第三类规则针对被认为是‘恣意妄为’或‘在懒惰和罪行中长大’的年轻人。这些儿童或许并未违反任何为他们设定的特定规则或违反父母特定的命令,但显示出在一些情况中已经或可能做过错事。”构成身份犯的未成年人主要由警方通过释放、劝告、训诫等方式进行转处。故域外关于身份犯的规定充实了警方对未成年人的转处任务。
在我国,域外的身份罪实则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和第34条规定的内容,我国并未将这些行为入罪,故进入司法程序的行为均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只能遵循严格限制逮捕和监禁的原则对未成年人进行有限的正当处遇,除此之外,刑事司法领域在侦查阶段并没有留下太多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的机会和空间。
虽然我国侦查阶段对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基本处于空缺状态,但是也不应为了司法转处而扩大未成年人入罪的可能性。因为域外国家对于未成年人身份罪的管辖经历过一个较大的转折,最终保持现在的平衡状态。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前叶,少年法院诉讼时间表中的身份罪审判占据了至少1/4,在一些统计数据中,甚至占到了1/2,然而60年代至70年代,不少司法裁决和评论家们开始质疑少年法院程序上的非正式性所具有的优点,反思那种认为少年法院的干预是仁慈、良性的而非惩罚性的,以及少年法院在救济策略上的有效性。同时,标签理论的支持者也认为将实施了非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贴上罪犯的标签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福祉是非常不利的,对于犯有身份罪的未成年人的干预是值得怀疑的。甚至1976年司法管理研究所——美国律师协会的少年司法标准项目《关于非犯罪不良行为的标准》提议取消少年法院对于身份罪的普遍管辖权,赞成通过一种主要基于自愿参与的服务网络,将司法干预限定在有限的和特殊的情形下。美国《少年法院法》认为将专门机构矫治项目或个别化处遇适用于没有参与刑事不法活动的未成年人并不恰当。①参见[美]李·泰特尔鲍姆:《身份罪与身份犯》,载[美]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伯纳德·多恩著:《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75-191页。因此,对于域外的身份罪或我国的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不论是否进行司法转处,都无须将其纳入司法范畴而急于干预、严加干预,这或许是更好的选择。根据域外的经验和中国刑事司法现状,公安机关无须过于积极地参与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
3.转处方案:社区功能分析与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根据国际准则的要求,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之后,主要发挥社区帮助监管矫治的作用,社区功能的发挥对于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大陆的社区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直到2000年,国家民政部发布《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才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②吴晓林、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然而,社会分工细化,职业群体结构多样化,人口规模较大且流动性强导致城市社区成员异质化程度较高,影响了城市社区的建设及其相应功能的发挥。农村社区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也呈现出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结构不完整等问题。在我国,社区建设起步晚发展慢,无力承接国家权力转移,无力承担治理责任,因此主要依托社区辅助和支持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似乎不太现实。
相较于域外,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群体中流动儿童的比例较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对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未成年人是否转处以及转处方案有别的问题。通常非本地户籍未成年人由于缺乏监管和帮教条件,对其进行司法转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此可见,社区对司法转处所能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
此外,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转处后,大多是检察官和法官一直关注未成年人的动态,开展跟踪帮教工作,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矫治和帮助的社会工作者非常短缺。在东部地区社工群体有一定的发展,在中西部很多地方,社工的价值和意义并未受到重视且发展社工的动力和条件不足。检察官、法官的本职工作是根据未成年人及其行为的情况处理司法程序内的法律事务,他们对转处的未成年人提供教育矫治和帮助只能体现我国司法人员充满人性关怀,对未成年人的转处并非是应然的路径。一方面,他们本职工作任务繁重,无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充分的帮教;另一方面,他们并非专业的社工,无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专业和有效的帮教。
【责任编校:陶范】
Think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Localization of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Divers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8,China)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diversion is the core of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integrates experience of judicial practice in various countries to provide basic guidance and standard forjudicial diversion.Thediversion foundation ismultifariousand emphasizes the welfare of juveniles.The diversion stage be full of process and shall be taken as soon as possible.The subject is professional,diversified and has greater freedom of judicial discretion.The diversion scheme is diversified and shall be properly intervened.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diversion in China,we study the practice present situation of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nd the possibility to continue.Find that i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i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control and influence of adult criminal justice mode.Public security organization need not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diversion in crimes.As community function is very limited,unreasonable treatment should be avoided as far as possible.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Diversion;Adult Criminal Justice Mode;International Standards;Localization
DF8
A
1673―2391(2017)01―009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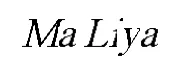
2016-09-13
马丽亚(1992—),女,山西吕梁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事诉讼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未成年人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