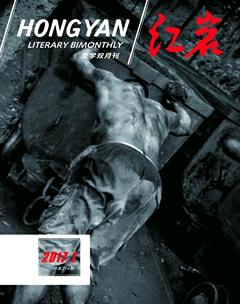山坟(外一篇)
筱敏,1955年生于广州。主要作品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长篇小说《幸存者手记》和散文集《阳光碎片》、《成年礼》、《捕蝶者》和《涉过忘川》等。
三嫂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大姐未满两岁,而刚出生的婴儿是我二姐。那时母亲在广东新兴县人民政府工作,公家便从新兴县城外的一户农家,请来了三嫂。1950年代初共产党干部施行供给制,从住房家具到口粮零用,都由公家统一配给,薪水这个东西,要到1955年才有。三嫂到我们家带孩子,也是由公家配给,每月酬劳五元,那时的币制叫五万元。“公家”这个词现在我说起来有点别扭,那时却是个时兴词,连三嫂这样的农妇也耳熟能详,它指的是政权,或说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三嫂原住的村子叫南外村,大约是县城南门外的意思。她的丈夫早早离世,一个儿子十几岁便去往海外打工,家中还有一个女儿,约八九岁。三嫂给我们家帮佣的一点收入,用于抚养她的女儿,供她上学读书。
三嫂就这样成为我们家的成员,须臾不可缺少,与我们朝夕相处达十年之久,带大了我们姊妹四人。实际上,她比母亲更可依赖,依靠,比母亲更知我们的饥渴,冷暖,她完全是我们的家人。家里最贵重的东西是一个小红匣子,里面装着粮本,各种票证,钱。简单地说,这匣子是我们一家的生活之本,它就由三嫂掌管。三嫂不识字,却能记得清楚各人的粮食定量,各种票证的名目和它们所对应的物质数量,以此打理我们一家数口的生活,从没听说出过什么错。
三嫂做活时,用一条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她的背几乎没有直过。她把我二姐背到四岁,然后背我,到我两岁,又背我妹妹。按照我母亲的描述,母亲总是赶在外面工作,哺乳期需要两头赶,每一到家,三嫂便把孩子交给她,同时端出饭菜,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哺乳,一边还要盯着闹钟,时间一到,她便放下碗筷,把怀里的孩子递给三嫂,匆匆又扑出门。
1955年初,母亲离开新兴县,迁往广州与我父亲团聚,三嫂便随我们家一同到了广州。那时新兴到广州的路很远很周折,对于三嫂来说是离乡背井,三嫂的心里当然和我母亲不一样,广州对于她是全然陌生的所在,她是为了带别人的女儿抛下自己的女儿。当时母亲是个孕妇,正怀着我,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其中一个还生病发烧。三嫂担着行李,用一个热水瓶装上粥,准备路上喂给发烧的孩子。她们站在铁轨边上等过路的火车,小站之小连站台也没有。火车之后是轮渡,之后再换长途汽车,又或者是汽车,轮渡,再到汽车,三嫂自己也记不清了。她记得的是,站在江边等轮渡的时候,风把人变得僵硬,十个手指都不会伸展。我母亲对她说,这个孩子烧得太厉害,怕是不能拖到广州了,我要马上带她去看医生。母亲把全部家当交给三嫂,让她带着我大姐上轮渡,先去广州找我父亲。我母亲作出这个决定,一点犹豫也不曾有,因为三嫂完全就是我们的家人。
所有人称呼她三嫂,我父母这样称呼,我们姊妹也这样称呼,这两个字叫起来很亲切,我甚至觉得那音调里带有撒娇的成分,这是我们在父母面前所不敢有的。等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照料一個孩子有多么操劳,而三嫂要操劳的还得多上几倍。做饭洗衣不必说,还要担米挑柴,把黄泥和煤粉揉在一起做煤球,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为了给我们买上一点肉、蛋和副食品。三嫂的手是粗糙的,掌上的沟壑密得可以吸水,我们当中谁流了眼泪,她会用手在那哭脸上抹,三两下泪水就干了。她的指关节像老树的疤痕,拉不直,指甲倒像崩裂过的岩砾,没有一个光滑平整。我以为人到老了都会那样,几十年后我也老了,才知道并不是的,那样的手指其实全是疼痛。而三嫂的手却能给我们止痛,我们肚子痛了,三嫂会在手心点一滴生油,搓热手心给我们揉肚子,直揉到红红的发热。我们哪里磕碰青了肿了,她也那样给我们揉,直到疼痛缓解消失。她用枇杷叶子煮水,给我们治咳嗽。她用大铁盆盛上热水,搓衣板横架在铁盆上,把我们当中生病的那个搁在板上,让蒸汽给发汗退烧。
我记事的时候,三嫂的女儿已经在广州念书,不久便进了工厂工作。周末她会到我们家来过,和我们一起玩,我们叫她阿姐。她把长辫子搭在我和妹妹肩上,让我们假想自己也有这样漂亮的辫子。
到我妹妹三岁,公家规定不能请保姆了,三嫂求我母亲说,你再生一个吧,再生一个就是儿子了。但我母亲不愿再生了。在我们这个国度,生不生孩子不归个人决定,而属于国家大计。我这一代,生孩子需要报告组织批准,必须持有有关部门发给的一张准生证。我母亲那一代,国家提倡的是英雄母亲多生育,不生孩子需要报告申请组织批准。母亲打报告,三嫂小声嘀咕,你看楼下那家,生六个了,二门那家,都九个了,公家不会批准的。但母亲一个报告再接一个报告,公家终于批准了。几十年后三嫂对我讲起这件事,眼眶里还是湿的。
这个时候正好是1960年,大饥荒降临了。那三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明显减少,从1952年到1958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浮动在1700万到1800万之间,1959年却一下缩减到1300万,1960年是1400万,1961年是1100万。饥饿的父母难以喂养孩子,这大约是母亲铁了心的主要原因。
城市人是有口粮定量的,即便以各种名目消减,也比农村人要好过得多,何况我们还是住在军队大院里,供应算是相当优越。但还是饿。院子里但凡有一点土的地方,都变成了菜地,种上番薯南瓜之类可以充饥的东西。更多的面积种的是君达菜,因为它速生,厚实,顶饥,我们叫它牛皮菜,三嫂叫它猪乸菜,说是她在乡下喂猪吃的。虽说现在的菜摊不时也能看到这种菜,正如也能看到番薯叶和南瓜苗一样,但我以为必得把它作为主食吃上一些日子,并且没有油和佐料,才算了解它的滋味。
大约因为公社化之风劲吹,大院里办起了幼儿园,一来可解决家属的就业问题,二来也解决我们这些小孩子的问题。我和妹妹进了幼儿园,三嫂也作为职工进了幼儿园。有三嫂在,幼儿园跟家便没什么两样。周一的早晨,我和妹妹拉着手,头也不回走出家门,一点无需母亲操心。三嫂会等在幼儿园门口,把她自己口粮中的一个黑馒头掰成两半分给我们。饥饿大约和眩晕是同伙,我总是赶不开眩晕。一天傍晚,照例对着碗里的一小坨双蒸饭,里面照例黑黑黄黄不知掺了什么叶子,我竟然就不饿了,反倒想要呕吐,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里,三嫂守在我身边,我就闭上眼睛再睡,觉得舒服得很。这个病房住着我和妹妹,三嫂是先带我妹妹住进来的,几天之后我也来了,于是她一并照看我们两人。病房外面的草比人高,某天听到草后面的坡地里声音很乱,有人喊,狼,狼,打狼,快打狼。因为有三嫂在,我倒也不怕,就趴在窗子上看,看见深草后面许多晃动的锄头和棍子。三嫂说,现在的狼也好饿啊,好饿啊。她用手臂把我和妹妹团得紧紧。
大饥荒时期有许多人逃往英国治下的香港,数目虽有不同说法,但总归是成千上万。仅在1962年5月,广东当局短暂放开了边卡,允许饥民自行赴港,前后十几天,就涌过去三十万人。据说当时的广九火车站,每天都潮水般挤满企图去往边境的人们。我们居住的军队大院当然没有饥民,但不时会看见有人收到亲友寄自香港的邮包,那些铁皮的花生油罐,饼干罐,花花绿绿漂亮得很,谁也舍不得丢掉,大人们总有很多心机,把它们做成各种生活用具。这些邮包启迪人们想象外面的生活,虽说想象力有限,但无疑是不会饿饭。三嫂动了去香港的念头,她当然不敢偷渡,便依法规申请赴港随儿子生活,但法规这东西老百姓总是捉摸不透,结果是不获批准。
我们的幼儿园是一阵风起来的,没多久又一阵风散了。三嫂又去给别人家带孩子。后来三嫂的女儿有了一间很小的宿舍,并结了婚,三嫂在广州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尽管那小屋连她的床铺也摆不下来。三嫂的儿子没怎么念过书,在香港做的是苦工,却尽责寄钱回来,赡养帮补母亲。国家非常需要外汇,便出台条文鼓励华侨给国内亲人汇款,国家收了外汇,按官方汇率折成人民币付给国内的收款人,鼓励的方法是,按汇款的额度发给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叫侨汇票,凭这种票,可以到华侨商店买市面上买不到的商品。三嫂记挂我们,我们家是她走动最勤的亲戚,她来的时候,手里端一个纸袋,里面便是华侨商店里买来的面包,她把面包分给我们。我从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那样喷香,那样松软,如果纸袋里还有几点碎末,我和妹妹也会用指尖捏起来放进嘴里。看着我们的吃相,三嫂的脸上是满足的笑纹。
离开我们家之后,三嫂又背过几户人家的孩子,我已经记不清了。之后她做了外婆,又背大了两个外孙。到我结婚生子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岁了,还执意要来背我的孩子。她的背一生都没有直过。
三嫂留在我记忆中的样子是沉默的,面容和体态都静着,几乎没有声音,没有歌谣也没有故事。她话很少,笑声也很少,脸上的皱纹都是苦味。有时那些皱纹舒展一下,像小风拂过水面,就是她苦中品出一点点甘甜。有一次她指着电视里的字幕问我,那里讲“小”什么?我叫起来,三嫂你是识字的?她羞涩地笑了,说,那个不是你名字的“小”么?
好不容易熬到孙儿长大,经过一轮拆迁,回迁,三嫂家的住房松动了一点,她终于有一个小间摆下她的床铺,有一个安定的角落养老了。然而没有安定几年,外孙娶媳妇需要房子,三嫂便用一个帆布袋收拾自己的铺盖衣物,返回新兴乡间去了。三嫂叫我帮她买一个小电饭煲,说她带回去自己煮自己吃,乡下的老屋虽然几十年没有住人,收拾一下还是好的。我把三嫂送到长途汽车站,到了栅口,检票的不让我进去,我只好站在栅栏外,看着三嫂吃力地把巨大的帆布袋举上车门,心里明白三嫂老了。
三嫂是在乡下的老屋里去世的。她的侄女告诉我们,她那两天不想吃饭,或者说,吃不下饭。不过两天,就过去了。她没有麻烦别人,她一生都照料别人,从没有麻烦别人。
今年春天我们姊妹去新兴给三嫂扫墓,现在路途顺当了,轮渡之类全不需要,不过两个多小时车程。
三嫂归老的老屋是她夫家的老屋,左近是她夫家的亲戚,村中的祠堂还是她停灵时的样子。她所以叫做三嫂,依据的是她丈夫在家中的排行,这个村子和这个祠堂,是以他丈夫 的名分容留她的。我从未听她说起过她丈夫的故事,只知道他姓甘,因为他的女儿阿姐姓甘。即使三嫂,我以为熟悉,其实也并不知道她的故事。
村子后面不远处,是先人们居住的山坟,已经许多世代了。由于城镇的扩张和世事的衍变,自然已经收缩了从前的蓊郁和静稳,看上去倒像流变之中的一个孤岛,近前已有车道穿过,距离三嫂的坟头咫尺之遥,已是一片被人承包的果园。所幸坟前那几棵大树年岁够深,应该是三嫂所认识的,夜里它们若是在小风中说话,想来那口音三嫂也能听懂。
三嫂的名字我是知道的,她姓陈,名灶养,但她的墓碑上没有她的名字。墓碑刻的字是:南外 甘复园 佑东公陈氏甘太母之墓。南外是村名。甘复园是甘氏的一支,山坡上另有一些墳碑上也有这样三个字。尽管三嫂与她丈夫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至少有四十多年完全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但在这片山坟中,她只能以其夫的名字为符号,碑上的佑东公该是她的丈夫。阿姐告诉我们,她父亲的名字其实是甘佐东,刻碑的写错了。此外碑的两侧还各有一列字,左侧是立碑年月,右侧是“二十一世”。我问阿姐“二十一世”是指什么,阿姐想了一想,摇头说不知道。
清明刚过,坟上的草已很长,是雨水洗过的青绿。我们俯身拔草,烧纸钱,给三嫂烧几套四季衣衫。但愿她用得着,但愿她能收到吧。
小学
我的小学校竟然还在那条小街里,五十年了。昨天偶然走过那条小街,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五十年而不变的事物难免令人生疑。它所以能在满城的大拆大建中幸存,总是有原因的,我上学的时候听说过,伟大的革命领袖早年在广州操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曾经居住过这里。
校门依然敞开,但已经不再是学校了,操场比记忆中的小,却也还在,白晃晃的阳光凛然镀在上面。两层的旧楼还站在操场边上,还是浅黄的粉墙,想必经历过不止一次粉刷,颜色比我记忆中的要新。楼下一层曾经是一年级的教室,左侧第一间是一年级一班,第二间是一年级二班。一班的墙上有一扇窗子,非常高,仅能用于通气,就算使劲踮起脚,也不可能看到外面的风景。我所在的二班就连这样的窗子也没有。为了采光,教室的后墙是全敞开的,坐在后排的同学,弓一下背,身体就到了走廊上。这种老式的房子楼层高,仰头向上张望的时候,觉得顶上黑森森的,横排的木梁大约是岁月的颜色,纵排在梁上的木楼板也黑得深沉,没有光线能让我看到蜘蛛在不在那里结网,但每当下课铃响,便能听到头顶上马群奔腾。
班主任老师姓李,我一定不会记错,她个子瘦小。1962年是饥饿的年份,几乎每天两节课过后,我便开始眩晕。但即使在普遍的饥饿之中,李老师的瘦小也还是过于明显。那时不少女孩子入学时间较晚,全班一起立,李老师就失去了身高的威严,于是我特别能感觉到她脸上的威严。大约因为作业得了几个五分,李老师偏心我,派我做班长,全没料到这其实是让我每日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上课铃响我便得站到讲台一侧,面朝全班同学,等着老师出现在门口,待她点头示意,我便喊起立。我不敢告诉她我是多么害怕这样一件事,只好一直忍受害怕。我默念着起立起立起立,唇齿也加入无声的练习,有时她的示意突然打乱我的节奏,我就变成口吃。
大叶榕或许不是从前那棵了,因为它不应该在围墙外面,但看树干的年龄似乎又是,横在我记忆中的,还有眼前这特别壮硕的横枝。从前操场边上立着两支粗大的竹竿,就是固定在榕树的横枝上,那是我们玩耍的器械,双手和脚掌变成小兽的爪子,从竹竿底部一下一下攀爬到顶部,然后刷的滑下来,这种乡村孩子擅长的游戏,也是我们体育课测试的一个项目。体育老师手持一个秒表,计算我们跑步的速度,也计算我们爬竿的速度,颈上还挂一根软尺,量我们跳到沙池里的脚印。他高而且瘦,以致脸小得看不出喜怒,我们都叫他“米七”,这称谓中有钦羡他的高度难以企及的意思。
我的书包是母亲缝的,蓝布面上的两朵花儿也是母亲亲手绣的,那是她早年为自己预备的花儿,为的是等待一个她自己的时辰。后来革命来了,花儿就折到箱子底下,日子一天比一天粗糙,枯涩,她自己绽放的季节就错过了。她把那块蓝布缝成我的书包的时候,心境肯定和在布面绣花的时候大不一样。走在上学的路上,我时常会用手指摩挲花儿的针脚,指尖就能知道那是花瓣还是叶子。
那是饥饿的年代。米和各种菜叶树叶合在一起蒸成饭,再加水蒸一遍,看上去量增多了,叫双蒸饭。树叶不仅是我们的主食,更是我们的零食。早晨上学,街面的落叶都是新的。有一棵树,至今不知道叫什么树,树叶是酸的,我每天捡一把酸树叶揣在兜里,做为零食。还有一棵树,许多年后才知道叫石栗,叶子大而厚,结出的果子模样有点儿像桃子,我也吃过掉在地上的这种“桃子”。酢浆草最好吃,也就不容易让我先看到,看到的时候它必是鲜嫩的,我们叫它酸味草,轻轻一嚼就满口清汁。
课桌与生活一样简陋,桌面凹凸不平,书包里必备的文具除了铅笔,还有一块铁皮垫板,时新一点的是塑料垫板,把它垫在作业本的纸页间,才能写出平整的字。
同学中我记得最真切的是汤佩兰,她总是坐在前排,与我为邻。她不言不语,上课和下课都安静地呆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也一样,于是我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汤佩兰比我要大几岁,她作业本上写的字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些字工整方正,笔划很多,一行一行把方格子全部填满,但显然跟老师课上教的不一样,跟所有的同学不一样,无论语文课还是算术课,她的本子上写的都是我不認识的字。每次收作业本我都先收汤佩兰的,偶尔一次慢了一步,她的本子就飞了起来,后排的同学接住了又抛向前排,左边的同学接住了又抛向右边。我和汤佩兰在课室里来回来去跑,我听到她开口叫喊,但没听清她喊的是什么。抓住那本子,我才偷偷看她一眼,她哭了,她的眼泪是清的。
这会儿我站在学校门口,太阳暴烈,过往的记忆都被强光遮没,操场上停了几辆车,阳光在那里更堂皇了,亮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米七不会走出来了,李老师也不会,这里没有人认识我,岁月已经流变。
离开校门我拐向西面的巷子,我的好些同学曾经住在这个巷子里。侧壁的红砂岩是前朝的遗物,但青石板路不见了,换成了水泥铺的街面。街面太直了,不再是我记忆中曲曲拐拐的巷子。我没有企图找从前的旧房子,我想我的记忆是靠不住的。
而台阶下的那口井竟然还在,井旁的鸡蛋花树还在,它真的就是那口井吗?五十年前我投落一颗石子到井里,现在它是否还在那里?
创作谈
我心目中好的散文大约是,有自己的话要说,有诗性,有个人风格,文字要干净。耐读,经得起时间考研。其中有自己的话要说最重要。现实的困难是要在言与止之间迂回周折,即如一棵树屈曲成盆景,艺术是艺术了,但终究成不了大树。我欣羡自由生长的大树。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