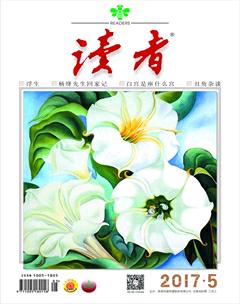浮生
任晓雯
曾雪梅

曾雪梅七岁时,喜欢趴在窗台上,仰面数飞机。飞机跟小鸟似的,翅膀不动地滑过去。时或起一记嘘声,仿佛有人吹口哨。地平线轰然颤动,团起阵阵乌云。曾雪梅觉得像是过年放鞭炮,便拍手欢呼。母亲兜头一掌道:“看啥西洋镜,东洋鬼子投炸弹呢,把闸北炸平了,还在南京路上开枪杀人。回头捉牢你这种不听话的小囡,扯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
是年,曾雪梅已开始念书。父亲说:“女小囡学点文化,以后不被婆家欺负。”送她到私立小学,读至十三岁,又报名爱国女子中学。尚未入学,校舍便被日本人炸坏。曾家弃了房产,逃到法租界,在寺庙院子里搭了个滚地龙(简易住房——编者注)。
曾雪梅断续上了四年夜校。父亲道:“家里情况不好,你相帮分担点吧。”她便辍了学,由邻居引荐,到日本人的厂里做工。厂子在川公路,叫福助洋行。曾雪梅定在门口,不肯进去。邻居反复诘问,她才憋红脸道:“日本人,会吃小囡吗?”
曾雪梅过了考试,因为识字多,被派作车间记录员。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外加大米、菜油、黄豆各十斤。逾数月,养得颊圆颐润,头发也黑了回去。工头二本松是日本人,一对近视眼,腰背微微佝偻,走起路来,拖着两只扁脚。他的夫人千代子,也在车间工作。一次,千代子邀了几个中国女工去她家吃饭。曾雪梅走过南京路时,渾身觳觫,谎称不舒服,让同事们先行,自己坐到街沿上,掏出用来送礼的苹果,边啃边想心事。食罢,核子一扔,返身往回走。
旬余,有个机修工来车间做工,嘴巴不清爽。曾雪梅道:“钟阿宝,我又不上车子,机器坏了关我啥事。你再说话不二不三,我就骂你八格牙鲁了。”钟阿宝不怒反笑:“曾雪梅,你觉得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曾雪梅睃一眼围观的同事,道:“宁波猪猡,我才不上你的老当。”钟阿宝跌足道:“大家都是中国人,又是同事,屋里厢也住得近,说话做啥这么难听。等着,有你后悔的。”
曾雪梅回得家来,说与母亲。母亲道:“当然中国人好,有啥不敢讲的,随他告到东洋拿摩温(工头——编者注)那里去。”曾雪梅道:“我也不晓得。听说中国工头都打人的。二本松不打人,也不拖欠工资。日本大班来视察时,还给每人发十块洋钿奖金。”母亲嘴唇一抖道:“小恩小惠的,就把你收买了。若不是鬼子杀人放火,你爸还在四马路小菜场卖甲鱼呢,那样我们家就不会穷,你就会一直念书,保不准念成个挺括的女大学生了。”曾雪梅默然一晌,问:“那为啥让我去日本工厂做事?”“嘁,赚鬼子的钞票,也是爱国啊。”
旋而到月头,发了工资,曾雪梅背回大米和黄豆。母亲借了一座台秤过磅,忽道:“好像少脱了。”曾雪梅听得母亲口齿有异,抬眼见她嘴巴歪斜,唇角拖下一线涎沫来。“妈,怎么了?”母亲想伸手去擦,却感觉天花板一动,面孔已然贴倒在地。
一日工间休息,千代子问曾雪梅是不是有心事。曾雪梅犹豫了一下,说:“我妈跌了跤,半边身子僵掉了。找过郎中,不见好。现在她不肯吃饭,说要早点死掉,帮我们节省钞票。”千代子取了六十块钱,让她给母亲找西医,补营养。曾雪梅推却着,收下,回去说与家人。母亲回光返照似的,嗓门铿铿响道:“我是个强硬的人,不讨日本人便宜。”一口气接不上,眼乌珠翻了白。曾雪梅扑过去,见一滴浊黄的泪水滑过母亲的太阳穴,在鬓边略作停滞,吧嗒滴落于枕上。
曾雪梅把钱还给千代子,自此避开她和二本松。母亲过世不久,大哥和一家电话公司的女职员结婚,住上公司分配的大房子,把父亲也接了去。阿嫂给曾雪梅介绍了在南华酒家当厨师的老乡。谈了一年多,请亲友在扬子饭店吃一顿饭,算是把婚结了。
婚后,丈夫建议曾雪梅辞工。犹豫间,日本投降,福助洋行解散。曾雪梅归得家来,专心养胎。忽一日,老邻居捎来二本松的信,她才晓得,厂里的日本人,都被关到了提篮桥。她瞒着丈夫,买了六包稻香村鸭肫肝,找来几张连史纸,学千代子的做派,将点心盒子包起来,用绢带扎了个蝴蝶结。
曾雪梅拎了鸭肫肝,去提篮桥探监。登记、盘问、等待。听到喊她名字,已是入暮时分。晃眼见一个灰发女人,穿着空阔的囚服,挪着碎步出来。曾雪梅“啊呀”一声,汪起半眶泪。千代子坐下,咬咬嘴唇,微笑道:“我们快被遣送回日本了。以后没饭吃,到上海来讨饭,你会给点吃的吗?”曾雪梅用力点头。千代子深鞠一躬,泪水甩在点心盒上,连史纸的颜色一摊摊深了起来。是日临别,千代子送了她一包童装,都是亲手缝制的。她本来以为,自己会在中国生孩子。曾雪梅怕丈夫见怪,留了一件电机纱短褂,其余的送去了典当铺。
三个月后,曾雪梅开始做母亲。她将电机纱短褂给大儿穿,很快短小了,便收起来,转与二儿穿。怀第三胎时,解放军来了。派出所唤了她去,“日本人撤离前,把工厂机器运到吴淞口,扔进海里了。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她说不晓得。派出所的人问道:“听说你跟日本人关系好,会讲日本话,经常骂中国人八格牙鲁?”曾雪梅道:“放他娘的狗臭屁,我顶顶恨东洋鬼子了,我妈就是给他们气死的。不信把钟阿宝叫来,当面问问。最讨厌男人家背地里嚼舌头。”派出所的人道:“不是钟阿宝讲的,是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又盘问几句,才放她走。
曾雪梅把在弄堂里玩耍的二儿揪回家,闭紧房门,剥了他身上的电机纱短褂,剪成一条条,混着废报纸烧掉。二儿号啕不已,被她甩了一巴掌:“哭你个魂灵头。日本鬼子良心忒坏,啥人稀罕他们的破烂衣裳。”二儿道:“你说千代子阿姨蛮好的。”“呸呸,什么千代子万代子,乱话三千。当心日本鬼子把你撕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二儿嘶了一声,不再说话。
江秀凤
人人都说,江家三小姐酷肖宋庆龄。一帘垂丝刘海,鬟发低绾在后颈窝。她五岁练毛笔字。及至上学,文章写得周正。十三岁,由老师带领,出去抵制日货。江老爷恰路过,见女儿站在杌子上,和男同学一起高喊“打倒日本人”,怒极,替她退了学。江秀凤垂手喏喏,偷哭一场。
江家初住镇江。地方军变,逃至东北边的姜堰。江老爷垂亡,对江秀凤说:“八个子女里,我最对不起你。你识字最早最快,本该去苏州,读所女子中学。你心肠太软,文化最低。务必找户好人家,乱世里撑着你。”
江秀凤十八岁成亲。婆家开当铺。丈夫孙震东读过私塾,高中毕业,在洋行上班。逾数年,时局动荡,职业不稳,他跑去泰州,与人合开影院。钱财被骗失殆尽,暂搬至岳母家。
少时,日本人来。满街火药味,熏得人鼻痛泪流。孙震东不顾内兄反对,携妻挈子,逃到沙港子。当地传言:“孙震东是江纯甫女婿。江纯甫在南通做过大官。家里的袁大头、孙小头,用麻袋装。法币堆得一屋屋。”孙震东被绑票三次。江秀凤从大哥处求得两次赎金。第三次,她拖着四儿二女,跪在绑匪家门口,号啕喊穷。绑匪不忍,放人。孙震东见到妻子,兜头一耳光:“你做的好事,把我面子都落光了。”
他们回姜堰,受四弟资助,开一爿店,取名“镇太和”,从大店批了日用百货卖。江秀凤坐店理账,做警察的远房表哥帮忙罩护。孙震东想重振当铺,未遂。他从自家店里拿酒,喝得酲酲然。时或詈骂江秀凤,说她和表哥走动太密;扯住她前襟,抖筛似的甩来晃去。
江秀凤悄悄拜托二姐:“他再没工作,就要毁了。”彼时,二姐夫留美归来,就职于上海工务局,便把连襟介绍到芜湖信托局。孙震东对妻子道:“我就说吧,只要是人才,总有人求上门。你还想去托关系,哼,也太小看我。”江秀凤唯唯。
此后一段太平日子。孙震东面颊滚圆起来。他爱把孩子拢在身边,来回数点:“我养了四只光榔头,三根小辫子。家子婆亦有功劳。”江秀凤匿笑。她已鬓角藤灰,眉毛疏淡,面相比丈夫年长。
春杪,局势暧昧。信托局的同事纷纷南逃,让孙震东同逃。弗肯,举家回上海,借住五弟家。上海一夜翻天。孙震东没有工作,去做了登记。人民政府将他派至宣城,当小银行职员。工资五十五,补贴完父母,每月寄回三十元。儿女渐长,家用不够。江秀凤到街道当扫盲夜校的老师。
年余,“三反”“五反”。孙震东被人揭发旧时待过洋行。“五反”队自安徽来,搜查“孙震东贪污的金首饰”。江秀凤上交一把银勺子、一根红木文明棍、一只英国奶粉铁皮罐,给丈夫写信,叮嘱他服从国家,回音渺然。
七年后,孙震东回沪。其牙齿半落,踽踽有老态。“我是清白的,他们啥都没审出来,”又说,“是我自己辞职,不想干了。他们反复挽留我。”翌年,他脖颈水肿,胸腔疼痛,查出肺癌晚期。
冬至,后夜,月光冷黄,窗框摇动。孙震东呼吸如鸣笛。江秀凤抱紧他,感觉他浑身震颤,似有猛兽挣扎,要从他轻瘦的骨骼里出来。江秀凤的耳朵凑向他墨灰的嘴唇,听见他一字一噎说:“政府晓得冤枉了我,赔了两百块钱。我怕人偷走,没告诉你。”
孙震东落葬不久,扫盲夜校解散。江秀凤抠挖墙脚。果真埋有人民币,裹了数层油纸。油纸遭鼠啮,边角残缺。里头钞票张张霉湿,一碰即烂。江秀凤抓了废钱,撒在亡夫遗像上:“孙震东,孙震东,我忍了你一辈子。”
江秀凤找街道干部,求一份工作,“我啥苦都能吃。”旬余,如愿。到新单位报到,着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大美华绣花软底鞋。同事嗤笑:“收个垃圾废品,还要穿旗袍。”江秀凤回家,拆却旧衫,缝制劳动装。她初次穿两截头衣裤,感觉仿佛赤身裸体。
废品站二人一组。一人称废品,一人付钱。江秀凤同组的同事,以前是个阔少,因政府动员劳动力,被迫出来工作。他说:“我堂堂大学生,竟和家庭妇女是一样的工资。”终日枯坐废品站内,捧一本《新名词辞典》。
江秀凤独自出站,拉着板车,在徐家汇兜转。双目受曝晒,刺痛流泪。后颈晒伤起泡。脚底老茧厚硬,被撕剥得坑坑洼洼。一次,上门收废品,遇故人。对方注视良久,忽道:“三小姐,是你吧?”她赧然红了脸,仓皇下楼,缩立于墙边,放任自己哭个够。俄而摇摇小铃,起车前行。
江秀凤收了十年废品,光荣退休。住大儿家,朝北小间,一床、一椅、一马桶。她把孙震东的遗像挂在床前,又裁开月历纸,书写兄弟姐妹名字,粘到墙壁上。他们都不在了。大哥殁于“镇反”;二姐、五弟、六妹亡于“文革”;四弟在五七干校病重不治;小弟远赴西双版纳,在原始森林里,被一棵大树砸死。
江秀凤不明白,自己明明最没本事,怎就一不小心,活得最长。孙子孙女们,个个比她高了。她久患白内障的眼睛,望见万物模糊发黄,渐次褪色。她开始对着空气说话,叙往事,发牢騷,叹生平。有时蓦然住嘴,环顾左右,似为身外存在真实事物而震惊。
忽一日,江秀凤头脑清透,水洗似的。她甚至想起幼时,母亲教自己折锡箔。她对大儿道:“锡箔要买不掉粉的。元宝不必太大,但一定要折成实心。”大儿嗯哈敷衍,回头说:“老娘糊涂了,脑筋搭进搭出。”
江秀凤捻尽碗底米粒,端端正正躺上床。她已九十七岁,知道日子将至,因而安心。她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去日留痕摘自《南方周末》,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