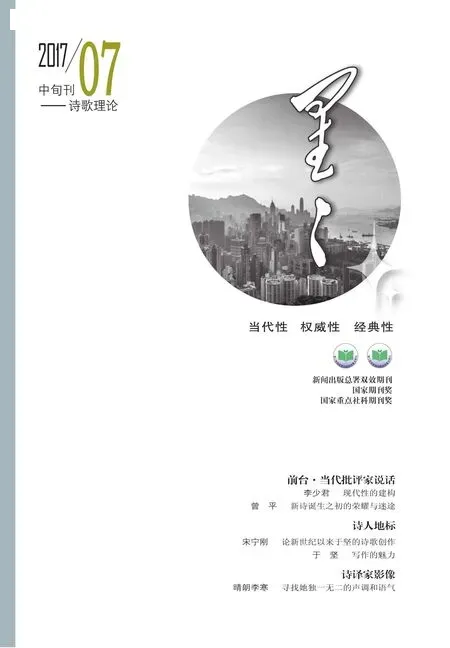沉默:心灵之诗
何方丽
黍不语
沉默:心灵之诗
何方丽
试想你正站在灿烂的春日,微风轻拂,吹来淡淡花香。你是否会驻足闭目,聆听心跳的声音?不论阳光明媚还是黑云压城,寂静的午后不免给人欲说还休之感。事实上,明媚春日与寂静午后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共同的魅力。这份魅力跨越时空,与纪伯伦的沉默互为印证。在散文诗集《沙与沫》中,纪伯伦写道:“虽然言语的波浪永远在我们上面喧哗,而我们的深处却永远是沉默的。”“情不知所起”固然是一种常态,但对好的诗歌而言,诗人总能在心灵的某一角落找到其发端。依此而论,沉默不语的心灵承载了所有诗意:或优雅、或闲淡、或热烈。于是,诗人如何将这沉默的诗意转换成动人的文字,就成为了一首诗“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对诗歌而言,“成功”或许就是让沉默的心灵至少有一个角落被真切地言说。
《我的母亲坐在那里》娓娓道来的叙述和贴近日常的语言,是典型的“黍不语”风格。诗人以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姿态,追溯自身与母亲之间的联系。在诗歌前三节,作者冷静地观察母亲孕育生养的过程。每一个过程母亲都“坐在那里”,诗人各自用一个比喻来诠释。受孕时,母亲“像土豆落在敞开的地里”,静穆无言;生产后,母亲“像被摘除果子的枝蔓”,同时拥有突然彻底松懈的身躯和怅然若失的情感;哺乳期间,母亲“像石头,在秋风中的寺庙前打盹”,诗人捕捉到了母亲疲惫中的坚强和宁静。最后一节,诗人走进母亲的世界,在寂静的黑暗中,实现了与母亲心灵的交流。母亲像阳光一样的寂静与诗人的沉默结合成一种默契——“像我们同时经历了某种消失”。这种消失或许仅限于母女之间的言语交流,女人之间的默契在这种消失中得以显现。作者也是女人,她也将经历或正在经历为人母的种种过程。所以这首诗不只是女儿对母亲的体悟之诗,更是一首作为女人沉默的、“经历某种消失”的心灵之诗。
毛子《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是一首典型的沉默之诗。诗人有意落后于时代甚至逆时代而行——“是逆时针,不是顺风车”。这种有意的逆行不是对时代的背叛,反而是一种可贵的坚守。毛子始终坚守着这个时代应有的精神内核:独立、自由、人性。他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喧哗的异样,保险柜、快递公司、有效的公章等一切代表“现代”的事物,正在侵蚀当代的诗意。喧闹嘈杂的现实让诗人对言说、对话语失去信心。诗人有意抵抗被轻佻言说、诗意残损的现实,沉默由此成为其逆行的凭借。诗人用沉默抵抗时代,但其坚守却使他难以袖手旁观,于是他以诗歌为媒介,记录着时代的诗意。读毛子的诗是一种曲折的享受,一方面,他无情地戳破时代的谎言,不堪的现实时常给安于现状的人当头一棒,另一方面,他自满于诗歌的力量,其诗中自然地存在另一个诗意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足以令读者为之神往。从这首《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子特有的“清高”以及这个时代所匮乏的沉默,而这沉默代表赤诚:对生命的赤诚,对人性的赤诚。
上述两首诗着力表现个人的沉默,风荷的《桔子》则隐喻性地表现集体沉默,我们从中似乎能隐约感受到诗人对此沉默所持的悲惋态度。桔子被时间吹黄然后咬碎、被人拿走而后供于墓碑前,诗中的桔子始终是被动的。桔子在果盘中“集体做梦”是一个颇具现实色彩的隐喻。纵观古今,人在安逸的“果盘”中集体做梦并不罕见,但当这种状态被诗歌呈现,带给读者更多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悲哀。反思?要在时代的秋风中快乐地生存,除了集体做梦好像并无他法。批判?自己似乎并未从梦中醒来。诗人残忍地指出了时代的弊病却给不出治疗的方案。集体做梦体现出的沉默与认清现实后所选择的沉默不同,前者在沉默中沾沾自喜,后者在沉默中反思质疑。当桔子梦中的故乡和初恋终于被时间咬碎,它们才从梦中惊醒,但为时已晚,“最后,它们中的几只被人拿走 /供在墓碑前—— ”。桔子集体沉默的结果是被咬碎、被支使,那么人呢?诗人没有回答,因为无从回答。
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沉默不能被消除,也无法被消除。对现实而言,沉默或许是风荷桔子式的悲惋,但对心灵而言,沉默却是毛子坚守的诗意、黍不语袒露的心灵。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本期推荐诗歌
我的母亲坐在那里
黍不语
当我从无数黑暗中,寻到她的子宫
我的母亲,坐在那里
像土豆落在敞开的地里。
当我开始一点点膨胀,一点点,与她分离
我的母亲,坐在那里
像被摘除果子的枝蔓。
当我怀揣她的汁液,耗尽她的日夜
我的母亲,坐在那里
像石头,在秋风中的寺庙前打盹。
我的母亲她,坐在那里
像一小块寂静,一小块阳光
有一会儿我们一起,走在黑暗处
像我们同时
经历了某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