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贝索和马赫的“三人戏剧”
阿曼达·格夫特
在爱因斯坦和贝索第一次见面时,爱因斯坦还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世界闻名的“爱因斯坦”。他还只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大约17岁的少年,有着属于他那个年龄的烦恼,小提琴拉得很棒。米歇尔·贝索年龄大一些,23岁,他们志趣相投。米歇尔·贝索在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里雅斯特长大,那时的他已经开始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天赋,但是由于不听话,被就读的高中开除了,只好到罗马投靠他的叔叔。因此,他与爱因斯坦有了交集。爱因斯坦当时在瑞士理工学院读书,他的教授十分憎恶他在智力上表现出的傲慢自大,为了泄愤故意刁难他,不让他进入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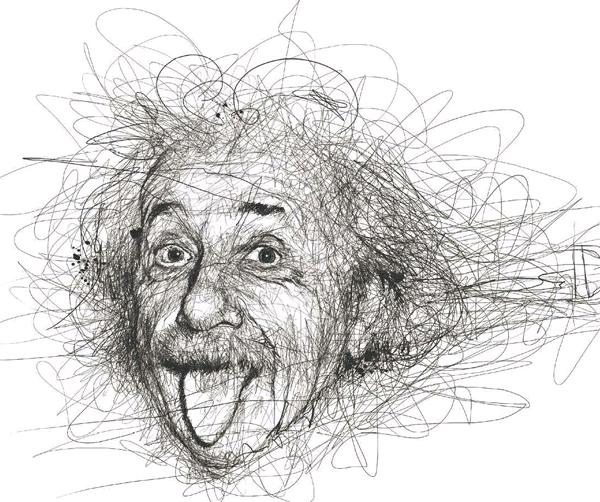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瑞士北部城市苏黎世。那是1896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来到塞琳娜·卡普罗蒂位于湖边的住所,参加她举办的一个音乐派对。当时的爱因斯坦英俊潇洒,一头黑发,留着小胡子,还有一双充满深情的棕色眼睛,属于看起来很酷的那一类。贝索则个头矮小,给人一种拘谨而率直的感觉,头上顶着一堆浓密的黑发,下巴上留着大把黑色胡须,像是一位神经兮兮的神秘主义者。他们愉快地聊天,爱因斯坦得知贝索在电机厂工作,贝索得知爱因斯坦正在研究物理学。他们迅速成了朋友——最好的朋友,真的。他们一口气谈了几小时。也许从那时起,他们就意识到彼此某些内在的东西很相似:他们都想找出事情的真相。
后来,贝索成为爱因斯坦全方位的密友,无论有什么事情,爱因斯坦都会先征求贝索的意见。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贝索是“全欧洲最好的回音壁”。贝索会提出正确的问题,从而激发爱因斯坦找到正确的答案。有时,他会做更多的事情——变身为一个合作者,提出建议,做些计算。在其他时候,他则是一个完美的傻瓜,爱因斯坦称他为呆子。有一次,贝索被指派去检查一些在米兰郊区新安装的输电线,但是他错过了火车,第二天又把这件工作给忘了。第三天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却完全想不起来被派到那里做什么了。于是,他给他的老板发了一张明信片:“请打电报,指示我要做什么工作。”
尽管贝索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贝索的伟大力量在于他的智慧,”爱因斯坦写道,“他的智慧是非凡的,就潜藏在他对自己的道德义务和职业义务的无尽奉献中。他的弱点是决策精神不足。这就是他一生取得的成就与他卓越的才能以及他那非凡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不匹配的原因。”
贝索同时也扮演着爱因斯坦良师益友的角色,敦促爱因斯坦与未来的妻子米列娃一起攻坚克难,或者在儿子面前做一个更好的父亲。在米列娃生病时,贝索帮忙照顾他们的儿子。“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跟我如此之亲近,没有人如此了解我。” 爱因斯坦在1918年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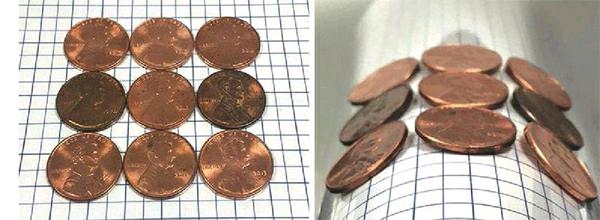
在贝索身上,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随后的几年,他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扮演着完美救世主的角色,直率地提出建议,刺激爱因斯坦,把爱因斯坦推向正确的道路,就好像他计划好了一样。“我看着我的朋友爱因斯坦与伟大的未知世界做斗争,”贝索后来写道,“看着他做着大量的工作,承受着巨大的折磨,这一切我都是见证人——一个矮小的见证人。但我这个矮小的证人被赋予了超人的洞察力。”
作为体现他们友情的第一个行动,贝索递给爱因斯坦两本书,并且坚持要爱因斯坦读一下。这两本书都是恩斯特·马赫的作品。恩斯特·马赫是这出“三人戏剧”中最后一位出场的演员。
马赫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生理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他认为,心灵和物质是由相同的基本成分构成的;自我就等同于一个幻觉,心智和物质是由某些中立的东西构成的,这种东西在一种结构中表现为实体物质,在另一种结构中表现为非物质的精神活动。
1902年,失业的爱因斯坦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以每小时3法郎的价格提供物理课辅导,一位名叫莫里斯·索洛维林的哲学学生出现在了他的门口。他们开始谈论物理学和哲学,而且根本就停不下来;至于辅导的事情,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很快,一位学习数学的学生康拉德·哈比希特也加入其中,三位年轻人形成了一个类似读书俱乐部的组织。他们阅读哲学和文学作品,并加以讨论,有时甚至为一个问题讨论一个通宵;他们抽着烟,吃着廉价的食品,还越说越激动,以至于吵醒了邻居。他们一周总有几个晚上要见面。为了嘲弄古板乏味的学术界,他
们称自己为奥林匹亚学院。
贝索在里雅斯特担任工程顾问,但是,只要有机会他都会来,作为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他成为学院的荣誉成员。在贝索的影响下,奥林匹亚学院的人也阅读并讨论了马赫。最终,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的专利局找到了一份工作。1904年,他在同一个办公室为贝索谋到一份工作,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并肩作战了。奥林匹亚学院阅读了《堂吉诃德》,这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共鸣。后来,当爱因斯坦的妹妹马娅生命垂危时,爱因斯坦也给她读了这本书。
至于奥林匹亚学院的男孩们,谁又能说清,那时的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如果把爱因斯坦比作堂吉诃德,贝索则在慢慢变成桑丘·潘沙。当索洛维林和哈比希特离开时,只剩下爱因斯坦和贝索,他们会从专利局一起走回家,边走边讨论空间和时间的本质,还有一如既往的话题——马赫。
马赫将物质与心灵统一起来的理论要求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点都是相对的,不得存在任何例外。但是,在他设想的这条路上有一个顽固的障碍:根据物理学原理,所有的运动都得相对于绝对空间才能被定义,但是绝对空间是不能相对于任何东西被定义的。绝对空间就存在于那时,它是自我定义的,就像是现实的最基础的水平——它不会有任何移动。马赫知道这个障碍的存在,并为此耿耿于怀。他批评牛顿的绝对空间概念——就是只把空间作为其本身来看待的概念——
是个“概念上的怪物”。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将所有观察者都囊括在内的“现在”。时间是相对的,空间也是相对的。
多年来,这个障碍一直困扰着爱因斯坦,所有试图从观察者的角度确定观察者相对于绝对空间是否静止的实验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对他能够想到的每一个实验,大自然似乎都有一个绝妙的应对技巧来掩盖任何绝对运动的证据。这绝对是一个彻底的阴谋。因此,人们可能都会像爱因斯坦那样,怀疑绝对空间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马赫的引领下,爱因斯坦试图确定运动并不是通过参考绝对空间来定义的,而是相对于其他运动。不幸的是,物理学法则似乎提出了另一番建议。尤其是电磁学法则,坚持认为不管观察者取何参照系,光都必须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传播。但是,如果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对的,那么光的运动也必须是相对的:在一个参考系中以每秒300万千米的速度传播,而在另一个参照系中以另一个速度传播——这公然违反了电磁学法则。
因此,爱因斯坦去拜访贝索。“今天我来到这里,是与你并肩作战,共同对付这个问题的。”一到贝索家,爱因斯坦就向贝索大声宣布。
他们从每一个角度讨论了可能的情况。就在爱因斯坦已经准备放弃时,他们又苦心研究了一番。
第二天,爱因斯坦又回来了。“谢谢,”他说,“我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5个星期内,他的狭义相对论完成了。
在那次意义重大的对话中,贝索说了什么有魔力的话?他似乎提醒了爱因斯坦,马赫的中心思想是测量一直是一种关系。
爱因斯坦和贝索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测量时间,我们会拿哪两个量来进行比较。爱因斯坦意识到,在时间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以同时发生的事件为前提的判断。例如,如果我说“火车7点到达这里”,我的意思是我的手表的时针指向7点和火车的到来是同时发生的事件。

但是人们是怎么知道两个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呢?也许你静止站着,看到两盏遥远的灯在同一时刻亮起。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如果你一直在移动,又会怎样呢?如果你正好向着A灯的方向移动,而远离B灯,那么你会看到A灯先亮,因为B灯发出的光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你的眼睛。
同时性不是绝对的。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将所有观察者都囊括在内的“现在”。时间是相对的,空间也是相对的。
随后,爱因斯坦渐渐明白了这一切:所有观察者,不管他们自身的运动状态如何,都可以看到光线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传播,这是完全可能的。光的速度是在一个给定时间内对光穿过的距离的度量。但是,时间是会根据你的运动状态而改变的。因此,即使你相对于光线移动,时间本身也会减慢到足够长,从而使你测量到的光线的速度正好是麦克斯韦方程要求的光线的速度。
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的论文《论正在移动的物体的电动力学》中向世界介绍了相对论。根据这一理论,时间和空间是可以随着观察者的相对运动减慢或拉伸的。这篇论文没有提到任何参考文献,是以这样的一段话来结尾的:“最后我想说,在我致力解决本文处理的问题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朋友和同事贝索的忠诚协助,对于他给我的若干宝贵建议,我十分感激。”
爱因斯坦很自豪地把他的大作寄给了马赫。当马赫给他回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时,爱因斯坦幸福得几乎晕了过去。“您友好的回信,给了我巨大的快乐,”爱因斯坦回复说,“我很高兴您对相对论感到满意……再次感谢您友好的来信,我仍然是您的学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但是,要看透马赫的远见,爱因斯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问题是,狭义相对论只能用于观察者以恒定速度移动的运动。而对于加速运动的观察者——那些正在改变速度或旋转速度的观察者——问题更为棘手。在狭义相对论中,你无法将伴随加速度产生的力归因于相对运动。绝对空间还在苟延残喘。
1907年,爱因斯坦取得了突破,这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他说:“在小空间区域,观察者将无法判断在引力场中他是在加速还是保持静止。”这表明,有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加速的绝对性以及绝对空间。正如马赫所想,引力似乎是使所有运动具有相对性的神秘要素。这从本质上给了引力一个全新的意义:加速观察者通过时空的轨迹是一条曲线。因此,如果加速度等于引力,那么引力就是时空的曲率。此时,距离爱因斯坦将他的广义相对论全面完善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爱因斯坦已经知道自己正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爱因斯坦抑制不住兴奋,给马赫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取得的进步,以及最新发表的论文。一个新的引力理论正在起步中,他说,一旦他能证明该理论是正确的,“你对力学基础具有创见的研究将得到精彩的确证”。换句话说,爱因斯坦做到了马赫想要做到的事情。他在1915年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第二年,马赫就去世了。
爱因斯坦写了一篇长长的、令人动容的讣告,高度赞扬了马赫对科学的先见之明,其中心点,是“物理学和心理学应该彼此分开,但不是根据它们的研究对象划分,而是根据它们之间关联与排序的方式划分”。爱因斯坦认为马赫已经接近于得出相对论,他以钦佩的语气写道,马赫“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给了我很多帮助”。
这是爱因斯坦和马赫之间亲密关系的顶点。爱因斯坦最终会否定他这位导师的纯粹相对主义, 甚至和他的“桑丘”(贝索)决裂。裂痕始于一个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件:马赫的身后话。
这对爱因斯坦来说肯定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理论气势高涨而来,又远离自己而去,去证明的恰恰是自己反对的东西。
1921年,马赫的《物理光学原理》一书出版,书中包含了马赫于爱因斯坦将其发表的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寄给他之后不久(1913年左右)写的一篇序言。
“我感到时间紧迫,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要取消原来对相对论的看法。”马赫写道,“我从送给我的那些出版物和信函中收集到的信息使我意识到,我正在逐渐被认为是相对论的先行者。我必须肯定地拒绝。”
马赫很可能看到了爱因斯坦后来才会妥协接受的现实——广义相对论没有达到它的名字的高度。广义相对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知识壮举,但它并没有如马赫梦想的那样使一切都关联起来。在广义相对论的最终版本中,似乎可以使所有运动都具有相对性,加速度和万有引力之间的等价性被证明只适用于无穷小的空间区域。如果将局部区域拼接成一个大宇宙,在这些局部区域的边缘就会产生错位(就像给一个球体铺上平瓷砖,平瓷砖的边缘会产生错位一样)。这种错位揭示了时空的曲率。这是一个普天之下皆存在的几何问题,不是仅仅通过改变视角就能解决的。每个局部的区域都是一个自相一致的相对世界,是巨大的四维冰山上永远隐藏在视线之外的一个小尖端而已,而且绝对不是相对的。
这对爱因斯坦来说肯定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理论气势高涨而来,又远离自己而去,去证明的恰恰是自己反对的东西。问题是,根据该理论,时空几何不完全是由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决定的,所以,即使你移走其中一切可观察的事物,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东西依然存在——就时空本身而言,动态依然是绝对的。它在现实世界和心灵之间创造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在其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又加入了一种纯粹的信仰,甚至是神秘主义——一个信仰四维基础的信念。这个四维基础就像一张纸,现实在这张纸上被绘制出来,虽然这张纸本身是不可见的。
爱因斯坦在1915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后,又花了几年时间继续推动马赫的观点,完全否认自己的理论与马赫的观点是相抵触的。他不遗余力地试图将自己的理论打造成马赫哲学的样子。他增加了一个宇宙常数,使宇宙有限且无边无际,但是这个宇宙常数并不合适。“所有同事都认为没必要坚持马赫原理,”他说,“但我觉得绝对有必要。”
所以,当爱因斯坦第一次阅读马赫的序言时一定被刺痛了。在马赫的序言发表后不久,1922年,爱因斯坦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说,马赫是“一个很好的力学家”,也是一个“可悲的哲学家”。他不再声称他的理论是马赫相对主义的一种。到了1931年,他完全抛弃了马赫的观点。“我们必须坚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独立于感知主体的外部世界,这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他写道。当被问及他是如何相信超越我们感官体验的东西存在时,他回答道:“我不能证明我的观念是正确的,但这是我的信仰。”在他去世前一年,即1954年,他说:“我们不应该再谈论马赫原理了。”
马赫一直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他真正的信徒从来就不是爱因斯坦,而是贝索。
贝索准确地看到了爱因斯坦在哪里偏离了马赫原理,而这将很快导致爱因斯坦误入歧途。那就是在量子力学领域。
当爱因斯坦全力以赴地应对马赫对相对论的拒绝时,物理学界已经被量子理论震动。爱因斯坦帮助物理学界发动了一场革命,现在他却拒绝加入这场新的革命。当爱因斯坦与绝对时空——一个绝对的现实——言归于好时,量子力学正在使这个世界表现得更具相对性。量子理论提出,测量结果只能由给定的实验来定义,例如,电子相对于一个测量装置可以是波,相对于另一个测量装置却是粒子——尽管其本身两者都不是,而且什么都不是。用尼尔斯·玻尔的话来说,这个理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追踪我们的体验在多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但仅仅是这种联系而已。换句话说,量子理论在爱因斯坦舍弃的那个节点上又重拾了马赫的程序。这一点,玻尔和贝索很快都会着重加以强调。
在爱因斯坦抱怨一个同事的工作时,他对贝索开玩笑说:“他骑着马赫那匹可怜的马,那马快累死了。”贝索回答说:“关于马赫的小马,我们不应该侮辱它。正是有了它,才使得我们能够穿越这趟关于相对性的地狱之旅。而且,谁知道呢,在考虑到讨厌的量子的情况下,它也许可以驮着堂吉诃德平安度过呢!”
“我没有咒骂马赫的小马,”爱因斯坦回答说,“但是你知道我对它的想法。它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事实是,在还是一个小男孩时,爱因斯坦就对隐藏的现实有着深刻的信仰,只不过这种信仰多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他4岁那年的一天,也许是5岁,他的父亲来到床边,给了他一个指南针。爱因斯坦把它握在手里,发现自己在敬畏中颤抖。指南针的针尖抖动着,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牵扯着,使他感到“在这些事物的背后,必定深深隐藏着某种东西”。现在,在他进行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演算时再次出现了这一情形。随着马赫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可以加以讨论,当他还是
一个男孩时感受到的那种敬畏又回到了爱因斯坦身上。当贝索试图引导他走向马赫、走向量子力学时,爱因斯坦责备他这位忠实的“侍从”:“看来你没有认真对待现实中的四维。”
作为一个年轻的破局者,爱因斯坦在这场破立之中拥抱了马赫的观点并乘之前行,决心创立一个纯相对性的理论,尽管他的自然现实主义观正在倾斜。难道这些实际上是贝索做的吗?贝索这位“侍从”,最后是否转向了他的主人呢?在短篇小说《关于桑丘·潘沙的真相》中,弗朗茨·卡夫卡认为,这种逆转事实上是塞万提斯的故事的关键。堂吉诃德其实是桑丘·潘沙塑造出来的,桑丘·潘沙自身无力面对这一切,所以他邀请了一位密友以实现自己心中所想。贝索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这个科学体系(指相对论)算是我欠你的,没有这段友谊,一个人永远不会有这一收获。一个人做的话,至少要耗尽那个人所有的力量。”这像是在说,感谢你为我发现了那个理论。但这个科学体系并不完整,在成功地引导爱因斯坦来到水边之后,贝索似乎没能让他喝上一口水。
贝索从未放弃引导爱因斯坦回到马赫的相对论上来。但是,堂吉诃德已经永远地放弃了骑士风度,留下桑丘一个人抵挡风车。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头顶乱蓬蓬的白发,坐在杂乱的办公桌前,努力与现实做斗争。而物理学在爱因斯坦去世后,继续大步前进着。在瑞士日内瓦的图书馆里,贝索坐在自己的书堆上,静静地、神秘地独自工作着,他如同钢针般的胡须越来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