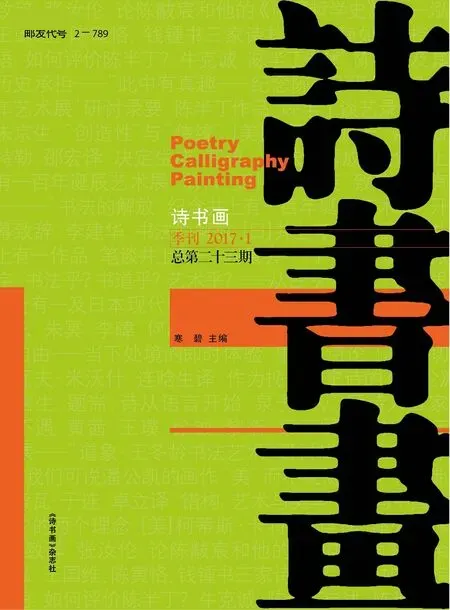王璞
阶级的黄昏
王璞
阶级的黄昏
阶级的黄昏之后
紧随着没有星星的首都之夜。
啊,夜空的锈铜镜,
煤黑色的运河;小知识分子
多年前途经,拖拉着懒
洋洋的阶级意识,
无目的:但也曾彼此激励。
记忆不外乎错失的良机,
几度烟火匆匆,暗
地里较劲,暗中
吸吮。
我真想冲出我的皮肤跃入你脏兮兮的身体。
距离的阻滞 组诗选二
1.意识流
午饭后,内陆和海洋死活不结婚。
云雨的司仪被痰卡住了,时间撑坏了,负责补妆的爱神也歇了。
大姑娘们最后一次举起玫瑰色的酒,像拎着时间的卷尺,给北大西洋量腰围。
这等于是三一律在阻挠你我搞对象。远方的你,能答应么?
午饭后有消化的意识流,意识流着母语。
沾满尘土的、干瘪的玫瑰,冒充年鉴的皱褶。但深深的是老欧洲的牙疼。耕耘者耕耘,拾穗者俯身拾穗。间或有共和与帝制勾兑于小资,在街角青涩着情调,在地铁里题诗、被捕。价格又何妨普世:与其在世界的卷轴中寻找十月的匕首,不如展读一册老连环画,在铅色的河面上,如落叶纷纷。
—但这真成了越文明越忧伤,伤及风、雨、动植物。
俯身拾垃圾者,刚吃完茕茕孑立的一餐。
3.农事诗
田野与薄雾脸贴着脸。
外省的农业安静了。像宇宙做了次深呼吸,像酿造者和不务正业者经过了一夜的长谈,膝仍促着膝。
乡镇游乐场、老风车、稻草人,
孤独。大海在泥土下汹涌。葡萄园里浑浊的浪尖、墓地里退潮时的白沫,
孤独。写诗也没用。薄雾中,我对你浑然不觉,又怎样?
但诗与孤独并不互相酿造。它们只是脸贴着脸。
休耕的地里,牲口们正沿着雾的毛边,反刍着它们之间的无缝隙但没关系。
雾转浓。我对你浑然不觉:没关系。
宝塔—给李春及一代人
宝塔亦是蜡烛。树边的湖
和湖畔的酒瓶,从中取暖。
宝塔为什么不是酒瓶呢?
你举起来,是要再饮一口?
是吹瓶哨?还是将它投入湖中,
扯开嗓子向夜生活一唱?
大我、小我风驰电掣。宝塔
忽然从周末的购物清单上立起来,说:爱!
仇恨!你的右手摸索的,不像是
鼠标或西文书,而是窗棂:推开吧,
让翻译的细雾进来。山形在多语中浮现,
犹如磨沙面的曙光—太伪劣!如此背景下
宝塔是险峰。你转而握住的黑暗,
总是它的倒影。宝塔于是向左看齐。
向你看齐。它可以是毛茸茸的,果味儿的,荧光的。但首先是红色的。
社会的性质
木窗被吹开了。
布帘浮动,好像被牧师撩起的围裙。
看不见的手
怯生生地抚摸你的肩膀。
在阶级的醋意中,
你的肉绽放出一片租界,
你的皮肤透明如水仙。
晚霞在银行业的针毡上
慢慢地凝成最初的夜气:
冰冷时如锁链,
而到了春天它就是人民的脾。
实验室里的郡主—为婧婧而作
那些失去了月亮的女生
像附录一样坐下。男人们太重。
瓜子的脆响也就是翻书的声音。
年长者的职称在睡意中被掂量,
像命令。空气变成亚麻色,
拆解着自身的轮廓;一个未解的
世界汹涌在玻璃窗上。只有
这房间,不原谅大地,悬在缄默里
并断然否认了天使的脚印。
整下午所论述的并不比接下来的夜
所给予的更多。流星在边缘。
起伏的小山,脏手帕似的云,及荒谬:
你,我们的郡主,委屈于其中,
是一场潮湿而年轻的雪。然后消散,无形,
你所剩下的座位约等于你的偏头痛。
万柳乱
1
时气颇佳,正适宜怀念那些在盗版英语教材中
消失的女研究生。她们从剑走偏锋的年龄里
努力露出的面影,注定是你的几个人生污点间
的插曲:时而是凯歌,当你像战争的胜利者那样
昂起细读的头颅;时而是乏味的催眠曲,回荡于
你奢侈的记忆的小旅店—她们真的消失了,座位
空了数月,只留下词汇书占座,像等你用答错的谜底来补空。
此地,路越走越窄;路越走越窄的犹疑者们
挤在一起,挤在了集体无意识的牛角尖里。
扁桃腺和天色一样暗红,个人信念如豆腐渣
楼盘里的瓷砖一样剥落。在这一群中“消失”,
是一门技艺。比低声说“咱们出去走走吧”
更俊逸,更必需。你有时想加入那些已经消失的
女士们,却无法把你那一片灯火通明的好地段
从你冒险的灵魂上挪开:哦,你太正版了!你太不动产了!
昆玉河边吹来了晚风,
翻动着你心头的一万个俞敏洪。
2
若这里是音乐厅,那大家的确在侧耳倾听。
但却是在室外,一首激进的钢琴曲
从天而降;激进的十指在向上帝索要
黑云,沙砾,冰雹,电,和坏脾气。
初夏的雨啊,有初夏的剧烈:
如同一个女孩子,终于认识到勉强的爱
只能勉强维持,在水房落下的急匆匆的眼泪。
人们抬起头,像是忽然翻一页挂历;
三三两两,那么安静,那么守纪律,
凑到门口,去列席这剧烈的无纪律。
而一只蝴蝶,像躲债一样,躲进了
近乎于无的室内乐。还有比它更动人的
凶兆么?虽然看似比任何命运的馈赠都
更袖珍:女同学看着它露出了男同学的笑容。
它又准备将哪一只因阅读而红肿的眼
误认为是初霁时月季的花苞?
到了这时,如果才轮到你,起身去
欣赏这场雨,你只会目睹:
高等教育的公寓楼上,几百个公费非定向的
窗户正整齐划一地向水线吼叫着肾结石般的隐私—
Mais, c’est trop tard! Trop tard!
注:万柳,北京市海淀区一地名。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此地经
历大规模地产开发。另有“北京大学万柳公寓”,系学生宿舍。
怀远—为新生命而作
人民坐着火车缓缓地靠站。
月台却留在了另一省,
目送者的眸子里曾有火苗一样的手帕。
“时间再慢也不过如此吧,出差途中阅读亚当•斯密。”
新生命的心跳却如红军
在丛山峻岭中。就这样
亚当和夏娃开始了自助游:
那可是一生一世。
七年之痒,没办法,
干脆进一步到一摩擦就疼痛:
那是他们在建设无神论的自治区吗?
专列慢悠悠地,压实朝霞中的地平线,
为了“呜—呜”的惜别。
真相是
真相是
朝阳洒满草场。
列车上有婚宴的气氛,
仿佛跃跃欲试者撞上了
红青蛙,仿佛运河也被疏浚了。
但最大的政治莫过于
海伦产下了拜伦。
生产真像是在团团葱郁中,
果子狸和推土机你追我赶。
当我植根于你时,
你化为芦苇,繁茂而脆弱,
遍及我的水系,我的十万八千里。
这等于小声宣布
最难忘的时刻是
我在你身上进退忽而失据。
于是,风波和露水
沿着虫鸣、鸟啼的堤岸,
暗暗较劲。一次新生
就是一次歌咏比赛。
敞开心扉却只开一道缝。
这等于默认此地风物都上了锁:
它们轻轻摇曳,有着芦苇的姿态,
招手时留了一手。
但真相还诸远方的早晨,
私奔的一日,短途旅程:
淡水鱼跃,虎跃,
最硬的道理跃然纸上;
万物皆备于我的茁壮,
铁轨刷刷地跃过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