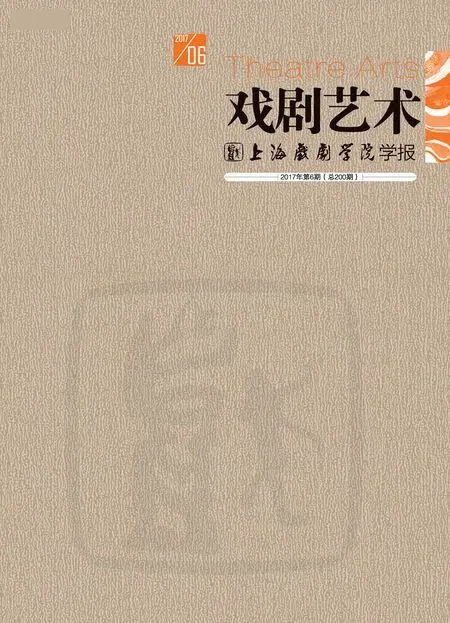从“雅”到“俗”:沈 戏曲创作的转型及其意义
沈璟是万历以后重要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他的居室别号为“属玉堂”,因而他一生中创作的十七部传奇作品,也被后人称为“属玉堂传奇”。这十七部剧作现今只存七种,即《红蕖记》《义侠记》《埋剑记》《双鱼记》《桃符记》《博笑记》。此外,胡文焕所编写《群音类选》中收录了他的《十孝记》;沈璟自己的《南曲全谱》和沈自晋的《南词新谱》中还收录了《四异记》《分钱记》《鸳衾记》《凿井记》《奇节记》《结发记》《珠串记》等作品的部分曲文。
对于沈璟这些剧作,学界深入研究不多,特别是在与其同时代的汤显祖对比之下,评价也不高。但如果将它们放在万历至明末戏曲发展的史境中考察,它们明显表现出明代戏曲创作由“雅”向“俗”的转型,其所蕴含的明代中叶后戏曲发展的内在轨迹不容忽视。
一、市井风情——题材的新拓展
在沈璟之前,传奇创作的题材总体来说不过三类:一为历史题材,是包含了历史人物、基本史实,结合历史传说和想象情节加工而成的作品。如王济的《连环记》、苏复之的《金印记》、沈采的《千金记》、姚茂良的《双忠记》等。二是悲欢故事题材。这类题材并非着重于男女主人公爱情的产生和发展,而是借由历史传说或是虚构的故事,描写生、旦的悲欢离合命运。代表作品有沈鲸的《双珠记》《鲛绡记》、陆采的《明珠记》、郑若庸的《玉玦记》、丘濬的《伍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三是反映现实政治斗争的题材,这些故事有的描写实事,有的想象虚构,是明代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下朝廷政治斗争的直接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等,都是这一类题材作品中的翘楚。
沈璟的传奇创作与上述三类题材相比,有着继承与明显的转变。“属玉堂传奇”十七种当中包含了传统题材,如历史故事《埋剑记》《奇节记》,悲欢离合故事《双鱼记》《合衫记》《凿井记》。还有较为少见的爱情题材,如《红蕖记》《鸳衾记》《珠串记》《一种情》;公案题材如《桃符记》。
但更为突出的是,沈璟创作了一系列着墨于市井生活的作品。明代初年,兵乱初定,在元代时地位一落千丈、求官无门的读书士子,又得到一条通往宦仕的康庄之路——八股科举制。在元代迫不得已走向市井勾栏的文人们,再也无需回归其中、苦度春秋了。再加上明代前期“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品经济萎缩,城市发展步伐较慢,因此以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传奇作品在明代前期的曲坛上濒于绝迹,甚至明中叶时这类作品仍少之又少。而沈璟的《博笑记》《四异记》《义侠记》等以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
沈璟在作品中反映市井生活时,还将笔触延伸至下层社会,将下层社会的人情世态也纳入了自己的作品中,这亦是他开拓新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明代前期的传奇作品多为上层士大夫所作,题材也多不脱于上层社会的风雅生活。如前文所描述的三类传奇题材中,历史题材或政治斗争题材的主人公主要是帝王将相、忠臣烈士,而悲欢离合故事题材的主人公也往往是义夫节妇。即便主人公的身份地位低下,但在作品中,他们的性格特点也仍旧是高贵风雅,其思想行为均不逾越封建纲常,连言辞应答也是张口“诗云”、闭口“子曰”,并不是下层社会人民的真实面貌。沈璟的作品却切实开始勾勒下层社会的风土人情、世间百态,如其《合汗记》便是根据元代张国宾《合汗衫》杂剧改编而成,描写了一个开“解典铺”的小商人张义一家的悲欢离合;《鸳衾记》中在描写一个小家碧玉和穷书生的爱情故事时,间杂着能言惯骗的小贩湛婆,乘人之危的无赖骆喜,强夺钱财、谋杀人命的莫弄风之流;《桃符记》中的核心人物则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裴青鸾。至于《四异记》《义侠记》《博笑记》等作品,重点描写市井生活,则更属于下层社会生活的范围。
沈璟的剧作中也因而有一批具有现实人情味的下层社会人物形象脱颖而出。《桃符记》虽然根据元杂剧《后庭花》改编而来,但是对其中的女主人公裴青鸾形象的塑造却有所加强,特别突出了她的“悲情”色彩。因家乡连年水灾旱灾,裴青鸾不得不随父母到汴京投靠亲友。不料亲友家无力接济,父亲也病恨而亡。山穷水尽的境况下,她只得卖身枢密傅忠为妾。不幸的是,傅忠之妻是个善妒成性的女子,她指使奴仆去谋害青鸾,但青鸾侥幸逃脱了。青鸾逃到一个客栈里,又被店小二图谋强奸,以致惊吓而死。通过这些情节设置,沈璟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中悲情的下层女子形象。
沈璟在题材上的新变,不仅与明前期,即便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较,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当时的顾大典、汤显祖、屠隆、陈与郊、梅鼎祚、汪廷讷等剧作家的作品,有的仍以历史故事为题材,有的以神仙释道为题材,有的则致力于爱情戏的创作。但总的看来,题材范围仍不够广泛,对于下层社会生活的反映更为少见,即便有些爱情戏在对“人欲”的肯定的同时表现了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倾向,却又不免表现出文人学士与大家闺秀的脉脉柔情。只有到明末清初的李玉、朱素臣等作家那里,下层社会的生活才更多地被反映到传奇创作中来,一大批下层社会的人物形象才更多地走上了戏曲舞台。
二、浅近本色——语言的通俗化
戏曲不同于诗词。诗词是文人把玩的高雅文学,而戏曲是演给文化水平高低不一的观众看的。因此,两者的语言运用因接受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别。明代前期,一些文人创作的传奇剧本,语言骈俪典雅,就受到了戏曲批评家们强烈的批评,徐渭首倡“本色论”以反对“案头之曲”,他在《南词叙录》中说道:“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徐渭243)。王骥德在《曲律》中也指出这个道理:“作剧戏亦须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也”;他认为“须奏之场上,不论士人闺女,以及村童野老,无不通晓,姑称通方”(王骥德154)。清初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这个问题阐发得更加清楚:“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李渔 25)
沈璟剧作的语言显然具有浅近通俗的特点。
首先在曲词写作中,他不满于“案头之曲”中描述性语言冗长拖沓、令人“不解做何语”的弊病,故而在创作中力求少用大段描述性、抒情性的曲词,多采用与剧情发展有关的叙述性语言。我们可从《埋剑记》第十五出“对泣”中姚州都督杨安居所唱的一支〔商调引子·高阳台〕窥其一斑:
战鬼啾啾,荒燐闪闪,夷歌尤自杂沓。束手孤城,愧看架上金甲。姚州越雋(隽)是唇和齿,奈溃围远信难达。纵城存,别旅舆尸愿同斥罚。
曲词的前三句用“战鬼”“荒燐”“夷歌尤自杂沓”三个特征表现了姚州战后的凄凉败况,十分简洁。接下来是叙述性语言,说明姚州战败,是因为姚州亦在危急之中,他不能前去救援。杨安居是被当做正面官吏来塑造的,他谴责李蒙轻进致败,对郭仲翔的正确建议不被李蒙采纳、并且被蛮兵生俘深感惋惜和同情,在仲翔叔父代国公死后还资助吴保安,促成他早日救出仲翔,这是一个既关心人民又讲究仁义的正直官员形象,因而这段曲词又表现了他对兵火洗劫、百姓遭难的伤感,以及“纵城存,别旅舆尸愿同斥罚”的敢于承担责任的品德。
又如《义侠记》中,武松为衙门送信回城想见兄长、后又得知兄长死讯时,沈璟写道:
远迢迢见他乡传信,慢悠悠英雄自哂。望巴巴到吾兄宅前,急煎煎欲把平安问。
——第十七出“悼亡”〔山坡羊〕
想我去匆匆程途忙奔,见你哭哀哀别离未忍。谁想生擦擦连枝锯开,哀呖呖双雁惊分阵。
——同上〔刘泼帽〕
两曲中使用了“望巴巴”“急煎煎”“生擦擦”“哀呖呖”等口语叠词,加重语气,将武松见兄心切、痛伤兄亡的思想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也通俗条畅,明白如话。
其次,沈璟在处理道白时,不仅经常使用口语叠词,还大胆采用了方言俗语入戏。如《博笑记》《假妇人》中的“老孛相”“小火囤”即是当时苏州方言,指市井中游手好闲、专事诈骗之徒。沈璟还尝试用苏州方言作为道白语言,如《四异记》“丑、净用苏人乡语”。运用了方言俗语,无疑使剧作更受下层平民观众的欢迎。在沈璟之后不久,“苏白”成了昆剧演出中常用的道白语言,清初李渔就记载了这一情况:“可怪近日梨园,无论在南在北,在西在东,亦无论剧中之人生于何地、长于何方,凡系花面脚色,即作吴音。”(李渔 104)沈璟无疑是以“苏白”入作品的先行者。
再次,结合舞台场面,使用通俗浅近的语言。如沈璟笔下“兄弟分金”的故事:一对结义兄弟发现地下有金银,两人相约共同挖掘,作品在他们上场时安排了一段对白:
净:世人结交须黄金,
丑:黄金不多交不深,
净:纵令然诺暂相许,
丑:终是悠悠路人心。哥,我们两个相厚得紧。
净:正是,人就取我们两个诨名,唤我是个赛范张。
丑:唤我做胜管鲍。
净:我每拍肩设誓,
丑:攘臂为盟,
净:愿同生死,
丑:可通富贵。……
对于二人的对话,沈璟在角色安排上是一“净”一“丑”;他们的对话,不仅通俗浅近,也富有舞台的动作性,可以设想他们在“攘臂为盟”时的那种亲密的样子。然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为了独吞这笔金银,赛范张请胜管鲍饮用了一杯药洒,胜管鲍则将利刃插入赛范张的身体,对金钱的贪欲,让他们在互相算计中真正“同生死”了。这样的结局,让“胜管鲍”和“赛范张”的诨名,具有极大的讽刺效果。这也使得浅近的语言有着不必寻常的穿透力。
又如《义侠记》第四出“除凶”写的是武松打虎,沈璟将小说的描写转换成为了戏剧场面,突出了虎的凶猛和武松在紧急情势下的威勇。在这个场面里,武松与老虎的搏斗有三个回合,开始是他躲,后来他打虎,虎走脱逃跑,他又拿住老虎并将它打死,由退而进,层次分明。武松的唱词安排也很讲究层次,开头几句表现了他在棍子打断后面对猛虎不免紧张的心情,“俺这里趋前退后忙,这孽畜舞爪张牙横”,但是他凭自己的威勇打死老虎后,就非常轻松并且幽默地唱,“你今日途也么穷,抵多少花无百日红”,显出了他的英雄本色。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评论这一场面道:“由此可见,沈氏撰作此曲,及使用口语和谚俗,已很自然,这较之《红蕖记》那种扭捏作态的写法,不但有了一定的距离,而且可以单从这两支曲子里看出武松和那只猛虎的形象和动作来。”(周贻白322)这场戏在后世一直传演于舞台,大概也就是因为如此吧!
三、“市井细民”——人物形象的世俗性
《水浒传》本来就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语),沈璟的《义侠记》将其描写武松传奇故事这部分内容搬上戏剧舞台,生动地再现了市井生活的若干方面,如王婆的茶铺、武大郎的贴卖炊饼、郓哥卖梨而寻找西门庆这样有钱的主顾等,充分体现了沈璟剧作市井气息浓重的特点。由于以市井生活为题材,其中的人物也具有鲜明的“世俗”化的特征。
例如第二十一出,王婆让西门庆猜潘金莲是什么人的妻子,沈璟安排了一支〔红衲襖〕曲,由西门庆(净)唱,王婆(丑)答:
(净)莫不是卖枣糕徐三的女艳娇?……(净)莫不是银担子李二的亲底老?……(净)莫不是花胳膊陆小四的家生哨?……(净)莫不是卖粉团许大郎的留客标?
西门庆猜测潘金莲的丈夫可能是“卖枣糕”“银担子”“卖粉团”的,这些都是市井中的营生。通过他的唱词,市井生活也被展现了出来。
《博笑记》更是直接塑造了一批形象鲜明的市井民众角色。他们或善成恶,或亦善亦恶,性格特点鲜明突出。善者如《巫举人》中的老店家,热心成全巫孝廉的爱情,鄙薄借妻子容貌诈骗钱财的无赖,一片古道热肠,外加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恶者如《假活佛》中的和尚,为了骗取不义之财,他竟给一个身材肥胖的过路官员服用哑药,又强行灌以肉汁,使之面白如玉,然后扬言活佛降世,引得远近百姓皆来瞻仰,他趁机收“香资”,中饱私囊。亦善亦恶者如《贼救人》中的一个小偷,夤夜掘墙入一赌徒家,准备窃取赌徒日间所赢银款,不想进屋之后,却看见主妇因为屡劝丈夫戒赌无效、衣饰典尽、生计无门而欲悬梁自尽,无意之中,小偷喊醒了主人,却暴露了自己。《博笑记》中有老店主帮助一对有情人逃避流氓无赖纠缠的小品(《巫举人》),有以诈骗为生的“老孛相”和“小火囤”串通一个戏子讹诈好色和尚钱财的片断(《诸荡子》),还有两兄弟奸谋卖掉嫂子却反中计谋卖掉自己结发妻子的令人捧腹的场面(《恶少年》)……是明中叶市井生活的生动展览。《卖脸客》和《英雄将》则是《博笑记》中的两个喜剧小品,前者写一个卖儿童面具的小贩,借面具吓退并除掉妖魔,并与深受妖魔之害人家的女儿结为婚姻。后者写几个强盗白天强抢了一个民女,将她放在一口枯井里以待天黑带走,恰逢一位出猎的青年将军将她救出,并放了一条恶狗在枯井中,晚上,强盗欲取民女,反被恶狗咬倒,又被将军所派兵卒俘获。
在这些人物形象的背后,也表现了沈璟的思想倾向和褒贬态度。《邪心妇》和《巫举人》分别代表了沈璟对封建道德与“人欲”矛盾的态度。《邪心妇》写一个守寡的妇女起初装模作样地拒绝一个过路男客借宿的请求,但是半夜里来了一只老虎,它以爪叩门,寡妇以为是男客求欢,便开门接纳,于是被老虎衔咬而死。很明显,这则故事是警告妇女们要有贞节观念的。《巫举人》却完全相反,它肯定了一个不守贞节的女子。这个女子的丈夫是个市井无赖,常常骗人说,她是新寡的妹妹,并假嫁于人,收取聘金后又率一帮无赖把她强抢回来。巫举人又成了那女子丈夫的猎物了,夜里,她见巫举人“心存志诚”,对她有真情实意,京城中又有很多朋友,不怕她丈夫以及那帮无赖,于是向巫举人说明真实情况,并且毅然抛弃行骗的丈夫,随巫举人连夜出走。她的这一举动违反了封建伦理道德,既不从夫,又易嫁他人,自然也不贞不节,但是作者却肯定了她的这一举动。这个故事被后来的凌濛初改编成白话小说《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收入《拍案惊奇》中,现代研究者对它评价甚高。
《博笑记》寓庄于谐,还揭露和讽刺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乜县丞》写一个县官愚蠢颟顸、终日昏睡,他去拜访一个乡绅,岂知后者也同他一样昏睡不醒,于是两人相对而坐,彼睡此醒,彼醒此睡,一直睡到天黑,二人竟未交谈一句话。这幅漫画式的小品反映了明中叶官僚地主阶级庸俗无聊的精神状态。《误鬻妻室》在这“风世”方面尤为深刻,作品写一家三兄弟,长兄外出经商,数年未归,老二和小叔竟计谋将嫂子卖给过路商人以赚得钱财。世俗浇漓已经到了为钱财置手足之情于不顾的地步。
《义侠记》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武松。作品汲取了《水浒传》中对其侠义性格的描绘,将他与封建社会政治和道德诸种邪恶势力的冲突转化为戏剧冲突。西门庆、潘金莲、王婆之流所代表的是道德邪恶方面,他们为了一己之欲,不惜杀害善良无辜的武大郎;而以张团练、张都监、蒋门神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又将武松逼上绝路。武松面对着现实道德和政治的邪恶势力,他凭着英雄之胆,与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手刃潘金莲、西门庆,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最后投奔梁山泊。本来,武松故事在《水浒传》中就令人击节、令人扼腕、令人掀髯,沈璟又将它化为具体的舞台形象,其艺术感染力更强。吕天成评论它的艺术效果说:“今度曲登场,使奸夫淫妇、强徒暴吏种种之情形意态宛然毕陈,而热心烈胆之夫,必且号呼流涕、搔首嗔目,思得一当以逞,即肝脑涂地而弗顾者。以之风世,岂不薄哉!”(吕天成)明代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有十几部,可是即使像李开先的《宝剑记》也未能像《义侠记》那样出现一问世便“吴下竞演之”的空前盛况。该剧在清代仍然不断演出,《品花宝鉴》第三十回中,在华公子府中演出,即提到《挑帘》《裁衣》等出(陈森 427),可见该剧传唱之久之广泛。
四、“雅”“俗”转向——沈璟创作转型的意义
戏曲艺术本是下层社会的产物,它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形式,同时也为下层百姓所喜爱,但是它一旦成熟起来,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上层社会的统治者以及文人士大夫们就要干涉和参与,其结果就是脱离下层社会平民观众。明代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们虽然开始创作戏曲作品,但骈俪典雅的风格非但远离下层社会的观众,甚至连士大夫本阶层也感到难于“欣赏”。因此,一些关心传奇艺术的戏曲家们纷纷批评骈俪典雅之风,如徐渭说:“《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徐渭 243)王骥德说:“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近郑若庸《玉玦记》作,而益工修词,质几尽掩。”(王骥德 122)
沈璟由“雅”到“俗”的转型,首先基于他本人理论上的自觉。根据吕天成记载,沈璟很不满意于《红蕖记》的骈俪典雅,“自谓字雕句镂,正供案头耳。此后一变矣”。“变”为什么呢?祁彪佳解释道:“先生此后,一变为本色。”
的确,沈璟在编著《南曲全谱》时,就或多或少地以曲词本色为尚。沈璟在一些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曲例中加上眉批和尾注,希望它们成为戏曲家创作本色戏曲的典范,如《卧冰记》〔古皂罗袍〕一曲:
理合我敬哥哥,敬哥哥行孝礼。昆仲两个忒和气,休忘了手足的恩义。虽然和你是两个娘生,哥哥道都是一爷养的,都是我母亲的孩儿,你缘何把这骨头都落在哥哥碗里。哎,娘也娘,你煮着一锅羹呵,缘何有两般滋味?
沈璟于此曲眉批说:“此曲质古之极,可爱,可爱!”为什么“可爱”?乃是因为这支曲子反映了下层社会家庭中善良纯朴的伦理关系,其感情真挚生动,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通俗浅近,读后犹如看到王祥兄弟虽然同父异母却互敬互爱、孝敬娘亲的平凡而亲切的生活画面。
沈璟对戏曲语言的主张,也体现在《南曲全谱》中。谱中有不少曲例,从格律方面来看并不符合要求,但沈璟也将它们选为曲例,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浅近易懂、通俗明白。如《南西厢》的〔河传序〕、《风流合十三》的〔白练序〕、《唐伯亨》的〔丑奴儿近〕等曲子,沈璟都眉批说:“用韵甚杂,然词甚古。”所谓“甚古”,也就是指它们多出自民间文人之手,语言浅近通俗,“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而歌可已”(徐渭 242)。
在要求戏曲语言浅近通俗的同时,沈璟还进一步主张,戏曲语言也可以吸收民间俗语。如《琵琶记》〔雁鱼锦〕一曲有这样两句曲词:
这壁短道咱是个不撑达害羞的乔相识,那壁厢骂咱是个不睹事薄幸郎。沈璟眉批道:“‘不撑达’、‘不睹事’,皆词家本色语。”在他看来,骈俪秾纤并非戏曲艺术的最高境界,浅近通俗、令观众能解能懂的才是真正的戏曲精品。
沈璟由“雅”到“俗”的转型,与吴中地区商品经济活跃带来市民阶层的扩增后,对戏曲艺术的欣赏需求有关。
至弘治、嘉靖年间,商品经济又再度活跃起来,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我吴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嗽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蒋以化)
市民不再以传统的单一农作物谋生,而是依赖手工业,或者开办手工作坊,即“大户张机为生”;或者为作坊进行加工,即“小户趁织为活”。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生,出现了一大批工业者,加之从事商品贸易的一批商人小贩,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增。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增,带来了对戏曲艺术的需求。在吴江县,至迟从弘治前后开始,就有了频繁的戏曲演出。弘治元年莫旦的《吴江志》即记载:“立春日前期,县官督委坊甲,整办什物,选集方相、戏子优人、小妓装扮社伙,教习两日,谓之演春。”“……有力者搬演杂剧,极诸靡态,所聚不下千人。”这种风俗一直到乾隆十一年沈彤的《吴江县志》均有记载,可见其相沿日久。戏曲演剧活动在沈璟所处的万历年间更为频繁:“每岁必演剧月余,男女杂沓。……”(沈彤)每年演戏达一个多月。如果官府不严加禁止,恐怕时间更长。此外,吴江县的几个大镇戏曲活动也不少,如庉村,“春三月演戏甚盛,供以赛刘猛之神,多则四五十本,少则二三十本”(曹);黎里“二月中有马灯会,择村童之秀丽者扮演故事”“八月十五……更有太平盛会,十三日设筵演剧”。(徐达源)
正是处于这样的戏曲氛围中,在沈璟之前退隐吴江的顾大典,就沉迷于戏曲,不仅创作戏曲作品,还蓄养戏班。沈璟,一个曾经的进士、朝廷命官,在退隐吴江后,也同样以创作戏曲和钻研曲学为后半生的精神寄托。也正是处在这样的戏曲氛围中,沈璟较之其他的戏曲家更为自觉地实现了由“雅”到“俗”的转型。
实际上,这种转型,不仅仅体现在沈璟的理论自觉和创作实践中,其他的戏曲家和理论家也在呼唤和实践。
王骥德在批评《香囊记》《玉玦记》等作品“益工修词,质几尽掩”后,提出了化“雅”为“俗”的主张:“夫曲以摹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来。”(王骥德 122)徐复祚评论梅鼎祚的《玉合记》道:“余读之,不解也。”他借此提出:“传奇之体,要在使田陵红女闻之而伹然喜,悚然惧。若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何异对驴而弹琴乎?”(徐复祚 238)凌濛初的抨击也很激烈:“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崇尚华糜;弇州公以维桑之谊,盛为吹嘘,且其实于此道不深,以为词如是观止矣,而不知其非当行也。以故吴音一派,兢为剿袭,糜词如‘绣阁罗帷’‘铜壶银筋’‘黄莺紫燕’‘浪蝶狂蜂’之类,启口即是,千篇一律,甚至使僻事、绘隐语,词须累铨,意如商谜,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余,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露已。”(凌濛初 253)并指出,这是传奇创作的“一大劫”。
沈璟由“雅”到“俗”的转型,到了明末清初的“苏州派”戏曲家那里,蔚为大观。“苏州派”作家生活在苏吴这一城市经济极为繁荣的地区,并且生活于社会下层,这使得他们更加得天独厚地把笔触伸向市井下层社会。他们的作品中虽然也免不了有才子佳人、神仙幽怪、忠臣孝子之类的形象,但是,纺织工人、行商坐贾,以及各式各样的城市平民如种菜的、杀猪的、卖唱本的、卖卦算命的、帮闲筋片、妓院鸨儿,乃至江洋大盗等江南下层社会的人物占有更多的篇幅,从而形成了“苏州派”作家创作的共同而鲜明的特色。
回望历史,在明代万历年间,正当曲坛弥漫着骈俪典雅的创作风气之际,身份同样是士大夫的沈璟,先是创作了一部也沾染着骈俪之气的《红蕖记》,此后便非常自觉地从骈俪中走了出来,注重从市井生活中选择题材,以通俗浅近的语言,书写市井中的小人物,从而实现了由“雅”到“俗”的自我创作的转型。这一转型当然属于他个人,但审视他的周围,一批理论家都强烈批评骈俪典雅的创作风气,稍后于沈璟的“苏州派”作家则以更大的声势,实践了这一由“雅”到“俗”的转型。再往后,以“雅”为尚的戏曲家以及作品固然不在少数,但“俗”的一脉更是绵延不断,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俗”的“花部”地方戏终于形成大势。由此可见,沈璟的自我创作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戏曲发展的大方向,或许他本人未曾意识到,但戏曲史发展的事实却证明了他的方向的必然性。
徐渭:《南词叙录》,选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Xu Wei.“Nan Ci Xu Lu,” Collected Essays of Classic Chinese Xiqu, vol.3.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 1959.]
王骥德:《曲律》,选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Wang Jide.“Qu Lv,” Collected Essays of Classic Chinese Xiqu, vol.4.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 1959.]
李渔:《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Li Yu.Xian Qing Ou Ji.Hangzhou:Zhejiang Classic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5.]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Zhou Yibai.History of Chinese Theatre.Shanghai: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吕天成:《义侠记·序》,选自《万历继志斋刊本卷首》。
[Lv Tiancheng.“Preface,” Yi Xia Ji.Ji Zhi Zhai edition.]
陈森:《品花宝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Chen Sen.Pin Hua Bao Jian.Shanghai:Shanghai Classic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0.]
蒋以化:《西台漫记》,选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Jiang Yihua.“Xi Tai Man Ji,” The Catalogue Series Edition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沈彤:《吴江县志》,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
[Shen Tong.Wujiang County Annals.Block-printed edition, 1746.]
[Cao Ci.Tun Cun County Annals.Stereotype edition, 1934.]
徐达源:《黎里志》,清嘉庆十年(1805)刻本。
[Xu Dayuan.Lili County Annals.Block-printed edition, 1805.]
徐复祚:《曲论》,选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Xu Fuzuo.“A Study of Qu,” Collected Essays of Classic Chinese Xiqu, vol.4.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 1959.]
凌濛初:《谭曲杂札》,选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Ling Mengchu.“Tan Qu Za Zha,” Collected Essays of Classic Chinese Xiqu, vol.4.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