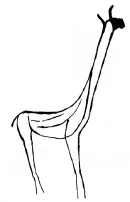一石二鸟
◆◇ 单永珍
一石二鸟
◆◇ 单永珍
抓喜秀龙草原的午后(一)
它用热烈修饰灿烂,走马的消息
沸腾在牧人的风干肉里
草尖上,格萨尔的伤口
让政协秘书长扎西尼玛的解说有些慌乱
这是抓喜秀龙草原,青藏高原最东端
几丛苏鲁梅朵私下里开会
商议着茶马交易,以及一匹疲惫的走马
满脸羞愧地躲进青稞的阴影
柔旦尕擦寺院,鲜花吟唱,这些
阳光与风的子民,绽放神圣之美
念经的阿卡放下经书,喝一碗酥油茶
听着汽车的喇叭声,会心一笑
来自远方的方方,惊讶地听着走马的脚步
她实在想不通,马踏飞燕的造型
竟藏在抓喜秀龙的草丛中
让约会的蜜蜂,高声朗诵一首情诗
午后。抓喜秀龙草原。万物生长——
我醉卧阳光的手掌,磨牙
回到章嘉活佛万人空巷的讲台下
静听相思一章
抓喜秀龙草原的午后(二)
我止步于你疼痛的舌尖。黑暗的黄蜂漫漶于口蹄疫的叹息。
有声音自狼毒花的根部患破伤风,这阳光的罪罚。这是抓喜秀龙草原的基层哲学,或者一个贫下中农的脱盲演说。
“你在卖什么,啊,糊涂的姑娘裸露着乳房?”
诗人仁谦才华在洛尔卡的谣曲中醉生梦死。
而谁又不想醉生梦死?
牺牲的羔羊,热爱着人类的牙齿,像烈士,义愤填膺成手抓肉和一锅寂寞肉汤,在欢呼的草原,风把失身僧人的语录还给鹰的翅膀。
我多想醉生梦死于这荒唐人世。
白日忏悔,举义的双手瘦骨嶙峋。
夜晚谱录号角——你身体的温度以及卓玛的笑。
主啊!请饶恕一朵野花的歌唱,在这不合时宜的时代。我面临深渊,无力自拔,只看见鹰翅划破虚伪和风的角力之阵。
我满身鲜血,胸前挂着诬陷的证词。
无物之阵的抵抗。
独自舔舐伤口,一次咳嗽竟将我击倒。
抓喜秀龙,我全部的知识源于谬误;我金刚的真理毁于一旦;我崇高的朗诵憔悴于章嘉活佛的开悟。
我自取灭亡,一如飞蛾醒悟于酥油灯盏。
我醒来,在一捧糌粑的灰烬里;一壶酥油茶的泥泞里;一蓑羊皮大衣的坦途上。
“你在卖什么,啊,糊涂的姑娘裸露着乳房?”
—— 洛尔卡咏叹着。
我如此讨厌自己沉重的肉身——
这阳光的午后,一赤子辩日。
一俗人数着体内的舍利。
马 蹄 寺(一)
一群麻雀点名批判纷乱大雪
难道是天空破坏了早餐秩序
还是一炷香火
让屋顶的白
回到原来的青
马蹄寺的台阶上,一场雪掩盖了
法显的脚印
鸠摩罗什的舌头
和一个初生婴儿的姓名
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有一双中年的老寒腿蹒跚而来
向马有才学习西凉谣曲
从才旺东珠口里偷走藏花儿
马蹄寺。一群麻雀让雪地更白
一个衰老的张掖僧人,一袭灰袍
和我讨论叙利亚战争
以及雪与春天的轮回
马 蹄 寺(二)
奔突。自我放逐的嘶鸣。河西走廊最后的巡游者。
阵阵蹄音刺穿汉长城垛口,那些摇滚、秦腔、骚花儿、小调混杂在一起,像革命者投身梁山。躲在史册阴影中的征夫、戍卒、流浪汉、酒鬼、偷情的银匠,指点一盘残棋,手舞足蹈。
矛与盾的血腥辩证。
这是河西走廊常态的叙述画卷。
古代的行吟诗人。现代的役夫。未来的太阳之子。
我无法区分光阴强附于我的身份证。
万千响箭扑向我—— 丝绸破碎。
一只出家的青鸟翻动经卷,和一老僧人正午入定。
马蹄寺正午的香火,浓烈、艳丽。几个穿牛仔服的童子,黑牙白目,用山丹方言唱着郑智化的歌:
“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
抽搐的日头泼在脸上,童音苍老,仿佛败北者迷失于一场电子游戏。
诗人昌耀于我布道云:我,只是一部行动的情书。
我羞愧。我的情书在马蹄寺刚刚完成第一章。
黄昏来临。
马蹄寺的黄昏一如逃遁的鹌鹑,瘦小,心理极度不健康,带着狐臭。我痛苦地发现,它与煌煌《金刚经》不甚匹配。它拽着寒鸦的肩膀,陷入黑暗哲学和内部斗争。
方方,我无法证明我自己。
我是你的灾难。
而你说,在马蹄寺,谁在此刻沉沦,谁就获得拯救。
华 藏 寺(一)
白牦牛广场。华藏寺仅占西南小小一角
它甚至被人忽略
如果不是晨起老者来煨桑
小小桑烟肯定被认为是
几个游方僧捣弄早饭的结果
这里绝对适合我这样的旅行者
用大把的时间停留、驻足
把躁动不安的心安定下来
看几只鸟雀啄食供品
看几缕桑烟被广场上
晨练的大妈挥舞的扇子
扇得惊慌失措
华藏寺。小小的神殿里
端坐小小的佛
三个朝拜者
一个来自青藏高原
一个来自蒙古高原
一个来自黄土高原
念叨着口音不同的六字真言
转着经筒
唯有一个来自黑龙江的萨满信徒
站在树荫下
一言不发
华 藏 寺(二)
哦,白海螺在低音部开始旁白,使《金刚经》在民众中得到解放。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一个疯子絮絮叨叨地在白牦牛广场散布心得,他夸张的箴言,让庄重之人纷纷躲避。而我竟尾随疯人,看他飞沫四溅的口中,如莲语滂沱,在梵音低沉的白海螺感召下,华藏寺大音希声的寂寞顷刻间显露起来。
我在人生的旱码头,恓惶如秋菊。
荆棘遍布的街道,我荒芜的学历长满疥疮。谁能疗治苋麻草的愤怒,谁让一只荆棘鸟的飞翔变成求证的终旅。
我穿着问号的羽衣,沐浴在白海螺的音乐之诗。
这些年了,我浪迹高原腹地,磨洗自己。
我执著于异质的求索,以此卸下浑身的累和暗藏的毒。我无法跳出五千只蝙蝠织就的梦魇——语言虚伪、行为卑琐,心上装满暗算的箭。
是的,我坦白,绝不隐瞒。
为什么我无端拥有暗含的伤,到底有多少座坟驮在我背上。
华藏寺的杨树下,浓阴如盖,我无法禅定,披肝沥胆地怀疑着自己。
而天空蓝得心碎,我无法适应。我的体内盛满重度污染的习俗,习惯了汽车尾气,有铅的奶粉,刺耳的音乐,还有传教的图画。我艰难咀嚼着糌粑,咽下痛苦的酥油茶,这母亲的饭食,竟与我中年的身体如此相隔。
就让我赤身裸体奔向你,华藏寺,从第一个高贵的字母开始。
“求知者走过人类,如走过兽类一样。”尼采在羊颊骨上端正态度。我肃穆如一临产白牦牛,背诵经验的民谣。
我惊诧于这高原一隅,来自低处的声音总让颓废的意志获得拯救;无援的抵抗遭遇知音;独行者寒夜相遇一炉牛粪火的牺牲。
哦,天空之下,云朵之上,我看见三个角斗士冲出栅栏,挥舞着巨人般的宣言,投影于大地,投影于华藏寺的朝夕里。
方方,请你领诵,青海高车的暄响:
“黎明的高原,最早
有一驭夫
朝向东方顶礼。”(昌耀)
我倾心向西,途经华藏寺,蓦然东方,身后是血迹斑斑的脚印。
我打碎自己。
主啊,请赐予我泥沙俱下的朗诵和尘土般的赞美。
(选自《朔方》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