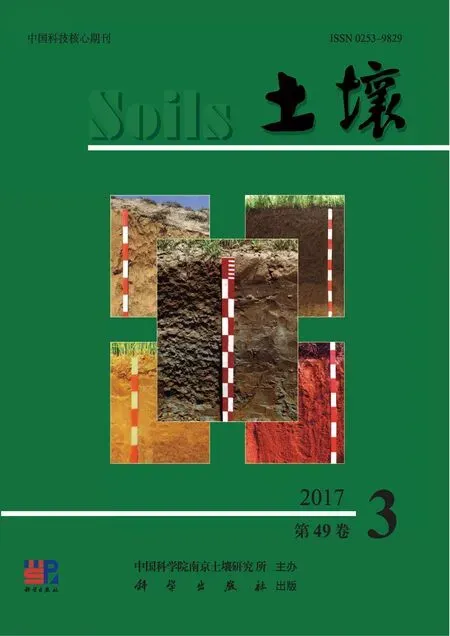中国农田土壤农药污染现状和防控对策①
赵 玲,滕 应,骆永明
中国农田土壤农药污染现状和防控对策①
赵 玲,滕 应*,骆永明
(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 210008)
随着农药长期大量的施用,农药残留及其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因此,针对我国农业生产中涉及的三类主要农药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的施用情况及其农田土壤中残留特征进行了阐述,对农田土壤因农药残留造成的作物抗性危害、生态环境风险以及人类健康潜在风险等进行了分析,并对农药污染农田土壤的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以及菌根修复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田土壤农药污染综合治理的防控对策。
农田土壤;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污染风险
农药作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对农业发展和人类粮食供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药主要包括杀菌剂、杀虫剂和除草剂三大类。世界范围内农药所避免和挽回的农业病、虫、草害损失占粮食产量的1/3[1]。然而近年来随着农药长期大量的施用,农药残留及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2]。据统计,农田中施用的农药量仅有30% 左右附着在农作物上,其余70% 左右扩散到土壤和大气中,导致土壤中农药残留量及衍生物含量增加,造成农田土壤污染[3]。这不仅会破坏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还会通过饮用水或土壤−植物系统经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就开始了土壤农药污染的治理与修复工作。目前,德国、丹麦和荷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领先地位[4]。我国随着民众对农产品安全和品质需求的提升,土壤农药污染的治理与修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农田农药的使用与污染现状,介绍土壤农药污染产生的危害和生态风险,评述国内外农药污染的修复技术,为我国农田农药污染防控与治理提供科学参考。
1 农田农药的污染现状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生产和使用的农药有几千种,世界农药的施用量每年以10% 左右的速度递增。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农药年产量在400万t左右,90年代则超过3 000万t。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药使用量居世界第一,每年达50万~ 60万t,其中80% ~ 90% 最终将进入土壤环境,造成约有87万 ~ 107万hm2的农田土壤受到农药污染[3,5]。我国农药使用量较大的地区有上海、浙江、山东、江苏和广东,其中以上海和浙江用药量最高,分别达到了10.8 kg/hm2和10.41 kg/hm2[6]。以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北方干旱地区施药量小于南方水稻产区;蔬菜、水果的用药量明显高于其他农作物。目前,农药污染已成为我国影响范围最大的一类有机污染,且具有持续性和农产品富集性。随着使用量和使用年数的增加,农药残留逐渐增加,呈现点-线-面的立体式空间污染态势。
1.1 除草剂的使用量与污染现状
近年来,除草剂的增长率远高于杀虫剂和杀菌剂,约占到农药产量比重的1/3。目前全国农田化学除草面积较1980年增加了十多倍,据估算除草剂将以每年200万hm2次的速度增加,每年需除草剂6.7万~ 8.6万t,占农药需求总量的30% ~ 40%,未来十年全国化学除草面积可能会增加0.31亿hm2[7]。中国农药市场先后有近百个除草剂产品,其中以莠去津、扑草净、西草净制剂为主的三嗪类,2,4-D等苯氧羧酸类,以苄嘧磺隆、甲磺隆制剂为主的磺酰脲类和乙草胺、丁草胺等酰胺类除草剂是市场的主流品种。而莠去津、甲磺隆、绿磺隆、咪唑乙烟酸、氟磺胺草醚和豆磺隆是长残效除草剂,占到除草总面积的15% 左右[8]。草甘膦作为一种高效、低毒、广谱、适用范围极广的灭生性除草剂[9],由于其优良的传导性,最初主要用于非粮食作物以及免耕土壤上的除草,随着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发展,草甘膦的应用从非粮食作物转向粮食作物,使其在全球的使用正以每年20% 的速度递增[10]。
随着除草剂的大量施用,造成的环境影响也日益突显。研究表明,在南非、瑞士、西班牙、法国、芬兰、德国、美国和中国等莠去津使用历史较长的国家,地表水和地下水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欧洲委员会有关饮用水的规定中(80/778/EC) 要求,任何农药在饮用水中含量不能超过0.1 μg/L,农药总含量不能超过0.5 μg/L[11]。我国在1998年规定莠去津Ⅰ、Ⅱ类地表水中的标准为3 μg/L。然而,美国USGS在1991—1992年调查发现,West Lake湖的13个水样中就有11个水样的莠去津浓度超过了饮用水的标准,1996 年再次调查地下水时仍发现50% 的水井样品中检测出莠去津和它的代谢物[12]。Oldal等[13]调查了匈牙利土壤中农药活性成分和残留,发现24个土壤样品中只有2个样品含有莠去津,浓度分别为 0.07 mg/kg和 0.11 mg/kg;但是地下水样品中测到莠去津166 ~ 3 067 μg/L,乙草胺307 ~ 2 894 μg/L,二嗪农15 ~ 223 μg/L和扑草净109 ~ 160 μg/L。德国自1991年3月开始禁止在玉米田施用莠去津,Tappe等[14]1991—2000年对德国地下水的监测中发现,莠去津及其衍生物的检出量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莠去津是我国玉米田主要施用的除草剂,2000年我国莠去津的使用量为2 835 t,仅辽宁省使用量就超过1 600 t[15]。由于莠去津水溶性较强,农田中的大量施用使它成为各国河流、小溪等水体中检出率最高的除草剂。我国淮河信阳、阜阳、淮南、蚌埠4个监测断面检测到莠去津的残留量分别为76.4、80.0、72.5、81.3 μg/L[16]。严登华等[17]剖析了东辽河流域地表水体中莠去津的含量和富集特征的时空分异,得出辽河流域旱田分布区和非旱田分布区内地表水中莠去津的平均含量分别为9.71 μg/L和8.85 μg/L,7月份流域地表水中莠去津含量最高,可达18.93 μg/L。目前,关于我国土壤中除草剂残留的报道较少。王万红等[18]报道了辽北农田土壤中除草剂的残留特征,莠去津、乙草胺和丁草胺3种除草剂均有检出,其中莠去津和乙草胺全部检出,丁草胺检出率相对较低,仅为27.8%;残留量莠去津、乙草胺和丁草胺分别为0.14 ~ 21.20、0.53 ~ 203.20和nd ~ 30.87 μg/kg。在高使用量的条件下,土壤中草甘膦的浓度可能达2 mg/kg,若考虑土壤对草甘膦的吸附,土壤表层中实际的浓度要比这个数值高得多[19]。
1.2 杀虫剂的使用量与污染现状
现阶段杀虫剂包括新烟碱类、拟除虫菊酯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天然类、其他结构类等六大主类。在全球农药市场中,2011年杀虫剂约占了28% 的市场份额,销售额达到了140亿美元;2014年在农药市场的销售份额占比29.5%,销售额为186.19亿美元[20]。杀虫剂最大的应用作物为果蔬,其他应用较多的有大豆、水稻、棉花等。从2014年全球销售情况来看,有机磷类杀虫剂市场销售额占杀虫剂市场的15.3%,在杀虫剂所有类别中排名第四。目前统计用于农业的有机磷类杀虫剂品种有46个,其中销售额排在前7名的依次是毒死蜱、乙酰甲胺磷、乐果、丙溴磷、敌敌畏、喹硫磷和马拉硫磷。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市场销售额占杀虫剂市场的17.0%,在杀虫剂类别中排名第三,其中销售额和年增长率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高效氯氟氰菊酯、溴氰菊酯、氯氰菊酯、联苯菊酯和氯菊酯。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市场销售额占杀虫剂市场的6.7%,在杀虫剂类别中排名第六。目前统计用于农业的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有17个,其中使用较多品种有4个,依次为灭多威、克百威、杀螟丹和丁硫克百威。在中国,除杀螟丹外,其他3个均被限制使用。新烟碱类杀虫剂市场销售额占杀虫剂市场的18%,在杀虫剂类别中排名第二。目前统计用于农业的新烟碱类杀虫剂有7个,分别为噻虫嗪、吡虫啉、噻虫胺、啶虫脒、噻虫啉、呋虫胺和烯啶虫胺。近年来,该类型产品中多个品种受到管制,尤其是2013年底起,噻虫嗪、吡虫啉和噻虫胺等在欧盟的使用受到限制。天然类杀虫剂主要包括植物源、动物源和微生物源物质及其代谢物。2014年销售额排前4名的天然类杀虫剂依次为阿维菌素、多杀霉素、乙基多杀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销售额较大的微生物杀虫剂主要有苏云金杆菌、坚强芽孢杆菌、蜡蚧轮枝菌等;销售额较大的植物提取物杀虫剂有印楝素等。有机氯类杀虫剂市场销售额仅占杀虫剂市场的0.7%,目前市场上有机氯类杀虫剂主要有硫丹、三氯杀螨醇和林丹。有机氯类杀虫剂虽然在发展中国家保持了一定的销售额,但在发达国家的销售额一直在下降。此外,2014年销售额较高的其他类杀虫剂有氟虫腈、氯虫苯甲酰胺、氟苯虫酰胺、螺虫乙酯、茚虫威、吡蚜酮、虫螨腈、氟啶虫胺腈、氰氟虫腙、乙虫腈和氟啶虫酰胺。
我国杀虫剂的使用情况与全球杀虫剂的销售状况类似。以江苏省为例,农用杀虫剂使用量占农药使用量的比重远高于杀菌剂和除草剂,2000年以来每年杀虫剂的使用量在5万~ 7万t,约占农药使用总量的60% 以上。从杀虫剂种类来看,有机磷类杀虫剂使用量最大,约占杀虫剂使用总量的70%;其次是新烟碱类,约占18%;氨基甲酸酯类和杂环类约占12%[21]。2000年以来,不同类型农药使用量所占杀虫剂比重变化不大。高毒的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虽然用量下降,一些中等毒性的氨基甲酸酯类农药2004—2008年用量不降反升,比2000年前后用量增加2倍以上。至2007年,甲胺磷、甲基对硫磷等高毒农药品种基本停止使用,水胺硫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等高毒品种虽未被取消登记,但使用量降幅较大。敌百虫、乐果和咪嗦酮等中等毒性杀虫剂用量变化不大,如敌百虫在2000—2009年基本保持在年使用量1 000 t左右。辛硫磷、毒死蜱、氟虫腈、吡蚜酮等中等毒性杀虫剂用量迅速上升,其中辛硫磷的用量几乎增加了1倍,毒死蜱取代甲胺磷成为用量最大的有机磷杀虫剂。
多年施用农用杀虫剂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污染。有机氯农药(OCPs)因高生物富集性和放大性、高毒性的原因,在大多数国家已禁止使用,但是OCPs的污染问题仍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环境和公共健康问题之一。我国在20世纪50—80年代曾使用过OCPs,其中六六六(HCHs)490万t,滴滴涕(DDTs)40万t,分别占全球总用量的33% 和20%[22]。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已基本禁用OCPs,但部分地区土壤中OCPs的残留量依然相当严重。2004年,我国对5个省市表层土壤中OCPs污染状况调研结果表明,DDTs仍是土壤中OCPs污染的主要组成,约占总量的90% 左右,平均浓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省>湖南省>湖北省>北京市>安徽省。根据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的规定,HCHs和DDTs在一级土壤中的质量分数标准限值为50 μg/kg,我国大部分地区土壤中OCPs污染水平集中在中低浓度水平,但部分地区OCPs的浓度分布差异较大,存在OCPs污染严重超标的现象,如广州、成都、呼和浩特等城市[23]。安琼等[24]对南京地区土壤中OCPs残留分析的结果表明OCPs在不同类型土壤中的残留量依次为露天蔬菜地>大棚蔬菜地>闲置地>旱地>工业区土地>水稻土>林地;耿存珍等[25]报道青岛地区不同类型土壤中OCPs残留量为菜地>农田>公路两侧区域;Li等[26]报道了珠江三角洲地区HCHs和DDTs的平均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农田>稻田>天然土壤。这说明了土地的耕作类型不同,对于OCPs的使用量也不同,从而使不同类型的土壤中OCPs呈现出不同的残留水平。作为一种危害性极高的OCPs,硫丹曾广泛用于棉花、烟草、茶叶和咖啡等农业生产,导致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土壤、大气、雨水、地下水等样品中检测到其残留[27]。近年来,我国在多个省份及流域的各种环境介质中检出硫丹。对我国的37个城市及3个背景点的空气监测发现,α-硫丹和β-硫丹的浓度范围分别为0 ~ 1 190 pg/d3和0 ~ 422 pg/d3[28],同时发现,含量较高采样点出现在棉花种植区,表明农业使用是我国空气中硫丹的重要来源。水环境中同样有硫丹的存在,我国太湖中也检测出硫丹,浓度为0.32 pg/L[29]。有机磷、氨基甲酸酯、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应用非常广泛,这些非持久农药与土壤都有较强的结合能力。有机磷杀虫剂在土壤中的结合残留量高达26% ~ 80%,氨基甲酸酯类农药西维因的结合残留量达49%,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结合残留量达36% ~ 54%[30]。有机磷农药在蔬菜、粮食和一些畜产品中的残留引起的农药中毒事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据报道,1998年1—10月全国蔬菜农药中毒人数达94 165人,死亡9 107人,因农药残留量检验不合格的出口农产品被退货金额达74亿美元[31]。
1.3 杀菌剂的使用量与污染现状
农药杀菌剂是防治作物病害最重要的武器,杀菌剂近年来一直成为研发的热点。据统计,2012—2014年全球杀菌剂销售额分别占农药总销售额的26.3%、25.8% 和25.9%。我国杀菌剂的需求量从2000年的5.98万t 到2012年的7.94万t,增加了32.7%,2013年我国的杀菌剂用量同比增加4.68%。苯醚甲环唑等三唑类杀菌剂需求量增幅较大,从2000年的1.9万t (制剂量)到2012年的 3.04万t(制剂量),增加了59.7%[32]。近年来世界杀菌剂新品种的开发取得很大进展,如三唑类、酰胺类、嘧啶胺类、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等。从农药市场需求量来讲,全球杀菌剂增长速度达到近8%,三唑类杀菌剂仍将是主角;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因其现阶段无可替代的作用效果将逐渐占据杀菌剂的主角地位。杀菌剂主要用于水果、蔬菜、中草药等的病害防治。由于大部分杀菌剂为较低效或低效农药,在施用后一段时间内才可以看到明显的防治效果,因此使用过程中用量常被刻意提高数倍甚至数十倍, 杀菌剂就成了蔬菜生产的重要污染源之一。欧盟早在1996年就指出异菌脲、腐霉利、百菌清、苯菌灵、代森类等几种杀菌剂是作物生产中主要的危害残留物。法国国家环境所200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法国90% 的河流及58% 的地下水中含有杀菌剂、除草剂及杀虫剂等农药。由于我国农药监管的重点是高毒高残留的杀虫剂,而对杀菌剂的监管重视不够,因此杀菌剂的用量一般会比登记用量大几倍甚至十几倍,特别是多菌灵、福美双、代森锰锌等在我国已经有很长的使用历史。在我国生产的水果、蔬菜中,多菌灵和百菌清的检出率均较高,某些地方还会超标[33]。
2 农田土壤农药残留的风险分析
2.1 农药施用产生的抗性危害
由于农药的长期使用,其防治对象害虫和杂草会对农药产生抗性,而害虫的天敌却遭受农药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报道,截至2009年全世界189种杂草对1种或数种除草剂产生抗性,其中双子叶杂草113种,单子叶杂草76种[34]。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已有540种昆虫和螨对310种化合物产生抗药性,在我国已发现产生抗性的昆虫和螨类达45种[35],如吡虫啉这类害虫产生抗性风险较高的品种, 因害虫抗性迅速上升, 防效快速下降而将会被其他产品取代。在连续多年使用同一种(类)除草剂后,大量对除草剂敏感的群体被杀死而减少,而一些不敏感或已产生抗性的群体得以繁衍,致使农田杂草种群迅速更迭,群落结构发生改变,演替加速,次要杂草上升为优势种群并滋生为害,增加了防除的难度。早期应用的除草剂品种从开始应用到杂草产生抗性约需10年以上,而最近则仅用4 ~ 5年便产生抗性。抗性的形成会使农药的使用量增加,在中国东北地区,一些旱田除草剂每公顷用量成倍增长,如莠去津由开始的1.5 g已增至目前的3 g,乙草胺由1 g增至2 g,稻田苄嘧磺隆由30 g增至50 g[8]。从而使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形成恶性循环。杂草抗药性问题的严峻形势已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除草剂抗药性的严重程度有可能超过杀虫剂和杀菌剂[36]。
2.2 农药对作物生长和品质的影响
一方面被农药长期污染的土壤将会出现明显的酸化,土壤养分(P2O5、全氮、全钾)随污染程度的加重而流失,土壤孔隙度变小等,造成土壤结构板结,从而影响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残存于土壤中的农药对生长的作物有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除草剂。不同的作物对除草剂的敏感程度不一样,若把除草剂用在敏感作物上,或气传漂移在其上面,就会产生药害,甚至死亡。田间喷洒除草剂后,有效地控制了当季农田杂草,但对下茬敏感作物却容易造成药害。在除草剂使用过程中与杀虫剂、杀菌剂以及其他农药混用不当,容易对农作物造成药害。此外,研究表明除草剂会影响作物的生化组成和氮代谢。如丁草胺和二氯喹啉酸等除草剂处理后,水稻叶鞘内游离氨基酸含量明显增加,蔗糖含量和总酚含量均下降[37]。氟乐灵可诱导马铃薯产生一种具有杀菌活性的化合物。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生理生化上的变化会影响作物的抗虫、抗病性,促进或抑制害虫或病原生物的生长和增殖,从而间接地影响作物的生长[38]。一些长期使用长残效除草剂的田块还出现了除草剂残留量累积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后茬作物的轮作,形成了“癌症田”的现象。除草剂如咪唑啉酮、三唑嘧啶磺酰胺、三氮苯甚至用于小麦田的敌稗也会伤害后茬作物。
2.3 农药对土壤酶的影响
农药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这主要取决于农药本身和环境因子。一般情况下低浓度农药对土壤酶表现刺激效应,高浓度则表现出抑制效应,且抑制作用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强[39]。闫颖等[40]研究表明百菌清、百菌清-多菌灵混剂、氯氰菊酯在实验浓度范围内(0.1 ~ 50 mg/g)明显抑制土壤转化酶活性,多菌灵、吡虫啉浓度低于0.1 mg/g时对转化酶有激活作用,而浓度高于0.5 mg/g时抑制转化酶活性;百菌清和多菌灵联合使用,会使农药毒性明显增强。磺酰脲除草剂对土壤酶的活性有抑制作用。研究发现甲磺隆浓度为0.1 μg/g时不影响脲酶的活性,当甲磺隆的浓度提高为0.5 ~ 2.0 μg/g时,脲酶活性显著降低[41]。Sannino等[42]考察了4种杀虫剂(苷草磷、百草枯、莠去津和甲萘威)对22种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苷草磷作用下磷酸酶活性受到抑制,抑制率为5% ~ 98%。农药对土壤酶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考虑时间的影响。杀虫剂久效磷、喹硫磷和氯氰菊酯两两复合处理时,其交互效应对土壤纤维素酶和淀粉酶活性的影响与土壤中相应降解纤维素和降解淀粉的微生物种群数量显著相关[43]。土壤类型及其性质也起着重要作用:黑土与草甸土相比,前者有机质含量更高,对环境改变有更大的缓冲能力,故除草剂氯嘧磺隆和杀虫剂呋喃丹施用在两种土壤中,黑土中脲酶活性的变化较缓慢些[44]。
2.4 农药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农药污染对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往往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农药种类和浓度关系密切[45],而微生物对农药的抗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46]。在相同浓度下,百菌清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比对嘧菌酯和戊唑醇两种农药的影响程度更大,时间更长[47];同样在相同浓度处理下,草甘膦和噻唑啉能提高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和生物量,而乐果则降低微生物的活性和生物量[48]。研究表明乐果施用后10天能显著降低土壤微生物的呼吸作用,有机磷农药污染的土壤中土壤动物的种类及数量都显著地减少。农药浓度与其毒性效应直接相关,低浓度的除草剂苄嘧磺隆对水稻土中微生物有轻微、短暂的不利影响,而高浓度处理下,细菌群落数量急剧下降,该水稻土中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与苄嘧磺隆的浓度显著相关[49]。低浓度(<60 mg/kg)甲氰菊酯杀虫剂对蔬菜土壤中微生物数量影响不大,高浓度(>90 mg/kg)的甲氰菊酯在短期内就能对微生物有抑制作用。农药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是有选择性的,敏感类易受抑制,耐受型的优势群落则可利用农药作为碳源和能源而增殖[49]。因此,土壤微生物对农药的抗性也是农药影响微生物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2.5 农药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一般情况,有机磷杀虫剂对土壤动物的影响比除草剂、杀菌剂等更显著。有机磷杀虫剂对土壤动物的作用速度快、毒性强,是一类急性农药,而除草剂、杀菌剂对土壤动物是慢性的,毒性也较弱[50]。蔡道基等[51]研究发现,蚯蚓对甲基对硫磷与克百威的毒性反应快,用土壤法处理30 min后皮肤发红充血,遇光或受机械触动刺激,急剧卷曲、扭动,失去逃避能力。受害严重的蚯蚓1周死亡,死亡前颜色变淡,环节松驰、脱节,甚至溃烂。Bouwman等[52]研究也表明,当赤子爱胜蚓暴露在2 mg/kg呋喃丹污染的土壤中,蚯蚓个体不能发育出环带和产卵。不同研究者分别对3种除草剂苯磺隆、乙草胺和百草清的研究,均得出随着农药处理浓度的增加,土壤动物种类和数量呈递减变化,多样性指数值亦呈递减趋势的结论,同时一致认为,土壤中的优势种群弹尾目和甲螨亚目,是对这些农药较为敏感的一类,可作为土壤环境污染的重要指示生物[50,53–54]。
2.6 农药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土壤中残留的农药通常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湖泊,对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污染。同时,进入水体的农药也会对水生生物造成一定的毒害作用。莠去津能在水生生物体内产生富集,对水体中的低等动物毒性极大,研究表明对淡水中的软体动物如水蚤、水蛭的取食、生长、产卵产生抑制作用[55]。它在鱼体内富集的浓度可以达到周围水环境浓度的11倍。暴露在0.5 μg/L莠去津的水环境中的金鱼发生明显的行为变化。莠去津对水生动物和两栖动物产生某些生殖毒性。Dodson等人[56]的研究发现,水蚤Daphnia在胚胎形成期,低浓度0.5 ~ 10 μg/L莠去津的暴露就可使它的雌性后代出生率增加。将蝌蚪放在含有不同浓度莠去津的水中饲养,0.1 μg/L的莠去津水溶液就能导致青蛙产生雌雄同体现象。草甘膦对鲫鱼具有一定的毒性,但不具有剂量效应,与染毒时间的长短也无明显相关性[57]。溴苯腈能导致啮齿类动物的生殖障碍,一旦进入水体,会产生很强的毒性,对鱼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几乎所有水生生物对硫丹都非常敏感。研究表明,硫丹对藻类具有较高毒性[58];无底泥条件下硫丹对甲壳动物的毒性比存在底泥时要高数倍到数十倍[59];硫丹对鱼类同样具有较强毒性,淡水鱼类相对海水鱼类具有更高的耐受性,高等鱼类较低等鱼类对硫丹的耐受能力更强一些[29]。另外,硫丹与其他污染物的联合毒性效应更强。研究表明,394 μg/L毒死蜱与4.5、7.9和1 μg/L硫丹分别共同作用下,太平洋树蛙幼体(Pseudacrisregilla)致死率显著高于硫丹单一染毒[60]。稻丰散、福美双和敌百虫对鱼具有中等急性风险;硫丹和敌百虫对鱼具有慢性风险;三唑磷、二嗪磷和毒死蜱对溞具有急性高风险;敌百虫、毒死蜱、硫丹、丙溴磷、福美双、抗蚜威、阿维菌素、稻丰散、溴氰菊酯、吡蚜酮和多菌灵对溞具有中等急性风险和慢性风险;乙草胺和莠去津对藻类具有急性高风险;氟乐灵、敌百虫和福美双对藻类具有中等急性风险;同时这几种农药对藻类也具有慢性风险[61]。
2.7 农药对人类健康的潜在风险
由于农药使用者缺乏农药知识和用药技术,长期大量不合理地使用农药,造成蔬菜、水果、畜禽养殖产品等农药残留量过高,而这些农产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慢性中毒危害。例如,莠去津和2,4-D 已被美国环保局列为致癌物[62]。农药和重金属是蔬菜、茶叶及粮食作物的主要污染物。其中,叶菜类易受农药污染。蔬菜中超标的农药品种主要为菊酯类、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如氰戊菊酯、联苯菊酯、氯氟氰菊酯、三唑磷、水胺硫磷、对硫磷、苯醚甲环唑、克百威、敌敌畏、毒死蜱、氟虫腈、乐果等。受农药污染的主要粮食品种是水稻,农药品种主要为敌敌畏、氧化乐果、甲胺磷等有机磷农药[63]。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2001年第三季抽查结果显示,23个大中城市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47.5% 蔬菜农药残留量超标。慈溪市1992—2000年的1 221例农药中毒事件中,因食用被农药污染的蔬菜、水果而中毒的317例,占26%[64]。2012年,叶雪珠等[65]对浙江省蔬菜生产中的农药使用情况和94种农药残留进行了分析,发现目前蔬菜生产中主要使用78种农药,包括杀虫剂、杀菌剂、生长调节剂和除草剂,以低毒农药品种为主;蔬菜中主要残留28种农药,检出频率较高的农药依次为啶虫脒、多菌灵、毒死蜱、吡虫啉、烯酰吗啉、三唑磷、霜霉威和哒螨灵等,检出的残留农药品种中,有46.4% 在调查中未发现有使用,甲胺磷等高毒农药仍有检出,说明蔬菜食用仍存在农药残留安全风险。此外,研究表明很多农药都具有内分泌干扰物(EDs)的特性。EDs对个体的生殖、发育以及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表现出拟天然激素或抗天然激素的作用。在已报道125种EDs中,农药就有86种,占68.8%。我国当前几种主要除草剂中乙草胺、莠去津、甲草胺、草克净、杀草强等均是EDs。近20年来出现的拟除虫菊酯类,被农业和家庭广泛用作杀虫剂,现已证实它能刺激乳腺癌MCF7细胞增殖和p52基因表达[66]。世界各国广泛使用残效期很长的有机氯杀虫剂,包括DDT、氯丹、狄氏剂、毒杀芬和六氯苯等物质是EDs。虽然已禁止在中国使用,土壤中的残留也在逐步降低。但是由于EDs具有低剂量效应,一些用量并不多的农药也可能因为低剂量效应,危害具有相加作用而应给予重视。此外,农药乳化剂,如烷基酚类,包括壬基酚、辛基酚等或者杀虫剂载体,如邻苯二甲酸酯类,不仅污染广泛,而且其雌激素活性也很高。具有EDs特性的农药不仅具有致癌作用,而且有可能导致男性基本丧失生育能力,使人类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灭绝[66]。
3 农药污染农田土壤的修复
目前用于修复农药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主要有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等。其中,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技术具有周期短、修复效率高,但工程量大、费用高、易产生二次污染等特点,更为适用于农药残留浓度较高的土壤修复,如农药场地污染修复。生物修复法虽然修复周期较长,但因其经济环保,且不易破坏生态系统等优点,更加适合中低残留浓度的农药污染土壤,如农田土壤中的农药污染修复。针对农田土壤中各类农药的生物修复主要包括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菌根修复等。
3.1 微生物修复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药的微生物降解是能够彻底消除农药土壤污染的主要途径[67]。微生物降解农药的作用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微生物直接作用于农药,通过酶促反应降解农药,常说的微生物降解有机磷农药多属于此类;二是通过微生物的活动改变了化学和物理的环境而间接作用于农药,一般有矿化作用、共代谢作用、生物浓缩或累积作用及其他的间接作用等。农药微生物降解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细菌、真菌、放线菌、藻类等对农药都有降解作用,现已发现了大量农药降解菌及其降解的农药[68]。以毒死蜱为例,毒死蜱在非灭菌土壤中的降解比在灭菌土壤中快得多,证明了土壤微生物对毒死蜱的降解作用[69]。杨丽等[70]从蔬菜大棚土壤中分离到一株能以毒死蜱为唯一碳源和能源生长的粪产碱杆菌DSP3 (DSP3),在含100 mg/L毒死蜱的土壤中,20天后该菌对毒死蜱的降解率接近100%。真菌以毒死蜱为唯一碳源,对毒死蜱浓度在20 ~ 200 mg/L,pH 6.5 ~ 9.0,温度30 ~ 40℃时的降解效果较好[71]。Mukherjee等[72]利用绿藻门中的小球藻进行毒死蜱的降解实验,发现该藻不仅能够降解毒死蜱,对毒死蜱的两种降解产物3,5,6-trichloropyridirol和Chlorp- yrifosoxone也有降解效能。由于微生物种类和功能的多样性,一种毒死蜱降解菌往往可以降解多种农药,如产碱杆菌(sp.)、布鲁氏杆菌(sp.)对甲基对硫磷、对硫磷、毒死蜱、辛硫磷等都有一定的降解效果[73]。微生物的种类、数量、活性对于农药的代谢至关重要,而改善土壤的环境条件,特别是营养条件,如勤松土、少积水、多光照、多通气以及定期投加营养物等,以满足污染环境中已经存在的降解菌的生长需要,以便增强土著降解菌的降解能力。微生物降解的本质是酶促反应,即农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入细菌体内,然后在各种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最终将农药完全降解或分解成分子量较小的无毒或毒性较小的化合物的过程[74]。可降解农药的酶主要有加氧酶、脱氢酶、偶氮还原酶和过氧化物酶等。在许多情况下,农药的微生物降解是在多种酶的协同作用下完成的。因此,利用固定化酶对农药的降解研究国内外均已有报道,如颜慧等[75]将三嗪类除草剂扑草净降解酶固定化后应用于受污染土壤的生物强化研究,结果表明,以海藻酸钠作包埋剂将降解酶固定化,纤维为最佳的添加剂,利用固定化酶对受污染的土壤进行处理6周后,土壤中扑草净的含量减少85%。
3.2 植物修复
利用植物能忍耐和超量积累环境中污染物的能力,通过植物的生长来清除环境中的污染物,是一种经济、有效、非破坏型的污染土壤修复方式。植物对土壤中农药的修复主要包括有3种机制[76]:①许多植物可以直接从土壤中吸收农药等污染物进入植物体内,通过木质化作用或在植物生长代谢活动中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化或降解;②植物释放到根际土壤中的酶可直接降解有关化合物,其中农药类有机污染物的降解起着重要作用的植物酶是水解酶类和氧化还原酶类等降解酶,这些酶通过氧化、还原、脱氢等方式将农药分解成结构简单的无毒小分子化合物[77];③植物根际与微生物的联合代谢作用,根分泌物和分解物给微生物提供营养物质,而微生物活动也促进了根系分泌物的释放,两者互惠互利,共同加速根际区农药的降解。目前,人们在利用植物对一些杀虫剂污染土壤的修复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以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Lunney等[78]研究西葫芦、大牛毛草、紫花苜蓿、黑麦草和南瓜5种植物在温室内对DDT及其代谢产物DDE运输传导和修复能力时发现,两种葫芦科植物南瓜和西葫芦具有较强的运输和富集能力。Pereira等[79]研究了地中海蓟和埃里卡藻对杀虫剂HCHs同分异构体的吸收和分布,在地中海蓟和埃里卡藻的组织中β-型的HCHs所占的比例最大,且地上组织比在根中的HCHs含量要大得多,这些结果对于修复HCHs污染的土壤有很重要的意义。文献报道香蒲对甲基对硫磷有很高的去除率,是一种很有应用前景的植物修复候选物[80]。Flocco等[81]将紫花苜蓿放在10 mg/L的保棉磷中培养,结果显示种植紫花苜蓿可以使保棉磷的半衰期由10.8天下降到3.4天。Garcinuño等[82]研究表明了狭叶羽扇豆种子对杀虫剂甲萘威、苯线磷和氯菊酯有极强的保留能力。
植物修复几类常用除草剂的研究也有一些报道。研究发现狼尾草在污染土壤中生长80天后,能将莠去津和西玛津的降解率分别提高23% 和32%[83]。Lin等[84]发现风倾草降解了80% 以上的莠去津;Kruger等[85]研究发现地肤草可明显地吸收多年沉积的莠去津,降低土壤中生物可利用的莠去津量,且莠去津的降解不受污染土壤中其他农药存在的影响。Gaskin等[86]研究表明在外部根际菌群与宿主植物松树共存时,对于土壤中的莠去津其修复效率比单独的植物修复高3倍。这些研究表明利用植物降解污染土壤中的莠去津是可行的。虞云龙等[87]通过对根际土壤和非根际土壤中丁草胺降解的研究发现,棉花、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种植明显促进了丁草胺的降解,其降解半衰期缩短了26.6% ~ 57.2%。Olette等[88]研究了浮萍、伊乐藻和水盾草对磺酰脲类除草剂啶嘧磺隆的吸收能力,发现吸收能力从高到低依次是浮萍、伊乐藻和水盾草。Li等[89]研究发现,多花黑麦草能吸收氟乐灵,并在植株体内将其代谢。Conger和Portier[90]研究发现黑柳、北美鹅掌楸、落羽杉、黑桦及栎属植物都能有效地降解除草剂灭草松。近年来,将特定外源基因导入植物以提高植物对农药的降解效率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如表达CYP2B6基因的水稻植株对除草剂呋草黄的降解作用至少增强了60倍;表达大豆CYP71A10和P450还原酶基因的烟草植株,对苯脲型除草剂降解能力提高20% ~ 23%[ 91-92]。植物修复具有的经济有效、绿色环保、以太阳能为驱动等优点使得该技术成为非常适合我国国情的实用技术,但是植物修复也存在其局限性,比如不能降解环境中所有的有机农药污染,且对农药浓度有要求,只有适宜浓度范围植物修复才能实现,此外植物修复周期比较长。
3.3 菌根修复
菌根是土壤真菌菌丝与植物根系形成的共生体。据报道,外生菌丝一方面增加了根与土壤的接触,能增强植物的吸收能力,改善植物的生长,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和耐受能力[93];另一方面菌根化植物能为真菌提供养分,维持真菌代谢活性,并且菌根有着独特的酶途径,用以降解不能被细菌单独转化的有机物[4]。林先贵等[94]研究了施用绿麦隆、二甲四氯和氟乐灵的土壤接种菌根对白三叶草生长的影响,发现接种VA菌根真菌后,植株的菌根侵染率、生长量和氮、磷的吸收都高于不接种的对照植株。另有研究表明,菌根真菌摩西球囊霉(Glomus mosseae)侵染的大豆,其生长不受杀虫剂乐果的影响,施用0.5 mg/L的乐果反而增加了摩西球囊酶的孢子萌发[95]。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菌根化植物对农药有很强的耐受能力,并能把一些有机成分转化为菌根真菌和植株的养分源,降低农药对土壤的污染程度。
4 农药污染农田的综合治理对策
4.1 加强农田土壤农药残留的调查研究
加强土壤农药污染的监测,了解土壤农药污染的情况,是防治土壤农药污染的必要措施之一。然而我国有关不同区域、不同土壤利用方式下农田土壤农药污染残留累积情况的报道还很不足,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情况也缺乏常规化的监测数据。针对不同类型的农药在环境中的半衰期、毒性效应以及环境行为差异较大的特点,有必要加强农田土壤的农药残留情况及不良后果的调查研究,为制定合理恰当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4.2 加大危害较大农药的替代技术研发力度
有些农药在中国使用较多,暂时还没有技术上和经济上都可行的替代品,短期内难以完全淘汰,对于此类农药应该加大力度进行替代技术的研究。对于那些危害较小、替代困难的农药,要加强管理,做到合理使用以减小用量,使危害最小化。还可实施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技术(IPM)和农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从而实现少用农药。同时,要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研发低毒高效农药,积极开展生物防治技术的研究。近些年来,无毒或低毒无污染的生物农药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已研究了80种不同的浸染生物种,防除约70种杂草。生物杀虫剂在我国加快发展,苏云金杆菌、阿维菌素和病毒杀虫剂等已开始在一些主要作物上得到广泛应用,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大生物农药的研制和推广。
4.3 调整农艺措施,增强土壤的自净能力
农药在土壤中可通过微生物分解、水解、光化学分解等作用而降解,因此可通过各种农业措施,调节土壤结构、黏粒含量、有机质含量、土壤pH、微生物种类数量等增强土壤对农药的降解能力。此外,通过翻土使除草剂、DDT以及某些有机磷农药暴露在太阳光下,以促进其光化学降解。
4.4 引导农民合理用药和安全施药技术,提高环保意识
造成我国农田土壤农药污染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药使用技术落后。对农药的具体施用方法、施用时间、所用器械以至于废药的处理、容器清洗等诸多方面进行严格规定和规范操作,以确保土壤环境及作物生长安全性最高,而完善的培训制度是规范执行的必要保障。因此有必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和其他信息媒体的建设,及时发布农情、病虫害监测动态信息,通过广开宣传渠道,利用广播、影视、录像和印发或免费赠送防治手册、科普读物,举办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各种植保短训班、防病虫战役前的集训班等,全面向农民宣传讲授科学种田、科学施药的使用新知识与技术,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
4.5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质量标准体系
针对当前农药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问题,首先要建立健全现行的农药管理法规体系,要加紧制定和出台农药污染防治和农药环境安全监督管理方面的条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强化检测与执法工作,为消除农药危害创造条件。其次是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建立起一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农药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检验体系,对现有生产企业的产品实施质量认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流通领域管理,促进农药市场的良性发展。
[1] 刘长江, 门万杰, 刘彦军, 等. 农药对土壤的污染及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J].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2002, 18(4): 295–297
[2]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M]. 2版.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3] 仲维科. 我国药品的农药污染问题[J]. 农药, 2000, 39(7): 1–4
[4] 何丽莲, 李元. 农田土壤农药污染的综合治理[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3, 18(4): 430–434
[5] 赵为武. 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及治理对策[J]. 植物医生, 2001, 14(3): 10–13
[6] 肖军, 赵景波. 农药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防治对策[J]. 安徽农业科学, 2005, 33(12): 2376–2377
[7] 苏少泉.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与除草剂发展[J]. 现代化农业, 2003, 291(10): 4–6
[8] 梁丽娜, 郭平毅, 李奇峰. 中国除草剂产业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J]. 中国农学通报, 2005, 21(10): 321–323
[9] 魏福香. 除草剂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 安徽农业, 1999(3):8–9
[10] 王宏伟, 梁业红, 史振声, 等. 作物抗草甘膦转基因研究概况[J]. 作物杂志, 2007(4): 9–12
[11] 苏少泉. 除草剂作用靶标与新品种创制[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 268
[12] Kolpin D W, Sneck-Fahrer D A, Hallberg G R, et al. Temporal trends of selected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 Iowa’s groundwater, 1982–95: Are things getting better?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1996, 26(4): 1007–1017
[13] Oldal B, Maloschik E, Uzinger N, et al. Pesticide residues in Hungarian soils[J]. Geoderma, 2006, 135: 163–178
[14] Tappe W, Groeneweg J, Jantsch B. Diffuse atrazine pollution in German aquifers[J]. Biodegradation, 2002, 13(1): 3–10
[15] 叶常明, 雷志芳, 弓爱君, 等. 阿特拉津生产废水排放对水稻危害的风险分析[J]. 环境科学, 1999, 20(3): 82–84
[16] 王子健, 吕怡兵, 王毅, 等. 淮河水体取代苯类污染及其生态污染[J]. 环境科学学报, 2002, 22(3): 300–303
[17] 严登华, 何岩, 王浩. 东辽河流域地表水体中Atrazine的环境特征[J]. 环境科学, 2005, 26(3): 203–208
[18] 王万红, 王颜红, 王世成, 等. 辽北农田土壤除草剂和有机氯农药残留特征[J]. 土壤通报, 2010, 41(3): 716–721
[19] 苏少泉. 草甘膦与抗草甘膦作物[J]. 农药, 2008(9): 631–636
[20] 陈燕玲. 2014年世界杀虫剂市场概况[J]. 现代农药, 2016, 15(2): 1–7
[21] 刁春友. 江苏省农用杀虫剂使用现状与前景分析[J]. 世界农药, 2010, 32(增刊): 1–3
[22] 化学工业部农药情报中心站. 国外农药品种手册[M].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0
[23] 徐鹏, 封跃鹏, 范吉, 等. 有机氯农药在我国典型地区土壤中的污染现状及其研究进展[J]. 农药, 2014, 53(3): 164–166
[24] 安琼, 董元华, 王辉, 等. 南京地区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残留及其分布特征[J]. 环境科学学报, 2005, 25(4): 470– 474
[25] 耿存珍, 李明伦, 杨永亮, 等. 青岛地区土壤中OCPs和PCBs污染现状研究[J]. 青岛大学学报, 2006, 21(2): 42–48
[26] Li J, ZhangG, Qi S H, et al. Concentrations, enantiomeric compositions, and sources of HCH, DDT and chlordane in soil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6, 372: 215–224
[27] Coupe R H, Manning M A, Foreman W T, et al. Occurrence of pesticides in rain and air in urban and agricultural areas of Mississippi, April-September 1995[J]. 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 2000, 248(2-3): 227–240
[28] Liu X, Zhang G, Li J, et al. Seasonal patterns and currentsources of DDTs, chlordanes, hexachlorobenzene, and endosulfanin the atmosphere of 37 Chinese citi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9, 43(5): 1316–1321
[29] 武焕阳, 丁诗华. 硫丹的环境行为及水生态毒理效应研究进展[J]. 生态毒理学报, 2015, 10(2): 113–122
[30] Khan S U, Hamihon H A. Extractable and bound (nonextractable) residues of prometryn and its metabolites in an organic soil[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1980, 28(1): 26–132
[31] 杨德宝. 浅析蔬菜农药污染及解决途径[J]. 湖北植保, 2003(1): 35–36
[32] 杀菌剂占比增加,新品难觅[J]. 行业观察, 2013(8): 94–100
[33] 宋卫国, 李宝聚, 赵志辉. 杀菌剂安全风险及解决途径[J]. 中国蔬菜, 2008(9): 1–4
[34] 杨彩宏, 田兴山, 岳茂峰, 等. 农田杂草抗药性概述[J]. 中国农学通报, 2009, 25(22): 236–240
[35] 唐振华. 我国昆虫抗药性研究的现状及展望[J]. 昆虫知识, 2000, 37(2): 97–103
[36] 黄顶成, 尤民生, 侯有明, 等. 化学除草剂对农田生物群落的影响[J]. 生态学报, 2005, 25(6): 1451–1458
[37] Yuan S Z, Wu J C, Xu J X, et al. Influences of herbicides on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of rice[J]. Acta Phytophylacica Sinica, 2001, 28(3): 274–278
[38] Grinstein A, Lisker N, Katan J, et al. Herbicide-induced resistance to plant wilt diseases[J]. Physiological Plant Pathology, 1984, 24(3): 347–356
[39] 杨敏, 李岩, 王红斌, 等. 除草剂草甘膦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J]. 土壤通报, 2008, 39(6): 1380–1383
[40] 闫颖, 袁星, 樊宏娜. 五种农药对土壤转化酶活性的影响[J]. 中国环境科学, 2004, 24(5): 588–591
[41] Endo T, Taiki K, Nobatsura T, et al. Effects of insecticidecartap hydrochloride on soil enzyme activities, respiration and on nitrification[J]. Journal of Pesticide Science, 1982, 7: 101–110
[42] Sannino F, Gianfreda L. Pesticide influence on soil enzymaticactivities[J]. Chemosphere, 2001, 45: 417–425
[43] Gundi V A K B, Viswanath B, Chandra M S, et al. Activities of celluloseand amylase in soils as influenced by insecticide interactions[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07, 68: 278–285
[44] Gianfrda L, Rao M A, Piotrowska A, et al. Soil enzyme activities as affected by anthropogenic alterations: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acticesand organic pollution[J]. 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 2005, 341: 265–279
[45] Widenfalk A, Bertilsson S, Sundh I, et al. Effects of pesticides on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activity of sediment microbese responses atvarious levels of microbi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8, 152: 576–584
[46] 张瑞福, 崔中利, 何健, 等. 甲基对硫磷长期污染对土壤微生物的生态效应[J]. 农村生态环境, 2004, 20(4): 1–5
[47] Bending G D, Rodriguez-Cruz M S, Lincoln S D. Fungicide impacts on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soils with contrasting management histories[J]. Chemosphere, 2007, 69: 82–88
[48] Eisenhauer N, Klier M, Partsch S, et al. No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esticidesand plant diversity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and respiration[J]. Applied Soil Ecology, 2009, 42: 31–36
[49] Lin X Y, Zhao Y H, Fu Q L, et al. Analysis of culturable and unculturable microbial community in bensulfuron- methylcontaminated paddy soil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08, 20: 1494–1500
[50] 李淑梅, 盛东峰, 许俊丽. 苯磺隆除草剂对农田土壤动物影响的研究[J]. 土壤通报, 2008, 39(6): 1369–1371
[51] 蔡道基, 张壬午, 李治祥, 等. 农药对蚯蚓的毒性与危害性评估[J]. 农村生态环境, 1986, 2(2):14–18
[52] Bouwman H, Reinecke A J. Effects of carbofuran on the earthworm, Eiseniafetida using a defined medium[J].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1987, 38(2): 171 –178
[53] 孔军苗, 郑荣泉, 顾磊, 等. 乙草胺对中型土壤动物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05, 24(3):576–580
[54] 邱咏梅, 郑荣泉, 李灿阳, 等. 百草清除草剂对农田生态系统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J]. 土壤通报, 2006, 37(5): 976–980
[55] Streit B, Peter H M. Long-term effects of atrazine to selected fresh water invertebrates[J]. ArchivHydrobiol, 1978, 55: 62–77
[56] Donson S L, Merritt C M, Shannahan J P. Low exposure concentrations of atrazine increase male production in Daphnia [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1999, 18(7): 1568–1573
[57] 南旭阳. 除草剂“草甘膦”对鲫鱼外周血红细胞微核及核异常的影响[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 24(4): 329–331
[58] DeLorenzo M E, Taylor L A, Lund S A, et al. Toxicity and bioconcentration potential of the agricultural pesticide endosulfanin phytoplankton and zooplankton[J].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2002, 42(2): 173–181
[59] Daoud D, Fairchild W L, Comeau M, et al. Impact of anacute sublethal exposure of endosulfan on early juvenilelobster ()[J]. Aqua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2(2): 14–40
[60] Dimitrie D A, Sparling D W. Joint toxicity of chlorpyrifos and endosulfan to Pacific Treefrog ()Tadpoles[J].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and Toxicology, 2014, 67: 444–452
[61] 程燕, 周正英, 单正军. 长江三角洲流域保护水生生物优先控制农药品种筛选[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4, 30(6): 785–794
[62] 曹坳程, 郭美霞, 蒋红云, 等. 抗除草剂作物对未来化学农药发展的影响[J]. 生物技术通报, 1998(4):22–24
[63] 杨晓霞, 龚久平, 柴勇, 等. 我国农产品产地环境现状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 南方农业, 2014, 8(28):68–72
[64] 吴燕君, 吴善钰. 慈溪市1992 ~ 2000 年农药中毒情况分析[J]. 职业与健康, 2002, 18(2):32–33
[65] 叶雪珠, 赵申燕, 王强, 等. 蔬菜农药残留现状及其潜在风险分析[J]. 中国蔬菜, 2012(14): 76–80
[66] 刘德英, 张剑波, 丁剑. 我国农业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使用现状和对策[J]. 自然生态保护, 2005(6): 45–50
[67] Mulbry W, Kearney P C. Degradation of pesticides by microorganisms and the potential for genetic manipulation[J]. Crop Protection, 1991, 10: 334–346
[68] 虞云龙. 农药微生物降解的研究状况与发展策略[J]. 环境科学进展, 1996, 4(3):28–35
[69] 刘新, 尤民生, 廖金英. 土壤中毒死蜱和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研究[J]. 应用生态学报, 2004, 15(7): 1174–1176
[70] 杨丽, 赵宇华, 张炳欣, 等. 一株毒死蜱降解细菌的分离鉴定及其在土壤修复中的应用[J]. 微生物学报, 2005, 45(6): 905–909
[71] 王金花, 朱鲁生, 王军, 等. 3株真菌对毒死蜱的降解特性[J].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2005, 11(2): 211–214
[72] Mukherjee I, Gopal M, Dhar D W. Disappearance of chlorpyrifos from cultures of chlorella vulgaris[J].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2004, 73: 358–363
[73] 张瑞福, 戴青华, 何健, 等. 七株有机磷农药降解菌的降解特性比较[J]. 中国环境科学, 2004, 24(5): 584–587
[74] 孙秀敏, 郑培忠, 万旗东, 等. 农用化学品污染及其控制技术[J]. 现代农药, 2011, 10(5): 4–11
[75] 颜慧, 冯炘, 李军红, 等. 扑草净降解酶的固定化及其对受污染土壤的生物强化研究[J]. 南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 36(2): 109–115
[76] 卢桂宁, 党志, 陶雪琴, 等. 农药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研究进展[J]. 土壤通报, 2006, 37(1): 189–193
[77] Steer J, Harrisja A. Shift in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in rhizosphere and nonrhizosphere soils during the growth of[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0, 32(6): 869–878
[78] Lunney A I, Zeeb B A, Reimer K J. Uptake of weathered DDT invascular plants: Potential for phytoremediati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 , 38(22): 6147–6154
[79] Pereira R C, Monterroso C, Macias F, et al. Distribution pathways of hexchlorocyclohexane isomers in a soil- plant-air system[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8, 155(2): 350–358
[80] Amaya-Chávez A, Martinez-Tabche L, López-López E L, et al. Methyl parathion toxicity to and removal efficiency byin water and artificial sediments[J]. Chemosphere, 2006, 63(7): 1124–1129
[81] Flocco C, Carranza M P, Carvajal L G, et al. Removal of azinphosmethyl by alfalfa plants (L.)in a soil-free system[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4, 327(1-3): 31–39
[82] Garcinuño R M, Fernández-Hernando P, Cámara C. Evaluation of pesticide uptake byseeds[J]. Water Research, 2003, 37(14): 3481–3489
[83] Jordahl J L. Effect of hybrid poplar tree on microbial populations important to hazardous waste bioremediation[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1997, 16(6): 1318–1321
[84] Lin C H, Lerch R N, Garrett H E, et al. Bioremediation of atrazine-contaminated soil by foragegrasses: Transformation, uptake and detoxification[J]. Environmental Quality, 2008, 37(1): 196–206
[85] Kruger E L, Anhalt J C, Sorenson D. Atrazine degradation inpesticide-contaminated soils: Phytoremediationpotential// Kruger E L, Anderson T A, Coats J R. Phytoremedi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taminanants[C]. ACS Symposium Series, 1997, 664: 54–64
[86] Gaskin J L, Fletalher J. The metabolism of exogenously providedatrazine by the ectomycorrhizal fungusand the host plant// Kruger E L, Anderson T A, Coats J R. Phytoremedi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taminants[C]. ACS Symposium Series, 1997, 664: 152–160
[87] 虞云龙, 杨基峰, 潘学东, 等. 作物种类对根际土壤中丁草胺降解的影响[J]. 农药学学报, 2004, 6(1):46–52
[88] Olette R, Couderchet M, Biagianti S, et al. Toxicity and removal of pesticides by selected aquatic plants[J]. Chemosphere, 2008, 70(8): 1414–1421
[89] Li H, Sheng G Y, Xu O Y. Uptake of trifluralin and Lindanefrom water by ryegrass[J]. Chemosphere, 2002, 48(3): 335–341
[90] Conger R M, Portier R J. Phytoremediation experimentation with the herbicide bentazon[J]. Remediation, 2006, 7(2): 19–37
[91] Kawahigashi H, Hirose S, Hayashi E, et al. Phytotoxicity and metabolism of ethofumesate in transgenicrice plantsexpressing the human CYP2B6 gene[J]. 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2002, 74(3):139–147
[92] Siminszky B, Freytag A M, Sheldon B S, et al. Co-expression of a NADPH:P450 reductase enhances CYP71A10-dependent phenylurea metabolism in tobacco[J].Pesticide Biochemistryand Physiology, 2003, 77(2):35–43
[93] 耿春女.生物修复的新方法—菌根根际生物修复[J].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2001, 2(5): 20–26
[94] 林先贵, 郝文英, 施亚琴. 三种除草剂对VA菌根真菌的侵染和植物生长的影响[J]. 环境科学学报, 1991, 11(4):439–444
[95] Menendez A, Martinez A, Chiocchio V, et al. Influence of insecticide dimethoateon arbuscular mycorrhizal colonisation and growth in soybeanplants[J]. International Microbiology, 1999, 2(1): 43–45
Present Pollution Status and Control Strategy of Pesticides in Agricultural Soils in China:A Review
ZHAO Ling, TENG Ying*, LUO Yongming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Remediation,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residual pesticides in agricultural soils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because of substantive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s in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and pollution status of pesticides, including herbicide, insecticide and fungicide, in agricultural soils in China were presented in this review. The harm of pesticide resistance and the risks of residual pesticides on ecological and human health were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bial remediation, phytoremediation and mycorrhizal bioremediation on pesticide contaminated agricultural soils were also introduced. On this basis, the control strategies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pesticide contaminated agricultural soils were proposed.
Agricultural soils; Herbicide; Insecticide; Fungicide; Ecological risks
10.13758/j.cnki.tr.2017.03.001
X53
A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308) 和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BK20150049)资助。
(yteng@issas.ac.cn)
赵玲(1977—),女,江苏金湖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有机污染土壤修复研究。E-mail:zhaoling@issas.ac.cn
- 土壤的其它文章
- 欧洲地理学会2017学术年会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