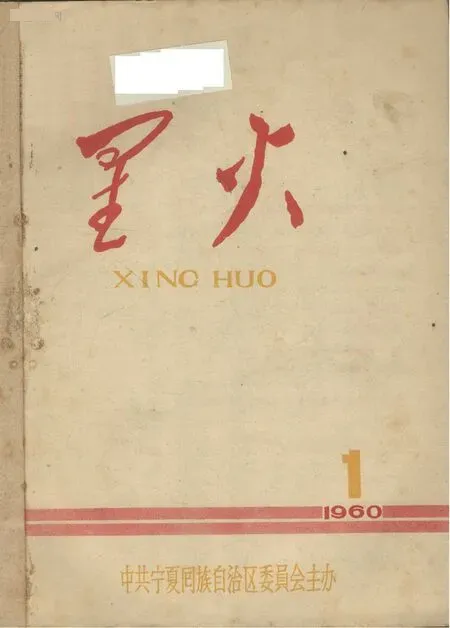刘玉栋小说三题
○刘玉栋
刘玉栋小说三题
○刘玉栋

刘玉栋,1971年出生。山东庆云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天涯》《上海文学》等多家文学期刊;出版有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小说集《我们分到了土地》《公鸡的寓言》《火色马》等十多部。小说被多家选刊转载,并入选多种选本。两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首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韩等文字。
喜鹊喳喳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池塘里的冰慢慢地化开了。柳树一夜之间发出了新芽。一场细如牛毛的春雨,安静地下了三天三夜,待太阳一出,原野全绿了,大地猛地变得蓬蓬勃勃。隔着教室的窗户,牲口脖子上悠扬的铃铛声,时常传进耳朵里,我的心思也随着它飘出去好远好远。
有一天放学后,树墩站在门口等着我,说:“冬冬,走,到我家去,我爸爸让我送你样东西。”
志成舅舅要送我东西!我的心一下子跳得飞快。是不是要送我一只小鸽子?志成舅舅养了一群鸽子,他曾经说过要送我一只鸽子的。他说过的话,肯定不会忘的。可我还是压住兴奋劲儿,问树墩舅舅要送我什么。
树墩一笑,很神秘地说:“很好玩很好玩的东西,见到就知道了。”
我问:“是能动的还是不能动的?是死的还是活的?”
树墩说:“当然是活的了。”
我更加肯定了心里的想法,高兴得禁不住蹦起来。
可是,事情总是那么出人意料。我们来到树墩家。树墩捧过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我顿时傻了眼。活的不假,是一只鸟也不假,可它绝对不是一只小鸽子。这只小家伙歪着黑色的小脑瓜,看到我们,便张开大嘴吱吱叫,它的嘴巴四周,还有一圈儿黄嘴丫。树墩用手指头挖了一些和好的小米面,它一口便把食儿吞了进去,还使劲儿抻了抻脖子。那样子太可爱了。动一动黑色的圆眼珠,张一张黑色的小翅膀,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而翅膀两侧则是毛茸茸的白色。
树墩看我一眼,说:“一只小小的灰喜鹊,我爸爸下地干活时,在树下捡的,它肯定是不老实,从树上掉了下来。我爸爸让我送给你,他说他还欠你一只小鸽子呢。不过,小鸽子不好养,他没有送给你。而喜鹊是杂食动物,啥都吃,所以他让我送给你。”
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小东西。我把盒子抱进怀里,眼睛紧紧地盯着它,一刻都舍不得离开。我就这么抱着它回到家。没想到,姥姥和妈妈却反对我饲养它。
姥姥说:“喜鹊是野鸟,养不活的,快给树墩送回去。”
妈妈说:“玩物丧志,你懂不懂?再说,它太脏了,会把疾病传染给你的。”
我低着头,紧紧地抱着盒子不松手。哼,不让我养,我就不吃饭。
后来,还是姥爷说:“好了,先吃饭。愿意养就养吧,别耽误学习就行。”
姥爷找出一个圆圆的大竹筐,又在下面铺上一张报纸,说:“来,放在这里面,这里面宽绰。吃完饭,姥爷教你怎么养。姥爷小时候,可是养喜鹊的高手啊。”
真的?姥爷也养过喜鹊,我一听,便来了精神,忙把小喜鹊递给姥爷。姥姥很不高兴,没好气地跟姥爷说:“你就宠着他吧,孩子早晚让你宠坏了。”姥爷好像没听见似的,笑眯眯地帮我打理喜鹊的家。
姥爷说,养喜鹊的学问可多了。首先得用心,喜鹊是很聪明的鸟,你待它不好,它会记住的。再就是如何喂养,喜鹊尽管啥都吃,但小喜鹊还是要喂得讲究些,平时用香油拌点玉米面,一天喂它三次四次的,每次要让它少吃,每天再给它两只活虫子当点心吃就行了。
活虫子?老天爷,这哪儿弄去?
“放心,虫子交给我来弄,”姥爷说:“最要紧的一件事,是防猫。”
“防猫?”我惊呼。
“对,猫最喜欢偷吃小鸟了。”姥爷说,“猫吃小鸟就像吃一块点心。”
我突然明白了。我说今天怪了,自从我走进门,这只大狸花猫就“喵喵”地围着我转呢。我寻思它喜欢我呢,原来它是想吃我的小喜鹊呀。我恨不得一脚把它踢出门去。
姥爷说:“不要紧,我把大竹筐盖上盖子,挂在屋梁上,猫够不到,就只能干瞪眼了。”
多亏了姥爷。以后的日子里,每天放学后,我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踩着凳子,摘下大竹筐,看我的小喜鹊。在我和姥爷的精心喂养下,小喜鹊长得很快。没过几天,它就长出尾巴来,并且越来越长。小喜鹊见到我,就会激动地扑棱翅膀,张着嘴要吃的。它嘴角上的那一圈儿黄嘴丫渐渐地褪去了,嘴巴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有劲儿了。
一个周末,天气非常好,刚脱掉厚衣服,觉得像蜕了层皮儿,浑身轻松。我把竹筐子提到院子里,把喜鹊从竹筐里捧出来,放到地上。喜鹊一下子来了精神,它朝着我,翘了翘长长的尾巴,又蹦跶两下,突然张开翅膀,想要飞起来的样子,但它离开地面没有两秒钟,最终还是跌跌撞撞地扑进我怀里。我高兴得不得了,忙喊来姥爷。
“姥爷,喜鹊会飞了。”我激动地说。
姥爷接过喜鹊去看了看,点点头说:“嗯,现在可以这样来训练它了。你蹲在墙根下,伸开手指头,弄点食儿放在上面。”
说着,姥爷双手捧着喜鹊,走到枣树下。我和姥爷相隔大概十米的距离。我按照姥爷说的准备好。姥爷朝着我蹲下来,撒开手里的喜鹊。我心里很紧张,瞪着眼,不时地弯动着手指上的食物。
只见喜鹊歪了歪小脑瓜,蹦跶了几下,突然张开翅膀,朝我飞过来。只是它还不能完全飞得起来,它歪着身子,踉踉跄跄的,爪子还不时地撑一下地面。它飞到我面前,一伸嘴巴,便把食儿吞了下去。它嘴巴的劲头真大,啄得我手指头生疼,然后,依然急切地望着我。那样子可爱极了。
姥爷说:“该架养了。”
我没弄明白姥爷说的话。不过一会儿,姥爷便用铁丝和一根带皮的柳木棍儿做了个架子。姥爷把架子往枣树枝上一挂,接着,把喜鹊放到架子上。一开始,那架子晃悠得厉害,喜鹊也晃悠了两下身子,可它的两只爪子牢牢地抓着木棍。它一点儿都不害怕。姥爷把一只面包虫举到它面前,被它一口便啄进嘴里。它高兴地在木棍上腾挪了几下爪子,歪着头看着我们,猛地“喳喳”叫了两声,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姥爷,那竹篮子,还用吗?”我问。
“还得用几天,等它完全会飞了,就用不着了。”
“那,它晚上睡觉怎么办?”我还是有些迷惑。
“睡觉也在这架子上呀。”
“它不累吗?”
“哈,冬冬,这是鸟的习性啊。”
听姥爷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一些。
不过,在学校里,我可有了吹牛的资本。我和同学们谈我养的喜鹊,都快把我的喜鹊吹成一只神鸟了。我领着他们回家来看我和喜鹊的表演。当我把蹲在架子上的喜鹊提出来,挂在枣树枝子上时,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
张得月喊:“它会飞走的。”要论调皮捣蛋,张得月是我们班上的第一名。
我笑了笑,随手给喜鹊喂了口馒头,然后双手把它捧在手里,说:“让它飞走吧。”说着,我一用劲儿,把它抛上天空。同学们都“哇”地叫起来。只见喜鹊飞过屋顶,掠过树梢,越飞越高。
孙大头说:“不好了,飞远了。”
张得月说:“肯定飞走了。”
大家都昂着脖子抬着头,盯着在空中盘旋的喜鹊,脸上露出焦急的样子。可我心里呢,一点都不慌张。我高高地举起胳膊,朝着喜鹊招了招手,“呵呵”叫了两声。只见喜鹊箭头一般朝我飞来。我放下胳膊,伸手拍了拍肩膀。喜鹊一下子落在我肩膀上。同学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尽管被喜鹊的爪子抓得好疼,但我的心里充满着自豪感。
我把喜鹊放回到架子上,又喂了它一口馒头,算是奖赏吧。喜鹊好像是知道自己演出成功,翘翘尾巴,“喳喳”地叫了两声,很得意的样子。
张得月凑上前,说:“让我摸摸它,行不?”
我笑着说:“它可是认生人的。”
张得月嬉皮笑脸,龇着兔子牙说:“没事的,我只是摸一下了。”
说着,张得月便伸出手去。还没等摸到喜鹊的羽毛呢,只见喜鹊扭过头,张开嘴巴,使劲儿在张得月的手上拧了一把。速度快到一眨眼的工夫。只听张得月“哎呀”叫了一声,向后连退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伙都哈哈地笑弯了腰。
张得月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捧着被喜鹊拧红了的手指头说:“你们看,你们看,这鸟还真厉害呢。”
喜鹊昂着头,在架子上挪了两下步子,又“喳喳”地叫了两声,看上去,对张得月似乎是不屑一顾的样子。
这一下,我和我的喜鹊都出了名。来找我玩的小朋友明显地多起来。星期天,我肩头上扛着喜鹊,走到哪里,哪里就跟着一帮小伙伴。大伙都听我的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这么骄傲过。
天气渐渐地热了。梦也渐渐地多起来。
有一天夜里,我一夜都梦到喜鹊喳喳的叫声。早晨醒来,我跑到院子里,看到喜鹊蹲在架子上,劲头十足。我放下心来,回到屋里,却看到姥爷和姥姥都是哈欠连天,我也禁不住打了两个哈欠。
我说:“姥爷,我做了一夜的梦,梦到喜鹊喳喳地叫个不停。”
姥姥撇撇嘴说:“什么做梦?根本就不是做梦,你那神鸟就是喳喳地叫了一宿。”
真的吗?我将信将疑地看看姥爷。
姥爷点点头,说:“冬冬,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件事呢。喜鹊真的长大了,我们得让它回家了。”
喜鹊回家?我真的搞不明白。这里不就是它的家吗?
“冬冬,喜鹊的家不是村北的那片松树林,就是鬲津河大堤上的那片杨树林,反正那里才是它的家。我们该把它放回去了。”姥爷说道。
“不!”我一听急了,说:“你们是烦它叫,才想撵他走的。”
“不是的,”姥爷摇摇头说:“你想想,它长大了,它得需要伙伴玩啊。它太孤单了,它才叫呢。”
“它一点都不孤单。我就是它的伙伴,我天天都陪它玩啊。”我据此力争。
“傻孩子,你是人,它是鸟。你怎么会是它的伙伴呢?那些在树林里飞来飞去的喜鹊,才是它的伙伴呀。”姥爷说。
“不,反正我不会放它走的,它是我的。”我愤愤不平。
“还有啊冬冬,它那么小就离开了爸爸妈妈,它当然不是愿意离开的,它是因为调皮,才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现在,我们把它养大了。它会飞了,它想念它的爸爸妈妈了,它应该回去找它的爸爸妈妈了。”
姥爷这么一说,我脑袋里“嗡”地叫起来。姥爷说得在情在理啊,它的爸爸妈妈也肯定想它了。可是,可是……我一着急,禁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姥姥赶紧走过来,说:“别哭了,别哭了,先吃饭吧。”
那天早晨,我没有吃饭。后来,我找到姥爷,说:“姥爷,再让我跟它玩一天,好不好?”
姥爷拍了拍我的后脑勺,说:“真是个好孩子。”
牛掉进了井里
白雾村的春天真短,枣树叶子刚能遮成阴凉地,天便热起来。
我想念我的灰喜鹊。
我问姥爷:“灰喜鹊去了哪里?”
姥爷朝北边指了指,说:“放进了村北的树林里,你放心好了,那里有成群的喜鹊,它很快就会找到伙伴的。”
我爬上屋顶,朝北边看。目光掠过成片的菜畦和成排的枣树,我看到了更远处那墨绿色的松树林,好像是有一些鸟儿在那里起起伏伏。我看不清楚。
我的灰喜鹊会在那里吗?它还认识我吗?它见到我,还会飞到我的肩头上来吗?我突然特别想念它。
在学校里,我见到树墩。我把树墩拉到篮球架下面,跟他说了我对喜鹊的想念。树墩一拍胸脯说:“等到了星期六,我带你去。”我高兴极了,最善解人意的就是树墩表哥。
我掐算着日子,盼着星期六早点到。今天是星期三,明天是星期四,后天是星期五,哇,星期六总算到了。吃罢早饭,我就来到志成舅舅家。志成舅舅正牵着牛出门,说一声树墩在家呢,便走远了。我走进院子,看到树墩正弯着腰坐在树下磨镰刀,身子一耸一耸的,很专注的样子。我悄悄地来到他身后,“嗨”地一声,把他吓了一跳。
“咱们走吧。”我刚说完,只见志成舅妈正瞪着眼看我。
“冬冬,去地里割猪草,你怎么不背草筐呢?”舅妈问我。
我愣了一下,看到树墩朝我使眼色,忙说:“我先看看树墩表哥准备好没有?我这就去背草筐。”说完,我便走出来。
树墩接着追了出来。他背着草筐,提着镰刀,朝我眨眨眼,低声说:“要不是说跟你一块去割草,我妈才不让我去玩呢,她让我牵着牛,跟着我爹去干活。”
我吐吐舌头说:“我还用回去背草筐吗?”
树墩说:“你姥姥不用你割草,你背什么草筐。咱们走吧。”
我想想也是,如果回家说我去地里割草,姥姥还可能不放心呢。还是算了吧。
“那好吧,”我伸手说:“来,我帮你拿着镰刀。”
树墩把镰刀递给我,说:“正好,今天我带你到‘三棵树’去看看。”
“三棵树?”
“就是一敲树干,蛇会爬出来的地方啊。”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树墩曾经跟我说过那地方,说要带我去看的。
“你害怕了?”树墩问。
“有你我不怕。”我说得很干脆,尽管脊梁沟有些发凉。我们俩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三棵树,多么神秘的地方!我心里又多了一个期待。
“你说,喜鹊见到我,还会飞到我肩头上来吗?”
“当然,喜鹊是认人的,是你把它喂大的,它忘不了你。”
“太好了。”我禁不住跳起来,“阿弥陀佛,但愿能遇到我的灰喜鹊。”
我们说笑着,不一会儿便走出村子,来到村北的那座水泥桥上。我们站在桥上,看桥下的流水。我说:“这水里的鱼肯定不少。”树墩点点头说:“等放了暑假,咱们到地里找块水洼,能淘到好多鱼呢。”太好了,逮鱼是我最喜欢干的事。
“树墩、树墩,”突然身后传来喊树墩的声音。我们回头看,原来是迷糊舅。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一只脚支在地上。迷糊舅喊道:“你干什么去树墩?你们家的牛掉进村东的水井里了,还不快去看看。”
“牛掉进井里了?”树墩皱起眉头说:“你骗我玩吧?我爹牵着它干活去了。”
“我骗你干什么?你爱信不信,我先救牛去了。”说完,迷糊舅骑上车子,一溜烟窜没影了。
“他好像不是骗人?”树墩说。
我忙点点头。我觉得迷糊舅也不像是开玩笑。我们急忙扭过身,呼呼地往村东边跑。我们都知道村东的水井,是刚刚挖好的新水井。上个星期天,我和张得月他们去看了,水井刚刚修好,从井底往上全部砌的是新砖,一直砌到井口周围好大的一片。那井口跟一间房子那么宽,探头往下一看,好深好深,脚心都发痒呢。
志成舅舅怎么把牛牵到井里去了?我一边跑,一边瞎琢磨。
果然,井口那里已经围了一些人。人们围着井口探头探脑、交头接耳,什么表情的都有,有龇着牙笑的,有咧着嘴摇脑袋的,有蹲在地上抽旱烟的……井口已经堆了好多绳子,可是,人们好像没有办法下手。
我和树墩挤进人群,来到井口,朝下一看,不禁傻了眼。只见那头大黄牛只露着一颗脑袋在外面,两只弯弯的尖角还不时地动一下。志成舅舅身上拴着绳子,已经站在了井底,井水也没到他的胸脯以上,他好像正用双手往上托着牛脖子。舅妈正愁眉苦脸地跪在井口,脑袋恨不得钻进井里去,嘴里不停地说着:“都怪你都怪你,你说你咋这么闷事儿,非得牵着牛过来看这新打的井。好了,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吧?”
树墩看到井底的牛,禁不住一下子哭了。他哭着说:“让我下去,让我也下去。”
“谁下去都不行,关键是怎么把它拉上来。”说话的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我认识他。他是村支书。姥姥说,他跺跺脚,白雾村的地都会颤的。
旁边的人们出着各种各样的主意和办法,可一说出来,很快便被村支书给否了。
“牛太大太重了,这是关键。”村支书威严地说。
站在井边的吉祥舅说:“志成啊志成,你说你平时把它喂这么好干什么?好东西舍不得给老婆孩子吃,都让牛吃了。好嘛,这下子。多亏是新井,水不深,还有时间想想办法。要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你让我提着刀子下去,把它大卸八块,大伙分吧分吧得了。”
周围的人“哄”一声笑起来。大伙都知道,吉祥舅是宰牛的。
树墩不愿意了,哭着说:“人家的牛都快不行了,你们还好意思笑。”
这时有一个人说:“要是有台大吊车就好了。”
支书说:“你说得太对了,可是,哪里去找大吊车?咱们县里也没有一台呀。”
大伙七嘴八舌,我的脑子也没闲着。我看到树墩伤心的样子,心里难受极了。刚才一提大吊车,我的脑子深处好像被什么戳了一下。我想啊想,突然想起爸爸单位基地里那高高的铁架子,那上面挂着牛头那么大的一个铁家伙,样子像葫芦似的,铁链子哗啦哗啦地从里面钻出来,能吊起好大好大的石头。我问过爸爸那是什么。爸爸告诉我说:那叫吊葫芦。
对,吊葫芦!我一下子蹦起来。当然,爸爸单位的基地那么遥远,不可能把吊葫芦拉到白雾村。我想到吊葫芦,是因为我跟着姥爷去赶年集时,路过镇上的一家工厂,看到过这个东西。当时,它正把一块厚厚的水泥板吊在空中,我就多看了两眼。
我身上陡然升起一股力气。这股力气推着我,来到威严的村支书身边。我说:“我有一个办法。”支书低头看看我,笑了,说:“呦嗬,这是谁家的孩子?”
一旁的吉祥舅跟支书介绍了我。支书马上变得亲切起来,他呵呵笑着说:“原来是个小亲戚,来,跟我说说你的办法。”说着,支书弯下腰。
我趴在他的耳朵上,低声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像是怕别人听到似的,我还伸出一只手来遮住我的嘴巴。支书听完,一巴掌拍到大腿上,大叫一声:“好办法。快,快给我自行车,迷糊,走,跟我跑一趟。”
迷糊舅蒙头蒙脑的,但得到支书的钦点,他的大板牙立刻就龇出来。支书和迷糊舅一溜烟没影了。人们呼一下围上来,问我到底是啥好主意。我马上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微笑着说:“这办法,还不知道行不行呢。”
我故作神秘,可把吉祥舅急坏了,说:“好外甥,你先跟舅舅说说不成?”
我嘿嘿一笑,说:“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
大伙说:“这小家伙,还藏着掖着,真是人小鬼大啊。”
这时候,树墩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冬冬,你出的主意肯定行,你是从大地方来的,懂得多。你要是救了我们家的牛,我跟我爸爸说,送你一群鸽子。”
我忙把树墩拉到一边。树墩肯定是急红了眼,要不,守着这么多人,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我说:“说这些话让人家笑话,现在最要紧的是救牛。你别着急,支书和迷糊舅去镇上搬救兵去了,只要人家肯帮忙,我觉得问题不大。”
接着,我把吊葫芦的事跟树墩说了。树墩高兴得蹦起来。我忙说:“先别说,如果这办法不行,还不让大伙笑掉了大牙。”
“保准行。”树墩说完,便跑到井口旁,捡起绳子,往自己身上缠了几圈儿,说:“吉祥叔,快把我放下去吧,我去帮帮我爹。”
“不行,你个头矮,井水能没了你。”吉祥舅说。
“我的个头没那么矮。”树墩说着,使劲儿挺了挺胸脯,跟吉祥舅比了比个头。说实在的,树墩的个头还真是不矮了,只是我平时没注意。
志成舅妈不愿意了,大喊道:“树墩,你个熊孩子,都啥时候了,你还乱掺合?”
树墩跺跺脚,正想反驳妈妈的话,只听一个声音从井下传来:“快,让他下来吧。”原来是志成舅舅的声音,他在井下的水中站了这么久,肯定是累了。
树墩喊一声好嘞,恨不得立刻跳下去。吉祥舅说:“慢着点,掰好井沿,扶好井边,攥紧绳子,慢慢下。”说着,边把长长的绳子递给身后的几个壮汉,边喊道:“拽好了,可别让树墩掉下去砸死牛。”大伙又是一阵笑,全然不顾志成舅妈的眼泪。
井边的人越围越多,我看到姥爷和姥姥也来了。姥姥看到我站在井边,便跑过来,把我拽到离井远一些的地方。人们开始跟姥姥讲是我出了个好主意,支书到镇上搬救兵去了。姥姥笑眯眯地说,他一个小毛孩子,能有啥好主意?
我觉得时间过得真慢,跟糖浆那么黏稠。我想到井下站在冷水里的父子俩,心里默默祈祷:快点来吧,快点来吧,但愿能把牛捞出来。要不树墩会伤心死的。
大约又过了抽一支烟的工夫,终于从远处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大伙喊着来了来了,自动让开一条路。迷糊舅的破自行车“唰”一下子冲进来,骑到井边才停住,人群禁不住发出一阵惊呼。迷糊舅一只脚撑着地面上的红砖,低头朝井下喊道:“志成哥,坚持住,你家的牛有救了!”然后他抬起头,挥着拳头喊道:“拖拉机一会就到,那上面拉着吊大石头用的吊葫芦,人家说吊头牛是小菜一碟。支书大人有令,老九爷正在打寿材,去几个人,到他家拉两块长长的木板来,越厚越好。”
“拉木板干什么?”有人问。
“这还用问,把牛吊上来的时候,横在井口上,好让牛踩在上面。”迷糊舅挥着胳膊,像个英雄似的。
去拉木板的人刚走,远处便传来拖拉机的哒哒声。只见支书在前面骑着自行车带路,脸上的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面跟着的,竟然是一辆大拖拉机,长长的车斗上,横放着一个高高的宽宽的铁管架子,像一个足球门似的。支书支好自行车,顾不得擦汗,便指挥着人们干起来。
人多力量大。人们抬着铁架子和吊葫芦,来到井口一放,大铁架子的两头,正好跨过井口的两头。太棒了!我的心一下子放下来。支书也乐了,他拍着巴掌说:太好了。支书把绳子扔给井下的志成舅舅,让他把绳子绕在牛肚子上。镇上来的人固定好铁架子后,又一边安排两个壮汉扶着。这才把吊葫芦中的铁链子哗啦哗啦顺下去。
除了镇上来的人指挥井下志成舅舅怎么做,井口突然没人说话了,只听见铁链子哗啦哗啦的声音。大家平心静气,突然,井下传来轰隆一声响,接着,开始有了如下雨一般的滴水声。
“牛出水了。”支书喊道,“往后退,都往回退。”
当湿漉漉的牛一露出井口的那一刻,人群一阵骚动,大家都禁不住鼓起掌来。志成舅妈舞动着双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好。
我悬着的一颗心,也一下子落下来。
七色玻璃球
尽管没能去看我的喜鹊,但我心里还是非常高兴。比我更高兴的当然是树墩全家。支书带着志成舅舅给镇上的工厂送了锦旗,顺便请人家喝了一顿酒。志成舅舅还专门去了趟供销社的门市部,给我买了一盒七色玻璃球。他带着树墩来找我。他知道这是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的东西。我高兴地接过来,抓出一把送给树墩。树墩不要,并且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弹弓塞进我手里,说:“送你的。”
哇,一把崭新的弹弓!榆木树杈做的弹弓架,淡黄色的胶皮气门芯弹性十足,黑皮子蛋兜儿,漂亮极了。我喜欢得不得了。我做梦都想拥有这么一把弹弓。
志成舅舅走后,妈妈、姥姥和姥爷都夸我是个聪明的孩子。更重要的是,星期一刚一上课,光头徐老师就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徐老师夸我是救牛少年的同时,把一粒白色的“子弹”精准地射在张得月的脑门上,因为张得月正搬起自己的臭脚丫子闻味儿。
下课后,张得月揉着脑门来找我,虎着脸说:“都是因为你,你救了树墩家的牛不假,可我却倒了霉,挨了一颗白子弹,咋办吧?”
我心情很好,说:“好办,我送你五个玻璃球,七色的。”
张得月一把抓住我的手,龇着大板牙说:“真的?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变脸可真够快的。我乐了,说:“君子出口,驷马难追。不过,等到了星期天才能给你,到时候,你得陪我去河堤上打麻雀。”
我知道张得月有一把弹弓,他经常把弹弓插在腰里,神气得不行。
“太好了,我正想找个伙伴一块去玩呢。”张得月拍着胸脯说。
放学后,我从大湾边挖了一大团红泥巴。红泥巴粘粘的,回到家,我把它揉成一粒粒像羊粪球大小的圆蛋蛋,晾晒在猪圈顶上。等干了,它们就是打弹弓用的子弹。我坐在猪圈顶上,盯着夕阳下一大片红彤彤的泥子弹,兴奋极了。这可都是我的杰作啊。
第二天一上午,盯着徐老师的光头,那些光滑的圆圆的泥蛋蛋总在眼前晃啊晃。放学回到家,我没进屋便爬到猪圈上,用手一捏,泥蛋蛋已经变得硬梆梆。我心里不觉痒痒起来,禁不住从书包里掏出弹弓,拿起一粒放进弹弓的皮兜里。我拽着弹弓,闭着一只眼,朝周围瞄了一圈儿,看到远处的墙根下,有一只花母鸡正悠悠达达地走着。我想,这么远,我肯定打不准的。于是,一松手,“子弹”便射出去。
我想到了徐老师手中的粉笔头。
我想到了揉着脑门的张得月。
突然,花母鸡“吱嘎”一声叫,飞起来一米多高。落下去,原地转了两圈儿,再迈步,竟然变得一瘸一拐的了。我坐在猪圈顶上,惊呆了,吓傻了。我急忙把弹弓塞进书包。还好,姥姥没从屋里出来。我急忙跳下猪圈,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屋去。那天晚上,我老实极了。做完作业,便钻进被窝。
星期天,张得月来找我。我把五个七色玻璃球放在他手里。他抚摸着玻璃球,兴奋得打了个冷战,眼睛瞪得也跟玻璃球那么圆。路上,张得月神气得很,腰里别着弹弓,走路都是飘飘忽忽的。
我和张得月爬上鬲津河大堤。我们提着弹弓,用泥巴做成的弹子,每人都装了鼓囊囊的一兜儿。我们猫着腰,走路小心翼翼的,在树林子里转啊转,果真像两个猎人一样。一旦发现目标,我们立刻蹲在潮湿的草丛里,颤抖着手举起弹弓。每到这时候我总是紧张。嗖的一声,树叶唰啦啦响了一会儿,随着颤悠悠飘下的几片树叶,麻雀轰一下全飞了,又倏忽落到另一棵树上。我和张得月又悄悄地转移到那棵树下。就这样,在紧张的猎鸟中,时间过得真快。虽然跑得快,跑得气喘吁吁,鸟儿也没打着,但还是玩得尽兴。阳光把树林照得斑驳陆离,我和张得月都感到累了。
我们坐在树林边缘的土坎上,背后是一排茂密的紫穗槐,散发着一种温馨的苦香。河堤下面不远处,是一片片的菜畦,菜畦的尽头就是清澈宽阔的鬲津河了。蝉声像透过一层层的滤纸,显得十分飘渺;昆虫在湿热的泥土里爬行;蜜蜂在菜畦的花丛中舞动着。在这种清新的环境里,古老的鬲津河宛若一个安静的少年。
张得月歪着脑袋瓜儿瞅我,他龇着大板牙,正诡秘地朝我笑。我知道他不定又打起了什么坏主意。果然,他问我饿不饿。我说是有点儿,对,我是说有点饿。他说:“你等着,我去弄点吃的东西。”
我看到他身子一出溜就滚到堤下。他跟我扮了个鬼脸,然后弯着腰消失在墨绿的菜畦里。我想这家伙有点像小兵张嘎,就缺少一支枪……我脑子里正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的那件破背心已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透过用竹竿撑起的黄瓜架,我看到他正鬼头鬼脑地向这边走来,他的双手紧紧地兜着那件红背心。背心里面鼓鼓的,突出一些诱人的形状,我似乎闻到了那青生生的甜味儿。黄瓜、西红柿。我使劲地咽了口唾沫。
意外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站住!我听到沉闷的一声喊,像闷雷似的打破了这静谧的世界。我的脖子禁不住缩了一下。我看到张得月怀里的黄瓜西红柿都露了出来。它们纷纷摔到地上,沿着水沟土坎滚得满地都是。张得月的两只手显得不知所措,他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懵了。他的面前站着一个黑塔似的小伙子,这大概使他消除了逃跑的念头。如果他的面前是个老头,我想他准会撒腿就跑。可面前却是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
这个黑家伙模样凶极了。我不认识,他可能不是白雾村的人。当然,这些菜地也不是白雾村的了。我知道,白雾村的菜地都在村北边。想到这里,我禁不住冒出一身汗来。
这个黑家伙伸出手,猛地扇了张得月一个耳光。“啪”,声音特别清脆。如果说开头张得月只是恐惧的话,那么后来他的脸上生出了仇恨,我看到他的目光里喷着火。
果然不是一个村的。我知道,如果是一个村的,下手不会这么狠的。我害怕极了。
嘿,小子,还不服气。这个黑家伙满脸的青春痘兴奋地抖动着,紧接着他又给了张得月一个耳光。
张得月满脸通红。他使劲啐了口痰。但他又能怎么样呢?谁让他偷了人家的东西呢?可是,不就是几个黄瓜西红柿吗?也不能打人这么狠呀。
我不知道哪来的胆量,大喊一声:“别打了。”
这个黑家伙抬头看到了我,笑了,说:“呵,还有一个,下来吧。不打也行,得罚你们给我浇菜畦。”说着他就拉起张得月的胳膊。
张得月像一只兔子似的在他手里挣拽着。
我想我过去还是不过去。说实在的,我真没有勇气跑过去。我怕姥姥和妈妈知道了,她们会骂我的,我刚成为救牛英雄,接着又变成了小偷,真丢死人了。
我听到张得月在喊我。他说:“嗨,过来吧,我们去给他踩水车。”
我只好从紫穗槐下面钻出来。阳光刺得眼疼,我用手搭起凉棚来,看到了立在河边的水车。
我极不情愿地走过去。在穿过菜畦的土埂时,有一只青蛙嗖地从我腿边掠过,把一线森凉的尿撒在我的凉鞋里,我被吓得滑了个趔趄,引得那个黑家伙龇牙咧嘴地一阵笑。
他带着我们来到水车旁,说:“干吧快干吧,浇完这片菜畦,你们才能走。你们谁都跑不了,我跑得比老虎还快呢。再说,我知道你们是白雾村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那天上午,我们顶着烈日,不停地踩着水车,汗水湿透了裤头背心。起初,看到清澈的河水哗啦哗啦流进菜畦时,心里觉得还挺新鲜的。可是后来,我们的腿麻木得像根木棍,都没法打弯了。我几乎趴在上面睡着了。我听到张德月把牙齿磨得咯吱咯吱响,他的腮帮子已经肿起来,几个血红的手指印在阳光下变得红灿灿的。
可气的是,那个黑家伙倒是自得其乐,他脱掉裤子,身上只剩下一件灰裤头,然后在河里游起泳来。后来,他干脆躺在岸边的水里,只露出一颗黑黑的脑袋,不时地回头看我们一眼。
“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张得月说。
“他打人太狠。”我说。
“我得报仇。”张得月像是自言自语。
又过了一会儿,张得月悄悄地对我说:“咱们准备逃跑。”
我心里马上就紧张起来,但脚下还是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我们停下踩水车。张得月不慌不忙地掏出弹弓,又从口袋里摸出一粒“子弹”,不是泥蛋蛋,竟然是一个七色玻璃球,他把玻璃球放在皮兜里。
嗨!张得月喊,嗨!
那黑家伙似乎意识到什么,忙从水里爬起来。这时候,那个七色玻璃球像一颗子弹般弹了出去,不偏不正地落在那家伙的脸上。只听“哎呦”一声大叫,接着就是“扑通”一声响,清澈的水面泛起一圈圈的浑水。
我和张得月撒腿就跑。我们一口气跑到河堤上,这才敢回头看一眼。那黑家伙并没追上来,他站在河边,一只手捂着脸,一只手指着我们,像是在说着什么,接着,他弯下腰,似乎是在地上找着什么。
张得月乐了,说:“就是离得太远了,真想再给他一弹弓。”
我们狠狠地出了口恶气。天已是正午,正好该回家吃饭去了。
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天下午,那个黑小子带着一群人,直接找到了张得月家,牵走了他家的一只母羊。他被玻璃球打掉了两颗牙,脸肿得像发面馒头那么高。他叫喊着说:“还有一个小子,还有一个小子。”可是,张得月被他爹打了十几棍子,死活没有供出我来。最后,那伙人只好牵着母羊走了。
人家一走,张德月他爹便蹲在地上哭起来。不知道是心疼张得月,还是心疼他的羊。
张得月被他爹打得好几天没去上学。有一天放学后,我带着那盒子七色玻璃球,悄悄地来到他家。我看到躺在床上的张得月,心里愧疚得不行。我把盛着玻璃球的盒子递给他,他却把我的手推回来。他摇摇头,龇出两颗大板牙,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