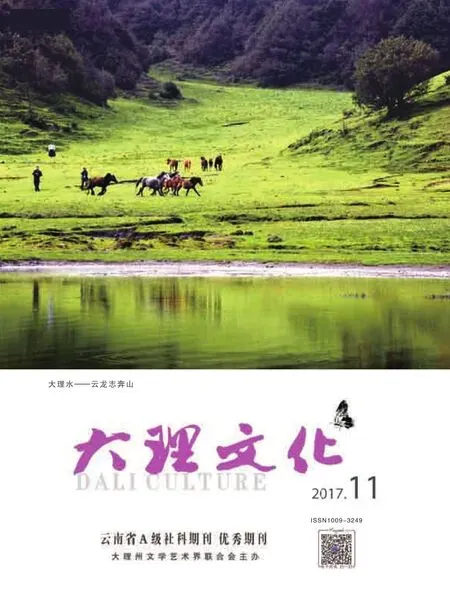迁徙记
●陈苑辉
迁徙记
●陈苑辉
一
当过往的路人驻足观望它时,预示着一间店铺的经营就要画上句号了。它是一块表面积不大却镌刻着生存的艰辛与无奈的红纸,也是一片泄露季节秘密的叶子、一群候鸟举家迁徙与漂泊的讯号。十二年来,穿街过巷的我总会不经意发现某些店铺的边角或银白色铝合金闸门上贴着它,上书:
旺铺转让
联系电话:XXX
端正的打印字体在油墨气味中交织着一股严肃与认真,也有的用毛笔或大头笔书写,一概分成两行向人们传递信息——此地急需易主,欲觅下一个接盘人,非诚勿扰。适逢经济不太景气之际,一条街走下来你会看见很多这样的告示。
“旺铺转让”的告示,有的刚贴出不久就被人撕了,像古时的揭榜,大概是担心这个信息被别人捕捉了然后捷足先登,抑或店家很快谈定了接主,自个儿撕了告示以免被再次烦扰。怪异的是,有的转让告示贴了三百六十多天,店铺仍在经营、运转,让人摸不透是真转还是假转。真转让的话,倒也无可厚非,若是假转,目的肯定是为了掩人耳目(多半是营业手续不齐全),试图摆脱工商部门的盘查、追责。这种世俗、老到、善于表演又懂得钻营、配合的高情商者,俗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曾经无不揶揄地对一个很熟悉的店主说过:你又不是真正要转让,干嘛天天贴着“旺铺转让”啊?他说:你啊,书读太多了,经商的事有所不知,现在什么工商局啊卫生局啊这部门那部门天天来人检查,手续不齐全就要罚款就要逼着你走,我做小本生意的,哪里耗得起?不如想一计谋,上面来人盘查,我就说经营不下去了,正在转让,不信你看门口贴的告示。没想到,居然还蒙混过关了,拖个一年半载,生意好就继续做,办齐那些乱七八糟的手续,假如生意不好我就真转让,中间赚个转让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呗。
合法经营是正确的,办齐了手续既是保护店主自己,也是捍卫消费者的权益。可是望着那位店主有些得意、狡黠的眼神,我却读懂了他藏在眼窝深处的无奈和感慨。同是寄居城市的异乡人,彼此的眼神欺骗不了,也隐瞒不了。由此我萌生了另一番感慨,不管真是黄金地段抑或偏僻的角落,告示一律写着 “旺铺转让”,甚至门可罗雀、寸草不生的巷口也要用上这四个字,我突然觉得很滑稽,这不等于自欺欺人吗?当然了,没有谁那么笨会坦白交代这里“不是旺铺”,除非他(或她)脑子进水了。
我上班的地方属于闹市区,一出大门便街铺林立。外出办事、接待亲友等等,我都会经过它们。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下意识地抬头望一眼店铺,似乎在捕捉那张熟悉的朱红色的纸,那张映射出我们外来人员生存状况的告示。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商铺,有商铺的地方就理应聚人群。沿着弧形的街道一路过去,两边都是商铺,一间挨一间绵延过去。令我颇为好奇、重点关注的店铺,位置很特别,它夹在街道的中段,其频繁的转让常常吸引着我的眼球。2005年,它是一间蛋糕店,面积大约三四十平米,稍方正。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明亮的橱柜里整齐地摆放着各式糕点,有蒸烤的夹丝面包,有棱角分明白里带黄的三明治,也有垒着三四层的蛋糕样板,每次从那里经过,我的两腮总会酸酸的,然后唾沫溢上牙床、舌尖,喉结情不自禁地抽动一下,接着咕噜一声吞了下口水。
有一次生日,我从蛋糕店里预定了蛋糕才知道老板的三个孩子都在我们学校上学。他最小的女儿,头发蓬松,眨着两只大眼睛,样子甚是可爱、乖巧。两个儿子比较大,一个念五年级,一个念初一。在等蛋糕的时刻,我跟老板东拉西扯聊起了天。他们的老家在宁波,来到东莞做小本生意几年了,三个孩子跟着流浪般换了好几间学校。每换一个地方开店就要找一所学校,三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开支也比较大,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四十有几的老板理了个寸头,齐整的短发根显得特别精神,可是他掩盖不了浓黑眉毛下的困顿,那是因疲惫而有些拢拉的眼睑,看上去是让人担心的操心过度。他的嘴巴厚而宽,常常裂开嘴无声地笑,别人误以为他是一个很乐观、阳光的男人。每个学期交学费的时候,他都会跟学校的领导商量可不可以减免一点学杂费,但每次都被善意地拒绝了。没办法,学校也是市场的产物,也需依靠学生的学费维持开支并生存下去的。
蛋糕店的生意说不上好,不知道罪魁祸首是不是手艺。店铺临近学校,几千名学生密集地来往着,本应呈现生意兴隆的景象。可是,没有多少孩子进去购买糕点。果然,我的担心还是出现了,才一年半,蛋糕店就搬走了,老板的三个孩子也在暑假转走了。杳无音讯地离去,没有话别。也许他找到了新地,孩子们也跟着找到附近的学校入学了吧。换了好几个学校,其实孩子们的成绩都不好,挣扎在及格线上。他们的漂泊我感同身受。在民办学校教书的我,也是漂泊不定的,前几年从惠州、深圳再辗转到东莞,仿似一尾随波漂流的鱼,没有一弯温馨的港湾。这是令人辛酸的历程,也是我不得不接受的宿命——因为我选择了民办学校,就意味着更为艰辛的付出和面临更多的不公平、不公正甚至屈辱。后来,每次经过蛋糕店的原址,我便会想起店主疲惫的眼神,不禁悲凉顿生——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过客,我们的漂泊都是下落不明的,可悲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也挣脱不了命运的束缚,像一只只迁徙的小候鸟世代延续、轮回下去,一眼望不到尽头。想想亦是悲哀。可是,悲哀又有何用?怨叹改变不了我们凄凉的境况,唯有不断前行、不息奋斗。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因为不甘心,我们含着泪踏着历史轮回般的足迹,不囿于命运的藩篱,在一次次揪心的迁徙中留下倔强挣扎的身影。
二
旺铺转让的本色调是阴冷的,泛出一股寒光。透过“旺铺转让”纸张的红艳,我分明看到了它无法掩饰的洗刷不去的投降的白,如店主贴上告示后苍白的脸。
一间店铺经营的结束往往是另一间店铺的开始。时常散发甜腻气息的蛋糕店转走后不久,自下而上传来一阵敲敲打打——我正好在二楼的教室上课——没几天,一块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就挂门楣上了,上书遒劲之字:川菜馆。一看到这三个字,我的两腮条件反射似地涌出一股酸辣劲。川人喜麻辣,个性也相对较为豪放、爽快,对我这种从小在客家山区长大的人来说,它还不具备多大的诱惑。诡异的是,后来我却经常光顾它。
来找我玩的朋友以及学校的同事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外省的,比起客家菜的清淡、江浙菜的甜腻,香辣对他们来说更为嗜好。久而久之,我也基本上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多元的饮食习惯成为候鸟们的特性。身材魁梧的川菜馆老板,古铜的肤色呈现出阳刚之气,他鬓角的毛发往下巴延伸,静静垂落的样子像两条黑布粘贴着。他从厨房出来,时常往肩上搭一条浅红色的毛巾,偶尔抹一下渗汗的脸庞、双手,模样很憨实,待人亦诚恳。端坐在收银台后的老板娘却是一位肤色白嫩、带着金黄镶边眼镜的女人,文静,高雅。顾客来买单,她抬头推推镜框露出圆润微笑的的脸和一排白净的牙齿。举手投足之间,她都透出一股大家闺秀的涵养,而蜀地更是滋养了她令人眼前一亮的肤色。暗地下我猜度,她的脾气应该是极好的,娶老婆就该以她为参考。他们请了一个小女孩协助清理桌子、收拾碗筷的工作。小女孩看上去大约十八九岁,据说是一位远房亲戚,顺带照顾一下。她就像被导演初次入选一部影片的角色,台词极少,默默做事,喜怒不挂在脸上,所以我对她了解甚少。
朋友和我端坐在川菜馆说些工作、生活琐事。一般是先上酒,冰凉的百威啤酒,在凳角上手掌一拍,哧,白沫从瓶口涌出来往外冒、泄。在酒精的麻痹与亢奋中我们呵护着友谊的温度与恒度。酒精充分激发了年轻的荷尔蒙,接近二两的杯子倒尽、放下、灌满,循环重复只为捍卫哥们间的义气。多少次,我们在川菜馆密谋着干一番事业,要有宏伟的框架、铺展的地盘、高档的装潢、气质高雅的员工,有些想法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最后所有美好的构想又化成了泡沫,就像橙黄色啤酒发酵而起的泡沫,渐渐萎缩成一小滩液迹,令人无奈、喟叹。但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 2008年的晚秋,谈了几年的感情突然灰飞烟灭,怎样也挽救不回来。暑假本来是去提亲的,谁知会直线急下,陷进了地平线,就像一条几何书本上的抛物线落入了横轴的泥沼里。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川菜馆喝得烂醉如泥,踉跄的脚步扛着受伤而敏感的心。酒精未彻底麻醉记忆之前我的头脑还清醒,晃动的眼神盯着一堆横七竖八的空酒瓶,眼眶抑制不住地滚出了几行泪,很快滑到我的两腮,咸咸的,热热的,我仿佛觉得它们是从我的内心里滚落出来,还保留着心房的伤痛与体温。依稀又记得那位肤色白皙的老板娘过来劝慰了很多话,可是现在一句也回忆不起来。同学和同事也靠在旁边劝慰,有的高声吆喝着,有的紧紧楼住我的肩膀,告诉我挺住,没有过不去的坎。藉着我苦闷的心情他们似乎也找到了久违的宣泄的窗口,感同身受般悲伤着我的悲伤,痛苦着我的痛苦。我那灌满酒精的沉重的肉体已悄然下滑至桌底,像一堆烂泥。我缓缓听见身后的椅子吱吱着挪动然后顶住了某扇墙,他们纷纷过来扛住我……之后我的记忆就消失了……
人,确实应该经受一些坎坷或挫折才会长大。有时这样的代价是让身体的某个部件亮起红灯,多年以后我终于尝到了它们对我的反抗和报复。
好几次在川菜馆喝得酩酊大醉,一段一段的记忆悄然缺失了。终于,途经川菜馆的我常常故意绕路走,因为我羞于碰见善良而美丽的老板娘了。这样的羞耻心衍生于教师这个神圣而光辉的职业。我想:那些生意人对教师还是保有最起码的尊重的,认为师者乃传道、授业、解惑,乃知识分子,拥有更为高尚的心灵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该如此放纵自己或者虐待自己,况且,每日喝得醉醺醺的,怎么给学生上课啊?洋相真是出得不大不小。我记得之前有一次,老板娘曾经问我的工资待遇,当我道出可怜巴巴的几千块时,她半信半疑地连说几个“没想到”,这令我颇为自卑,有点抬不起头来的尴尬。
鉴于此,情绪激动之时、烦闷之时我就转移战线,约上几个好兄弟,找一些偏僻的、不易碰见熟人的地方去喝酒……如今,我已羞于提起那段堕落的时光了,中年人应该学会沉稳了,喜怒不轻易表现出来,这也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吧。
大概过了一年,川菜馆居然也贴出了“旺铺转让”的告示。它似乎变成了一面镜子,照出我的不安与愧疚,仿佛它的转让与我脱不了干系。直到有一天它被人接手,改成了一家照相馆,面目全非。八九年过去了,现在路过那间店铺,我的嗅觉似乎还能捕捉到当年川菜馆熟悉的香气,内心泛起一股酸楚,便怔怔地望上一阵子。
三
黑沉沉的乌云是变天后骤雨的征兆,卯足了劲的飓风从大道直往街巷里灌,能够抵挡此番架势的只有方正的广告牌和撑开的太阳伞,散落于街道的瓶瓶罐罐早已哐哐当当地滚动,滚到了路边。风云的骤变隐喻着市场经济的规律,“互联网+”的时代冲击着街边的商铺,很多实体店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与冲击。
那条街道,能经受十二年岁月轮转而依然存在的大概只有农科站和口腔医院了,其余的店铺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个月走马灯似地替换。开店时的热闹喜庆到转让时的冷清无奈,正是抛物线的运转轨迹。当盛产油烟香气的川菜馆改装成几乎隐匿油烟气息的照相馆,行业间的取代隐喻着博弈中的突围与超越。
平静的照相馆生意不算好,白净的玻璃柜挂上了“代办社保”的招牌。近水楼台先得月,几年来,学校六、九年级的学生毕业照都是委托他们来照、冲洗、过塑,老板做事的态度也认真、细致。我的一寸个人头像也在那里照,性格和蔼的老板每次都热心地问我是否需要底片,QQ传一下即可。因为那几年学校被暴雨淹过几次,我的工作电脑硬盘进了水,恢复后个人头像的底片皆损坏了,不得已补照了几次。家乡音很重的老板娘有个外甥,之前在老家读书,成绩不太好,还经常跟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去泡网吧,后来他父母就托付她照管一下,又送进了一街之隔的我所在的学校念书,当然,我没有教他,很多不良信息都是道听途说的。那个男孩子积习难改,常常被老板娘呵斥。老板娘顾面子,一见到我就扯出一张善意而无奈的笑脸诉苦说,现在的孩子真难管,要不是他爸妈叮嘱,我才懒得理他。但是,这个孩子终究还是闯出了祸。
某天晚上八点多,忽闻校外人声嘈杂,还在加班的我快速从办公室跑出校门,见对面小店陈旧的招牌下,聚集了一些人。我小跑过去,见地上斑斑的血迹刚凝固成一滩,甚至能感觉到它们未曾散尽的余温。鲜红的血液离开了血管的保护和管束,失去了流淌、衍生的本能,泄出毫无规则的模样。鲜血凝固在光亮的瓷块上,无辜地迎来了一双双惊悚、诧异的眼神。来了一群警察和治安员,漫不经心地做着调查和笔录。治安员说,这些小孩子,我们很熟悉的,早就警告过他们不要目中无人,不要太放肆,不要去惹是生非,可就是不听,现在玩大了,伤人了。颇为惋惜的我就站在店外不时向里张望,心底却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据说参与砍人的孩子也才初三毕业不久,从小就在综合市场晃荡着长大,而今终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听人说,两个孩子伤势较重,手臂基本被砍断,老板娘的外甥是其中之一,附近的医院甚至不敢接,只好辗转到市人民医院、骨科医院救治。
几个月后,受伤的手臂是接好了,但已经干不了重活。一辈子那么长,他们早早吞了下苦果。一脸愧疚的老板娘交还了外甥,被他父母带回了乡下养身体。砍人的青年是对方请来的帮凶,肇事后亡命天涯去了,被公安局列为网上追捕的对象。若干年过去了,不知凶手抓到没有。但是,我的心里却被砍出了一个疤痕,再也无法愈合了。
生意不好做。照相馆的老板一边收拾器材,一边无奈地摇了摇头说。
我问,还找地开照相馆么?
哎,找了一个镇区的新开发的工厂区,也不知生意好不好做……走一步看一步呗。
那你的孩子也要跟着转学了吧?我幼稚地问。这个问题等于是废话,但是已然说出,收不回去了。
哎,那也没办法呀,孩子还不想转学,说你们学校的老师教得好……
照相馆搬走后,七零八落的店铺又经过了一番大装修,改成了沙县小吃。后来,这间店铺分别变成了便利店、包子铺、裁缝店、化妆品店……
四
从踏上讲台以来,我认为“旺铺转让”跟我是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因为教书和做生意存在着角色的差别,我骨子里仍残留着古时轻商重文的迂腐。况且,相比于其他行业,教书的岗位还是相对稳定一些。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其实也是一只被动迁徙的候鸟。一年前,我任教的学校接到上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通知,合同到期必须搬走。尽管学校开办了十二年且小有名气,但是上面的态度很坚决,没有回旋的余地。
没办法,几千名学生得有个交代,学校董事会找遍了整个区域,才找到一处旧厂房,正紧锣密鼓地改造为新校区。毫无疑问,处于市区中心的旧校区就成了旺铺,像一间平常的小店一样面临转让的命运。从租赁性质上来说,学校只是一间更大的商铺,有合同开始之时必有终结之日,这无可厚非。办得好好的教学用地被迫搬走,最受牵连的还是就读于该校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了,尤其是附近的走读生,他们将面临是否转学的问题,若是跟着转到新校区,路途有些远,必须交中餐费和校车燃油费,比原来的收费增加了两千多元,这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一个考验。
一所占地面积达到两万多平方米的学校,如果需要写出“旺铺转让”四个字,也不过600平方厘米的红纸那么大。但我转念一想,它是不需要贴“旺铺转让”的,因为财大气粗或者手握大权之人,恐怕早已对它垂涎欲滴了吧?
相隔很近的综合市场里,那些小商小贩们也闻风而动,逮住我就问:老师,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搬走啊?我答,大概明年开春吧,新校区正在装修。卖菜的阿姨们突然愁眉不展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哦,你们学校搬走了,我们也没什么生意了,我们的租铺也要考虑转让了,哎——
寄居在这座城市,我们是其日益繁华的建设者和见证者。漂泊不定的我们是一只只候鸟,也怀揣着迷鸟般的无奈,在未知的迁徙路线上被命运之手摔打、驱逐。然而,我们的梦想并未破灭,我们得继续埋头工作、求生、赶路以及做梦。每一张“旺铺转让”告示的背面,沾染着候鸟迁徙者的无奈与彷徨。
刹那间,当我环顾一望,眼前突然飘出了无数张“旺铺转让”的红纸,落在这座我深深爱着的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