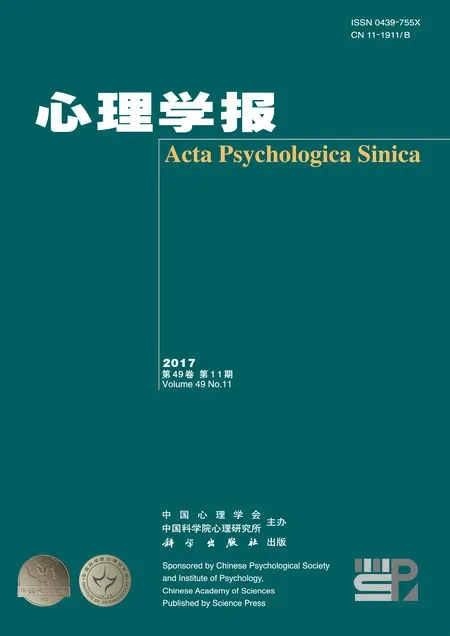破解“通勤悖论”:通勤时间如何影响幸福感*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1 前言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 中国主要城市正在进入一个整体性交通拥堵的时期。过长的通勤时间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关注焦点。然而, 政府的规划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例如北京回龙观、苏州工业园。这背后的原因, 除了政府部门的主观“设计”之外(郑思齐, 徐杨菲, 谷一桢, 2014), 我们对于个体如何配置通勤时间还知之甚少, 这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近年来, 通勤时间如何影响幸福感?这一议题引起了多学科的关注(如 Stutzer & Frey, 2008;Turcotte, 2011; Olsson, Gärling, Ettema, Friman, &Fujii, 2013; Martin, Goryakin, & Suhrcke, 2014;Kroesen, 2014; Nie & Sousa-Poza, 2016)。通勤是最不快乐的活动之一(Kahneman, Krueger, Schkade,Schwarz, & Stone, 2004), 传统经济学假设通勤时间的配置是理性经济人权衡通勤成本与收益的结果, 认为通勤时间增加必然可以由低廉的房价和高收入的工作得到补偿。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Stutzer和Frey (2008)对德国员工的研究发现, 通勤时间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健康满意度。学者们将“通勤时间延长未必换来相应补偿”的效用失衡现象称为“通勤悖论” (commuting paradox)。
通勤是由于居住地与就业地的空间分离而产生的。一些研究支持了通勤悖论, 例如英国女性员工的通勤时间负向影响其心理幸福感(Roberts, Hodgson,& Dolan, 2011)、美国员工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将导致通勤满意度下降(Smith, 2013)。然而, 一些研究却没有发现通勤悖论, 例如 Humphreys, Goodman和 Ogilvie (2013)对英国员工的研究没有发现通勤时间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联; Dickerson, Hole和Munford (2014)也发现通勤时间与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的相关不显著。Olsson等人(2013)通过瑞典员工的调查发现, 通勤过程的感受以中性和积极的情绪为主, 而不是消极情绪。Turcotte (2011)对加拿大雇员的研究发现, 通勤时间超过 45分钟可以提升雇员的通勤满意度。上述研究表明, 通勤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可能是复杂的。基于此, 深入探索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边界条件和内在机制, 不仅对通勤悖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而且对政府和企业管理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制度设计, 避免个体陷入通勤悖论, 同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本文借鉴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思想, 将通勤视为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的过渡带。工作与家庭边界包括物理边界、时间边界、社会边界和心理边界(Clark, 2000; Ashforth, Kreiner, & Fugate, 2000)。通勤作为工家边界的过渡带, 也应该包括了物理过渡带、时间过渡带、社会过渡带和心理过渡带。以往的研究只探讨了通勤的物理和时间属性, 尚未涉及其社会和心理属性。本文认为, 对于不同社会过渡带、不同心理过渡带的员工, 配置等量的通勤时间可能形成不同的幸福感。社会过渡带是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来界定通勤:连接了工作的社会关系(如上下级、客户)和家庭的社会关系(如夫妻、子女)。心理过渡带是个体根据物理过渡带、时间过渡带和社会过渡带的相关要素, 采用心理策略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 建立起自己的心理过渡带, 以此来管理自身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因此, 从社会过渡带和心理过渡带出发剖析通勤时间的影响边界及其内在机制, 可能是进一步明晰“通勤悖论”的重要突破口, 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以往的通勤研究大多关注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 不仅局限于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的探讨, 还很少在实证方面涉及通勤效用, 这使得“通勤悖论”未能得到较深入的考察。本文首先采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两个指标, 分别从认知、情感维度评估通勤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紧接着,本文考察了通勤效用在通勤时间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并分析婚姻状态(社会过渡带的决定因素之一)和恢复体验(心理过渡带的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是否通过通勤效用的中介而实现。图1为本文的研究框架。
目前的研究背景多以西方国家为主, 关于中国员工的研究很少。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在对通勤时间的权衡上, 中国员工与西方员工可能不同(Spector et al., 2004)。在中国员工中, 白领是伴随中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程度加深产生的中产阶级, 这一群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因此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为排除劳动力市场供需水平、城市规划、房价、医疗保障状况等因素的干扰, 我们对同一城市员工开展调查与分析。本文选择超大城市广州的白领员工, 以提高取样的代表性。同时, 本文为提高内部效度, 将从多个时点调查采集数据。通过以上工作, 本文试图解析中国背景下的“通勤悖论”, 刻画出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边界条件和作用机制, 为城市管理和企业管理提供有益信息。

图1 本文的研究框架
2 理论与假设
2.1 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
通勤效用源于边沁(Bentham)的“效用”论, 涵盖着通勤相关的快乐和痛苦的体验。本文借鉴Milakis和Cervero等人的研究, 将通勤效用划分为心理效用和衍生效用(Milakis, Cervero, van Wee, &Maat, 2015; Milakis, Cervero, & van Wee, 2015)。如图2所示,U
代表通勤效用, 是心理效用和衍生效用的总和, 其中U
表示心理效用, 指员工在心理过渡带获得的效用(如有趣、疲劳);U
表示衍生效用,指员工在社会过渡带获得的衍生效用(如满意、焦虑)。通勤效用随着通勤时间呈现出包含“三个阶段”的通勤效用曲线。
图2 通勤效用解析
在第一阶段, 即“效用递增”阶段, 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正相关。该阶段U
和U
的边际效用都为正,U
处于迅速增长状态。U
在“理想通勤时间”最大, 此后因厌倦和疲劳, 随着时间而递减。由于U
仍为大于零, 通勤效用U
在“可接受通勤时间”达到最大化。第二阶段是“通勤时间陷阱”阶段, 通勤效用不随通勤时间显著变化。此时通勤效用U
随通勤时间的变化不显著, 即人们对通勤时间的变化并不敏感。该阶段的特征是:快速递减的U
可以由缓慢递增的U
(如居住环境或工作报酬改善)得到补偿。第三阶段是“效用递减”阶段, 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负相关。随着通勤时间的延长,U
加速下降,U
减速增加(因边际效用递减)。此时减少的U
不能够从增加的U
得到补偿, 使得通勤效用U
随时间递减。2.2 婚姻状态的调节作用
本文认为, 婚姻状态改变了工作−家庭的社会边界及管理策略, 影响社会过渡带的构建。已婚者需要管理边界以维持工作家庭平衡, 比未婚者多了丈夫或妻子等边界维持者(border-keeper), 也多了更多的家庭角色要求。然而, 未婚者大多没有区分边界(马璐, 刘洪, 2015)。作为边界跨越者(bordercrosser), 已婚员工需要在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进行角色转换, 不断调整他们的沟通风格, 以适应不同生活领域的要求。
当通勤的社会过渡带较短时, 已婚者可能形成角色冲突和工作压力。随着通勤时间延长, 社会过渡带有助于已婚员工减少角色冲突, 缓解了U
的下降, 从而形成更“平缓”的效用曲线和较长的“通勤时间陷阱”。另外, 已婚员工还可以从通勤的社会过渡带中获得更多U
, 如满足家庭需要的学校、医院等, 这降低了他们通勤效用U
的递减速度。因此,随着通勤时间增加, 已婚员工的通勤效用是鲜明的曲线。对于未婚员工而言, 他们不需要频繁地切换工作和家庭角色, 通勤过程形成社会过渡带较不明显, 且与家庭有关的U
较少, 未婚员工的通勤效用曲线较不显著。本文提出假设:H1a:对于已婚者,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有曲线影响。通勤时间较短和较长时, 员工的通勤效用较高, 在中等通勤时间, 员工的通勤效用较低。
H1b:对于未婚者,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有负向作用。
2.3 恢复体验的交互作用
本文认为, 对于未婚员工和已婚员工(社会过渡带不同), 恢复体验改变了他们的心理过渡带,导致他们通勤效用有所不同。恢复体验是个体在工作应激中恢复的心理过程, 包括心理解脱、放松体验、掌握体验等策略(如Sonnentag & Fritz, 2007)。心理解脱指在个体在心理上与工作相抽离的状态,不仅停止工作活动, 而且在心理上不去思考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放松体验是个体通过一系列放松活动,以降低应激水平、减轻负面情绪, 并达到较高积极情绪水平(Geurts & Sonnentag, 2006); 掌握体验是个体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挑战经验或技能, 如在线学习、碎片化学习等。研究表明, 恢复体验有助于减少失眠、抑郁等身心疾病, 减弱了工作家庭冲突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Moreno-Jiménez et al., 2009)。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曲线影响, 可能随着恢复体验而减弱。虽然过长的通勤时间会急剧地降低心理效用U
, 但当员工的恢复体验强时,形成的心理过渡带能够减少疲劳并增加积极情绪(Geurts & Sonnentag, 2006), 减缓了U
的下降速度。同时, 已婚员工的工作边界和生活边界相互渗透(高中华, 赵晨, 2014), 心理过渡带对工作和生活边界的分隔, 也增加了其心理效用。对于未婚员工而言,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负向影响, 随着恢复体验而减弱。由于心理解脱可以阻断资源流失, 放松体验促进资源恢复, 而掌握体验可补充新资源,恢复体验强的未婚员工能减少通勤过程的消极情绪体验, 增加其积极情绪, 从而缓解了通勤效用的下降。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H2a:对于已婚者,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具有交互效应。随着心理解脱、放松体验、掌握体验的加强,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曲线影响减小。
H2b:对于未婚者,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具有交互效应。随着心理解脱、放松体验、掌握体验的加强,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负向作用减小。
2.4 通勤效用与生活满意度、快乐度
从当前文献看, 通勤时间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被广泛探讨, 然而研究分歧多于共识。通勤时间有时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如Stutzer & Frey, 2008), 有时是正相关(如 Turcotte, 2011), 甚至不相关(Dickerson et al., 2014)。本文认为, 通勤效用是解释通勤时间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通勤效用源于“效用论”思想, 是从通勤过渡带获得的效用(心理效用和衍生效用), 在哲学观、理论脉络、测量方法和发生顺序方面均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
幸福感的形成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自上而下的理论强调个人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解释其生活环境及事件, 自下而上的理论强调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Tay & Diener,2011)。根据需要层次理论, 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的满足对幸福感形成有重要作用, 而满足通勤“行”之需要(效用)才会进一步产生幸福体验。相对于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距离, 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的关系更为密切。另外, 从变量的属性看, 通勤时间是本质和客观属性, 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是比较长久的心理状态, 通勤效用是短暂的心理状态。对主观幸福感而言, 通勤效用比起通勤时间是一个更加近端(proximal)的因素。基于此, 本文假设:
H3a:对于已婚者, 通勤效用中介了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U型影响。
H3b:对于未婚者, 通勤效用中介了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作用。
H4a:对于已婚者, 通勤效用中介了通勤时间对快乐度的U型影响。
H4b:对于未婚者, 通勤效用中介了通勤时间对快乐度的负向作用。
如图2所示, 在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婚姻状态和恢复体验是重要的边界条件。一方面,相对于未婚者, 已婚者可利用通勤过程管理工作与家庭的边界, 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从而形成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另一方面, 通勤过程的恢复体验不仅使员工在工作付出努力之后恢复到基准水平, 还可以获取新资源以修复流失的身心资源, 进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van Hooff, 2015)。也就是说, 婚姻状态和恢复体验改变了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在分析通勤效用是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后, 本文进一步推断: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心理解脱、放松体验和掌握体验)的交互效应, 也经过通勤效用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由此, 本文假设:
H5a:对于已婚者,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心理解脱、放松体验和掌握体验)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交互效应, 以通勤效用为中介。
H5b:对于未婚者,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心理解脱、放松体验和掌握体验)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交互效应, 以通勤效用为中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研究对象是来自广州地区在职硕士班的学员,主要是电子商贸、通信服务、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银行的行政和财务人员, 他们工作要求类似, 通勤地点和时间较固定。为避免同源偏差的影响, 数据采集分三次进行, 间隔 1个月, 第一次测量通勤时间、恢复体验和婚姻状态; 第二次测量通勤效用;第三次测量生活满意度及快乐度。为了匹配3次测量的数据, 我们请每位被试在问卷后填写学号的后5位, 以方便数据的跟踪。最后获得匹配数据 822份, 有效回收率为84.22%。其中男性324人、女性498人; 管理人员264人, 普通员工558人; 大专学历335人, 本科487人; 未婚462人, 已婚360人;工作年限均衡分布, 3年以下297人, 3~5年208人,5年以上317人。
3.2 测量工具
(1)通勤时间。请被试回答如下问题:“您每天上、下班通勤平均需多少分钟?即从家中到工作地点的往返过程。”我们将通勤时间换算为小时单位。
(2)婚姻状态。通过以下问题确定被试的婚姻状态:“您的婚姻状态如何?(1)未婚; (2)已婚。”未婚设为0, 已婚设为1。
(3)恢复体验。采用 Sonnentag和 Fritz (2007)开发的恢复体验量表, 选择心理解脱、放松体验、掌握体验三个分量表, 共12题。预试中删除了跨因子载荷高于0.35的2个项目(下班路上我的身心得以恢复和放松; 我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后休息一下)。正式调查采用10个项目, 从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评分。放松体验、心理解脱和掌握体验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0、0.88、0.83。
(4)通勤效用。根据 Kahneman等人(2004)提出的“日重现法”, 请被试构建关于前一天的简短通勤日记, 回答关于通勤过程的起止时间, 在哪里, 正在跟谁一起, 对给定的积极情绪(快乐、满意等)和消极情绪(疲劳、闷闷不乐/焦虑等)进行评分, 从 1“几乎没有”到6“非常多”。正式调查中积极情绪量表和消极情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和0.86,以通勤的积极情绪减去消极体验计算通勤效用。
(5)快乐度。采用PANA量表(Watson, Clark, &Tellegan, 1988), 请被试评估在过去的 2周内的积极情绪(如兴奋、感激)和消极情绪(如难过、易怒),从1“几乎没有”到6“非常多”。本文中积极情绪量表和消极情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1和0.85, 以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差值计算快乐度。
(6)生活满意度。采用Pavot和Diener (1993)开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5个条目(如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 从 1“非常不同意”到 6“非常同意”评分。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7)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研究(如:高中华, 赵晨,2014), 控制了性别、学历、工作年限、相对收入和职位级别等人口学变量。相对收入量表共三个项目,即“①和你认识的朋友相比, ②在你居住的地方,和别人相比, ③和你同职业的人相比, 你的收入较高吗?”从1“非常不同意”到 6“非常同意”评分。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7。
3.3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首先, 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检验和相关分析; 然后, 参照Girme, Overall, Simpson和Fletcher (2015)建立层级多项式回归方程并绘制交互效应图; 最后, 采用Baron和Kenny (1986)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检验研究假设。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未婚员工和已婚员工的通勤时间和通勤效用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31和−0.29, 而通勤时间与快乐度的相关比较微弱, 说明有必要采用非线性分析。另外,性别、教育、工作年限、职位级别和相对收入等控制变量与通勤效用、快乐度和生活满意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 说明有必要在分析中加以控制。
4.2 研究假设的检验
借鉴 Girme等人(2015)的分析程序, 首先对通勤时间、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然后构建通勤时间的平方项“通勤时间”, 接着分别对未婚和已婚两个样本进行层次多项式回归分析。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第二步加入通勤时间; 第三步检验通勤时间和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 第四步加入通勤时间; 第五步分析通勤时间与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最后检验通勤效用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2。如模型 1、2a、3a所示,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负向影响通勤效用(β
= −0.28,p
< 0.01)和生活满意度(β
= −0.13,p
< 0.01), 但是对快乐度的作用不显著(β
= −0.8,p
> 0.05)。通勤时间正向影响通勤效用(β
= 0.22,p
< 0.01)、生活满意度(β
= 0.16,p
<0.05)及快乐度(β
= 0.11,p
< 0.05)。已婚员工的分析结果验证了 H1a。其次, 通勤时间与放松体验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通勤效用(β
= 0.19,p
< 0.05)和快乐度(β
= 0.13,p
< 0.05), 通勤时间与心理解脱的交互项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β
= −0.14,p
< 0.05)。交互效应的结果支持了H2a。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分析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负向影响通勤效用(β
=−0.29,p
< 0.01)及生活满意度(β
= −0.12,p
< 0.05),对快乐度的影响不显著(β
= 0.06,p
> 0.05)。未婚员工的分析结果支持H1b。心理解脱与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交互效应显著, 但是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验证了 H2b。此外, 通勤时间与放松体验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快乐度(β
= 0.14,p
< 0.05), 这是一个假设以外的发现。图3~图5为在多项式回归基础上的交互图型。图3(a)~图3(c)显示:随着未婚员工通勤时间增加,其通勤效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已婚员工通勤效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随着通勤时间先下降后上升。在通勤时间陷阱, 即1.75小时至2.75小时之间效用均衡, 人们对通勤时间的变化不敏感。

图3 通勤时间与婚姻状态的交互
图4(a)显示:未婚员工心理解脱较弱时, 通勤时间对其通勤效用有较强的负向影响, 随着心理解脱提高, 这种负向影响逐渐变小。图 4(b)显示:未婚员工放松体验较弱时, 通勤时间对快乐度有很强的负向影响, 随着放松体验增强, 快乐度随通勤时间先升后降。另外, 图5(a)~图5(c)显示:已婚员工放松体验强时, 通勤时间对其通勤效用和快乐度都有较强的曲线影响, 随着放松体验减弱, 曲线逐渐变为倒U
型。图5(c)显示:已婚员工心理解脱较弱时, 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U
型影响较大, 随着心理解脱增强, 通勤时间的曲线效应变小。
图4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交互

图5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交互
通勤效用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在模型2a、3a的基础上, 加入通勤效用后(见模型2b、3b),未婚员工通勤时间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 对快乐度的作用由不显著变为显著(0.06→0.19)。这表明未婚员工通勤时间对快乐度的影响存在通勤效用的遮掩效应(温忠麟, 叶宝娟,2014), 部分支持H3b和H4b。对于已婚员工而言,模型加入通勤效用后, 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对通勤时间的回归系数减少且不再显著, 这说明通勤效用中介了已婚员工通勤时间的曲线作用, 验证了H3a和 H4a。
同时表 2还表明, 模型加入通勤效用后,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放松体验对快乐度的交互效应增强, 其交互项的系数增加(0.14→0.18), 表明通勤效用具有遮掩效应, 部分支持H5b。已婚员工的模型加入通勤效用后, 通勤时间与心理解脱对生活满意度的交互作用不再显著(−0.14→−0.07)、通勤时间与放松体验对快乐度的交互效应均不再显著(0.15→0.04), 这说明已婚员工的通勤效用不仅传递了放松体验与通勤时间对快乐度的交互作用,还中介了心理解脱与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交互效应, 验证了H5a。
5 讨论
5.1 理论贡献
传统经济学假设通勤时间增加必然可获得职业、住房方面的经济补偿, 人们的效用是均衡的。然而现实情况是“通勤时间延长未必换来相应补偿”, 这种效用失衡的现象与经济学的传统假设相违背, 被称为“通勤悖论”。为了解析该悖论, 本文根据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思想, 从社会过渡带(涉及衍生效用)和心理过渡带(涉及心理效用)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为通勤悖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发现,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一致(如Stutzer & Frey,2008; Smith, 2013; Nie & Sousa-Poza, 2016)。研究还表明,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负相关, 但是与快乐度之间的关联不显著。对于已婚员工而言,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函数关系都是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需要注意的是, 在1.75~2.75小时的“通勤时间陷阱”, 员工的效用达到均衡, 对通勤时间的延长并不敏感。这不仅呼应了通勤时间与幸福感无关的研究结论(如Humphreys et al., 2013; Dickerson et al., 2014), 而且与通勤时间增加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一致(如 Olsson et al.,2013; Turcotte,2011)。这些研究结果说明:第一, 婚姻状态不同(社会过渡带不同), 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方式存在差异, 验证了本文的社会过渡带观点。第二, 当前文献偏向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如 Stutzer & Frey, 2008; Robert et al., 2014), 很少考察幸福感的情绪维度。本文综合考察了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维度(快乐度),发现通勤时间对快乐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所不同, 这拓展了当前的文献。第三, 先前关于通勤时间与幸福感的研究结论不一, 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化解先前文献的分歧, 推进研究结果的整合。

表2 多项式回归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还发现,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心理解脱的交互效应显著,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与放松体验的交互效应显著。亦即对于未婚员工, 心理解脱的调节作用较为突出; 对于已婚员工, 有效的恢复策略是放松体验。这可能是因为:未婚员工采用基本的恢复体验, 即心理解脱, 可以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区分开, 构建心理过渡带; 已婚员工需要更深层的恢复体验, 即放松体验, 才能形成通勤的心理过渡带。然而, 掌握体验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可能因为:掌握体验需要耗费身心资源, 在适度劳动下能够补充新资源并构建心理过渡带。然而, 中国人均年工作时间介于2000~2200小时(吴伟炯, 2016), 在过劳频发的情况下, 员工使用掌握体验的效果显然不佳。本文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已婚员工心理解脱增强时, 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U型影响减弱了, 本文对此的解释是:通勤的社会过渡带与心理过渡带互为补充。当工作与家庭边界模糊, 通过心理解脱构建心理过渡带, 可以减缓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降低通勤时间的负向影响; 随着通勤时间的延长, 时间过渡带和物理过渡带都延长了, 心理过渡带的作用降低。以上结果支持了心理过渡带的观点。
本文剖析了通勤时间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研究证实,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以通勤效用为中介; 对于已婚员工, 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快乐度的作用经过通勤效用发挥出来。深入分析发现, 对于未婚员工而言, 通勤效用在通勤时间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但是在对快乐度的影响上, 通勤效用发挥了遮掩效应(温忠麟, 叶宝娟, 2014)。亦即如果没有引入通勤效用, 那么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快乐度之间的实际关系就被掩盖了。对于已婚员工而言, 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快乐度的非线性影响以通勤效用为完全中介。此外, 无论婚姻状态如何, 心理解脱和放松体验对通勤时间影响效果的调节效应仍是以通勤效用为中介。以往的研究很少直接考察通勤效用, 未能剖析“通勤悖论”的深层原因。本文表明, 对于未婚员工和已婚员工(社会过渡带不同)来说, 通勤效用发挥的作用不同的(心理过渡带不同),使得人们配置等量的通勤时间形成不同的幸福感。这说明, 聚焦通勤效用才能够真正地揭示通勤时间与幸福感的关系。总之, 本文以社会过渡和心理过渡的新视角, 打开了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过程“黑箱”, 深化了“通勤悖论”的研究, 对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有积极启示。
5.2 管理启示
根据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管理建议:(1)规避通勤时间陷阱。本文表明, 通勤时间陷阱介于1.75~2.75小时。城市管理者的规划应该致力于帮助市民跨越通勤时间陷阱, 同时支持企业灵活办公方式、采取弹性工作制和提供班车服务, 增加市民的通勤效用, 规避通勤时间陷阱, 有利于在整体层面提升城市幸福水平。(2)构筑通勤的社会过渡带。通过培育传统观念、降低成家成本、拓展婚姻渠道等方式, 减少单身者的比例, 构筑通勤的社会过渡带, 也是克服“通勤悖论”和应对“职住分离”需要兼顾的重要举措。(3)强化通勤的心理过渡带。对于未婚员工和已婚员工(社会过渡带不同)来说, 通勤效用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心理过渡带不同)。在当前中国主要城市的通勤时间普遍较长的情况下, 组织和员工根据社会过渡带的不同, 强化通勤的心理过渡带(未婚员工侧重心理解脱, 已婚员工侧重放松体验), 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幸福水平。
5.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首先, 选取的研究对象为来自同一城市的白领, 为提高外部效度, 未来可以针对不同城市和其他职业人群进行实证检验。第二, 由于研究精力所限, 本文只探讨了通勤时间与幸福感的关系, 但通勤时间对工作家庭(如冲突、促进、溢出等)的影响过程是否也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测?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 鉴于中国的“工作干涉家庭”更严重, 本文将研究重心置于下班的恢复体验, 但是关于上班(家庭→工作地点)的通勤过渡带还值得进一步挖掘。最后, 本文的调节变量只关注恢复体验和是否成婚,婚姻长短、子女数量、组织支持、通勤方式和城市特征(如交通服务、土地利用)是否对过渡带具有影响?这尚待更深入地探讨。
6 结论
本文从社会过渡带和心理过渡带两个方面解析“通勤悖论”。通过对广州市白领的追踪调查和多项式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婚姻状态(社会过渡带)具有调节作用,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有曲线影响; 恢复体验(心理过渡带)具有交互效应,心理解脱调节了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的关系, 放松体验调节了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快乐度的关系;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和快乐度的关系受放松体验调节, 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受心理解脱调节; 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以及婚姻状态和恢复体验的调节效应, 以通勤效用为中介; 员工在“通勤时间陷阱” (1.75~2.75小时)的效用均衡。
Ashforth, B. E., Kreiner, G. E., & Fugate, M. (2000). All in a day's work: Boundaries and micro role transi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 472–491.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 1173–1182.Clark, S. C. (2000). Work/family border theory: A new theory of work/family balance.Human Relations, 53
, 747–770.Dickerson, A., Hole, A. R., & Munford, L. A.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ll-being and commuting revisited:Does the choice of methodology matter?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9
, 321–329.Geurts, S. A. E., & Sonnentag, S. (2006). Recovery as an explanatory mechanism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ute stress reactions and chronic health impairment.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32
, 482–492.Girme, Y. U., Overall, N. C., Simpson, J. A., & Fletcher, G. J.O. (2015). “All or nothing”: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the curvilinear effects of partner suppor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
, 450–475.Humphreys, D. K., Goodman, A., & Ogilvie, D. (2013).Associations between active commuting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Preventive Medicine, 57
, 135–139.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A., Schwarz, N.,& Stone, A. A. (2004).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Science, 306
, 1776–1780.Kroesen, M. (2014). Assessing media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te ti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Journal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2452
, 114–123.Ma, L., & Liu, H. (2015). The work and nonwork boundary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heir effect.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2), 25–33.[马璐, 刘洪. (2015). 员工工作与非工作边界管理风格类型及其效果研究.南京社会科学,
(12), 25–33.]Martin, A., Goryakin, Y., & Suhrcke, M. (2014). Does active commuting improv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eighteen waves of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Preventive Medicine, 69
, 296–303.Milakis, D., Cervero, R., & van Wee, B. (2015). Stay local or go regional? Urban form effects on vehicle use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 theoretical concept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Journal of Transport and Land Use, 8
, 59–86.Milakis, D., Cervero, R., van Wee, B., & Maat, K. (2015). Do people consider an acceptable travel time? Evidence from Berkeley, CA.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44
, 76–86.Moreno-Jiménez, B., Mayo, M., Sanz-Vergel, A. I., Geurts, S.,Rodríguez-Muñoz, A., & Garrosa, E. (2009). Effect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on employees’ well-be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covery strategies.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4
, 427–440.Nie, P., & Sousa-Poza, A. (2016). Commute ti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 doi:10.1016/j.chieco.2016.03.002.Olsson, L. E., Gärling, T., Ettema, D., Friman, M., & Fujii, S.(2013).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with work commut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1
, 255–263.Pavot, W., & Diener, E. (1993). 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5
, 164–172.Roberts, J., Hodgson, R., & Dolan, P. (2011). “It's driving her ma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commuting on psychological health.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30
,1064–1076.Smith, O. B. (2013).Peak of the day or the daily grind:Commut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Sonnentag, S., & Fritz, C. (2007). The recovery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for assessing recuperation and unwinding from work.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2
, 204–221.Spector, P. E., Cooper, C. L., Poelmans, S., Allen, T. D.,O'Driscoll, M., Sanchez, J., … Lu, L. (2004).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k-family stressors, working hours, and well-being: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versus the Anglo world.Personnel Psychology, 57
, 119–142.Stutzer, A., & Frey, B. S. (2008). Stress that Doesn't Pay: The Commuting Paradox.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 339–366.Tay, L., & Diener, E. (2011).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
, 354–365.Turcotte, M. (2011). Commuting to work: Results of the 2010 general social survey.Canada Social Trends, 92
, 25–36.van Hooff, M. L. M. (2015). The daily commute from work to home: Examining employees' experiences in relation to their recovery status.Stress and Health, 31
, 124–137.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 1063–1070.Gao, Z. H., & Zhao, C. (2014). Why is it difficult to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An analysis based on work-family boundary theory.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6
, 552–568.[高中华, 赵晨. (2014). 工作家庭两不误为何这么难? 基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探讨.心理学报, 46
, 552–568.]Wen, Z. L., & Ye, B. J. (2014).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731–745.[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 22
, 731–745.]Wu, W. J. (2016). The impact of hours worked on occupational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typical occupations.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3), 130–145.[吴伟炯. (2016). 工作时间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三种典型职业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
(3), 130–145.]Zheng, S. Q., Xu, Y. F., & Gu, Y. Z. (2014). Rethinking“jobs-housing balance”: Providing more choices rather than imposing constraints.Academic Monthly, 46(5)
, 29–39.[郑思齐, 徐杨菲, 谷一桢. (2014). 如何应对“职住分离”:“疏”还是“堵”?学术月刊
,46
(5), 2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