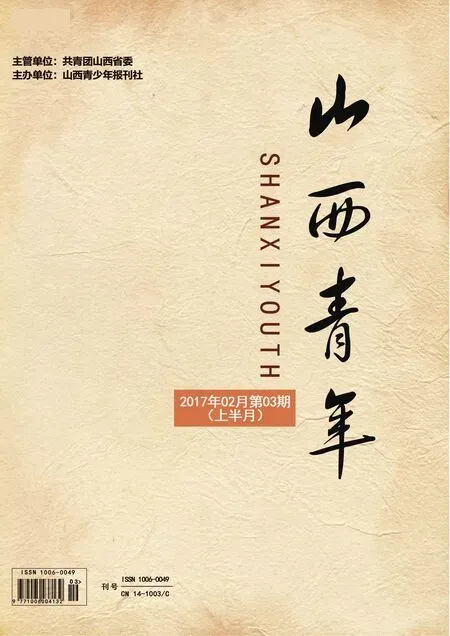论马克思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当代价值*
郭 英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论马克思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当代价值*
郭 英**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变使公众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迫切探寻确保经济发展速度得以保持、发展成果得以保存、发展的消极影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消除的新兴发展模式。因此,调整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对于我们全面审视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出契合当前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国家治理建设,进而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内容
(一)政治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自主性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曾长期被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这实际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虽然经济基础在决定历史斗争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处于关键性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也对历史进程的走向发生着影响。
恩格斯关于国家的经典定义“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法摆脱这种对立面;……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实际上暗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何者为基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的。二是,在得出社会决定国家后,恩格斯突出强调了国家对于社会的反作用。一国内的统治阶级为了解决冲突,保持秩序,将国家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具有日益与社会脱离的倾向。
(二)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一直以来都被一些政治学家简约化为“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即突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思想。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突出国家的阶级性、工具性的同时也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在这里,他们将国家的社会职能置于国家的政治统治得以存在、维持的基础性地位。而对于何为“社会职能”,也许可以从恩格斯的下列论述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持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在恩格斯看来,为了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斗争压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国家就作为“第三种力量”而存在。这第三种力量“似乎”是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大阶级之上,承担着将斗争的激烈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合法形式”的制度供给这一社会职能。在这里,恩格斯认为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根本上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被统治阶级只有在用极端的形式强烈表达自身的愿望时才能得到国家表面上的暂时妥协。
而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对法兰西第二帝国进行分析时曾指出“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马克思观察到,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某些时期,国家曾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牵制“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强调的是国家不顾统治阶级的反对而对被统治阶级作出某些让步从而在客观上维护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
(三)官僚阶层相对于国家意志的自主性
马克思结合其社会分工理论不仅揭示了官僚阶层产生的历史过程,而且根据封建君主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经验,指出了官僚阶层所形成的相对于国家意志的自主性,“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同样也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机关最初是为了满足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本质上是为社会的顺利运行而提供服务的社会公仆,它同农民、铁匠一样仅仅是一种社会职业。但是由于
官僚阶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垄断了关于社会真实状况的信息以及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具有很强专业性的知识,从而渐渐形成自身的特殊利益,成为社会的主人。
恩格斯在写给康·施米特的心中也曾表达相同的意思,“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强调官僚阶层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逐渐形成了同社会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但是恩格斯比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官僚阶层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对立状态直接促成了政府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虽然具有以上三个层面的具体内容,但它的理论本质是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即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与以市民社会为表现的经济基础的关系、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与作为社会力量代表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关系、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与其名义上的代言人而实际上被社会“捕获”的官僚阶级的关系。因此,为了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就必须首先理清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黑格尔渊源。
马克思直接承接的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是在纯粹逻辑思辨的基础上产生的。黑格尔在国家、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对比中完成了其市民社会思想的建构,“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随着马克思对社会观察的深入,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最大影响已不是具体的理论内容而是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层面的启发。
马克思汲取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成分,克服其唯心主义倾向,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完全区分开来,并深刻指出“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域下,马克思完成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当代价值
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倒逼着政治领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归根到底面对的是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规范权力的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展的成本。具体到马克思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三个层面:
(一)政治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这是因为,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过多的行政审批项目和繁琐的行政审批增加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动成本,从而抑制了他们的活动积极性。李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了本届政府对于减少行政审批的决心和目标:“本届政府任期五年内,至少取消和下放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省级政府也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明确要求。而且不光要看数量、还要看质量。今后省一级原则上不得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因此,仅在本轮行政体制改革开始的2013年,国务院就分四批共取消或下放了344项审批权,占国务院当时所有行政审批权总量的18%。2015年,仅中央指定地方实施上的审批事项这一项就分两批,共需要了210余项。行政审批的“取消”和“下放”,精简了政府机关的职能,释放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相对独立性是全面深化改革“啃硬骨头”的理论基础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是我国民众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阶级斗争虽然仍然存在,但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马克思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第二个层次的主要内容即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统治阶级的相对独立性对当前中国的适用性应经过一定的变形。这里的“统治阶级”应置换为社会利益集团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就是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而相对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问题的关键是获取利益的渠道是否合法,数量是否正常。利益集团占有的大量社会资源既削弱了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又对进一步改革坚持正确的方向造成威胁。因此,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必须找到形成各个利益集团的原因,从源头上铲除利益集团,而对利益集团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的根除必然依靠力量强大的国家。马克思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中谈到的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保持对强势利益集团的相对独立性,以维护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突破强势利益集团束缚的理论基础。
(三)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于官僚的相对独立性是反腐的理论基础
自国家诞生,出于管理的需要通过或任命或选举的方式从民众中选出一部分人作为管理者之日起,官僚的腐败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的种种制度设计在就是在高效的行政效率与预防腐败之间进行平衡。中国有着千年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官员廉政的保持依靠的是皇权的权威和个人的道德感。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国,皇权的威慑力早已不复存在,而道德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也失去了“熟人社会”中的约束力,再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很大一部分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实际需求相比是滞后的,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了官员的腐败成本。腐败约束力的减弱,成本的减少再加上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和官员身处制度内的优势,使当前官员腐败成为影响政府行政效率乃至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和民众对政府认可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党工作作风的改良和查处、惩治和预防腐败。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从2013年至2016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其中,查处的中管干部覆盖了31个省区市,共计109人。查处腐败官员数量之多,涉及领域之广,特别是一些副国级官员的落马让民众感受到了此次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将运动式反腐常态化为制度性反腐的能力。马克思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中的国家对官僚的相对自主性既解释了为何在作为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会存在官员腐败现象,也为解决官员腐败问题提供了解决依据和方法,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国家必须作为主体解决侵害公共利益的官员腐败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4.
[2][德]黑格尔.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9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47.
[4]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A].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00.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M—CX—ZD—201601)。
A
A
1006-0049-(2017)03-0023-02
**作者简介:郭英(1990-),女,汉族,河南南阳人,北京化工大学,2014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