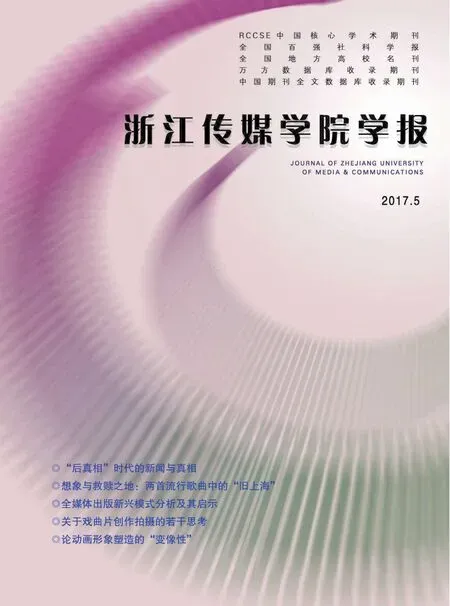论动画形象塑造的“变像性”
苏东晓 蒋 平
论动画形象塑造的“变像性”
苏东晓 蒋 平
动画艺术的特质既是技术的也是美学的,动画艺术因为对造像的依赖而不可避免地更具偏离自然主义表象的表现性风格,它对人为性、建构性的彰显带来的是感觉索引性,可以一定程度打破普通影视中虚拟影像的客观索引性带来的超真实幻觉,所以,变像是动画形象塑造的形式法则。
动画;表现性;间离性;变像性;现实关系
聂欣如教授在探讨动画的本体时,认为动画是一种仿真的意指,他以迪斯尼动画《白雪公主》对白雪公主的造型设计为代表,指出动画逐渐削弱其漫画基础的鲜明意指性,推崇仿真性,而动画的仿真性正是动画获取观众的魅惑力之所在,因为只有在仿真的条件下,动画才能通过细腻的表演传达情感,感染观众。但聂欣如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动画的极端仿真却没有获得其期盼的观众反应,美日合拍的动画电影《最终幻想》(2001)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聂欣如教授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提出“动画是一种仿真的意指”,既要仿真,又不能失去意指。[1]但意指这个概念研究的是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模式,换言之,所有符号都涉及意指问题,实景真人的普通影视与动画归根结底都不是自然真实,都是一种人为的艺术符号,都有意指性,那么动画的“仿真的意指”与普通影视的“仿真的意指”的区分又在哪儿呢?聂欣如教授在对动画的漫画基础和影像进步的区分上探讨动画本体,论说动画魅惑力,似乎更多地还是在技术层面上孤立地阐释动画的当下市场反应,而未能在艺术本体上更深入地探析动画的审美特质。
笔者认为动画艺术确实有其不同于普通影视艺术的特质,动画的形象塑造也必定有其区别于普通影视的形象塑造的特质,但它不是简单的“仿真的意指”,它应该是动画形象塑造中突出的“变像性”。这种“变像性”既是由动画技术的特质决定的,也是由动画不同于普通电影的美学追求决定的,因此,“变像”法则构成了动画形象塑造的形式法则。
一、“表现性”:动画形象塑造“变像性”的技术特质
作为人工制品都不可避免地受人工制作技术、手段的影响而与原始真实有所偏离,从而带上人为的“风格”,这就是人工制品本性上无可回避的“风格化”问题。但是从人工制品呈现原始真实的程度上进行区别,艺术史上还是有了强调摹仿与再现客观真实的自然主义,以及强调抒写与描绘人类精神世界的主观真实的表现主义之分。众所周知,影视与建筑、音乐和书籍一样,都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而制作出来的人工制品,因而,影视本身也必然是有“风格”的,但普通影视的风格与动画的风格是否仅仅只在它们都作为影视作品这一层面上探讨呢?笔者认为风格的产生首先受到了技术手段的影响,普通影视与动画的生成在技术手段上虽同源却异流,这也就决定了它们在“风格”上显现出了不一样的追求。
(一)摄像与造像
如果说照相是记录了自动世界中的某个静止画面,凝固了永恒流动的时间长河中的某个瞬间的话,那么录像则是一系列自动的世界的投影,保留了某个已终结的时间片段的永恒运动。从科学本性上讲,这两种技术都有客观的、物质性的原物像源,以逼近原物的方式满足于我们潜意识里提出的再现过去世界的需要;从美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两种技术的发明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热爱,是基于我们对时间(生命)流逝的恐惧及以人的“类本性”与这种恐惧的对抗。早期的影视建立在摄影和录像的基础上,它们离不开现实时空中的实景和真人,因此,巴赞称“由机械产生的影像……达到与被摄物等同”[2],“电影成为现实的渐近线”[2](307);即使是强调电影的幻觉和造梦功能的蒙太奇派,他们的“假定性”不过是影像叙事结构中的“假定性”,影像本身仍然是以“逼真”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的普通影视以“摄像”为主要技术手段,着重依赖机械本身的复制和记录功能,重真人实景拍摄,也就决定了它的影视形象更倾向于自然主义的写实。
然而,早期动画的制作虽然也借助摄像机,但动画摄像却没有一个在真实的自然世界中存在的真人实物像源,而是由动画制作者先用绘、塑、剪等方式构造一个个无生命的人物及人造景观,再将其摄录处理成影像。动画创作在绘制图像时,虽然也参照真人实景,追求一定的表象相似,但相较于普通影视的直接摄录真人实景,动画创作还多了一道创造摄录像源的工序,即“造像”,因此除了依赖摄像机本身的功能外,动画创作对其它造型技术的依赖也十分突出,比如,水墨晕染的画像绝不同于橡皮泥捏制的塑像,这也就决定了动画创作的人为建构性更为突出,动画创作者的主观选择会更明显地印渍在其创造出的形象中。所以,与普通影视相比,动画的影视形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更容易偏离客观自然的图景。
(二)摹像与衍像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当今的影视已经可以摆脱现实时空中客观性与物质性的原物的限制,进入了完全虚拟的时代,如《侏罗纪公园》《阿凡达》等科幻影片就建构了现实中并无原物却在屏幕中栩栩如生的原始动物和外星世界,给人以极大的震憾。当代影视屏幕中出现的这些由真人实景摄录与虚拟技术处理共存的影视形象是属于普通影视形象还是属于动画形象呢?亦或是由于技术的合流趋势,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把普通影视与动画作为两种艺术类型加以区分?我们认为,虽然同样使用虚拟技术,但对技术开发的路径和具体运用,普通影视与动画仍然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称之为“摹像”与“衍像”之别。
尽管《侏罗纪公园》屏幕上的恐龙在当今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它们的确曾经是这个星球远古时代的霸主,无数留存至今的化石也标示了它们曾经的真实形态,电影不过是遵循着基本的科学原则,努力在虚拟的空间复活了过去的“真人实景”罢了。《阿凡达》虽然虚拟的是并未为科学所证明的外星世界,但外星世界中那些形态奇异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毫无疑义地使人联想起真实存在的地球生物,或者说,《阿凡达》中虚拟景观的色彩、纹理、运动等构成因素对应了我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经验,因此使我们在感官的表层体验上对这些虚拟景观真真切切地感知到了真实,亦即虚拟景观非“真人实景”但胜似真人实景。上述两部电影虽然使用了虚拟技术“无中生有”,但这里无中生有的形象却栩栩如生,这不正是古典造型艺术摹仿理想的最高境界吗?所以说,普通影视制作即使使用虚拟技术,实际上技术开发、使用的路径和目的也重在以“真人实景”为第一参照源的“以假乱真”,这不过是特效化的摹仿和再现,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普通影视的特效化。不管是普通的摄录影像还是特效摄制影像,它们都高度忠实于真人实景或以真人实景为第一像源的摹仿理想,共同追求一种将表象与现实同一的效果,即所谓“摹像”。
而动画创作在绘制图像时,更强调的并非忠实摹写真人实景,而是更忠实于表现人对世界的独特感知和想象,并且相较于强调再现外在客观世界真人实景的“摹仿”理想,它更强调表现内在主观世界的情感真实,强调人为性,即所谓“衍像”。在创造影视形象时,是重视摹仿真人实景的“摹像”,突出形象的自然主义特征,还是重视演绎内在精神世界的主观抽象的“衍像”,突出形象的表现主义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制作倾向往往会影响人们对一部“非真人实景”拍摄的影片像不像动画作品的判断。比如,斯皮尔伯格的《丁丁历险记》(2011)虽非真人表演,但由于采用“真人动作捕捉”技术及仿真人拍摄电影的理念,其人物的形象与表演都极其逼近真实,往往使人产生恍若在看真人表演电影的错觉。
技术本身及使用技术的理念不同,使得动画在建构手段上并不呈现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而是不可避免地呈现创作者的人为性建构,充满创作者的丰富的个性。所以,与其说“非真人实景”拍摄是动画的特质,不如说原初动画因其“非真人实景”拍摄的技术基础产生并强化了其比普通影视更具偏离自然主义形象的表现性风格。
二、“间离性”:动画形象塑造“变像性”的美学追求
虚拟技术在现代各领域中的广泛运用并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激进的批评家对此产生了深深的忧虑。鲍德里亚说“今天,整个制度都在不确定性中摇摆,一切现实都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3]在这个表述中,鲍德里亚的忧虑更多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但至少对于我们思考虚拟影视的审美问题提供了两个维度:一是虚拟影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二是我们凝视虚拟影像时与屏幕的关系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思考动画的艺术与审美特质的两个维度。
(一)真实与超真实
鲍德里亚揭示并批判了虚拟影像的“超真实”问题,他说“模拟是和表征对立的。表征始于符号与现实物对应的原则(即使这一原则是乌托邦,它也是基本公理)。相反,模拟则始于这一对应原则的乌托邦,始于符号即价值的激进否定,始于符号乃是任何指涉的颠倒和死亡宣判。表征力图通过把模拟解释成虚假表征来吞噬模拟,而模拟则是把表征作为一个仿像来统摄表征的整个体系。”[3](170)也就是说,在这里,“表征”下还有相对“真实”的存在,而“模拟”下的“真实”只是一个完美的外壳,这个外壳下却是完美的不存在,即“模拟”是一种“超真实”,所谓“超真实”就在于“它不仅把一种缺席(absence)表现为一种存在(presence),把想象(imaginary)表现为真实(real),而且也潜在削弱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4]鲍德里亚提出“模拟”与“表征”的对立,辨析“真实”与“超真实”的本质差异,显现了他对现代文化的审美忧虑,极其逼真的虚拟可能破坏我们与现实的真实关系,使我们把虚拟当做了现实的真实,因而也就给予了某种意识形态以极权。如果说鲍德里亚的对虚拟影像“超真实”的批判显得有点抽象晦涩的话,那么,斯蒂芬·普林斯从感知心理分析视角对数码影像“感知真实”的揭示则浅显易懂得多。普林斯说:“感知真实的影像对应于经验,是因为电影制作者们正是为此而将它们制作出来。这样的影像展示出一种诱因的成套的等级制度,将光线、色彩、纹理、运动和声音的展示都以与观众对于日常活动生活中同种现象的理解相符的方式组织起来……于是就在电影影像和观众之间指定了一种关联性,并且它能够涵盖不真实的影像,以及那些指涉真实的影像。正因为如此,不真实的影像可能在指涉上是虚构的,然而在感知上是真实的。”[5]从鲍德里亚和普林斯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家们都承认虚拟影像极其“逼真”的外在形式,它们一定要在现象学意义上建构起自身与现实世界的某种相似性,以致于能诱使我们对它们“感知真实”。但理论家们恰恰又最反感这种仅仅作为感知上的真实,因为他们认为在那里可能存在着一种可怕的虚假和欺骗,别有用心者可以利用它轻松地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的企图,人类文化也可能因此自甘堕落。
然而,虚拟影像在当代社会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中已势不可挡,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自身不在过度的欢娱和自傲中迷失?换言之,虚拟影像有无实物像源并不成为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建构和审视虚拟影像的目的和态度。鲍德里亚和普林斯的批判与其说是责备虚拟影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如说是警示我们关注凝视虚拟影像时自身与屏幕的关系。在虚拟影像的建构和审视中,我们或许应该追求这样的审美理想:虚拟影像的建构既能满足我们开拓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本能欲望,同时也要我们能在当中时刻意识到自身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同样,使用虚拟技术时,作为一种艺术类型而言,动画可能比普通影视更趋近于这种审美理想。
(二)客观索引性与感觉索引性
“现实关系”和“现实关系的表达”是这里讨论的核心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某种意义上,“表象”或者“现象性”已经跟现实混杂在一起,构成我们眼中的现实世界。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是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现实世界的物质本性,因此倾向于把现实关系简化为语言所描绘的世界,把现实关系的表达等同于现实关系。马克思主义则坚信现实世界存在着物质性的客观对应物,恰当的现实的关系的表达则更能呈现真实的现实关系,反之,不恰当的现实关系的表达则可能对真实的现实关系产生遮蔽。鲍德里亚的批评显然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对虚拟影像的分类及对其所表达的“现实关系”的程度的考察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中进行的。
如果把现实关系看作是对象,普通影视与动画看作是对象的符号,那么,对象与其再现符号之间的关系会有哪些可能呢?符号学家C.S.皮尔斯认为同一种对象有多种不同的再现符号,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像似符(iconic signs),它的符号形体以肖似的方式来代表对象,它是对符号对象的写实与模仿。第二个是指示符(indexical signs),它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存在着因果相承的联系,能够指示或索引符号对象的存在。第三个是规约符(symbols),它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没有肖似性或因果相承的关系,仅仅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6]我们可以认为,普通影视与动画作为符号表征现实关系,大致上也可以有以上三种符号形体,但普通影视与动画作为技术基础有原生差异的两种符号系统,它们的符号形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种可能中还是存在不同的。
莫林·弗尼斯指出,对活动影像进行分类,可以考察它们在以“模拟—抽象”为两个端点的轴线之中处于什么地带,而动画与其它影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动画在这个轴线图形中大概位于中间位置,其它的影像则是更接近于模仿的一端。[7]所以,笔者认为,普通影视与动画都不是现实本身,我们借助它们观照现实,不过都是在“索引”与“象征”关系中寻求它们的“现实对应物”;但又恰恰因为它们对现实表象的模仿在肖似性上存在着差异,以至于我们在惯有的情境中更容易相信更逼真的表象的真实性,当这个更逼真的表象所指涉的是虚假的真实时也是如此。然而,现实和表象并不等同,为了完整地反映现实,就需要一种更能揭示现实深层结构关系的表达模型。布莱希特在批评现代摄影术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连一个简单的‘现实之复制’也比过去都更拙于解释任何的现实状态,因此情况变得极为复杂。像拍摄克虏伯或A·E·G工业集团的工厂时,相片对这些机构的内在真相几乎无所透露,显现的只有外在。而真正的现实却是在功能方面。比如工厂把人类关系物化的事实就并未在表现工厂的照片中传达出来。所以必定确实‘有什么应当建构’,某种‘人工的’、‘制造出来的’东西必要指明出来”。[8]在本雅明看来,照片不过是以更逼真于现实细节表象的外在更隐蔽地掩饰摄影者的主观性,从而也以“世界本来就在那里”的客观存在表象消解了摄影者、观众与摄影对象之间独特的关系。在这里,实景影像与极其逼真地虚拟现实的影像正如本雅明所批评的照片一样,这种影像与表象世界之间明显的一致性决定了观众愿意相信影像是“真的”,换言之,实景影像与逼真的虚拟影像具有“客观索引性”,在惯有情境中给人带来影像等同于现实的幻觉,而为了更好地揭示现实,恰恰需要打破这种客观索引的幻觉。
如上所述,动画也有虚拟性,但是,动画的影像可以不那么受物理法则的约束,可以偏离客观自然物的外在形式,可以偏离大家所熟悉的日常表现形态的诉说方式,首先能够形成视觉感官上的陌生化,从而在符号索引现实对象的认知时间轴中造成一种延缓和暂留,留给观众更多主动思考、唤醒真实感知的空间;其次,动画对人为性、建构性的彰显,也使得动画制作者因此并非像实景拍摄影片制作者或者以“摹像”为原则的虚拟影像制作者那样可以“隐藏自己”对影片施加的作用,从而也更清晰地让观众感知动画影像与现实对象之间内在的索引性、解释性关系。换言之,同样作为索引符,普通影视与动画因为与现实表象肖似性的差异,它们的索引功能有别,动画影像在视觉上对客观自然形式的偏离程度更易于打破客观索引的幻觉,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感觉索引性”,在通常的情境下,它不直接索引客观,以造就“以假乱真”的自欺,而只是索引向“感觉”本身,显现出符号表征现实的局限性,从而可能更多地唤起观者的能动性,更好地拨开遮蔽真实的迷雾。
因此,与其说一般虚拟影像与动画的区别在于技术上的根本差异,不如说在于两种影像在艺术形象与审美追求上的差异。动画影像应该具有这种显而易见的“风格”,即与一般影像相比,它们更加以视觉上突破客观自然、现实表象的形式为表现基础,以更强调与更创新性地创造影像的“间离性”,更努力地以唤起观者对真正现实本质的感知与追问为精神追求。
三、“变像”:动画形象塑造“变像性”的形式法则
如上文所分析,相较于普通影视形象的客观自然化,动画形象则更具表现性风格,所以,“变像”就构成了动画形象风格的主要形式法则。作为动画形象塑造的剧本创作法则,“变像”大致指动画形象塑造比普通影视形象塑造更强调根据内在的、抽象的、精神的真实感等因素改变动画形象的外在客观自然形态及常规表现形态。“变像”之“变”实际上强调的是动画形象塑造中人为性的袒露,动画形象塑造不极端追求以事物的客观自然形态和常规感知促成观众对事物的认同,相反,动画形象常常用各种变形的方式来突显形象的特点,表现强烈的意趣,这样的变形就使动画形象与现实世界通常事物的自然表象形态产生差异。在这里,“变像”并不限于成为动画形象的事物之可见的视觉形象之变,而是涵盖视觉、听觉等感官综合因素的变异,主要是事物形体、事物时空存在感、事物话语声音等方面的自然表象之变。
(一)事物形体的变像
事物形体的变像,即动画形象塑造中对事物的外观形状、比例、色彩等进行夸大、缩小、简化、抽象和更换,偏离客观事物的自然形态,突显创作者的审美意趣。动画中事物形体的变像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境中突出表现。
首先是造型变像。造型变像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带着谐趣效果的变形。如,《海贼王》里的路飞,他眉毛细如线,嘴巴只呈现为一道弯弧,眼睛大而圆,眼珠却小得成一个黑点,正是这种非常的形貌变化形成谐趣的效果,突出了路飞乖张鬼马的性格;《海贼王》里的另一角色,海贼船的女船长亚尔丽塔小姐,身体似大象一样庞大,脸极扁肥、小眼、阔嘴,而偏偏自命为美女,这样夸张的丑态与她的自恋性格正好形成强烈的反讽。这种比较夸张的造型变像在漫画改编的动画里表现得比较突出。造型变像的另一种情形是严肃叙事中对事物特性的审美突出。这种情形下的事物造型设计总体上是比较克制夸张式的表现的,如宫崎峻动画电影中的主人公造型就相对写实,迪斯尼动画剧情长篇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但是,变像依然是这类严肃动画的主要旨趣,如动画中俊男美女的眼晴在五官中的比例总是远远超越于真人的真实比例,显得更大更亮,身材比例也更趋于完美,显得更高挑俊秀。
其次是剧情变像。动画中事物形体的变像有些并非造型设计本身形成的变形,而是在叙事过程中靠特异的剧情设计完成。动画中事物的形体往往可以伴随着剧情的进展、情感意念的瞬息变化,不受物理规律约束而更自由地改变。如迪斯尼动画《猫和老鼠》中的汤姆与吉米就常常因为相互追逐被重物所压而变成纸片,脑袋被打得缩进脖子里,但随后马上又完好无损地恢复;日本动画《灌篮高手》中的人物常常在受挫瞬间从帅哥猛男一下变成面貌身形扭曲的滑稽小丑,而等受挫情绪复原后,马上又玉树临风;皮克斯动画《超人总动员》中的弹力女超人的形体各部分则可以随剧情需要变成降落伞、皮艇等等。
(二)事物时空存在感的变像
这里所说的“事物时空存在感”,强调的是事物的自然时空存在方式及人们对其感知的自然状态;这里的“变像”则是指在动画形象塑造中,通过动画技术手段及特定的剧情设计,有意改变人们对事物自然存在的日常感知,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首先是创设极度感知。所谓极度感知,是指超常规的感知,非自然状态的感知,是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的感知。目前动画有几种创设尤为受到关注:其一,对速度和时空的极度感知的创设。人类的感觉器官对自然中的速度和时空的感知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超出了这个范围,就无法实现很好的感知,但人类创造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人们突破自身物种的限度。动画擅用虚拟镜头等手段营造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如《驯龙高手2》开场,“小嗝嗝”和“没牙仔”穿越云霄的一连串翻飞镜头,就使观众仿佛亲历云端、尽享极速飞行的快乐。此外,动画在制作中借鉴经典的实拍照明方法和摄影技巧,但又不完全遵循纯自然的效果,而通过对实景拍摄的方法进行改造,使观众看到近似真实,却又与现实场景不完全吻合的画面,从而获得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如《驯龙高手2》中龙飞过风向标的这一场景,在传统制作中,制作者会对作为背景的天空和作为前景的龙群分别曝光,使画面里的所有细节都清晰可见;在实景摄影中,导演会选择只曝光天空,使龙群暗淡下来,或是只曝光龙群,使天空变暗,而《驯龙高手2》则选择了中间点——龙群曝光不足而天空曝光过度,这样的曝光范围小于实景拍摄影片,但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画面——略显昏暗的龙群在明亮的天空中映射出美丽的轮廓。又如此片“冰洞重聚”的一幕,拍摄团队将光源设定在冰的内部,从而展现出极度柔和、自然且浪漫的效果。[9]其二,对微观事物的极度感知的创设。微观世界是一个庞大而又充满神秘性的世界,因为在日常中不易感知,人们对微观世界充满了好奇,当动画技术能将这个微观世界聚焦放大时,动画是充满吸引力的,如毛发渲染技术的开发,可以使动画中动物的毛发表现得栩栩如生,令人惊叹。但这里的极度感知并不仅仅体现在仿真的意义上,而更强调其借用仿真的技术表现和释放人们发现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审美快感。如《冰雪奇缘》里对雪花之美的表现,制作团队为电影模拟出两千多种不同的雪花,细腻地呈现了日常生活中不易感知到的完美的雪花形态及其晶莹剔透的质感。但最令观众惊叹的还是艾尔莎的冰雪宫殿的建造,艾尔莎的冰雪宫殿从一个非常小的雪花凝结开始,由小变大,由少变多,最后变成了一座巍峨壮观、精美异常的梦幻宫殿。制作团队将一个自然界小雪花的凝结过程放大,并将近似于雪花形成的效果艺术化地模拟转换为了梦幻宫殿的形成,这个镜头成为电影中最长的镜头之一,也是最具魅力的镜头之一。其三,对人格的极度感知的创设。虽然动画里也不乏性格丰满立体的圆形人物,但总是不同于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典型,动画人物人格简化、类型化、象征化的意味要更浓厚些。在叙事性较弱的动画里,如中国学派的两部经典之作《山水情》《牧笛》以中国水墨画的大幅留白与高山流水的空灵意境烘托出来的一师一徒、一童一牛就以一种极简蕴籍无限。在叙事性较强的动画里,对人格的极度感知的创设并不是以牺牲现实人格的复杂多样为前提,而是指在动画镜像叙事的过程中对能映现深刻现实的人物人格作出特定的强调和超出日常均值的突出,唤起被日常平淡所麻木了的感知。好莱坞动画虽风格各异,人物性格有从迪斯尼的经典向皮克斯的后现代的流变,但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表现和对比还是较为强烈,超出日常均值,容易识别。如白雪公主的单纯善良和皇后的邪恶歹毒、《飞屋环游记》里艾丽的活泼和卡尔的古板、《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等等。宫崎峻动画充满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人物更具人性的多面,但人物依然以其突出的人格特征让人记忆犹新,如红猪、无脸人等。
其次是推崇审美幻想。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幻想是艺术的专长,影视艺术则将这种想象与幻想视觉动态化,而动画的媒介特点则使其在将想象与幻想进行视觉动态化审美表现方面尤其具有优势,也必将成为其界定自身、发展自身的必要条件。以下两方面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动画较普通影视更乐于并善于表现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幻想,更需要通过这样一种审美变形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其一,动画幻想性题材选择的倾向性。虽然动画也可以表现现实主义题材,但幻想性题材更能展现其优长。杜桑·伏科蒂克曾说:“动画不受物理法则的约束,也不为客观真实所奴役。它无需模仿生活而只需解释生活。所以,当我接到一个动画片剧本时,首先要问自己:如果不做实质性的改动,这个本子能否用真人拍摄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这个剧本不适于动画片。换句话说,‘画’一部可以用真人来拍摄的影片是愚蠢的。”[10]纵观迪斯尼长篇动画电影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1937年的《白雪公主》直到今天,迪斯尼动画电影故事有几乎一半以上是取材自各国的童话、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取材于其他名著的故事则做了较大的改编,最显著的改编特点则是将原著中的人类故事改编为动物故事,如《狮子王》取材自莎士比亚的名作《哈姆雷特》,但只是保留了原著的叙事结构,讲的却是非洲大草原上动物王国里一只小狮子经历磨难,成长为王的故事。就算是不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通常也少不了拟人化的(动)物的存在,或者反其道而行,充满奇观性地将人拟物化,让人类角色充满超常能力,如《海贼王》中的路飞吃了恶魔果实后变成橡胶人,宫崎骏动画里能通灵百兽的幽灵公主等等。其二,动画史上众多经典的亦或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都非常优秀地呈现了这样的想象和幻想。如,迪斯尼著名的音乐美术片三部曲《为我谱上乐章》《旋律时光》《幻想曲2000》将音乐情感用炫酷的视觉画面呈现,给观众带来震撼;《哆啦A梦》长演不衰近五十年,机器猫百变的道具映照了我们无数的幻梦;《疯狂动物城》有着些许阴谋,但这里出行的火车有根据动物不同体型制作的车门,饮料传输管道高低不同适应不同身高的动物,交通道路有水陆之分适应不同物种习性……大小不同,强弱各异的动物们各有各的社区,怡然自得地活出自己又彼此和谐相处,影片中呈现的动物乌托邦不知触动了多少人的内心。
(三)事物话语声音的变像
影视中的声音不仅具有渲染情绪的作用,还具有重要的造型作用,对于动画而言,声音的造型作用更甚于渲染情绪的作用,所以,动画中事物话语声音的变像性也与事物外在形体和时空存在感知的变像性相呼应。事物话语声音的变像主要是指对位于事物外在形体与时空存在感知的不同于自然形态而有意变形了的话语声音表达,从而赋予事物话语声音的音色创造的无限性,以及事物话语声音强烈的舞台夸张性与表演性突出。
首先,动画形象话语声音具有更为强烈的画外性,而通过话语声音的非自然常态式变形,动画形象话语声音导向象征世界、意想世界或情绪情感世界的桥梁作用更突显。如变形了的动画声音更具意指性。捷克的动画片《鼹鼠的故事》系列没有对白,完全通过有意指的声音表现情感与思想,《鼹鼠与推土机》里推土机破坏花园时发出的“哧溜—哧溜”的声音就不是自然形态下推土机工作发出的声音,但这样的变形却将推土机破坏美丽花园的快速行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也表达了鼹鼠的焦急;鼹鼠、刺猬、兔子的声音未必稚嫩细弱,但《鼹鼠去城市》里鼹鼠、刺猬等动物发出稚嫩细弱的声音却能与推土机、电锯、拖拉机等机械低沉的轰鸣形成鲜明的对比,意指成人世界与现代世界对本真美好的摧毁。另外,动画的声音变形也指将本来无声的情感和思想有声化,如极度伤心时,以并不实际发生的心脏碎裂的视听呈现。
其次,动画的角色配音在动画创作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好的角色配音为人物增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如迪斯尼动画《米老鼠与唐老鸭》中,唐老鸭的声音沙哑急促,带着嘎嘎的鸭叫尾音,很有特征,代表了角色是一只脾气急躁、笨头笨脑的滑稽鸭子;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动画片《变形金刚》中,汽车人与霸天虎众多角色的声音都带着一种金属振动特有的音色,擎天柱沉稳的声音是其正义中坚的领袖角色的表征,威震天沙哑低沉的声音显现其狠毒阴险的个性,声波自带机械合成性的音色也音如其名;海绵宝宝的声音清亮,聒噪不安……此外,动画里那些善良纯真的角色往往声音清脆甜美,滑稽人物常常声音急促、喋喋不休、大呼小叫,声音与其类型的对应性也比普通影视明显。可以说,普通影视的人物语言声音一般真实自然,声音的变化与其话语表达的自然情境相适应,而动画人物的语言声音则通过目标明确的特定性调整,如音高、音长、音色、音量的特定性改变等,成为动画人物性格标志的声音代表。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动画形象的审美特质恰恰不在于无止境地“仿真”,当然也不在于简单意义上的“意指”,而在于其执着地以“变”逐“真”。动画不否定一定程度上的仿真,但仿真决不是动画的审美本体,但强调动画审美特质在于“变”也不是仅仅从形式上为“变”而变,动画之“变”是一种体现人文情感、对现实表达深刻关怀的审美之变。所以,具体到动画形象塑造的原则来说,就是无论在动画形象塑造的文学剧本创作还是动画设计制作中,都要充分关注作为动画形象的事物形体、事物时空存在感、事物话语声音等方面的自然表象之变,要充分张扬其与习惯性认知、日常状态之间的适当距离,以一种永恒的“拒斥”和“不完全合作性”来保持人的超越日常、自由自觉的能动性。
[1]聂欣如.动画本体美学:仿真的意指[J].艺术百家,2013(5):56-63.
[2]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3.
[3]Mark Poster.JeanBaudrillard:SelectedWriting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20.
[4]鲍德里亚.拟仿物与拟像[M].洪凌译.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98:135.
[5]吴琼.凝视的快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5.
[6]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50-70.
[7]Furniss Maureen.ArtinMotion:AnimationAesthetics[M].Sydney:John Libbey and Co.,1998.
[8]本雅明.摄影小史[A].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C].许绮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8.
[9]动画电影《驯龙高手2》技术亮点解析[J].现代电影技术.2014(11):57-58.
[10]杜·伏科蒂克.动画电影剧作[J].世界电影,1987(3):72.
[责任编辑:詹小路]
本文系20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和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的研究成果。
苏东晓,女,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蒋 平,男,讲师,文学硕士。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J954
A
1008-6552(2017)05-008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