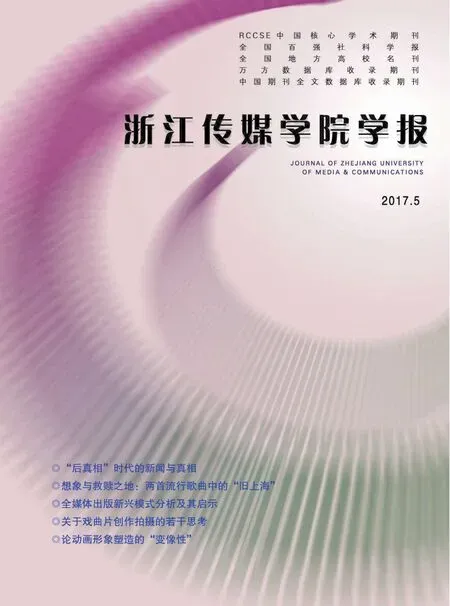纪录片新体裁初探
——以《辛普森:美国制造》《纽约灾星》《制造杀人犯》为例
王 培
纪录片新体裁初探
——以《辛普森:美国制造》《纽约灾星》《制造杀人犯》为例
王 培
《辛普森:美国制造》《纽约灾星》《制造杀人犯》等作品的出现使纪录剧集这种新的纪录片体裁逐渐进入业界和学界的视野。这种纪录片与连续剧的结合,能否成为未来被广泛采用的纪录片创作载体之一?影片长度和体量上的变化对纪录片创作将带来何种影响?目前看来,纪录剧集在题材偏好和创作风格上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它与系列纪录片在创作和表现上的区别在哪里?笔者从这些问题出发,以《辛普森:美国制造》《纽约灾星》《制造杀人犯》等作品为例,对纪录剧集这一纪录片体裁进行初步分析。
纪录剧集;纪录片;新体裁
北京时间2017年2月27日,《辛普森:美国制造》获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这在纪录片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焦点几乎都集中于一个问题:《辛普森:美国制造》到底算纪录片还是电视剧集?有些评论者甚至认为它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奥斯卡评奖,因为这是一部由ABC、ESPN等电视平台播出的5集纪录式连续剧。尽管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该片导演伊斯拉·埃德尔曼说,执导这部纪录片的唯一理由就是渴望制作一部史诗般的电影,但是绝大多数观众都是通过电视看到这部纪录片的。
抛开电影还是电视的争论,《辛普森:美国制造》作为一部纪录片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也是近年来国际上最好的纪录片作品之一。在笔者看来,它不仅为观众提供了精彩的内容和值得深思的命题,也为世界纪录片领域开拓了新的纪录片体裁。作为纪录片研究者来说,后者更值得我们关注。这种纪录片与连续剧的结合,笔者姑且将之称为纪录剧集,能否成为未来被广泛采用的纪录片创作载体之一?影片长度和体量上的变化对纪录片创作将带来何种影响?目前看来,纪录剧集在题材偏好和创作风格上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它与系列纪录片在创作和表现上的区别在哪里?本文中,笔者将从这些问题出发,以《辛普森:美国制造》《纽约灾星》《制造杀人犯》等作品为例,对纪录剧集这一纪录片体裁进行初步分析。
一、纪录片新体裁——纪录剧集
(一)作为一种新兴现象
《辛普森:美国制造》获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所引发的争议使纪录剧集这一新的载体为更多人所注意,但事实上,纪录剧集这一新的纪录片载体的出现并非从《辛普森:美国制造》开始。应该说,是它与2015年2月美国HBO电视网首播的6集纪录剧集《纽约灾星》和同年12月美国网络台Netflix首播的10集纪录剧集《制造杀人犯》的先后推出及各自引起的巨大轰动效应,才使纪录剧集作为一种新的纪录片体裁被业界和研究者所关注。
《纽约灾星》的主角是时年72岁的纽约著名地产大亨西摩·杜斯特的长子罗伯特·杜斯特。一百多年来,在美国纽约,杜斯特家族拥有及管理着诸多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包括世贸中心、美国银行大厦以及位于时代广场的康泰纳仕集团总部,家族资产达到44亿美元,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最富有的美国家庭之一。然而,令罗伯特·杜斯特被公众关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其家族背景,而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被质疑至少与前妻失踪、密友被杀和邻居被杀并肢解等三起案件有关。于是,剧集从2001年杜斯特涉嫌杀害邻居并肢解的案件开始,层层深入地挖掘了他如何三次成为罪案的主要嫌疑人,又三次都离奇脱罪的传奇经历。剧集中不仅采访了案件侦办人员、受害者的亲友、杜斯特家族成员等相关人员,还两次采访了罗伯特·杜斯特本人。而最具戏剧性的是,在该纪录片的最后一集结尾,也即对杜斯特的第二次采访结束后,杜斯特走进酒店的洗手间时,身上无线话筒并没有关闭,从还在收音的麦克风中传出了杜斯特低声的自言自语:“行了,你被抓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究竟干了什么?当然,(我)把他们都杀了。”至此,这部志在讲述谋杀悬案的纪录片,从主创者原本的镜头记录和事实展现的初衷,到随着拍摄的进展,导演和团队不自觉地承担起探寻真相的使命,最后因为一次意外而协助了案件的侦破。该片在播出后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其原因除了影片出人意料的结尾之外,还有该片极强的戏剧性,使许多观众在引人入胜的情节推进中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纪录片,因而也有人将该片称为一种新连续剧。
《制造杀人犯》是由两名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劳拉·瑞奇阿迪和莫伊拉·德莫斯历经十年拍摄而成的10集纪录片。影片的主人公,智商只有70的史蒂芬,于1985年因强奸罪名被判入狱。从此,他的人生轨迹急转直下。入狱18年间,他和家人从没放弃过为了证明其清白而努力,期间也有两次能够获得清白的机会,却都因警方的置之不理而白白错过。2003年,美国法庭引入了DNA技术,史蒂芬才沉冤得雪。在他正为3600万美元赔偿金与当地政府对簿公堂时,他的人生噩梦再次上演。2005年,史蒂芬和智商同为70的侄子布兰登,因涉嫌杀害女摄影师被捕。警方拿出的DNA证据真假难辨,但依然说服了陪审团和法院,二人被判终身监禁。影片通过大量的采访,对案件进行了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分析,过程中展现出了警方办案程序的诸多问题。该片一经播出,产生了巨大反响,在美国社会掀起了关于美国司法体系公正性的全国性大讨论。
在5集、总时长近8个小时的叙述中,《辛普森:美国制造》采用两条故事线索的叙事方式,讲述了O.J.辛普森如何从一名黑人聚居区的无名少年到橄榄球超级巨星,又是怎样从人人崇敬的美国英雄沦落为杀妻疑犯。在轰动全美的现象级案件中,辛普森的“梦之队”律师团如何利用媒体的力量、种族的矛盾和警察办案、检方公诉过程中的漏洞,使辛普森顺利脱罪,以及英雄形象陨落后的辛普森最后堕落,并最终因为一起无聊的“抢劫案”被判刑33年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在影片中与之交叉讲述的则是尤拉·拉芙事件、罗德尼·金事件、娜塔莎·哈林丝事件、洛杉矶黑人暴动等事件背后,美国加州,特别是洛杉矶地区几十年来种族问题的历史状况。同时,司法体系、媒体环境、名人光环与大众心态等美国社会一直以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都集中在影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与系列纪录片的差异
其实,多集纪录片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的纪录片领域不仅不鲜见,而且已逐渐成为电视纪录片的主要形式。仅以国内纪录片来看,近年来诸多取得收视佳绩、引起社会热议的现象级纪录片几乎无一不是多集式的纪录片。但这些传统的多集纪录片几乎都是系列片,每集单独成篇,集与集之间完全或相对独立。而近来新出现的纪录剧集则类似电视连续剧,每集不单独成篇,叙事、情节、人物连贯,整部纪录剧集以完整的结构讲述一个事件、人物或主题。
如果将二者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传统的系列纪录片在结构上一般更为丰富和多样。全片的主题通常会分解为若干个单元主题,分解的原则根据题材的类别不同而有所区别。如自然类纪录片大多按照地域、动植物种类、生命阶段等进行分解,社会和人文类纪录片则大多以全片主题的不同侧面和层次来进行分解。每集的单元主题又依据篇幅的长短通过3-5个相关故事和人物的穿插讲述来实现。以《舌尖上的中国2》为例,全片共7集,编导者将“舌尖上的中国”中“中国美食与美食背后的中国人”这一主题分解成了时节、脚步、心传、秘境、家常、相逢、三餐等七个单元主题,涵盖了中国美食的地域差别、千年传承、碰撞转化,以及背后的日常生活、聚散离合与情感文化传统。在每一集中,例如,《舌尖上的中国2》的第二集“脚步”,又以不同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甘肃山丹牧场的老谭夫妇正准备向下一站进发,宁夏固原的回乡麦客们开始收割自家的麦子,东海的渔民夫妻则满载着对收获的期盼出海,共同阐述着本集的单元主题:无论身处中国的哪个角落,无论他们的脚步怎样匆忙,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提醒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参见《舌尖上的中国2》,官方网站http://shejian2.cntv.cn/。
相对而言,传统的系列记录片人物和故事更多,但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讲述的深度往往不够,对于单集主题的表现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每集内不同人物和故事之间的相互呼应与对比实现,每个单元主题之间的相互勾连再共同完成全片的总题旨。仍以上文提到的《舌尖上的中国2》为例,在第二集“脚步”里,若干个故事交错叙述,但片中无论对老谭夫妇、麦客们还是渔民夫妻的关注,包括他们的生活以及与美食的联系,几乎都只停留在表面,也就是对几个日常生活场景和食物料理过程的记录,缺乏对故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对主题的提炼则依靠大量的解说词。而纪录剧集则与电视连续剧相类似,全片动机唯一,事件相对集中,叙事与人物塑造基本围绕影片主要事件和动机展开。这一巨大区别使得纪录剧集无论在题材选择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呈现出不同于系列纪录片的独特之处,也决定了它能够成为纪录片新的体裁和载体。
二、纪录剧集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上的特点
从2015年至今,世界纪录片界接连涌现出了前文提到过的三部纪录剧集佳作。以此为观照对象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纪录剧集的创作在题材选择、主要风格和艺术表现等方面都显现出了非常鲜明的特征。总体来说,在题材选择上大多以谜案、事件追踪为主;风格选择体现为以戏剧型纪录风格为主;在艺术表现上,不局限于事件和人物本身的历史性叙事思维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一)题材选择
不知是否巧合,目前纪录剧集的几部重要作品的题材几乎都是对广受关注又悬而未决的谜案或重大事件的深入调查和追踪。创作者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有力地说明了纪录剧集这一载体极其适合于表现时间跨度较大、涉及人物和资料较多的重大事件。一方面,与常规的纪录电影相比,纪录剧集巨大的体量能够保证创作者有充足的空间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深入挖掘。“辛普森杀妻案”作为对美国乃至世界司法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现象级案件,已经多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但《辛普森:美国制造》一片的主创者并没有将视线仅仅局限于案件本身,而是在采用档案资料、采访、媒体观点展示等多种记录手法对案件进行全景式展现的同时,用更多的篇幅讲述了辛普森从少年时期到最终入狱的几乎整个人生。队友、儿时玩伴、教练、经纪人、成名后的富豪朋友等,从这些形形色色于不同阶段围绕在辛普森身边的人的回忆中,编导拼凑出了一个不同于公众面前的辛普森,也描绘出了辛普森从名不见经传的黑人少年如何演变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全过程。除此以外,影片编导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州种族问题的进化史,来自当地居民、政府、警方、宗教团体、种族双方的大量采访不仅为影片营造了浓厚的理性思考的氛围,也解释了辛普森成长轨迹的必然性,更为辛普森杀妻案的离奇发展提供了合理的环境因素。显然,上述这些都需要足够的影片时长,如果以常规纪录电影的篇幅,如此具有史诗性的叙事将很难完成。
另一方面,与系列纪录片相比,纪录剧集在表现需要层层递进的追问型或调查性题材上无疑更有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叙事逻辑的连贯性上。一般来说,系列纪录片大多采用横向的叙事逻辑,即将一个主题分解成并列的若干侧面。与此不同的是,纪录剧集采用的多数是纵向的叙事逻辑,即按照事件发展或调查进展的不断深入而层层推进。《纽约灾星》的叙述从2001年在加尔维斯顿发现被肢解的莫里斯·布莱克以及警方如何锁定重大嫌疑人——乔装成聋哑老妇多萝西·吉内尔的罗伯特·杜斯特开始,随着案情的进展,杜斯特的身份被揭露。随之,影片叙事转向他显赫的家庭背景,童年经历和与他有着紧密联系的另外两起案件——他前妻的失踪案和好友的谋杀案,各种迹象都显示杜斯特是这两起案件的最大嫌疑人,但却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至此,影片叙事再次回到2001年加尔维斯顿的杀人分尸案,通过法庭录像、控辩双方相关人员的采访和各种资料展示,向观众讲述了富豪杜斯特如何借助著名大律师的帮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顺利脱罪的过程。这时的影片主创已经随着采访的展开逐渐由客观的记录者转变为真相的调查者,并最终意外地探得了事实的真相。在上述影片叙事的全过程中,制片人对主人公杜斯特的两次访问一直穿插其中,不仅是全片的叙事线索之一,第二次采访更成为了影片的高潮。显而易见,《纽约灾星》题材对叙事连贯性的要求决定了它只能采用纪录剧集,而不能采用系列纪录片的载体形式,这也是该片出色的戏剧性效果的主要成因之一。同样,如果《辛普森:美国制造》采取系列纪录片的形式,将始终交织的两条叙事线索切断,分解为辛普森的成长经历、案件过程、辛普森的结局、加州种族问题等环节作为单元主题分别叙述,则极易消解掉两条线索之间个人成长与社会、历史的关联,从而对全片的整体性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主要风格
从纪录剧集目前出现的这三部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来看,相较于常规纪录电影经常采用的揭露与批判风格和系列纪录片常采用的知识/风俗/风光展示的风格,纪录剧集则更适合营造具有高度戏剧性的影片风格。当然,这主要是由纪录剧集容量大的特点决定的。在这一点上,纪录剧集有着与电视连续剧类似的特点。如今,在常规纪录电影的创作中,戏剧性也是创作者们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事件讲述或主题表达时大多采取多人物、多线索交叉叙事的策略,即便是人物传记类的纪录片,创作者也会尽量挖掘主人公的不同侧面,讲述其与各色人等的交集和其中的矛盾点,从而使影片的戏剧张力最大化。但受到篇幅的限制,无论是纪录电影还是系列纪录片,都不可能将诸多人物、事件进行详细的记录和展示,于是在大多数此类纪录片中,创作者一般会采用以观点的矛盾性为中心,将一定数量人物的简要故事进行拼贴,通过剪辑实现提升戏剧张力的目的。以世界纪录片领域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迈克·摩尔揭露美国医疗保险体系黑幕的纪录片《医疗内幕》为例,在113分钟的片长里,从没有医保自己缝合伤口的流浪汉、因为太胖或太瘦被拒绝投保的公民、前保险公司业务受理的审核员、无法在美国获得医疗保障而被迫到加拿大治疗的癌症患者,到因无法得到妥善的医疗救治而穷困潦倒的911英雄们,导演以简单讲述和大量拼贴的方法使用了超过15个人物或群体的故事,用来佐证其观点,一步步揭露出美国医疗保险企业与政客勾结的黑幕,使影片达到戏剧高潮。而在体量充足的纪录剧集中,以《纽约灾星》为例,创作者有足够的空间细致挖掘主人公及相关人物和事件的各种细节,在细节的堆叠中使叙事向戏剧性走向发展。6集、每集50分钟左右的影片长度,基本相当于一部英美迷你连续剧的容量,于是主创们能够以主人公专访、大量相关人士的采访、资料展示和场景重现等手法详细地向观众展现主人公罗伯特·杜斯特涉嫌的三起案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不同说法中透露出的矛盾和疑点。同时,6集的篇幅使创作者能从容地按照电视连续剧的方式在每集内都设置多个阶段性悬念,如第一集中海边分尸案疑凶如何确定、轻松支付25万担保金的杜斯特究竟是何许人、弃保潜逃的杜斯特如何被缉拿归案?而随之杜斯特母亲自杀、前妻失踪时究竟有没有离开他们度假的小屋到达纽约、密友波曼被杀时杜斯特到底在哪里、给洛杉矶警方寄去“尸体”字条的人是谁、杜斯特寄给波曼的信与“尸体”字条的笔迹是否一致、多次撒谎推迟采访时间的杜斯特最终是否会接受第二次采访、面对笔迹一致的两封信他将作何解释等悬念的不断设置与揭开,叙事也随之呈现出曲折离奇、高潮迭起的效果,直到杜斯特在洗手间承认罪行的自言自语被仍在工作的无线麦克风记录下来,至此剧情发展的最后一个悬念被揭开,影片也在剧情的峰回路转中达到最高潮。
(三)艺术表现
纪录剧集体量上的优势和连续性的特点使人物形象塑造成为这一体裁在纪录片的艺术表现上呈现出的最大特征。除人物传记类纪录片以外,在大多数纪录片观点先行的叙事策略之下,人物及其身上的故事基本都是为说明观点而服务的。人物形象是否立体、鲜明并不重要。换句话说,这些纪录片既没有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也没有过多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和空间。与之恰恰相反,与电视连续剧类似的体量和结构使纪录剧集不仅需要在影片中完成既定的纪录主题,也需要在叙事的过程中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充分的人物描写的篇幅则给人物塑造提供了可能。在《辛普森:美国制造》里,随着叙事的展开,影片用大量的细节给我们描绘出了辛普森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形象:大学橄榄球新星时期,在儿时伙伴、队友和教练的回忆中,在与拳王阿里和黑人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对比下,辛普森的形象呈现为一个不关心种族和社会纷争,极其在意个人前途,只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抹去肤色差异,对人友善的上进青年;在声名鼎盛的时候,搬进几乎全是白人的富人区,结交白人名流,此时辛普森的形象呈现为一个被美国主流社会和白人精英阶层完全接纳的英雄形象,但是其白人精英好友对其高尔夫球品的叙述也为观众揭示了在这一完美形象背后,辛普森好胜甚至无赖的性格另一面,这也为之后其形象的转变埋下了伏笔;数次家暴历史被曝光直至杀妻案发生之后,辛普森性格中的两面性被揭露,其形象也从国民英雄沦落成为脱罪不择手段、善于表演的无耻之徒;而最后他因绑架和抢劫被捕,其形象已经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可以说,在诸多讲述辛普森案件的影视作品中,这部纪录片在塑造辛普森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上是最为全面和立体的。不仅如此,该片在塑造人物上的成功还体现在,除了辛普森之外,影片还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普通人形象,其中有辛普森曾经的好友、凭良心上庭指证他而被称作“叛徒”的黑人警察西普,有在杀妻案审理中被辛普森的“梦之队”律师团塑造成极端种族分子的白人警察福尔曼,也有被种族矛盾和仇恨裹挟的黑人陪审员。特别是对西普的描写,影片花费了相当的笔墨。当西普叙述他心理转变的动机时,提到了他第一次处理命案时见到的第一位受害者——一个19岁的女孩,被人虐打致死弃尸停车场。主创并没有因为这一情节与辛普森案件无关而将其舍弃,正是这个细节,将西普内心的正义感和善良表露无遗,不仅佐证了他最终选择了站在正义一边而不是为明星老友开脱的心理基础,更让观众看到了全片几乎最动人的一幕。
同样,在《纽约灾星》里,对主人公罗伯特·杜斯特出身豪门,外表斯文、内心冷酷狡猾的形象塑造也贯穿整部纪录剧集,成为该片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我们能明显看出,《纽约灾星》的主创在人物塑造方面是有着明确构想的:一方面,在结构的构建上,将对杜斯特的采访穿插于全片故事的讲述中,多次采用旁证与自述相对照的手法,镜头细腻地观察着主人公的表情和身体语言,特别是在影片结尾处,主创在前期已经采访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情况下再次采访杜斯特,当制片人抛出关键证据之后,杜斯特面无表情地捂脸,同时用仿佛事不关己的冷静口吻评价着这一证物将对自己非常不利。他的所有举动都被镜头完完全全捕捉下来,而他性格中冷静甚至冷漠的特质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在主人公形象的勾勒方面,主创们多次采用对比的手法,比如使用中近景的肖像画式构图对杜斯特的形象进行白描,并将镜头里清瘦、安静、满头白发的杜斯特形象与恐怖的案情并置在一起;或者跟着主人公到他弟弟家门口转悠,把镜头里穿着普通、徘徊在豪宅门外的落魄老人与其弟道格拉斯·杜斯特申请禁制令、聘请保镖以防被兄长伤害的采访放在一起,使观众似乎也能从主人公不起眼的外表下感受到一丝暴力和邪恶。
我们可以预见,在纪录片界,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必将成为纪录剧集这一载体区别于以往纪录片体裁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将成为未来判断纪录剧集好坏的最主要标准之一。
除了人物塑造和前文提到的戏剧化叙事之外,不局限于事件和人物本身的历史性叙事也是纪录剧集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个优势。这一点在《辛普森:美国制造》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前文所述,辛普森的个人经历和美国加州种族冲突发展这两条线索交叉讲述是这种历史性叙事得以实现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段,而在大量的个体讲述的细节中不断加入种族冲突大环境的描写则起到了强化叙事的历史感的作用。例如,当被问到“对1968年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时,辛普森当时的大学橄榄球队教练的回答是“我们带领球队夺冠,辛普森一战成名”那个瞬间,而此时主创者适时地切入了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马丁·路德·金遇刺、越战、黑人运动员发起抵制墨西哥奥运会等更加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画面,在极具讽刺性的强烈对比中不仅强化了影片的历史感,也加强了叙事的戏剧性。
而在常规纪录电影中,为了突出主题观点,创作者大多选择集中笔墨对相关的事件和观点进行阐述,涉及历史发展的部分多数采用简明陈述的方式来完成,如揭露现代企业本质的纪录片《大企业》里以画外音讲述的手法对企业发展历史的说明,或迈克·摩尔批判美国枪支问题的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中用动画的手法对美国历史的简要回顾。以往,在表现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事件或主题时,系列纪录片是创作者最常选择的载体,一方面其体量能够满足历史性内容的需要,另一方面,创作者也可以将需表现的内容按照时间、地域等因素进行拆分,从而使叙事变得相对简单。与纪录剧集相比,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常规纪录电影的突出事件和主题,还是系列纪录片的拆分式叙事,都或多或少地牺牲了对历史的整体观照或历史/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纪录剧集这种新的体裁更能够营造历史氛围和史诗感。
三、结 语
纪录剧集作为纪录片内容与电视连续剧形式结合形成的新产物,目前出现的作品还相对较少,题材也不够丰富,但从它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等方面的特点来看,这一新的纪录片体裁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同时,也应看到,纪录剧集将更适合于表现具有较长时间和地域跨度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是需要深入挖掘和追踪的复杂事件。从受众目标群体来看,这种题材对有一定深入思考能力和需求的人群,如高级知识阶层,将更有吸引力,而题材和体裁的局限性无疑会限制其在纪录片市场的发展。因此,对于纪录剧集未来的发展,还需要业界和学术界密切关注,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华晓红]
王培,女,讲师,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 电影电视学院,上海,200040)
J952
A
1008-6552(2017)05-00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