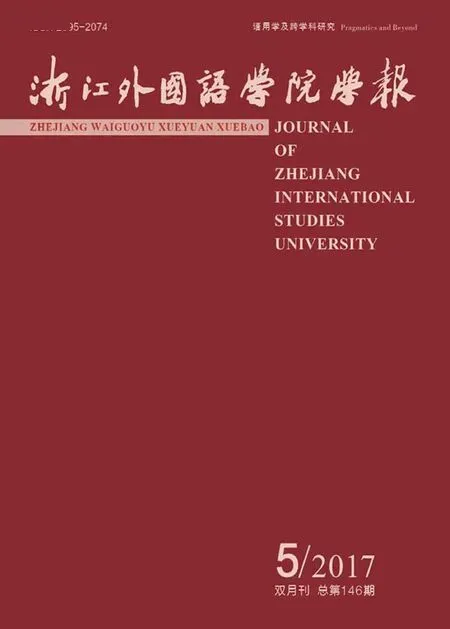安全与自由之间:《数字城堡》中的他治秩序与伦理选择
束少军
(衢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安全与自由之间:《数字城堡》中的他治秩序与伦理选择
束少军
(衢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数字城堡》中,丹·布朗以万能解密机的使用权限为切口,书写网络时代中弥漫的监视焦虑。两种“现实需要”使国安局对电子邮件的监视得以合法化,同时又带来一种他治秩序。布朗以这一秩序为轴心转动安全与自由间的伦理选择,揭橥由此引发的两种道德悬置及其背后根由。在分陈两种各异的选择时,布朗有意点明暗藏其中的悖论,以突显安全与自由间既抵牾又互补的辩证关系。这表明监视焦虑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彼此倾轧直至一方完胜另一方,而是妥善地在二者间寻建一个平衡点。
监视;安全与自由;他治;伦理选择;道德悬置
一、引言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使安全与自由这一伦理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同时也重燃大众阅读与此相关小说的热情,《数字城堡》(DigitalFortress,1998)就是其中之一。某种程度上说,该小说可视为对十多年后斯诺登事件的超前摹写,因为其核心情节直指网络空间中美国国安局无所不在的监视及对此的曝光行为。该小说是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1964—)的处女作,“虽然比之其后的小说稍显青涩,但其重要地位却是不可取代的”[1]300。除呼应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雅俗合流之势外,它也确立了布朗在审视与反思当下社会热点问题时所持的“矛盾的但又温和中庸的伦理观”[2]42。小说在围绕万能解密机使用权限上的选择与冲突展开叙事的同时,也极力书写监视引发的二元难题。一方面,该机器由于能及时破解任何加密的电子邮件而有效地打击了电子恐怖主义,大众的安全因此得以维护;另一方面,该机器不加区分地对所有电子邮件实施拦截与破译,这实际上抹杀了大众一心谋求的隐私自由权。尽管布朗最初的创作动机源于对政府秘密监视公民一事的愤慨,但与乔治·奥威尔以“绝望的心态写出《1984》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3]71有所不同,他没有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悲观窠臼。小说中,他聚焦监视背后的权力建构,在揭示技术与知识共谋下的他治秩序之余,又理性地分陈与之相关的两种伦理选择和由此而引发的道德悬置现象。故而,虽同是书写权力机构无处不在的监视,布朗更侧重引导读者关注与体验两种选择中蕴含的悖论与焦虑,重审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非简单地对政府监视这一道德灰色地带作出非此即彼的论断和控诉。
二、“现实需要”:技术与知识共谋下的他治秩序
关照现实伦理问题一直是布朗创作的焦点之一,其六部小说都“一以贯之地对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深切的伦理关怀和深层的伦理思考”[2]38,《数字城堡》就是其中的典型。布朗的传记作者莉萨·罗格克指出,《数字城堡》的创作完全源于布朗对现实生活中一次偶发伦理事件的反思。在埃克塞特学院里,一名学生由于用学校电脑给朋友发送邮件而被两名来自情报局的特工带走。事后查明,这名学生原来对美国政局大感不满,在邮件里宣称恨不得马上干掉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与斯诺登事件让公众“如梦初醒”一样,学生被捕一事使布朗感到既意外又愤怒:“美国政府竟然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公民的一举一动,像手机、电话、电子邮件这样随处可见的日常通讯交流都被他们尽收眼底,而且一切还在悄然进行。”[4]64与校园中其他人将此事渐渐淡忘不同,布朗继续探究监视实施细则及其背后权力关系的博弈,这最终构成《数字城堡》的主要伦理结之一。小说中,万能解密机是国安局开展监视的关键所在,其发明被视为“现实需要的产物”[5]16。随着电子邮件广泛采用公钥加密法,国安局先前的人工解密法陷入困境,因为“正确地猜出一个万能钥匙就相当于从三英里长的沙滩上找寻一粒正确的沙子”[5]17。由此可见,“现实需要”完全是一种技术上的需要。然而,当国安局宣布他们可以绕开司法部门而无限制地使用该机器时,“现实需要”的另一维度,即伦理上的“需要”便浮出水面:大众“失去了信仰……变得多疑起来”[5]191。可以说,在使监视变得必要之余,两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国安局进行权力建构的修辞工具。在它们的合力下,国安局实施监视所面临的技术与伦理难题迎刃而解,同时国安局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权力。最终,在以“维护国家安全”这一理性规则的名义下,国安局建构起剥夺大众道德能力的他治秩序。
在对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的考据中,福柯发现“权力的行使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6]216。“圆形监狱”是一种中间设有中心瞭望塔、四周由相互隔离的小囚室组成的圆形建筑,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操纵和存心重组作为社会关系(即上述的权力关系)的空间透明性”[7]32:一方面,处于囚室被监禁的人只能被看而他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另一方面,处于瞭望塔内的人则可以自由地观看而他自己却不被看到。这种机制分解了观看/被看的二元统一,由此“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6]226。在以后工业社会为背景的《数字城堡》中,尽管建筑、身体及光线等物理配置早已被电子设备所取代,监视也更为隐蔽,但权力运作的方式依旧建立在观看/被看的分割基础之上。万能解密机本身不是监视工具,但却发挥着与中心瞭望塔相似的功能。它由三百万台中央处理机组成,能在几分钟之内将任何拦截的加密信息转换成完全可读的明码文件。这样,网络空间中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被它完全消解,“全景敞视”也得以真正实现。在促成被监视者可见性的同时,国安局又极力掩盖其监视者身份的可见性。当万能解密机测试成功后,副局长斯特拉斯莫尔立刻向外界宣布研发失败。为了让大众更加相信他们在破解邮件密码上无能为力,国安局还四处游说国会否决所有电脑加密软件的通过。最终,国安局“可以阅读任何人的邮件然后再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之封上了事,就像是在世界上每部电话机里都装上窃听器”[5]28。从而这种监视机制不仅成功解决了国安局先前面临的监视危机,而且还带来一种权力,因为权力内在于这种监视机制,即“任何一个主体,只要利用这个机制,都可以产生权力效应”[8]201。
本质而言,监视“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技术问题”[9]10。万能解密机只是解决了监视技术层面上的难题,并未触及由此引发的道德争议与诟病等社会问题。“围绕密码技术的讽刺之处在于,政府出于追捕犯罪分子的目的而提出的措施,更有可能影响普通人而不是犯罪分子”[10]131,这也是小说中作为公民社会代表的电新会一直将国安局视为“自希特勒以来对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5]80的根源所在。因此,为弥补技术层面上的“现实需要”带来的安全悖论,也为使权力的运作更易被接受,国安局不得不生产另一种“现实需要”,即关于大众道德感知能力的知识。国安局对外否认该机器的存在并封锁一切解密信息,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忍受不了消息走漏之后造成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5]30。在这种“关怀”的背后,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式不信任隐约可见:大众是缺乏判断力与承受力的非理性群体。斯特拉斯莫尔直接无视大众道德能力,并不无骄傲地对苏珊说:“这个世界总有一些天真的人,他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我们介入的话,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恐怖事件。我一直认为将他们从无知中拯救出来是我们的责任。”[5]191由于权力与知识彼此勾连,即“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6]29,那么大众是道德群氓这一知识,就一方面使国安局和大众间的关系演变成少数精英与多数无知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国安局自此成为道德权威;另一方面,使践踏人权演变成国安局对大众的一种关怀,监视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关系被进一步合法化。这样,在对大众道德能力进行想象性阉割的过程中,监视成为一种“拯救”而非侵害自由的行为,监视者的权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彰显。
在技术与知识的双重支持下,监视得以无孔不入且堂而皇之地进行,一种绝对的公共因而获得保障。随之而来的,是这一过程中衍生出的以国安局为道德权威的他治秩序。齐格蒙特·鲍曼认为,道德上的他治指的是“由于国家对伦理标准的掌控,现代个体做道德决定的权利被剥夺了”[11]306。在国安局外部,在生产大众道德知识时,国安局主观上就已取消大众做道德决定的权利。而在国安局内部,其宗旨“保护美国政府通信系统,拦截别国情报机密”[5]12业已成为一种伦理标准,规训其成员在具体微观的工作事务中的道德决定权,由此引发以苏珊与远诚友加为代表的两种对待此秩序不同的伦理选择与冲突。
三、“分辨好坏”:道德主体的臣服与道德冷漠的生产
国安局对他治秩序的图谋可视为一种暴力行为,因为它威胁到了作为人类自我管理能力的自主性。当黑尔质疑监视合理性时,苏珊反驳道:“网络里有很多好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掺杂其中。必须要有人接近所有的东西,分辨好坏。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职责。”[5]101“我们”代替大众“分辨好坏”,一方面表明苏珊认同了国安局的“现实需要”逻辑,继而以大众道德监管人身份自居;另一方面,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威胁甚至否定了大众的道德自主性,因为“在建立道德要求和认识道德要求时,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权威……道德要求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理性对自己提出和施加的要求”[12]373。相比于黑尔,智商高达170的苏珊并不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然而,在服从或抵抗暴行的伦理选择中,苏珊却显然没有黑尔那样“明智”:她有悖常理地主动臣服于国安局的“正常的工作秩序”[5]100,即他治秩序,继而成为暴行的坚定执行者。这种悖论选择的根源可追至国安局的科层制管理体系。科层制发展得越成熟越“非人性化”,也就“越成功地从职务中排除掉包括爱恨在内的一切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超出计算的感情因素”[13]216。可以说,国安局“非人性化”的科层制产生了道德冷漠,悬置了苏珊等精英分子本该有的“分辨好坏”及抵抗暴力的能力,最终促使理性之人作出非理性之选择。
尽管国安局被外界称为“神秘迷宫”,但其错综复杂的科层体系主要体现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整个部门被横向切割成若干个单位,而每个单位又纵向地被划分成等级鲜明的上下级关系。横向上看,这种劳动分工使监视的流程无异于工厂的生产流水线——每个人都参与了产品的生产,但绝大部分人都不与终端产品见面。监视的流水作业“不仅导致责任分散,也减少了做决定的次数,限制了决定的范围……每一级只需要做出操作性的决定,考虑道德寓意的希望与可能性被大大降低”[14]47。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中面对的只是一些数据、材料与机器等,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些数字是否准确、材料是否属实及机器是否运转正常,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数据、材料及机器背后有什么样的道德指涉。以系统安全部门的技术员查特鲁基恩为例,他根本不会考虑其工作会给大众带来什么影响,他所关心的只是用他的“技术、训练和直觉来保护国安局这个上百亿美元的资产”[5]65。即使有些员工对监视的可能结果有所体悟,但也不会劳心费力地对此进行深究。当黑尔质疑监视的合法性时,苏珊则认为:“这个组织的创建只有一个目的——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这可能需要时不时地摇摇几棵树,找一找烂掉的苹果。”[5]101苏珊显然明白监视的副作用,但由于其职责仅限于破译万能解密机解开的“乱码”信息,她根本不会有黑尔那样的监视焦虑。这样,由于细致的功能划分与任务分离带来的距离感,国安局中大多数人克服了动物性的同情本能。他们坦然地在办公室里进行情报收集及系统维护等看似与监视无关的工作,却浑然不知自己已直接参与监视暴行了。即使知道了,正如苏珊那样,他们也不会真正地谴责自己。
横向上的分工实际上拉开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淡化了前者对后者的道德关怀,钝化了但并没有抹杀个体的道德良知。与横向相比,纵向上容易产生的道德权威化则真正悬置了个体的道德感知能力。在道德权威化的伦理情境下,道德语言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15]210由此,对上级命令的服从与执行取代了对命令后果的道德判断,上级便成为下级的道德代理人,其结果是“个体不再认为自我该对其行为负责,而是将自我定义为执行他人愿望的工具”[16]134。在国安局上下级权力体系中,由于“特别关注国安局在难以抉择时面临的道德困境,做事始终不渝地从大局出发”[5]20,副局长实际上成为发号施令的最高领导及道德权威。当工作中遭遇挫折时,苏珊总会想起他的权威形象:“他高风亮节地将重任独揽,从容应对,面对困难时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5]92“重任独揽”意味着苏珊在潜意识中早已把国安局中一切行动,尤其是与监视相关的工作,视为副局长一人裁决之事,而她只不过是执行副局长愿望的工具。副局长“从大局出发”的工作理念及“冷静的头脑”让苏珊一类的下级“从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衡量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将这种忧虑留给命令他去行动的那些人去思考”[15]30。这种悬置在解锁“数字城堡”上体现得尤为显著。起初,当副局长命令苏珊潜入黑尔的电脑找寻密码时,“解锁的恐惧现在又向她袭来。未来的命运令她感到一阵不安”[5]168。然而,当副局长告之改造“数字城堡”的计划后,先前的“恐惧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5]193。她不再思考解锁会置国安局及大众于何种伦理情境或困境,而是将此焦虑悬置并让渡于权威去考虑。故而,纵向上的上下级关系使苏珊的道德关怀“获得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焦点:下级按照完成权威下达任务的程度而感到羞愧或骄傲”[16]146。至此,个体本该有的道德自主性因遭到完全的悬置而罄尽。
苏珊在权威面前主动割让其道德自主性,这既承认并维护了国安局谋求的以其自身为权威的他治秩序,又容易导致道德冷漠的产生。这种冷漠窒息了苏珊等人判断是非的自由,使国安局上下“万众一心地”从事监视工作,进而确保安全的有效落实。然而,没有自由的安全终将是不安全的。一方面,道德冷漠很有可能使国安局追求的绝对安全转变为极权主义。届时,大众犹如监狱中的犯人,安全成为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招致了电新会对国安局的攻讦,进而给国安局苦心经营的安全埋下不安全的隐患。另一方面,在国安局内部,当查特鲁基恩认为有病毒文件入侵万能解密机时,由于将道德关怀限于分内之事及上级的命令,丧失判断自由的苏珊等人根本没有把他的说法放在心上,以至于错失抢救作为安全表征的万能解密机的良机,最后只能任之自毁。因此,离开了自由,安全势必因独木难支而偃旗息鼓。
四、“谁来监视这些监视者”:陌生人的质疑与网络无政府主义的肇端
与J. K. 罗琳及斯蒂芬·金等同时代的畅销书作家相比,布朗“更侧重于从后现代伦理语境下再现伦理的宏大叙事消解后,人们所面对的选择自由与不确定”[17]53。质疑可被视为后现代伦理境况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对任何宣布为绝对可靠的东西都表示怀疑”[18]24。这种怀疑腔调已成为布朗创作的惯有姿态。他将兰登系列小说的主角——罗伯特·兰登视为“自己的影子”,其身上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敢于质疑一切文化、宗教和历史上的权威观点。在其成名作《达·芬奇密码》中,布朗就借兰登之口质疑并颠覆了男权主导下的基督教文化。回顾处女作,虽无兰登式的人物,但却有相似的质疑之声。面对国安局的霸权规训,与苏珊的臣服不同,远诚友加及黑尔则似看穿了其政治权谋。他们的口号“谁来监视这些监视者呢”[5]101旗帜鲜明地表明其立场与态度。可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体现了与苏珊正好相反的道德悬置。在对监视进行道德判断时,他们选择悬置权威的力量。为何同在科层制体系之中,他们却作出与苏珊截然不同的选择?这种以追求自由为己任的道德自治是否为个体带来了真正的自由?
“几乎所有的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9]21,我们就可从身份入手推导其选择根由。某种程度上说,远诚友加与黑尔可视为国安局内的“陌生人”。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层面上的陌生人体现为接近与距离的对立统一:“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20]342陌生人来到一个地方后,会与当地人产生某种社会互动,且往往会被吸纳到当地的群体中去。但是,与当地人内部之间血缘与价值观等更为有机的联系相比,由于陌生人身上携带着不属于这个地方的特性,他们和当地人之间仅存在一般特性上的共同点如国籍、生理特性等。这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含糊身份状态在远诚友加及黑尔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前者的日裔身份及畸形的外表使他始终处于国安局的边缘位置,后者则是由于揭发国安局监视丑闻而被国安局半路招安。由于其国安局程序员身份中陌生性的存在,他们不像苏珊一样臣服于权威,而是敢于质疑,乃至否定权威。国安局一直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实施严密有序的监视,但认同了远诚友加理念的黑尔对此嗤之以鼻。他对苏珊说:“你以为政府会为人民着想啊?好吧!那如果以后的政府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怎么办?……如果总统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信件,老百姓还怎么对抗这样极权的国家?”[5]215-216如果说苏珊的臣服使国安局的他治秩序由自造的神话变成现实,那么,远诚友加等人的质疑则冲击了此种秩序,使之有可能走向反面——网络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追求绝对自由,反对以强制权威为基础的一切组织形式,如国家、法律及宗教等。在为人类开拓一种全新生存空间的同时,网络技术也为无政府主义的中兴提供可能,因为网络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存有天然的亲和关系。互联网的非中心性、匿名性及游戏性等现实社会难以彻底实现的特征激发了无政府主义的潜力,并形成一种全新的思潮——网络无政府主义。除秉承传统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外,它强调虚拟空间的自由独立性,倡导建立虚拟的无政府主义社区。远诚友加及黑尔对国安局监视行为的揭发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网络无政府主义。在网络交流中,加密技术不仅使大众免于政府权威的窥视,而且还构成“虚拟的无政府主义领地的围墙”[21]49。然而,万能解密机强大的破译功能让一切加密技术失效,冲垮了这堵“围墙”,从而让网络无政府主义所强调与提倡的自由成为一种假象。远诚友加发明无法破解的“数字城堡”,从而使“万能解密机成为一堆废物”[5]26。黑尔则时刻监视着副局长的一举一动,伺机暴露其鲜为人知的监视计划。虽然方法不同,但本质上他们都致力于揭穿国安局编织的自由假象。这种“补墙”行为使国安局无法像从前那样肆意地实施监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由。吊诡的是,这种为大众谋自由的行为却意外地使大众陷入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中。
小说结尾时,“数字城堡”被证明只是一种普通蠕虫病毒。而正由于副局长偏执狂般的爱国主义及其同僚们的道德冷漠,“百毒不侵”的万能解密机才会被它感染,最终因无法散热而在高温中自爆。远诚友加的“无心插柳”宣告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最终胜利。万能解密机的毁灭不仅解除了“围墙”危机,更意味着国安局他治秩序的终结。随着“数字城堡”对国安局安全过滤系统的侵蚀,国安局的数据库逐渐面临着被黑客及电新会等势力攻陷的危险,国家及个体安全在追求自由中濒临崩溃。尽管小说并没就此展开叙事,而是选择以苏珊成功解除“数字城堡”感染为结尾,但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现实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追求无秩序的自由必然招致混乱与恐怖。因此,缺乏安全作为保障的自由最终会反噬自由,使网络无政府主义追求的自由成为一句空谈。
五、结语
吉登斯认为:“现代国家的监控运作,在某些方面是公民权利的实现所不可缺少的;然而,监控的扩大又将千辛万苦赢来的权利置于威胁之下。”[22]369《数字城堡》以隐私自由这一公民权利为切口,恰如其分地呈现出当下互联网时代弥漫的监视焦虑。安全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但一味地追求安全必然导致自由的丧失,反之亦然。小说虽以他治秩序引发的安全与自由间的伦理冲突为叙事主线,但暗藏其后的是对二者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度叩问:安全与自由不能偏废一方,否则任何一方的善意初衷都会走向反面。在苏珊解码“数字城堡”时,远诚友加编写此程序的真实意图也被揭示出来。他并非想要毁掉万能解密机,而只是借此逼迫副局长向外界承认该机器的存在。只有将万能解密机的运行置于公众视野之内,监视与反监视的博弈才有可能转变为安全与自由的共赢。妥善地建构二者间的微妙平衡而非相互倾轧直至一方完全压制另一方,这或许就是布朗“矛盾中庸的”立场蕴含的道德关怀所在。
[1]朱振武. 解密丹·布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朱振武. 丹·布朗小说的伦理选择[J]. 外国文学研究,2014(5):37-45.
[3]张中载. 十年后再读《1984》——评乔治·奥威尔的《1984》[J]. 外国文学,1996(1):66-71.
[4]莉萨·罗格克. 《达·芬奇密码》背后的男人——丹·布朗传[M]. 朱振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丹·布朗. 数字城堡[M]. 朱振武,赵永健,信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7]齐格蒙特·鲍曼. 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 郭国良,徐建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汪民安. 福柯的界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Monahan T. Surveillance and Security:Technological Politics and Power in Everyday Life[M]. New York:Routledge,2006.
[10]Hamelink C. The Ethics of Cyberspace[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0.
[11]Mirchandani R. Reconstructing Zygmunt Bauman’s postmodern sociology of morality[C]//Lehmann J (ed.). Social Theory as Politics in Knowledge(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Volume 23). Bradford: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05:301-335.
[12]徐向东. 自我、他人与道德——道德哲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3]Weber M.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M]. Gerth H,Mills W,tr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14]Kelman H. 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t[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1973(29):25-61.
[15]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M]. 杨渝东,史建华,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
[16]Milgram S. Obedience to Authority[M]. New York:Harper,2009.
[17]朱振武,束少军. 丹·布朗《地狱》的伦理之思与善恶之辩[J]. 外国文学动态,2013(6):51-53.
[18]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伦理学[M]. 张成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9]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20]齐美尔. 陌生人[C]//林荣远,编译.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41-348.
[21]陶文昭. 网络无政府主义及其治理[J]. 探索,2005(1):48-51.
[22]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赵力涛,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
BetweenSecurityandFreedom:TheHeteronomousOrderandEthicalChoiceinDigitalFortress
SHUShaojun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QuzhouUniversity,Quzhou324000,China)
InDigitalFortress,Dan Brown uses the TRANSLTR as a key to represent the surveillance anxiety in the Internet Age. Supported by the double “child of necessity”,NSA’s surveillance becomes legal. Meanwhile,a kind of heteronomous order evolves. While revealing the ethical choice between security and freedom with the order as the diverging point,Brown exposes two related moral suspensions and explores reasons for its emergence. When presenting the two different choices,Brown also aims to illuminate the covert paradox to highlight the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the two,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solution of the current surveillance anxiety does not lie in conquering but constructing a proper balancing point between the two.
surveillance;security and freedom;heteronomy;ethical choice;moral suspension
I712.45
A
2095-2074(2017)05-0092-07
2017-06-09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1534274)
束少军(1988-),男,安徽合肥人,衢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