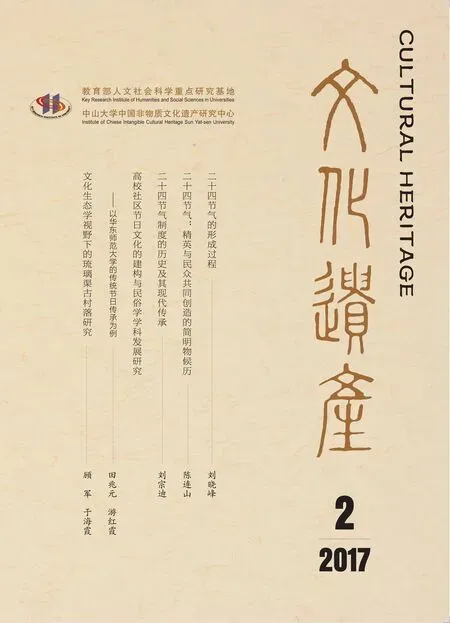《清俗纪闻》中的清代汉语与清代民俗*
李 宁
《清俗纪闻》中的清代汉语与清代民俗*
李 宁
中川忠英编著的《清俗纪闻》成书于1799年,是对当时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民间风俗、传统习惯、社会情况等的一本调查记录,是了解我国清代民俗的珍贵文献。该书记录的主要是哪些地方的民俗?书中的汉语词句反映了什么地方的方言?编者在书末所列的“清国”八人是接受调查的清朝商人还是绘制插图的画工?在这些问题上学界的认识并不清楚。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对《清俗纪闻》进行研究,通过梳理该书汉语词句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主要是语音)上的特点,指出该书所记录的清代汉语是一种具有浓厚吴语色彩的南方官话,而绝少闽语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该书关于民俗的地域性特征的记录,认为该书记载的主要是江浙一带的民俗,而不是福建的民俗。本文还指出书末“清国”八人即是实际接受调查的清朝商人,而非画工。
《清俗纪闻》 清代汉语 唐音 清代民俗
一、引言
日本江户时代宽政十一年(1799),东都书肆出版了《清俗纪闻》一书。该书是对清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民间风俗、传统习惯、社会情况等的一本调查记录。调查的主持者(同时也是该书编者)是曾担任长崎“奉行”(即地方长官)的中川忠英。据记载,该调查是由其幕下的官吏指挥长崎当地的“唐通事”(即汉语翻译官),向那些到长崎进行贸易的清朝商人询问而展开的。询问调查长达一年之久,内容十分广泛,记录颇为详尽,除文字叙述之外还命画工在清朝商人的指导、确认之下绘制了各种事物的图像,图像部分与文字叙述部分几乎各占一半的篇幅。全书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依次编为六册,共由年中行事、居家、冠服、饮食、闾学等十三卷组成。由于它是直接从清朝商人口中得知情报,又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其记录是鲜活的、原生态的,所以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民俗学价值,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们的重视。
同其他江户时代的很多出版物一样,《清俗纪闻》是用变体假名写成,对现代日本人来说识读起来十分不便。直到1966年村松一弥和孙伯醇两位先生将其转写为规范的现代日语假名*中川忠英著,村松一弥、孙伯醇编:《清俗纪闻》,东京:平凡社1966年版。,并对书中所涉事物详加考察与解说,才使得人们对它的阅读和利用更为方便。日本学者在他们的研究论著当中也开始对此书屡有提及和参考。该书引入我国的情况也颇值得一提。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本书。他在1936年就说:“日籍《清俗纪闻》……叙述中土岁时及一般礼俗,各附以图。(中略)其中所记,虽多限于江浙民俗,然颇有足供吾人考证之处。中国人士其有愿以国文译之者耶?”*钟敬文:《芸香楼文艺论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页。呼吁将其译成汉语。1983年5月台北大立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影印本,却未做出翻译。没几年,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争议的作家兼评论家舒芜看到了这个影印本,随即向中华书局推荐他的表兄方克(方威廉)翻译此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书译毕后竟拖了十多年,才于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使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到这本书的内容。译者除了方克先生之外,还多了一位孙玄龄,据舒芜说就是他的表侄、方克先生的儿子。*此处关于《清俗纪闻》中译本的成书过程的叙述,参考舒芜《清俗纪闻》,《万象》2007年第4期。2007年5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介绍了这本书,书中所展现的日本江户幕府官方的华夷观念及其对华情报搜集的精细程度,一度引发热议,进一步扩大了这本书的知名度。与此书在国内的日渐流行形成反差的是,国内学界对它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王凌的一篇书评及曲彦斌、徐晓光、高薇三位学者的研究论文。*王凌:《〈清俗纪闻〉日人眼中的清代民俗》,《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11月23日。曲彦斌:《〈清俗纪闻〉说略》,《辞书研究》2004年第6期。徐晓光:清俗纪闻探赜,《沧桑》2013年第4期。高薇:《论18世纪日本的中国观——以〈清朝探事〉〈清俗纪闻〉为中心》,《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综观前辈时贤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与本书相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还存在认识不清、甚至不一致的情况。兹举几例如下。
问题1:《清俗纪闻》记录的是我国什么地方的风俗?
这个问题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编者中川忠英在卷首的“附言”中说的已经很清楚,“今来长崎之清人,多来自江南浙江,故此处所记,亦多为江南浙江之风俗。”然而,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清俗》卷首还有三篇编者友人为他所作的“序”,其中,林衡认为是“闽浙”,黑泽惟直认为是“三吴”,中井曾弘认为是“闽浙”。中井曾弘甚至提到,“清客”(即接受调查的清朝商人)曾经私下里告诉“舌人”(即实际进行调查的翻译官,唐通事):“臣等小人,生长闽浙,其所能诵特闽浙之俗耳,名物象数亦唯闽浙矣。”如此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书中所记的风俗是“江浙”还是“闽浙”。
或许是因为一开始就认识分歧,后世学者在介绍此书时也往往游离于“江浙”和“闽浙”之间。村松一弥和孙伯醇合编的东洋文库本《清俗纪闻》(1966)在第1卷“解说”部分开宗明义,指出本书记载的是“中国乾隆时代福建、浙江、江苏地方的风俗惯行文物”,将“福建”置于浙江、江苏之前。日文版维基百科“《清俗纪闻》”词条、方克和孙玄龄的中译本以及高薇的论文,都沿用了这样的介绍。曲彦斌论文称“闽浙”,而徐晓光文则主要称“江浙”。那么,该书记载的到底主要是哪些地方的风俗呢?到底包不包括福建?如果包括,又占了多大的分量?是主要还是次要?
问题2:《清俗纪闻》卷末列出的“清国”八人是画工还是接受调查的清朝商人?
《清俗纪闻》卷末载有编者中川忠英的“跋”,他感慨“虽编辑之名在余,彼官署等力实为多矣,岂可虚其功哉?因备记与此役者姓名于卷末云”。
大通事(略)
小通事(略)
画工 石崎融思 安田素教
清国苏州 孟世涛 蒋恒 顾镇
湖州 费肇阳
杭州 王恩溥 周恒祥
嘉兴 任瑞*原书为竖排,这里改为横排。
这些参与本书调查工作的人员当中,有八人明确记载为“清国”,甚至交代了他们的籍贯,都是清一色的江浙人。但这些人到底是画工,还是接受调查的清商?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村松、曲彦斌认为是清商,而王凌、徐晓光则认为是清国画工。这也难怪,原书将“清国”列于“画工”之后,这种排列方式本身就令人无所适从。这八人中可以查考到的只有孟世涛和费肇阳两人。这两人既是商人又是画家。孟世涛,字涵九,号蓀田,多称“孟涵九”,苏州府吴县人,天明、宽政年间渡日,能诗文,擅书画,他还精通日语,会做日本和歌,《长崎名胜图绘》中载有他用日语平假名写在扇子上的和歌。费肇阳,字得天,号晴湖,又号耕霞使者等,以“费晴湖”之名行于世,湖州府苕溪人,画家,为日本江户“来舶四大家”之一,是对当时及后世的日本绘画界深有影响的人物。
问题3:《清俗纪闻》记录的汉语是什么地方的汉语?
《清俗》一书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在涉及中国事物的时候,在其词语的右侧用日语片假名标注了“唐音”,即接受调查的清商们的实际汉语发音。这些词语用片假名标注,一方面记录了它们的实际读音,另一方面也将这些词与其他用平假名标注的词语相区别,突显出它们当时实际汉语的性质,而非日语中的汉字词。那么,这些标注片假名的清代汉语词汇和句子是什么性质?或者说是反映了哪个地方的方言呢?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也不尽相同。
村松一弥、孙伯醇在《清俗纪闻1》中认为,“作为18世纪末宽政年间长崎唐通事和唐商之间的共通语,在语法和词汇层面,尽量使用官话;而在发音层面则是一种夹杂了厦门方言、福州方言和苏州方言的混合语言。”书中的大量解说和论证都强调了福建音系的重要性。然而,在《清俗纪闻2》中,他们又引用了音韵学家藤堂明保的观点。藤堂先生认为,《清俗》的标音是一种略带人工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结合了“南京杭州式官话”和“上海苏州式吴语”的特点,其声母带有吴语色彩,而韵母则酷似南京式官话,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有限度的“江南地区共通语”。这几乎是推翻了他们在《清俗纪闻1》中的观点。与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同,在2004年出版的《辞书游步》一书中,若木太一认为《清俗》的发音属于漳州语系。而方克、孙玄龄在中译本“译者前言”中指出,“此书中的对话与绝大部分的名词用语,均为清代当时南方江、浙、闽一带所用的日常官话”。
那么,《清俗》所记载的汉语词句,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官话、吴语还是闽语?无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上述三个问题都牵扯到《清俗》的地域性特征。本文拟从语言学角度切入,详细考察它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并结合书中有关民俗的记载,判断它的地域属性,回答上述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二、《清俗纪闻》所记清代汉语的语音特点
1.唐音片假名标音的整理*本文所使用的《清俗纪闻》版本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东都书肆翫月堂发兑,宽政11年(1799)。
书中的汉语词句数量十分庞大,每个字在其右侧都用片假名标有“唐音”,未标注声调。我们将这些字连同其片假名标音一起输入Excel表格,制成“《清俗纪闻》片假名标音数据库”,便于检索和分析。全书共13卷,其中卷三没有带标音的词句。根据统计,12卷中带有片假名注音的汉字共5388个。合并重复项,并排除一些异体字后,共约1300个不同的汉字。
这些汉字的片假名标音是十分复杂的。首先表现在很多汉字有多个标音。其次,记音并不十分规范,比如行文中相邻的两个词“泥墙、板墙”,两个“墙”字,前者标为浊音,后者却未加浊音符号。另外,标音有明显的错漏之处,如“花娘”一词中的“花”标作浊音バア;“火牌”标为ホーイ,“牌”字明显漏标了一部分读音。
这样繁杂的语音情况讨论起来自然十分不便,尤其是很多字多次出现,且很多字不止有一种标音。但需要指出的是,某字有多种“标音”,并不等于它有多种“读音”。不同的“标音”可能显示的是相同的“读音”。结合日语语音发展史及日汉语语音对应规律,下列几种情况中的不同“标音”应视为同一“读音”。
(1)日语长音表记方式不同,有的使用“ー”,有的使用“、”,有的则使用同一段的ア行音。但其所代表的实际读音相同。如:吕リー/リイ,武ウ、/ウー。
(2)效、流摄字有的使用隔音符号,有的未用,但其所代表的读音无别。如:教キヤウ/キヤ∘ウ,走ツヱウ/ツエ∘ウ。
(3)エヱ、イヰ、オヲ三对假名在江户时代读音各自相同。如:也ヱー/エー,归クヰ/クイ,温オン/ヲン。
(4)ハ行假名出现在其他假名之后时与ワ行音发音相同,即日语所谓“ハ行转呼音”现象。如:句キヒ/キイ,问ウヘン/ウエン,带タヒ/タイ。
(5)ザ和ヅア,ヅ和ズ,ツア和サ∘,スア和サ所代表的读音各自相同,依次为a、u、tsa、sa。
另外,江户时代日语的浊音与半浊音的表记还不成熟,表现在部分古浊音声母字绝大多数标有浊音符号,少数没有标注浊音符号;部分古清唇音声母字绝大多数标有半浊音符号,少数没有标注半浊音符号。
这样,如果排除上述“标音”不同而“读音”相同的各种情况,1300字中就有1100多字其实只有一种读音。如果再排除一些由于明显的错漏导致的“标音”不同的情况,以及由于日语吴音、汉音混入导致的“标音”不同的情况,就仅有100字左右的异读字,占全体字数的比例不到10%。而这100字左右的异读字绝大多数是由于声母清浊的不同导致的。
经过这样的整理之后,《清俗》的唐音片假名作为一个整体就显现出相当程度的内部整齐性和一致性,可以作为一个音韵系统加以讨论了。下面列举这一系统的一些显著特色。
2.唐音声母的特点
(1)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绝大多数仍读浊音(约70%),少部分读为清音(约30%)。如果考虑到江户时代日语浊点标记的非积极性(见上文),那么读浊音的比例会更高。但有些並母字标有“半浊音”(日语术语,实为清音)符号,则不应解释为浊点标记的非积极性,应理解为清音。如:“傍”字出现六次,其中四次标为バンbaN,一次标为パンpaN,一次标为ハンhaN;“箔”字出现一次,标为ポpo;“簿”字出现一次,标为プウpu-。就“傍”字而言,标为ハン的一次没有加浊点或半浊点,显然是由于标音者浊点标记的非积极性使然,因为“傍”读haN在汉语各方言中都是难以想象的。而“箔”“簿”两字读为p声母,应该理解为清音,而非浊音。
(2)有尖团之别。精组读ts系,见、溪、群、晓母字读k、h系,不论洪细。
(3)古微母读为零声母。例外只有一个“无”字,该字出现四次,其中三次读为u,一次读为mo。而读mo的这一次出现在“南无阿弥陀佛”中,属于佛教特殊读音。
(4)古匣母读为h或零声母,比例大约各占一半,另有“项狭环鬟宦”五个字读为k声母。
(5)除止摄字及少数例外,知组二等和庄组字读为ts、s等舌尖音,知组三等和章组字读为、ʃ等舌叶音。
(6)古疑母字有约一半读为零声母,少数读为n,个别字读为g或k。如“仪”字出现20次,其中十二次读i,八次读ni;“银”字出现十二次,其中十一次读in,一次读gin。
3.唐音韵母的特点
(1)有入声韵,但无p、t、k韵尾。日语是节拍式语言,区别长短音。此书的标音,古阴声韵字均标为两个音节,而古入声字则均只标一个音节,可见其入声字仍为短促的发音(喉塞音),与阴声韵字相区别。例外只有两个字,“八”字出现五次,其中四次标为短音パ,一次标为长音パア;“切”字出现一次,标为长音ツイーtsi。个别字有k韵尾,如“域”イキiki、“乐”ガクgaku,这显然是日语吴音、汉音的混入,应该排除。
(4)古山、臻摄合口三等字读为eN(或ieN)、iN韵母,没有u、y介音。如:元eN、川ieN、君kiN、雪si、出i。
(5)古蟹摄一二等字、流摄字和效摄字读为复合元音韵母。以下几个字有单元音韵母的读法,属于例外情况。如,灶tsa、爱o、代da、酒tsi、周tsu。
(6)古精知庄章组的止摄开口字,声母均为舌尖音,韵母均为u类韵母,对应汉语的韵母。例外只有一个“至”字,“至”出现三次,其中两次标为ツウtsu,一次标为ツイtsi。
三、《清俗纪闻》所记清代汉语的性质
将上述声、韵母系统与现代江、浙、闽沿海地区各汉语方言相对照,可以看出,《清俗》唐音主要体现了江淮官话(以南京官话为代表)和吴语的音韵特点。古浊塞音、塞擦音绝大多数标为浊音、匣母字标为零声母、疑母字读n等主要是吴语的特征。而部分古浊塞音、塞擦音标为清音、部分匣母字标为h声母、疑母字读零声母以及古咸深山臻摄带有鼻音韵尾、蟹摄一二等和效摄字读为复合元音等,则主要是官话的特征。古入声字读为短促的喉塞音而无p、t、k之别,微母读零声母等特点则为现代江淮官话和吴语(吴语微母白读m,文读v)所共有。而《清俗》唐音的有趣之处在于,往往一个字之内既有吴语的成分,又有官话的成分,即声母有更多的吴语成分,韵母有更多的官话成分。
江户时代有不少唐通事编写的唐音、唐话文献存世,成书年代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纪。将这些文献中的音韵特点与《清俗》唐音相比较,也可以看出《清俗》唐音的一些特点。朝冈春睡编写的《四书唐音辨》成书于1722年,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抽取2400余字,每字用片假名标注唐音,左注“浙江音”,右注“南京音”,是唐音文献中少有的注明了语音性质的文献之一。观察此书的标音,可以发现《清俗》唐音与其“浙江音”十分相似,前文所列声韵母各六个特点(除韵母特点3和4之外)二书基本一致,尤其是古精知庄章组的止摄开口字都读dz、ts、tsh、s这一特点,与“南京音”迥异。《清俗》唐音与《四书唐音辨》“浙江音”的最大不同在于,古遇摄合口三等字(除非组和庄组外)《清俗》读i韵母,而“浙江音”读iu韵母;古山、臻摄合口三等字《清俗》读为eN(或ieN)、iN韵母,而“浙江音”读iuN韵母。另外,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标为浊音的比例,《清俗》比“浙江音”少一些;古匣母标为零声母的比例,《清俗》比“浙江音”少一些。
《磨光韵镜》(1744)和《三音正讹》(1752)是江户时代著名僧人学者文雄的音韵学著作。他在《磨光韵镜》中给每个字都标注了日语汉音、日语吴音和“唐音”,并宣称其中的唐音是依据当时杭州话的读音,且是他心目中的“正音”。但他标注的唐音有很多是他个人根据古代的韵书人为“制造”出来的,比如还保留有古代的m韵尾等,受到有坂秀世的批评。谢育新(2010)*谢育新:《日本近世唐音:与十八世纪杭州话和南京官话对比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将这两本著作中的人为加工成分剔除后,认为文雄的杭州音系统与《四书唐音辨》的“浙江音”十分类似。这样,《清俗》唐音与《四书唐音辨》的“浙江音”和文雄的杭州音,除韵母特点3和4之外就十分相似了,可以认为它们都反映了杭州话的读音。张昇余和杨春宇*张昇余:《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研究》,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版。杨春宇:《社会语言学视点下的清代汉语与其他言语的对音研究——以日本近世唐音资料、满语资料、罗马字资料为中心》,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还是把这样的系统看作是是带有吴语色彩的南方官话。现在看来,这一争议还有待进一步解决。我们认为,不管将《清俗》唐音的主流表现(不含韵母特点3和4)看作是杭州音还是带有吴语色彩的南方官话,其声、韵系统中的官话因素都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的杭州话在吴语中独树一帜,有很多官话的特点,被称为吴语中的官话方言岛,这在学界也是公认的。为表述的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将《清俗》唐音看作是带有吴语色彩的官话。
韵母特点3和4,即古遇摄合口三等(除非组和庄组外)“鱼、句”等字和古山、臻摄合口三等“元、君”等字,《清俗》与“浙江音”“杭州音”不同。“浙江音”“杭州音”反映的是有撮口呼的情况,《清俗》反映的是没有撮口呼。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清俗》混入了闽语的成分。众所周知,闽语的一大音韵特色是缺少撮口呼。闽语区的人在说普通话时往往将普通话中的y读成同部位不圆唇的i。《清俗》中缺失撮口呼,也有可能是闽人在说官话时受其闽语影响而产生的现象。但我们不要忘了,吴语当中也存在缺少撮口呼的方言,如湖州话。而《清俗》卷末所列几位清人中的费肇阳正好就是湖州人。现代湖州话在古遇摄合口三等和古山、臻摄合口三等字上的表现与《清俗》基本一致,最大的不同是湖州话古遇摄合口三等在与知章组搭配时读为舌尖元音,而《清俗》读i。而这很可能是湖州话两百年来语音演变的结果。i元音与ts系塞擦音、擦音搭配时变为,在汉语史上是很常见的演变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清俗》古遇摄合口三等和古山、臻摄合口三等字中与古浊音声母搭配时仍读浊音,如“厨、拳、船、传”等字,这也是闽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
另外,江户时代的唐音、唐话材料中有几种记录了当时的通事们所说的福州音和漳州音。如《粗幼略记》(写本,作者、年代未详,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唐话辞书类集》)记录了福州音,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1708年)和篠崎东海《朝野杂记》(1716年)记录了漳州音。这些材料中,知组声母有标为t的,阳声韵有标为m尾的,入声韵有标为p、t、k尾的,与现代闽语一致。而这些特点在《清俗》中均未得到体现。
2015年11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中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将国有农场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基本完成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任务。
再来看《清俗》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清俗》是日本官吏和通事向来航长崎的清朝商人询问清朝民俗的纪实性文献,询问者关心的是与中国民俗相关的各类事物,所以书中记录的带有唐音注音的词汇主要是询问所得的相关事物的专有名词。如:上元灯、冰厂、扁豆汤、藕粉糕、龙井茶、拜匣、稳婆、内厅、火牌、金银纸、凉伞、天后圣母、关帝等等。从这些词语中,我们很难找到吴语或闽语的特征词。居家、闾学、婚礼、宾客等卷出现了较多的句子,但大多很短,都是待人接物时的寒暄语和客套话。
“东人不在,有什么贵干说把我。”(卷二居家)
“可以随时来馆上学。”(卷五闾学)
“拜望,谢谢,但不必费心。”(卷五闾学)
“请坐。”(卷八婚礼)
“各位先生少陪。”(卷八婚礼)
“好热啊。”(卷九宾客)
“主人不在家,是哪位?”(卷九宾客)
很明显,这些句子都没有什么方言色彩,而最后一句则是典型的官话表达。
综上,《清俗》汉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是官话的,在语音上除了官话成分又带有浓厚的江浙吴语特征。就像现在很多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一样,它实质上是一种江浙腔或吴语腔的官话。因此,整体上看,我们可以说,《清俗》汉语主要反映了官话和吴语的特点,是一种带有强烈吴语色彩的官话,而没有多少闽语的成分。
四、《清俗纪闻》所记风俗的地域属性
《清俗》由文字叙述部分和绘图部分组成,大约各占一半的篇幅。两部分都记录了一些地名,从这些地名可以观察它的地域属性。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在文字部分,“江南浙江”或“江浙”并称出现8次,“杭州”“福建”各出现4次,“江南”“山东”各3次,“苏州”“山西”各2次,“浙江”“江苏”“湖州”“常州”“绍兴”“松江”“徽州”“湖广”“台湾”“兴化府”等各出现1次。在绘图部分,除一幅“福建竞渡船”的插图跟福建有关外,其余均为浙江,如卷十“羁旅行李”的绘图“平湖县印照”和“浙海关商照”中录有嘉兴府、平湖县、乍浦等浙江地名。
《清俗》的体例是通事向清商询问,清商回答。书中行文显示出清商回答提问的口气,在涉及相关风俗的地域性时往往“江浙”并称或“江南浙江”并称,或先提江浙再言他处。
卷一年中行事提到过年时“某些地方亦制屠苏酒于家中饮用并以待客”,*本节引用《清俗纪闻》相关文句均出自方克、孙玄龄的中译本《清俗纪闻》,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用小字注明“江南浙江一带此风已绝迹,故其制法已不详。”显然,接受调查的人是江浙人,因为当时江浙一带已然没有制作屠苏酒自饮或待客的风俗,所以他们不知道屠苏酒的制法,只说某些地方还存有这种风俗,以应付日本通事的询问。
卷一年中行事讲到“人日”说:“据传正月初七是人类始生之日,故称人日。浙江一带于此日用秤称量体重,谓之称人。江南一带在立夏之日亦有此风俗,是谓防止夏瘦。”未提福建等其他地方。
卷二居家讲到“米价、运米”时说:“米分高下不等。江浙之米为上谷。目前运到长崎之米为湖广等地所产,称之秈米,系下谷,即早稻。与江浙之上谷价格相比,行情约低一成二分。”此处暗含将湖广等地与江浙相比之意,显示出被调查者的江浙身份。又下文提到小麦价格时说:“麦每升价钱十三四文。江浙福建山东一带均相同。”先提江浙,然后才提到福建和山东。再如“盐价”:“盐每斤约五十文钱,亦以江南浙江之产品为上等。”结合前文“江浙之米为上谷”的说法,甚至可以窥察出被调查者作为江浙人的一丝优越感。
卷二居家“来客之应对”讲到家里来客人时奴仆“到里面禀报主人某相公来到”,用小字注明“江南浙江等地称‘相公’,对用钱米买到官职之人则称某爷。福建等地称某之一官、二官。山东或徽州等地则称某朝奉。”可见被调查者是说“相公”的江浙人,但也了解福建、山东、徽州等地的一些情况。
卷五闾学讲到小孩“入学之礼法”。其中提到小孩初次与先生见面时,先生要与新生和其他同门学生共饮“和气汤”的习俗。但特别指出,“此非任何地方学馆均采用之方法,而是江南地方之习俗。”显然,此处的被调查者是江南一带的人。
另外,书中记录了的一些风俗显示出江浙色彩。如卷二居家:“概言之,灯油、炸食均用菜籽油,称为菜油,乃菜籽榨出之油。”卷四饮食制法:“烹调食物,均是酒多,酱油少。各种菜之味道均稍淡。均以小碟盛酱油。依个人口味,喜好咸者,可蘸酱油食用。一般不采用过分咸的做法,从而配方亦无固定份量,多以淡为佳。”喜食菜籽油、口味清淡,与今天江浙人的口味是吻合的。
卷四还记录了两种食品,颇具江浙特色。一为鸡豆汤,一为眉公饼。鸡豆,即芡实。乾隆年间的苏州《元和县志》(1761)载“芡,叶似荷而大,俗称鸡豆,出江田何家荡车坊及葑门外杨枝荡。”(豆、头二字在吴语中除声调外,声母、韵母皆同,发音相似;在闽语和官话则只有韵母相同。)清初的沈朝初在《忆江南·姑苏四时食品词》中说:“苏州好,葑水种鸡头,莹润每凝珠十斛,柔香偏爱乳盈瓯,细剥小庭幽。”对鸡头大加称赏。今天的苏州人依旧爱吃鸡头米,且仍以葑门所产为佳,每年中秋前后上市,人们趋之若鹜,一物难求。鸡头米现在有两种吃法,当菜吃和作羹吃。《清俗》“鸡豆汤”的吃法应属作羹吃。从制法上来看,《清俗》的制法与现代也相同,都要加糖煮沸。*此处关于苏州鸡头米的叙述,参照“无意花香的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d50e43a00101c2x8.html。眉公饼的得名源自明末松江人陈继儒。陈继儒(1558-1639),文学家、书画家,号眉公。《艮斋杂说》载,松江陈继儒(眉公)每事好制新样,人辄效法。其所坐椅称眉公椅,他所喜欢吃的饼被人称为眉公饼。沈朝初在《忆江南·姑苏四时食品词》中说:“苏州好,茶社最青幽。阳羡时壶烹绿雪,松江眉饼炙鸡油,花草满街头。”*此处关于眉公饼的论说,参照百度百科“沈朝初”词条。
事实上,《清俗》文字叙述部分只有4次提到福建。其中,两次列举在“江浙”之后,一次是“福建竞渡船”,另一次则是在讲到“天后圣母”的诞生地时提到,卷十二祭礼:天后圣母“诞生于福建兴化府湄洲”。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江户时代中日长崎贸易的历史研究也指出,18世纪中后期来往长崎的商船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商船。如孙文通过考察明末清初我国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省份在对日贸易中的地位,认为一开始郑氏家族控制闽海时期,与郑氏家族相关的商船几乎独占了对日贸易;而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拥有资源优势的江浙一带迅速崛起,对日贸易重心向北移动*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张照旭统计了1780、1789、1800、1815、1826年五艘前往长崎进行贸易的清朝商船乘员的籍贯和职务,认为“船主”“财副”等与贸易相关的人(即商人)几乎全为吴语区的江浙人,而“总官”“舵工”等与航海、运输有关的人(即水手等)几乎全为闽语区的福建人*张照旭:《明治期中国語教科書における中国語カナ表記についての研究》,冈山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清俗》中能与通事们进行对话,描述清朝风俗的只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商人阶层,而非身份卑微、不通文墨的下级水手等劳动阶层。这样,《清俗》中接受调查的商人是江浙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笔者认为,《清俗》卷末所列清国八人即是实际接受调查的清朝商人,而非画工。他们的江浙籍贯与书中带有唐音标记的汉语词句所体现的汉语方言特点是完全吻合的。孟世涛和费肇阳二人(包括但不限于)是兼具绘画才能的江浙商人,除了接受调查外,也参与了插图的绘制工作,但此二人绝非画工。正如编者中川忠英在卷首“附言”中所说,“本书绘图,系遣崎阳画师往清人旅馆据所闻而绘。绘时稍有差错,立即由清人纠正,且由清人图示者亦颇多。”可见,画工(画师)不是清朝人,而是崎阳(即长崎)人石崎融思和安田素教,他二人奉命前往清商住所根据对方的描述和通事的翻译当场绘制。而幸运的是,这些清商中竟也不乏善画之人,正好可以帮他们绘制部分图像。
五、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对《清俗纪闻》的研究,通过分析整理书中汉语词句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主要是语音)上的特点,指出该书所记录的清代汉语是一种具有强烈吴语色彩的南方官话,而无闽语的语言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书中关于民俗的地域性特征的记录,认为《清俗纪闻》一书记载的主要是江浙一带的风俗习惯,且卷末清国八人即是实际接受调查的清朝商人,而非画工。
因此,笔者建议,今后在介绍《清俗》时,应该说它记载的“主要是清朝中期江浙一带的风俗习惯”。至于福建,强烈建议不要加入。如果非要加入,也应该置于江浙之后,称“江、浙、闽”。而“福建、江苏、浙江”和“闽浙”之类的提法并不准确和严谨,有误导之嫌,应该摒弃。
前面提到,《清俗》的编者在卷首“附言”中明确指出书中记载的“多为江南浙江之风俗”,未提福建。那么,后世学者为什么又加了一个福建,且将福建置于江浙之前,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呢?
笔者认为,这一错误认识的产生,一来可能是由于做序者“闽浙”说的干扰,二来其责任主要应在1966年村松一弥和孙伯醇编著的东洋文库本《清俗纪闻》一书。该书分1、2两卷,在卷1中,编者极力论证《清俗》唐音、风俗与福建的关系,并在“解说”部分将福建提到最重要的位置。由于不熟悉汉语方言音韵的情况,他们的“论证”虽然十分“细致”,但显然是失败的。在卷2末尾,他们介绍了日本音韵学家藤堂明保先生的观点(藤堂先生对唐音的观点与本文的结论比较接近,但未进行全面详细的考察),做出了补正,但却只用了不到两页的篇幅,显然没有引起读者的足够重视,甚至可能被完全忽略掉了。
《清俗》原文用日本江户时代的变体假名书写,除非受过这方面专门的学术训练,一般读者甚至学者根本难以读懂,只能参看村松二位先生转写的现代日语版本。事实上,在现代日语版东洋文库本《清俗纪闻》两册问世之前,已有学者提到《清俗》这本书,比如有坂秀世*有坂秀世:《国語音韻史の研究》増補新版,东京:三省堂1957年版。和钟敬文。他们都称“江浙”,不提福建。而在我国,方克、孙玄龄的中译本《清俗纪闻》照搬了日本东洋文库本的“解说”,中文世界的读者以讹传讹,出现认识偏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庄初升
李宁(1985-),男,山东东平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广东 广州510275)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末以来西方人创制的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研究”(项目编号:13BYY1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项目编号:12&ZD178)的阶段性成果,其主要内容曾先后在第四届海外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年会(2014年11月,深圳)和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专题研讨会(2014年11月)上宣读,得到内田庆市、奥村佳代子、汪维辉和庄初升等前辈学者的指正,特此致谢。
G122
A
1674-0890(2017)02-129-08
——以浙江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