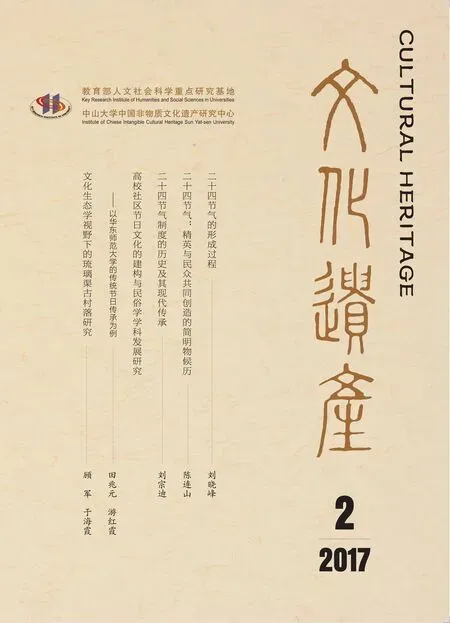手帕姊妹:明清江南地区娼妓结拜习俗研究*
崔若男
手帕姊妹:明清江南地区娼妓结拜习俗研究*
崔若男
我国下层女性间一直存在着结拜行为,这在娼妓间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分析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娼妓结拜习俗可以发现,娼妓间结拜而成的“手帕姊妹”是一种女性自发的互助行为,它有助于女性间“姐妹情谊”的形成。而娼妓间特有的习俗——“盒子会”则可以看成是娼妓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自我“展演”。娼妓是拥有能动性的“主体”,而非“他者”话语里被欣赏或被玩弄的“商品”。从娼妓主体的视角来解读其结拜习俗,有助于打破娼妓研究中“高雅”与“卑贱”的二元对立视角,也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娼妓的生活。
娼妓 女性结拜 手帕姊妹 盒子会
前言
结拜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一种很普遍的文化现象。一般来讲,现有的对于“结拜”行为的研究,其潜台词多是指向男性之间的结拜行为,“结拜”被认为是在宗族“血缘关系”之外创造的一种“拟制血亲”。*冯尔康:《拟制血亲与宗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4分册,1997年12月。通过建立“拟血亲”的关系,结拜双方将这种身份关系纳入社会认可的家庭伦常秩序之中,进而以实现某种目的,或满足某种需要。*李祥文:《结拜风俗研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事实上,梳理历史可以发现,不仅男性之间存在结拜行为,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之间的结拜也是自古至今皆有。唐代有教坊女的“香火兄弟”*“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详见(唐)崔令钦《教坊记》,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版,第159页。,宋代有娼妓的“香火姊妹”*(宋)罗烨《醉翁谈录·潘琼儿家最繁盛》:“儿家凡遇新郎君辈访蓬舍,曲中香火姊妹则必醵金来贺,此物粗足以为夜来佐樽利市之费。”参见(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版,第52页。,明代有旧院里的“手帕姊妹”,清末至民初闽、粤一带有“金兰会”*(清)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记载了广东顺德蚕女组成的“金兰会”:“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能禁也。李铁桥廉使令顺德时,素知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且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清代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中也有广州妇女结成金兰的记载,“广州女子多以结盟拜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渐染至番禺、沙茭一带,效之则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竞可终身不嫁,风气极坏矣。”(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三十四辑史部地理类第二十二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近代上海有娼妓的“十姊妹”*“十姊妹”是女性结拜组织的一种,多流行于下层社会,特别盛行在娼妓之间。上海娼妓尤其流行结拜“十姊妹”。“十姐妹”并非都是女的,而是九个妓女加一个男的,或十个妓女加一个男的,而且这个男的必定是黑社会中有势力的人物。妓女与其结拜,就是为了求得他们的一些庇护,而不至于受到嫖客的欺负,作为回报她们对结拜的兄弟是白玩不收钱。见云中鹤《黑道教父杜月笙》,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当代还有广东客家妇女的“香烟姊妹”*参见徐霄鹰,《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女性结拜里,身处社会下层的娼妓之间更易产生结拜的行为。本文拟以“手帕姊妹”为例,探讨娼妓间的结拜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社会意义。
一、“手帕姊妹”命名的深意
“手帕姊妹”的记载多源出于清人的文学创作与伤怀忆旧的笔记之中,如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有言:
这院中名妓,结为手帕姊妹,就像香火兄弟一般,每遇时节,便做盛会。……结罗帕,烟花雁行,逢令节,齐门新妆。……今日清明佳节,故此皆去赴会……赴会之日,各携一副盒儿,都是鲜物异品,有海错、江瑶、玉液浆。会期……大家比较技艺,拨琴阮,笙箫嘹亮。*(清)孔尚任:《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周亮工的《书影》卷一称:
闻古老言:南京旧院有色艺俱优者,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元节,以春檠具殽核相赛,名盒子会……今日院鞠为茂草,风流云散,菁华歇绝,稍负色艺者,皆为武人挟之去,此会不可复观矣。*(清)周亮工:《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相较于把女性结拜看作是对男性结拜行为的模仿,是对男性社会秩序的复制*诸如廖珮芸、岳永逸对“香火兄弟”的研究。详见廖珮芸《从〈教坊记〉之“香火兄弟”则探讨唐代特殊的婚姻关系与性别意义》,《东海中文学报》第22期,第27-52页;岳永逸《眼泪与欢笑:唐代教坊艺人的生活》,《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明代娼妓以“手帕姊妹”自我命名,正好提出了相反的佐证,即此种命名是娼妓作为女性的独立意识的体现。
手帕,又有手绢、丝帕、手捏子、尺素、红绡等说法。在我国,手帕是从“巾”发展而来的,它本来只是一种男女通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人们寄托相思之情、友爱之情的物件,被赋予了与女性相关的意义,成为了一种文化意象。
《礼记·内则》中:“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郑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于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也。”“帨”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女子的象征物。《仪礼·士昏礼》中:“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婚礼上,母亲会把“帨”给女儿系上,并叮咛嘱咐一番。“帨”因此也成了嫁妆的一部分,“结帨”也成为了婚礼的别称。但是,“帨”作为随身的佩物,并不是像今天的手帕一样拿在手里,而是有点类似于今天女子做家务时系在身上的“围腰”。《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郑注:“巾以帨手。”《释文》里“帨,拭手也。本作捝。”诸家注《说文》者皆以帨为做家事时妇女拭手、拭物的佩巾。《诗·召南·野有死麕》有言:“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尨”,指多毛的狗)也吠。”毛传:“帨,佩巾也。”《诗经》里的姑娘对着小伙子规劝到:“轻轻慢慢别着忙!别动围裙别鲁莽!别惹狗儿叫汪汪!”*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程俊英在这里将“帨”译为“围裙”并非没有道理的。
汉朝以后,诗文中所涉及的“巾”,实则已经分化为佩巾和头巾了。在男子多指头巾,在女子则指手巾。作为头巾的“巾”与冠、弁、帻成为男子的重要饰物之一。而作为手巾的“巾”,其用途也有所扩大。这时,已经有了专门的“手巾”的说法,而且平时流泪时也多以“手巾”揩拭。汉乐府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有“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之句,指的就是擦眼泪的手帕。
到了唐代,兴起了“手帕”的名称。以描写宫廷生活著名的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之四写道:“缏便红罗手帕子,中心细画一双蝉。”“缏”即是编织物,放在这里来讲,可以理解为“绞边”。也就是说,“手帕子”不仅有绞的花边,还有绘画刺绣。无疑这时的手帕已经可以称为装饰品或者工艺品了,它已超出了生活日用品的范围。
从“事人之佩巾”的“帨”到“拭泪”的“帕”,手帕成了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手帕的“拭泪”之用,使得“手帕”逐渐作为一种意象,与女性的情感生活紧密相连。手帕是女性的贴身之物,它既是女性的美好象征,也是寄托相思之情、友爱之情的物件。在冯梦龙收集的《山歌·桐城时兴歌》里有一首《素帕》对此描写更为直接,“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在《红楼梦》中,“手帕”更是屡屡出现,成为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信物。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中,黛玉在得知宝玉与宝钗即将成婚的事后,将曾经提过诗的旧帕不仅撕毁,还要烧掉。作为宝黛爱情见证的丝帕,也随着爱情的消亡,化为一片灰烬。
手帕,蕴含着少女情思,里面满是女儿家的眼泪与心事。因此,才有了明朝中叶以来,一些关系亲密、交往深厚的女性以“手帕”为名结为的“手帕姊妹”。相较于教坊女子以“香火兄弟”命名自己,“手帕姊妹”选取具有女性气质的“手帕”来自我命名,更凸现出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
二、“手帕姊妹”的结拜
历史上,结拜的原因有很多。一般来说,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结拜的人有着相同的志向、兴趣,或相同的相处经历,承担着共同的社会压力;二是追求功利的目的。*李祥文:《结拜风俗研究》。而对于“底边社会”*参见乔健《底边阶级与底边社会:一些概念、方法与理论的说明》,《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版,第429-439页。的人来说,他们的结拜原因主要是前者——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共同承担的社会压力,使得他们为了求得生存,或减少生活压力,而形成一种“拟血亲”的互助关系。
如唐代教坊诸女,以“气类相似”*(唐)崔令钦:《教坊记》,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第159页。,约为八九到十四五人的香火兄弟。香火兄弟之间不像那些出于政治、军事、外交等目的的暂时“苟合”,而是教坊女艺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形成的生存策略。*岳永逸:《眼泪与欢笑:唐代教坊艺人的生活》。
再如清末的上海滩妓女流行结拜“十姐妹”。所谓“十姐妹”并非都是女的,而是九个妓女加一个男的或十个妓女加一个男的,并且这个男的必须是黑社会中有势力的人物。妓女与他们结拜,就是为了求得他们的一些庇护,而不至于受到嫖客的欺负,妓女则以自己的身体回报“保护”她们的男人。闻名上海的“流氓大亨”杜月笙刚到上海时,就是靠结拜“十姐妹”,混在青楼里吃保护费起家的。*汪澄清主编:《反洗钱在行动》,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明初期,南京作为明王朝的首都,“集中了封建国家的中央军政机构及最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并集中了数量众多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官僚士绅猬集于此,从而造成了城市商业贸易发达的雄厚物质基础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同时,政府还“从江浙等地将大量富户迁入南京”,*陈忠平:《明代南京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这使得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随之而兴起的,同时还有各种服务业。娼妓就是这样的一种职业。明清时,中国的娼妓业可谓是达到了鼎盛。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官妓和私妓并盛,*《五杂俎》卷八就曾记载:“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参见(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人部四》,《续修四库全书》本。娼妓事业也以南京为中心,*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7页。秦淮河畔成了名闻天下的烟花盛地。中国几千年的娼妓史,娼妓在各种力量中浮沉起落,但其社会地位和身份却是大致没有变化的——她们始终是“法外之人”、“化外之人”、“域外之人”的非良人身份*岳永逸:《眼泪与欢笑:唐代教坊艺人的生活》。。有关娼妓的悲苦生活的研究已多不胜数,笔者在此不作赘述,但需要明确的是,娼妓间相似的悲苦经历使得娼妓间的结拜更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手帕姊妹亦如是。
一般来说,“姿貌相当、性情相契”*《记桐严妹近事》,《申报》1873年7月31日,总第386期。是娼妓们结拜的基本条件。并且,娼妓们多是与自己阶层内的人结拜。娼妓之类的下层女子若是和男子结拜,有可能成为美谈,但娼妓若是与良家女子结拜,则成了败坏风气。《浮生六记》里沈复的妻子陈芸就因为与娼妓之女憨园结拜,而被公婆驱逐:“汝妇不守闺训,结盟娼妓。汝亦不思习上,滥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宽三日限,速自为计,迟必首汝逆矣!”*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此外,结拜情谊在娼妓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娼妓们的生活不同于一般的良家女性。对于大多数良家女性来说,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有可以依靠的娘家和婆家。也就是说,她们始终处于“家”文化(宗族文化)之中,良家女性的结拜只是她们家庭生活向外的一种延伸和扩展。即便她们婚后会从夫居,离开以前的团体,但她们进入新的环境后,还是可以与夫家女性亲戚或邻居另组成新的团体。虽然有断裂,但是也可以说是进入了另一种延续的过程。*王智珉:《性别、差异与社会理想的承转与维系南势阿美的女性结拜》,济慈大学人类学研究生硕士论文,2005年,第24页。但“旧院女子”则不同,她们大多数一生都生活在妓院里,她们所处的特殊生活环境,使得她们之间更需要互相扶持,“姐妹情谊”(sisterhood)也得以长久地发挥作用。
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乏,我们没有直接的手帕姊妹关于其情谊的口述资料,但通过与其相同阶层的人的结拜情谊来看,大致是一致的。
今天南势阿美族的结拜姐妹在提到结拜情谊时就说:
结拜感情比姊妹还要深厚,兄弟姊妹结婚后有自己的家庭,关系比结拜复杂,结拜的感情很多是说不出来的,有事马上帮忙,心是凝聚在一起的。*王智珉:《性别、差异与社会理想的承转与维系南势阿美的女性结拜》,第128页。
而与娼妓同属“底边社会”*参见乔健《底边阶级与底边社会:一些概念、方法与理论的说明》,《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第429-439页。的杂技艺人、说唱艺人,他们同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相似的经历使他们也拥有相似的“情谊”。今天的天桥老艺人杜三宝在谈到自己的拜把兄弟时就如是说:
我们把兄弟好到什么程度呢?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就跟一家子亲兄弟一样,‘不能同生死也要同患难’,就是‘义气’。把兄弟好像比亲兄弟还要亲一些。自己的亲兄弟不一定在一块儿待一辈子,可把兄弟同行同业,就很有可能在一块儿待一辈子。*《同盟、联盟与口盟——杜三宝访谈录》,见岳永逸《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6页。
跟天桥艺人一样,娼妓之间的结拜,也可以说是出于业缘,即同行业内的结拜。同行业内的人朝夕相处,感情已经远胜过血缘兄弟姐妹,何况娼妓一旦进入妓院,更是几乎断绝了与血缘亲的来往,她们自是十分珍惜手帕姊妹间的“情感共同体”。
情感共同体的凝聚力十分强大,以致于能影响到团体内成员的价值观念。诸如在顺德地区的“女仔屋”,原本是一种提供少女结群的地方,但据叶汉明推断,女仔屋的存在及少女们在其中的活动,不仅强化了姐妹之间的情感,而且增加了相互影响的程度,进而使她们选择终身不婚。*叶汉明:《地方史与妇女/性别议题:一个研究案例的启示》,刘咏聪主编《性别视野中的中国历史新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因为有了“女仔屋”这样一个实体空间,女性们得以进行情感和价值的交流。但共同体的缔结不仅依托于实体空间,还可以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存在。江永女书就是这样一种由女性主体自发自觉创造的看不见的“文化空间”。女性们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交流着日常生活的种种经验,充分展现了女性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骆晓戈:《从田野考察看明清江南才女诗歌对江永女书的影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而娼妓们长期生活在“院中”这个相对独立、与主流社会生活隔绝的实体空间里,同样的生存境遇和朝夕相处的情感,不仅促成了她们通过结拜这一仪式性行为实现亲密关系,而且,娼妓们还充分发挥主体性,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如“吊柳七”、“老郎会”、“冬至酒”等*详见徐君等:《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妓女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盒子会”就是手帕姊妹间的一种特殊习俗。
三、“手帕姊妹”的特殊习俗:盒子会
除了上文《桃花扇》和《书影》记载的“盒子会”盛况之外,清代的笔记小说也描写了“仿秦淮盒子会”。通过这些文献,大略也能知晓“盒子会”一二:
清江、淮城相距三十里,为河、漕、盐三处官商荟萃之所,冶游最盛,殆千百人,分苏帮、扬帮。有湖北熊司马随官河上,甫逾冠,美丰姿,多文采,尤擅音律,丝竹诸艺,靡不冠场。家雄于资,千金一笑不吝也。一时目为璧人,羊车入市,争掷果焉。春日,群艳廿四人,仿秦淮盒子会,设于淮城之荻庄。其地水木明瑟,厅事在孤诸中,窗棂四达,绕槛皆垂杨桃杏,渺然具江湖之思。乃相聚谋曰,是日不可无善歌者侑觞,佥曰必约熊郎来。君欣然就之。挟琵琶筝笛先期往,欢讌竟日,执壶觞遍酬群艳,转喉作诸曼声,一坐为靡。临河观者数千人,皆以为神迁高会也。酒罢,各出一玩好为缠头,或珠、或玉、或披霞、或汉璧,皆人世罕有而精巧绝伦物,二十四人无一雷同者。盖皆预以重价购觅于数百里外,备此日之用,计其值殆万金,为千古未有之豪举。计熊君所结好于诸人者,殆已十倍过之矣。此为嘉庆中事。数十年,淮人犹能道之。*(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撰,谢光尧 点校:《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中,也描写了南京娼妓的“盒子会”:
每到春三二月天气,那些姊妹们都匀脂抹粉,站在前门花柳之下,彼此邀伴顽耍。又有一个盒子会,邀集多人,治备极精巧的时样饮馔,都要一家赛过一家。那有几分颜色的,也不肯胡乱接人。又有那一宗老帮闲,专到这些人家来替他烧香,擦炉,安排花盆,揩抹桌椅,教琴棋书画。那些妓女们相与的孤老多了,却也要几个名士来往,觉得破破俗。
《香艳丛书》第十九集《花国剧谈》中也有记载:
一日若涛告生曰:“明晨花朝,妾等姊妹为盒子会,画船箫鼓,当于虎邱山塘间作竟日清游,各奏一技,琴棋书画,但须惟其所能。君盍同往一游,绘图以志胜会何如?”翌日,生与若涛偕往,众美毕集,或拈毫觅句,或对局弹棋,或抚氷絃,或摹晋帖。*(清)淞北玉魫生《花国剧谈》,收入虫天子编《香艳丛书》十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综合上述文献,关于“盒子会”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以下几点:
(1)盒子会是明清时江南地区,尤其是南京娼妓间的习俗。
(2)盒子会的时间是在春天,文献里有上元节(农历正月十五)、花朝节(农历二月初二、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清明节前后等几种说法,地点多是选在室外人多、风景好的地方,因此盒子会也有踏青、游春的意思。
(3)盒子会得名于娼妓们提着食盒前来赴会。装满美食佳肴的盒子,起初是娼妓间联络感情的一种活动,后来逐渐发展为厨艺和吃食比拼,再后来就直接成为娼妓们争奇、斗艳、炫技的秀场。娼妓们不仅各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带上自家的珍玩巧物来赴会,会上还要“琴棋书画,惟其所能”。
(4)盒子会并不仅仅是娼妓群体间的活动,文人名士也构成了盒子会的另一性别主体。
(5)盒子会所产生的影响重大,以致于“临河观者数千人”,盒子会被称为“神迁高会”、“胜会”。
聂绀弩曾在《蛇与塔》这部杂文集中多次提到中国古代的娼妓及娼妓制度,他认为“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污点,是旧世界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制度的最丑恶,最不合理,最高度,最尖端,最集中的表现。”而娼妓则是“不被允许有节操的圣洁者”、“被风化妨害者”、“被社会秩序、幸福家庭所坑害者”。*分别见《论娼妓》、《谈鸨母》,收入聂绀弩《蛇与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可以说,聂绀弩的几句话,使得娼妓的“受害者”形象跃然纸上。然而,在盒子会上,我们却看到别样的画面:娼妓既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不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她们公然在城市公共空间之中行动,展示自己的美貌与才情。而且她们选取的还不是一般的城市空间,而是“官商荟萃之所”、商贾往来频繁的秦淮河两岸,尤其成为娼妓的首选。她们这样“明目张胆”的活动,不仅没有受到主流社会的蔑视,反而让无数的观者赏心悦目。这与传统风化中对娼妓的抵触和排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娼妓及其盒子会成为了秦淮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娼妓来说,最好的出路,大致是以下三条:“一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皇帝的宠幸,但这毕竟是少数,甚至是极个别的例子。二是结交名公或名士,从中选择一人,做人之妾。三是寻觅富商大贾,作为自己一生最后的归宿。”*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从历代的文学作品来看,后两者无疑是大部分娼妓的选择,但这也并非她们最好的“归宿”。但相比起孤老在院中,她们还是很乐意为这种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搏的。
因此,藉由盒子会,娼妓们在公共空间中通过对身体、物品和技艺的展演,扮演自己的角色,满足大众对其身份的想象。在表演者(娼妓)、观众(主要指赴会的其他男性)和表演场合(城市公共空间)的同时作用下,一场“香艳”的演出被制造出来,在互动中不同的人得以实现各自的目的。
在这场“演出”中,娼妓最主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手帕姊妹间的感情交流,而是通过盒子会张其艳名,为自己作一次免费的广告,为日后的“美好生活”(不管是赢得更多“客人”的青睐还是嫁于良人)积累资本。用娼妓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作面子”*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娼妓是一个备受屈辱的群体,而在盒子会上,她们乐于被欣赏。谁的盒子会若能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光彩,是一件足够有面子的活动。反之,如果谁的盒子会没有人来捧场,那简直是奇耻大辱。
此外,手帕姊妹们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还间接成为社会时尚。就以最初盒子会中的“饮馔”来说,妓女们的食品讲究“精巧”二字,名酒好茶、荷花细饼,加上丝竹袅袅,“盒子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韵味。妓女们连带着也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刘鸿伏:《文物古董传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同样,藉由晚清名妓“四大金刚”对服饰时尚的引领,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盒子会中的手帕姊妹对服饰审美的影响。1899年的春季上海赛马盛事详细报道了“四大金刚”在赛马场上的着装与风姿:
昨日为赛马第二日,游人较第一日为盛,而各校书尤无不靓装艳服驰骋于洋场十里间,足以游目骋怀,洵足乐也。
计是日林黛玉蓝缎珠边衫,坐四轮黑马车,马夫灰色绉纱短襖黑边草帽。陆兰芬湖色珠边衫,坐黑皮篷,马夫竹布号衣黑背心草帽。金小宝白地黑蝶华衣,坐黄色红轮马车,马夫湖色绸号衣黑边草帽。张书玉蓝珠边衫坐黑皮篷马车,同坐者为顾庽,穿月白珠边衣,马夫各戴黑线凉帽穿鸭蛋色号衣。*参见《靓装照眼》,《游戏报》1899年5月4日第2版。转引自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页。
按照朱国昌对晚清娼妓的分析,“上海妓女喜欢驱车兜风,喜欢出风头,她们知道和感受到市民对自己接纳的态度并同时给她们带来了心理的体验,被欣赏的快感和满足感。在当时还没有电影明星的时候,她们充当了电影明星的作用,丰富了都市的娱乐内容,补充了市民的猎奇、猎艳心理,加强了社会的风化意识。”*朱国昌:《晚清狭邪小说与都市叙述》,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4页。这段话同样可以用于明清娼妓的身上。在盒子会上,娼妓们不仅是被欣赏的“商品”,她们更是能动的主体,她们知道如何利用大众的期待,来完成自我的彰显。
余论
相较于一般的女性,娼妓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现有的与娼妓有关的研究中,无论古今,不外乎几种视角:一是欣赏介绍,二是维护道德,三是意识形态指导(阶级批判与阶级教育),四是法律评判(罪与非罪,合法与非法)。*刘平:《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2005年版,第14页。就中国古代娼妓的研究来说,主要集中于前两种视角。一方面,她们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从文学、艺术、娱乐等多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另一方面,她们也身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与“乐户、丐户、堕户”等非良人被认为是最卑贱的人,遭遇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高雅”与“卑贱”的二元对立在娼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由“局外人”或者“客位”的男性视角所塑造的娼妓形象,是造成这种二元对立认识论的主要原因。在“他者”的话语里,娼妓群体成为了被欣赏、被玩弄的对象。同普通的妇女一样,没有自主性与话语权。然而,通过本文对明清时期“手帕姊妹”的结拜行为及习俗的梳理,却得以窥见另一面向的娼妓群体。她们有自己独特的心理与生活,更重要的是,她们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
引申开来,下层妇女间的结拜、结社、结群等行为,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无论是制度性还是非制度性的,其本质都是一种女性主体意识的凸现。女性结拜(结社、结群)不仅可以帮助共同体内的成员解决生活困难,更难得的是使女性有了情感寄托,丰富了她们的精神生活,展现了女性的自主独立与姐妹情谊。这一行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强势的男性话语之外,建立了属于女性自己的独立空间。
[责任编辑]刘晓春
崔若男(1991-),女,陕西西安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K890
A
1674-0890(2017)02-0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