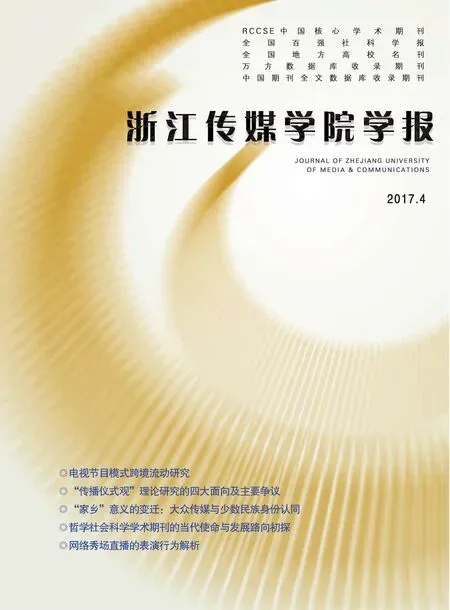聚焦浙江新诗,反思百年辙迹
——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俊杰
聚焦浙江新诗,反思百年辙迹
——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俊杰
中国新诗迄今走过了整整100年的旅程,百年中国诗歌履历中,既包含了无穷的文化创造性,又引发了许多论争。为更好地反思百年新诗传统,促进新诗健康发展,弘扬浙江文化精神,5月13日,由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浙江传媒学院联合主办、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协办、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承办的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浙江百年新诗反思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召开。
浙江传媒学院副校长姚争、浙江省社科联学会处处长王三炼、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吴秀明、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殷国明、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吴利民、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张邦卫、文学院分党委书记徐洲赤、副院长赵思运以及全省专家、学者、诗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师共七十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就“百年中国新诗反思”、“百年新诗视野下的浙江诗歌”、“木心诗歌研究”和“新诗教育研究”等多个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一、整体性的回望与思考:百年中国新诗反思
面对文学多样化趋势,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吴秀明(浙江大学)就当代文学的历史性问题提出建议。结合当下诗歌考察,他对退回到内心世界、强调纯文学方向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反思新诗走向异质空间“异托邦”的可能,并以现代民主开放的思维理念和学术立场,重新审视朦胧诗讨论中“反对者”的声音及其合理性,希望以弹性豁达的姿态,将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当代文学放入历史长时段中,用更开阔、更富有纵深感的学术眼光进行评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欣赏朦胧诗“反对者”的声音,但应尊重他们,将其摆在与朦胧诗“欢呼者”平等地位进行探讨,允许发声,它是“历史化”而不是“道德化”的评价。这在当代文学学科已近七十年历史,不再那么“年轻”的今天,尤有必要。
百年中国新诗反思,最引人瞩目的是旧体诗问题,是否入史,价值几何的追问方兴未艾。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先生首先通过近年来对当代文学旧体诗词入史问题的研究,指出当代文学进程中的“一体化”泯灭了个人经验独特性和艺术独创性,从而指出当代文学另一种难能可贵的方向,即旧体诗潜写作,并且以陈寅恪、聂绀弩和王辛笛的旧体诗创作为例,探讨其如何在苦难中安顿个体人格尊严,保存风骨,体现文学韧性。重新审视新诗百年来的反向坐标“旧体诗”,体现了学术视野的进化和发展。21世纪以来,这一层面的问题得以正视,正由于如钱理群、夏中义等多位前贤的倡导,文学史逐步跳出“新”“旧”对峙的传统格局,走向更宏阔的学术视野。
殷国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则在另一层面重新审视百年中国新诗,他提出百年新诗是被过度阐释的“早产儿”。他揭示了新诗先天基础的羸弱和短暂孕育的不良,提出其未来可能性,即满足人们诗意生活的要求。这一视野强调诗与“日常性”关系的重要命题,为新诗在阐释过程中的不堪重负进行“松绑”。回归日常逻辑,把新诗当作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既是百年中国新诗值得反思的命题。
南志刚(宁波大学)教授以“朦胧诗的文学史叙述问题”为题展开反思,并通过文本细读三首朦胧诗展开论述,结合史料,追本溯源。他提出,朦胧诗作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学事项,在通行的文学史中一直充当着“反叛”者的形象,从而割裂了朦胧诗与文革时期社会语境、文革文学的复杂联系,进而切割了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联系,而直接将“接续”的目标对准五四文学,很大程度上造成20世纪80年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叙述视阈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子张(张欣)(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则以一种独特的姿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强调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和更为准确的文化描述对于新诗讲述的重要性。他提出,所谓“浙江诗人”这一称谓的定义究竟以籍贯还是以文学活动展开地还是其他,本身就需要详细考辨,借由这一看似“狭小”的问题,导向一个更为宏阔的命题:学术之真伪。范家进(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通过列举时事热点,从余秀华到范雨素,谈及草根诗人作家的文化意义。伴随媒体的助力和普遍的文化心态的利用,20世纪末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草根诗人”或曰“底层写作”,这一批创作者的文学价值始终悬而未决,文学史地位也忽隐忽现,范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提出应正视和研究这一类诗歌。这种将舆论中的诗歌热点充分学术化的思路,是对最新脉象的捕捉,体现了反思之中的展望。
金进(浙江大学)研究员主要进行了对华语新诗的跨区域研究,通过对上世纪的一批马华诗人作品的考察,站在域外的独特角度扩张了新诗研究的地理空间,他提供的诸多材料让我们感受到,域外华文诗人与20世纪中国本土诗人对话的可能,这种对话将可能使我们对“新诗”的历史书写呈现出更具“世界性”的意义。
赵卫东(浙江科技学院)教授则是从一则具体的案例出发,进行百年新诗形式层面的重要问题探讨。他借助朱湘的《采莲曲》,探讨其节奏问题,并以此推及新诗中的节奏与分行问题,提出诗歌的节奏是由外在节奏——诗人的情绪节奏以及诗行诗韵相结合的产物,诗歌即内外节奏的相遇。这是从最令人忽略的小问题,进入到整体性把握百年新诗形式特征大问题的一次具体实践。这也引发了与会学者诸多关于新诗音乐性问题的讨论。
最后,张晓玥(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通过《诗与史的融汇——读子张〈历史·生命·诗〉》的主题发言,进一步探讨了历史和生命、诗之间的多重关联。以研究之研究的独特学术沉思,讨论了百年新诗学术范式的演进。
在整体性的回望与思考中,蕴含着我们对百年新诗的既有观念、叙述范式、研究理路和视野格局的整体性期待。
二、地域性的观照与研究:百年新诗视野下的浙江诗歌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百年新诗,既包含整体性的文化特征,又有其独特的地域性文化。新文学的半壁江山,是由浙籍文人构筑的,作为文化输出大省,浙江的诗歌创作中包含的地域性特征令人瞩目。
余连祥(湖州师范学院)教授首先从周作人《儿童诗杂事诗》与丰子恺漫画的“语图”关系入手,着重分析了丰子恺在忠实原著的原则上对周作人诗歌的二度创作。浙籍文人丰子恺与周作人在创作之中熔铸了既趋同又各异的典型江南文化想象方式,对此进行比照分析,将不断为民国文化中的“江南”形象找到诗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孙良好(温州大学)教授谈及了对诗和歌的体认,他编选了《中国现代歌诗精选100首》,撰写了《漫说中国现代歌诗》,以李叔同、刘半农、胡适、赵元任等创作的“歌诗”探讨诗与歌的互动,为文学史和诗歌诗史写作注入了新的理念。庄伟杰(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提出,经典文本离不开“怎么写”和“写什么”这两个话题。他提出“地理空间拓展与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问题。他认为重新审视如穆旦等的诗歌,非诗意性语言应当受到重视。他提出诗学视域中的“海洋”观念的价值,这让人不得不缅想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与海洋文明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也让人回望浙籍知识分子具有地域性格的文化表达及其与具体文化地理形态的密切联系。
左怀建(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从艾青晚期诗歌中的异域都市想象谈到民族文化的发展。他认为:“艾青终其一生是一个具有鲜明现代主义倾向的左翼诗人。”其诗歌创作显示了艾青作为一个现代都市诗人其文化审美路向的复杂和多元。这些诗歌合起来构成西方现代文明史的一个缩影。他借由艾青关于“巴黎”的异域想象,理解了农民之子艾青的知识左翼立场,展示了地域文化之中投射的精神性追求。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揭示了当代诗人对鲁迅接受的惨淡现状。他认为,鲁迅也是人,不必圣化,更不可感性地一度否定;最理想的办法是继承鲁迅,如《野草》打破诗歌的规范,挖掘深层的悖论和体验。
百年新诗的研究与地域性文化的关系,迄今仍是值得深耕的学术沃土。诗歌研究与历史、地理、政治等实事相关的综合性考察,应成为学术自觉。一方面,地域性的考察包含了中国传统以来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理想,地域自然因素与文化气质和风格有一种粗糙的因果联系,它构建了具有古典文化色彩的地域文化阐释方式,但往往使一些研究进入某种大而化之的感受性路径。现代以来的学术理路之中,崭新的思想资源中现代知识体系构建了文明与地理的新研究体系,梁启超以降,地域文化以更为精细的展示方式出现在学术界面前,政治历史、文学学术、地理风俗、军事格局与地域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缔结的具体的历史情态和语境,值得在探讨新诗审美情趣的同时,更突出其中包含的实证性因素的兴味。这样,地域文化之中包裹的诗与史跨越式对话的张力,或可得以呈现。
三、个案的挖掘与辨析:木心诗歌研究
以木心诗歌为中心进行专题研讨,既是回应社会热点,同时也是将热点纳入学术尺度之中丈量。木心现阶段产生的社会影响力错综复杂,一方面,他被看作最具世界性的中国诗人,另一方面,他本人文化叙述中的“乡愁”又反复感染读者;一方面,他是媒体渲染下的“诗人中的诗人”,其创作的社会影响力极大,另一方面,他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往往呈现两极分化。
任少云(海宁文联)通过“论诗性生活的现实意义”指出诗意人生、诗意生活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良性社会将为保存诗人尊严,维护诗歌环境,最终诗意栖居提供保障。这事实上在精神深处指向了木心的文学创作。木心诗歌艺术中,最为昂扬的力量,即对个体尊严和文化尊严的坚守。王芳(浙江工商大学)则从辛迪的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意向考察”切入,结合辛迪作品,讨论现下知识分子如何安顿自己,安顿心灵。借此谈及木心诗歌中的“安魂”力量,并且讨论了知识分子个人境遇与诗歌创作的复杂关系。
曾莹(浙江传媒学院)以“木心小说的跨境之旅”进入木心文学创作中特殊的美学追求,从音韵、图像及节奏等诸多问题进入到木心文学创作之中,以细致的文本分析进入木心文学研究,事实上是理解木心的不二法门。宗培玉(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以《九月初九》为例探讨了“木心的精神密码”的话题,侧重于木心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木心诗歌创作的读解极依赖于文本细读。不断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何种层面的文本细读,才能导向那些与木心相关或者与中国文学相关的“问题”,文本解读的最终归属又在哪里。
李俊杰(浙江传媒学院)指出,木心诗歌需放置在“百年新诗传统”这一坐标中解读,不能因其文学创作表象中呈现的某种风格化特征而忽视其本土文化传统的面向,他指出“五四”是木心文化的根。理解木心的诗歌,一方面要通过20世纪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木心个人遭遇来探查,另一方面还是要回归到他自己的叙述中去,通过《文学回忆录》的探究,或许会对木心的诗歌观念、艺术主张乃至人生哲学有更为恰当的理解。
赵思运(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谈到木心的《洛阳伽蓝赋》,以发生学方法,揭示了木心在这件作品中潜藏的灵魂密码,如他的艺术情结、诗人角色的自珍、去国忧思等等。他的研究展示了如何从文本的细节走向历史的细节,在对一首诗歌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呈现出超越文本意义的精神内涵。这一具体文本分析解密过程,展示了木心诗歌研究的一种方法,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引发了热烈反响。
木心及其诗歌的研究是浙江学人应尽的义务,在会议最后,会长吴秀明对这一问题提出重要关切,他提出,学会将为各位学者进行有关研究提供更充足的学术资源保障。如何逐步解开木心诗歌艺术的“密码”,如何为百年以来的每一位中国诗人寻找一个恰当的位置,也是这个话题的应有之意。
四、热点的透视与探查:新诗教育研究
通过文学教育研究视角来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中国学界引发过持续的关注。新诗教育作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在本次会议中也被充分讨论。
陈小亮(宁波工程学院)以叶维廉为中心,探讨其诗歌研究中的“中国性”,肯定其对中国诗歌语言的新发现。叶维廉作为学院派的诗学家,兼具理论和创作的双重身份,从“传道”这一角度来看,他为中国文学理论、美学、诗歌艺术等多方面提供了文化资源。清理叶维廉资源,同样是新诗教育研究的一个面向。雷水莲(丽水学院)追忆起数年前在浙江大学访学时萌发了研读孙大雨作品的想法。不同于平时接触较多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闻一多,孙大雨浓墨重彩又颇为粗鄙的文字,在诗学上显得与众不同。孙大雨在新格律诗理论上的建树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充分展现,别具一格,并由此奏出“新月”诗派互补共生的多彩韵律。刘树元(湖州师范学院)认为,学者们应该允许新诗的幼稚,就像唐诗、宋词在初创阶段良莠不齐,并在教育之中加以阐释和讲解。从个人教育经历中提出对学术问题的具体感受,从而引发学术问题,体现了个人生命体验中“教育”经验与学术过程往往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也是探讨20世纪中国诗人、诗论家必须关注的命题。
陆孝峰(湖州师范学院)表达了她对北岛艺术地表达生活的方式的赞赏。她指出,诗歌本身就和哲学、宗教有关,学者们应心怀虔诚,把北岛作为一个诗人去理解。诗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常读常新,在一定范围内,合理的解读都应被接纳,涉及教育与解诗学的相关问题。作为进入文学史的典型作家,在教育过程中被塑造起来的那个北岛,和现实之中那位诗人、散文家、西方诗歌译介者的北岛,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值得深思。周敏(嘉兴学院)在论题“如何教中文系学生读诗”中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诗歌和散文都有一定教学难度。他对诗歌一味走向内心而无所共通的现象持否定态度,他强调教育过程中诗歌呈现并不以艺术阐释为唯一的路径,其中还包括对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个人心绪、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表述。这一极具鲜明特色的论题,从对文学性弥散的质疑说起,足见张力。
新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发展成熟的过程,与文学教育密不可分。校园情境不仅为文学活动提供了传播空间,同是也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体,诗歌教育是诗歌创作、消费和诗歌知识生产的媒介。新诗借助高等教育,使这一媒介不断扩大,其历史意义不断凸显,教育情境中的新诗创作、讲述、批评、和学术研究又开拓了新诗的艺术高度和理论主张,持续开拓艺术性探索和社会性意义。与会者纷纷表示,这一具有学术生长型的话题值得持续研究。
本次会议的四个议题,蕴含着浙江学人对百年新诗整体风貌、地缘特征、边缘诗人和热点动态的精准把捉,彰显了浙江学人对百年中国文化进程的热切关注,此次会议的意义也在于此:通过百年的契机进行历史反思,在回顾中展望未来。本次研讨会推进了对这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思考和认识,为进一步走向共识提供了交流的重要平台,对新诗的创作、研究和传播,做出了应尽的努力。
[责任编辑:高辛凡]
李俊杰,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