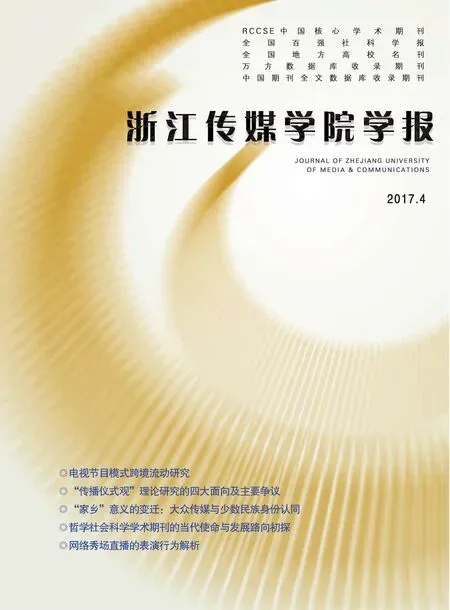新媒介场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传承
杜洁莉
新媒介场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传承
杜洁莉
随着人类进入个性化、数字化、开放化、碎片化、交互化为特征的新传媒时代,“新媒介”作为一种自主的、跨界的、流通的、集成的、协同的信息数字化平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场域、方式以及传承媒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契机。然而,新媒介具有传统媒介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道德困境等负面效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寻找一条科学传承之道,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性传承的关键问题。
新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性传承;
一、非遗传承模式的历史变迁
植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的非遗文化,其传承模式经历了从口传身授的“学徒制”,到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等音像文字传播方式,直至今日以信息技术、互联网为载体,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工具展现出来的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相融合的媒介传播方式变迁。非遗模式变迁,是时代技术的发展的推动,更是人类文化生态的内在需求。
长期以来,植根于中国乡土文化的非遗传承模式是“学徒制”,即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模式。“学徒制”的传承方式主要靠口口相传、文书、身体演示等进行知识传递。非遗是一种受制于传承人主观倾向的文化遗产,人们通过技艺的习得内化成为自身技能乃至文化素养,并将其个性化的技艺进行展现。但是,人本身具有个体性、情感性、自私性、多变性,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以及个体命运的变化,其个体承载的文化因素变动性日益增强。“学徒制”传承的利弊兼而有之。随着社会文化大交融,信息流动速度加快,“学徒制”作为单一的传承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生态的变化,传统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等随之成为非遗传承的主要载体,民间歌舞如京剧、昆曲、粤剧、客家山歌、古琴等传统文化通过传统媒介广为传播,甚至鲜为人知的门巴族、珞巴族的原生态歌舞表演、畲族山歌中唯一幸存的畲族二声部山歌“双音”、被誉为“深山珍宝”、“天籁之音”的苗族《担水歌》等独一无二的民族表演形式通过电视、广播传播受到民众的广泛喜爱。传统媒介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尤其电影、电视、广播等作为综合性视听平台提供良好的感受性,便于打破原有非遗文化时空的限制,进行多元化的交流。报纸、期刊则具有理性度高、针对性强、重复阅读率高、便于引导受众需求、艺术性强等优势。但是传统媒介时效性差、成本较高、受众互动性少,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其互动性、开放度、个性化程度、视觉效果等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新媒介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空间和路径。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新媒介的形式是指继传统媒介之后,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传播渠道,以电脑、手机、数字接收设备为终端进行信息传播的新型媒体,具有互动性、主动性、个性化等特征。文章中的“新媒介场域”是指一种自主的、跨界的、流通的、集成的、协同的信息数字化平台。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介技术具有众多比较优势,弥补了传统媒介的不足,打开了非遗传承的新格局。非遗传承进入了一个“学徒制”传承为基础、传统媒介传承为辅助、新媒介传承为拓展的融合模式。
二、新媒介在非遗传承中的比较优势
(一)低成本高效益
非遗文化多植根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其原来的主要价值囿于庙会表演、社区娱乐、传统生产等,受众面窄,传播渠道有限,传播成本较高。新媒介通过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的传播方式,形成个性化的市场需求,使得原本无人问津的文化产品广为人知,降低传播成本,并形成可观的市场经济效益,实现非遗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素材等商业价值,甚至将非遗引领到文化产业链中,例如通过微信号推送工匠故事,运用影像技术、动漫艺术展示非遗的技术细节和工艺过程等,并在线下单交易,从而带活整个产业链,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全面结合。
(二)新传播新理念
非遗传承从现实场域转向虚拟空间——赛博空间。例如,某些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被电子游戏开发商借用,制作成为网络游戏,从而作为一种新的流行文化而被大众广泛接受。流行的恐怖冒险电子游戏“零——红蝶”便是借用日本的民间传说“红贽祭”,即一种双胞胎姊妹被当作活祭品的民间仪式创作而成。整个游戏围绕民间传说的内容展开,通过光影、音乐等技术操作渲染恐怖气氛,玩家通过机器寻找隐藏的区域并与鬼魂战斗。传统文化在赛博空间中可以超越国界、题材以及形式,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体。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非遗被进行传统再造,并在新的场域中得以传承。与此类同,中国的民歌、诗词、舞蹈等亦在赛博空间中脱胎换骨,成为消费文化,人们通过更为便捷的方式学习传统文化,并进行文化创造。赛博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三空间”,为“赛博公民”文化的传承提供新的场域。赛博空间中,人们可以实现无身份性,文化传承中的身份障碍将会消除,各种信息可以在人、机器、文本之间畅通无阻。机器超越人体的限制,为人类技艺、思想的传递提供辅助,亦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场域与监督机制。
因此,新媒介的应用不仅仅带来了新的传播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传播理念,将地方性文化纳入全球性的时代话语中,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更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明发展。
(三)立体性互动性
非遗以门户网站为平台,采用视频、三维动画、图片、文字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创意互动区、游戏区等模式,为用户提供工艺模拟、工艺创作的平台,例如将民间歌舞、乐器、工艺美术以及神话传说等文化资源转化为商品,为用户提供参与式文化体验,用户可以在网络上学习、传播各种形式的非遗特色工艺,并利用新媒介进行创作,丰富非遗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以非遗为游戏创作素材,充分挖掘文化元素符号,实现虚拟场景与真实景观的结合、线上互动与线下互动的结合,吸引更多人群的参与和关注。
手机媒体具有移动性、交互性、个性化等优势,通过微信平台等可以自主发布和选择信息,实现非遗更具时效性的传播。用户通过手机APP,可以下载各种手工技艺的操作软件,进行学习乃至DIY。通过网站还可以将用户的APP发布到苹果的App Store和国内知名的Android应用市场,扩大文化传播的范围。
(四)超验性与多元性
非遗传承场域拓宽的同时,其传承方式也日益多样化。新媒介的应用,使得人类可以借助影视技术进行文化的记录、创造与再现,各种民间造型艺术,例如绘画、雕塑、工艺、印染织绣等,将不再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艺人经过夜以继日地千锤百炼方能代代相传,仅仅通过电子数据库便轻而易举地得以继承。
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笔者曾亲眼见到,电子人(即机器人)与民间艺人相辅相成,成为非遗新的传承者。电子人即机械和基因组成混成的新生物,其打破了自然与机械、肉体与精神、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成为一个备受推崇的新文化概念。目前,电子人已经从想象成为现实,并在医疗、销售、服务等行业里开始应用。“电子人”以千姿百态的面貌出现在观众的面前。各种非遗传承“电子人”功能各异,有会炒菜的电子人,演奏长笛的电子人,制作工艺的电子人,绘画的电子人等等。“电子人”初步具备各种娱乐科普功能,在人类社会发挥其作用,其在非遗传承中的应用指日可待。相对民间艺人而言,“电子人”在文化的传承上具有精确性高、不受时间精力限制、不受情绪影响等优势,尽管还存在感染力不足、灵变性较差等劣势,但是“电子人”足以辅助民间艺人,成为非遗的传承者之一。
新媒介技术使得非遗的组织方式、仪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微博、微信、电子邮件、网络敬拜成为新的宗教渗透工具以及宗教文化活动组织方式。网络宗教社区(Online faith community即OFC)成为宗教组织交流与管理的虚拟空间,在OFC中,宗教活动的时间呈现全天候、随时性的新特征,宗教对象呈现多元性、多变性的特征,宗教的话语权从结构组织为主导的控制转向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控制,宗教活动从传统的组织性更趋向于后现代的参与性。新媒介视域下,宗教文化的严肃性减弱,活泼性增强;时空地理的限制减弱,边界可以无限拓展;理性思考减弱,感官宣泄增强;政治权利性减弱,自由民主性增强。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再局限于某个政治主体、教派或者宗教内部人士、文化机构不遗余力的保护,而成为一种大众参与的文化自觉。
(五)全面性直观性
影像通过纪实性的记录和传播,可以将非遗通过声音、画面、文字、动画等进行全方位展示,其表现手法多样,覆盖面广,可以全面、直观地传播其艺术特征、技术特点及历史文化,甚至可以将不同地区同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比较、赏析。由于数字存储器具有强大的存储能力和复制能力,可以将海量的文字、图像、影视信息存储起来,集成性强,可拷贝性强,既节约成本,又可以迅速、逼真地传播,因此可以防止信息丢失、技艺失传而造成的损失,作为历史性资料永久性传承。
三、新媒介场域中非遗传承的现实困境
目前广泛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官方中文本,该文本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官方文本解析可以发现其内涵包括:传承主体为以群体性为特征的“人”;传承对象包括作为非遗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知识和实践以及手工艺技能等。新媒介尚未在概念中出现,未能体现非遗开放的、解构的、多元的、超验的特质。由此可见,新媒介作为一种新的非遗传播方式,尚未被广泛接受与推广。
笔者带领学生于2012—2016年期间对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的非遗展区进行问卷调研与访谈,发现绝大多数非遗在传承、传播上仍然是以传统媒介为主。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为例,传统媒介展会、口口相传、电视、报纸、广播、图书等在非遗传播中仍然占据较高比重,新媒介网络、手机传播仅分别占18%、3%。
据访谈发现,新媒介在非遗传承中未能得到迅速推广的原因:一是资金问题。新媒介的使用必须投入相当数额的前期资金,而且投资回报预期难以预测。多数非遗传承单位资金不足,不能够借助新媒介进行展示和跟踪,而多数企业即使尝试新媒介也常常因为一时得不到回报而半途而废;二是沟通障碍。非遗传承人对新媒介缺乏足够的了解,本身没有和新媒介对接,无论其自身的知识结构,还是其文化表现的方式、传承的方式还是运作的方式,都与新媒介的传播理念格格不入。
同时,新媒介的应用带来非遗传承创新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随之彰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伦理的困境
新媒介传承的专业性较低,自由性强,在非遗的传承中,其信息传播者和受众群体具有平等的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和反馈权。但是由于随意性强,导致某些非遗被扭曲,失去其文化内核。甚至一些邪教等非健康的文化遗产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传播,腐蚀了人们的精神,乃至影响了人类文明。例如“天堂之门”事件,邪教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红色警报”,警告世人“海尔—波普尔彗星要关闭天堂之门了”,导致39名信徒在教主阿普尔怀特的率领下集体自杀。此类事件说明了网络传播非遗的不安全性。此外,宗教文化的发源与延续,其主要原因便是生命的不可知性,以及自然力的神秘感。因此,宗教思想中体现人类内心深处对于生命起源的猜想,以及对永恒生命的追求。这种生命思考在佛教中表现为涅槃、轮回,在道教中体现为羽化登仙,在基督教中则是教徒对天堂的向往。这种宗教思想在新媒介发展中面临着困惑。人类对于生命未来的想象方式发生变化,新的技术条件下,人类可以得心应手地医治疾病、优化生命,人类对生命的操控能力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生命延续的追求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奢望。此时,宗教的神秘感将逐渐淡化,宗教传统也将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面临解构。
非遗中的“人生礼仪”也将面临着无可避免的困境。不同民族,由于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其人生礼仪即出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等皆表现出丰富多样的风貌,以此记录与印证不同人群每一段独特的生命历程。人生礼仪衍生出纷繁复杂的仪式体系,广泛地影响着各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族群关系、家庭婚姻以及日常生活。其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民族集体记忆,具有深远的意义。新媒介的应用,使得许多人生礼仪简化成为网络上的祝福、纪念,其传统的存在方式和庆典意义正在日趋弱化。
(二)神秘性、地方性特质的丧失
人类学家布莱恩·斯波纳说过“真正的东西并不仅是手工物品,它由特定的个人制造,由特定的工艺材料制成,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条件中生产出来,并且具有从上一代那里学来的花纹图案与设计。”[1]这里的特定个人、特定工艺、特定社会文化与环境指述的便是指代一种工艺源于本土的独特性、本真性。新媒介的应用,使得非遗本真性、地方性特质日益丧失,同质化问题日益凸显,各种伪劣仿冒产品层出不穷,更多的非遗产品只是在商品化经济中被包装上一层本土化的传统外衣。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传统的发明》中写道:“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2]。例如魔术的发展,人类初始对生命本体与自然界存在种种困惑,巫术等带着迷信色彩的现象流行于民众之间,魔术便由巫术而来。而今魔术已经成为备受推崇的大众文化,并且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现代技术的高水平表演,通过新媒介的推广广为人知。人们不再对魔术存在神秘感,而是欣赏表演的同时,破解技术并学习技术,刘谦的春晚魔术表演在短短的10分钟内便被破解。魔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与技术的高度结合使其实现了华丽转身,从平民艺术登上大雅之堂,并展现其时代的魅力,但其核心的神秘感却在日益丧失。
在新媒介的影响下,非遗精益求精的精神日益丧失,随意性取代专业性,解构性取代神秘性,全球性取代地方性,更多的传统被发明,甚至文化遗产脱离了原有存在的社会环境,脱离生活源泉,成为一种娱乐方式。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亦弱化了非遗所具有的地方性、族群性、个体性特质,非遗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就在于其独一无二的文化个性,在一个可以广泛复制的时代,非遗遭遇价值危机。
(三)真实性准确性不足
为了吸引观众眼球,某些非遗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被夸大与扭曲。非遗本身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其文化价值是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沉淀和民间智慧的集合荟萃而成,需要深度挖掘和真实传递,但是新媒介在进行大众化传播的时候,常常进行表象报道,缺乏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甚至某些时候其报道、评论及模拟表演与真实性相去甚远,对受众进行了错误的引导。非遗属于地方性文化,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原来的受众面窄,地域性强。大众缺乏对其本土文化的了解,对其理解必然产生误差,互动存在障碍。非遗亦俗亦雅,既有植根于乡土文化的“俗文化”性,又有受小众精英青睐的“雅文化”性,缺乏足够的领悟能力和审美能力者便难以将两者融会贯通,难以了解该文化遗产的艺术特质和文化价值。绝大多数受众在快餐式消费的文化内容面前也显得浮躁,对于非遗的真实性缺乏甄别能力。新媒介在进行文化传播的时候容易失去精髓,流于表面,导致非遗的变形,乃至最后失传。
总之,新媒介为非遗传承带来无限发展空间,非遗传承在新媒介文化形态下却遭遇重重困境。
四、新媒介场域中非遗传承的管理模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技发展,新媒介环境下作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关系、性别差异、婚姻家庭、意识形态、工艺审美等因素发生变化,人类的种种不确定性预示着非遗传承的多元取向。新媒介时代中非遗的特质是开放的、解构的、多元的、超验的,非遗的传承不再墨守陈规,而是在时代思潮中海纳百川。在这种情境下,应当借助新媒介的优势,进行非遗的传承、传播以及创新,一方面有利于非遗在全球化、商品化社会中的保护与发展,防止非遗因空间限制以及传承人个体私有性导致的消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借助非遗丰富大众生活,充分发挥非遗的趣味性、知识性、技能性、互动性,弥补社会由于过度商品化带来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提升社会精神文明。同时,在充分挖掘非遗内涵,并借助新媒介进行多元化、虚拟化传承的同时,也应当扬利去弊,进行科学管理。
(一)知识产权保护
新媒介的传承环境下,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开放化、大众化,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更大的难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新媒介环境下非遗的传承和创新没有真正的传承人和原创性,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容易被扭曲以至于失去本真性、地方性特质。因此,为保持其特色,需要组织协会、学会等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一定比例的社会传承群体,通过定期的讨论、研究,确定其保护的基本思路和文化范畴,努力保持其特色,促进其发展。同时,对于部分具有原创性的核心文化特质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由国家或地方培养非遗传承大师,以其作为传承与发展的标杆,或者培育传播机构,成立专业网站进行保护与推广。
(二)文化媒介选择
进行各种新媒介传播方式、渠道的研究开发,对不同媒介进行分类和特性定位,同时对非遗的传承特性进行相应的分类和定位,并针对不同非遗的传承特点选择合适的媒介。例如语言、神话故事、民歌、戏曲等口头传说和表述注重的是内容、声音方面的特性;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对图像、影像要求更高;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则偏重于其道德性、思想性、情感性;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更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需求,进行推广应用;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则可以通过游戏等互动环节进行保存和展现。
(三)动态监督审核
针对非遗保护中出现的道德、伦理性困境,政府相关文化、法律部门应当建立专门的非遗管理机构,对网络、手机以及其他数字接收设备为终端的新媒介进行动态跟踪,定期检查,对于借助非遗宣传不健康内容的网站进行严惩,并通过制定以新媒介传播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化保护法》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控制方式,对新媒介传播带来的负产品及时控制、取缔。尤其随着非遗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递,要综合考虑各国法律法规方面的差异性,避免由于法律法规冲突导致非遗的流失,进行国际化保护。但要警惕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借助非遗进行的文化侵略、文化颠覆,保持文化的中立性、客观性,使得非遗成为我们国家在全球化发展中一股强劲的软实力。
(四)现实虚拟兼顾
新媒介环境下非遗出现虚拟化倾向,人们渐渐习惯在虚拟空间中举办某些传统仪式,如清明节进行网络扫墓;某些手工技艺成为电子游戏而非投入现实生产,其现实空间的价值弱化,娱乐性渐渐超越专业性,使得某些非遗失去了现实意义,成为无根之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注意平衡非遗的现实价值与虚拟价值。在充分借助新媒介进行传播的同时,不可顾此失彼,应当明确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不能离开本土土壤,不能离开现实市场,新媒介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应当重点扶持非遗的现实传承,通过开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以及扶持非遗相关生产企业等方式,挖掘非遗的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使之在新媒介时代中保持其独特的社会价值,持续、有序地发展。
(五)公益性文化传承
随着网络公益模式的推广,非遗的传承可以结合时代需求,与网络公益性活动相结合,例如借助腾讯公益等公益组织,通过网上众筹等方式为非遗项目筹集发展基金,同时也通过网络、微信等新媒介将非遗作为一种文化创意活动,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并将活动所得的部分利润用于公益事业,一方面增加公益创意活动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成为推广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
总而言之,将传统非遗与现代技术相融合,借助城市背景,形成产业集群,并通过法律、制度对非遗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对其传承中发生的问题进行动态的监督管理,同时利用文化元素增强科技产业的吸引力,或者借助非遗传承服务于城市公共事业,形成文化与科技良性互动、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相得益彰、开放性与监管性融合发展的创新型传承模式,是实现非遗传承的必然趋势。
[1]Brian Spooner,“Weaver and Dealers:the Authenticity of an Oriental Carpet”,in Arjun Appadurai 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英]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
[责任编辑:华晓红]
本文系2013年国家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项目“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困境及对策研究”(TYETP201351)的阶段性成果。
杜洁莉,女,副教授,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518055)
G206.2
:A
:1008-6552(2017)04-0053-06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