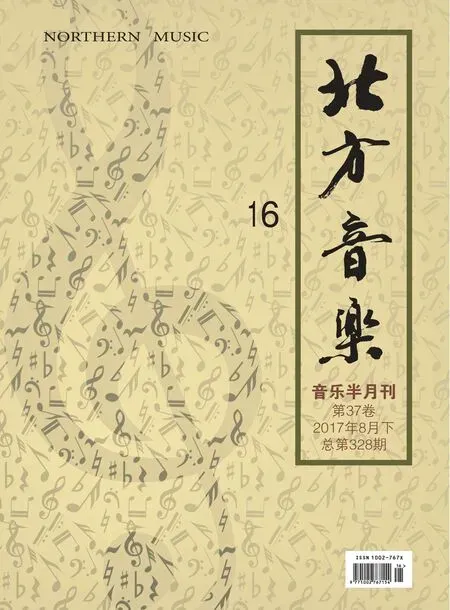论音乐表演的游戏因素
肖金勇
(广东嘉应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论音乐表演的游戏因素
肖金勇
(广东嘉应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在音乐表演实践中借鉴游戏手法渗透进某些游戏因素,又不至于使艺术的精神内涵丧失于游戏的迷宫中。更多地汲取原生态音乐的率真质朴和生命活力,使我们的民族声乐事业在固有的大河中,以多样化的姿态滚滚向前;使我们的美声唱法,在共享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的基础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使我们的流行唱法,在精神气质上与原生态音乐对接,使音乐表演艺术健康地、健全地发展。
音乐表演;游戏因素;游戏性;谐谑之美
艺术与游戏有不解之缘。它们不仅在起源上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在历史的进程中互补互利,携手共进,伴随着人类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今天,并展望璀璨的明天。正如柏拉图在《法律篇》卷七中所指出:“每一个人都要依此为职责。让美丽的游戏成为生活的真正内涵。游戏、玩乐、文化——我们认定这才是人生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事。”[1]
一、音乐表演中的游戏因素
作为一种艺术本体论的“游戏说”,在美学史上正式开始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由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予以发扬光大。“游戏说——用游戏活动揭示艺术起源和审美本质的美学原理。认为游戏在形态上多为对实际生活活动的模仿,在性质上是与纯粹快感相结合的身心自由活动。康德提出‘自由游戏’是审美快感的根源,席勒发展了这一论点,认为艺术冲动是一种‘游戏冲动’,表现为‘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的总和。游戏的根本特性是人性中理性与感性的和谐。游戏的状态即自由审美状态,审美即游戏,艺术起源于这种游戏……朗格认为,艺术是形式成熟的游戏。谷鲁斯认为“艺术是高级的游戏”[2]这是一种从艺术本体论角度出发的游戏观,并非狭义的游戏的释义。是一种宏观的艺术游戏观,是一种审美的游戏观,对于音乐表演来说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积极的启迪作用:在想象力的自由翱翔、理解力的自由驰骋、创造力的自由心境方面给予音乐表演以有益的启发,有利于弘扬音乐表演的诗性品质;游戏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样,音乐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因此,音乐表演要注重生命力的展示和释放;游戏必须遵守游戏规则,音乐表演也要恪守音乐的内在规则及规律,以及音乐表演的规则。游戏活动中,艺术地运用技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也是作为成人游戏主要形式的各种球类运动和下棋等活动,能给我们以乐趣的原因所在。
二、游戏因素在音乐表演中的作用
音乐表演是以技术运用为基础的。在音乐表演中,技术与表达是一对难以把握的矛盾,成功的音乐表演者是把握这对矛盾的高手,技术与表达的辩证统一,技术与表达的和谐融合,是音乐表演的最高境界。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13届青歌赛上,歌手演唱、表演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均与上述三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音乐表演的角度来看,原生态歌手及流行歌手的表演相对于美声唱法及民族唱法的歌手,在想象力的自由翱翔,创造力的自由心境,生命力的展示及释放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相较之下,一些美声唱法的歌手及民族唱法的歌手往往端着架子、绷着脸在演唱,呆板的表演削弱了音乐表演的魅力。以致有人认为“青歌赛”的亮点在于余秋雨评委的文化知识的点评。尽管这种说法有其片面性,但从宏观的艺术游戏观、审美的游戏观的角度来看,一些歌手缺乏超功利的自由心境、放松的表演心态,丰富想象力和理解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青歌赛上,新疆喀什地区原生态组合演唱的《刀郎木卡姆》给人以为之一振的艺术冲击力。他们上台来张口就唱,唱即入情,入情便沉醉,原本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这样率真地歌唱,分不清这是生活状态,还是舞台艺术状态,没有虚情,没有假意,没有包装,没有宣传,生命的活力与张力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正应了那句古话——唯乐不可以为伪。他们质朴、活泼、狂放、自在的演唱及对生命力的展示和释放深深地打动了观众和评委,他们的演唱获得高分自然在情理之中。原始艺术的粗犷的生命张力,质朴的田野气息,活泼生动的游戏冲动,自在自得的愉悦心境应该为被称作为“高雅艺术”的美声唱法及民族唱法“充电”、输血。
与此遥遥相对的是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催生的通俗音乐。作为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的捷径。它的出现,与当代社会历史条件所产生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定位为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所出现的公共艺术的重要门类之一。它的文化、美学函义,可称之为人的还原,美的还原,人类童年的游戏精神的还原。真实的生活往往是具体的,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崇高,也不卑下,于是,它着力为具体的生活立法,把传统认为有意义的东西还原为无意义,又在无意义中展示出新的意义,追寻着具体的缠绵、具体的温柔、具体的伤感、具体的美丽……使人们不再仰望,而是平视;不再说教,而是娱乐;不再敬畏,而是参与,广义的游戏精神和狭义的游戏精神尽显其中。因而,敏捷地激活了人们的生存意识,激活了濒临僵死的传统美学,激活了艺术中的游戏意识,禀赋了一种异常的亲和力。它的自然率真,它的俚俗亲和,它的没有距离感,实现了与原生态歌唱的对接。广义的游戏感和狭义的游戏感是原生态音乐与流行音乐遥相呼应的纽带。《刀郎木卡姆》中那手鼓敲击的强烈个性化的节奏不正是对映着流行音乐中架子鼓震撼人心的节奏吗?原生态演唱中的载歌载舞的形式不正是在流行音乐表演中的大幅度舞动,无拘无束的歌舞中频频“显灵”吗?自由想象的驰骋,自由心境的放飞,创造力的勃发,自娱自乐的游戏精神弥漫于原生态及流行音乐的音乐表演中。
相比之下,两极之中的西方美声唱法及中国当代民族唱法(“青歌赛”上有人称之为“学院派民族唱法”)在音乐表演上游戏因素的缺失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丝毫没有贬低美声唱法、当代民族唱法的意图。传统的美声唱法及当代民族唱法毫无疑问是一种美的结晶。否则,传统美声唱法不会延续几百年,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演唱者所接受,所传承。同样,当代中国民族唱法倘若没有生命力也不会有那么多传承者。它有一批有成就的,为广大听众所喜爱的歌唱家,积累了一批为歌唱家及听众喜爱的曲目,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民族唱法的主流唱法(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这两种唱法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比较科学的,能够系统地进行教学的,有文本积累的声乐艺术。他们的任何一次演唱,都意味着演唱者有数年、数十年的美的声乐训练基础。你一旦听到这种歌声,就会清醒地意识到——留给你的位置是在一定距离外的静静欣赏。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美声及民族唱法的歌手端着架子,绷紧脸面,在功利及技术压力下的非自主、非自在的音乐表演。在这样的音乐表演中艺术的游戏因素则荡然无存,这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音乐表演状况。
我们褒扬音乐表演的游戏因素及游戏性,并不说明我们赞同艺术起源于游戏的观点。游戏只是艺术发生的动力之一,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的劳动生产实践。艺术发生的动力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劳动、情感、巫术、想象、游戏、模仿等等原始社会的一切,他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了一个系统,组成一个合力,推动着艺术的发展。
三、游戏因素与音乐表演的关系
游戏既有广义的概念,也有狭义的概念。这就是具体的游戏。关于游戏,《辞海》的释义是:“体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娱乐的一种。有发展智力的游戏和发展体力的游戏两类。前者包括文字游戏、图画游戏、数字游戏等,习称‘智力游戏’;后者包括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搬运接力等)和竞赛性游戏(如足球、篮球、乒乓球等)。”[3]这种游戏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通过这种游戏使人们得到休息,得到快感,得到愉悦。因而,音乐表演中的游戏因素往往使音乐在美学形态上呈现一种谐谑之美。谐者,诙谐;谑者,戏谑也。它是一种愉快的风格,一种轻松活泼的意趣,也是美学范畴的喜剧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自身(器乐、声乐)在对喜剧的体现中有一定的可能性。适用于音乐的喜剧的范围异常广泛:从无忧无虑的、疏忽大意的、善良的幽默到狂放的嬉戏(如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末乐章);以儿童的恶作剧到怪诞离奇、辛辣讽刺等;从机智幽默、乐观戏谑的木偶片《阿凡提》的主题歌到焦躁、宣泄的通俗歌曲《别挤了》;从调皮、嘲讽的《爱挑剔的大姑娘》到嘲弄、轻蔑,辛辣讽刺的《跳蚤之歌》,都说明了谐谑之美在声乐领域中得到了独特的体现。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各民族民歌的海洋中跃动着具有谐谑之美的浪花。如《回娘家》、《龙船调》、《阿拉木罕》、《大坂城的姑娘》等;表演唱中的《逛新城》、《歌唱光荣的八大员》、《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吉祥三宝》等;舞蹈音乐《洗衣歌》等等。
游戏中十分注重游戏规则,没有规则就不成为游戏,不遵守游戏规则,游戏的愉悦感就丧失殆尽。音乐在结构内部也有严密的规则,在音乐表演上同样有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以相应规则为前提的游戏活动中,技术的运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作为游戏主要形式的各种球类运动和下棋等活动,能给我们乐趣的原因所在。音乐艺术是讲究技术的艺术,技术成熟与否,技术运用的合理与否,技术与艺术表达的融合与否决定着音乐表演艺术的成败。在音乐中要体现游戏因素,取得戏剧性效果也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如故意破坏音乐发展的习惯逻辑,破坏听众感知的既定惯性,节奏上、力度上、音调上的夸大,纠缠不休的反复,“粗野的”对比与夸张的模仿等等,从而营造喜剧性的效果,体现音乐表演的谐谑之美。
我们强调了音乐表演的游戏因素、游戏感,强调了游戏与艺术的深刻联系,但这并不说明音乐艺术、文学艺术等同于游戏。
艺术与游戏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关系。艺术尽管具有某些游戏因素,但根本上并非纯粹的游戏。倘若游戏就是艺术,那么,“为什么早期人类除了游戏活动之外又从中进一步衍生出艺术行为,并且使之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获得进步?”[4]同重在消遣休闲的游戏相比,艺术蕴含更多的精神内涵。与游戏活动中注重当下的欢乐时刻不同,一切艺术创造和意识享受都伴随着心灵内在地提高的状态。“如果我们把艺术与游戏的相似当作等同,将两者一视同仁,那就会遮蔽艺术精神的实质。‘当孜孜不倦地游戏时,便退化为它诞生之初的那种平凡状态。’”“游戏对于艺术的意义其实是搭建一个精神的平台,以便让人们以轻松的方式‘在无阻碍的游戏领域里认识自己。’诸如下棋、打球、躲猫猫、猜字谜,以及开碰碰车、坐过山车等游戏活动,这是我们世俗旅途上不可缺少的无数客栈,而艺术则是我们最后也是唯一的精神家园。”[5]
游戏是“避重就轻”;艺术是“举重若轻”。艺术中具有游戏性,又有对游戏性的拒绝。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辩证地把握音乐表演中游戏性的“度”。我们既要在音乐表演实践中借鉴游戏手法渗透进某些游戏因素,又不能使艺术的精神内涵丧失于游戏的迷宫中。使音乐表演艺术健康地、健全地发展。
我们论述音乐表演中的游戏因素,游戏性,是要人们关注在音乐表演中借鉴某些游戏手法渗透进游戏因素,使我们的音乐表演更具想象的自由翱翔,心境的自由放飞,创造力的勃勃生气,生命力的展示与释放。更多地汲取原生态音乐的生命活力,率真质朴,使我们的民族声乐事业在固有的大河中,以多样化的姿态滚滚向前;使我们的美声唱法,在共享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的基础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使我们的流行唱法,在精神气质上与原生态音乐对接,从而在总体上体现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艺术精神、文化内涵、诗性品质,及技术含量,为人类的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1]加塞尔.什么是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4:67-68.
[2]美学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72.
[3]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099.
[4]徐岱.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01.
[5]徐岱.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02-103.
J604.6
A
肖金勇(1980—),男,汉族,甘肃陇南人,本科,讲师,广东嘉应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研究方向:声乐教学、声乐表演和艺术实践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