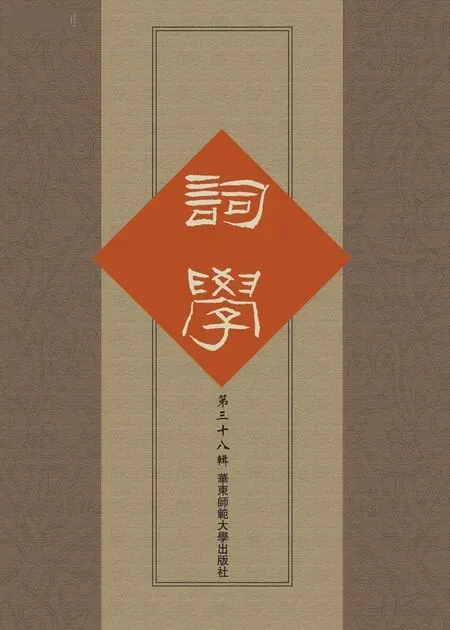别體·正體·破體: 論梁啟超的詞體革新
李曙光
内容提要 詞體革新是詞之發展繁榮的重要動因,梁啟超生當社會大變革之際,在詞體革新上作出了卓越貢獻。其早期詞作,多爲‘别調’,慷慨激昂,豪邁雄直,頗有稼軒之風。中期詞作,深受常州派影響,講究‘比興寄托’,富有言外之意,情思隽永,實屬‘正聲’。晚期詞作,‘破體’爲詞,以白話寫作,是對胡適白話文運動的支持。這一革新,其意義早已超出梁氏早年所提倡的‘詩界革命’之藩籬,對詞體的衍變及新詩的寫作均有深遠影響。
關鍵詞 梁啟超 詞體 白話文
作爲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維新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梁啟超的詞作在其全部創作中只占極小一部分,所以學界向來對其關注不夠。其實梁啟超生當社會劇烈變革之際,其詞作受社會政治、文化之影響,發展演變的軌跡十分清晰,帶有鮮明的新舊文化交融的痕跡。從早期的多爲‘變體’,到中期的追求‘正聲’,至晚期以白話入詞,‘破體’爲詞,可以説梁啟超不僅在文言詞創作上成就粲然,而且在白話詞的創作上導夫先路,爲詞體革新作出了卓越貢獻,對於詞的發展衍變、乃至白話詩歌的繁榮,具有深遠影響。
詞體革新是詞之發展繁榮的重要動因。在千年詞史上,對於詞體的認識向來有正、變之分,論者多以婉約爲源爲正,以豪放爲流爲變。梁啟超對於詞體的認識,也有正、變之别,但是却有自己獨特的視角,這就是情感表現的方法。
梁氏論文學以情感爲核心,爲此他曾專門研究了‘表情法’,將之分爲三類: 奔迸,回蕩,蕴藉。所謂奔迸的表情法,是指情感‘忽然奔迸一瀉無餘的……例如碰著意外的過度的刺激,大叫一聲或大哭一場或大跳一陣’〔一〕。詩如《易水歌》、《虞兮歌》、《大風歌》,詞則有辛棄疾的《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回蕩的表情法則‘是一種極濃厚的情感蟠結在胸中,像春蠶抽絲一般,把他抽出來’〔二〕。這種表情法,在情感的熱烈方面與前者一致,所異者在於‘前一類是直綫式的表現,這一類是曲綫式或多角式的表現;前一類所表的情感,是起在突變時候,性質極爲單純,容不得有别種情感攙雜在裏頭。這一類所表的情感,是有相當的時間經過,數種情感交錯糾結起來,成爲網形的性質’〔三〕。如《黍離》、《柏舟》,杜甫的《春望》、《月夜》,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等。擬諸形容,前者如飛瀑奔流,駿馬下坡,長風出谷;後者似江水盤旋,曲徑蜿蜒,回風激蕩。前者近乎豪邁奔放,後者近乎沉郁頓挫。至於含蓄蕴藉的表情法,‘和前兩種不同: 前兩種是熱的,這種是温的;前兩種是有光芒的火焰,這種是拿灰蓋著的爐炭。’〔四〕
總之,梁氏所謂的‘表情法’,是從情感的强弱及表現的直曲入手分類的;强而直者爲‘奔迸法’,强而曲者爲‘回蕩法’,弱而曲者爲‘蕴藉法’。這就和傳統的風格上的豪放、婉約二分法有所差異,奔迸、回蕩之作和婉約、豪放之作彼此交叉,只要情感濃烈熾熱之作,體性剛者則歸入豪放一派,體形柔者則歸入婉約一派。事實上,在梁氏所舉奔迸、回蕩之作中,就有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周邦彦《蘭陵王》(柳陰直)等婉約作品。當然,梁氏的分類帶有較强的主觀性,如對同一作品情感的强弱,恐易出現各依其心、人人言殊的情况;此外其所分之類亦不能涵蓋所有,如情感柔婉之作在表現上不一定含蓄,對情感柔婉而又表現直接的作品,不知將置於何處?
對於‘表情法’和填詞之間的關系,梁啟超謂: ‘向來寫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爲原則,像那彈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欖的那點回甘味兒,是我們中國文學家所最樂道。’〔五〕‘回蕩的表情法,用來填詞,當然是最相宜;但向來詞學批評家,還是推尊蕴藉,對於熱烈盤礴這一派,總認爲别調。我對於這兩派,也不能偏有抑揚(其實亦不能嚴格的分别)。’〔六〕可見梁氏内心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其本人偏嗜熱烈盤礡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尊重傳統學者對於含蓄蕴藉之作的喜好,所以采取了一種折中的態度。梁氏所論,作於其晚年一九二二年,代表了他比較成熟的看法。本文所言梁氏詞體之正、别,即以此論爲基本出發點,同時參照梁氏創作實際,變其雙重標準爲單一標準,即以含蓄蕴藉之作爲‘正體’、‘正聲’,以爽直明朗之作爲‘别體’、‘别調’。當然這樣做只是爲了論述的方便,並無絲毫褒貶之意。至於梁啟超晚年的破體爲詞,則完全超越了傳統的正變觀念,實爲一種詞體革命。
一 别體: 雄放勁直的‘稼軒風味’
梁氏詞體創作具有鮮明的階段特征,有人將其分爲三個時期: 早期、居日及歸國後。〔七〕筆者認同這樣的劃分,不過出發點不僅僅在於梁氏創作時間和創作主旨的變化,更在於其詞體特征和藝術風格的嬗變。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七年爲梁氏創作的第一階段,其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兩年作品相對較多。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直抒胸臆,極少采用興寄手法,那些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作品,感情熱烈奔放、慷慨激昂,頗得稼軒之風。當然,這是就梁詞的整體特征而言,若從局部而言,一首詞中難免采用比喻、暗示、烘托等手段,但不足以改變其詞體整體亢直的風貌。
爲何梁啟超此一階段的創作多慷慨激昂、雄健亢直的‘别調’呢?這與當時動蕩的社會狀况及作者的自身遭際關系甚大。一八九四年農歷六月,中日甲午戰争爆發,當時梁啟超寓居北京,‘憂憤時局,以人微言輕,無從爲力,遂遣妻歸寧貴州。十月,歸廣東’〔八〕。次年二月,復同康有爲返京應考,恰值清廷戰敗,朝野震恐,清廷決議割讓遼、臺,並賠款兩億兩,於是康、梁等人鼓動各省公車上書,拒簽和議,而會試亦因此下第。據梁啟超弟梁啟勛載: ‘是歲春闈,乃順德李若農典試,誤於伯兄之試卷爲南海之作,故抑而不録,批曰: “還君明珠雙淚垂,惜哉!惜哉!”’〔九〕國變之禍,不遇之悲,使梁啟超内心憂憤深廣,發而爲詞,便湧現出一些辛棄疾式的慷慨悲歌的‘壯詞’。
梁啟超對稼軒可以説是終生服膺,極爲推崇,爲此花費很大精力,綜合運用各種研究方法進行稼軒詞研究。他不僅以大量的詞話、評點,表達了對稼軒詞的認識,而且又以專題論文,從藝術審美的角度對稼軒詞的情感表達作了較爲系統的分析。到了晚年,他又開始從文獻學入手對辛棄疾進行全面研究,先後作有《跋四卷本稼軒詞》和《跋稼軒集外詞》,前文詳考四卷本源流優劣,後文采集稼軒四十八首佚詞並加考辨。然後著手編述《辛稼軒先生年譜》。梁氏研究稼軒的目的,是要將‘整個辛棄疾’公之於世。他認爲: ‘稼軒先生之人格與事業,未免爲其雄傑之詞所掩,使世人僅以詞人目先生,則失之遠矣。’但是稼軒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畢竟是由其詞作而奠定,所以梁氏對稼軒的文學成就自然極爲關注。他認爲‘詞中用回蕩的表情法用得最好的,當然要推辛稼軒。稼軒的性格和履歷,前頭已經説過: 他是個愛國軍人,滿腔義憤,都拿詞來發泄;所以那一種元氣淋漓,前前後後的詞家都趕不上。’〔一一〕由此看來,梁氏最欣賞的是稼軒詞的‘滿腔義憤’和‘淋漓元氣’,無怪乎梁氏的早期詞作具有一種‘長歌當哭’的悲慨和‘金戈鐵馬’的氣勢。
梁啟超這一時期所創作的‘壯詞’,較有影響的有《水調歌頭》(拍碎雙玉斗)、《滿江紅·贈魏二》、《念奴嬌·壽何梅夏》、《蝶戀花》(法界光明毛孔吐)等,悲壯中寓豪邁,沉郁中見昂揚,確實有一種沛然之氣。兹以《水調歌頭》爲例:
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爲銷磨。願替終生病,稽首禮維摩。
此詞一本於詞牌後有‘甲午’二字,據此當作於一八九四年甲午戰争爆發之後。作者痛感朝廷腐敗,國事日非,而自己却懷玉見棄,無緣報國,因此慷慨悲歌,筆力矯健,氣勢宏偉,直如黄鐘大吕。這是現存梁啟超詞中編年最早的一首,時年作者二十二歲,而襟懷、才氣赫然可見,頗有稼軒氣度。
除了得‘稼軒體’的沉雄,梁啟超詞還頗具稼軒詞的博大,主要表現爲詞匯、典故的包羅萬象。稼軒把東坡開創的恣肆豪縱的語言風格繼續向前推進,東坡詞‘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一二〕。到了稼軒那裏,則‘别開天地,横絶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説》、選學、李杜詩,拉雜運用,彌見其筆力之峭’〔一三〕。梁詞在質和量上當然都無法比肩稼軒,但是仍能看出博大恢弘的氣象,其語言不僅有詩詞語,而且有經史語、佛道語,乃至神話語、小説語,等等。他的詞多處化用《詩經》、《楚辭》、白居易詩、李商隱詩、辛棄疾詞等詩詞。〔一四〕此外,引用史籍的也頗多,如《水調歌頭》(拍碎雙玉斗)中‘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出自《史記·項羽本紀》,《滿江紅·贈魏二》中‘使不盡,灌夫酒’出自《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屠不了,要離狗’出自《史記·刺客列傳》,‘鏡中應詫頭顱好’出自《通鑒·隋紀》,《念奴嬌·壽何梅夏》中‘只恨犖犖頭顱,顢頇髀肉’出自《三國志·蜀志·先主傳》,‘叢社鬼謀’出自《史記·陳涉世家》。至於佛家語,亦頻頻用之。根據初步統計,‘“維摩”、“塵勞”、“泥犁”等佛家語在詩中被使用七十多次,在詞中亦不下十五次’〔一五〕。其《蝶戀花》(法界光明毛孔吐)更是幾乎通篇釋家之語。(當然,這裏的統計包含了梁氏流亡日本及歸國之後的部分詞作,也包含了梁氏除‘稼軒風’之外的部分詞作,但是它們數量有限,並不影響對問題本質的判斷。)事實非常清楚,梁啟超師法‘稼軒體’的詞作,在語言上確實具有一種包羅萬象的氣度。
不過此期的梁詞學稼軒多少有些欠缺火候,豪壯有餘,精細不足,未免遺人粗豪之譏。論家公認稼軒詞豪中見細,如蔡嵩雲謂: ‘稼軒雖接武東坡,而詞之組織結構,有極精者,則非純任自然矣。’〔一六〕謝章鋌云: ‘學稼軒,要於豪邁中見精致。’〔一七〕以梁氏所推崇的稼軒《賀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爲例,此詞開篇連用鶗鴂、鷓鴣、杜鵑等意象渲染悲劇氣氛: ‘緑樹聽鶗鴂。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覓處,苦恨芳菲都歇。’然後以‘算未抵、人間離别’一抑,隨即推出四個與生離死别相關的典故。煞拍又以鳥鳴結束,呼應開頭: ‘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這首詞首尾描寫現實景致,中間敘寫歷史事實,在結構上收放自如,法度謹嚴;對鳥啼的描寫則將全篇籠罩,營造了情景交融、渾融完整的意境。而梁啟超的豪壯之詞,則純以氣勝,情之所至,信口而出,猶如漢魏古詩作法,像‘鐵骨酣霜,繡腸織月,簫劍雙無價’(《念奴嬌·壽何梅夏》)等句,尚能情中帶景,至於‘炯炯一空餘子目,便便不合時宜肚’(《滿江紅·贈魏二》)、‘熱血一腔誰可語?哀哀赤子吾同與’(《蝶戀花》(法界光明毛孔吐)),則過於直白,略無形象可言了。
二 正體: 興寄幽微的‘芳草美人’
梁啟超第二階段的創作是在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二年間。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寄居海外的生涯,其間數次往返於中日,並遊歷臺灣等地,直至辛亥革命後,始於一九一二年十月歸國。此一時期梁氏詞體創作的一大特點,就是開始注重抒情的藝術。他在《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極力推崇情感的價值,指出爲了更好地實現情感教育,藝術家‘最要緊的工夫,是要修養自己的情感,極力往高潔純摯的方面,向上提絜,向裏體驗,自己腔子裏那一團優美的情感養足了,再用美妙的技術把他表現出來,這才不辱没了藝術的價值’〔一八〕。這裏明確提出藝術家應該注重表達的‘美妙的技術’。不過在創作的初期,梁啟超積極投身於變法維新的浪潮,無暇在表達技術上精雕細琢,這個功課要到他寓居日本時才有精力完成。
梁氏此一時期的作品,廣泛學習兩宋名家,詞人具備了强烈的‘效體’意識,對前人諸體進行了有意識的效法模擬,其中明確標示名目的‘效體’或‘用韻’(‘用韻’實際上也是一種‘效體’)之作有五首,所效之體或所用之韻有: (一)清真體(《六醜》);(二)草窗韻(《三姝媚》);(三)美成韻(《西河》);(四)玉田韻(《念奴嬌》);(五)夢窗韻(《八聲甘州》)。可以看出,梁啟超對浙、常兩派所推崇的詞家都曾模擬學習,其不拘一格、轉益多師的意識還是很强烈的。不過這並不等於對各家一視同仁,從其創作實踐來看,他對常派接受更多,這是與其思想觀念、審美情趣相一致的。
清代以張惠言、周濟爲代表的常州詞派主張‘比興寄托’、‘意内言外’,較爲重視詞的社會功能,這對於以宣傳變法革新、‘改造國民之品質’爲己任的梁啟超來説,自然一拍即合,心有戚戚焉。梁氏與常州派的關聯主要體現爲: 首先,梁啟超論詩詞亦主張比興寄托,如其在《飲冰室詩話》裏曾説: ‘美人香草,寄托遥深,古今詩家一普通結習也。’〔一九〕(梁氏所謂的‘詩’,多就廣義言之,包括詞在内。如其曾在《〈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中言: ‘中國有廣義的詩,有狹義的詩。狹義的詩,“三百篇”和後來所謂“古近體”的便是。廣義的詩,則凡有韻的皆是。所以賦亦稱“古詩之流”,詞亦稱“詩餘”。’)在《遊臺灣書牘》第六信中説: ‘復有詞數闋,托美人芳草以寫哀思。並以寄上,試請讀之,或可喻其言外之意耶。’其次,梁啟超對常州派認同的詞家頗多推崇。如梁氏之女令嫻編選《藝衡館詞選》,在‘例言’中謂: ‘詞之有宋,如詩之有唐。南宋則其盛唐也。故是編所鈔以宋詞爲主,南宋尤夥。清真、稼軒、白石、碧山、夢窗、草窗、西麓、玉田,詞之李、杜、韓、白也。故所鈔視他家獨多。’〔二一〕常州派推崇的四家悉數‘隆重推出’,編選宗旨於此可見。劉逸生更爲明確地指出: ‘《藝衡館詞選》選輯於光緒末年,正當社會變革日烈之際,編者自然受到常州派理論的影響,接受了該派的“意内言外”之説,强調詞的比興、寄托的作用(選者把温庭筠作品選了二十一首,還把張惠言的評語全部抄録,就是明證)。而同時對於周濟等人推尊的周、辛、王、吴也作爲重點作家選入。選取周、辛、王、吴,四家之詞共九十一首,加上補遺的吴文英十三首,共達一百四首,竟爲所選宋詞的三分之一。那就可見選者的趨向了。’〔二二〕而梁令嫻編選《藝衡館詞選》,明確説過是在其父指導下進行的,故此書也可看作梁啟超詞學觀念之體現。
梁啟超不僅在理論上接受常州派的影響,而且在實踐上也步武常州派的楷式。他此一時期的詞作,大都以‘芳草美人’寫家國情懷,憂時傷世,纏綿悱惻。詞人對此亦不避諱,屢屢言及自己的興寄之旨,如《六醜》(聽徹宵殘雨)序云: ‘庭院碧桃,開三日落矣,借寓所傷。後之讀者,可以哀其志也。’《鵲橋仙》(墜歡依約)自注云: ‘此二詞皆頗有寄托,想一讀能解之。’《蝶戀花》(感春)組詞: ‘臺人多有欲脱籍歸故國者,故第四首及之。其第五首則當英俄邊境正劇時,故不自覺其詞之哀。實則中國若亡,則吾儕將來之苦况,又豈止如臺灣人哉!’〔二三〕兹以《六醜》爲例以窺一斑:
聽徹宵殘雨,正簾外、曉寒衣薄。莫道春歸,便濃春池閣,已自蕭索。問歲華深淺,愔愔桃葉,在舊時欄角。繁紅鬥盡無人覺,待解尋芳,東風已惡。歡期未分零落,尚曲墻扶繞,頻動春酌。 情懷如昨,只休休莫莫。似水流年,底成漂泊?故枝猶綴殘萼,又蜂銜燕蹴,乍欺怯弱。愁對汝、自扃深閣。却不奈、一陣輕飈無賴,送敲垂幕。感啼鳥、未抛前約,向花間、道不如歸去,怕人瘦削。
作者自序此詞‘傷春’,從表面看,確實如此,但實際上該詞蕴含著對國事的深切憂慮,蕭索的春天實爲變法失敗後形勢之寫照,無情的東風則是慈禧太后等頑固派之象徵。需要指出的是,詞人並没有采取簡單比附的方式,將其寫成一篇字謎,破壞小詞圓融完整的意境,而能做到興象玲瓏、不落言筌,深得羚羊掛角之妙。
爲了保持詞體本色,梁啟超常選用柔媚的意象言志抒懷,除了常見的‘殘春’意象(如《蝶戀花·感春》六首)之外,又以幽蘭象喻孤高幽獨的逸民(《高陽臺·題臺灣逸民某畫蘭》),以鄭成功祠前的古梅象喻被日本侵略蹂躪的臺灣人民(《暗香·延平王祠古梅,相傳王時物也》),等等。這些詞作,廣泛吸收了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的藝術營養,用典使事‘體認著題,融化不澀’。而其情感之郁勃,尤令人動容。如《金縷曲》:
瀚海漂流燕。乍歸來、依依難認,舊家庭院。唯有年時芳儔在,一例差池雙剪。相對向、斜陽淒怨。欲訴奇愁無可訴,算興亡已慣司空見。忍抛得、淚如綫。 故巢似與人留戀。最多情、欲黏還墜,落泥片片。我自殷勤銜來補,珍重斷紅猶軟。又生恐、重簾不捲。十二曲闌春寂寂,隔蓬山何處窺人面。休更問,恨深淺。
這首詞以漂泊天涯的燕子象征流離失所、眷戀祖國的詞人,抒發了對國事的深沉感慨。以燕子寫飄零之感,《詩經》時代即有,《邶風·燕燕》云: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宋詞中的名篇則有周邦彦的《滿庭芳》: ‘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來寄修椽。’至於以燕子抒興亡之恨,唐代劉禹錫的《烏衣巷》最爲有名,宋詞則有周邦彦的《西河》: ‘燕子不知何世,向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説興亡斜陽裏。’這些是本詞‘瀚海漂流’、‘差池雙剪’、‘算興亡已慣司空見’等語所本。但是本詞並非一味模擬,相反帶有鮮明的梁氏印記,這突出表現在燕子不再是冷眼旁觀歷史興亡的形象,而變成了一個熱切的建設者,它修補故巢,‘欲黏還墜,落泥片片’分明就是補天的女媧和銜海的精衛,拳拳愛國之心真是感天動地。它的‘淒怨’、‘奇愁’、‘淚如綫’,無不顯示作者心中感情的沉郁深厚,但是此時的詞人却不像早期那樣任由情感傾泄而下,而是以比興手法,寫鸞婉之情,頗有要渺幽深之致。
三 破體: 白話入詞的詞體革命
梁啟超第三階段的創作是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這一時期的創作雖然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不如第二階段,甚至不及第一階段,但就在詞史上的意義來講,却遠遠超過前兩階段。如果説前兩階段主要是繼承前人的藝術成果,按照傳統體式的審美規範進行寫作,那麽這一時期則是‘破體爲詞’,以白話入詞,在詞體革新上堪稱革命之舉。
梁氏此一時期的詞作以白話詞爲主,語言通俗,自然率真,頗有返璞歸真之妙,其中有些作品還具有較高的藝術性,比如這首《虞美人·自題小影寄思順》:
一年愁裏頻來去。淚共滄波住。懸知一步一回眸。嵌著阿爺小影在心頭。 天涯諸弟相逢道。哭罷還應笑。海雲不礙雁傳書。可有夜床俊語寄翁無?
思順即作者長女梁令嫻。首句作者自注: ‘小女去年侍母省婿跋涉海上數次。’‘天涯諸弟’,謂思成、思永,時二人在美留學,思順則偕思莊在加拿大。詞作在動作、神態及心理描寫上惟妙惟肖,質樸感人。
雖然白話詞在詞體草創之際即已存在(比如敦煌曲子詞),但是從唐代到清末民初,詞體所面臨的文化背景和創作環境已經完全不同,文人詞和文言詞早已雄踞詞壇千年之久,所以易文言爲白話,絶非等閑之事。梁啟超這樣做,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胡適白話文運動的呼應與支持。
一九一七年,胡適著《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新青年》,標志著文學革命及新文化運動的正式發軔。在此文中,胡適提出‘八事’,關於‘不避俗字俗語’一條,胡適斬釘截鐵地指出: ‘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注略)。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注略),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二四〕此後的實踐證明,正是這一條成爲文學革命取得成功的關鍵。胡適不僅大力提倡白話文學,而且積極寫作白話作品,欲以親身實驗來驗證自己的觀點。一九二年《嘗試集》出版,一石激起千層浪,贊成者有之,批判者有之,一時議論紛紜,大有水火不容之勢。當時梁啟超尚在歐洲遊歷,國内一幫守舊文人寄希望於梁氏,‘方望梁歸,有以正之’〔二五〕。但是梁氏歸國之後,得觀胡詩,極爲欣賞,遂向胡適去信表示祝賀: ‘《嘗試集》讀竟,歡喜贊歎得未曾有,吾爲公成功祝矣。’〔二六〕以梁氏在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他的這一表態對白話詩的發展推動之大,可以想見。爲何梁氏對白話文運動如此贊賞呢?有論者以爲: ‘其一,早在世紀初年,梁啟超即已高舉“詩界革命”的大旗,認爲文言向俗語轉化、書面語向口語靠攏是大勢所趨……其二,梁啟超時代感極强,白話新詩乃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部門,與新國新民新時代共命運,對此,梁是朦朧地意識到了的。他之贊賞《嘗試集》,乃是其緊跟時代的表示。’〔二七〕此話大體不錯,但須辨明的是,梁氏當年提倡俗語,主要是就小説、戲曲等俗文學而言;對於詩歌,並不曾主張白話寫作。以白話入詞,早已超出其當年‘詩界革命’的範疇,體現出巨大的進步。
‘詩界革命’的内涵,在梁啟超那裏曾經歷了一個微妙的調整。梁氏最早明確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是在其一八九九年所作的《夏威夷遊記》中: ‘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余嘗戲名詞章家爲鸚鵡名士,自覺過於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然後可……欲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爲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二八〕但是以‘新語句’入詩,則必致難有純正的‘舊風格’,所以在一九二年後,他在《新民叢報》上陸續發表詩話(即後來結集出版的《飲冰室詩話》),多次言及‘詩界革命’,對之前的觀點作了修正,摒棄了‘新語句’的提法,如謂: ‘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二九〕‘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喜,然必非詩之佳者,無俟言也。’‘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三一〕梁氏關於‘詩界革命’的表述,被簡稱爲‘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可見,其革命的主要精神在於‘意境’、‘精神’,而非‘風格’、‘形式’。這與胡適的‘文學革命’重在語言和文體是迥然不同的。所以反觀梁啟超留日期間的詞作,純以舊風格寫之,彼時梁氏雖提倡‘詩界革命’,其實質不過‘改良’而已;但其第三階段的創作,以白話填詞,則開創了嶄新的風格,堪稱真正的‘詩界革命’。
但是梁啟超和胡適在如何創作白話詩詞上並非完全一致,比如在詩歌的音韻問題上,胡適認爲: ‘詩的音節全靠兩個重要分子: 一是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至於句末的韻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三二〕他强調節奏和詞句的‘自然’,並不在意是否押韻和辨别平仄。關於用韻,他認爲有三種自由: (一)用現代韻;(二)平仄互押;(三)有韻固然好,没有韻也不妨。〔三三〕總之,要來一場‘詩體的大解放’。相較於胡適的完全解放,梁啟超顯得有些保守,他認爲: ‘格律是可以不講的,修辭和音節却要十分注意。因爲詩是一種技術,而且是一種美的技術。若不從這兩點著眼,便是把技術的作用,全然抹殺,雖有好意境,也不能發揮出價值來。……音節是詩的第一要素,詩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賴乎此。’〔三四〕‘我雖不敢説無韻的詩絶對不能成立,但終覺其不能移我性。韻固不必拘定什麽《佩文齋詩韻》、《詞林正韻》等,但取用普通話念去合腔便好。句中插韻固然更好,但句末總須有韻,自然非句句之末,隔三幾句不妨;若句末爲語助詞,則韻挪上一字(如“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我總盼望新詩在這種形式下發展。’〔三五〕
梁啟超的白話詞,基本實踐了他的理論主張。點檢其白話詞,如《虞美人·自題小影寄思順》、《鵲橋仙·自題小影寄思成》、《好事近·代思禮題小影寄思順》二首、《沁園春·己巳送湯佩松》等,可以發現在節奏和音韻等方面,它們具有如下特點: (一)嚴格按照詞牌規定,做到‘詞有定句,句有定字’。(二)基本按照詞譜要求處理字音平仄,但是並不墨守成規。如以《欽定詞譜》爲則進行比勘,《虞美人·自題小影寄思順》有兩字不合平仄(‘諸’、‘不’),《好事近·代思禮題小影寄思順》第一首也有兩字不合(‘四’、‘麽’)。(三)在韻脚上,平仄通押的現象十分普遍,且偶有出韻者。如《鵲橋仙》(冷瓢飲水)四個韻脚字,‘和’、‘過’、‘麽’皆屬於《詞林正韻》第九部,而‘錯’則屬於第十六部。(四)基本不用拗句,亦有極少之例外,如《鵲橋仙》詞,末尾的七字句通常作‘三四’頓,而梁氏《鵲橋仙》(冷瓢飲水)則作‘五二’頓: ‘寄不去的愁,有麽?’可見梁氏的白話詞在音韻格律方面雖有突破,然以繼承爲主,對傳統和經典體現出較爲尊重的態度。
如何正確看待梁、胡二人在對白話詩詞要求上的差異?現在看來,胡適的主張未免有些‘矯枉過正’,但是在當時文言詩歌盤踞詩壇、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不如此不足以收大功效,不能夠獲大勝利。對此,他應該是有清醒認識的。就像他主張‘全盤西化’是考慮到在推行過程中的‘自然磨損率’一樣〔三六〕,胡適主張‘詩體的大解放’也未嘗没有考慮到其‘自然磨損率’。作爲一種革命策略,胡適的主張在當時予人石破天驚之感,從而得以完成其以文學爲載體的思想啟蒙運動。其實胡適並非一味的‘破壞’,他也有‘建設’,爲此曾作《建設的革命文學論》,其《嘗試集》中也有對新詩音節、韻律的建設性‘嘗試’,所以有論者認爲: ‘胡適既認定由其發軔的“文學革命”與歷史上“無意的演進”不同,而以“有意的主張”爲特點,並以之爲“這個運動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因此,胡適的“文學革命”論也應該用他後來的表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來指稱,才更近實際。’〔三七〕但可惜的是,胡適的‘破壞’之影響,遠大於‘建設’之影響。今天的新詩寫作,其成就斐然,自然有目共睹;而其亂象叢生,亦毋庸諱言。這一切都與胡適關係甚大。而梁啟超則采取較爲謹慎的態度,其白話詞相對於文言詞,既有破壞,又有建設,因此對我們今天的新詩寫作不無借鑒意義。
首先,要重視新詩的詩體建設。新詩誕生已有百年,然而對於詩體建設,迄今仍無共識。有人認爲新詩之‘新’,即在於其寫作的高度自由,所以不應有任何格律和形式對其加以約束和規範,應該‘放開天足’,大膽馳騁,再也不能回到舊體詩、詞、曲的老路。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清醒地認識到,新詩必須加强詩體建設。實際上,不走老路,固然正確,但這並不意味著新詩可以否定詩體建設,因爲自由與規則從來就是辯證統一的,形式的過度膨脹使得詩歌和散文等文體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從而抹煞了其獨特的審美性,取消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時至今日,新詩創作出現了一些不良現象,晦澀的説理詩、粗劣的口水詩大行其道,完全無視詩歌的審美個性和體制特征,不能不讓人深以爲憂。
其次,要加强對古典詩歌的學習。新詩雖以漢語寫作,却主要脱胎於西洋文化,因此國人極易與之産生隔膜。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意識和文化趣味,它們早已内化成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並不會因一場新文化運動而被消滅。這就要求新詩寫作決不能割裂和傳統的關聯,必須向古典詩詞汲取營養,從而創造出既有時代特色又有民族風格的優秀作品。實際上,早在胡適《嘗試集》剛出版時,就有人抱怨無韻的詩不容易記。而新詩史上的經典,大多帶有民族美學的質素,像郭沫若的《女神》帶有《離騷》氣象,冰心的《繁星》、《春水》具有小令風神,等等。正確的道路,必須做到古今融合,中西聯姻,而梁氏對經典的尊重無疑是值得今人學習的。
因爲帶有嘗試的性質,梁氏的白話詞數量較少,在意境的塑造及藝術的開拓等方面亦有明顯不足,但是他所開創的以白話入詞的道路,爲詞體注入了新的活力,對今日新詩寫作也不無啟示,在詞體革新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二〕〔三〕〔四〕〔五〕〔六〕〔一一〕〔一八〕梁啟超《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梁啟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九二二頁,三九二五頁,三九二五頁,三九三九—三九四頁,三九二二頁,三九三二頁,三九三二頁,三九二二頁。
〔七〕〔一五〕鄧菀莛《梁啟超詞的分期、特色及其情感基調》,載《中國韻文學刊》二一四年第四期,第七二頁,七六頁。
〔八〕〔九〕汪松濤《梁啟超詩詞全注》,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四七三頁,四九一頁。
〔一二〕劉辰翁《稼軒詞序》,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二一頁。
〔一三〕吴衡照《蓮子居詞話》,《詞話叢編》第三册,中華書局一九八六版,第二四八頁。
〔一四〕閆繼英《梁啟超詩詞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二八年,第七三—七四頁。
〔一六〕蔡嵩雲《柯亭論詞》,《詞話叢編》第五册,中華書局一九八六版,第四九二頁。
〔一七〕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詞話叢編》第四册,中華書局一九八六版,第三三三頁。
〔二一〕梁令嫻《藝衡館詞選·例言》,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二二〕劉逸生《藝衡館詞選·前言》,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二五〕李肖聃《星廬筆記》,嶽麓書社一九八三年版,第八三頁。
〔二六〕〔三五〕杜春和等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二三四頁,第一二三六頁。
〔二七〕董德福《回觀梁啟超與胡適關於白話詩的意見分歧》,載《江蘇社會科學》二二年第五期,第一七九頁。
〔二八〕梁啟超《夏威夷遊記》,《梁啟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一九頁。
〔三二〕〔三三〕胡適《談新詩》,《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三九二頁,第三九五頁。
〔三四〕梁啟超《〈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梁啟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四九二八頁。
〔三六〕楊萌芽《傳承與斷裂—梁啟超與胡適思想之若干比較》,載《蘭州學刊》二六年第九期,第三八頁。
〔三七〕夏曉虹《胡適與梁啟超的白話文學因緣》,載《學術界》二六年第五期,第五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