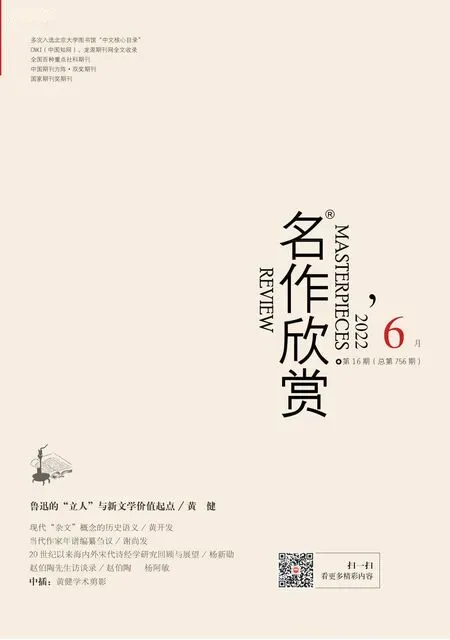刘芳坤《代际风景·跋》
天津 艾翔
刘芳坤《代际风景·跋》
天津 艾翔
曾有好友形容刘芳坤“女酒鬼、死文青、假名流”,我以为此人不做批评家可惜了,如此精准、精练的概括,让后来我们再对她做出描述时都显得多余不讨好。不过话说回来,想要深刻认识刘芳坤应该也并不是难事,作为一个真挚到几乎没有任何城府的人,她的内心势必不用花费太多心思就能搞明白,换句话说,她有一个善结人缘的好性格。
刘芳坤是我的同门师姐,我们认识已经六年。2013年9月,在刚入学的一段时间里,她多次找我“约谈”,了解我的情况,并为我出谋划策。慢慢地我辨清了她和密友杨晓帆之间的性格差异,晓帆师姐温婉,大脑回路异于常人,虽然语速高效但出口之前已经在脑中过了初稿、校稿和定稿,极可能地把建议包裹上令人舒适的糖衣;芳坤师姐完全相反,心里怎么想立刻脱口而出,完全假定听者的心跟她一样宽大。有一次我在讨论课上遭受了一万点伤害,心灰意冷地跟她说:“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做科研。”因为当时正在学院博士生办公室例行帮忙,重压之下一度产生行政工作就是好的想法,未料刘芳坤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不做科研还能做什么?”一句更严厉的刺痛瞬间掩盖了之前的创伤,也见识了刘芳坤式的直接爽达。
如此直接地回击我,一方面出于性格,另一方面也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希望我也同她一样不抛弃不放弃。读博后第一个“五一”,我去香港玩,回来后问芳坤师姐:“你去香港最想要化妆品还是禁书?”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禁书!”我回宿舍还跟舍友开玩笑:“女博士果然更接近博士的属性。”再后来经历失恋,被师姐得知,以为她要跟我做一番伟大光明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导我舍小家、保大家,或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类,没想到她一脸邪恶地说:“看你心情不好,给你推荐本书看看?”我接过来一看,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书系之一《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伴我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时光。可见,虽然是女文青,但并不“小娇羞”,将“女酒鬼”放在第一称谓实在准确不过了,刘芳坤身上确有种酒神精神。这一点是得到导师马俊杰教授认可的,马老师虽然海量,但门下弟子大多不沾酒,马老师评价:“芳坤酒量是最好的,艾翔跟芳坤差不多。”老师的鼓励非同小可,毕业前夕,刘芳坤一边自酌自饮,一边修改博士论文,一时传为美谈。
虽然平日大大咧咧,但写起论文来瞬间变得一丝不苟。我至今仍然以为《诗意乡村的“发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80年代文学批评》是刘芳坤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充分体现了她的文学史研究水平。刘芳坤与知青文学结缘,这篇论文的撰写是一个重要节点,以致她一度想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足见准备之充分。这篇论文符合人大课堂“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论指引和“小题大做”的操作惯例,没有局限于一部中篇小说的再解读,视野远远超出了作品,将其置于整个知青文学史乃至知青史的宏大框架内展开讨论,显得气象非凡,底气十足。同时另一方面,论文又溢出了文学史研究,通过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赋义,倒追“知青”内涵的变迁,从而对这一历史名词的政治意涵发出责难。这种精神正是许多人所一直期待的,突破既定概念的束缚,走进真正的生活或历史,放弃如此,才能谓之“独立”。
虽然最终博士论文选题发生了变更,很大意义上是在完成一项建构性的论述,但刘芳坤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素养和知青相关的知识储备很好地填充进了最终的成稿。《诗意乡村的“发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80年代文学批评》指向的是过往知青(文学)含义的变迁,站在20世纪80年代向过去看,《城与人》则针对当下作为“身份”走进新时代的“知青”,站在八九十年代向未来看,前后视角刚好衔接,表面无关的主题,却有一条隐含的红线贯穿刘芳坤的思考脉络。
当然,女博士与女人相比,“博士”是第一属性,但与男博士相比,“女人”就成了第一属性。虽然刘芳坤的性别意识在毕业后才显著彰显,这或许同儿子的降生密切相关,但之前并非毫无征兆。《女知青爱情叙述的失效——从〈分界线〉到〈北极光〉看1980年代文学的起点性问题》从情感的角度分析历史的演进,《从张爱玲到王安忆:服饰描写中的历史观》从服饰描写角度区分批判的张和认同的王、悲凉的张和淡然的王,其实正是女性视角的显现,在动辄从政治运动、社会思潮、历史文献铺展历史观照的一般性套路大格局下,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刘芳坤论文的另一个性别特点是流畅明快的语言,同艰深晦涩的理论思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感。或许正是这一原因,从北京再回山西后,她一手抓学术研究之外,一手又抓起了文学批评,换挡过程平滑无顿挫感。在文学评论的写作中,她特别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同一些作家、期刊编辑、出版社编辑以及同行批评家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并逐渐产生了自己的影响。《“80后”的爱欲与文明——压抑性富裕期的城市文学表达》放肆地谈论着长辈眼中仍未长大的青年们的性爱问题,其实触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她看来,性爱的自由自主自觉同主体意识和身份息息相关,前者可以视为后者的表征。城市对人的压制直接体现为性爱的扭曲,不由让人想到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提到的一个事例,他与李陀一道去合租屋走访,疑惑年轻夫妇根本不具备性爱的条件。城市对个体性爱自由的挤压背后是一个自然人性遭到异化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芳坤推崇孙频的创作,虽然面对现代化等级秩序格局下的城市的步步紧逼,难免有所退让,但孙频依然摆出一副不屈不挠的抵抗姿态,甚至不惜令人物成为精神疾病患者,呈现出一种反英雄的悲剧英雄意味。或许在这一类文学评论中,历史维度较之其学术论文稍显单薄,但却支撑起了强劲的对每个普通个体的人文关怀。这样来看,刘芳坤的学术研究和新作时评乃是一种相互滋养的关系,让她笔下的文学永远是厚重又亲切的“文学”。
这部论文集是刘芳坤这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一次总结,她的关注点分布面广,然而收集起来后却有一种奇异的效果:作为焦点的“知青”和“文青”并列,一方面是对我们的父辈和同辈的同步观测,另一方面是外呼应总题,努力为“代际”作为研究视角去污名化,展示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和融通性。将前人也统筹进这一概念,不失为一种叛逆行为。不过对于刘芳坤来说,任何稀奇古怪的举动都有可能发生。如今提及山西,人们最先联想到的便是醋,往往将多年前走红过的汾酒抛诸脑后。刘芳坤身上有精神性高蹈的汾酒,也有日常性凡俗的陈醋,她还敢往汾酒里勾兑陈醋,让你记住,混合过的味道,才是文学。这样看来,她是女酒鬼和死文青,但却是真名流。
2016年9月18日
于借调岗位上的开小差中
作 者:
艾翔,青年评论家,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