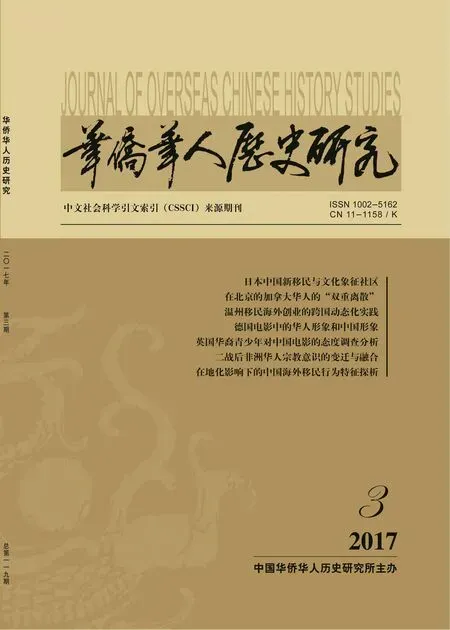在地化影响下的中国海外移民行为特征探析*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 100007)
在地化影响下的中国海外移民行为特征探析*
黄纪凯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 100007)
移民研究;在地化;行为特征;社会融入;边缘性杠杆;中外交流
论文阐释了“在地化”的概念界定和移民在地化表现并对“在地化”的几个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论文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在海外生存发展,为住在国家和祖籍国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还处于“两头不是人”的尴尬境地。缘于生存需要,移民对移居地(国家)有利益从属性,由此构成移民行为的一般规律。将移民在地化与边缘性杠杆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地化是中国海外移民形成对中外双方而言具备居间比较优势的前提。通过撬动边缘性杠杆,中国海外移民一直在为提升自我的同时发挥着促进中外交流的社会历史作用,进而充分体现出其爱国情怀。
就世界范围而言,选择移民的民族有很多,数量也很大,移居地域也不尽相同。作为世界移民的一部分,中国海外移民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他们日趋活跃,从而引起国内外各方关注。那么,他们的群体行为特征与其他族裔的移民是否有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又会产生什么影响?相应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海外移民的尴尬处境
从历史上看,中国海外移民曾被封建王朝视为“自弃祖宗坟茔之人”,抓住要被杀头,即使后来朝廷转变态度,也多缘于他们比较富有,可以成为官方的财源之一。在移居地,中国移民也经常受到歧视、排斥、打击甚至屠杀,如著名的“红溪惨案”。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六年(1741)四五月间,侨居于噶喇吧(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华人遭到荷兰殖民者残酷杀害的消息在福建侨乡引起震惊。[1]当时署福州将军策楞和署福建巡抚王恕联名上奏道:“(该番)随于是夜(十九日)大肆凶恶,闭城放炮,四处放火。至(八月)十九日,城内汉人无论老幼,俱被戕害。即城外居住者,亦为赶杀甚多,约伤万余人。余皆逃往网加屿藏匿”。[2]在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也发生过类似排华事件,当地政府甚至运用法律手段实施排华政策。
时至现代,印尼曾数次发生大规模的排华行为,有些国家也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形式实施排华或限制华人政策,还有些国家将历史上曾经生效的排华法律延续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方才废止。有学者用“替罪羊现象”概括对移民的排斥。“‘替罪羊现象’指当一个国家的国内危机或国际矛盾激化时,该国政府或公民往往将社会中某一有关联的非主流群体特别是移民作为责怪和发泄的对象,‘族体认同’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移民成了转移社会矛盾的‘替罪羊’。”[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中国海外移民主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来,由于受左倾思想与路线以及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垒形成对中国外来威胁的综合影响,归侨侨眷被划入不能完全信任之人。
实际上,“移民问题通常是一个笼统的问题,它掩饰了目的国家公众对失业、住房和社会凝聚力,以及来源国的公众对人力资本的流失或浪费和经济依赖的担心和不确定”。[4]移民在移居国与祖籍国被另眼看待、不被信任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以上种种尴尬处境或令人不解的状态,长期以来主要发生在中国海外移民身上。原因何在?如何破解这一问题,设法避免这种窘境持续陷中国海外移民于不利,让他们可以发挥移民优势,促进国际交往和友好往来是亟待加强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二、在地化概念界定与移民在地化表现
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西尼耳定量确定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由此归纳出“经济人假设”,帕累托将其引入经济学研究。[5]它是经济学对人的社会行为及其动机做出的基础性分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利益选择与维护是人类谋生的基本行为。移民到达移入地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适应还是改变?是顺从还是抵触?一般而言,适应比改变更为容易,顺从比抵触较为有利。适应或顺从指的是包括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行为选择,又有主动与被动的不同方式。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指,在生活中,人必然具有趋利和避害的行为倾向,移民的动因是趋利和避害,顺从与适应也是趋利和避害。中国海外移民也是如此。
为讨论方便,在此引用一个概念—在地化。这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对的概念。全球化强调的是标准的统一和个性化的抽离,而商品与服务的全球化蔓延,又必须适应不同地域消费者的个性需求,由此又强化了地域特性,悖逆了个性化的抽离。简言之,全球化推动了在地化觉醒,在地化又助推了全球化的扩张。如同哲学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全球化与在地化也在博弈中共生。
本文的在地化是指,在进入新的居住地之后,出于构建生存发展基础的需要,在主客观条件的内外作用下,以有利于自身持续生存发展为前提,移民必然作出适应性选择。在地化的结果是,在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移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移入地烙印,即使日后他们再度移居他地,这种烙印也不会很快消失。比如,许多离开侨居地多年的归侨在节庆时仍然乐于表演侨居地的音乐舞蹈,不少留学归国人员仍然保留着留学国家的生活习俗等。在地化是移民迫于生存发展需要而进行理智选择的适应过程,是移民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同移居地自然与社会环境逐步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移民一直保持着形式不同、程度不同的自身原生文化特质。这是所有移民都不能避免的一般规律。不仅中国海外移民如此,菲律宾海外移民、印度海外移民、希腊海外移民等其他移民群体也常如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空间,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民族和社会环境,移民在地化影响的范围、形式、结果等都会有明显差异,即使是同一来源地的移民群体,只要移入环境不同就会形成相应的差异。移民在地化还表现为,移民群体与祖籍地民众的文化差异会逐渐显化。
需要明确的还有,本文所称在地化是针对移民群体而言,他们可能有第一代移民,也有二代、三代甚至更多代的移民后裔,只要他们身上还存有祖辈移出国原生文化特质且并未实现完全融入,就还处于在地化进程中,就仍在移民群体范围内。当完全融入后,就彻底归化为当地人而脱离了本文考察的移民群体行列。进一步讲,在地化的研究对象,是仍然保持原生文化特质的移民及其后裔,注重的是文化传承。一般认为,在地化是主体不明状况下的客观融入过程,本土化是主体明晰的主观融入过程。本文使用在地化的概念,则是反映移民在主客观综合作用下与当地文化互鉴的必然过程。以下从五个方面分析中国移民在地化的行为特征。
(一)在地化与经济活动
从历史上看,就多数移民而言,从到达移居地的那一刻起,不论他们本意是否念祖恋乡爱国,都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在地化的进程。出于生存需要,首先经济生活必然在地化。这种现象很普遍,限于篇幅,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据史料记载,“1930年,爪哇华侨从事商业及运输业者占百分之六十一。而从事糖业、食品工业及木材业则居其次。”[6]
从现实看,移民经济活动的在地化表现得更为深入。199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东南亚某著名华人商业帝国也受到冲击。但是,该企业不解雇任何一名员工。这一做法得到该企业数十万当地员工的普遍认同,大家同舟共济,最终渡过难关。如今该企业在当地仍然蓬勃发展,并且经营地域有了更加广泛的扩展,企业整体实力也更加强大。这个案例证明,华人企业的成功同样受在地化的深刻影响。当企业能够正常赚取利润时,任何人都会坚持在利润来源地发展企业。但是,当企业陷入困境时,还坚守在当地且不解雇任何一名当地员工,这就不是常人能够做出的选择了。笔者认为,能够做出这一选择,说明该企业创始人不仅仅是出于维护企业诚信、着眼长远发展的利益考虑,同样还有为当地员工设身处地着想的情感付出。这是华人企业求得持续在地化经营的证明。由此可见,取之于当地,回馈当地,是华人企业经营成功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反之,华人企业如果不能给当地带来利益,只将当地作为自己攫取经济利益的飞地,是注定不会有发展前途的。类似这样的例证,在世界各国不胜枚举。
(二)在地化与政治权利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海外移民通常不关心当地政治,只顾自己赚钱。此说虽不无道理,却也不完全符合实际。许多事实显示,中国移民也很重视政治参与。例如,1956年4月27日,在吉隆坡精武体育会,数百个华人社团举行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其大会议案录记载如下议题及决议:
(甲)凡在马来亚出生之男女,均为马来亚当然公民,议决:一致赞成照案通过。(乙)外地来马居住满足五年者得申请为公民,议决:一致赞成通过,并须免受语言考试。(丙)凡属马来亚之公民,权利与义务应一律平等,议决:通过照案一致赞成。(丁)应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议决:一致赞成通过。讨论事项:(子)应否联络本邦各民族共同争取公民,议决:应与本邦各民族联络,共同争取公民权。(丑)大会备忘录,正本由主席团签名,并亲自连袂呈递独立宪制调查团主席。每团体共签六份。议决:一致通过,争取公民权达到目的为止。[7]
众所周知,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1963年,马来亚同新加坡、沙巴及沙捞越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从会议召开的时间看,当时马来亚尚未宣布独立,马来西亚联邦更未宣布成立。在国家还未成立的情况下,华人社团集会商议争取公民权,构成这一动议的行为逻辑应该是:我们是此地的主人,在即将成立的国家中我们有当然的公民权!由此看出,当时大马地域内的华人内心在地化意识表现同步于他们的国家想象。另一方面,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确有不少东南亚华侨纷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从以上引述的内容看,仍然有更多的华侨选择留在当地,争取公民权利,建设既有家园。即使回国,大多也是部分家庭成员回国,家庭主体和生活基础仍然稳固在当地。现在国内七八十岁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归侨,不少人都有仍然生活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人等亲戚,他们当年的分离就是在地化影响在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所致。当然,也有一些人当年回国是父母决定的,这恰好说明他们的父母受在地化影响,只愿意让部分家庭成员返回祖国。
再看与马来西亚为邻的新加坡。有学者认为:“华人作为多数族群的新加坡岛国,处于马来人占绝大多数的印尼人和马来西亚人的汪洋大海中。华人主政者如何取得与国内的马来少数民族的合作,是其成功建构多元社会,从而保持与邻国良好关系的关键。……新加坡成功地通过社会多元化战略使族群政治关系基本和谐,避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常发生的强势民族或社会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激烈对抗,使国家意识能为各族群所接受”。[8]新加坡华裔执政者不以己强为大,尊重马来人等少数族裔,与他们分享政治权利,圆融族群关系,让自己得以安身于马来人汪洋大海之中。新加坡华裔不仅与前例中的马来西亚华人有同样的在地化政治权利观,而且为了能够在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半岛生存发展,他们主动与本国马来人等少数族裔分享政治权利。显而易见,这些举措同样是在地化影响的结果。
(三)在地化与源流认同
众所周知,早期中国移民的目的是为了积攒钱财,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但实际上,自有向海外移民至今,包括那些早期怀着强烈叶落归根情怀的中国海外移民大多也都在当地终老,回归故土的人数只是少部分。以美国为例,“据不完整的数据表明,19世纪中期移居美国而又重返原籍的人较少。”[9]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与华人曾经因为华人墓园发生了争执,原本政府拟推出的移山填海计划因全马华人的强烈抗争而终止。这一墓园争议证明了多数华人先人的人生终点和后人的源流认同都在地化了。即使是那些实现了叶落归根愿望的中国海外移民,以生命终点的定位诠释了他们的祖先源流认同,但在他们回到家乡后,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侨居地形成的文化印记,这同样证明了在地化的影响。
(四)在地化与社会生活
除了经济、政治层面在地化外,中国移民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在地化程度也很深。他们积极回馈当地,体现了主人翁精神。以菲律宾为例。在菲律宾,中国海外移民经历了很长一段困难时期。在西班牙殖民者和美国统治期间以及二战结束后,他们长期面对排华的生存环境。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菲律宾华人的在地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开始,菲华社会逐步推出惠及菲律宾各地多方面生活的公益性活动,并坚持数十年,受惠人数以百万千万计,形成了当地民众充分认可的“菲华三宝”:一是志愿消防队,二是捐建农村校舍,三是义诊活动。志愿消防队不仅扑灭了火灾,还熄灭了民族怨恨的心火;捐建的农村校舍不仅改善了当地农村孩子的教育条件,还培养了菲华社会与当地人民的友好感情;义诊活动不仅医治了当地困难民众的疾病,还拉近了当地民众与菲律宾华裔心灵交往的距离。在“菲华三宝”的基础上,近年来,菲华社会的救灾活动已呈现出制度化、常态化的趋势,向着“‘菲华三宝’+”纵深发展。这不仅证明了菲律宾华裔生活的在地化,而且预示着在地化的进程也会长期化。
(五)在地化与宗教信仰
中国移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在地化同样明显。以印尼孔教为例。根据王爱平教授的研究,印尼孔教是源于中国儒学而在印尼发展起来的制度化宗教。也可以说,印尼孔教是中国儒学的宗教化、印尼化或本土化。[10]显而易见,儒学在印尼的传播是印尼孔教得以形成的基础。“虽然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由来已久,但是印尼孔教组织的出现却是与华人民族意识觉醒、有目的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的努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1]民族意识觉醒后的印尼华人,通过恢复华人在祭祖、婚丧仪式等方面的传统习俗以防华人被同化;通过把儒学经书翻译成当地文字和经书原文改写成白话文传播儒教;通过孔诞纪年的使用和“庆孔诞、建孔庙、建学堂”完善孔教的制度化宗教形态。印尼华人孔教徒借以信奉孔教确立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通过将孔教发展成为与印尼社会信奉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五大宗教同在的合法宗教,谋得在印尼的生存发展。以在地化的观点看,印尼华人孔教徒创设发展了适合自身在印尼安身立命的宗教,他们以当地语言传播孔教,是孔教在地化的表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通过信奉孔教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在当地生存,而不是要回到祖籍国。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印尼,他们以中华文化认同表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身份,以此求得其他民族和信徒的认可乃至尊重。“印尼孔教的历史正是表现和反映了一部分土生华人确立文化认同和华人身份认同的历程—那就是:既认同印尼国家,同时又对自身的华人身份持有强烈认同,……他们打出了儒学的旗帜,孔子的旗帜,这是源自祖籍国—中国,同时也被西方世界和印尼的伊斯兰文化所承认的。”[12]事实上,孔教得以在印尼确立,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地化的结果。
以上分析了中国移民在地化的种种表现,说明在地化是一种必然选择和结果,但在地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自身的文化特质和族群认同。在地化是相当复杂和宏大的课题,下文将着重分析与在地化相关的几个问题。
三、与在地化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在地化与融入的差异
在地化不同于移民研究中常常提到的“融入”概念。融入的终极结果是失去原本的民族性,是移民群体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行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论及新客华人和土生华人时指出:“华人的克里奥尔文化是福建文化与马来文化两种文化特性的交融:华人的姓氏与非近亲繁殖的要求被保留下来,但婚丧嫁娶则显示出两种文化的相互交融,华人父系为主的严格家庭模式为本土习俗所拓宽。……还有,土生华人的衣着既带有明显的马来特色,却又有别于本土地道马来人的服饰。”[13]显而易见,土生华人虽已成为当地人,但他们与当地原住民马来人还是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如果这种状态也是融入,那么,与完全消失华人民族性之后的状态又该如何区分呢?
在地化或许是融入的前奏,或许还达不到融入,或许是部分人可以完成融入,部分人无法完成。在地化是过程,融入是结果和状态。在地化从一开始就是对全部移民而言,融入则是发生在部分人身上。在地化在主客观综合作用下发生,融入则完全以主观意愿为前提。此外,“融入”与“同化”也是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在现代移民研究中,融入是指移民在移入地社会逐步文化趋同的过程,同化则多指移入地社会要求外来移民屈从于本地文化而归化为当地人的过程,两者相同的是结果以及过程中移民的适从行为。以开封犹太人为例。“开封犹太人同化的最根本动力来自犹太社团内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犹太人对犹太教信仰的逐步淡化和对儒教的深层次认同,犹太教的儒化过程正是开封犹太人的同化过程。”[14]尽管从立碑阐释犹太教、延续传统的犹太教礼仪和积极修建会堂、保存《托拉》经卷等方面,都反映出那时的开封犹太人尚未被同化(融入)。但早期开封犹太人用汉语立碑阐释犹太教就证明了他们无可避免地在地化了。开封犹太会堂室内外结构与布局充满浓厚的儒学氛围,开封犹太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学习儒家思想参加科举考试之风等,这些都揭示了“犹太知识分子信仰热诚的减弱与行为方式的儒化,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使得更多的人背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15]最终,开封犹太人完全融入中国社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地化是不可选择的,而完成融入则与主观认同相伴。在地化是移民原生文化与移入国文化两者互鉴、衍生、创新的过程,融入则是移民原生文化对移入国文化的皈依。
(二)移民在地化与边缘性杠杆
孔飞力对中国海外移民有如下分析:“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呈现诸多投资获益的机会,那么,中国可能是其海外移民投资的理想地,甚至海外移民也可能往来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拓展其事业。如此,海外移民就可能从身处两个世界之中而谋获最大效益。如果该海外移民进一步成为其移入国华人社团的领袖人物,那么,这就还可能有助于在他返回中国时提升他的社会地位,而如果同时,他因为作为海外华人社团领袖而在中国得到较高礼遇或获得一定荣誉,那么,这又会为他在移入国的形象进一步增光。在如此往来互动中,移民就可能成功地撬动了自己身处两个世界的边缘性杠杆。”[16]孔飞力先生所阐释的边缘性杠杆源于李明欢教授提出的跨国移民理论中的两个世界理论。[17]对此,李明欢教授进一步作了阐释:“无论是华人还是其他民族,他们的确身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政体的边缘,对此,虽有无奈,但亦有追求。换言之,身处边缘,尽管有种种不便与难处,然而,正是这一特殊性,却能够给予那些具有雄心抱负的移民以极其宝贵的特殊机遇。”[18]两位学者的分析论证,描绘出中国海外移民在身处中外两方边缘时,如何趋利避害,巧妙运用自身具有的居间比较优势,发挥桥梁、纽带、媒介作用,在满足中外两方面不同需求的同时改善生存处境,提升在中外两方面的地位与影响,以获取最大效益。
居间比较优势的形成条件是中外两方面经济社会文化差异及信息不对称等。中外双方相关差异越大,涉足其间的中国海外移民具备居间比较优势的机会就越大。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长期落后于外部世界,中国人走出国门后,受在地化影响,必然在经济、科学、人脉交往等方面与国内相比具备比较优势,其强弱程度因人而异。换言之,在地化影响是中国海外移民得以具备居间比较优势的唯一前提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少人在国内一文不名而出国一段时间后再归来时却不断受到追捧,假以时日甚至在中外两边均可“手眼通天”,游刃有余。现实中,中国海外移民与其他移民都在努力保持着与祖籍国的联系。亨廷顿就此指出:“在1965年以后的移民当中,20%至35%的人会重返原籍,可是留在美国的人并不一定是想成为美国人,而有可能是想要有双重国籍。这些人既要享受美国这里得到的机会、财富和自由,又要保留自己原籍的文化、语言、家庭联系、传统和社会关系网络,二者得兼。”[19]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海外移民在充分利用边缘性杠杆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中外交流。这一作用,从历史到今天始终未变。从宋元时期以对外贸易促进中外经济交流,到清朝末年将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推介给祖籍国和同胞用以代替帝制的辛亥革命,再到二战结束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进程中,中国海外移民积极发挥居间比较优势,架起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充当媒介,参与催化,为中国社会进步勇开风气之先。总而言之,中国海外移民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就是促进中外交流,历史上如此,未来也不例外。假如中外双方都能认清中国海外移民的桥梁纽带和媒介催化作用,客观看待他们往来于中外之间的行为,以共同利益因势利导,以多方合作谋求双赢、多赢、共赢,就有望建成和合共生的国际经济文化交往新格局。
(三)在地化与爱国情怀
虽然在直观感觉上,移民在地化概念似乎有悖于中国海外移民长久以来表现出的强烈爱国情怀,①此处讨论的爱国情怀是指中国海外移民对于中国的情感认同。但深入分析起来,两者并不矛盾。
首先,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如前所述,移民在地化的影响是自他们到达移入地那一刻即开始且持续发生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国海外移民并未因受在地化影响而放弃爱国情感,比如积极支持和参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都是他们爱国情怀的强烈表达。对移民而言,爱国情怀是国家情感认同而不是法定义务或当然责任,可以提倡或设法激发而不能强迫。无论如何,移民在地化与爱国情怀并无矛盾。中国海外移民既没有因受在地化影响而失去爱国情怀,也没有因为对祖籍国的情感认同而对在地化影响产生抵抗力。
其次,中国海外移民群体爱国情感的集中表达是以特殊自然或社会事件发生为前提的,历史上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例证,近期有北京奥运会前全球范围的中国海外移民群体性声援游行集会,汶川地震后全球中国海外移民慷慨赈灾等。未发生重大自然或历史事件时,他们也密切关注祖籍国的一切,与祖籍国保持各方面的联系,爱国情怀常留于每个人心中,否则,他们集中表达的爱国情怀就成为无源之水。
再次,移民在地化影响是时刻都在发生的客观过程,爱国情怀则是常怀在心而有条件的主观表达。移民的在地化是他们到达移居地后基于生存与安全需要的自然适应过程,是环境约束与人性使然,与国家效忠、爱国主义等政治价值观并不冲突,略举几例。
1999年7月10日,包括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内的9万余名球迷汇集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沙迪那的玫瑰碗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女子足球决赛,见证了美国队通过点球大战5-4险胜中国女足的过程。关于这场比赛,笔者听到两个故事。
故事一:有一位女性美籍华人,在那场比赛前几天正式加入美国籍。比赛时与友人一同观赛,当中国队首先进球时,她欢呼雀跃,霎时,她突然感觉到周围投来异样的目光,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在美国,她前不久已成为美国公民。随后的比赛中,她不断盼望美国队也进球。当看到美国队也进球之后,她即刻离开球场。她自己讲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下一个进球,无论是哪个队进的球。
故事二:笔者的一位友人,当年比赛期间担任支持中国女足的当地华人后援队队长,每日不辞辛劳为女足提供保障服务,因此中国女足回国前全体成员在一面小锦旗和一个足球上签名赠送给他留作纪念。他告诉笔者,观赛时他们(一众中国海外移民)集体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为两国运动员的精彩比赛助威,无论是任何一方进球,他们都喝彩。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把对中国的情感认同、作为美国国民应有的国家效忠观念与体育比赛结果联系起来,从而不知所措。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环境认知比较客观,态度选择比较理性,以体育精神看待比赛结果,因此,就没有让自己陷于前者的精神困境。笔者的友人还讲述了这场比赛背后小球推动大球交往的故事。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开战,悍然用导弹野蛮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两国高层交往因此中断。当得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将观看中美女足决赛时,中方派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赴美观赛。在比赛前,李岚清与克林顿会晤半小时,由此中美两国恢复高层交往。当时,包括手举中美两国国旗观赛的华人在内的全美华人绝大多数都希望中美友好。他们的这一期盼即是在地化影响与爱国情怀并存的明证,因为谁又能说希望中外友好是没有爱国情怀,甚至是叛国呢?
还应看到,中国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中,爱国情怀还是起着经常性的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敢于来华开风气之先的大都是中国海外移民,他们基于爱国爱乡情怀想帮助祖籍国和家乡发展经济,但从事经济活动又必须遵从盈利法则,否则难以为继。企业可持续经营,才能一好变两利,否则是一损成两败。如若不然,何不慷慨捐赠?还能落个好名声。当然,宁愿捐助家乡公益事业而不在家乡投资者,也不乏其人,他们顾虑的是亲情与盈利相互冲突,恶性循坏。
在此特别要说明的是,爱国情怀与爱国主义是不完全相同的范畴。爱国情怀属于个人情感,而爱国主义则属于集体思想与行为的政治性选择。对于国内民众而言,倡导爱国主义完全应该。而对中国海外移民来说,若还倡导爱国主义,则会引起住在国人民对中国海外移民的疑虑,给中国对外友好交往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那些与中国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爱国主义的政治倾向必将导致这种不利影响更甚。对中国海外移民而言,尊重他们的爱国情怀,不仅符合他们的个人情感实际,也囿于情感属人权范畴而不易为外人所诟病。
笔者认为,到任何时候,祖籍国都应当尊重保护中国海外移民的爱国情怀,同时也照顾到他们对于当地的利益从属性,并且把他们看作自己在当地的亲友,通过他们大力发展与当地人民的友好交往。进一步讲,能够促进中外友好交往,是中国海外移民爱国情怀的特有表达方式,并不是举家回国才是爱国。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受在地化影响,中国海外移民群体通常不会因住在国生存环境的寻常变化而选择离开。对他们而言,离开意味着放弃现有生存基础,重新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和二次在地化的机会风险,经济人的行为理性与生存及安全需求的制约,都会促使中国海外移民尽其所能维护移入地的既有基本生存环境。这种行为可以称为移民的在地化生存依赖,并由此导致他们缘于生存发展需要而生成的对当地的利益从属性关系。此外,与在地化相关的几个问题也有必要探讨。笔者认为,“在地化”与“融入”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就移民在地化与边缘性杠杆的关系来看,受在地化影响,中国海外移民具备了相对于中外双方而言的居间比较优势,借游走于中外之间构建并利用边缘性杠杆谋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他们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外交流的社会历史作用。至于在地化与爱国情怀,中国海外移民并未因在地化影响而丧失爱国情怀,这一情怀的集中表达是以重大自然或社会事件为前提的,促进中外交流是他们爱国情怀的特有表达方式。中外各界都应客观看待中国海外移民,善待他们,发挥他们的桥梁、纽带、媒介作用,鼓励他们往来于中外,促成中外两方为共同利益开展交流合作,为双赢、多赢、共赢而努力。
[注释]
[1][2]韩永福:《清代前期的华侨政策与红溪惨案》,《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
[3]李安山等:《双重国籍问题与海外侨胞权益保护》,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3页。
[4]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译:《2011世界移民报告:关于移民的有效沟通》(内部资料),《内容提要》第4页。
[5]李田雨、林熙祺、王如璋:《论“经济人”假设的渊源、发展及启示》,《现代商业》2012年第17期。
[6]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五辑,第93页。
[7]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议案录,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藏品,馆藏号:W09037 Zz0214。
[8] 庄国土:《东南亚华商软实力及其对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贡献》,贾益民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9][19]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40、141页。
[10][11][12]王爱平:《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315、46、314页。
[13]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6~67页。
[14][15]张倩红:《从犹太教到儒教: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内在因素之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16] [18]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79、444~449页。
[17] Minghuan Li,We Need Two Worlds: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9.
[责任编辑:密素敏]
Exploring Behavior Features of Overseas Chinese under the Impact on Localization
HUANG Ji-kai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Museum, Beijing 100007,China)
migration studies;localization;behavior features;social integration;marginal lever;China and foreign exchang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mmigrants’localization, and it raises new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issues on localization.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overseas Chinese’s overseas development ha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both destination countries and home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are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s that still leave immigrants embarrassments. Due to immigrants ‘survival requires to bring benefits to the resettlement country. This research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with marginal lever; it reveals that localization is the priority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form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rough leveraging marginal lever, overseas Chinese has been enhancing self-development as well as playing a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functions of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D634.3
A
1002-5162(2017)03-0067-08
2017-04-21;
2017-06-12
黄纪凯,男,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陈永升博士、许金顶教授和同仁张志加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