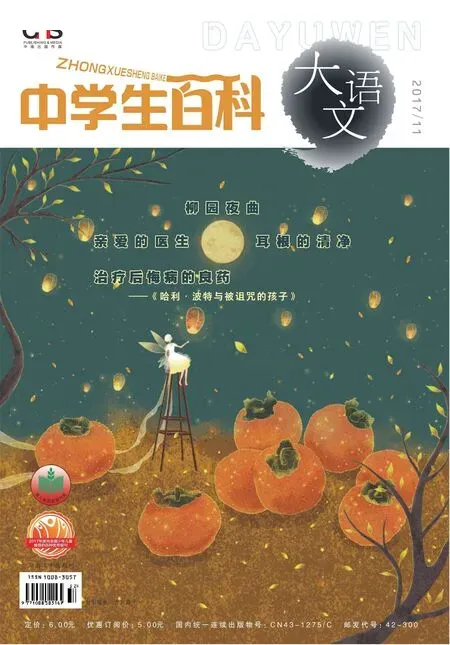庄生醒入蝴蝶梦
——读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文丨目田菌
庄生醒入蝴蝶梦
——读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文丨目田菌
■历史不是沉睡在书本和地壳里的遗迹,历史所繁衍的文化是我们每天温习的课程。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材生的独特视角,一定会是你写作时的精彩素材,更是你反思生活的细致入口。
在往期的专栏中,我们讨论过中国非城市聚落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以降,遭受战乱的流民在城邑与城邑之间的荒地聚集,屯田筑堡,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城邑的“乡村”这种聚落;我们也曾讨论过士大夫这一阶级的形成——汉代儒士和文吏的融合,造就了“亦儒亦吏”的士大夫阶级,科举制则造就了他们极强的阶层流动性。而当乡村和士人两者融合时,便发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即士大夫占据了乡村间的话语权,成为地方精英,化身士绅阶层,登上了地方行政的舞台。
古代中国地方行政的特点是“中央政令不下县”和“地方半自治”,乡间行政几乎由士绅和豪族们把持着,他们大多接受过传统教育,有文化,或是经商致富,或有科举功名。总之,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20世纪前半叶,士绅这个阶层变得“臭名昭著”,原因是他们代表着落后的“传统中国”,近代许多文学作品都会拎出一个或几个“乡绅”的角色,用以批判。如《阿Q正传》中骂阿Q“哪里配姓赵”的赵太爷一家,《子夜》中抱着《太上感应篇》而死的吴老太爷,《风波》中装腔作势吓唬七斤的赵七爷,更有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坏”出了风格的恶霸。他们要么是封建大家长,要么是欺压农民的土豪劣绅。
下文我们谈论的这位住在山西农村的乡居士人,可能是位“非典型”的乡绅。
这位“非典型乡绅”名叫刘大鹏,英国学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根据他记了51年的《退想斋日记》,为他写了一本传记,便是《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一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便是结合刘大鹏的日记,描绘这位华北乡居者的一生,以及他眼中的中国变迁。刘大鹏并不是一个什么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商绅,一个普通的儒者,一个普通的农民。正是这些身份聚合在一起,造就了他的不普通。他无疑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乡绅,但我无意为所谓的“地主”翻案,只想和大家一起讨论:在面临巨大变动的近代中国,夹在城市居民与一般农民之间的“乡绅”乃至更加边缘的乡村没落知识分子,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有着什么想法。了解这些,或许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当时的历史,乃至现在的城乡二元现象及现代化潮流。
在谈论他之前,请允许我粗略介绍一下刘大鹏的生平。
他出生于咸丰七年(1857),这一年,太平天国在南方占据了多个省份,英法联军则攻陷了广州,俘虏了巡抚叶名琛。当首都被攻占时他才4岁。他在22岁时通过县里的考试成为生员,38岁时通过了乡试,拥有了举人的身份,虽然随后三次考进士不中,但他回到了山西赤桥村乡居时,他仍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的长子也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举人,两年后科举制被废除。作为最后一届举人,长子受命去天津候补官吏,接触到了西方思想。宣统年间,清廷预备立宪,刘大鹏在县里乡间颇具声望,被推举为省里咨议局的议员,随后被选为县议长、省议员。他家中并没有多少田产,为了补贴家用,1916年他参与经营煤矿,有了一定的收入,但到了1926年,主政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对煤矿课以重税,刘大鹏便从煤矿经营中辞职,回乡务农,但乡村经济此时已恶化,他只能靠种植蔬菜来维系家用,他已时年70岁,第二年,他的长子去世,长媳吞鸦片自杀。1937年,日本侵华,进入山西,老人已81岁了,县中的官员请他草拟一份对日投降书,他无奈接受,接着因反对日军进村留宿而挨了打,又因其有文化而被逼迫向日军军官介绍晋祠。1940年,他的三子、四子因吸食鸦片而分家。直到刘大鹏于1942年86岁去世,他的家乡山西一直在日军手中。
大家看到这份生平履历可能会感觉十分熟悉,刘大鹏似乎很像余华作品《活着》中的徐福贵,只不过所处的时代更早一些。但并非如此。福贵的经历更像是一代人的缩影,余华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民族性中对于生存的追求。但刘大鹏并非当时乡绅知识分子的典型,沈艾娣女士也认为她写刘大鹏并非是因为其代表了一个阶级或某一类人——与之相反,写他正是因为希望还原一个经历了诸多变革的“真实的人”。他的《退想斋日记》,便是他在那段快速变化的历史时期中的观察——不仅有对外部社会的观察,更多的是对自我道德的反省。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谈论他呢?或许并非是为了寻找什么能反映一代人的共性,而是他身上的特殊性吧——他先后或者同时身兼士人、商人、政府人员、农民等多重身份,同时拥有儒者的道德和信仰。他从小有家财的“商绅”没落到贫穷务农的“文化士绅”。他是一个不满民国的前清遗民,也是积极参与公共行政的事实“公民”,他的视角特殊而珍贵。更准确地说,他是真真正正见证了“现代”与“传统”冲突的“人”,而非一个符号或代表。他的命运,和他的日记一样都值得我们去审视。
刘大鹏自取笔名“梦醒子”,指的是他在科举失败后的一场梦中自觉从事“诚、敬”不足,经梦中人指点后决心忘记那些功名利禄,恪守儒家教导,专注修养内心,“乃知从前竟在梦中过活,今日方才梦醒耳”。有一评论说得极好:“刘大鹏是从庄子之梦,醒入了蝴蝶之梦。”在现代化、西方化侵入日急的20世纪初,刘大鹏选择了他最熟悉的儒家思想,全面拥抱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来应对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他的痛苦与焦虑,都是源于他所赖以栖身的精神世界逐步崩塌。
同时,这个精神世界的崩塌和农村的没落是分不开的。传统中国重视农村,是因为农村是重要的税收和徭役的来源,生活在农村里的大家族,也是儒家教导施行仁义的基本单位。但在现代的冲击下,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熟知儒家经典的士人们不再有文化上的优势,农村的经济也被城市的工厂生产冲击得七零八落。人们对于乡村和城市的认知不再是“无事居于乡,有事赴县城”,城乡的格局开始发展成二元对立,这在过去或许是难以想象的。
沈艾娣女士称她写作刘大鹏的传记,是为了向英国的学生们介绍他们比较陌生的中国士绅,但百年之后的我们再回头望,似乎对那乡居的边缘知识分子们也并无太多思想上的共鸣,只能对他的遭遇和焦虑寄予同情。但对刘大鹏来说悲哀的是:我们这类现代读者之所以能够同情他,恰恰是因为我们已不再认同他所抱有的儒家价值观。我们脱离了那层儒家道德的语境,才能体会面对时代浪潮而不肯变动思想的人物之悲哀。
但我们所认为的悲哀,源于现代社会的教育中,我们耳濡目染的一种进步观——现代化必然进步于传统。这固然没错,然而在现代化的大潮下,有许多曾被时代抛弃的人,他们的经历并非无一可取,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或许,也是对我们所处的当代思想潮流中的一种反思吧。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如是,沈艾娣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