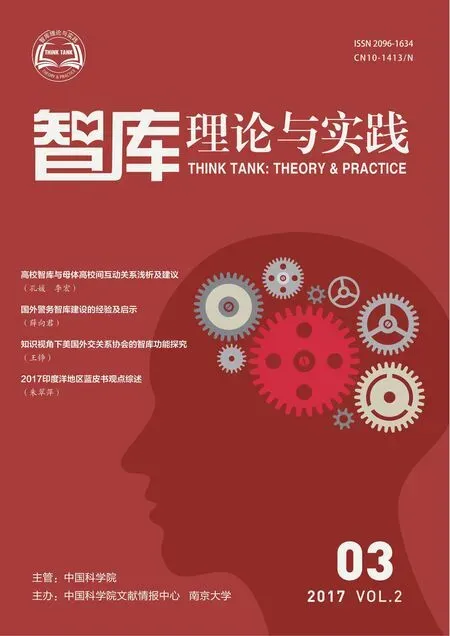智库与政府关系的调整与探索*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智库为例
■ 张骏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广州 510640
智库与政府关系的调整与探索*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智库为例
■ 张骏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广州 510640
[目的/意义]分析、解读智库与政府关系根源,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我国正在高速发展的智库行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方法/过程]通过观察分析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智库如何调整和探索与政府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与政府“再结合”,“剥离”与“统合”并行及“政府布局”与“高官参与”兼备等举措背后的行为逻辑。[结果/结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智库普遍呈现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政府普遍保持着对包括智库在内的社会组织更为积极和直接的介入,另一方面这些智库本身对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有着也不同于西方的理解。
智库 政府关系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1 引言
理想中的智库,纵使大部分资金来自政府,也应试图保持高度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自由。这些机构应该更倾向于通过知识性的分析和论证,而不是策略性的游说或施压来影响政策。在寻求消息和完善政策方面,智库应当具有平等的公共精神。然而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认为,许多亚洲智库并不回避以(与权力和财富关系亲密的)精英组织的身份示人[1]。在西方人看来,这些智库“更多地致力于‘制度提升’而不是‘制度批判’”[2]。事实上,智库所具有的以上特征不能不说是与他们置身的社会生态有关。华威大学学者认为,较之西方,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总体上保持着对包括智库在内的社会组织更为积极和直接的介入。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当一些智库既不甘纯粹依附,又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面对国家权力,他们往往会很有策略地徘徊在出走和回归之间。当然,独立或依附、出走或回归都不是绝对的。比起任何一种一边倒的局面,无论是智库还是政府,都更愿意在彼此关系的调整与探索中进退有度。
2 日本:智库与政府的“再结合”
根据《2016全球智库报告》[3],日本智库数量位居全球第9,共有109家。现在的日本智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多种类型,其研究领域广泛,研究形态以委托研究为主,但是自主研究积极发展。从法律性质上区分,日本智库主要有3类:(1)营利型智库,细分为营利社团法人(企业)和一般财团法人①营利社团法人:以营利为目的,实行企业化运作。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大和总研、日本综合研究所等企业系的智库都属于营利社团法人。根据日本综合研究机构2014年统计,181家参与调查的日本智库中,有82家(45%)智库为营利社团法人。2008年11月以前,日本的财团法人均是公益性的,但随着公益法人制度的改革,从2008年12月开始,出现了不以公益为目的的财团法人形态——“一般财团法人”。;(2)非营利型智库,细分为公益社团法人、公益财团法人和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即NPO法人)3种②如日本调查综合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协会等都属于公益社团法人,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属于公益财团法人,而SOHO智库、智库九州等则属于NPO法人类型。;(3)中间法人型③中间法人型: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目的,且不以将剩余金向成员分配为目的的团体,是既非公益(共益)也非营利性质的团体。如民主党设立的“公共政策平台”即属此类。智库。另外,根据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日本智库可以分为官方智库(政府背景,甚至直接隶属省厅)和民间智库(民间筹资、独立运营),后者在日本占多数。官方智库的代表机构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外务省)、防卫研究所(防卫省)、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民间智库的代表机构有PHP总研、日本综合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等[4]。
日本的智库生态中,民间筹资、独立运营的智库也确实存在相当的生存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少了公共资金的“兜底”,其在市场整体遇冷时生存能力也更弱。吴寄南、刘少东、朱猛等学者有关日本智库的研究均指出,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智库曾进入发展速度渐趋缓慢的“盘整”阶段[5]。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社会捐助持续滑坡,一些缺乏稳定资金来源的智库也被迫关门,智库总数一度减少了约两成,显然民间智库在此期间折损不少。然而故事的另一面却是,这一阶段也有行业新贵陆续问世。以东京财团为例,这家机构与政府再结合的色彩就颇为鲜明。东京财团成立于1997年,主要出资者是日本财团,该财团在中国被认为是右翼组织。东京财团网罗了一批顶级学者,就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对华政策偏右的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与政权中枢关系十分密切[6]。
国内学者通过观察日本智库近几十年来与政府关系的变迁指出,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外交决策机制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可供智库发挥的议题日趋多样。这些研究机构多是由政府资助或直接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另外有一些虽然属于独立法人性质,但也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机构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很大,其中有些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建议己被日本政府采纳。
例如,“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堪称是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日本的海洋政策制定方面,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为中心的政、学、官、军界联合体,通过媒体、研讨会、论坛频频发声,操纵舆论,影响决策。特别是日本近些年在离岛管理、低潮线维护、专属经济区设立、延伸大陆架和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安保应对等海洋政策、战略和立法方面,都与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及其关联的政、官、学、军界密切相关[5]。某些机构或其中的个人则走得更远。日本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和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隆星山这样的学者就中国军费增长、中日领土纠纷,特别是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和台湾问题都发表过颇为尖锐的观点;PHP研究所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大国,进而向日本政府提出战略警告。这些观点客观上为右翼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背书和舆论准备,因此很难使其不被评价为一种与执政当局的(预设观点立场的)“再结合”。
3 韩国:官方智库的“剥离”与“统合”;民间智库的“补充”与“分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赴韩国智库专题调研考察团(以下简称“国发院考察团”)的报告指出[7]:比起单纯的机构数字增减,韩国在官方智库的管理机制和民间智库的引导方式上的探索更加值得关注。官方智库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统筹协调政府研究机构的力量,1999年1月韩国国会通过《关于政府投资研究机构的建立、运营与培养的法律》。根据此法律,1999年3月相继成立经济和社会研究会、人文社会研究会等5家直接归属总理(即韩国执政内阁首长)领导的研究会,实行对政府各类研究机构的统筹管理。2005年,经济和社会研究会、人文社会研究会合并,成立了现在的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NRCS),负责管理政府创办的23家研究机构。相应地,政府研究机构全部归属到研究会,不再是原政府各主管部委的直属机构,与原主管部委没有人、财、物关系,只是业务关系。此举无疑形成了官方智库与行政机关的“剥离”。
然而“剥离”并不等同于“脱离”,研究会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形成了新的“统合”。设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23家政府所属的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提供支持服务,支持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政策的研究,为政策研究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研究会的最高领导为理事长,该职务经公开招聘选拔,由总理任命。研究会属于直接向政府负责的非政府部门,其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但类似于公务员,可以类比国内的“参公”体系。出于管理目的的根本定位,研究会并没有研究职能,只负责统筹管理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计划。政府研究机构自定课题需获得研究会的审批,经其同意后,预算才能从国库下拨到各研究院。国发院考察团还注意到政府研究机构自定课题的设立需经多方协商、综合协调后确定。每个研究机构首先要和业务主管部委沟通,明确政策研究覆盖的大致范围。研究会收到各研究机构上报的研究计划后,经过在全局范围内的统筹协调,审查批准各研究机构的研究计划,并将预算报告国会审批。
从预算数额来看,2013年研究会预算总额为250亿韩元,其管理的23家研究机构的预算总额为10,737亿韩元。23家研究机构的总预算中,财政拨款为4,560亿韩元,自主收入为6,177亿韩元,财政拨款占总预算的42%。由此可见,研究会在资金方面扮演的是一个重要但非垄断的角色。受其管理的智库虽然是官方性质,但是财政拨款尚不足总预算的一半,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从国家财政的“剥离”。但是凡接受财政拨款的项目,无论资金多寡,一律受到研究会的审批和监管,无疑又体现了政府主导的“统合”。
然而,再完善的官方智库体系也有短板,在一些如产业动态、就业情况、技术趋势等高度市场化和精专化的领域,官方智库的嗅觉就未必足够灵敏。这个时候,往往可见韩国的企业智库利用比较优势来“补充”承担官方研究职能,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还自筹部分经费,“分担”国家的经济负担。根据国发院考察团的统计,韩国民间智库以大企业设立的研究院为主,“没有大企业作支持的民间研究机构很少,以个人名义设立的研究机构也很少”。韩国各大企业附属的研究机构的人数没有完全统计,但就目前已知而言,平均每家人员规模为100人,实际上这个规模在世界范围都不算小。韩国民间智库主要有LG、三星、大宇等实力雄厚的大公司附属的经济研究院。大公司附属研究机构主要为本企业的战略发展提供咨询服务。由于长期关注产业方面的发展动态,在产业技术、产品市场和对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比政府研究机构更强的优势。政府因此会委托民间研究机构从事政策方面的研究。例如 LG 经济研究所就承担了政府委托的促进ICT(信息产业)就业问题的课题。根据国发院考察团的报告,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委托的题目一般费用都很低,如果研究机构自身没有实力,根本无法完成这些委托研究。所以,韩国民间智库可以说是在功能上“补充”官方智库的研究短板,在财务上“分担”国家的研究成本。
4 新加坡:“政府布局” “高官参与”的智库有效作用于“制度提升”
由于国家体量的关系,新加坡智库的数量(12家)并不算多,但是就历年《全球智库报告》所反映的质量而言,却相当不错。除了比较笼统的综合国际排名,东南亚研究所(ISEAS)在国际事务方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DSS)在防务方面,以及能源研究所(ESI)、水政策研究所(IWP)在能源与资源方面纷纷取得良好的世界级专业排名。
即便跳出《全球智库报告》所设立的体系,也不难看到新加坡智库在其所在区域和对相关利益国家所投射的影响。比如东亚研究所(EAI)作为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新加坡智库就与中国官方和学界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学术领头人提出的“中国模式”理论为解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能够被西方理解而又不同于西方的角度。又比如新加坡的国际事务研究所(SIIA)就与马来西亚的战略与国际研究所(ISIS)、菲律宾的战略与发展研究所(ISDS)、印度尼西亚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泰国的安全与国际研究(ISIS)于1988年共同创立了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智库网络)(ASEAN-ISIS network)①ASEA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EAN ISIS): http://www.siiaonline.org/page/isis/.,这一组织后来又加入了文莱政策与战略研究所(BDIPSS)、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所(CICP)、老挝外交研究所(IFA)、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MSIS)和越南外交学院(DAV)(原国际关系研究所(IIR)),为东盟探索区域整合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智力供给,增加了这一地区诸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
按说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智库发展都是基于众多复杂因素的综合结果,因此自然很难将新加坡智库取得的良好发展成就简单归功于某一两个因素。但是由于新加坡智库建设中政府参与的痕迹异常明显,所以学界很多观点都将新加坡智库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政府的支持。例如持该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加坡智库经验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政府布局”,其次则很可能是“高官参与”。以比较著名的几家国际问题智库为例,东南亚研究所(ISEAS)、东亚研究所(EAI)、南亚研究所(ISAS)、国际关系学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DSS)和政策研究所(IPS)均由新加坡政府部门根据其当时的需要而设立,并根据新加坡、地区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逐渐成为新加坡和该地区的知名智库。而这背后则是开国总统尤索夫伊萨克(Yusof Ishak)、前副总理吴庆瑞(Dr Goh Keng Swee)、前国防与安全部长陈庆炎(Tan Keng Yam)、前总理吴作栋(Goh Chok Tong)等人持续发挥的重要作用[8]。时至今日,新加坡主要的国际问题智库聘请前部长级高官或者国家领导出任一把手已经形成行业惯例。
由此可见,在新加坡,以人民行动党为活动阵地的政治精英们当仁不让地扮演了当地智库行业奠基者的角色,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对该行业一定的引导和控制。这种先当“国父”再作“保姆”的角色路径分明透露着威权(至少是准威权)主义的家长作风。只是那种引导和控制在新加坡被十分巧妙地操作着,它们未必是强硬的,一般都不明显危及学术自由和价值独立;但它们又是坚韧的,深刻地塑造着智库从业者的问题意识(比如认为“建议性”当然优于“批判性”),甚至是全社会的精英主义情结。应当承认,智库具有符号功能:一个智库的成长,也在政治、经济和教育发展中扮演着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在曾经殖民新加坡的英国,智库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先进社会的标志性附属物”;在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伊斯兰研究院(IKIM)是马哈蒂尔政府温和和包容的伊斯兰价值观的有力体现[1];因此在新加坡,智库肩负起实现国家战略的使命发挥“制度提升”作用,当然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5 智库与政府在互动中对独立性的探索
3国政府总体上保持着对包括智库在内的社会组织更为积极和直接的介入;从智库的角度出发,智库似乎又乐意于以(与权力和财富关系亲密的)精英组织的身份示人。那么这种似乎并不以独立性见长的模式难免会让人产生担忧,是不是目前3国智库和政府间至少从结果评价来看总体尚好的互动只是偶然的和阶段性的;在往后的发展中,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力会不会产生不可抑制的绑架知识的冲动,从而使得智库和政府间的互动最终僵化。
如果对这种观点进行学理化的演绎,则呈现这样的推理过程:首先,假设政府与智库间的关系,即权力与知识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主体相对于知识客体的关系;其次,这种关系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所营造的通常是主客体规则模式,显示出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监管,提供关照和分配机会的行为则更像是家长式的恩赐;最后,结论自然是政府和智库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甚至根本并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互动。
然而事实上,即便在以上3国中政府对智库介入最深的新加坡,这种担忧也并未最终成为现实。笔者就该现象请教了曾供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23年(1992—2015)的杨沐教授2杨沐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他认为新加坡的智库与政府当局关系紧密,客观上呈现一定的主客体关系特征,但并未完全陷入主客体规则模式:一方面政府长期以来确实对智库进行总体上的控制和监管;另一方面,智库在政策研究和机构管理上的相对独立也逐渐得以确立。
具体来说,首先新加坡6家主要智库②的资金支持毫无疑问主要来源于政府,而政府部门对智库的财政支持并不是铁饭碗,这和智库能否保证政策报告的质量、能否在政府决策中具有参考价值、能否在国际上取得相应的影响力等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政府对于智库产品的评价具有间接但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政府(卸任或现任)要员又在智库担任重要职务(通常为理事会成员),这势必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智库从政府那里获取资源和参与决策的难易程度。所以就这两点而言,新加坡政府与智库的关系确实呈现出主客体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智库开展政策研究的自主性问题则要更加复杂。原则上,智库政策报告的对象选题、方法路径、观点偏好都由智库自己决定,和智库联系的相关政府部门等不作规定和指示。但是由于新加坡的主要智库均为政府创立,并主要依靠公款以维持其运作,所以要极力避免功能重叠、重复投资和(国家系统)内部竞争等可能为纳税人所诟病的问题。故而当两个及其以上智库的研究课题重叠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动用行政手段予以调节。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亚所个别研究就曾因其研究课题涉及到南亚国家问题而被政府叫停。但是随着新加坡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化,跨地域、跨领域研究愈加成为国际趋势,以及“政策思想市场”的逐步形成,根据杨沐教授的回忆,进入21世纪后,这种案例越来越少,直至2010年后基本消失。这一历史变迁的起点是新加坡政府作为主体对智库客体的控制和监管,但是落点则在于智库在政策研究上愈发稳固的独立性,而与此同时政府原则上又保留了必要情况下介入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观察,至少不应该仍将此视为典型的主客体规则模式。甚至可以说,新加坡的这种模式较之于韩国将所有23家从事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公立智库的项目审核权全部统合到一个研究会的模式更为自由。
另外,政策研究上的独立性当然不可能脱离机构管理上的独立性而单独存在。新加坡6家主要智库的管理模式差别不大,内部的管理层都具有决定员工的录用、工薪、课题、考评、晋升等重要事项的权力。但是一旦涉及财务问题,情况就大相径庭。新加坡的多数智库设立在公立大学内,一方面为智库运行提供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另一方面政府也依托大学的管理体系对智库进行特别是财务方面的监管。大学对智库的各项财务开支有严格的管理办法和管理程序。各研究所(如东亚所、南亚所)所长几乎没有什么自行决策的空间。即便如此,大学财务主管部门仍然会每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到智库查账。严格的财务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库内部管理层的自主权,但也减少了财务中可能存在的漏洞,保证了透明和清廉,从而保护了智库的相关责任人[9]。
以上新加坡的实证经验无疑说明现实中政府和智库间在互动时并未呈现主客体规则模式,即政府并没有以权力主体的身份全面主导与智库这一知识客体的关系。更为主流的情况是双方在磨合中各有进退,更确切地说,智库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成为知识与权力的缓冲地带,使知识与权力形成了良性互动。
智库的兴起和完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识与权力在政治决策中的两难问题。这就意味着政府和智库间的关系并不适用主客体规则模式,而是更多地呈现出主体间性问题的特征。哈贝马斯在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哲学思想的阐释中所倡导的就是权力和知识间的互动,即决策咨询确实不是纯理论层面的从知识到权力的线性过程,而是交流与互动的网状结构,在这张大网上,需要能促使知识与权力交流互动的智库平台[10]。基于本节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此说法完全可以作为智库与政府在互动中对独立性的探索的相关学理解释。
此外,本节以上部分虽然是针对3个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分析,但也对我国智库建设中有关独立性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可以肯定政府和智库间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主体间性问题的特征。其次,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提升至价值讨论的层级,我们还可以借助哈贝马斯有关科学与政治间的“知识-价值”关系论述进行比较解读。哈贝马斯将“知识-价值”关系区分为3种模式:决断主义、技术统治和实用主义。决断主义是政治决定价值,知识成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技术统治是科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实用主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道路,“在这里,科学与政治是互相依存的,是对话交流的”[11]。
本文认为,过去我国各级政府在寻求外部意见时确实存在着决断主义的倾向,但是随着近些年来的观念革新,在寻求智库的咨询意见时秉持实用主义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智库既然是相互依存、对话交流的关系,就没有必要通过不断削弱智库(在不触及原则性问题时)的独立性,或者利用智库独立性方面现阶段可能存在的某些制度建设的漏洞,来有意地消解智库在公共政策领域内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虽然没有采用美国理论界从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框架出发讨论智库独立性的传统路径,但亦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思路。
6 结论
3国政府普遍保持着对所在国家社会组织更为积极和直接的介入;现实中却很少观察到这种强势出现极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智库与政府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会与对方做出必要的互动,彼此拿捏对双方都比较有利的距离。具体的操作方法在不同的国家当然有所不同:在日本,主要是因为某一人员构成相对稳定的精英集团(如自民党内实权派)长期执政从而对公权力产生粘连,与这个集团中某些派系在政治上的“左”“右”协同起来,自然成为某些智库与权力“再结合”的契机;站在韩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政府并行不悖地实现了对其官方智库的“剥离”与“统合”,且有效发动了民间智库来对官方智库的研究进行“补充”与“分担”,显然是一种颇为可取的“制度提升”;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建国以来长期稳定执政的体制无疑使得该精英集团具有了超乎西方式政党的政治角色而成为一种“建国者”与“人民保姆”的混合体,有关西方主流意见对于这种体制的评价暂且不论,客观上也促使了新加坡的智库展现出国家战略的格局感和使命感。可见,国家在智库建设中的角色能够、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以适应现实环境。
3国智库确实更多地致力于“制度提升”而非“制度批判”,它们始终不可能距国家权力太远。但是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它们同样为巩固智库独立性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1] Stone D, Nesadurai H E S. Networks, Second Track Diplomac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Experience of Southeast Asian Think Tanks[C]//inaugural conference on Bridging Knowledge and Policy. Bonn, Germany, 1999.
[2] Stone D.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Symposium: How to Strengthen Policy-Oriented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Viet Nam; 31st August 2005, Hanoi[J]. 2005.
[3] James G. McGann, 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5.
[4] 朱猛. 日本智库的运作机制: 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例[D]. 外交学院, 2015.
[5] 刘少东. 智库建设的日本经验[J]. 人民论坛, 2013(35): 18-23.
[6] 吴寄南. 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J]. 日本学刊, 2008(3): 16-28,157.
[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赴韩国智库专题调研考察团,李国强, 陈波. 韩国智库考察报告[J]. 中国发展观察, 2013(12): 35-39.
[8] 韩锋. 新加坡智库的现状、特点与经验[J]. 东南亚研究, 2015(6): 4-9.
[9] 杨沐.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经验[M]//郑永年.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151-519.
[10] 王友云, 朱宇华. 基于知识与权力关系视角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J]. 探索, 2016(02): 178-184.
[11] 萨拜因•马森,彼德•魏因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探求科学咨询的新模式[M]. 姜江, 马晓琨, 秦兰珺,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The Adjustment and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 Tanks and Governments——Taking Japa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Think Tanks as Examples
Zhang Jun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Purpose/signif i cance] The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think tanks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s would allow us to get closer to the root of any problem, which would be extremely helpful in further optim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the rapidly developing think tank industry in China. [Method/process] By focusing on how think tanks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to adjust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ir respective localit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behavioral logic behind the performance of think tanks. [Result/conclusion] The widespread emergence of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e think tank industry can in part be explained by regional governments maintaining a more proactive and direct interventional role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ink tank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a point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is that think tanks themselves perce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in a way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think tank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ments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G311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7.03.09
2016-12-22
2017-05-09 本文责任编辑:吕青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决策咨询制度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JZD023)研究成果之一。
张骏(ORCID:0000-0003-0809-1990),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硕士,E-mail: zhangjun@ipp.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