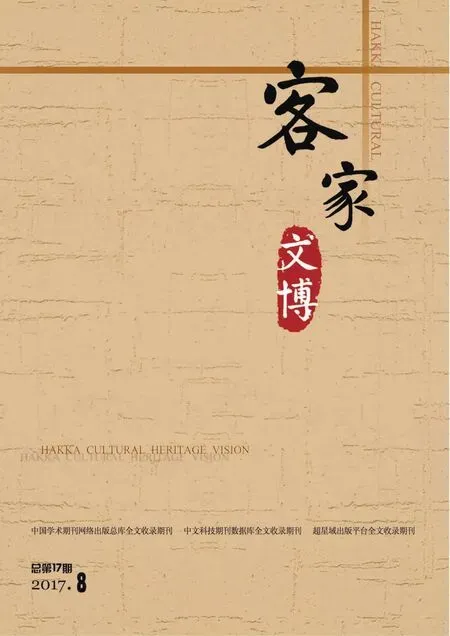提倡科学研究 补助公众教育:国立中央博物院之筹设
吴昌稳
提倡科学研究 补助公众教育:国立中央博物院之筹设
吴昌稳
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设是延续晚清以来知识阶层强烈要求建设国家博物馆的设想。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从一开始就着力建立新的一套政权体系。博物馆作为近代西方民主革命的衍生物,自然也成为民国政府改造文化事业、塑造国民性格、发扬固有文化、进行公众教育的重要工具。实际上,国家博物馆或者说中央博物院,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博物馆水平,特别是该国对于博物馆的认识。因此,考察中央博物院之筹设,可以观察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前,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博物馆的认知及想象。
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博物馆观念开始传入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不久博物馆实体开始扎根中国,开启了中国博物馆的旅程。其时,博物馆在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平民化过程,普通人被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在国内,博物馆被当作富强文明的象征,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以及文教的基石。正如时人所言:“一国的文野,视乎期文化程度的发达与否。惟其文化的真精神,全恃博物院为代为表现。故欧美各先进国家莫不视博物院为文化的大本营,教育的实验室,期政府既目此为国家元气,其人民复藉此求知识源泉。”1国立中央博物院筹设于南京国民政府权力较为稳固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京国民政府重视文化的姿态。
学术界对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徐玲《艰难的探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建始末》(《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4期)主要依据刘鼎铭选辑《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对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情况进行呈现。类似的还有邱龙虎、辜美惜《现代化和民族性导向下的中央博物院1933-1949》(《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1期)一文。倪明《可贵的尝试——原中央博物院建筑缘起与历史评价》和李海清、刘军《在艰难探索中走向成熟——原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缘起及相关问题之分析》(《华中建筑》2001年第6期和2002年第2、4期)对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建设情况进行了考察,与本文题旨关系不大。此外,杜臻《民国时期博物馆理事会制度探析——以国立中央博物院为考察中心》(《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年第3期)和《国立中央博物院贵州民间艺术考察初探——以庞薰琹为中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年第1期)研究国立中央博物院相关史实和人物,在细节上见功夫。上述研究在揭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建的本事方面已有推进,但对国立中央博物院筹设的立意认知仍有空间,资料挖掘仍可努力,本文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设放在民国二三十年代的时代话语之内,通过各种史料的排比与挖掘,揭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设的立意、史事、价值与意义。
一、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立意
从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宗旨来看,其旨在“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知识之增进。”2这一宗旨将博物馆的研究、教育、展览的功能都已点出,唯一未指出的藏品,可能因系筹建,藏品尚未到位之故。比对今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和博物馆发展现状,上述认知差强人意。
曾昭燏阐释了国立中央博物院宗旨的内涵:
一是综合现有各种学术机关研究之成果,“作一系统的陈列,及永久之保存。”3这一点,弥补了宗旨的不足,涉及到了藏品的保存与展示,既包含文物的保护又包含文物的利用。
二是推动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此类集团的调查,实为现状极迫切之需要,一切建设及国防问题,皆有赖于此类工作。故应有一国立博物院以主持其事。或自己为之,或联络他机关合作之。”4曾氏还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为例,认为需要集合各种专业背景的人士合力推动科学研究,这样才能有实际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不单纯从事文化方面的发展——它还有服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初衷,甚至服务国防发展的需要。这与我们认知的博物馆功能相差甚远。但是,揆诸实际,当时国民政府边患甚多,东北告急,博物馆从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着手,是可以为边疆问题提出因应对策的。
三是集中有限力量为全国古物保存作全局之统筹。“有此博物院,可从事正面古物保管之工作,一切古物或进之院中,或就地保全,可以作一全盘之计划。”5可见,建立国立中央博物院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一座国家博物馆这么简单,尤其是国家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国立中央博物院还被寄予管理和处置全国文物的重任。
四是作为民众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普及所与说明机关,协助各项建设事项之开展,“现代之建设,非基于深切之科学的调查及研究,莫能为功。但一切科学的研究及调查,若不能公之与民众,则只限于少数专家。民众既不了解,一切建设计划必难着手。若有一博物院陈列其事,将少数专家之知识传之民众,民众一明其利害,则一切设施自可收事半功倍之效。”6也就是说,国立中央博物院要发挥其社会责任,通过与民众互动的方式普及知识,减少和化解民众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决策的误解。
五是传播现代知识。“欲使中国现代化,非先使民众了然于工业文化之实质不为功。此种工作,非学校所能独立胜任者。若有一大规模之博物院,陈列现代工业之一斑,则一切使中国进于现代化之阻力,自可消灭无形,民众对于现代文化亦必渐有正确之了解。”国立中央博物院“非仅陈列保存,亦重科学研究,不仅普通教育作用,亦有关于国计民生。”7
上述五个方面,已经从较为全面的角度解释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性质与定位,即它不是个零星和片段的陈列馆,而是系统展示各学术机关研究成果之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博物馆机构,还是整合学界力量进行有组织的研究的机构;不仅仅是个博物馆机构,还是政府管理文物的统筹单位;不仅仅致力于文化建设,还需要成为民众了解国家建设之窗口;不仅仅是古物之陈列保存,而是国计民生的助产士。
简言之,在国力有限的当时,国立中央博物院承载着一个国家对博物馆的所有想象,不管这种想象是否与博物馆本身职能有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博物馆虽然是近代以后的一种普世价值观的承载体,但是来到每个国度,它又不可避免地与本土诸种氛围相结合,于是派生出各自特色的博物馆想象,这种想象慢慢即会固化为该国博物馆的一种禀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强化。博物馆在中国的命运,就是逐渐承载着超出博物馆自身的功能与定位,形成一种镌刻着中国烙印的中国博物馆认知体系。
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组之推进
蔡元培先生早年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时,深受讲授文明史的兰普来西(Lemprechs)教授影响,同时参观当地美术馆,对美学产生浓厚兴趣,亦蒙发他日我国美术馆、博物馆之建设的种子。81928年,他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长,创办中央研究院,并再次提出创办“中华民族博物馆”的设想。之后,蔡氏创建中央研究院事竣,开始着手实施上述计划。1929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往北平后,正式接收国立历史博物馆,并改称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李济任筹备委员。9
上述筹备中央博物院的努力终于在1933年进入快车道。蔡元培于当年4月正式将集收藏、整理、研究和展出古代文化遗产的国家级博物馆的设想提出,并选址首都南京。“南京为国民政府建都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中外士宾观瞻所系。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馆,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智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10
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设立。傅斯年被委任为筹备处主任,主持其事。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与蔡元培交好,在傅斯年眼中,他与蔡元培的关系是“受师训备僚属”,且长达25年之久。11傅斯年在民国学界是一位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可以从事学术组织及行政的多面手,堪称“学术精英群体的纽带性人物”。12
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后,又延聘翁文灏为自然馆筹备主任,李济为人文馆筹备主任,周仁为工艺馆筹备主任。媒体在采访教育部相关人员(教育司司长沈鹏飞)时,教育部对中央博物院的期待很高,希望借博物院来“启发人民对于学术之兴趣,而促进科学及文化之进步者”,13在中央博物院的主管机构教育部眼里,傅斯年是既有学术见识,又有行政经验和长远眼光的允当人选。《云南教育》对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也有报道,不过角度稍有不同。他们除了介绍自然、人文、工艺功能定位,还特别提到中央博物院在边疆、实业和国防三方面的意义。14
翻检《傅斯年全集》并无多少与中央博物院筹建相关文字,而当时傅斯年工作重心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虽然是第一流的学者和学术组织者,但是毕竟精力有限,无暇顾及或难以顾全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傅斯年在任年余,贡献仍不少,他“拟定本院进行计划,编制筹备处预算,筹划建筑经费,收购绘园古物,接洽各学术机关合作,商定古物陈列所所存物品划作本院人文馆基本物品,凡本院基础工作,悉于是时筹拟妥善,分别进行。”15
1934年7月,傅斯年辞去筹备处主任一职,该职务由李济接任。李济接任后,大力推进筹备工作。首先是建章立制。因为制度建设是基础,基础扎实,各项工作的开展才能有条不紊。因此之故,《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组织章程》成为筹组该院的依据和基础。在这一份1935年9月经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的章程中,对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各个方面,有明确的框定和分野。16《规程》奠定了中央博物院发展的基础及内容。1935年12月,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商定,聘请蔡元培、王世杰、胡适、黎照寰、李书华、秉志、朱家骅、张道藩、翁文灏、李济、傅斯年、罗家伦、顾孟余为第一届理事。171936年4月15日,理事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蔡元培为理事长,傅斯年理事为秘书,会上议定了中央博物院工作方针。
三、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建
一个定位于中央的博物馆,筹建问题当然十分繁多。选址问题是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的重要议题。根据筹备处暂行规则规程的第三条规定需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筹划建筑事项。建筑委员会委员长为翁文灏,委员为张道藩、傅汝霖、傅斯年、丁文江、李书华、梁思成、雷震、李济。1934年7月26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公推张道藩、傅斯年、丁文江三委员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领导建筑工作。经过中央博物院与南京市政府反复磋商,中央博物院获得了近200亩的建设用地。
经费是筹备中央博物院的根本要件,为了筹集办院经费,傅斯年在筹备处设立伊始,就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补助。1933年6月,中英庚款委员会复函同意补助建筑费150万元。自1935年11月开始至1936年5月,中央博物馆等各处共计领到庚款补助费60万元,由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委员张道藩、李济共同保管。
建筑设计方面,建筑委员会于1934年7月开始制定建筑设计的简章。1935年9月,建筑委员会一致选出“巳”字方案为当选建筑设计方案。该方案由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徐敬直所设计。其后,博物院与徐敬直签订合作协议书,并请其会同梁思成从事设计图修改与完善工作,并且测量院址,以便营造。
根据计划,中央博物院分为三期建设。徐敬直建筑师接受委任后即绘制第一期建筑样图,计全院行政部分房屋全座及陈列馆一座,暂供人文、自然、工艺三馆公用。第一期工程大约耗资90万元左右,计划450天完工。
1936年4月11日,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和研究建筑招标问题。社会上共有22家公司竞标中央博物院建筑招标,据建筑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记载,“投标者二十二家,标价最低者陶记,单位计算多误,且以前经验不甚佳,议决不要;次之为江裕记(标价748602元,曾建外交部房)、余洪记(标价770800,曾建沪邮局及其他大房)、张裕泰(标价770800,曾建沪市府房)、新金记(标价797500,曾建炮兵学校)。复分析各项费用,减去一部分后,决定先向江裕记商订,如不合,再商余洪记,再不合,商新金记。共决电工设计Denison,监工朱葆初。”18最终,江裕记成为建筑建设方。
1936年5月,《时事月报》报道中央博物院即将破土动工的消息:“在筹备中之中央博物馆地址位于中山门内中央政治区,占地一百亩……建筑图样,经一年之计划,近始竣事。全部建筑费从俭计算,尚须一百五十yy万。首期工程先建陈列馆及总办公处各一,预算须六十万,定六月开工,明秋落成,建筑尽量采中国式。”19于是,中央博物院的兴建成为议事日程当中的首要任务。
工程自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止,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基建工程完成75%左右,便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告中辍。可见,日本侵华战争对民国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
四、各项业务工作之推进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兴建馆舍的同时,各项业务工作也在积极推进当中。其中,藏品征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一)绘园古物之购置。绘园古物原为闽侯何叙甫氏私藏,计二十余件,中有巨鹿瓷器、历代铜器佛像,尤可珍贵者为南北朝之石刻雕塑,何氏积廿年之精力,由豫陕古玩商手中展转而得者……经与何氏磋商,以三万四千元让归本院保存。”20其他如从刘善斋手中收购百余件藏品,又从东莞容庚处购买藏品32件。
国立中央博物院一方面努力购买重器充实馆藏,一方面通过政府划拨和调剂等方式收入了不少藏品。1933年10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决议将古物陈列所所藏文物划给中央博物院,作为建院之基础。古物陈列所的藏品来自奉天和热河两行宫,物品包含三代鼎彝、历朝书画、陶瓷、丝绣、髹漆等件,富有历史意义及艺术价值,奠定了中央博物院人文馆的坚实基础。教育部还将铁道部顾问斯文赫定在新疆收集的三箱古物发交该院,又将新莽朝的权衡等件交由中央博物院。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送宋元时期银锭7枚。1936年7月,北平历史博物馆与中央博物院合并,北平历史博物馆21万件藏品纳入中央博物院收藏体系,奠定了中央博物院雄厚的收藏基础。经过上述征集和划拨工作,中央博物院的藏品已经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在当时全国博物馆界来说,也是后起而突出的一家。
有趣的是,以故宫博物院文物为主、河南省博物馆文物深度参与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售票收入,中英双方根据分成比例,最终将9000余镑收益划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将该笔收入转给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筹备处遂组织专家委员会,选购西方艺术品,奠定中央博物院工艺馆之基础。
如前所述,中央博物院的筹备是在蔡元培的直接指导下着手进行的,蔡氏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所任命的傅斯年和李济都是中央研究院的专门人员,因此中央博物院从筹备之初就与中央研究院关系十分密切,并受益良多。中央研究院在中央博物院发展过程中,协助中央博物院作了以下事宜:(一)负担购地费,并承担一部分日常经费;(二)承担博物院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三)赠送中央研究院历年来所搜集的适合于陈列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工艺品。21这些襄助已不是一般简单的帮助,而是强力扶持。这对中央博物院筹备工作无疑是极大的助力。
不仅如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一道发掘安阳殷墟,以及联袂在山东日照开展两城镇遗址考古工作。上述两地考古出土文物在中央博物院馆舍建成之前仍由中央研究院保存与研究,待陈列室建成后则归中央博物院人文馆陈列。此间,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于1936年10月将所采集的大量动物标本庋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库房。此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还计划仿照中央研究院的做法,将历年收集的地质古生物及古物标本赠给中央博物院。22
国立中央博物院从一出生开始,就博物院建院之初即得到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大力扶助。特别是蔡元培,作为国民党元老,又是教育领域的掌权者,不仅深孚众望,而且深具格局。蔡元培为该院发展争取各种资源,如争取中英庚款、划拨文物等等,为中央博物院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天假以年,中央博物院的发展相信凭借着国字号和各种资源支撑,一定会大放异彩,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之渊薮。可惜,日本侵略者无端启衅,国军节节败退,国土迅速沦丧。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城疯狂屠城。中央博物院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该院房屋,战前已搭好钢骨水泥屋架,下面的墙也砌上一小部分,战事一起,全部工程停顿。敌人入城,以其地养马、作空军司令部。大殿屋顶钢架全部撤走。房屋弄得污秽损坏不堪。”23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历史命运。
在此过程中,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并未停止业务活动,除了将所藏古物在重庆举办公开展览外,还数次和其他学术团体合作,派遣考古队调查团从事于云南大理丽江、四川彭山、西康以及甘肃敦煌的考古调查工作。至于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建设,抗战结束后恢复进行,至1947年才完成大体轮廓,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完成人文馆之全部工程,后为今天南京博物院之老馆。
五、余 论
客观地说,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划和筹备阶段,都是以建立国家博物馆的意向来进行的。作为筹备处第一任负责人,傅斯年是一位既有学识又有执行力的全才性人物,在他的推动下,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密切合作,开展考古等事宜。李济接任筹备处主任后,推动场馆建设,可以说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持筹备工作的人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历史学者、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他们希望建立一所近代式的博物院,因此计划十分宏大。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假以时日,中国博物馆的事业必定能取得长足进步,独步东方。
注释:
1 杨成志.现代博物院学[A].博物馆历史文选[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27.
2、3、4、5、6、7 曾昭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A].博物馆历史文选[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82-183.
8 蔡元培.我的人生观[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73.
9、15、20、21、22 刘鼎铭选辑.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J].民国档案,2008(2):27-34.
10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2:2.
11、1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M].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89.
13 教育部筹设国立博物院[J].海外月刊,1933(9):78.
14 教育部筹设国立博物院之计划[J].云南教育,1933,1(3):40.
16 教育部编.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组织规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4-15.
17 教育部聘定中央博物院理事[N].时事月报,1936,14(20):8-9.
18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M](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36.
19 中央博物院即将开工[N].时事月报,1936,15(2 5):4.
20 向达.战后两年来的国立图书馆与博物院[J].中华教育界,1948,2(2):17.
[1]徐玲.艰难的探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建始末[J].博物馆研究,2008(4).
[2]刘鼎铭选辑.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J].民国档案,2008(2).
[3]邱龙虎、辜美惜,现代化和民族性导向下的中央博物院1933-1949[J].中国博物馆,2014(1).
[4]杜臻.国立中央博物院贵州民间艺术考察初探——以庞薰琹为中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1).
2017-6-5
吴昌稳,男,安徽舒城人,任职于广东省博物馆,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史。
本文系国家文物局2013年度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民国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国博物馆学(1935-1949)》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2013-YB-HT-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