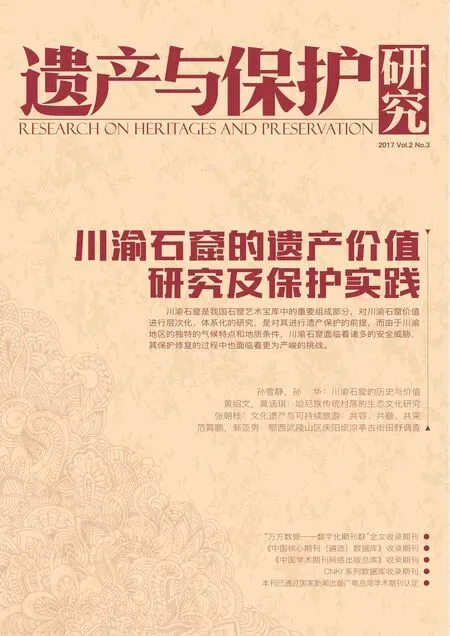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与时空变迁
张 弛,毕啸南
(1.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2.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857)
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与时空变迁
张 弛1,毕啸南2
(1.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2.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857)
清明节作为中国历史上3大节日之一,它融合了时间相近寒食节的上坟习俗和上巳节的春游传统。文章通过对贵州省铜仁地区清明前后“挂社”和“挂青”的习俗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无论是“挂社”中的集体吃社饭的习俗,还是“挂青”中家族墓田中的祭祀,都体现了中国人相互依赖的伦理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今天的“挂青”和“挂社”都出现了日益形式化的趋势,形成这种趋势主要有3个原因:家族墓地日益被国家公墓所取代,割裂了家族后人与祖先之间的联系;地方性的时间被统一性的现代时间所取代,“挂社”“挂青”这种具有地方性时间节律的活动受到了制约;清明期间集体性的传统娱乐活动被跨越空间的旅游和虚拟空间的个体性娱乐所取代。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清明的深层意义:对先人的缅怀和对家的眷恋是一种“实质性传统”“时空压缩”也不能改变这种实质性传统。
清明节;挂社;挂青;实质性传统;时空压缩
清明节仅仅在春节一个多月之后,同为中国传统3大节日,两者待遇却千差万别:春节是一首欢乐祥和的交响乐,天地同乐;而清明则是一曲悲伤断魂的牧笛声,怀念昔日去者。春节的习俗传统之一“发红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进化为“抢红包”的新习俗,“红包经济”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国人对春节喜庆的社会记忆,节日在市场经济中变成一个重要的消费节点,商家成为推动节日的主要推手;而清明节习俗背后的支撑产业——菊花、烧纸、鞭炮等,并不需要互联网大数据新兴产业的支持,因此清明节并没有春节那样的全民社会记忆。春节这个阖家团聚的时刻,在旅游产业的推动下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旅游黄金周,欢聚的社会记忆分散成个体和家庭的休闲记忆;清明节作为国家假期仅仅恢复8年,且只有3天的假期,在旅游产业的谱系上它的光芒仍然有些幽暗。
清明节的平淡在于它单单被误解为只是一个祭拜和哀思的节日,人们忘记了它还是一个合家出游的良辰美景,倾城而出的盛大节日;而作为祭拜和哀思的重要节点,过去的集体祭拜、亲朋好友在家族坟墓前与祖先同饮同食,如今变成了素不相识的、来来往往的众人在国家公墓里,各自对着各自亲人骨灰盒独自凭吊,或安静,或喧嚣;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便利的交通工具让“时空压缩”[1]成为可能:时间克服了空间的障碍。然而,时间并没有真正地克服空间,在今天的中国,不可逆的城市化浪潮反而产生了当代中国人特有的“时空延伸”的疏离心态:与已故的亲人之间巨大空间,仍然横亘在异乡人回家的路的面前,而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1 被误读的清明
今天我们一提起清明节,很多人脑海中首先呈现的是杜牧那首著名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场景,殊不知清明节在唐宋时不只是“寒食家家送纸钱,乌鸢作窠衔上树”的悲恸时刻,也是“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的盛大节日。清明节从唐代开始成为一个融合性的节日,唐宋时期的清明节融合了时间相近寒食节的上坟习俗和上巳节的春游传统,并最终在宋朝以后取代了寒食节和上巳节,作为一个既是慎终追远的纪念日,又是全民欢愉的节日,清明节成为全国性3大节日之一。
清明节在唐代之前,只是一个节气存在,并不是一个节日,“在唐代以后才逐渐融合了时间相近的上巳节、寒食节的习俗变成了一个以踏青、扫墓为主要活动的节日”[2]。
上巳节的历史最为悠久,形成于春秋末年,最初巫术气氛较浓,节日内容主要为河边沐浴,祓除不祥,并在河边招魂,后来节日的宗教性日益削弱,发展成为户外踏青的重要节日。因此,杜甫才能留下他的不朽名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3]。
寒食节和清明在时间上最为接近:寒食节在唐代规定禁火3天,这3天为冬至开始算起的第104天,第105天,第106天,分别为大寒食、官寒食和小寒食,而小寒食正是清明节。寒食节起源“三月应禁火”的民间信仰,寒食节的主要活动为:祭祀祖先和去世的亲人、春游和饮食[4]。宋代以后寒食节吃寒食的习俗日益衰落。
清明节盛大的春游传统在今天的中国逐渐消失了,这种地域性的出游被穿越时空的个体化旅游所替代,各种传统集体性、面对面的娱乐活动:荡秋千、斗鸡、拔河、蹴鞠也被现代组织化的体育运动、虚拟化的网络游戏所消解。
清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别的节日,特别在于它是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它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清明节不仅是对逝者的追思,也是对现世生活的热爱。
宋代高菊卿的那首《清明》正体现出这种智慧: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5]。
曾经,铜仁地区的“挂社”和“挂青”体现了这种人生智慧。
2 清明之祭拜
2.1 社日习俗的流变
提到社日,也许今天大多数人脑海里一片空白,即使是贤者,比如鲁迅,他对家乡盛大的戏曲演出时间也不甚了解,也关心具体为哪一日子,他称之或许为“社戏”罢了,可以看出“社日”在近代中国地位之一斑。
社日,和清明相去不远,在今天中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消失了,可是社日这个与农业息息相关的节日,在元代之前的中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在中国古代社会,农耕时代的人们对土地非常崇敬,在社日当天祭拜土地神,以祈求风调雨顺,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一个乡土社会中民众娱乐的节日,人们在社日当天停止劳作,击鼓喧乐,放歌纵酒。在汉代以后,一年有“春社”和“秋社”两个社日,汉代以后,社日时间一般确定在立春后第5个戊日(春分前后),立秋后第5个戊日(秋分前后)。社日在元代以后开始衰落,后来逐渐淡出历史的视野[6]。
然而,这些古老的习俗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保存了下来,并产生了新的形式和内容。贵州省铜仁市和周边的一些地区至今还保存了“挂社”的习俗,“挂社”在附近有些地区也称为“过社”[7]。铜仁市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山区,与重庆市秀山县、湖南省凤凰县接壤,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土家族、苗族、侗族等世代居住在这里。从秦代起,这里的不同区域就分属于西南地区不同的郡,在长期与中原文化的接触中,当地居民受到汉文化重视宗族和祖先的影响:直至今日,春节当天,很多人家会在在堂屋祭祖,有些地区会在堂屋贴上“天地君亲师”的字幅,进行祭拜,形成了他们的独特祭祀传统。
2.2 盛大的“挂社”
铜仁地区“挂社”的祭拜对象与中国古代社日有所不同,铜仁地区祭拜的对象为刚过世3年的亲人。为什么要提前祭拜,不在清明节祭拜呢?有学者运用6 000多年前中国古代“二次葬”原始风俗进行解释,死者的遗体在历经3年之后再次埋葬,死者的灵魂会更洁净[7]。我采访了当地几位老人,他们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解释:这些人刚走,在下面吃的东西不多,如果清明给他们送东西,他们的东西有可能就被别的人抢走了。这种民间的解释也许更能反映当地人们的社会心态。
农业社会的节日总是和饮食密切相关,铜仁地区的人们也不例外。他们会在社日到来之前在地里采摘刚发芽的野葱和野菜,采用自己家里饲养的土猪肉腌制的腊肉同当地的糯米一起蒸制,做上具有地方特色的“社饭”。“社饭”在物质水平匮乏的时代属于稀缺的美味珍馐,我采访了当地一位年过40岁的中年女性得知:在她小时候,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他们家人只有在过年才能吃上猪肉,而且只是猪头肉。因此,这种珍贵的食品,而且带着象征大自然的生命力的野菜,足以让九泉之下的亲人感到满足。
在社日当天,死者的家人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死者的墓地,有时甚至有近百人,家人带上从家里做好的“社饭”和酒菜,亲朋好友带上鞭炮、纸钱。他们先清理死者的坟头,插上新的“飘坟”(一种木棍,上有纸钱),放鞭炮、烧纸。完成这些庄严的仪式后,大家坐在死者的墓地前,开始开怀畅饮,和死者一起分享食物。马林诺夫斯基说过:“所有用献祭的方法与一切神祗分享丰富的食物,便等于与一切分享这天意底嘉惠了”[8]。而在参与“挂社”的铜仁民众看来,这种行为并没有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神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和已故亲人、朋友的分享,这种分享是一种友好的分享,和中国人“现世中心的倾向”的思维[9]有关。同时,他们也相信他们的照顾会让九泉之下的亲人生活得更好,将来老去后,后代仍然会像他们一样对待去世的亲属。这种思维是中国乡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是许烺光所谓的“相互依赖”[10]的心理。“挂社”结束后,参加“挂社”的每个人会带上一些“社饭”回家,作为对死者的思念。“挂社”的兴起也类似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被发明的传统”[11]。20世纪90年代,铜仁人在经济生活开始好转后,“挂社”逐渐兴盛。
2.3 惯常的“挂青”
在铜仁人的心目中,清明节上坟称为“挂青”,不如“挂社”那样重要,因为死者已经过了难熬的3年,顺利地安息在家族墓地中,也不像“挂社”那样热闹,不会有那么多亲朋好友共聚在墓地前,当然,也没有美味可口的“社饭”。
铜仁地区多山,墓地也基本在山上,一个山上分居着家族中故去的人们。清明节前后,每家每户只是派出几个代表,带着一些普通的酒菜和铜仁当地的小吃——米豆腐上山,祭拜仪式过程和“挂社”相同,只不过大家吃的是米豆腐,而不是“社饭”。
家族墓田,一直是中国祭祀的一个重要场所,和居住的房屋不仅在空间上存在联系,也在一个连续、稳定的意义系统中。许烺光在《祖荫下》中就指出:云南喜洲的房屋分为阳宅和阴宅,二者在一个系统中,阴宅即是家族墓地中的坟墓,祖先的身体住在坟墓中,灵魂居住在家里的神龛里,祖先一直和家人住在一起,保佑着家人。世间的人们和刚过世的亲人仍然还保持一种连续性的亲属关系,他们相信,已故者对子孙是善意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一直怀着一种敬意和思念[12]。而在铜仁“挂社”3年期间的人家里,新的坟墓也会影响阳宅的装扮,房屋上的对联由喜庆的红色变成肃穆的白色。
家族的清明节不如“挂社”那样热闹,只因为清明节承载着家庭的回忆,更确切地说,清明节是成年人的追思,特别是失去父母的成年人,而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欢聚的日子。下面是我访谈的一位在深圳工作,铜仁籍公司女白领Z女士的追忆:
“我从没读过博尔赫斯的书,只对他的一句以讹传讹的印象特别深刻——“记忆建立时间。”也许每个人的清明记忆开始于生命的离去,特别是至亲之人离开人世之时。我的清明记忆也是这样:它始于奶奶去世后的第2年,那年我刚9岁。9岁之前,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个清明,仅仅是万物复苏中某一天,“清明”在我脑海中一片空白。
9岁之后,清明对我来说是一幅欢快的画卷,随着时间流淌慢慢展开,日渐清晰起来:清明前后的某个星期天,和风细雨之中,我跟随父辈的脚步,踩着泥泞的土路,来到山林中祖坟旁,坟地里的土坟看上去就像一个个标准的圆锥体,奶奶的圆坟就在坟地的边缘。2年后,爷爷与奶奶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坟墓成为了这块墓地中最大的圆锥合体,每一年我们都会把坟墓周围的杂草清理掉。
祭拜仪式每年都一样,如同被一块“木板年画”刻出来:鞭炮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之后,我们将纸燃烧,纸的灰尘如同一只只白色蝴蝶的飞舞在空中,消逝在风里,不知道爷爷奶奶在地下有没有收到子孙们送来的巨大“财富”,纸钱即将燃尽之时,我们依次来坟前磕头跪拜,口中诉说着对逝者的思念和祈求。清明不止是对逝者的追思和怀念,更准确地来说,不止是父辈们对他们的父母的哀思,每次祭拜之时,我最爱同表弟嬉戏在山野中。祭拜结束后,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吃春天特有的食物——蒿菜粑粑。
直到我的父亲去世后,我才能体会到我小时候父母在墓地时的情感,可是由于我在深圳工作,没有办法参加父亲的“挂社”,然而我在心里牵挂着父亲,想着他曾经的教导:努力成为有用的人,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每到清明,我总是想回去看看父亲的坟墓,和父亲交流现在的工作、生活。虽然祭拜仪式很简单,但是和家里人在一起看到父亲的坟墓,大家觉得像是回到了从前在一起的时光,我很满足。
无论是“挂社”,还是“挂青”,都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家族墓地是他们寄托哀思和安放身后之地,埋葬在土中更是体现了乡土社会中人们对土地的感情,人与自然形成了被紧密相连。今天的铜仁,“挂社”和“挂青”,在各种因素影响下都日益变得形式化。
3 节日的时空变幻
节日之所以成为节日,在于节日具有社会性,也就是同一时空下的个体在同一规则指导下集体行动,行动产生的集体回忆作为经验不断地向下一代传递,形成一个稳定的时空秩序。而遗憾的是,节日的外在世界总是在不断地变迁,节日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变化。
3.1 家族墓地到国家公墓
中国目前最大的家族墓地也许是孔林了,不过在中国也只有孔氏后人才能享受到这份荣光。1997年,国务院出台《殡葬管理条例》,在汉族为主要居民聚居区,开始推行火化政策。虽然这个政策已经推行了近20年,可是一些老百姓仍然抱有极强的“安土重迁”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种记忆的传递,是一种“实质性传统”[13],在稳定的生活环境中日积月累中形成的固有思维,形成一种“文化的文法”[14]。
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中提到两个案例,都反映了中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一个是当时海外华侨想方设法死后安葬在老家;另一个是费孝通自己家族的案例,他的一个老祖在云南做官,不幸染病,客死他乡。他老祖的亲弟弟放弃了中举做官的机会,不辞劳苦,努力工作攒钱,历尽千辛万苦将哥哥的棺材送回老家,其行为被族谱大书特书。也许我们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在过去则被视为天经地义之理。相对静止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父子轴”为优势主位的家族成员,特别是男性成员,认为墓地是其灵魂的安放之处,而无论是中元节还是清明节,家族成员的祭拜都能使其成为家族共同体的一员[15]。
《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至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铜仁,农村一些地区仍然保存着土葬的习俗,然而城市用地的不断扩张,让没有土地的市民不得不选择火化。
“据统计,到2050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16]。”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将经历城市生活,和传统稳定的乡村生活说再见。在告别乡村的宁静和“熟人社会”的同时,也割裂了人与土地的联系,割裂了与家族祖先的记忆。米歇尔.德.塞托说过:“空间就是一个被实践的地点”[17]。这种空间性的实践不只是产生一种空间,更产生了一种特定的空间经验,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记忆。之前家族性的祭拜是一种群体性、互动性的行动:与亲友相聚,与故者相连;而国家公墓里的祭祀行为则变成了以核心家庭为主的行动。祭拜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祖先变成了三代之内的直系亲属。随着岁月的流逝,孤坟、残碑也逐渐多了起来,曾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家族墓地日益消逝,每座公墓中的逝者周围变成了冷冰冰的墓碑。
3.2 地方性的时间到统一的时间
布迪厄在通过研究卡比尔人的生活发现,每个群体对应着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每种东西都有时间和场所[18]。同样,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发现了“时间范畴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节奏”[19]。而传统社会中,无论是“社日”还是“清明节”的祭拜,都发生在固定的农业生产时间关键节点上,也发生在有限固定空间,而且祭拜的主体是相对固定不变的群体。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皇权不下县的社会,是一个规范性知识为主体的伦理社会,市场经济并没有将中国变成一个节律统一的实体,不同地方社会拥有各自的时间节律,而这种时间是连续性和重复性的。
“现代化毕竟必需不断破坏时间与空间的节奏,而现代主义当作它的使命之一的就是在一个短暂与分裂的世界里为空间和时间创造新的意义”[1]。当铜仁周边地区的时空被拉入到统一的市场经济的节律中,曾经祭拜的主体,特别是年轻人开始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来到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的时间、生活节律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形成新的时间观念。农业社会中,国家规定的假期对人们来说意义不大,农业的节律才是假期的基础和依据。而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假期对工作体系中的人们来说意义重大。然而,中国并没有规定“挂社”的假期,即使是清明假期,也只有8年的历史。这也是上文提到Z女士的困境:她不能在“挂社”期间回家,而她这次清明节回家“挂青”在于全国统一的假期——清明节的设立。
3.3 历史的必然
新的空间和时间,改变了现代人对祭祀的态度。
3.3.1 现代性的旅游
清明节的一条新闻:清明期间代理扫墓的业务出现在杭州[20]。象征个体回忆和追思的祭祀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能被别人代理呢?现代社会中什么样的活动比清明祭祀更重要。
答案是旅游。令人深省的是:出游在古代是清明节重要的活动,集体性的踏青、面对面的斗鸡等游戏让人生活在相对固定的时空中。唐代开元年间,官方禁止寒食节上坟期间游乐,然而并没有多大的作用[21],如同启蒙运动中人觉醒之后,摆脱了宗教,享受世俗化的快乐一样,出游成为清明节的重要活动。
现代性的旅游不同于古代清明时节地域性的出游,现代旅游是一种跨越空间的体验,科技进步摆脱了空间的束缚,人们在资金允许的前提下,可以无障碍地欣赏到旅游机构提供的各种“景观”,不同于古代出游的单一。旅游和工作一起构建起了经济发展的循环系统,在当今社会旅游已经成为工作领域之外重要的休闲活动,成为现代人们特别是都市人的重要时空体验。旅游提供一种“景观”,这种体验是一种“凝视”性的体验,也是一种逃避枯燥工作的世外桃源的幻象。
德波认为“景观积累”已经取代商品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统治方式:“景观”塑造了消费者的欲望,全面控制了人们的闲暇时间,扩展了资本的时间和空间控制[22]。老子曾经留下了“五色令人目盲”[23]的警世恒言,而在市场经济中,这句名言被“景观”开发者和制造者充分利用,个体被“景观”所俘获。
3.3.2 无所不在的网络
如果说德波的“景观”是资本主义生产最重要的内容,那么莫兰则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传播途径,这是大众传媒制造出的“全景式”加“毛细血管”的“神经网络”,“一个奇异的神经网络已经在全球巨大的躯体上形成……没有一个空气分子不由于传输一部机器、一个操作会使它们很快变成可听见的和可看见的东西的信息而振动”[24]。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这个“神经网络”在21世纪愈加清晰和重要,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受到信息的影响,不停地在接收图像,消费图像带来的商品。即使是在清明节上坟期间,笔者在墓田里也能不断听到微信铃声、电话声和一些音乐声。科技的发达和娱乐化的时代将祭祀变成不能承受之轻。
“社饭”在今天这个美食家盛行时代的边际效应也不断减弱,逐渐由一种存在亲情和纪念的分享品逐渐变成了一种商品,标价7元500 g,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的各种美食图像令人目盲。
4 结束语
无论是国家性的清明节,还是地域色彩浓厚的“挂社”,我们都在表达一种对先人的缅怀和生命的思考。然而,当新的时空开始出现时,过往行为的意义才开始逐渐弱化,我们的行为也寻求新的意义:这个流动性的社会中,个体的欲望渴望新的“景观”,新的体验,来代替曾经“机械团结”[25]中人们集体性的行为。
然而,生命中总有一些难以替代的情感,比如对家的情感和故土的眷恋,就像希尔斯所说的,对于祖先的孝敬和尊重家庭权威是实质性传统的重要内容,“大多数人天生就需要它们,缺少了它们便不能生存下去”[13]。而海德格尔在晚年贯通东西方哲学之后,也把“存在”的意义放在“家宅天使”和“年岁天使”[26]之中。
惠特曼说过:“时间或是地点是无能为力的——距离是无能为力的”[27]。既然我们不能压缩时空,清明节,还是让我们返家,重温家的温暖,回味故者的哀思。
[1]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55,271.
[2]张丑平.上巳、寒食、清明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18.
[3]杜甫.杜甫诗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57.
[4]黄涛.清明节的源流、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功能[J].民间文化论坛,2004(5):18.
[5]谢枋得.千家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134.
[6]萧放.社日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6):27-35.
[7]贺孝贵.恩施社节[J].民族大家庭,2008(1):50-51.
[8]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2016:26.
[9]中村元.中国人之思维方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11.
[10]许烺光.宗族、种姓与社团[M].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2:72.
[11]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
[12]许烺光.祖荫下[M].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25-42.
[13]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1,327.
[14]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
[15]费孝通.中国士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02.
[16]詹姆斯.M.汉斯林.社会学导引:一条务实的路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856.
[17]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
[18]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61.
[19]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76.
[20]澎湃新闻网.清明代扫墓者拒绝代哭代跪:“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买到”[EB/OL].[2016-04-04].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452046.
[21]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439.
[22]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2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6.
[24]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25]迪尔克姆.E.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3.
[26]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
[27]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278.
Traditonal Custom and Space Transition of Ching Ming Festival
ZHANG Chi1,BI XIaonan2
(1.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e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57,China)
Ching Ming Festival, which was one of three big festivals in Chinese history, had converged the custom of tomb sweeping on the Hanshi festival and the convention of spring outing on the Shangsi festival. The custom of "Guashe" and "Guaqing", which happened in Tongren district of Guizhou province around Ching Ming Festival, are represented and analyzed in the article. The interdependence among Chinese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nature are elucidated by the custom of eating "shefan" collectively on Sheri and the worship at the family tomb. However, these activities were in a formalized trend which was resulted by the three factors: the family tomb which was replaced gradually by the national tomb had led to the disruption of the offspring and the ancestors; the local time which was replaced by the monolithic time had constrained "Guashe" and "Guaqing"; the travel across the time and space and the individual entertainment on the network had taken the place of the collective and traditional recreation on the Ching Ming Festival. So we need to realize the deep meaning: missing the forebear and home attachment are a "substantial tradition", no matter what "time-space compression" happen.
Ching Ming festival; Guashe; Guaqing; substantive tradition; time-space compression
G112
A
张弛(1985-),男,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消费社会学、文化社会学。E- mail:zhangchi2320085@163.com.
毕啸南(1988-),男,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艺术、跨文化传播。E- mail:bixiaonanjn@126.com.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015MZD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