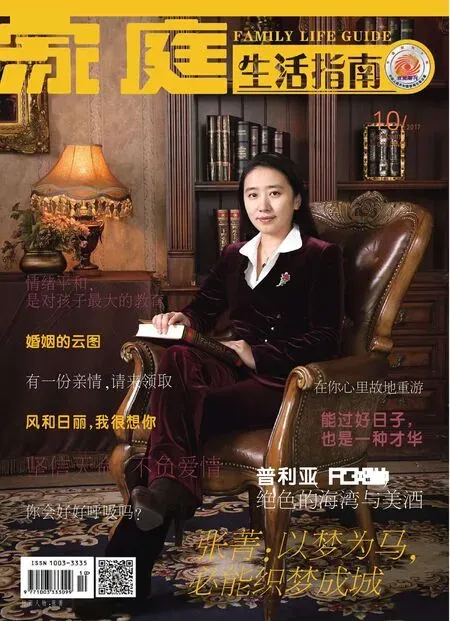在贝壳上给你写信
文◎南在南方
在贝壳上给你写信
文◎南在南方
总是不能免俗
阿朵对沈西说:“好好待我,如果没有爱,我就是一个孤儿。”沈西拥抱了她,他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爱你,我不会让你成孤儿的。”但是阿朵不相信,越来越不相信。
常常是夕阳时分,她会穿着柔软的棉睡衣坐在阳台上,沈西半闭着眼睛也坐在阳台上。多彩的余晖落在他们的肩上,世界很静他们很暖,两个人都喜欢这一小会儿闲暇时光。每次都有一个小程序是必须的过程,因为阿朵总是在这个时候悠悠地问他:“沈西,你爱我吗?告诉我你有多爱?你会爱多久?”她总是这样执着又不耐其烦地问他;而他呢,最开始是很痛快很快乐地应声做答:“很爱、很爱、很爱!”他的话特别肯定,让阿朵听了很安心很开怀。后来沈西就是点头,有时伸手拍拍她的脸,宠溺地轻声训斥她:“你这个小东西整天像个小老太婆,烦不烦啊?告诉你多少遍了还没完没了,爱爱爱!记住了?”
沈西的无奈和告诫没有阻止阿朵继续这个游戏,终于在这天黄昏,他终于怒火冲天了。他说:“你到底想要怎样?你告诉我,我到底怎么样你才能相信?你是不是病了?”
那一刻阿朵像是受惊的孩子,受惊的孩子还有母亲的怀里可以扑,她只是一头扎在被子里不言不语,被子的空隙可以呼吸,当然也可以听到他摔门而去的声音。这和阿朵想象中的争吵是不同的,没有喋喋不休和据理力争,就是那么一个过程:她柔柔地问,他傻傻地答,然后她再问,他就喊,然后她闭嘴转身,像是一个枕头一下子从高空落地就再也不能像皮球一样滚动,又像惊雷过后却没有下雨,片刻就恢复了宁静。
就在那时,阿朵决定自己去看海,那是她的梦想,她还没有看到真正的海。她想那明净的水可以让她的心安宁起来吧。当然她心里也闪过想要想一头扑进海里再也不出来的冲动。
她不知道如果不离开家会不会孤枕难眠,不过她奇怪自己竟然没有流泪。她没等沈西回来,她去了火车站。阿朵总是有些奇奇怪怪的话对自己说,比如现在她在心里轻声赞叹:火车真是好东西,只是一夜,就可以带我到烟台。
烟台好静,每个空间都不那么大,转一个弯儿就是一片高楼大厦,她直接去了沙滩。然后在刘公岛的海边,阿朵从中午一直坐到黄昏。太阳一点点地往下掉,海也变黑了一些,静默而安详。孤单突然袭击了她。很早的时候听人说日落时分感觉忧伤,每次看见夕阳时,这句话就跳了出来,像是一个咒语。而且她并没有来得及欣赏夕阳无限好就感受到夜的深沉。
当四周越来越寂静时,她不能不想沈西。沈西是她的一个同行,一年前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看到沈西的第一眼,你是不会记住他的。但他一开口说话,你就再也不会忘记。他那极富磁性的声音、幽默风趣的话语,像是能俘获任何人。她第一次见他便被吸引了,接着他们就恋爱了,接着就在一起了。他们挽着手逛街时会买一个甜筒,她一口,他一口,小两口的样子。
她的忧伤是从她想结婚没有得到回应时开始的。某一天她说我想结婚了。其实她一说出口就有点后悔了,她想婚要他求才好啊。但接着她就真的后悔了,因为他竟然没有明确地回应她。这远远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他应该瞳孔放大,就是不放光,至少也该闪亮一下,因为一个女子肯下嫁一个男人,总该是他的荣幸吧?
她看不见他的眼睛,他只是垂下眼睑说:“这样不是很好吗?”她很认真地想了想:“是很好的,可是……”
她想说的是:可她不能免俗;可是如果爱,又怎么不想结婚呢?这是一个让她憔悴的问题,至今也让她心力交瘁。于是她不再去想,她站起来了,走向了海,她想让脚底去感受沙子的剥离,让潮水涌上脚踝。
恋爱就是“我真傻”
潮声低沉,一波又一波涌上来。阿朵定定地站着想:其实爱也是这样的。源源不断、不能将息。她试着朝前走了几步,就在那时,一个不大的浪头竟然将她推得向后仰去,尽管她想努力站稳,可她还是一个踉跄倒在水里。水很浅,可她的裙子全湿了。
她狼狈的样子突然引来了笑声。她双手想要护住自己,可是她身体的细节还是一览无余。这时,一件宽大的T恤衫递在她手里。她顺从地接受了,迅速穿上。她转身,一个年轻男子看着她,笑意盈盈地说:“你倒下的样子很好看呢。”
她笑了一下说谢谢。那男子便直挺挺地向后倒下去。那滑稽的样子惹得她咧着嘴笑了。
原来他也从北方来,他叫林朗。他们一见如故,很熟络地并肩坐在那里说话,直到暮色细雨笼了下来。
林朗先站起来,把手伸给她,拉她起来。她起来了,他的手也没有收回,就那样拉着手去不远的地方吃海鲜烧烤。吃完烧烤,他就带着她去了他住的小旅馆,安顿她住下来。他说住在隔壁,绅士一样道了晚安,告辞了。
阿朵把他的衣衫洗了,挂起来,像挂着心事。她看着手机,信号是正常的,可她没有收到沈西的消息。她的脸一点一点痒了起来。对着镜子看,她吓了一跳,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一脸的红斑。
她敲了林朗的门,她说:“你看看我的脸怎么了?”林朗非常近地看了她的脸说:“应该是过敏了,肯定是吃海鲜落下来的。”他立刻出了门,不一会儿买脱敏的药回来,拿来了水看着她吃下去。
他说:“别回你屋了,一起说话吧。”她要他关了灯再说,因为脸上有斑。他轻轻笑了说:“原来爱美与臭美有时候是一样的。”
那是个有月的夜,他们先是坐在那里说话,后来他说不如卧谈吧。说着就躺了下来,一个人一张床。他们也说到了爱,他就问她:“女子在恋爱最大的秘密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点绕口,她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说:“有个女子丢了邮箱密码,系统引导她找回,密码提示问题是:你最大的秘密是什么?女子输入初恋情人名字,不对;输入第一次和男友约会的时间,不对;输入她暗恋很久的偶像的名字,也不对;女子咬咬牙,输入共度良宵的饭店,还是不对。女子生气了,她打出三个字,我真傻。哈哈哈,立刻找回了密码。”
她笑了说:“这个故事可真讨厌啊。”不知什么时候,她便睡着了。在梦里,她梦见林朗亲吻着她,她紧闭着嘴唇躲他……她醒来时,看见林朗趴在那张床上睡得很香,她看着他,心里滑过一丝柔情。
第二天,阿朵的脸看上去好了一些,她和林朗结伴出游,去看了烟台的旧街市,看了海天广场,然后再一次去了海边。转眼又是落日了,他们站在海边。那时他从怀里掏出一只海螺,吹了起来: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一曲完毕,他看着远处说:“阿朵,你要快乐。”只这一句,就让她的眼睛突然一酸,接着就湿了。两个人都沉默下来,回旅馆的路上,他再一次伸过手来,她把手给了他牵着。他坐在她的房间里,她要他再吹一次海螺。当那熟悉的曲子荡起时,她出神地看着他的嘴唇,她觉得很神奇。
也许她是凑得太近,他忽然环住了她的脖子吻她。他们像是水蛇一样缠在一起。她那时已经失控,如果他要求,她也顾不上什么了。但是他停了下来,他说:“阿朵,你要快乐,必须快乐,而我,却只是个偶然。”她的眼泪落了下来。他捧起她的脸,看了好久,他说:“我要记住你。”
他回他的房间了。
清晨她背着背包准备回家了,她站在他的门前,伸出手想要告别,没等她敲门,林朗打开了门。林朗接过她的背包,说要送她。去火车站的路上,他要了她的电话,他说:“也许某个时候会经过你的城市,我会去找你。”她说:“那一定要再见的。”
白色贝壳
沈西不在家。家里很整洁,一如她离开时的模样。拖鞋一如从前那样鞋跟朝外,这是她一直要求他做的。当她的目光停在梳妆台时,一支口红却刺激了她的眼睛,这不是她用的牌子。她没有多情地想是不是沈西买回来送给她的,她并没有太多恼怒和感伤。也许这是沈西用心整理过的房间,但还是露了破绽。
她相对从前确实很安静,想起一句话:爱情不过是曾经被彼此擦亮过,终归要燃尽,跌落尘埃。这世间对于情来说没有永远,一生所能够守候的大概就是爱的寂寞了。
这一次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物,没有犹豫和留恋。第二天沈西打电话过来道歉,他要她相信他不是故意的。她说他依然是个好男人,因为他把分手的话留给她说,她感谢他给了她一丁点儿的虚荣。沈西说其实他是爱她的。
她不想听他天真的话语,就挂了电话。爱没有其实,当他说其实时,他分明是有过比较的。而在爱情里,比较了就一定不是两个人的世界。
夕阳时分,她依然忧伤,这一次她的思绪只一会儿就飘向那个有海的地方。想起林朗,但她尽量不想那个有吻的晚上,她不喜欢自己有一点放肆的心思。
一个月之后,她收到一个包裹,她一眼就看出是林朗寄来的。那里有很多小小的白色贝壳,每一只贝壳上面都满了字。她试着把那贝壳排好,原来是一封信:
这是你走后,我在海边捡的,那时我就想着我在贝壳上给你写封信,想要告诉你,想念你。相遇得那么偶然,我在第一时间就爱上了你。但是我看出来你不快乐,因爱不快乐。那个晚上,我阻止了自己对你的疯狂,那是因为我决定给我们留下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至少不是由一夜情引发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快乐了吗?如果是的,就将贝壳丢掉。如果不是,给我一个消息……
终于间隔了许多天,她哭泣了,哭得酣畅淋漓,原来是因为爱。但是她没有给他打电话,虽然他的电话号码也写在小贝壳上面。她觉得日子像一块褪了色的棉布,但她要像蜘蛛,把它织成七色锦,她想让蓝色多点,那是大海的颜色;她也想让白色多点,那是林朗给她的贝壳。
最好的,她都给了沈西,那是永不再回的,现在想起来像是虚度了。她想她不会再爱了,可是在一个午后的黄昏,她手机传出来那个熟悉的号码,听见林朗说我爱你时,她却一点没有怀疑和停顿地说:“我也爱你!”
她不知道,原来阳光外向的林朗也会哭。在电话里他抽泣起来,他说幸福竟然如此毫无准备地击中了他。她轻轻地说:“你真傻。”
那一刻她看窗外的夕阳,原来是一抹玫瑰红,旁边的云朵是被玫瑰包围的白色,是她,她叫阿朵,可是也不是,因为那云朵分明长得很像贝壳,蒙上余晖闪着光泽。
编辑/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