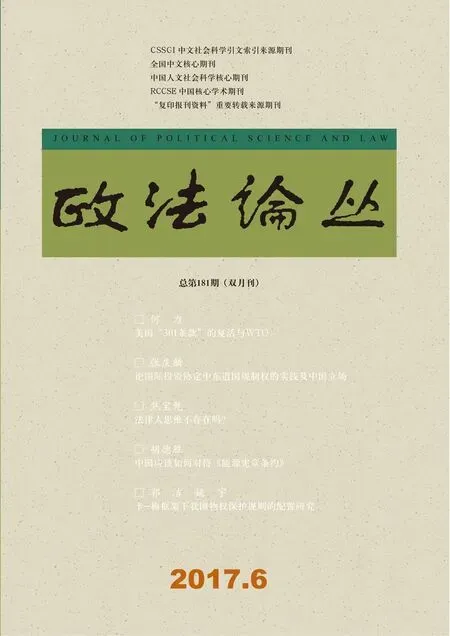从游走边缘到合入快轨:“赏金猎人” 迈向法治化的路径*
吴秋元
(江苏大学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从游走边缘到合入快轨:“赏金猎人”迈向法治化的路径*
吴秋元
(江苏大学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赏金猎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将市场规则引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有效手段。赏金猎人与私人侦探在涉及的领域及调查活动是否具有主导性方面均有不同。作为一种营利性群体,赏金猎人是刑事侦查的有益补充。赏金猎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存在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疑惑或者障碍不足为奇。赏金猎人的法律规则之治是其稳健发展的“绿色通道”。
赏金猎人 调查权 法律规制
通俗而言,所谓“赏金猎人”是指为获取警方悬赏通缉犯罪分子设置的悬赏金而协助警方抓捕悬赏通缉的犯罪分子之人。出于巨额赏金的诱惑,赏金猎人这一行业一直在顽强地生存着,并不断发展壮大;但由于赏金猎人行业在我国目前尚无法可依,致使这一领域仍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一方面,国家希望民众在对抗和遏制犯罪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打一场对犯罪分子的“人民战争”,通过全力协作和多方调查最终成功捉拿逃犯;另一方面,目前赏金猎人开展的刑事调查活动整体上尚处于无序状态,司法操作中可能会侵犯到公民权利。另外,赏金猎人的存在是否会侵犯侦查机关的侦查权,我国目前对于赏金猎人存在价值应持何种态度,等等问题,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此,本文拟就赏金猎人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赏金猎人”的元认知:根脉与特质
列宁曾经说过:研究任何问题,最可靠、最必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最基本的历史联系,因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怎么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些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P430我们认识、研究“赏金猎人”,也必须了解其根脉。“赏金猎人”原是动漫世界中的一种人物角色,出名于一本日本漫画书《铳梦》,特指依靠捉拿政府悬赏的犯罪分子来获得奖金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2]“赏金猎人”这一行当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格兰。当时英国法官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收取一定数额的保释金之后释放犯罪嫌疑人,罪行越严重,保释金额就越高。然而,并不是每个受到有罪指控的人都付得起保释金。如果想少交点钱,他就得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保证人提供一份保释保证书,作为回报,其需要向保证人支付一定的费用,通常是全部保释金金额的10%。但保证人也是要承担风险的,如果被担保的犯罪嫌疑人逃跑、不能如约参加法庭审理,保证人将要支付保释金。因此,一旦犯罪嫌疑人逃跑,不等警察追捕,保证人就会聘请赏金猎人来抓捕逃犯。赏金猎人一般会收取保释金的10%~20%作为追捕的报酬。[3]《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的1997年的“职业指南”中将赏金猎人列为未来的第二热门职业,文中声称,“只要看守所和监狱人满为患,该行业就有兴旺的可能”。[3]20世纪90年代初,在法律移植的大背景下,随着有奖举报犯罪机制的建立,诱于悬赏金的诱惑,“赏金猎人”这一特殊群体在我国也悄然兴起并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中不断发展壮大。
赏金猎人与私人侦探虽都是一群隐秘的职业群体且有相似之处,但赏金猎人与之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二者涉及的领域不同。目前赏金猎人存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赏金猎人专指针对司法机关发布的刑事悬赏广告而向其提供线索、举报、控告、扭送、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或罪犯,或是为司法机关打击犯罪提供其他帮助,并以此获取相应的报酬或赏金的人。而私人侦探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于婚外情第三者、个人资信调查、人事档案调查、保险诈骗调查、寻亲觅友、产品调查、个人犯罪记录调查等民商事领域。目前私人侦探介入刑事诉讼领域的尚不多见。另一方面,二者是否接受委托不同。赏金猎人一般是在看到悬赏通缉后积极、主动地开展相应业务活动;而私人侦探一般是接受委托之后才开始开展相关业务活动,相对前者来说,私人侦探所从事的调查活动具有被动性。从法律的视角对赏金猎人进行定位分析,笔者认为,赏金猎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赏金猎人是一种营利性群体。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P1而“利益源于人的需要。”[5]潜在的巨大利润正是吸引人们加入赏金猎人队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3]赏金猎人的主要业务是提供案件的侦破线索,帮助警方缉拿犯罪嫌疑人,从而获取悬赏金,这是一种基于营利为目的的有偿性的本身具有商品属性的服务。赏金猎人的调查协助行为与公共执法人员的服务行为有所不同,赏金猎人通过提供有偿服务来满足社会对私力救济的需求,并以此获取巨额的赏金作为对价,而警察等公共执法人员的服务不以收取任何费用为代价。
第二,赏金猎人的调查活动不同于刑事侦查权。上文已述,私人侦探的业务主要是来自于委托方的授权,而赏金猎人的业务来源具有主动性,一旦警方发布刑事悬赏的公告,赏金猎人就会积极踊跃开展各项调查活动,但是这种调查活动与刑事侦查权不同。侦查权属于公权力的一种,来自于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警察行使侦查权属于“羁束性执法”,[6]P383不容推卸,否则就可能构成渎职。而赏金猎人的调查活动属于私权利的一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即使中途放弃,也是由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只是在双方纠纷不能协商‘私了’时,才由司法机关介入裁决”。[7]P248但即使这样,其也无须承担公法方面的法律责任。易言之,从本质上说,刑事悬赏完全是私法上的行为,而非公法上的行为。站在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悬赏部分应当属于合同法中的“要约”,该“要约”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了正式书面声明,任何行为人只要愿意完成“要约”规定的行为,就构成了合同法上的“承诺”。“要约”与“承诺”达成了合意,悬赏合同依法成立。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是一方当事人,“赏金猎人”则是另一方当事人,亦即相对人。[7]由此可见,赏金猎人的调查活动显然与刑事侦查权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三,赏金猎人是刑事侦查的有益补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然而公众要求增加安全预防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但警力不足及警察工作效率的低下又使得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下降。“而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刑事犯罪发案率的持续、大幅上升,不仅仅是由于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对于严重刑事犯罪高发及其危害的认识和工作均不到位,打击、治理不力,还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理念、模式、制度并未能及时地更新、改革、完善。”[8]P1428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警方力量是无法全面有效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作为社会公众力量的赏金猎人的介入不啻是一种新尝试。赏金猎人不论是在追寻通缉要犯方面还是在诱捕毒贩方面,均节省了大量的警力和经费,可谓一项节约司法资源的措施,[9]同时也给犯罪分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谓是刑事侦查的一种有益补充。
二、我国“赏金猎人”聚焦:现状与疑问
在我国,赏金猎人作为一种新生体,难免遇到“成长的烦恼”。我国的赏金猎人分布较为零散,大多是单枪匹马地在战斗,尚未形成一股集体的“暖流”。受传统文化的“糟粕”及“文革”“亚文化”的影响,赏金猎人在人们心目中往往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现而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在人们看来,向司法机关报案和举报违法犯罪是公民应负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而赏金猎人为了贪图一点酬金协助司法机关缉捕案犯,只能说明他们只不过是一群逐利弃义、不明是非的“小人”。赏金猎人本来就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加之我国缺乏相关的立法和制度保障,他们常常遭到打击报复并不奇怪。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 90 年代每年不足500 件,到2008年上升到每年1200多件。鲜活的数字是一种无声的“呐喊”:真可谓“英雄流血又流泪”!另外,许多赏金猎人在行为之中往往滥施权利以及缺乏执法方面的必要的培训也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赏金猎人不受规制的权力、缺乏训练、追捕中的冲动兴奋、潜在的金钱报酬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火药桶’”。[3]
赏金猎人本来在解决我国警力不足、扩大就业、遏制犯罪等方面存在巨大价值,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执业活动也饱受诟病。赏金猎人在调查案件时其行为的“界限”常常“自由地”游走于法律的边缘。赏金猎人这种调查活动的“自由性”是目前这一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赏金猎人的案件调查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对于普通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赏金猎人这一职业群体的社会评价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产生以下疑问也就难免:
首先,赏金猎人是否侵犯侦查权。刑事侦查机关在采取秘密侦查手段前一般是需经过相关部门严格批准的,其取证的手段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均规定,如果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相关的证据,经过查证属实以后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与此不同,我国立法对于赏金猎人缺乏相应的规定,进而导致了其身份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身份则恰好给这一行业带来了“曙光”,相较于受到诸多限制的警察而言,赏金猎人实践中施展“技艺”存有较大的空间:“法无明文禁止便可为”,赏金猎人会采取诸如监视、隐蔽调查、卧底侦查等各种手段。赏金猎人施展空间的广阔性还体现在“网络”上:这种网络一方面是指虚拟的计算机数据库。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要想成功,赏金猎人需要靠情报消息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还指现实生活中的“线人”网络。除了靠一些科技的行为手段之外,确实还需要有自己的“人脉”网络。利用此两种网络可对信息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及研判,这样不仅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还能够弥补官方情报的不足。
即便是有关于赏金猎人专门立法的国家,也大多对其行为没有作出详细具体的说明,这同样给其施展空间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例如,在美国许多州,赏金猎人被授予了令经过专业训练的警官们都羡慕的权力。特别是,赏金猎人可以合法地不经取得令状就闯入嫌疑人的家中,使用必要的强制力量逮捕嫌疑人,不经州的事先授权就可以搜查和监禁嫌疑人。这些现实中赏金猎人享有的权力,是许多警察的梦想。[3]
赏金猎人施展空间的广阔性与便利性不免会使人产生疑问:这是否会侵犯侦查权。笔者认为,就我国而言,赏金猎人参与刑事案件的调查时,仅允许其采取暗访、跟踪等一些专门性的调查工作,其无权实施侦查机关的各种强制侦查行为。因而,笔者认为,赏金猎人在找寻“猎物”的过程中行使的不是侦查权,而是调查权。换言之,赏金猎人所行使的调查权其性质迥异于专门的刑事侦查机构的侦查权,赏金猎人的行为是不会侵犯专门的侦查机关的侦查权的。
其次,赏金猎人是否侵犯他人隐私权的问题。应当承认,赏金猎人在获取犯罪信息的过程中,难免会采取监听、暗拍、跟踪等手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或无意干扰其他人的生活,有时还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以监听为例,在美国,由于获得监听设备很容易,因此监听的使用在美国较为普遍,甚至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由于缺乏资源和专门的培训、设备,也难排查监听器进而消除美国境内的技术安全威胁。法律没有对赏金猎人侵犯隐私权的特殊调查手段加以明确规定,这些特殊的调查手段虽然在理论中是被强烈排除的,但却是实务中赏金猎人惯用的调查方法。赏金猎人认为他们可以采取的调查手段是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由专门机关采取的侦查手段以外的其他任何手段。应当说,这样的理解显然有失偏颇。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由立法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赏金猎人可以采取哪些调查手段,不可以采取哪些调查手段。上文已述,赏金猎人在获取犯罪信息的过程中,难免会采取监听、暗拍、跟踪等手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或无意干扰其他人的生活,有时还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但是也应当注意,从民法上关于侵犯隐私权的成立条件来看,主张赏金猎人只要介入刑事案件就必然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的说法也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
再次,赏金猎人的职业活动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应当承认,在调查案件过程中,赏金猎人采取诸如跟踪盯梢、窃听、偷拍、偷录、化装侦查、陷阱取证等一些技术性的措施时的确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导致赏金猎人违规操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赏金猎人在我国属于新生职业,刚刚起步不久,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尚不高,队伍建设问题还有待解决。二是法律尚未对赏金猎人可以采取的调查手段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上述因素决定了赏金猎人是一群踩着法律边缘的执业者。队伍建设是基础,法制建设是关键。我们一旦解决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导致赏金猎人违规操作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三、“赏金猎人”的深度考察:正当性与必要性
赏金猎人的存在在理论根据上具有正当性,其主要理论依据有:
第一,符合“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20 世纪50年代由公共选择学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属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其研究重点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一种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物品,私人企业根据民众的不同需求提供私人物品。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都应为民众提供高效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器的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统一管理者,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一般采取的是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国家或社会的整体利益。面对庞大的国家,十几亿人口,零零总总的事务,公权力存在稀缺性和资源紧张的问题,政府无法面面俱到地使所有事物做到公平公正。由政府包办一切,全方位地干预,只会导致低效能。“在原本封闭的一体化社会,并非不存在利益诉求,而是各种利益诉求被宏大的政治话语所压制,同时由上至下无孔不入的国家组织承担着利益分配者与利益冲突裁断者的职能”,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利益诉求处于封闭状态”。[10]因此,我们应当打破这种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推动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社会力量的参与无疑是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好办法。“市场运作的基本逻辑是只要有需求,就会出现与之对应的供给,供求双方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各自的目标。”[11]允许赏金猎人介入刑事诉讼领域,使“纯粹的公共物品变为‘公’‘私’结合”,[12]可以增加社会公共安全服务的有效供给。一方面,赏金猎人的调查工作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可以有效地弥补国家侦查力量的不足。如果以立法的形式使其按照合法的程序进行运作,可以推动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有效运转,从而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鉴于目前我国司法资源的稀缺现状,赏金猎人可以成为国家司法资源的重要的补充。目前,公权力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一些大案和要案上,如果允许普通的个人依法参与一些普通案件,调动社会群众的力量,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调查取证,这无疑会助推案件的快速查处。总之,“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不断变化的复杂犯罪形势,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需要正视国家在犯罪治理中的负面效应,民间社会参与犯罪治理应逐步被国家认可,并得到国家的鼓励与支持。”[13]P25
第二,符合“私力救济理论”。赏金猎人介入刑事诉讼领域的正当性问题完全可以追溯到私力救济的正当性上。赏金猎人的存在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它是私力救济在公共执法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况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力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14]P102私力救济是非到不得已时而为之,当公力救济不能有效保障私权时,处于最低限度的自我求生和自我保护的本能,私力救济被运用。赏金猎人的刑事调查行为属于重要的私力救济行为。赏金猎人通过查找案件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不仅满足了被害人迫切抓到真凶的心理愿望,也能够有效地弥补我国警力不足的现状,是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一种有力补充。当然,赏金猎人的调查活动如果不加以任何制约而任其发展,也会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其负面效应很快就会暴露出来。我们应当发挥赏金猎人的积极作用,限制并疏导其负面作用。这种限制和疏导主要是通过精密细致的立法构建,使得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互配合,互为补充。通过法律的规制,使赏金猎人这一私立救济手段能够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得力助手,为其提供侦破案件线索,及时查明案情,进而又快又好地保护被害方的合法权益。
除上述正当性外,赏金猎人的存在还有其必要性。理由是:
第一,赏金猎人的调查活动是群众情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此条规定是刑事侦查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的法律根据。刑事侦查工作中的“依靠群众、抓住战机、积极侦查、及时破案”的方针,[15]P20是这一工作原则的具体体现。人民群众不仅可以在警察侦破案件时提供各种协助,而且一旦发现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还可以将他直接扭送给公安等司法机关处理。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一个重要线索和来源渠道,而赏金猎人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由于以获取赏金为职业,因此,其在专业知识、经验和技术上更具有优势,在破获案件、查找犯罪嫌疑人方面作用也更大。
第二,赏金猎人的存在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法律的实施是有成本的”。[16]目前我国在打击犯罪方面存在警力不足和经费匮乏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主要的侦查力量只能集中于一些大案要案的侦破上,因此,刑事侦查不得不充分借助于社会力量来解决侦查资源紧张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愈加频繁,人们之间联系的纽带在减少,人民群众支持侦查活动的积极性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有时候因为担心被打击报复,有些群众在获得相关案件信息线索后往往不敢提供给公安机关。相对于普通的群众,赏金猎人调查方式更加多元化、专业化,他们更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各种风险,保护自己,因此,由较为专业的赏金猎人专门给刑事侦查机关提供各种情报线索,会大大增加破案率,实现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
第三,赏金猎人的存在能够有效打击潜在的犯罪者。潜在犯罪人是根据预期的刑罚概率来决定自己是否实施某种犯罪的。当犯罪的预期刑罚成本增加,那些预期收益较小的犯罪将被威慑。[17]P36赏金猎人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提高了国家对犯罪设置的预期刑罚水平,其存在对潜在的犯罪者能够发挥“恐吓”作用。在美国,赏金猎人常常装备有豪华车、微型录音机、激光撬锁器、手铐、麻醉枪等先进工具,被犯罪分子称之为“影子杀手”。一名有经验的赏金猎人每年可以接80到150桩案子,大约可以挣5到8万美元。据统计,赏金猎人逮捕了近90%的弃保潜逃者,由于直接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赏金猎人通常比警察更有效率。[18]由于赏金猎人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他们就像“无形的影子”给犯罪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让那些有犯罪念头的人心生忌惮,这对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四,赏金猎人的存在契合了打击现代犯罪的需要。高智能化、集团化、流窜化是现代犯罪的重要特点,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这给侦查机关获取破案的信息、线索以及取证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犯罪分子总是隐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赏金猎人制度肯定了社会主体理性经济人的地位,利用市场规则,对他们的付出给与相对应的回报,这就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使得“再狡猾的狐狸也难以摆脱聪明的猎手”,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再强,也难以逃遁疏而不漏的法网。
四、稳健发展的绿色通道:“赏金猎人”法律规则之治
“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19]P256赏金猎人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如果赏金猎人的执业活动没有一个活动规则的话,其就可能侵犯他人人权。“法治是规则之治”。[20]“制定良好的法律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21]为了使赏金猎人的活动符合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对赏金猎人的立法规制势在必行。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使赏金猎人在身份和地位上有法律的保障,同时也进一步对这一职业群体的执业活动加以规制,以有效地提高其自律化的程度,并能及时地排除人们对赏金猎人执业活动的种种疑虑与猜疑。笔者以为,赏金猎人的法律规则之治,需要建立对赏金猎人的外部和内部的双层约束机制。
建立对赏金猎人的外部约束机制,主要是指从法律层面而言的。这是一种“正式控制”,这种“正式控制”的特点在于:“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法律直接赋予的强制性,制约那些偏离社会秩序以及与社会秩序相冲突的行为,其往往以国家法律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22]对赏金猎人的外部约束机制,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设立赏金猎人的资格准入制度,明确规定赏金猎人的准入资格条件。赏金猎人的活动是一种自主性很强的活动,所以其对个人素质和道德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赏金猎人能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开展业务活动,取决于他们的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准。在今后的立法中对赏金猎人的年龄、学历、经历、有无犯罪前科等方面应当做出规定。明确列举哪些人不具有赏金猎人的资格,加强监管的力度。笔者认为,赏金猎人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首先,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年满二十周岁。毫无疑问,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对赏金猎人最基础的要求。年满二十周岁的要求主要是从社会经验方面考虑的,年纪太轻难以胜任这一职业。其次,无犯罪前科并且道德品质一贯良好。赏金猎人的活动也是一种执法活动,这种执法活动的实际操作如果把握不够精准就难免会侵犯他人人权,况且现实中人们本来就对赏金猎人的执法活动存有种种疑虑与猜疑,因此,在赏金猎人的执业资格条件中设置“无犯罪前科并且道德品质一贯良好”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的话,“让品行不端者或先前的罪犯从事这一特殊行业,更可能引发犯法犯罪,引发民众对这一行业的恐惧。”[17]P173再次,具有高等学校法律专业的专科以上的学历或者非法律专业的本科以上的学历。学历属于文化素养的基础条件。赏金猎人的执业活动专业性较强,较强的专业性就对执业者的文化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而,在赏金猎人的执业资格条件中设置“具有高等学校法律专业的专科以上的学历或者非法律专业的本科以上的学历”的条件是合宜的。最后,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例如驾驶、摄影摄像、调查询问技巧、防身自卫能力等等。能否拥有一个包含着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科学知识体系是衡量一个专业群体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赏金猎人的活动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潜伏”式的“暗战”。在这样一场惊险刺激的“暗战”中,取得制胜绝非易事。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第二,限定赏金猎人的活动范围。对于赏金猎人的活动范围,应该在立法上明确予以规定。“法律不明确,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就会无限扩大,法律的权威和效力就会大打折扣。”[20]离开赏金猎人活动的适用范围,我们就无法对其执业活动进行限制和制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赏金猎人的调查活动不属于政府行为;另一方面,应明确赏金猎人性质是专门为获取悬赏金而提供犯罪信息资源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的服务范围不能涉及到刑事案件的侦查。具体来说,为打击犯罪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应当允许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不管是公诉还是自诉案件都允许赏金猎人的介入。鉴于赏金猎人调查活动的灵活多变性,如果允许赏金猎人在所有的刑事司法程序中随意地获得各类线索和情报,有可能会损害到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因此,对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和秘密的刑事案件,在没有获得相关机关的许可的情况下,赏金猎人应当被禁止介入。
第三,规定赏金猎人的调查手段。现行法律对赏金猎人的调查手段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巨额赏金的诱惑下,赏金猎人往往为了查找案件线索而使用多重调查手段,侵犯公民权利以及其他种种违法犯罪行为也时有发生。笔者认为,赏金猎人的调查手段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不应当将赏金猎人的调查手段仅仅局限于公开调查的框架内,否则其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的能力将会降低。但是,为了保证赏金猎人的调查手段不陷入一种无序混乱的局面,必须对这种多样的调查手段区分情形进行规范和限制。普通的调查手段:普通的调查手段即法律并未加以禁止,普通公众也可以采取的一些公开的调查手段,比如通过询问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了解情况,通过授权向政府职能部门、有关单位查询、调取有关资料,公开的录音录像等等。就普通的调查手段而言,由于这些调查手段通常不会涉及到侵犯公民隐私等权益,因而,一般不存在对其加以限制的问题。 特定的调查手段:赏金猎人调查取证的难度很大,他们的调查活动通常具有秘密性,而这些秘密的调查手段则有存在侵犯他人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可能。笔者认为,我们并不是想从根本上否认赏金猎人调查取证时使用特定的调查手段的合理性,我们只是说赏金猎人调查取证时使用特定的调查手段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且应当受到监督。要做到这一点,法律就应该对跟踪、暗访、秘密录音等一些赏金猎人常用的调查手段作出相应的立法规制。这样不仅可以使赏金猎人使用这些特殊的调查手段时有法可依,同时,对这些调查手段的适用适当加以限制和规范也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制度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不竭的源泉,没有制度创新社会必然停滞不前。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23]P135对赏金猎人进行法律规制,仅仅依靠外部力量的约束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积极探索针对赏金猎人的内部的自律约束机制。这是一种“非正式控制”。这种“非正式控制”,“尤其是对那些潜在存在的风险,以及在正式控制下不便于直接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22]改革开放后,在中央和地方一系列重要经济政策的鼓舞和推动下,我国各行业掀起了建立行业协会的浪潮,行业协会在规范行业行为以及调处行业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建立赏金猎人的行业协会制度不失为一种规范赏金猎人执业行为的良策,其能够发挥行业内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赏金猎人行业内部的保证赏金猎人具有品质德性的约束机制。
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和行业之间的中介组织,是政府和行业连接的桥梁,[24]其具有全面保障行业主体的私权利、并使之与公权力形成良性互动、构筑社会经济秩序的自我调节等作用。法律应允许设置赏金猎人的行业协会,这样既可以保障赏金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同时也可以对赏金猎人从业人员进行有效监督,保障赏金猎人践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赏金猎人行业协会应当包括以下职责:
第一,保障赏金猎人依法执业,维护赏金猎人的合法权益,为赏金猎人业务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当赏金猎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行业协会应积极提供帮助。当赏金猎人之间发生冲突时,行业协会应积极劝解协调。第二,组织赏金猎人学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赏金猎人执业的合法性。赏金猎人从业人员的从业活动是同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执法活动,这种执法活动法律性很强,而且,随着犯罪态势发展的复杂性、专业性的强度增大,对赏金猎人从业人员的法律业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组织赏金猎人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学习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制定行业规程和惩戒规则,以使赏金猎人从业人员的从业活动有据可依。行业规程尤其应当对赏金猎人强调如下禁止性规定:不得行使警察所有的拘留和强制权;禁止使用政府标识物、警用标识物,如警服、警笛、公章等;禁止使用警察专用器材;不得在执业中建议、鼓励、帮助他人违法;不得将业务转让给无私人调查从业资格证的人;不得进行执业欺诈;不得向无关人员披露调查活动中获取的调查文件;不得妨碍警察执法;不得对国家、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监视等等。[17]P174第四,加强人员素质培训,建立高素质的赏金猎人队伍。加强赏金猎人队伍的素质建设是其成功履行职责、提升业务水平的必要的条件,也是维护赏金猎人队伍整体形象、提高群众满意度的需要。随着犯罪态势的变化以及知识更新的加快,加强人员素质培训也属“为现实所迫”。实践证明,赏金猎人执业效果以及口碑的好坏是与队伍成员的素质高低成正比的。加强人员素质培训要注意时间短、内容专、针对性强、实用性好。组织赏金猎人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交流和经验分享是提升赏金猎人队伍素质的十分重要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司法经验”。关于司法经验的价值,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司法经验能够使我们发现有关法律所具有的便利之处或者不便之处,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富智慧的立法机构在制定某项法律时亦无力预见的。那些经由聪颖博学的人士根据各种各样的经验而对法律做出的修正和补充,一定会比人们根据机制所做出的最佳发明更适合于法律的便利运行。[25]P66总之,司法经验在法律技术、法律职业精神、裁判规则和裁判事实认定等方面均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适用。当然,对赏金猎人的执法水平自然也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总而言之,要通过构建赏金猎人行业内部的自律体制,逐步构建一套内部的管理制度,最终形成赏金猎人这一职业的纪律和道德规范,从而进一步规范赏金猎人的从业资格、从业范围、从业操守和从业纪律。赏金猎人如果违反了相应的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就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
综上,赏金猎人是既可以利用某些手段进行刑事案件的调查、又可以协助警方抓捕嫌犯甚至罪犯的辅助人。赏金猎人行业的发展虽有高低起伏,但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这中间虽难免会有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这一职业群体的发展还是平稳有序的。[26]就域外经验来看,不管英美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在司法实践中也都是认可一定程度的私人取证的。[17]P177目前我们需要更多的考虑的是如何通过立法对赏金猎人的实践操作进行规范从而“避免随意性”。[27]总之,完善立法才能使赏金猎人这一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从而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立法当先才能使赏金猎人这一行业尽快驶入法治的快车道,从而使其尽早地摆脱游走于法律边缘的尴尬境地。
[1]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马祥富."赏金猎人"的法律思考[J]. 铜仁学院学报,2008,6.
[3] 李忠民.美国商业保释和赏金猎人制度评析[J].人民论坛,2010,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 曹爱军.论公共服务的行动逻辑[J].甘肃社会科学,2016,1.
[6] 李龙.法理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 郭道晖.法理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8] 张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与适用[A].赵秉志主编.当代刑事法学新思潮(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 吴占英.论坦白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政法论丛,2015,4.
[10] 曹胜亮.社会转型视阈下经济法价值的实现理路研究[J].政法论丛,2016,3.
[11] 赵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住房保障的困境与出路[J].政法论丛,2016,1.
[12] 马惊鸿.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属性反思及法律制度创新[J].政法论丛,2016,2.
[13] 卢建平等.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A].赵秉志等,主编.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上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4] 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5] 公安部教育局.刑事侦查学教程[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16] 宁立标.印度食品安全的法律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政法论丛,2015,1.
[17] 李忠民.美国刑事商业性私人参与研究与借鉴[D].西南政法大学,2012.
[18] 罗小龙.令罪犯闻风丧胆的赏金猎人[J].科技杂谈,2010, 4.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 张志铭,于浩.现代法治释义[J]. 政法论丛,2015,1.
[21] 陈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趋向[J].甘肃社会科,2016,6.
[22] 魏红.如何发挥社会控制在防控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作用[J]. 政法论丛,2016,2.
[23] 方晓.和谐社会与律师刑事诉讼法职能[A].康均心等,主编.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建设[C].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4] 王俊华.WTO与政府谈判体制改革[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4.
[25]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26] 王恺.私人侦探调查行为实证研究[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3.
[27] 张兆成.县级政府权力结构之变革与重塑[J].甘肃社会科学,2015,4.
FromWanderingEdgetoFittingintotheFastTrack:thePathtoLegalizationabouttheBountyHunters
WuQiu-yuan
(Law School of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As a companion of market economy, bounty hunters are an effective means to introduce market rules into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social security. A bounty hunter is different from a private detective in the related fields and leading character of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The bounty hunters are different from private detectives. As a for-profit group, bounty hunters are a useful complement to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s a new thing, the bounty hunter has its legitimacy and necessity.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some puzzles or obstacles are encountered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rule of law of bounty hunters is the "green channel" of its stable development.
bounty hunters; investigative power; legal regulation
1002—6274(2017)06—133—08
DF793
A
本文系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青年课题“刑事悬赏制度研究”(14SFB30025)、江苏大学高级人才专项资助项目“悬赏通缉制度研究”(13JDG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吴秋元(1982-),女,安徽六安人,法学博士,江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刑事侦查学。
(责任编辑:唐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