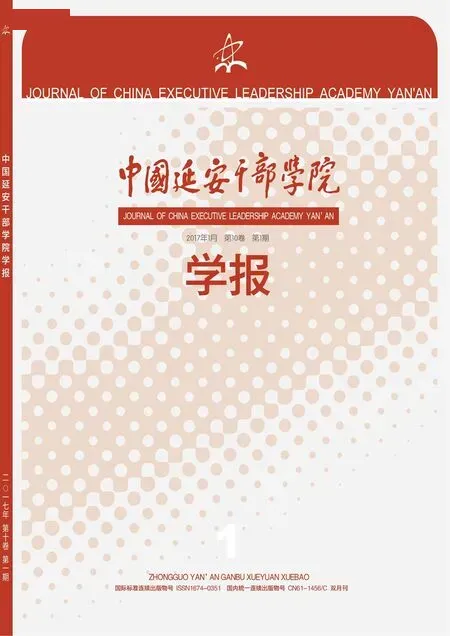民主社会主义何必以晚年马克思主义作伪装评《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
——民主社会主义》
陈文通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北京海淀100091)
民主社会主义何必以晚年马克思主义作伪装评《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
——民主社会主义》
陈文通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北京海淀100091)
以《选择》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期由“暴力社会主义”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资本论》第三卷和恩格斯为“马克思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否定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构成“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导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是“最后遗言”。然而事实证明,这纯粹是谎言。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基本理论方面是前后一贯的,从来没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不存在“晚年”否定“早年”的问题。股份公司作为资本和企业的社会化形式,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导言》对18世纪中叶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指出经济条件、群众觉悟、斗争方式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以合法手段进行斗争并不是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为最后的“决战”积蓄力量。本文的目的在于剥开民主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伪装,揭穿和批判编造的一系列谎言。
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批判
引言
题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1]一文(以下简称《选择》)在网上流传,并受到一些人的热捧。有人一方面肯定作者真正读懂了马克思的著作,一方面肯定民主社会主义包含了社会主义成分;更有人进一步借题发挥,力图以民主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仅仅是欣赏和推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做法,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遗言”执行者的面目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基础”,而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并力图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不能不令我们格外关注了。
《选择》的最主要之点有二:一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从暴力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说,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恩格斯的《〈马克思论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简称《导言》;马克思该著作全称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简称《斗争》)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二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勾画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说,经济上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定: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概括地说,以《选择》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前后两个阶段——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两条道路”:早期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为标志,走的是“暴力社会主义的道路”;晚期以恩格斯的《导言》和《资本论》第三卷为标志,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后一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武装斗争,放弃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消灭资本主义,“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那么,实际情况如何?需要对《选择》引述的内容和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进行考证和分析。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政治纲领
在逐一揭露和批判以《选择》为代表的一系列谎言之前,需要从总体上说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和政治纲领。
(一)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自称“高级资本主义”。《选择》的推崇者说,资本主义分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高级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或者说,“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总之,今后世界上只有一个“主义”: 高级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合二而一,实现世界大同。然后将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超级资本主义阶段。
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形形色色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者毫不隐晦地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二而一”,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如果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至于所谓“世界大同”,完全是骗人的。世界大同不过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说法,应当是没有对立关系、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只要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管是“高级阶段”还是“超级阶段”),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就必然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必然存在资本之间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就必然存在贫困(至少是相对贫困)、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
民主社会主义的始祖是当年法国的“社会民主派”。第一,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和改造社会的主张,不是来源于当年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是来源于当年法国的小资产者和工人联合而成的所谓“社会民主派”,即新山岳党——具有“社会主义的锋芒”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党。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它力图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而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2]613-614当时,“社会主义”这个口号很时髦,甚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处在两个发展阶段的直接对立物,在这二者之间不可能划等号。“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这纯粹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臆造和幻想;如果指的是资本主义(不管是高级的还是超级的),那就无所谓“长入”了。如果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高级资本主义”,那么,“高级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倒是可以成立的。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不包含社会主义因素
“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民主社会主义者说,社会发展存在一对矛盾,处理得不好,会发生社会动荡,若处理得好又会相辅相成。就是平等与效率。人们追求发财致富,就要发明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追求生产效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副作用是扩大了社会占有的不平等,甚至贫富悬殊,于是人们又要追求占有平等,用社会主义来表达。按照这种说法,平等和效率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追求效率,带来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而平等的要求就是社会主义,解决效率和平等的矛盾的途径,就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必须指出:第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无非就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些都依生产的社会形式的不同为转移,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平等和效率的矛盾”。在对立的生产方式中(无论是人的依赖关系还是物的依赖关系),基本的矛盾都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是由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方式产生的矛盾;在共同体社会中,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力之间没有对立的矛盾。第二,平等和效率都是历史的范畴。在资产阶级社会,平等和等价交换、市场竞争、平均利润相联系;效率主要是资本增殖的效率。因此,二者之间没有矛盾。资本就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利润)的。所谓矛盾,纯粹是主观想象造成的,是把平等(或者公平)理解为收入均等造成的。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的不是“生产效率”,而是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生产效率不过是资本增殖的手段。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贫富悬殊,还有雇佣工人的失业和经济危机。
所谓“社会占有的相对平等”的核心是保持私人占有。民主社会主义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主张有限度的社会占有不平等。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就是调节社会占有的相对平等,防止极端平等和不平等,促使社会大多数民众积极向上争取对社会作更大的贡献,以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幸福。这里把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和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混为一谈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等量劳动相交换),而不是按需分配。但是,这种分配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社会直接占有为前提的。所谓“社会占有的极端平等”无非是社会直接占有,消灭私人占有。如果否定了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也就否定了按劳分配。如果允许“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即使是“有限度”的,也只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分配方式只能是所谓“按要素分配”。问题还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调节社会占有的不平等”是根本做不到的。政府对居民收入有可能做出一些微调,但空间很有限,任何调节都不能违背资本的本性,都不能导致消弱资本的竞争力,否则,“资本的生产力”就不能发展。
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截然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当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截然不同。一是以所谓“平等”的要求代替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和消灭阶级的要求。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着眼于分配关系的调整,而不是变革生产方式本身。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要求。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第一,社会主义不能把“公平”和“平等”作为目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资产者和无产者对“公平”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生产方式中“公平”的涵义也是各不相同的,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分配”的观念是极不相同的。[3]302恩格斯也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平等的王国。[3]325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是消灭阶级。[3]448从理论上讲,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背面和表现;从分配关系上表现出来的问题,都根源于生产方式。所谓“平等和效率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矛盾。“平等”所涉及的不过是等价交换、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的平等。而真正的平等在于消除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在于消灭阶级。第二,社会主义绝不能提出“占有不平等”的目标。“占有不平等”意味着,社会一部分人可以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资本,意味着可以存在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意味着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或社会所有,每个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同样的。这是消灭阶级的经济基础。
中国现阶段和民主社会主义目标的类似性仅仅具有过渡性质。实现社会所有和社会直接占有是共产主义的目标;中国现阶段还做不到,而是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发展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现阶段来说,中国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占有方式、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方面确有一定的类似性。但这仅仅是一定阶段的经济关系,具有过渡性质,并不否定未来的共产主义目标。这种阶段性目标和过渡措施同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原则区别。民主社会主义所谓“有限度的社会占有不平等”,就是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代替共产主义(社会占有)的目标,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永恒的形式。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四大法宝”同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选择》说: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的选择,当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藉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标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四大法宝”究竟是什么,体现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它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
第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四大法宝”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它所体现的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共同特征,各国大同小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议会民主政治(多党制,议会民主),都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公营部分和私营部分),都是社会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加政府宏观调控),都是福利保障制度(对失业、医疗、贫困等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所谓“四大法宝”绝不是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所独有的。这“四大法宝”都是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的,都是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都存在诸如失业、贫困(至少是相对贫困)、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弊病。这些国家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之所以比较高,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发展比较早,科学技术水平比较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前期从全世界的后发展国家赚得大量资本红利。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四大法宝”根本不包含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纯粹是自我标榜。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如果做得好,如果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政策可能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劳动大众和弱势群体。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超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范畴,就生产方式和基本制度来说,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管是否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两个直接对立物;二者既不是“趋同”的关系,也不是对接的关系,而是后者为前者创造条件,并转变为前者。既然民主社会主义不包含社会主义因素,也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接”的问题。现在屡屡发生的事情是,西欧的几个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一起,力图在一切非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制造“颜色革命”,颠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使它们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难道这就是“对接”吗?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总是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作比较,并把后者说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形态。这是不正确的。传统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或多或少都犯了“超阶段”的错误。西欧某些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也许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的现阶段,但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
二、《选择》对《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歪曲
按照《选择》的说法,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从第三卷得出了“新的结论”,从而修正和否定了《第一卷》。对此,我们必须做一番考察,以辨真伪。
(一)《选择》是如何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的
《选择》假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义,从《资本论》第三卷及其他著作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中,概括出了如下观点:
1.股份公司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公有制的新形式”,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选择》称:马克思在研究了股份公司之后,马上做出了新的结论。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所设想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业股份。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在股份公司中,已经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人人持股)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概括地说,按照《选择》的说法,马克思从股份公司得出的“新的结论”是:股份公司是共同生产者财产共有,直接的社会财产;但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股份公司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2.股份公司改变了资本的生产目的,克服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选择》说,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因为恩格斯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意思是说,已经由共同生产代替了私人生产,由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变成以共同利益为目的)。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意思是说,克服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以实现有计划的调节了)。
3.股份公司使统治阶级的统治虚幻化,使和平过渡到新的制度成为可能
《选择》说,马克思非常看重股份公司的产生,认为股份公司作为一个过渡点,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中,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这就是说,股份公司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导致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已经自然而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了,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了。
4.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资本论》第三卷的“最终结论”否定了第一卷的结论
《选择》说,《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所谓“最终结论”是相对于第一卷的结论而言的),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 年6月出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经讲到: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这就是教科书所谓“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是,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创造了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相匹配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占有形式。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历史局限性。(意思是说,自从股份公司出现以后,《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已经站不住脚了——资本的垄断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再是生产的桎梏了,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矛盾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的外壳不需要“炸毁”了,剥夺者不需要被剥夺了。)简而言之,股份公司打破了资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了,资本主义制度不需要变革了,《资本论》第三卷的“最终结论”否定了第一卷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结论。
那么,《选择》所概括的这些观点同马克思的本意相符吗?股份公司真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吗?《资本论》第三卷真的修正和否定了《资本论》第一卷吗?我们只要和原著相对照就可以得出结论。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性质的有关论述
为了澄清《选择》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的解读是否正确,需要全面详细地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有关论述。
1.股份公司是实现“资本溶合”和资本集中的一种途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资本)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来实现,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4]723如果说资本规模的扩大首先取决于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那么,资本集中(小资本集中为大资本)则起了补充作用。实现资本集中有两种途径:一是“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吞并小资本;二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把众多大小不等的资本溶合起来。因此,股份公司不过是实现“资本溶合”和资本集中的一种途径。这种溶合和集中绝不会改变资本的本性——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权。
2.股份公司是发达资本主义时期“联合的资本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或者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或国家出资兴办;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例如给私人建造房子),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而是靠房屋的需求者提供资金)。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筑业主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为个别私人定造房屋(而是建造成批的房屋——商品房)。[5]260可见,股份公司是发达资本主义时期“联合的资本家”,是同资本的集中、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相联系的,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高级阶段。
3.股份公司作为转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是自行扬弃的矛盾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在《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专门讲到信用制度的产物——股份公司。由于股份公司的成立,造成如下正负两方面结果:第一,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以前曾经是政府企业的那些企业,变成了社会的(公司的)企业。第二,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公司)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第三,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第四,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导致的大规模剥夺以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并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而信用制度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在这里,(即在信用制度和股份制度中),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6]493-499
概括地说,股份公司的成立导致“三个社会化”:资本社会化——使私人资本(通过直接联合)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企业社会化——私人企业表现为社会企业(公司企业);企业管理社会化——企业全部资本由资本的代理人(职业经理)管理。股份公司中包含“三个分离”:一是资本所有权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生产剩余价值)完全分离;二是作为别人资本管理人的经理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三是劳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完全分离。正因为如此,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范围内的消极扬弃(工人合作工厂则是积极的扬弃)。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股份公司是资本再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但是,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高度垄断、新的金融贵族、投机和欺诈等等,便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和表现。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资本代理人)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在竞争中,股份公司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同时导致资本的进一步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对中小资本的剥夺),只不过是以对立的形式(而不是联合的形式)表现出来,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不仅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且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恩格斯对股份公司也有一些论述。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空想的发展》一书(1880年)中说,无论是信用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3]751-753很显然,股份公司只是生产的社会化形式,不仅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而且,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针对纲领草案第四段中“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句话指出:“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删掉‘私人’这两个字(即改成‘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个论点还勉强过得去。”针对草案第六段恩格斯说:“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创造出来,并且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7]408-409在这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第一,“资本主义私人生产”指的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即独资企业;“私人生产”和“私有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二,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内部“没有了无计划性”,但就整个社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个论点还是可以成立的。之所以加上了“勉强”二字,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有一定的计划性,而是说“无计划性”并不是最本质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并在占有剩余价值上表现出来;“无计划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第三,股份公司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在于,“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是工人阶级乃至一切社会成员解放的经济基础。实现这一转变所需要条件,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创造出来。
(三)《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
《选择》力图以《资本论》第三卷否定《资本论》第一卷。为此,我们需要搞清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中,究竟讲了哪些结论性的话。
在那里,马克思首先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兴衰的过程和历史必然性:一旦这一转化过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排挤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过程)使旧社会(即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即劳动和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接着,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和规律性: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4]873-875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都是经济事实,一切都是在经济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发生的,股份公司的出现不可能改变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更何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在“资本一般”和剩余价值抽象形式的层次上,阐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股份公司作为信用制度的产物和企业的具体形式,在这里还没有必要出现)。资本通过两种形式加速集中:一种是大的和强的资本打倒和吞并小的和弱的资本;另一种是单个资本通过股份公司而溶合。由于劳动的一般社会力——劳动的社会结合和通过科学利用自然力——的强大作用,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尖锐化了——利润率趋向下降了,两极分化更显著了,失业率更高了,生产的相对过剩更严重了。在这个基本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资本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外壳)。因此,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剥掉资本主义的外壳,由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它。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完全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否定,是社会所有制或社会直接占有的另一种说法,是联合劳动的经济基础。不言而喻,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股份公司的否定。
(四)驳斥《选择》所谓《资本论》第三卷否定第一卷的谬论
在完整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以后,现在针对《选择》假借他们的名义提出的论点一一进行分析和澄清,看看股份公司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形式,是否是实现和平过渡的形式,《资本论》第三卷是否否定了第一卷。
1.股份公司绝不是公有制的新形式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选择》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完全歪曲了股份公司的经济性质。股份公司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之后的“社会所有制”或“个人所有制”,也不是“公有制的新形式”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把“股份私有制”的股份公司说成是“新的公有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股份公司不过是“联合的资本家”。在股份公司这个概念中,包含一个“公”字,但绝不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是毫无关系。股份公司既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这种性质体现在对股本和对红利的占有权上),也没有改变资本的本性,没有改变企业内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一句话,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点至关重要。恩格斯在1886年曾经指出,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7]678股份公司只是资本集中的一种形式,它把一个个单个资本汇集在一个企业,形成一个法人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方面,股份公司不过是“联合的资本家”;另一方面,“股份公司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也就是说,相对于资本规模较小的单个资本的独资企业而言,股份公司是“联合的资本家”,是资本和企业的社会化形式。资本和企业的社会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本来性质,“社会化”既不等于公有制,更不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公司本身不可能“进入到新的生产方式中去”。相对于未来社会的共同生产而言,股份公司并没有改变“私人生产”(私有制经济)的性质。可见,股份公司绝不是“公有制的新形式”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把股份公司说成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完全是指鹿为马。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改革家”就是这样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
股份公司本身并不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股份公司的确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新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即共同占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但只是“单纯的过渡点”而已。只有在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新的生产方式中,才谈得上“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的物质要素属于社会,而不属于个人,更不可能存在私人资本(不管采取什么形式——独资的形式还是股份资本的形式)。股份公司作为“联合的资本家”,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行“剥夺剥夺者”,才能够转化为“工人的联合”,“再转化为”新的占有方式,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一旦实现所有制关系的这种“转化”,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也就完全改变了,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是生产的单纯的物质要素;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职能,也就转化为对生产的社会管理的职能。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说成是“已经完成过渡的点”,即说成是新的生产方式本身,把“资本所有者(股东)的共有财产”说成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完全是有意的歪曲和偷换概念。
“全民持股制”和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风马牛不相及。《选择》把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解读为股份公司和私人股份制。这是极大的歪曲。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完整地说是“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个人所有制”——小生产条件下的个体私有制;大生产和共同占有条件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是对作为个体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直接否定。通过这种直接否定,从个人没有财产(无产者)转变为个人有财产。但是,这里的“个人所有”,既不是相互分离的个人私有,也不是股权私有,而是以社会共同体为中介的个人所有——就像古代亚细亚形式那样。这里既然已经不存在私有制和资本,也就根本不存在个人股份——不管是小股东还是大股东。
股份公司的“三个社会化”和“三个分离”只是为“过渡”创造条件。马克思所说的“三个社会化”,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种资本、企业和劳动的形式,生产、销售、劳动都不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互相依赖,构成一部社会生产的大机器。正是由于“三个社会化”,要求企业(股份公司)必须实行“三个分离”——资本所有权和资本增殖的职能必须分离;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资本代理人)必须分离;劳动和所有权(以及剩余价值占有权)必须彻底分离。这种“社会化”和“分离”后的资本、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和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差别仅仅在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占有方式、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分配方式。在股份公司那里,是私人所有,雇佣劳动,自然规律调节;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社会统一组织和计划调节。因此,股份公司的“三个社会化”和“三个分离”体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而只是为“过渡”创造条件,离共产主义更近了。但是,只有经过“剥夺剥夺者”和“剥掉资本主义外壳”,才能实现这种过渡。
由上可见,《选择》在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时,运用了一连串偷换概念的骗术。把新旧生产方式的“过渡点”偷换为“新的生产方式”,把资本所有者的共有财产偷换为“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联合起来的资本私人所有制(所谓“全民持股”)偷换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把社会化偷换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私有制的社会化实现形式偷换为“新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样,一方面,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建立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就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就被颠覆了。
2.股份公司绝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属性
《选择》所谓股份公司“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对恩格斯有关论述的极大的歪曲。首先,关于股份公司的阶级性质,恩格斯说的是,“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其次,《选择》明显地曲解了“私人生产”和“无计划性”的涵义。在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前面还有一句话:“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7]408显然,“私人生产”指的是单个资本家经营的独资企业。股份公司当然不是独资企业。在股份公司中,集体的资本家代替了单个的资本家。但是,如果把“没有了私人生产”解读为“没有了私有制企业”或“私有制经济”,那就是曲解了。所谓“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指的是股份公司(特别是托拉斯)内部的计划,而不是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其实,在这句话后面恩格斯还有话,他说,“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很明显,股份公司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股份公司不是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生产的。但是,《选择》没有引用这几句话,如果不是疏忽,就是有意误导读者。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有两种企业形式,一种是早期的单个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另一种是后来出现的股份公司。这进一步说明,一方面,“不再是私人生产”不等于不再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另一方面,“没有了无计划性”不等于“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问题的关键是,股份公司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能够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不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经济关系的分离,而是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质的区别,二者是直接对立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它生产的产品不仅是商品,而且,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因此,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社会性质。从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和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就会得出全部价值决定和价值对全部生产的调节作用。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与此相对立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是:生产资料社会直接占有或社会所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实行劳动的直接交换,不需要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了,社会生产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使用价值,是直接满足社会需要,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总之,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股份公司的出现既没有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也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只要国内存在多个股份公司或者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只要存在国家间更多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那么,也就不会根本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无政府状态——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否则,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所有主张,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经济关系和生产目的完全没有改变。
3.股份公司并不是实现“和平过渡”的新的经济制度
《选择》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完全歪曲了股份公司内部两权分离的关系。在股份公司中,资本和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资本增殖)相分离,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的职业经理(代理人经营者)相分离,劳动和所有权相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并没有取消资本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就是股息和红利),并没有“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资本的管理者和企业的经营者不过是资本所有者的代理人。这是因为,和两权合一的独资企业相比,股份公司所发生的只是企业和资本的社会化,因而可以成为新旧两种生产方式的过渡点,但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没有改变,资本对社会的统治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股份公司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即使是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因而,也就谈不上“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不取决于企业和资本的社会化程度,而是取决于资产阶级是否接受和平过渡——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不进行有组织地武装反抗。把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说成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极大歪曲,也是对工人阶级的恶意欺骗。
4.股份公司并没有消除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的矛盾
按照《选择》的说法,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本身就是“生产社会化同劳动社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占有方式”,因此,《资本论》第三卷否定或者推翻了第一卷的论断。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论断,并没有错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不仅要求社会对社会生产进行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而且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直接占有。所谓“资本主义外壳”,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同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不相适应,而且,导致一系列不可解决的社会问题——失业、贫困、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在西方国家,现在的情况仍然如此;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如此,谁也拿不出医治这种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
5.股份公司并没有消除资本垄断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
《选择》说股份公司消除了垄断,事实恰恰相反。股份公司不仅不能消除垄断,而且更加垄断。其实,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说的“资本垄断”,已经包含着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资本垄断。第一卷是在“资本一般”(或“抽象资本”)和剩余价值一般形式的范围内谈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而第三卷谈论的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股份公司是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股份公司不仅没有打破垄断,反而为寡头垄断奠定了新的和更加雄厚的资本基础。股份公司改变的仅仅是资本垄断的主体,由单个资本的垄断,转向资本集团(联合的资本家)的垄断。看看现在的大公司、跨国公司的垄断程度就清楚了。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作为一个过渡点,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6]497恩格斯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于是出现了托拉斯。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3]751-752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股份公司并不是永远同生产力相适应的企业形式。股份公司不仅没有改变资本的私人占有,而且仍然包含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正是这一对立的关系,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工人失业、两极分化、相对贫困、经济危机等等,都是这一基本矛盾的结果。
6.《资本论》第三卷根本没有得出“和平过渡”的“最终结论”
《选择》煞有介事地说,“《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所谓“最终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以此否定和推翻《资本论》第一卷,证明马克思由“暴力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连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是自己随意定义的。前面已经指出,股份公司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包含社会主义因素,而只是转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这里需要指出,《资本论》第三卷不是孤立的,而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层次。单独把第三卷拿出来说事,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加上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四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均对全部著作的结构和内容作了说明。他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把流通领域作为前提,孤立地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这里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第二卷考察的正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其核心内容是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和形式。其中:第一篇考察资本在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和资本循环的各种形式;第二篇考察作为周转的循环,考察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按一定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第三篇考察由单个资本的循环构成的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流通),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就整体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第三卷的内容不是对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而是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的具体形式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剩余价值采取利润的形式,利润进一步转化为平均利润。主要具体形式是:产业资本和产业利润,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生息资本和利息,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地租)。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在“资本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形式的范围内,第一卷把所有的主要问题都讲到了。如果讲“最终结论”,那么,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已经讲了,这个最终结论就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的桎梏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资本论》第三卷不仅没有改变或者修改这个结论,而且呼应和重申了这个结论,第三卷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6]270又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在于:它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即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而它的目的是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它以现有的资本价值作为增殖的手段,而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却包含着利润率的降低和资本的贬值。其结果是,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6]278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构成生产的限制,这些限制同为生产而生产,同无条件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相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是发展物质生产力,但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经常发生矛盾。[6]278-279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是利润率,而利润率的下降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是动机和方法、目的和手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6]288-289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6]927-928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8-929由上可见,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既讲到了资本的文明面,也讲到了它的历史局限性;既讲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其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而最终难以为继,也讲到了它必然为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共产主义的生产形式)所取代。从这里能够得出“《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吗?
三、《选择》对《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导言》等的歪曲
如果说《选择》对《资本论》(主要是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的歪曲主要是采取望文生义和指鹿为马的手段,那么,对恩格斯《导言》和《共产党宣言》的歪曲则主要是采取断章取义和恶意曲解的手法。
(一)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如何制造“早年”“晚年”两个马克思主义的
《选择》说,1864年以后,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有两条道路。1871年马克思说,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1871 年巴黎公社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血战后,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普遍采取了让步政策,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看到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872年马克思说,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位竭力推崇《选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则进一步说,马、恩后来的研究终于明白,早年的极端主张是错误的、有害的。于是他们逐步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不遗余力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可惜马、恩对自己早年的共产主义理论批判不够坚决和彻底,被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钻了空子,列宁只接受马、恩早年暴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拒绝后期的民主社会主义。列宁从已经推翻沙皇政权的临时政府手中夺权,建立暴力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帝国。暴力社会主义被推广以来,人们发现,马、恩后期的研究多么准确多么重要,百年实践的历史证明,暴力社会主义确实只能破坏社会使社会倒退。
在这里,以《选择》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制造了“两个马克思”、“两条道路”、“两种社会主义”。这就是:“早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暴力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二)《选择》是如何诋毁《共产党宣言》和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
《选择》说:1836 年至1852 年,德国有一个密谋起义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思想领袖、裁缝魏特林“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这是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因理论不完备,同盟会求助于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选择》接着说: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虽然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却没有为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1852 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德国工人运动第一阶段从此画上了句号。1849 年欧州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 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改变曲高和寡的状况,1852 年11 月17 日解散了共产主义同盟,他们没有建立共产党,转而支持拉萨尔领导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上的重大转变,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转变。在他们指导下,1869年8 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这个德国工人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阶段。
《选择》还说,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考茨基说:社会主义也只能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职能发挥得愈好,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那种认为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会大厦,必须把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消灭掉的说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消灭旧东西的做法只意味着消灭新东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为新东西创造条件,而是强迫我们再一次重新建立旧东西。它不是使我们前进,而是使我们后退。这就推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打碎旧世界,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在这里,真实的历史和虚假的谎言、正确的见解和荒谬的东西是有意识地混杂在一起的。
(三)《选择》是如何歪曲恩格斯的《导言》和晚年有关论述的
1.《导言》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最后反思和修正”
《选择》说,1895年,恩格斯在《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要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2.《导言》作为“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修改
《选择》说,恩格斯在导言中说完这些话还不到五个月,1895 年8 月5 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3.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勾画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说,马克思认定:经济上的股份公司,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完成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选择》说,政治上,英国、美国、德国等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9 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5.1864年后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均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选择》说,恩格斯在1894 年1 月26 日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的信(《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时,对《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把“共产党人”改为“社会主义者”。这一重要改动表明,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人”没有被欧洲工人运动所接受,应该退出历史舞台。《选择》还说,自从1864 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
6.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来自恩格斯的遗嘱
《选择》说,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他的忠实学生倍倍尔、伯恩斯坦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898 年和1899 年,以伯恩斯坦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为标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十月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暴力革命派的地位,列宁另树旗帜,1918 年1 月18 日,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暴力革命派攻击“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道路”,批判伯恩斯坦说资本主义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其实伯恩斯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说过的话。
7.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忠实地执行了“正宗”的马克思主义
《选择》说,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体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枷锁,一切从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改良社会的先进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又说,1951 年6 月20 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了国家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通过了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宣言》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即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团结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运动。代表们把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看作是“1864 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在历史上的新阶段”。
8.改革就是要理直气壮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说,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是厌弃布朗基主义的,他说: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列宁及其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布朗基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专政,把共产党专政变成了党的领袖集团的专政,把领袖集团的专政变成了最高领袖一个人的独裁,奠定了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这种极权体制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也窒息了执政党的生机,导致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全面衰退。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四)恩格斯在《导言》中究竟阐述了什么内容
《选择》对恩格斯《导言》的解读是否正确?为了明辨是非,我们看看恩格斯在《导言》中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样,读者自会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导言》可以划分为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经受了实践的检验[7]506-507
(1)马克思在《斗争》中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2)马克思在研究当前事件时不得不把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不变的。(3)马克思对经济状况和政治事件内在联系的揭示经受了两度检验。
2.马克思在《斗争》首次提出了意义特别重大的工人政党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7]508-509
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及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表达了四个重要观点:第一,世界工人政党经济改造要求的唯一正确的公式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第二,“劳动权”不能准确表达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第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和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第四,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
3.以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方法已经过时[7]510-512
(1)19世纪中叶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是错误的。恩格斯指出,当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此,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庸俗民主派是有显著区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不可能再次爆发革命。恩格斯指出,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恩格斯指出,尽管如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2)以往的一切革命都只是少数人的革命。恩格斯指出,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多数人即使参加了革命,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另一方面,这种少数人推翻少数人的革命,在统治集团的不断分裂中反反复复持续下去。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
(3)无产阶级革命同样具有历史上一切革命斗争的共同特征。恩格斯指出,正因为如此,下述三个判断(关于革命形势、群众觉悟、革命前景的判断)都是不正确的:第一,当时的形势已经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第二,“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第三,在无产阶级因为有了经验教训而变得聪明起来的条件下,“完全存在着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前景”。
4.无产阶级必须以崭新的斗争方式代替过去的斗争方式[7]512-513
(1)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恩格斯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张能力。其实,马克思在《斗争》也很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于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2]385
(2)从今昔对比得出以突然袭击方式不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结论。恩格斯是用相隔40余年历史事实的对比说明,如果说,在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在都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那么,40年前力图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这里不仅仅是经济条件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还有斗争方式的不适应。
(3)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恩格斯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时结束了;跟着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 “从下面进行的革命”指的是,组织基层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进行不合法的突发性暴力事件;而“从上面进行的革命”指的是,在普选和议会中进行合法的斗争。
(4)法国向帝制倒退再次证明无产阶级的思想仍不成熟。恩格斯指出,1851年的向帝制的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愿望还不成熟。在1870—1871年间,似乎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然而,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两个多月。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1871年),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
5.工人运动的重心以及首要任务和斗争方式都发生了转变[7]514-526
(1)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开始无产阶级获得了最强有力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的失败并未使工人运动销声匿迹;恰恰相反,新的情况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强有力发展。所不同的是,工人运动的重心、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和斗争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2)作为欧洲工人运动新的重心的德国对工人阶级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恩格斯肯定了德国工人做出了“两个重大贡献”:一是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二是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这是第二个重大贡献。
(3)普选权使德国工人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恩格斯一共列举了五大好处:第一,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第二,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迅速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第三,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以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第四,在竞选宣传中,给了我们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一方面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另一方面,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第五,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使我们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这样一来,反社会党人法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简而言之,最大的好处就是,知己知彼、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孤立资产阶级和政府。
(4)利用普选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恩格斯说,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选举;只要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我们对此(旧式的起义)不应报什么幻想。
(5)现在的重要工作是使群众明白为什么而革命。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的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
(6)罗曼语族国家普遍修正旧的斗争策略和利用普选权。
(7)德国社会民主党占有特殊地位和负有特殊任务。恩格斯说,不管别的国家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它也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选民和拥护他们的非选民,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8)秩序党正在他们自己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恩格斯这里提到了两个“颠倒”:一是社会民主党以合法手段代替不合法手段和颠覆办法;二是秩序党作为昨天的颠覆者成了今天疯狂的反颠覆者。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合法斗争只有利于工人阶级和革命者,而不利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
(五)揭穿《选择》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共产党宣言》的谎言
1.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和《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历史不容歪曲
《选择》一开篇就歪曲“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实际情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魏特林创立的,更不是什么“思想领袖”,《共产党宣言》并不是在魏特林的“现成药方”的基础上写成的。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和空想共产主义者,是“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经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正义者同盟改造而成的、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1847年,正义者同盟表示愿意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同盟的纲领,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并要求改造同盟。1847年6月召开正义者同盟改造大会,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从追求“正义”到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是重大转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7]572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
2.所谓《共产党宣言》是“极左理论”纯属污蔑
第一,承认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本身就包含着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考茨基所说的“没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这不过是说,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因此,当经济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不管主观动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有可能建立的,一定是扭曲的、变形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后发展国家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但是,承认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消灭“旧的东西”。如果考茨基和《选择》对“消灭旧东西”耿耿于怀,这绝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旧东西”,指的是一切过时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些都将被淘汰。但是,“旧东西”中并不包括生产力。生产力是继承的,共产主义绝不会消灭现有的生产力;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就在于,使新的生产方式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从“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母体”这一论断,丝毫得不出不要“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这样的推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完成历史使命,必然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两个必然”的全部内容。问题是《选择》的观点同《共产党宣言》的精神背道而驰、格格不入,而不是什么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推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话!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空地”;即使是“打碎了旧世界”,也不会出现“空地”,这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的改变。但是,共产主义必须同传统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彻底决裂!《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理论,不是“极左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既包含继承,也包含否定,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但社会主义不可能“继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就如同资本主义不能不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全部封建制度一样。
第三,绝不能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混淆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在竞选中执政”,不过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之类的左翼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已经“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着,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条件仍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许不会反对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但是,他们不会同早已经蜕化变质的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他们会组织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苏东剧变以后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并不意味着“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认同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所谓全世界追求“社会主义前途”的国家的“改革者”都“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这是一厢情愿。
3.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拉萨尔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纯属捏造
《选择》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放下了共产主义的旗帜、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转而支持拉萨尔之说,完全是捏造的、无中生有的。
第一,恩格斯所说的“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并不是放下了“共产主义旗帜”。尽管德国乃至西欧的工人运动经历了高低起伏的变化过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坚持《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和提出的“任务”。这里有一系列史料可以作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2]248他们在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2]251恩格斯在1883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2521885年10月,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报》上发表的《当前的形势》一文中曾经说到,当前的形势,“正是我们共产主义者所需要的形势”。[8]263恩格斯在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当《共产党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这是因为,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而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虽然只是出于本能的、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在法国和德国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当时,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义地选择了“共产主义”;而且后来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2]256-257恩格斯在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的德文版序言中,都就俄国公社问题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261这就说明,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总是作为同“非科学社会主义”相区别的“科学社会主义”来使用的,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绝不是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纲领——其实质是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而不是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
第三,《选择》从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引述的关于拉萨尔的内容,不仅是断章取义,简直是恶意歪曲。恩格斯是这样讲的: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例如主张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的民族(即德国)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9]288由此可见,拉萨尔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过是德国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起点。拉萨尔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只兴盛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真正代表德国社会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正是作为爱森纳赫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维护的是地主和贵族的统治。拉萨尔主义主张和平的合法斗争,争得普选权,这在当时是对的;但它把斗争方式当成了目标本身。它所要建立的是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实现“公平的分配”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和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消灭雇佣劳动——是不一致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集中批判了拉萨尔派的错误观点。
4.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二阶段实属谎言
首先,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诞生,说成是德国工人运动进入“民主社会主义阶段”,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工党)大都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其中,最早(1869年)成立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89年 ,在恩格斯的领导和组织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第二国际,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的滋长,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都逐渐蜕化为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越来越接近于资产阶级政党。
其次,民主社会主义名义上标榜“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改良主义思潮。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形成纲领和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宣言》。“宣言”以民主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对抗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宣言》声称:“欧洲民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力量”,“指导他们的是进化社会主义的理论”,“无论如何不能以马克思的名言‘剥夺剥夺者’为目标”。宣扬“第三条道路”,即“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作为政治范畴的革命,失去任何现实内容”,“只有通过不断改良,社会才能发生变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制已经是社会主义所有制。[10]292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德国的“工人运动”,而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反动”。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自然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有关,但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5.所谓马克思从“暴力革命道路”转向“和平过渡道路”是严重歪曲
这一论断表现出明显的断章取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当时的法国和德国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也不可能通过街垒巷战实现总体上的社会变革,主张尽可能利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第一,这里所说的“和平手段”并不是同暴力革命相对而言的两条道路,这是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的改变,而不是社会变革道路的改变,而且,并不意味着根本放弃武装斗争。马克思在说了“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紧接着说,“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11]179第二,和平手段或合法手段可以宣传群众,在议会中可以占有较多的席位(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积蓄力量,但不可能根本改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性质,更不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财产社会所有(公有)”的基础上,而这一点不能不通过“剥夺剥夺者”加以实现。把“和平手段”和“和平过渡”等同起来,是有意混淆概念。
6.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
按照《选择》的说法,其一,1864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放弃了“共产主义”,并勾画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二,1894年恩格斯致意大利社会党人的信,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党人”换成了“社会主义者”,表明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这纯粹是煞有介事和捕风捉影!
首先看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1891年出版)中是怎么说的。他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公社就是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剥夺剥夺者,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而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如果合作制生产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3]59-60恩格斯在导言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在《内战》中的观点,它说: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蒲鲁东是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3]10-11可见,1864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工厂工人的联合和合作社的全国性联合,将导致可能的共产主义,而反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保持私有制、竞争和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1894年的信中完全肯定了一个重要事实:“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策略”。[9]515难道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吗?要知道,恩格斯的信是写给“社会党人”的,把“共产党人”改为“社会主义者”,更符合当时的情况;但并不是对《共产党宣言》文本作了什么“重要修改”,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更不能得出“共产”、“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提法应当退出历史舞台。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社会主义者”具有何种阶级性质。如果“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那么,“社会主义者”也不过是“共产党人”的同义语。当时欧洲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这里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没有质的区别。
为了澄清事实,有必要原原本本引述恩格斯信中的话。恩格斯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894年2月)一文中指出,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即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他们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段。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还说,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全国性的运动,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联合。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置——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就犯了接受这种位置的错误。[9]515-517恩格斯在题为《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1894年10月)的信中说,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阶级斗争”是我们生活所在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们组成为“以夺取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目的的政党”,那么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们严格遵循马克思和我在1848年 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和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而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党一样。至于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9]559-560由此可见,晚年的恩格斯仍然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标志的《共产党宣言》的纲领、路线、原则和策略。最重要之点就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坚持阶级斗争,以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选择》所谓“丢弃共产主义”完全是无中生有。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同一时期恩格斯的其他论述中得到证明。1893年7月,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的纲领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9]633“纯粹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共产主义的纲领。1894你11月,恩格斯在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批评了他的右倾错误。他指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左倾),而是来自巴伐利亚人。他们是庸俗民主主义者,他们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但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等等,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7]739-740可见,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和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改为《社会主义宣言》。由此可以充分证明,所谓“1864年以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文件中,“共产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纯粹是捏造。
(六)揭穿《选择》歪曲恩格斯《导言》的种种谎言
1.《导言》根本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反思和修正”
《选择》说,恩格斯在《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导言》只是对当时革命条件、革命形势和斗争方式进行了反思,并从中总结了经验教训。
恩格斯在《导言》中所讲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还不具备全面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第二,以往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是错误的,不仅新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不会爆发新的革命,而且,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也不具备发动全面革命的条件。第三,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和以往的一切革命一样,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只是孤军奋战,而且即使侥幸取得胜利,革命队伍内部也会发生分裂,从而重复过去的“少数人的革命”。第四,街垒巷战这样的斗争方式,不仅已经过时,而且不可能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因而不能看作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斗争方式。第五,根据德国已有的经验,当时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最适宜的斗争方式是利用选举权(普选权),通过议会斗争这种合法形式,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争取群众支持,影响政府决策,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7]506-526
恩格斯在《导言》所阐述的内容,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这个层次的问题,因此也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反思和修正”。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也就是恩格斯所概括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而在“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中,都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子理论体系——唯物主义历史观,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恩格斯在《导言》中所作的“反思”,丝毫没有涉及整个理论体系,既没有修正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没有修正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当然也没有修正由此得出的“科学结论”——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导言》中对当时革命条件、革命形势和斗争方式的认识,的确包含了新的思想和观点,但“利用和平手段”算不上新观点,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讲过。他说,“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问题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2]239恩格斯在《导言》中提出的新观点主要是,当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只能是“少数人的革命”。但这不过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化,已经包含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的“两个决不会”之中了。《选择》对恩格斯的《导言》的歪曲,不过是为了给“民主社会主义”披上“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以招摇过市和蛊惑人心。
2.恩格斯的《导言》并不认为过去革命的基本方面都“错了”
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那么,究竟“错”在何处,“幻想”指的又是什么?必须符合原话和原意。在《选择》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所做的一切都错了,《共产党宣言》错了,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方面都错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错了,武装斗争错了。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诚然,马克思在《斗争》中表达的认识的确有历史的局限性,没有认识到,革命不一定会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发生;而且,并未提出革命斗争方式的转变,相反,他认为,普选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恩格斯在40年以后(在《导言》中)则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以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方法已经过时,必须探索新的斗争方式;另一方面,铲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靠少数人的革命无济于事。恩格斯的《导言》重点就在于探讨这些问题。恩格斯所谓“错了”和“幻想”,主要涉及下述判断和观点:第一,19世纪中叶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是错误的。第二,当时对革命性质的判断有偏差,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和以往的一切革命一样,都是少数人的革命。第三,对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是否成熟的认识有偏差,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第四,对无产阶级思想是否成熟的认识有偏差,法国向帝制倒退再次证明,无产阶级的思想仍不成熟。第五,对以什么样的革命方式可以实现社会改造认识不清醒,以突然袭击方式实现社会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第六,过去没有及时认识到,在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以崭新的斗争方式代替过去的斗争方式,无产阶级革命应当进入了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即在普选和议会中进行合法的斗争。这几个判断和观点,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过去错在何处,“幻想”指的是什么。所涉及的主要是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条件、思想准备、斗争方式。很显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错了,而是当时不具备“多数人自觉革命”的条件;不是武装斗争根本不需要了、陈旧了、过时了,而是当时的“街垒巷战”的斗争方式陈旧了,过时了,而且不足以推翻整个旧社会。参加普选和议会斗争不等于和平过渡,也不等于以后不需要武装斗争。“和平过渡”意味着,当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剥夺剥夺者时,资产阶级不进行武装反抗,接受社会改造。然而,当时发生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恩格斯在《导言》中明确地讲到几句很重要的话——“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决战的那一天”,“决定性的战斗”,显然都不是议会斗争,而是超越国家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3.恩格斯从来没有期待以合法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选择》说,恩格斯“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恩格斯从来没有期待以合法斗争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一,一般地说,在阶级社会,任何一个新政权都不是通过合法斗争取得的,合法就意味着取消革命。难道封建社会的每一个朝代都是合法更替的吗?难道资产阶级革命是合法的吗?难道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可以合法地实现吗?
第二,恩格斯在《导言》中所说的,只是要改变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式,而不是要改变共产主义的目标本身。在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自然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也就不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不可能有一个“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当真正由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也就不存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了。
第四,《选择》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只能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4.“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纯粹是自欺欺人的幻想
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从而能够组织政府,“资本主义就可以完成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所谓“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9 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是明目张胆的歪曲。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必须搞清楚。为此。我们不得不不厌其烦地引证恩格斯的原话。
恩格斯在《导言》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7]523很清楚,利用选举权取得更多的席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前哨战”;这种斗争的“主要任务”,不是为了在原有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范围内“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而是不停地积蓄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错误。这里没有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帝国宪法反映了极端反动的内容,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政府可以对它(宪法)为所欲为。所以,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作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毫无意义。” 他还说: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就忽然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使党足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法国、美国和英国)。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掩盖那赤裸裸的东西。这样的政策只能是长期把党引入歧途。诚然,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最后,恩格斯强调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指纲领草案提出的某些要求)搬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7]410-414
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中还说,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政府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阶级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意思是说,“合法性”当时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9]292
在这里,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机会主义倾向,他十分清楚和肯定地指出:在德国,政治权利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帝国国会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切不可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法律的框子里,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资本主义的旧壳;在德国宣布“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只能是长期把党引入歧途;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舒舒服服地建立共和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想法,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可见,《选择》的解读和恩格斯的本意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利用选举权,掌握现成的国家政权,从而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工人阶级必须打碎和废弃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二是必须进行经济制度的变革,实行“剥夺剥夺者”。这两个关键问题都不是能够通过议会席位的增加可以解决的。“和平手段”(利用普选权,参加议会)只是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有可能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它所起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它既不是什么“另一条道路”,也不可能借此“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四、总的评结
(一)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
作为《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支撑的,一个是“经济上的股份公司”,一个是“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二者构成“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这就是《选择》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高度概括。但所有这些都和马克思、恩格斯无关,都是《选择》的作者杜撰出来的。
第一,把股份公司说成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完全是捕风捉影。好一个“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们的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改革家”就是这样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在《选择》那里,股份公司既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又是“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这是自相矛盾!所谓“直接的社会财产”,指的是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后的所有制形式——社会所有,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过渡点的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根本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说的否定之否定以后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在股份公司那里,仍然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仍然以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为直接目的,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而在“个人所有制”那里,资本主义所有制(私有制)被社会所有制否定了,雇佣劳动被联合劳动否定了,但不是倒退到作为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个体的私有制。恩格斯在1886年曾经指出,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7]678
第二,把一定条件之下利用普选权和议会形式,说成是“议会道路”,认为“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是十足的歪曲。“议会道路”是西方国家“修正主义”的用语。利用选举权进行合法斗争,不能代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和平方式(利用选举权)进行斗争,只是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基本形式或决定性的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问题的实质是,用议会方式,不可能做到既可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又能够“剥夺剥夺者”,如前恩格斯所说:在德国,政治权利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帝国国会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切不可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法律的框子里,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资本主义的旧壳;在德国宣布“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只能是长期把党引入歧途;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舒舒服服地建立共和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想法,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二)世界上从来没有早晚期两个对立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两个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如一的判断。“两个必然”包含着同一个趋势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严格说来,资本主义并不是被“消灭”的,而是自身寿终正寝并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和难以为继,是由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造成的,不可能在这种生产方式范围内通过“改良”得到解决,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剥掉旧制度的外壳。无产阶级革命往往需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所谓“暴力革命”,但暴力只是新制度借以诞生的助产婆。把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说成是“暴力社会主义”纯粹是歪曲和偷换概念。至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超越必要的发展阶段,并误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由此所犯的“左”的错误,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完全无关。
第二,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期“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歪曲。首先,“早年的极端主义”提法不确切。早年的工人政党对革命的条件、革命的形势、革命斗争方式的认识确实有错误,但这不属于基本纲领和指导思想的错误,也称不上“极端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没有错,斗争失败不是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因为条件不成熟,斗争方式不正确,同当时的情况也不适应。其次,根本不存在他们“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他们的理论思想中,从来不包含“继承资本主义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再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使它逐渐实现社会占有相对平等。”这样的内容。再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并没有否定第一卷;恩格斯的《导言》并没有否定《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以《资本论》第一卷为理论基础的;《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资本论》第三卷所讲的股份公司形式,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加深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导言》所涉及的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以及当时的革命斗争方式,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也没有取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时期是违背事实的。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暴力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污蔑。所谓“早年的暴力社会主义”和“后期的民主社会主义”都是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暴力社会主义”这个概括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污蔑。这个概念涉及到两个阶段:一是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阶段。
第四,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虽然借助于暴力革命而产生,虽然在取得政权以后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虽然存在超阶段的问题,但不能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可持续,主要不在于在革命中使用了暴力,而是混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远没有完成历史任务的情况下,力图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的社会主义,并通过“继续革命”为这种超前的经济制度开辟道路。纠正传统社会主义的“错误”,不是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开辟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之说纯属捏造
《选择》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说成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把《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是对一系列捏造的集中概括,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点有三:
第一,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纯粹是无中生有。在马恩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提法,更不用说“两条社会主义道路”了。在这里,《选择》把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两种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说成了“两条道路”,进而把两种不同的斗争方式说成是“两条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方式和世界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如果所讲的是不同条件的国家最终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途径,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即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不同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论述,主要是下述两种情况:一是西欧(首先是英国)如何直接或者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资本论》的分析适合于这种情况;二是俄国公社以及殖民地附属国如何最终转变为社会主义,《资本论》的分析不适合于这些国家。就俄国公社来说,它是从一种公有制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公有制形式,如果具备必要的国内外条件(特别是西欧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那么,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继续向前发展;但不是从俄国公社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而是必须经历一系列中间环节。如果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采取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那么,在西欧已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前提下,也有可能跟着走。问题的关键是,落后国家和西欧国家相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不同,落后国家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属于后者。这两种情况和《选择》所说的“两条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两回事。不仅如此,就斗争方式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所谓“《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恩格斯的《导言》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典型。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所谓“暴力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革命的性质、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是对立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时期著作的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都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有充分的论述。
第三,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暴力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完全是捏造的。工人阶级参加选举和议会斗争,和“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占有了较多的席位,也还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根本转变:一是经济基础的转变,从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二是国家制度的根本转变,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国家走向消亡。而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改变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关系。
(四)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第一,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鼻祖的伯恩斯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伯恩斯坦是恩格斯“著作的遗嘱执行者”、“发挥了恩格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重复了恩格斯说过的话”云云,都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推崇的“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虽然和利用普选权和合法斗争有关,但都不是恩格斯的思想。从伯恩斯坦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可以作出判断:伯恩斯坦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则进一步说明,他完全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伯恩斯坦完全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第二,现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及民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关。所谓“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实际做法,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他们继承的是伯恩斯坦等人的遗教。“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有可能适合于现在西欧的某些国家,但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因素。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在庸俗经济学那里,社会化、国家所有、社会福利等等都等于“社会主义”,但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消灭阶级,消灭奴隶般的分工。所有这些,“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想做,也做不到。所谓“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遮羞布。所谓“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是更加远离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德国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不包含任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因素。这个《宣言》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纲领,不过是在资本主义上面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而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所谓“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已经奠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说法,完全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的区别。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根本不需要再“奠定”;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是不同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根本不需要“转变”。所谓“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之说,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弊病涂脂抹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弊端?最主要的是贫困(现在主要是相对贫困)、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根源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这些弊端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更加严重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原则?最主要的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消灭阶级,消除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劳动者可以支配社会的全部生产力,整个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这些原则都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保护私有制,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全民持股,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团结资产阶级。所有这些都是同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第四,确认“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并不排斥消灭一切旧的生产方式。 “没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这不过是说,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因此,当经济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管主观动机如何,有可能建立的,一定是扭曲的、变形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但是,如果由此得出不应当“消灭旧东西”,则是不正确的。所谓“旧东西”,在马克思那里,指的是一切过时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些都将被淘汰。但是,“旧东西”不包括生产力。生产力是继承的,共产主义绝不会消灭现有的生产力。无论如何,从“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母体”这一论断,丝毫得不出不要“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这样的推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完成历史使命,必然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两个必然”的全部内容。实际情况是,民主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宣言》的精神背道而驰、格格不入,而不是《资本论》第三卷和恩格斯的《导言》“推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话!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空地”;即使是“打碎旧世界”,也不是“空地”,这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的改变。但是,共产主义必须同传统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彻底决裂!《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理论,不是“极左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既包含继承,也包含否定,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但社会主义不可能“继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就如同资本主义不能不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全部封建制度一样。
第五,决不能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混淆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质的区别。所谓“社会主义在竞选中执政”,不过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之类的左翼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已经“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着,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条件仍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许不会反对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但是,他们不会同早已经蜕化变质的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他们会组织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所谓全世界追求“社会主义前途”的国家的“改革者”都“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这纯粹是一厢情愿。至少中国绝对不会——尽管确有些“改革家”力图把中国引向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我们不会上当!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五)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丝毫不能给肯定民主社会主义提供论据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评价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截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布朗基是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是对立的;只不过他是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共产主义者。他不顾经济条件是否具备,只依靠少数人密谋和组织暴动,表现出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借布朗基的弱点和问题,完全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列宁没有完全准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可以率先独立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可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便完成。这说明,列宁在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列宁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其理论核心是“跨越论”,其他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但是,列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及其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布朗基主义”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不具有布朗基的特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和运用是有偏差的,因而也产生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但这和布朗基无关。无产阶级专政仅仅适合于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而不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所谓“最高领袖一个人的独裁,奠定了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云云,这种概括是不确切的,没有正确反映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明确,这些问题并不是所谓前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带来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领袖人物不过是这种经济条件和形成的经济关系的承担者和人格化。
第三,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文不对题。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取消作为社会所有制的“个人所有制”,而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照猫画虎地照搬了仅仅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制度。这样一来,社会所有制就成为由国家和政府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了,必然是南橘北枳。从这里可以肯定,民主社会主义对“个人所有制”的有意歪曲。“个人所有制”和所谓“全民持股”风马牛不相及,纯粹是张冠李戴。中国在改革中普遍采取了股份制形式,但这主要是资本社会化、企业社会化的客观要求。但是,把股份公司说成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说法完全一致。邓小平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偏差。在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有两个支点:一是公有制企业实行责任制;二是以全民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代替计划。这里不包括资本和雇佣劳动,因而也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但有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家则歪曲和利用了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所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合同劳动”、“市场型按劳分配”等等,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第四,所谓“主流社会主义运动大潮消退”有悖于事实。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体制,由于力图在落后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超越了必经的发展阶段,必然是难以为继和不可持续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与此有关。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通过“第二次革命”,已经开始走上了新型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代表世界“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并没有“消退”。在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常规道路都遇到挫折的时刻,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开始兴起,但绝不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不仅就社会性质说是如此,就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说也是如此。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过是自我安慰。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在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冲击面前,反全球化势力、极右势力、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排外主义正在兴起,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TPP胎死腹中,就是一种征兆。民主社会主义也难逃厄运。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主义遭遇挫折以后,中国道路已经站稳了脚跟,正在显示其魅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某种引领和带动作用。严格说来,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条“道路”,它不过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具体发展模式,也可以说是欧洲一部分国家的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否能够适合于世界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后发展国家),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这种模式曾经辉煌一时,但现在看来,前景不妙。
总之,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勾画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一派谎言。那么,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以晚年马克思主义作伪装?答案已经寓于以上的分析中了,这就是:以《选择》为代表的现代民主社会主义者,力图以“精心制造出来”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主义”诋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暴力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谎言误导中国改革的方向;以经过全面歪曲的所谓恩格斯的“最后遗言”动摇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和信念。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1]http://blok.sina.com.cn/u/2186390981(沙子的博客).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10]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1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责任编辑 张海波】
Why Use Marxism in Their Later Years as a Cover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A Critique on the Choice of 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Democratic SocialismCHEN Went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idian, Beijing 100091)
Advocate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represented by the Choice of 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Democratic Socialism hold that Marx and Angles in their later years turned from advocates of "violent socialism" to one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y maintain that as shown in the 3rd volume of das Kapital and Engles,Introduction to French Class Struggle by Karl Marx, the 1st Volume of das Kapital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ere negated, which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as "final reflections on and corrections to the whol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m", is their "last words". In fact, they are completely lies. The so-called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nothing but bourgeois socialism. The founders of Marxism were consistent in their basic theory, they never turned to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there is no proof that they negate what was in their early years with that in their later years. Joint-stock companies as a socialized form of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have by no means change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Introduction summarized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workers,movement since mid-1700s, pointing out that such factors as economic conditions, worker,s awareness, forms of struggl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 However, using means of legal struggles doesn,t mean to give up the revolution, but to build up the strength for the "final battl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move cover of Marxism from democratic socialism, disclose and refute its lies.
Marxism; democratic socialism; criticize
2016-12-20
陈文通,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D616
A
号】1674—0351(2017)01—005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