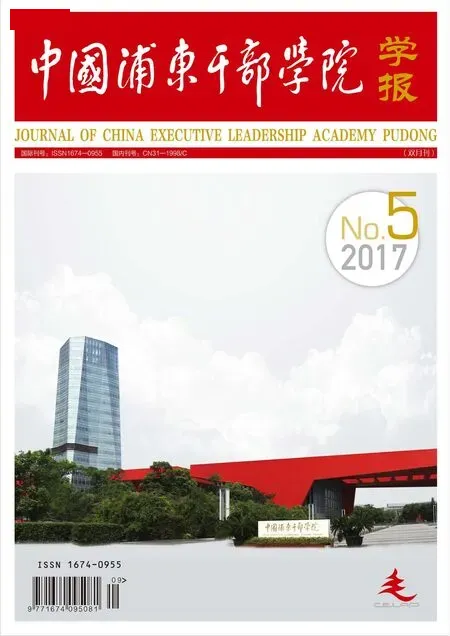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评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和实践
周尚文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评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和实践
周尚文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也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理想,深深地嵌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脑海里,自然也成为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追求的崇高理想。可是,世界历史时代的巨大变化,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使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世界革命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严重挑战,列宁时代已碰到这个问题,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今天,很少再有人重提世界革命的口号。然而,两种(或多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在一个星球上,应该如何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列宁晚年,已提出要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以及和平共处的设想。回顾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顿和新的思考,总结和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仍有所裨益。
列宁;世界革命;理想主义
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也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夺、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使一切阶级摆脱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桎梏,消灭阶级统治存在的条件,他们才能最后获得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解放全人类看作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们认为通常要经过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的路径。《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单靠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因此,他们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团结奋斗,互相援助,协调行动,国际主义便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
一百多年来,这一世界革命理论和路径,深深地嵌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脑海里,自然也成为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理论的思想来源和重要基础。可是,世界历史时代的巨大变化,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使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世界革命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严重挑战,列宁时代已碰到这个问题,他曾提出“和平共处”的设想和策略,那么,它与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能够并行不悖吗?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今天,很少再有人重提世界革命的口号。然而,两种(或多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在一个星球上,应该如何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回顾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顿,对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或许仍有所裨益。
作为理想的世界革命理论
列宁无疑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胸怀“解放全人类”崇高信念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在从事俄国革命活动的同时,始终关注着世界革命的进程。
进入20世纪,尽管世界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注意到,时代的变迁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新情况,各国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加剧会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和革命时机的来临。早在日俄战争期间,列宁就指出, 俄国这个欧洲反动势力堡垒的失败,预示着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俄国革命将是欧洲革命的序幕”。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争取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会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帮助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互推动,勾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革命场景。
20世纪初叶,帝国主义结成两大营垒互相争斗,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一开始,列宁对战争的性质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立场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这是一场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霸权和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必将对战后世界格局和革命情势产生重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理应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战争。可是,此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背弃战前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的承诺,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战争*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几乎无例外地在议会中对政府的战争宣言投赞成票。1914年12月2日,在德国议会讨论战争拨款议案时,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不顾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规定的“纪律”,对该议案投了反对票,其余成员均投赞成票。对此,列宁评论说:“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与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起,共同“保卫祖国”,甘愿充当资产阶级的附庸,驱使本国工人与别国工人互相厮杀,不仅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完全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宗旨。*列宁尖锐批评社会民主党人“保卫祖国”的立场和口号,不仅是因为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而且背弃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口号。“工人没有祖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个原则,在马克思看来,历来的国家都是剥削阶级统治广大民众的工具,所以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时候,各国无产者要摆脱“国家”的羁绊,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剥削阶级的旧世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从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立足点,就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国工人,清除当政者煽起的“爱国主义”迷雾,继续高举反战旗帜,抵制和拒绝参加战争行列,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遭受失败并削弱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造成革命危机,以便积聚力量,发动“国内”战争,争取本国革命的胜利直至争取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从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各国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战争造成的统治阶级危机,加速革命进程,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因此,如何应对战争,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也是施展其智慧和胆略的机会。
战争期间,列宁对世界革命的进程作了新的思考和部署。按照传统理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发动并取得胜利,而要在若干国家共同发动并取得胜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国间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成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一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利用资源开发和科技进步的优势赶上或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世界殖民地已瓜分完毕,势必引发争夺势力范围的争斗。愈演愈烈的危机和竞争不仅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而且这种不平衡趋势会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链条上形成若干薄弱环节,可以给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有利的时机和环境。由此列宁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722据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必仰仗共同发动和“共同胜利”,个别国家有可能突破处于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这一被称为“一国胜利论”的新思想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提供了理论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作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同时,他还是着眼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联动,他说:“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1]554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列宁着眼点仍落实于通过一国革命胜利以引爆或推动世界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强盗战争,为了揭示战争的根源,必须对帝国主义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战争爆发前,列宁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新现象并作过一些研究。*列宁不仅注意到资本主义的若干新变化,而且注意到同时代人,如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等著作,这些著作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作了有价值的考察和分析。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对帝国主义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发生严重的分歧和分裂。作为第二国际理论权威的考茨基在《超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是金融资本愿意采取的一种政策。对帝国主义是不是战争的根源以及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应有态度也众说纷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从1915年起,侨居瑞士的列宁着手搜集大量报刊资料,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记载着数百件从书刊报章上摘录下来的材料。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深入的经济分析,于1916年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对帝国主义的特征、本质、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作了深刻的剖析。列宁认为,由于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加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空前提高,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一小撮金融寡头控制了国家政治生活,对外扩张侵略,使其成为掠夺海外殖民地国家的食利国,也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酿成爆发战争的祸因。由此,列宁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分析而作出的政治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无产阶级应通过革命(主要是世界革命)最后埋葬资本主义,这就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使革命的方向、路径、前途更加清晰了。无需否认,列宁的这一结论也存在认识上的局限和误判,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能及其自我调节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对世界革命的进程过于乐观和激进。但就整体而言,《帝国主义论》在20世纪初叶仍不失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巨著。
世界大战的爆发,无产阶级领导人必须考虑战争与革命关系的问题。战争期间,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就明确指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初叶的时代主题。在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各国统治者已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加上俄国革命胜利,引发了欧洲各国革命热情的高涨,“战争产生革命;战争愈是拖延下去,各交战国就愈是没有出路,战争就愈是迅速地使它们接近革命”。[2]496事实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正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利用统治者力量极度削弱和疲惫的条件下发动并取得胜利的。同样,在列宁看来,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最终制止战争,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不是无所作为的,除了揭露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外,“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3]288-289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为起点,无产阶级要准备革命,利用战争危机发动革命,进而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最终结束战争。而这一切,列宁都是着眼于世界革命的。
作为行动的世界革命战略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地图,也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格局。从前,即在夺取政权前,布尔什维克只是世界革命舞台上的后补队员,而今一跃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员。列宁清楚地知道,俄国不仅在经济、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也都不及西方国家的工人,只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刻、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其次,当时苏维埃俄国只是“帝国主义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如果欧洲无产阶级不进行革命,俄国革命就难以坚持下去。因此,列宁始终牢记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引向世界革命,他说:“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4]279“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2]6新政权建立不久,列宁就告诫全党:“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国家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2]8可见,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把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此时新政权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要保住这个“婴儿”,没有德国革命、欧洲革命的支持是会夭折的。必须等待这样的时机的到来,必须以苏俄为后方基地,推进欧洲革命,并以欧洲革命的胜利反过来巩固俄国革命的胜利成果,保住苏维埃政权这个“婴儿”。出于这样的思考,列宁不顾党内多数人的反对,坚持与德奥签订屈辱性的和约。此时,处在“孤岛”地位的苏俄,列宁制定策略的重点,是在“防御”中推进世界革命。
为此,列宁认为苏俄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国际主义的策略,要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为支援别国革命,还要准备承担必要的民族牺牲。1918年的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声明指出:“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全部人力和物力来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5]521这一时期,革命激情迸发,列宁和俄共的设想,也已由先前的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发展到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3]503应该说,当时俄共(布)领导人及广大党员这种期盼和推进世界革命的思想和愿望是急切的,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尽管胜利初期的局势仍非常严峻,战争、饥荒、暗杀以及各类社会治安事件纷至沓来,但处于革命亢奋期的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群众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一直保持着对世界革命的高昂热情,期朌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随时准备为支援别国革命恪尽国际主义义务。
1918年下半年,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各交战国尤其是战败国国内危机凸现。11月9日,德国柏林爆发革命,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前广场上宣布德国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正在大剧院出席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会场上立即欢声雷动,天花板下的巨型枝形水晶玻璃吊灯都摇晃起来。随后,列宁号召俄国工人和农民集中一切力量帮助德国革命,首先就是集中粮食并运送到德国革命人民的手中。于是,在俄罗斯大地上,人们看到,“农民赶的大车,在薄薄地覆盖着一层初雪的俄罗斯原野上驶过去,车上载着一袋袋谷物,插着一面面红旗,旗上表明:这些谷物是请列宁调配的,请李卜克内西调配的,还有,是支援世界革命的”。[6]68这些场景体现了人们对世界革命胜利的渴望,毫无疑问,这一时期,列宁领导的俄共的世界革命思想是真诚的、无私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一些国家工人和左翼人士曾发起罢工、起义及“不许干涉苏俄”的运动,世界大战一结束,欧洲各国革命浪潮进一步涌动,作为对俄国革命的响应,德国、巴伐利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相继爆发革命,并仿效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的建立,就是为迎接世界革命高潮来临做组织上的准备。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使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欧洲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也比较高,革命的时机正在到来,只是由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蜕化,使世界革命的进程受挫。因此,必须把推进世界革命与反对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发生了分裂,党内左翼力量开始集结,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帮助下,一些国家如德国、芬兰、奥地利、荷兰、匈牙利、波兰等相继建立了共产党,也为建立新的国际准备了条件。正当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筹建第三国际的时候,战争期间完全停止活动的、由右派掌控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2月匆匆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会议,重新恢复第二国际活动,并宣布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为宗旨,这种情况下,使成立新国际更加紧迫地提上了日程。
由苏俄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发起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日于莫斯科召开,各方代表尽管在成立新国际的时间、条件等问题上产生过分歧和争论,但在世界革命的大目标下最终达成共识,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纲领》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是资本主义土崩瓦解的时代,这是资本主义内部分崩离析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参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莫斯科1933年俄文版,转引自《共产国际历史新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这一对时代主题的界定,无疑是对世界革命发出的动员令。共产国际一大还产生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并于3月6日闭幕,正式宣告共产国际诞生。
共产国际成立前后,苏俄虽面临国内战争的严峻时刻,但匈牙利、巴伐利亚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欧洲许多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似乎印证了共产国际一大对形势的估计,许多人仍沉浸在对世界革命形势过分乐观的情绪中。共产国际一大期间,列宁在《真理报》上著文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3]506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的《五一宣言》中声称:“共产主义已经走上街头”,“最后决战的时刻正在临近”,“不出一年,欧洲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第1-3合刊,转引自《共产国际历史新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季诺维也夫说:“我可以十分放心地预言,在一年的时间内……整个欧洲将是共产主义的了。”7月初,列宁也说:“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这个7月是最后一个艰苦的7月,我们将以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来迎接明年的7月,而这个胜利将是完全的和稳固的胜利。”[7]80-81
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在欧洲并没有得到广泛和积极的回应,中东欧国家所发生的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国家的苏维埃政权有的只存在两三个星期,最长也只存在四个月,列宁所设想的从俄国革命开始,然后德、法、英等国无产阶级来共同完成世界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不过,列宁对世界革命的期盼并没有冷淡。
1920年4月,苏俄与波兰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是由波兰方面挑起的。一次大战结束后,按照列宁民族自决权原则,苏俄已经无条件地承认波兰独立,但以毕苏斯基为首的波兰当政者一心要恢复1772年的波兰疆域,建立一个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甚至乌克兰在内的大波兰国。趁苏俄疲于应对国内战争之际,波军先后占领了上述三国的首都。苏俄一再避免与波兰发生战争,希望通过谈判,缔结两国的牢固的和持久的和约,但波兰在协约国的怂恿下,无意与苏俄通过谈判来解决领土问题。1920年1月28日,苏俄发表声明表示,苏俄的对波政策不是从一时的军事或外交局势角度出发的,而是以民族自决权为原则的,还保证,苏维埃军队不会越过白俄罗斯战线和乌克兰战线。但波兰对于苏俄的让步不屑一顾,仍一意孤行地实施其建立大波兰的计划。在扩张领土的贪欲驱使下, 1920年4月, 波兰无视苏俄的多次警告,对苏俄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苏波战争终于爆发。显而易见,在苏波战争的第一阶段,波兰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一方。
波兰对苏俄的武装进攻,立刻遭到了坚决有力的还击,苏俄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不仅工人和农民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走上了前线,就连一些前沙俄的官兵也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去。
战争开始的时候, 波兰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不到两个月,就在红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6月中旬,红军已夺回基辅。此刻,如何对待下一步战争,苏俄领导层内曾出现过不同意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主张立即收手,他说:“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和平的政策……我们不输出自己的制度,不能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枪尖上。”*《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2卷,转引自《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但处在胜利的高昂情绪中,这种声音十分微弱,未得到多数人认同。列宁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开始革命时说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开始革命。可是我们同时并没有忘记: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8]347-348
在战争进程发生转变的情况下, 7月,红军乘胜追击进入波兰境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改变了其参战的初衷,萌发了通过反攻推进世界革命的想法,意图让红军攻下华沙,直捣柏林,打开一条指向中欧的革命通道。7月2日,图哈切夫斯基命令西方战线的红军:“用我们的刺刀给劳动者带去幸福与和平,西进吧!”托洛茨基发布命令:“红军战士前进吧!英雄们,打到华沙去!”在红军队伍中,出现了“夺取柏林”的口号。此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也怀着急切的心情,在悬挂地图的会议大厅里注视着红军如何用武力把世界革命推向欧洲。对于苏波战争的转变,即想要借助战争引爆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这一点,与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也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列宁是极力赞同的。在与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法国代表谈话时,列宁以坚定的口吻说:“是的,苏维埃军队到了华沙。不久德国就是我们的。我们还要重新夺回匈牙利,巴尔干将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M.黑勒,A.涅克里奇:《执政中的乌托邦,1917年至今的苏联史》,转引自张盛发:《重评1920年苏波战争》,载《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3期。
苏俄红军对波兰的进攻,是试图用武力推进世界革命战略的一次尝试。1920年9月,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以前是防御性的,打败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以后,“防御战”已告结束,“当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是接受这个可给予我们有利的边界线的建议并从而采取一般说来单纯的守势呢,还是利用我军的高昂士气和当时的优势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我们正处于苏维埃政权整个政策的转折点”。结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利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应当用刺刀试探一下波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否已经成熟”。[9]413,415,416可是,红军在波兰国土上的出现,激起了波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世界革命的号召不仅没有得到波兰工人阶级的响应,反而受到波兰民众的普遍抵制和唾弃,在波兰军队的反攻之下,红军遭受到惨重失败。一开始,列宁认为,红军之所以失败,并不是方向错了,而是由于“准备不够”,由于“推进得太快了”,“当我们逼近华沙城下时,我军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8]315尽管列宁和俄共党内许多人不甘于战争的失败,但现实是无情的,迫使列宁不得不进行反思。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列宁承认:“我们在进攻时推进得太快了,几乎打进华沙,这无疑是犯了错误。……犯这个错误是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的优势。”不难看到,列宁在这里只是从战术层面作了反思,他在这个报告还说,评判进攻波兰是“战略错误”还是“政治错误”,“是将来历史学家的事情”。[10]71921年3月,苏俄与波兰正式签订了里加和约。事后,列宁对这场战争及其结局作了进一步反思,他在同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说:“你知道吗,同波兰媾和,最初遭到剧烈的反对,像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一模一样。我受到极其猛烈的抨击,因为我赞成接受和约的条件,而那些条件,又确是十分有利于波兰而很使我们吃亏的。……我们的局面并不一定要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去媾和。但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着眼,同敌人媾和是比较聪明的,据我看来,条件苛刻的和约所带来的一时牺牲,总比继续作战的代价小一些。……苏俄如果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它之所以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自卫,为了捍卫革命;证明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和平大国;证明它没有夺取任何国家的领土,征服任何民族的任何意图,根本无意于发动帝国主义冒险,——如果做到这一点,对苏俄只有好处。”[11]13-14从中可以看到,列宁已经开始转变试图用外部力量向别国推行革命的想法,着眼于以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与各民族国家之间有关国家利益的各种关系。
苏俄利用战争向波兰“输出”革命,特别是用武力输出革命,显然改变了苏波战争的性质。如果说,波兰向苏俄发动武装进攻,是苏波战争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波兰无疑是侵略者。而当红军乘胜进入波兰境内,“输出”并“制造”革命,则是苏波战争的第二阶段,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苏俄成了入侵者,它强行向波兰“输出”革命,企图推翻波兰现存政府,这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完全不相容的,也极大地扭曲和背离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宗旨。
“世界革命”战略的演变: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
苏俄进攻波兰遭遇失败,世界革命浪潮走向低落,而长达三年之久的国内战争行将结束,这一切,促使列宁和俄共领导人进行反思,苏维埃俄国确实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成为调整国内外政策、重新部署世界革命布局的契机。在国内,俄共(布)十大毅然决定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在国外,国际关系出现一种“均势”,即苏俄不可能通过世界革命推翻各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无法联合起来扼杀苏俄。列宁说,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苏俄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因此,“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12]22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前夕,列宁与蔡特金谈话时说:“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平息了,第二次浪潮还没有兴起,如果我们对它抱有任何幻想,那是危险的。我们不是用锁链来鞭挞大海的薛西斯*薛西斯是古代波斯的一个皇帝,在征战中因桥梁被海浪冲毁,下令鞭挞大海。。”[11]21世界革命的浪潮既已平息,列宁已经对国内外形势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现实的估计,在不放弃世界革命理想的前提下,重新制定前进的对外战略策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处理与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二是要将世界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东方国家,即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来。
其一,国内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迫切需要苏维埃俄国改善外部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列宁开始认识到,世界革命将是一个很长时期的斗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俄应首先搞好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进行经济建设,必须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与它们建立正常的经贸联系。1921年4月,列宁在一次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0]167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尽管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但已经不再强调它,而把搞好国内经济建设作为俄共的首要任务。他说:“现在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施加我们的主要影响。”[10]335-336有人提出疑问,“俄国这个落后的经济遭到破坏的农业国同一批先进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相互帮助,这是否可能呢?”[13]329列宁回答说,几年来西方列强试图在政治上、军事上扼杀苏维埃政权已经遭到失败,使苏俄与西方世界形成某种“均势”,它意味着苏俄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下去,这使得资本主义各国也认识到,使用武力无法扼杀苏俄,它们也需要恢复与俄国的经济联系,并改变对苏俄的态度,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3]33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认为苏俄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建立正常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同时,利用均势所提供的国际条件,俄国一国的经济建设也成为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苏俄逐渐在国际外交上打开局面,为国内建设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1922年1月,协约国最高会议提议在热那亚召开一个讨论战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国际会议,并向苏俄发出邀请。苏俄接受了邀请,决定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并积极进行了准备,列宁本打算亲任苏俄代表团团长去出席这次会议,后因健康和安全原因未能成行,由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全权代表出席。这是苏维埃俄国首次和西方国家一起参加的国际会议,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会议迫使苏俄接受它们通过武装干涉未能得到的东西,对此,列宁有充分的估计,在会议准备期间多次作出指示。他特别提出,虽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持有共产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但我们愿意用非共产党人的话语同对方进行会谈,“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而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需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最恰当、最有利地商定政治上合适的贸易条件,仅此而已”。[14]2
在4月至5月长达一个多月的热那亚会议上,英、法等国要求苏俄偿还十月革命后没收的企业及财产,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借的债务,取消对外贸易垄断。苏俄代表拒绝接受上述要求,但也指出,如果协约国赔偿苏俄受到武装干涉时期的一切损失,苏俄可以同意偿还债务。在会议上,苏俄代表团利用战败国德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决定两国在法律上相互承认,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双方相互放弃赔偿要求,并根据最惠国待遇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从此,欧美许多国家开始“承认苏联”,从1922-1925年苏联先后与2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除美国以外的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有关邻国。
其二,重新部署世界革命布局,将重心转移到支持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上来。列宁注意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在同一星球上竞赛、斗争并共处的必要性和长期性,他并没有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期待,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中来。20世纪初叶,世界已连成一片,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觉醒,撼动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后方”,单靠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的联合行动已经不够,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运动结合起来,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才能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已经注意到东方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对世界革命的巨大意义,建立不久的共产国际也把目光逐渐转向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夕,即1920年6月,列宁拟写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送给相关人员征求意见,稍作修改后,列宁亲自向代表大会作报告,对提纲作了说明,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提纲,从而为共产国际制定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路线和策略。列宁认为,当前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提纲》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8]161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同年9月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大会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对东方各族人民的宣言》,号召东方国家人民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进行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圣战。季诺维也夫在大会闭幕词中提出:“70年前我们的导师卡尔·马克思发出过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卡尔·马克思的学生,他的事业的继承者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加以扩大和补充,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纪录》,转引自《共产国际历史新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这个口号得到列宁的高度赞赏,并得到广泛流传,成为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十月革命后,东方各国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列宁不断地接见东方各国的代表,了解情况,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者提高觉悟,组建革命政党,制定斗争策略,并推动欧洲各国共产党人重视和支持东方革命。
1921年后,欧洲革命浪潮开始低落,而东方革命却继续处于高潮之中。从新的国际形势特点出发,列宁对民族殖民地革命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共产国际三大期间,他在论述了西方革命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的直线地进展”的前提下,要求共产国际各国党进一步认识民族殖民地革命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它对未来世界革命前途的历史作用。列宁指出:“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农民,虽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13]40-42这些新的认识,说明列宁已经逐渐摆脱那种“欧洲革命在世界革命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即通常所说的从“欧洲革命中心论”中转变过来,他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也得到新的发展。共产国际三大期间,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努力争取,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派出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三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并在大会最后一天,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发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关于张太雷等三人参加1921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的情景,见缪国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载《解放日报》2016年4月14日。
共产国际三大后,列宁更加深刻地思考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并作出了更为明确和肯定的回答。在他生前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4]391由此可见,在列宁晚年,他不仅把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和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东方人民的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且已经把东方革命的历史作用,看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关于世界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几点思考
20世纪初叶,正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对列宁世界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必须放在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
思考之一:理论判断的缺陷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列宁生活的年代,正值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转型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呈现一系列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一方面,列宁秉承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胆略。另一方面,他在那个动荡的流亡岁月里,潜心研究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作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结论,他的《帝国主义论》蕴含许多科学的内容,也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理论指南。然而,不可否认,其中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较为突出的一点是,他在对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充分揭露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及其自我调节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估计不足,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垂死”的结论。这个论断固然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世界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也带来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容易滋生急躁冒进情绪,企图通过一次冲击就能将资本主义送进坟墓。对此,早在1924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克拉拉·蔡特金就说过:“我们不应该隐瞒事实,资本主义比我们想象的更灵活、更有生命力、更强大。我们不应该回避,而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十分遗憾,能够重新巩固,因为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群众拒绝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无产阶级没有表现出革命的成熟性、革命的力量。”*转引自《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二次大战结束后,原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克劳丁在《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认为,列宁对西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同他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帝国主义看成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却对资本主义的“忍受能力”即通常所说的“自我调节能力”缺乏足够的估计,对西方改良主义对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影响深度也估计不足。这些评论都是较为冷静的、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论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有“自我变革”的能力,进而指出这种“取代”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宣言》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种“变”,也可称之为“改革”或“改良”,使资本主义在现有框架内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对于这一点,处在革命动荡年代又满怀革命理想的列宁,显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足够的估量,片面强调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脆弱性,并将这一理论判断作为世界革命的战略基点,是世界革命受挫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二:“急性病”与世界革命的战略失误。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革命家,他们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在与党内外妥协派、温和派的争论中,常常扮演激进派的角色,在制定战略策略时也经常表现出激进主义的色彩,特别是当形势发展较为顺利的时候,更容易犯急躁冒进的毛病,而当遇到失败和挫折的时候,又容易走向另一极端。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政权受到内外敌人包围,环境艰险,列宁采取不主动出击、在防御中推进世界革命的策略,可是,到苏波战争的第二阶段,苏俄红军反攻得胜,在世界革命思想的指引下,转而采取“武力输出革命”的策略。他们以为,只要红军一出现在柏林或华沙街头,德国和波兰的工人就会群起响应,就可以摧毁旧政权,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可是,情况恰恰相反,红军的“入侵”,激起波兰民族主义的高涨,各阶层人民奋起反击,使“入侵者”遭到失败。我们不怀疑苏俄推行世界革命的动机是真诚的,目的是要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但是,现实的教训是深刻的:革命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能由别人越俎代庖,从外部强加于一个国家的,理想主义的世界革命观只会在现实中碰壁。
红军兵败华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帖清醒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疏失,一是出于对形势的错判。当时的欧洲,革命浪潮已经退落,苏俄领导人仍希冀于欧洲革命高潮的到来,以便通过欧洲革命的胜利,反过来巩固俄国革命的成果。二是过高估计欧洲无产阶级的觉悟,过低估计欧洲国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事实上,千百年来,“祖国”“国家”“民族”之类观念在民众之中已经根深蒂固,抽象地谈论世界大同和解放全人类,无法吸引包括广大工人在内的各阶层民众,加上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这种思潮对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经过20世纪初叶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武力不间断地推动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因此,也可以说,苏俄当年推行武力输出革命的做法,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政治错误。
就一国革命而言,也要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判断形势,组织和积聚革命力量,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进退有据,切不可急躁冒进,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而错判形势,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常常是革命者犯“急性病”的重要思想根源。*邓小平在1985年8月一次接见外国客人时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这是一个老革命家的经验之谈,也可以作为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结论。
思考之三:当世界革命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发生碰撞、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出现对立时,如何协调和取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全世界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所有无产阶级政党都处于在野党地位,它们都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为己任,以世界革命和解放全人类为最高使命。而当时的国家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革命者无需顾及国家利益,相反,资本主义如果遇到危机,革命者可以利用它以削弱统治阶级力量,只会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战略要求,也易于得到各国无产者的认同。正如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国际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1]302
然而,当无产阶级政党在某个国家取得执政地位后,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必定要遇到如何处理坚守革命理想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执政前后,有着明显的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前,可以接受和信奉“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因此,在一次大战前期布尔什维克猛烈抨击欧洲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保卫祖国”的口号,并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失败”的策略,是有道理的。可是,当苏俄诞生后,执政后的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祖国”,所以在遭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时候,列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和“保卫祖国”的口号,因为此时苏维埃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祖国。这就说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坚守世界革命的理想信念,也必须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两者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是一致的,也是可以并重的。例如,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即使牺牲苏维埃这个‘婴儿’也是值得的”,列宁斥责这是“革命空谈”,是“奇谈怪论”,因为只有保住苏维埃国家这个“婴儿”,才能保住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根据地”,才能更好地推进世界革命。
总体上说,列宁通常是从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维护苏俄的国家利益,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在为共产国际二大所拟定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写道:“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5]219-220可是,国家利益是十分具体的,因此,推进世界革命和维护国家利益,常常会发生冲撞和矛盾,处理好两者关系,需要高超的智慧、胆略和方法。在这方面,列宁时期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政权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发表宣言,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独立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他们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据此,苏俄政府决定废除沙俄时期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以当时的俄中关系为例: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16]6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社会各界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1923年9月,苏联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苏联政府坚持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为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愿意实行“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一切领土和其他利益”的政策。经过谈判,中苏双方于1924年5月在北京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这一协定的时候,虽然重申“沙俄与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或与第三国订立的有损中国主权与利益的条约一概无效”,但苏方的态度已经与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了很大改变,当时中国北京政府以承认苏联在外蒙古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两国疆界将重新划定。可是,这个协定的许多内容并没有落实,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于1924年11月24日宣布独立,两国的领土问题也未解决。虽然苏俄政府发表的三次对华宣言原则上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同情和平等相待的态度,但在涉及领土争端等国家利益的时候,也是寸步不让的。当然,我们看到,此时列宁已经离世。列宁晚年,苏俄总体上是以世界革命的大局为前提处理俄中关系,比较充分体现国际主义精神。
思考之四:不同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有不同的内涵。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列宁,把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看作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苏俄当作世界革命的基地和后方,恪尽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特别是20年代初,欧洲革命浪潮趋于低落,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的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和发展,他就把目光转向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辛亥革命打开了进步的闸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后,形成了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提出要以苏俄为榜样,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正在此时,苏俄和共产国际把目光投向东方,在维经斯基、马林等人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早期的中共除了在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外,其组织机构、活动方式也全面仿效俄共。建党初期,党员人数少,白色恐怖严重,尤其在经费上面临短缺,使党的活动受到很大困难。据有关材料称,当年上海党组织连派人去广州的路费都筹集不出来,而随着党的活动的开展,经费困难日益加重。因此,从1922年中共二大起,共产国际即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不断增大。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达100万美元。不仅如此,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也都是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参与下作出的。自中共四大决定实现国共合作后,中国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苏俄即以多种方式援助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帮助建立军校,给予大量资金、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
怎样看待苏俄对早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各种援助?有人认为这是苏俄“对外扩张,输出革命”的表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对待不同的历史事件,必须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这些援助既不同于波苏战争时期的“武力输出革命”,也不同于西方列强为控制弱小国家所作的“援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时代主题和历史条件。20世纪初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是一个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备受西方各国殖民者的疯狂掠夺,辟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支持军阀割据,广大民众则在贫困和苦难中煎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然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恣意妄为,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向被侵略的中国人民伸出援手,传播革命理论,帮助建党,给予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武装,培训革命干部,提供经费和物资援助,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其次,列宁生前建立的共产国际,尽管在组织原则、活动方式等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它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和支持是真诚的、无私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苏俄,新政权自身处于极其艰难的初创时期,能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提供无私援助,是难能可贵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再次,苏俄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国家,它不仅援助其他国家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而且尽力援助落后国家的进步的革命势力,推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削弱世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这是与“世界革命”思想吻合的。当然,从道义上或物质上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反过来也有助于扩大革命势力,巩固苏俄的国际地位。总之,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指责苏俄“输出革命”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首先是帝国主义列强闯进别国的家园,对落后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列宁时期的苏俄,承担巨大的民族牺牲,恪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无可厚非的,这与后来斯大林借国际主义之名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思考之五:“和平共处”与人类的未来。经过三年艰苦的国内战争,红军打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地球上,虽然苏俄仍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孤岛”地位,但列宁看到了一国无产阶级政权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意识到国际间形成一种“均势”,世界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局面,即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存”在同一星球上。那么,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如何共存和相处呢?1921年底,也就是国内战争的炮火刚停熄的时候,列宁就向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一个问题:落后的破产的农业的俄国能否同一批先进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互相帮助呢?西方国家不是声称要用铁丝网把俄国包围起来,用经济封锁来扼杀苏维埃国家吗?列宁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他说,第一我们不怕威胁,也不怕封锁,因为苏维埃政权受过许许多多威胁,无论哪一种威胁我们都不怕;至于封锁,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吃的苦头更大。第二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趋势看,列宁认为,资本家总是要做生意的,尽管西方国家政治上敌视苏俄,却仍愿意和苏俄建立经济联系,建立正常的固定的贸易关系,设立商务代表处,订立通商条约,等等。他举例说,1921年刚开始开展对外贸易,苏俄就向国外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几百辆油罐车,虽然数量很少,价格很贵,但列宁强调说:“这终究说明,先进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恢复我国经济,虽然这些国家是由那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资本家领导的。”[13]330由此,在列宁看来,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已经使“和平共处”成为可能(当时尚未使用“和平共处”这一概念),同时利用“均势”所提供的国际条件,使俄国一国的经济建设也成为可能。当时列宁还把这种“均势”和“共存”看作可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他也没有放弃推进世界革命的思想,但随着热那亚会议的召开以及苏俄与西方国家的陆续建交,加上欧洲国家革命浪潮已经退落,指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的期待日益渺茫,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和互助互利已逐渐成为各国可以接受的国际规则,列宁“和平共处”的思想越来越显得清晰了。
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仍然在世界上占据绝对优势,社会主义的苏俄处于孤立和困难境地,“资强社弱”的格局十分明显,帝国主义仍然到处侵略扩张,恃强凌弱,“战争与革命”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这种情况下,“和平共处”还不可能是一种常态,不可能成为国际交往中普遍适用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列宁提出的“共存”“互助互利”等概念是一种初始状态的“和平共处”提法,只是处理不同制度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比较朦胧的想法,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和平共处”理论。这里,列宁能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与国之间互相依赖的角度提出“和平共处”的看法,处理好“一球两制”的关系,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而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仍然坚守世界革命的信念,也是无可厚非的。当时的形势,毕竟与二次大战后的国际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建国之初,根据当时的形势,一方面,我国就明确宣示“一边倒”的方针,另一方面,就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背景下,我国与不同制度国家的交往、合作更趋频繁,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这一切,都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说列宁所处的时代,怀有世界革命的理想是崇高的、合理的,但他生前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别人不能越俎代庖,革命不能输出,更不能用武力输出革命,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就在于此。列宁去世到今天已近一百年了,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看来不能通过世界革命的道路来实现,记取列宁时代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依然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1]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列宁全集:第3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列宁全集:第35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 列宁全集:第3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 [苏]德拉伯金娜.黑面包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7] 列宁全集:第37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列宁全集:第39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0] 列宁全集:第4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 回忆列宁: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 列宁全集:第40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 列宁全集:第4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 列宁全集:第4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闫明]
ConfusionsaboutRevolutionaryIdeals——A Study on Lenin’s Ideals and Practice of World Revolution
ZHOU Shangwen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is both the highest ideal of Marxism and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The ideals of world revolution in Marxism had been embedded in the mind of generations of Communists, and naturally became the highest ideal of Lenin and Bolshevik in Russia. Nevertheless, due to enormous changes of world history and conflicts between ideals and practical condition, the practice of theories about world revolution that taking 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 as historical mission became a though challenge in Lenin’s tim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slogan of world revolution has been rarely mentioned. However, it remains to be an important topic where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coexist. In his late years, Lenin had visioned principles for the co-existence of socialist system and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A study on Lenin’s confusion and reflections on this issue will help us to draw lessons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Lenin; world revolution; idealism
A82
A
1674-0955(2017)05-0068-13
2017-06-28
周尚文,男,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