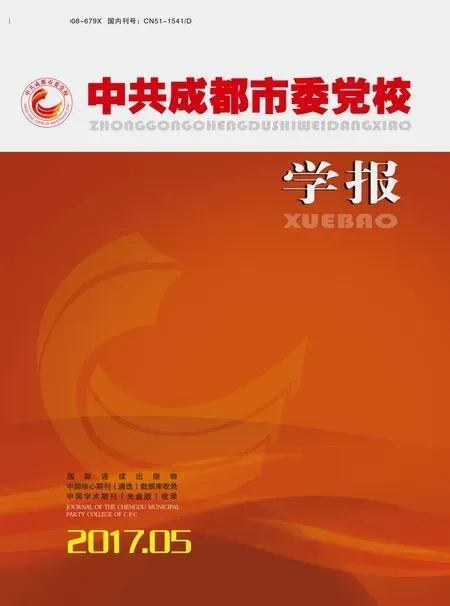现当代作家笔下的成都印象
■冯凌宇
成都兼有山景、平原、丘陵之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富饶,素称“天府之国”。成都有2300多年建城史,历史悠久,文化特色独具一格,向来为文人墨客心所向往,所谓“天下诗人例到蜀”(清·李调元)。
20世纪上叶,中国内忧外患,成都成为避难的大后方,一大批文化名人退避蜀中,川籍作家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何其芳等,外省作家茅盾、叶圣陶、何满子、老舍、张恨水、朱自清、臧克家、萧军、朱光潜等,都寓居或游历过成都,留下不少的川行华章。爰及当代,汪曾祺、贾平凹、余秋雨、肖复兴、舒婷等各地作家到成都采风创作。近百年来,外地和本土作家对成都风土人情的书写,成为传播、了解和认识成都的重要文化名片。特别是外地作家的成都印象,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观照方式。
一、物阜景美
环绕在成都周围的几百里平原,得益于温润的气候、都江堰的灌溉,土地是特殊的肥美。1941年,茅盾在《“天府之国”的意义》中写道:“四川的大部份,尤其是成都平原,如果用一个滥熟的形容词,就是‘锦绣’。这不是一片的绿色,这是一丛一丛色彩的集团。”“从你脚下那一寸土地,层层而下。如抱如偎,全是梯田,橙黄的告诉你,稻已经熟了,翠绿和绀青则是不同种类的蔬菜,而中间又有色彩较深的,那是一簇树木。”“成都平原人口的密度,大概不下于杨子江三角洲罢。但有胜于杨子江三角洲者,即这里几乎没有让一寸土闲起来。稻、麦、甘蔗、菜蔬、竹林,接连着一片又一片。甚至公路路基的斜坡上也都种上菜蔬,黄花和蝶形的白花点缀得满满的。”
1942年8月,重庆酷热天旱,老舍应邀偕朋友前往青城山避暑。他在《青蓉略记》中记录了在成都见到的另一番景象:“十一日早六时向灌县出发,车行甚缓,因为路上有许多小渠。路的两旁都有浅渠,流着清水;渠旁便是稻田:田埂上往往种着薏米,一穗穗的垂着绿珠。往西望,可以看见雪山。近处的山峰碧绿,远处的山峰雪白,在晨光下,绿的变为明翠,白的略带些玫瑰色,使人想一下子飞到那高远的地方去。” 他形容灌县(今都江堰市)“像一位身小而多乳的母亲,滋养着川西坝子的十好几县。”老舍住在一座临水的洋房里,两面是雪浪激流的河,把房子围住,一到晚上,就听到水拍乱石的声响。门外是静静的稻田,放眼望去,便能看到青翠的青城山。老舍在这个宁静的小县城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和清静。
成都花木繁盛,四季常青,素有“锦城花郭”的美誉。杜甫叹赏不已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早已家喻户晓。1945年3月,叶圣陶在《谈成都的树木》中说:“前年春间,曾经在新西门附近登城,向东眺望。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说得过分些,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少陵诗道:‘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少陵当时所见与现在差不多吧。”
成都一年四季,各有胜景,而春天是最美的。朱光潜在成都呆了一年多,在《花会》一文中深有体会:“梅花茶花没有谢,接着就是桃杏,桃杏没有谢,接着就是木槿建兰芍药。在三月里你可以同时见到冬春夏三季的花。自然,最普遍的花要算菜花。成都大平原纵横有五六百里路之广。三月间登高一望,视线所能达到的地方尽是菜花麦苗,金黄一片,杂以油绿,委实是一种大观。在太阳之下,花光草色如怒火放焰,闪闪浮动,固然显出山河浩荡生气蓬勃的景象,有时春阴四布,小风薄云,苗青鹊静,亦别有一番清幽情致。这时候成都人,无论是男女老少,便成群结队地出城游春了。”
1939年,易君左第一次到成都。成都花木扶疏的街景名胜、闲逸的生活让他眼前一亮。在《锦城七日记》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我经过一座两座小桥,那大桥跨着清涟的河,小桥配着浅浅的溪。那大桥使我回想到安徽的祁门——皖南的秀丽山色,那小桥使我回想到苏州的寒山寺带着钟声的幽径。在河边,在溪头,在人家院落里,在古巷斜阳里,点缀着一株两株的垂柳。江南的春色是够早的,而成都的一个初春,已翠遍了万柳枝头。红的梅花,东一处,西一处;带着微寒的旷野,花树下,竹林间,闲适地坐了许多茶客,娓娓清谈。”
成都的冬天缺少阳光,但仍不失清新活泼。成都本土作家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有着独到的描绘:“成都平原的冬天,只要早上雾散了去,阳光直照下来,就是相当暖和的。天空没有春季那样抹层粉似的起着光晕,但却蓝得很洁净,很清新”;“大多数的田地,则全长着青色的农产物”;“人们不像北方人似的,躲在屋子里烤火,大都高兴出来做户外的活动。只消太阳一出,雾还没有散尽,便牵着牛马在田埂上,做着暖脚的游行”,“就连喂养的鸽子,也格外喜欢在这个时候飞翔,把系在身上的哨子,悠闲地响在天空上头,仿佛在替原野里的众生,不息地奏着舞曲一样。”这分明就是一幅20世纪初的成都田园风光图,虽然那时成都冬天也多雾,但与今日之雾霾相去千里,那时可以像唐代杜甫一样,欣赏到“窗含西岭千秋雪”。
不亲身游历,终不能体会蓉城之美。1963年,谢国桢应邀到四川大学讲学,他在《锦城游记》中说:“久想到四川去游历的愿望遂能够实现了”,“沿着锦江慢慢地走回。看见对岸人家稀疏的灯火,岸旁泊了两三个船只,那样寥落的微光,想起了杜陵:‘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芙蓉变古今’的诗句。祖国的锦绣山河,何地无人才?何地无景物?惟有伟大的诗人杜甫才把锦城的风光刻画出来。读了杜甫的诗,更足以知道锦官城之美也。”
二、人文荟萃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形成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一般而言,这种文化既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融为一体,同时又保持着充分的地域特色,它既体现在建筑、器物等可见的物质层面,更体现在民风、民俗等只可意会的精神层面。
成都名胜古迹众多,如城东之望江楼,城南之武侯祠、杜甫草堂,城北之昭觉寺,城内之文殊院,城外的都江堰、青城山等,连同成都的街道、小院、茶馆等,既是作家游历之所,也大都留在了他们的文字之中,成为成都的标签式文化空间。
抗战时期,何满子在成都呆了三年。在《蓉城忆往》中,他说:“成都自古以来就文风极盛,司马相如、扬雄以下的历代文人不说,流风所被,市井之间攥谚子、掉书袋也相习成风。当年成都市上的小书摊,颇有一些他地所见不到的俗文学薄本子,或木版刻印,或石印,也有四号大字铅排的。许多公馆的看门大爷,识几个字的,都一面吸着叶子烟杆,一面悠闲地在这种薄本子里找文化享受。”一次,他在青石桥买菜,听到两个老婆婆在议论某人,其中一个贬薄她们议论的人“穷斯滥矣”,这分明是《论语·卫灵公》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巧妙引用,文绉绉得叫人惊叹!同时也说明成都人幽默风趣,有文化底蕴。
文人对城市的观照总是有着独特的文化审美需求。成都独特的城市文化散发出的个性魅力,让不少作家都乐意感受、沉浸于其中,并在文字中对成都形象加以塑造。
1941年,茅盾在《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中说:“在今天大后方的许多省会中,成都确有其特长,无论以市街的喧闹,土产的繁庶,手工艺之进步,各方面看来,成都是更其‘中国的’,所谓五千年文物之精美,这里多少还具体而微保存着一些。”
张恨水在成都一共呆了不足半月,在以后的三年中,却写出了一百多篇有关成都的杂文。1943年,他在《蓉行杂感》中说:“到过成都的人,都有这样一句话,成都是小北平。的确,匆匆在外表上一看,真是具体而微。但仔细观察一下,究竟有许多差别。凭我走马看洛阳之花的看法说,有一个统括的分析,那就是北平壮丽,成都是纤丽;北平是端重,成都是静穆;北平是潇洒,成都是飘逸。”“由江南来的人,看到了这个都市,自然觉得这是别一世界。就是由北方来的人,也会一望而知这不是江南,成都之处就在此。”
中国文人历来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近现代的北平充满了自然的、乡土的气息,保留了很多传统生活方式,古典文化气息十分浓郁,很多现代作家对它产生了家园般的依恋感。张恨水认为北平是最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而当时的成都有着类似于北平的城市氛围,自然让从北方来的作家们一见如故。老舍在《可爱的成都》中说,他似乎已看到了成都的灵魂,因为它与北平相似。而一些南方作家对成都的书写,则更在意成都的江南情调。黄裳的《成都散记》就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江南情调,他“望着越驶越近的布满了华灯的街道,心里微微的感到了一些温暖,觉得是走进晚唐诗句里来了”,“倒还不如让我在街上踱着,听着这悠扬的弦管,想着这些风雅的人们在过着‘燕子笺’、‘桃花扇’时代的那种生活的好吧“,“在这里,我对那还多少保持了古代与文化的成都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的一切深深的有着依恋的心情。”
对成都一见钟情,写诗记文的易君左是湖南人,对北平和江南都有深切的体悟。他说成都“不独像‘北平’,而且像‘江南’”,“成都的伟大即在能兼刚柔的美,兼有‘北平’与‘江南’之长。他好像戏剧中的皮黄。秦腔激昂悲歌而失之过刚,昆腔细微妩媚而失之过柔,惟皮黄得其中正,故能普遍。”
直至当代,成都的魅力仍然让人津津乐道。余秋雨在《五城记》中说:“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九州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才思横溢的文学家。”“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三、闲适安逸
城市的魅力从来不在于那些豪华的景观,更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将生活变成享受,将享受变成艺术的过程之中。文人对生活的态度总是将审美放在重要位置,他们对闲适也总是推崇备至。在这方面,成都自古以来就受到众多文人墨客的好评。
居住成都多年,朱自清对成都有着深切的体会洞察,他很欣赏友人易君左的一首小诗《偶成》:“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朱自清认为这首诗好就好在“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1944年,朱自清写下一组《外东消夏录》,其中《成都诗》有着这样的描绘:“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爱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养花天气。那时节真所谓‘天街小雨注意润如酥’,路相当好,有点泥滑滑,却不致于‘行不得也哥哥’。缓缓的走着,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园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的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这种闲,更多地表现在成都人的日常生活情趣中,如刘大杰《成都的春天》所说:“成都这城市,有一点京派的风味。栽花种花,对酒品茗,在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穷人家住的房子,院子里总有几十株花草,一年四季,不断地开着鲜艳的花。”
“在我到过的城市里,成都是最安静、最干净的;在宽阔平整的街上走走,使人觉得很轻松、很自由。成都人的举止言谈都透着悠闲。这种悠闲仿佛脱离了时代。”(汪曾祺《成都》)。而在贾平凹笔下,成都“满街红楼绿树,金橘灿灿。树叶全没有动,但却感到有薰薰的风,眼皮、脸颊很柔和,脚下飘飘的,似乎有几分醉后的酥软。我早早晚晚都在茶馆泡着,喝着茶,听着身边的一片清谈。这么一杯喝下,清香在口,音乐在耳,一时心胸污浊,一洗而净,乐而不可言状也。在那有名的锦江剧场看了几场川剧,领悟了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尤其那高腔,甚是喜爱。当一人唱而众人和之时,我便也晃头晃脑,随之哼哼不已了”(《入川小记》)。
成都这种闲逸的生活方式,在茶馆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的时候,吃惊于当地茶馆之多,不无夸张地感叹道:“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遍及大江南北城乡,几乎没有哪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与茶馆的联系,能像成都这样紧密。李劫人说,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上具有三种作用:一种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另一种是普遍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坐茶馆,已经成了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张恨水在《蓉行杂感》中说:“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路口,必有一家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我们就自绝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毫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盖碗茶而已。”
黄炎培民国时期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30年代,薛绍铭在《成都的印象》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
在享受了成都的轻松与悠闲之后,刘大杰说:“我时常想,一个人在成都住得太久了,会变成一个懒人,一个得过且过的懒人”(《成都的春天》)。对此,黄裳也颇有同感,他说:“对此使我不满足的还是那种悠闲的姿态,不慌不忙。”(《闲》)
当然,在今日社会,也有人另有体会。作家、翻译家高兴在《记忆中的形象、声音和味道》中说:“一个人如果总是像机器般运转,总是在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那他实际上也就没有了生活。这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世界现象。纽约,东京,上海,北京……无不如此。幸好还有克拉科夫,幸好还有伊犁,幸好还有大理,幸好还有成都——我们的成都。阅读昆德拉时,我曾想过:要是他能到成都来住上一段时日,兴许会感觉到某种欣喜和安慰,既有物质的,也有心灵的。”
四、和谐宜居
林语堂曾说,北平“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活的协调,使文化发展到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其乡村生活的协调”,这也正是成都所具有的城市魅力。宁静的街道,低矮的房屋,宽阔的马路,花木掩映的小院,悠闲缓慢的生活节奏,花样繁多、价格低廉而精美的饮食,文雅富有情趣的市民,让成都协调了乡村与城市的生活,人的心态自然平和松弛,成为有口皆碑的宜居之地。
1941年,茅盾在《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中说:“未到成都以前,就有人对我说,如果重庆可以比拟从前的上海,成都倒可以比拟北平。比如:成都人家大都有一个院子,院子里大都有这么一两株树;成都生活便宜,小吃馆子尤其价廉物美;乃至成都小贩叫卖的调门也是那么抑扬顿挫,颇有点‘北平味’。结论是住家以成都为合宜。”
何满子说,20世纪40年代,他在四川度过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在《蓉城杂忆》中,他满怀深情地感慨道:“一个城市的宜于安居,必须使人在生活上感到方便,各种服务行业齐全”,成都那时的住房没有卫生设备,客居成都的单身汉就麻烦了。于是,他同茶馆主人商量,冷热水随便用,老板娘还帮忙洗换下来的衣服,收费有限,确实帮了大忙。“要是在别的城市里,陌生人想要求这种非本业的服务,根本不会睬你。只有成都,才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情谊,这是成都这地方使异乡人依恋的好客风格。”
成都的经历让不少作家在很长的岁月里都难以忘怀。1939年,老舍第一次到成都,便有了好感。他《在成都》一文中说,华西坝的大学地旷、静寂、清洁,武侯祠和望江楼的树好、竹好,街上的鲜花又多又好又便宜,成都“街平,房老,人从容”,吃食精美而价廉。1942年,老舍第四次到成都,呆了将近一个月,对成都有了更深刻的观察和体验,并写下了《可爱的成都》。老舍曾向友人丧示,待夫人到川后打算去成都定居教书。1945年,他在《住的梦》中说:“夏天,我想青城山应当算作最理想的地方。在那里,我虽然只住过十天,可是它的幽静已拴住了我的心灵。在我所看见过的山水中,只有这里没有使我失望。它并没有什么奇峰或巨瀑,也没有多少古寺与胜迹,可是,它的那一片绿色已足使我感到这是仙人所应住的地方了。”“冬天,我还没有打好主意,香港很暖和,适于我这贫血怕冷的人去住,但是‘洋味’太重,我不高兴去。广州,我没有到过,无从判断。成都或者相当的合适,虽然并不怎样和暖,可是为了水仙,素心腊梅,各色的茶花,与红梅绿梅,仿佛就受一点寒冷,也颇值得去了。昆明的花也多,而且天气比成都好,可是旧书铺与精美而便宜的小吃食远不及成都的那么多,专看花而没有书读似乎也差点事。好吧,就暂时这么规定:冬天不住成都便住昆明吧。”
结语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能够张扬城市的个性、彰显城市的特征。而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建构,往往是与历代文人墨客的书写分不开的。文学作品参与了城市形象的塑造,从物质外观到意识形态、市民生活方式与精神气质等。在描述、表现的过程中,作家展现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对理想图景的想象和期待,探讨了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性。
在当代,城市化浪潮不断推进,市民社会的陌生化,城市生活的趋同化,现代意识、都市意识的泛滥使城市个性缺失;人口的急剧流动,导致地域文化的交融与本土文化生存空间的衰减。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如何建设好一个新城市,保护好一个城市的历史遗存,挖掘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已不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还关系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及城市文化品位问题。一个有灵魂的城市,能够凝聚人心,使人们有共同的历史认同感。在把一些历史文物古迹、生活方式保护传承下来的同时,也保护下了人们对故乡故土的情感脉络。
人们都说成都是可爱的,因为其休闲,节奏比较慢一点,城市中很多茶馆,围着城市还有好多农家乐。一座城市有这样一些特征固然有其可爱之处,但如果只有这些,也可能让人厌弃。人们喜欢并融入这座城市,是因为现在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一些人,这座城市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独特的个性魅力。
生态环境既是物质家园,也是精神家园。成都在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充分保护和利用好山水资源,并将其作为城市绿色空间发展基本脉络,尽量避免因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同时,既有的历史文化需要得到保护,特别是成都特色的山水田园以及生产生活方式。
[1]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
[2]蒋蓝主编.散文成都[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
[3]李永东.论外省作家笔下的成都形象[J].天府新论,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