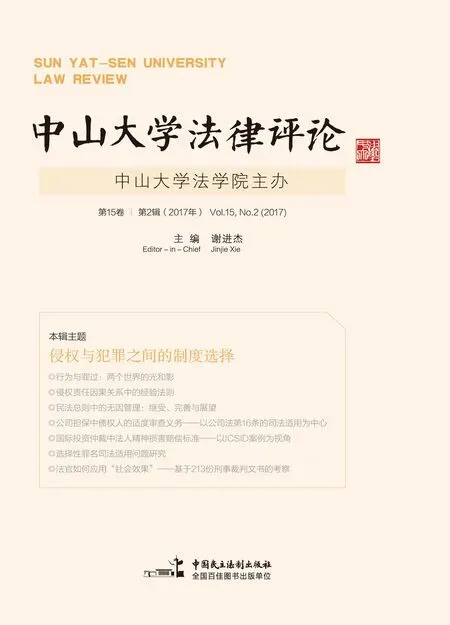道德哲学家能向刑法学家学到什么?
道格拉斯·胡萨克(著)/高山林(译)
有一小部分学者,他们既会读法学评论(law review),也会看哲学期刊(philosophy journal),我就属于这部分人。可以说,本人对刑法理论和道德哲学同样熟悉。因此我认为自己颇有资格来评论一下,其中一门学科能从另一门身上学到些什么。
我所仰慕并效仿的刑法学家,他们所采用的论证思路(argumentation),与道德哲学家类似。拿法律评论家(legal commentators)所写的任一话题来说,比如,不知法(ignorance of law)是否能够成为阻却刑事违法性(criminal liability)的抗辩事由?在何种情况下能够成立?大多数刑法学家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想办法明确,在哪些情况下去谴责那些不知法而犯法之人,是公平(fair)、正义(just)或合理(reasonable)的。我并不是说刑法学家会认为,不知法的相关理论应当完全是道德分析的产物。很多考量都会影响法律教义(legal doctrines),但在道德分析中,并没有与这些考量明显类似的部分。刑法学家必须敏锐地捕捉到,对某一抗辩事由的肯定,会如何影响守法文化(a culture of conformity to law)。他们还必须确保新的抗辩事由不会带来证明上的难题。同时,这些问题的产生,还存在一个前提:我们要能提出一个案例,令该抗辩事由得到道德基础上的认可。因此,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倘若有人并不知道某些规则(rules)的存在,同时又触犯了这些规则,那么谴责(blame)他们是否正当?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在这一背景下,道德和法律谴责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因此,这一问题,与道德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基本是一致的。
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接近,有人就会猜想,道德哲学家能给出比刑法学家更好的答案。这个想法基本上是准确的。道德哲学家更加细致,更加系统,同时,对于他们得出结论所依靠的历史传统(historical traditions)有更深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道德哲学家对观点的道德形而上学意涵(metaethical implications)更加了解。可是即便如此,我坚信,至少在本文提到的一个方面,刑法学者能够给出比道德哲学家更好的伦理学论证。
在考虑一个给定的原则或信条(principle or doctrine)是否公平、正义或合理,道德哲学家和刑法学家倾向于使用类似的方法。他们都非常重视人类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s)。他们常常在开头先叙述案例,然后提问,这些案例中,应该如何评价行为人的行为。他们认为答案或直觉能较好地解释:我们为何肯定某种原则,否定另一种原则。道德直觉就如同数据(data),那些彼此充满纷争的理论(competing doctrines)必须想办法把这些数据纳入考量。有些评论者认为这种思维实验(thought-experiment)得到的结论与科学实验得到的结论是类似的。我们应对这些观点持怀疑态度: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直觉,但这应当受到更多的审视。我们的道德直觉的本质及其来源,或者为什么我们应当如此重视道德直觉〔1〕Jonathan Baron,Nonconsequentialist Decisions,17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1994),pp.1-42。某些对道德直觉来源和实质的思考,认为道德直觉“作为哲学探究的基本数据,是可疑的”,参见该文第8页。——对于这两个问题,还没有人能够给出充分说明。即便如此,我们不应对诉诸直觉这种方法完全排斥。如果我们完全拒绝,我们恐怕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替代这种方法。相反,我们应该致力于尽可能地使道德直觉远离偏好(bias)和偏见(prejudice),以改进这种方法。如果把他们与通过科学实验获得的数据相提并论,我们就必须小心地避免实验设计中的常见问题,防止其损害我们获得的结果的价值。从这一点来看,在论证某些道德观点时,我猜想刑法学家可能会比道德哲学家做得更好。换言之,在刑法学家的使用下,这种方法会更加可靠。这一猜想,乃是源于这两个学科所审查之案例在种类上存在的两点差异。首先,刑法学家讨论的案例是真实的,而非想象的。此外,刑法领域中的回答者(respondent)通常会被要求从中立法官(a neutral judge)的立场来解决这些案例,而不是争议所涉及的任何一方。接下来,我会简要地阐明这两点差异,同时解释,为何我会认为这两点差异对于我们提升直觉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将挑战直觉的可信度。假设,我们遇到了一个案件,有一个人被他人置于伤害危险(risk of harm)之下,回答者需要回答,案例中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合理的。对于合理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大小,以及风险是否正当。我们知道,回答者的特征(characteristic)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回答者在这些问题上所产生的直觉的内容。〔1〕John M.Doris&Stephen P.Stich,As a Matter of Fact:Empirical Perspectives on Ethics,in Frank Jackson&Michael Smith eds.,Oxford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Analytic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尤其是人对于风险的感知,以及对“多大风险才是可接受的”这一问题的判断,经常是错误的,或者不理性的。〔2〕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47 Econometrica 263(1979),pp.263-92;Thomas Gilovich et.al.eds.,Heuristics and Bias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对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的经验证明。我们对于风险的错误估计,遵循一些著名的范式。思考下面一些例子。〔3〕Paul Slovic,The Perception of Risk,Earthscan Publications,2000(作者为接下来的每个观点都提供了经验上的证据)。人们倾向于高估他们所面对的实际上较小的风险,比如龙卷风和洪水。与此不同,人们也会低估生活中一些较大的风险,比如心脏病和癌症。若问题被大力向公众宣传,就会变得夸大;而媒体给予它们较少的关注时,它们又会被淡化(downplay)。对于自认为在掌控之外的风险,人们会更加担忧,比如人们更多地担心空难而不是车祸;对于那些毁灭性的风险,人们则总会夸大,比如核电站。当人们习惯了某些风险,人们就会觉得可接受;同时,新的风险则会带来更大的担忧。人们倾向于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风险的大小,当人们开车多年,却没有经历一场严重的车祸,他们就会觉得,驾驶并不那么危险。若风险是由显而易见的原因导致,人们就不会接受这些风险。人们若觉得某一行为有益,就会淡化其危险;但若觉得无益(have no utility),则会夸大其风险。
最后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于回答者及其所归属或认同的社会群体中的人,若被问及他们亲自参与的行为,回答者就不太会认为这些行为在道德上有问题。我们更倾向于对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的行为加以指责,说他们是不合理的〔4〕Paul Slovic,The Perception of Risk,Earthscan Publications,2000.。相比于否定并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挑别人的毛病是更容易的。进行某一改变,如果越需要某一个人作出牺牲,我们就越不会认为这种改变在道德上是必要的(morally obligatory)。正如Paul Rozin所观察的,“人们不想为德性付出很多!”〔1〕Paul Rozin,Moralizing,in Allan M.Brandt&Paul Rozin eds.Morality and Health,Psychology Press,1997,pp.379、394.
虽说这些错误和缺乏理性的思考难以避免,基本可以说,它们很多都会对应用伦理学产生有害影响。〔2〕Douglas Husak,Vehicles and Cashes:Why Is This Moral Issue Overlooked?,30 Soc.THEORY&PRAC.351,2004.除了提醒回答者警惕这些问题的影响之外,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去保证我们的直觉不会被这些问题所控制。当然,我并非认为刑法学家比道德哲学家更容易避免这些心理上的倾向。即便真的是这样,也只是一部分会扭曲我们直觉的因素能够被轻易地纠正。相比于道德哲学家研究的案例,刑法学家所研究的案例更容易使人回避偏见和偏好,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经验(empirical date)告诉我们,一个问题阐述的方式,对人们回答问题的倾向有非常关键的影响。换言之,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被议题的表达(frame)方式所影响。这种关于表达的现象有许多维度。一个有充分研究支撑的结论是:我们对于假设性问题的回应,会被我们所采取的视角(perspective)所影响。〔3〕表达方式等因素可以产生重大影响。Jonathan Baron,Thinking and Deciding(3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道德哲学家为唤起我们的直觉会提出一些假设性案例。而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这项研究并没有对道德哲学家表达案例的方式产生太大影响。
有许多例子证明这一点,我们这里仅考虑其中的一个。许多道德哲学家都试图通过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加深我们对防卫行为(self defense)范围和限度的理解:“无辜的攻击者”(innocent aggressor)威胁了其他人,于是这个人就使用致命武力对“无辜的攻击者”进行了攻击。〔4〕这一问题已有众多文献探讨,例如可参见Michael Otsuka,Killing the Innocent in Self-Defense,23 PHIL.&PUB.AFF.74(1994)。比如我们假设,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把一个本来遵纪守法的人暂时变成了杀人狂魔。那么,假设这个人被(所宣称的)防卫行为杀死了。我们的直觉会怎么评价这个案子?这一杀人行为是错的,凶手应受谴责?或者,它是正当的,也就是说,杀人(permissible killing)是被允许的一个例子?又或者,本案中杀人是不被允许(impermissible)的,但凶手不应该受到谴责,因此可以被宽恕?这样一个问题丛生的案例,哪里隐藏了偏好呢?我认为,回答者是在想象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人——在这样的例子中所扮演的某个角色,他们给出的特定答案乃是反映了他们自己的行为倾向。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站在狂怒的攻击者的立场上考虑,而是把自己置于杀人者的处境:即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被迫杀人。如果他们更容易与杀人者取得认同,我认为他们就更可能肯定此次杀人。不过,倘若这样假设:道德哲学家们被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抓走,去威胁一个无辜的杀手——这时,道德哲学家们恐怕就不太会同意,杀手杀死他们是可以被允许的。证明我的这些猜想并不困难,但我承认:我只是在本科生课程上询问了我的学生的想法,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证明。
既然我们对于这些案件的直觉,能够被自己想象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影响,为什么我会认为刑法学家比道德哲学家能够更好地排除这些影响呢?答案是,法律问题中所描述的案例,都是体现在司法判决(judicial opinion)之中的。这些案例是从法官而不是争议之两造的角度来写的。倘若明确地要求一个回答者思考,法官会如何解决这一争议,就更容易避免。当然,道德哲学家或许也可以想象他们自己在充当一个类似的角色。不过,法律层面的法官对于我们来说更加熟悉,我们会自然而然地(automatically)去扮演这种角色。而道德层面的法官,就会存在一个想象的差距。〔1〕原文为a leap of imagination,直译应为想象的跳跃。——译者注倘若没有明确的指示,回答者恐怕就会很自然地以为,他们被要求回答的问题不需要从中立法官的角度来看。
除此之外,法官所裁决以及刑法学家所讨论的案例是真实的,这就给一种哲学恶疾(philosophical malady)带来了一味解毒剂:哲学家总是虚构(devise)一些非常怪异的假想案例(hypotheticals),这些案例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真实经验非常遥远。我能够理解哲学家们编造出这些案例的用意:令某些无关的因素保持不变,从而能够突出我们应该关注的某一因素。不过,我们对刑法学家所给出的案例更加熟悉,因此最终能够对这些案例产生可信的直觉。我们不必担心法律没有办法给出充足的案例来让我们得出结论,是故也不必坠入想象的世界(realm of the fanciful)。刑法学家可以高兴地告诉道德哲学家一大堆真实的案件争议。
为了阐明我的基本观点,我将讨论Judith Jarvis Thomson的名作《为堕胎辩护》(A Defense of Abortion)〔1〕见于 1 PHIL.&PUB.AFF.47(1971)。。我选择这篇文章的原因很简单:读者对它应该比较熟悉。我可以确定地说,《为堕胎辩护》是应用伦理学历史上重印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章。它得到了广泛的评论,其中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不过,我的主要想法不是进一步地讨论Thomson的文章。我可以轻松地举出其他几篇关于道德哲学的文章来对我的观点进行论证,甚至可能比Thomson的例子更好。同时,我将会把我的观察限定在这一论点之中。
人们或许会想起来,Thomson提出了著名的“小提琴家之喻”〔2〕Judith Jarvis Thomson,A Defense of Abortion,1 PHIL.&PUB.AFF.47(1971).,借这个例子来唤起我们的直觉,进而论证大多数堕胎是应该被允许的。她这样写道:
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案例。你在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与一个失去知觉的小提琴家在一起,背靠背——一个著名的失去知觉的小提琴家。他被发现罹患某种严重的肾病,音乐爱好者协会仔细翻阅过所有掌握的医疗记录,发现只有你才有适合的血型能够帮助这位音乐家。于是乎他们绑架了你,昨夜,这位小提琴家的血液循环系统接到了你身上……如果你把这个系统从自己身上拔下来,你就会杀死这位音乐家。不过也别介意,这事只会持续九个月:当这位音乐家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你就可以安全地拔掉这个系统。你有没有道德上的义务(morally incumbent)同意这件事呢?〔3〕Judith Jarvis Thomson,A Defense of Abortion,1 PHIL.&PUB.AFF.47(1971),48-49.
这个比喻的确值得称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预设了对于大多数堕胎支持者来说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位与你相连的小提琴家无疑是一个人,他拥有与你这个被绑架的受害者完全相同的生存权(right to life)。大多数读者在直觉上似乎都会认为,你可以拔掉与这位音乐家相连的系统。这也就意味着,胎儿的人格(personhood)并不必然说明堕胎是应被禁止的(impermissibility of abortion)。
对这一想象出来的案例形成直觉,并考量(consult)这些直觉,我们究竟从中能够学到多少关于现实世界的东西?本科学生很快就发现了这里的主要问题。这个案例对我们来说,太怪异(peculiar)、太陌生(unfamiliar)了,我们不能过于相信我们这里的反应。如果这种事情在现实中真的发生了,人们应该期待警卫(safeguard)和司法程序(procedures)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的众多问题中,有一部分会是这样的:通过另一个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去过滤某一个人肾脏中的血液,音乐爱好者协会肯定没有这个能力去进行这样一个手术。显然,这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具有相关执照、经验丰富的医生来做。那么,为什么这个医生不在手术之前告知并征得病人的同意呢?这个被绑架的受害者能够同时起诉医院和音乐爱好者协会的民事过错吗?刑事过错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是否会觉得,这个人得不到损害赔偿(compensation)?除非民事损害的赔偿数额不够,否则,遭受他人之过错又得到赔偿,与没有遭受过错也没有得到赔偿对于受害者来说,是否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们很容易确定引申出来的问题的数量。由于对于Thomson所描述的这个困境之细节缺乏详细了解,我很怀疑我们真的可以认为,我们在这个案例中的直觉反应是很可信的。
第二个问题在于她的方法,这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对这些场景所产生的直觉必然会被我们所采取的视角所影响。注意,Thomson显然想让读者去设想被劫持的受害者的处境,而不是那个受折磨的小提琴家或者中立的(dispassionate)第三方。换言之,Thomson想要从我们的直觉中了解的是:如果你醒来发现,自己正处于与小提琴家连在一起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对于你而言,怎样做是可被允许的(permissible)?这个假定没有让我们去设想那个失去意识的小提琴家的处境,这绝非偶然。为了提升学生假设自己处于后一种境况中的能力,下面这个假设或许是有益的:这个受折磨的人并不是小提琴家。毕竟,很少有回答者会演奏小提琴。相反,我们设想这个罹患肾病的人是一个本科生,帮助他的也不是音乐爱好者协会,而是学生处主任(dean of the students)。接下来,比如我们要求回答者想象:如果你就是那个罹患致命肾病的人,醒来发现,你自己和另一个被院长绑架来的人连接在一起。如果那个人把连接系统断开,你们二人分离,导致你的死亡,这样做是可以被允许的吗?如果从防卫行为的角度出发,你是否可以阻止他断开这个系统?Thomson明确提出的问题会把读者代入被劫持的受害者,而不是那个失去意识的小提琴家的处境。如果我们把Thomson的问题换成上文这些,我们的答案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变化,恐怕就难以估计。我的猜想是:答案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我进一步推断,Thomson为其读者所选择的角色并不是完全无辜的(innocent),她会增加读者产生其所期望的那种直觉的可能性。
总结一下:如果所给定的行为来自现实案例,而不是那些与我们现实经验相差太远的想象案例,那么,所产生的道德直觉就会更可靠。更重要的是,当问题的回答角度会决定我们的答案时,如果我们的直觉对此有所警觉,那么此时直觉就更可信。〔1〕如果堕胎问题是我所提出的原则的一种例外情形,那么,其原因就在于堕胎问题中只需要考虑怀孕的妇女这一个方面。毕竟,胎儿或许会被认为是没有思维的,而Thomson承认胎儿是具有生存权的人。所以,上面的回应就削弱了Thomson所提出的假想案例的重要方面。倘若道德哲学家更倾向于从刑法学家所描述的那类案件中获得直觉,那么伦理学探究就会因此而获益。总之,从这一角度看,道德哲学家能够从刑法学家那里学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