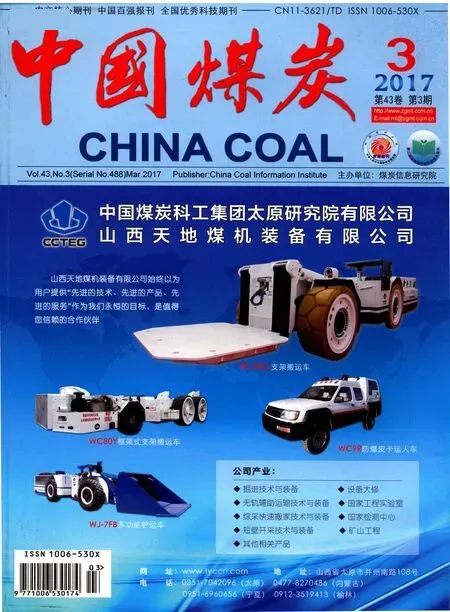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与征收碳税的必要性
毛 涛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北京市海淀区,100846)
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与征收碳税的必要性
毛 涛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北京市海淀区,100846)
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碳税和排放权交易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而且两种减排措施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在为减排温室气体付诸努力,主动创新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并于“十二五”期间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并提出完善建议,同时对排放权交易和碳税的制度协调问题进行探讨,可以为全面实施碳排放交易及创新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提供有益参考。
碳税 排放权交易 温室气体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提出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在此问题上,中国体现出大国担当,承诺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前夕,中国正式向联合国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减排温室气体的决心。要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我国还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此前,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节约能源法》、《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等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政策,确立了排放标准、排放申报、能效标识和限额等制度,对于节能减排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据统计,“十二五”累计完成节能降耗19.71%,超额完成16%的目标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要实现2030年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依旧需要在现有制度之外进行必要创新。“十二五”期间,我国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尝试运用排放权交易、节能量交易等市场化手段应对气候变化,并计划“十三五”期间全面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近期,一些迹象也表明,国家将启动碳税立法工作。在此背景下,对排放权交易制度完善、碳税立法的必要性以及两者的协调问题进行探讨,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1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实施效果评介
1.1 碳排放交易试点总体情况
“十二五”期间,国家正式启动碳排放交易相关工作,选择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省市作为试点区域。
在温室气体控制方面,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纳入各试点省市交易体系的温室气体会有一些差异。其中,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气体的重要组成,约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0%,其数据可得性强,成为交易体系重点控制的温室气体。7省市都将二氧化碳纳入交易体系,其中重庆市更是将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5类温室气体全部纳入交易体系。
在试点单位选择方面,基于各地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参与试点的行业则有所不同,北京、上海和深圳的重点是服务业,而广东、湖北、天津和重庆则是工业。试点主要涵盖电力、钢铁、水泥、石化等行业。在选择参与单位时,试点省市主要以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者年综合能耗为据,将重点单位纳入试点范畴。其中,深圳市和北京市门槛最低,为年排放5000 t二氧化碳的单位;湖北省门槛最高,为年综合能耗6万t标煤及以上的单位。由于产业结构存在着差异,纳入标准也会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如深圳市除执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标准外,还执行了建筑面积标准。无论门槛如何设定,纳入交易体系的单位通常为当地能耗大户或碳排放大户。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7个试点省市共纳入20余个行业、26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从总体上看,试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占当地总排放量的比例在35%~60%之间。
在具体操作方面,试点省市首先会在综合考虑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情况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排放配额总量。除上海外,其他省市均为一年一核定。比如,2014-2016年,湖北省配额总量分别是3.24亿t、2.31亿t和2.53亿t。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试点省市会依据历史排放法、历史强度法、行业基准法等,计算各纳入单位应得配额。比如,湖北省主要采用标杆法、历史法相结合的方法计算配额;广东省主要采用基准线法和历史排放法计算分配。在分配时,试点省市采用免费发放、有偿发放,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除广东外,其他试点省市都对配额进行免费发放。配额分配后,有配额盈余的企业以及额外需求配额的企业,则通过二级市场进行交易。
1.2 碳排放交易试点取得的成绩
在试点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如下:
(1)切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截至2015年底,排放配额总量约12.4亿t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和深圳碳市场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已经完成了2次碳排放权履约;7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排放配额交易约6700万t二氧化碳当量,累计交易额约为23亿元。其中,工业基础较好的湖北省虽起步较晚,但成效显著,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截至2016年12月31日,湖北二级市场碳排放配额总成交量2.93亿t,总交易额69.43亿元,分别占全国78%和82%。
(2)为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打下坚实基础。交易规则顶层设计,对于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试点中,各省市都颁布实施了相关法律政策,如《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碳排放试行管理办法》,对于试点工作起着积极引导和规范作用。当然,这些法律政策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对于制定和完善全国层面的交易规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碳排放核算和核查、碳配额分配、交易规则、履约机制、注册登记等碳排放交易的关键制度安排也日趋成熟。
1.3 碳排放交易试点存在的问题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国家明确2017年启动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然前期试点工作为全面开展此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依旧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相关基础比较薄弱。从目前的顶层设计看,碳交易体系的构建,尚处于能力建设阶段。一方面,试点省市都进行了规则制定工作,国家层面的相关制度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但现有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尚不健全,突出表现为全国性政策与试点省市间政策缺乏协调,还不足以有效支撑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另一方面,作为辅助碳排放交易体系实施的碳金融,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以及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及灾备系统等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2)交易体系不够开放。只有在自由开放的交易市场中,才能实现碳排放配额的有效配置并提高交易效率。从试点看,七省市相对独立,都有自身的交易规则和交易场所,配额也主要在各自辖区内交易,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缺少区域间的交易。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除了在区域内进行交易外,会存在大量跨区域交易配额的现象。但现有试点并未将配额跨区域交易作为重点,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3)相关机制缺少协调。国家在推动碳排放交易的同时,也有用能权交易、节能量交易两个类似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方案》明确提出2017年在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四川省开展用能权交易试点工作。此外,北京、深圳、上海、福建和山东等地也开展了节能量交易工作。在碳交易试点过程中,特别是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后,参与交易的企业很有可能也在进行用能权交易、节能量交易或者同时参与两者,但目前却缺少协调三者之间关系的规定。
(4)会导致一定的不公平性。纳入交易体系的企业主要为重点耗能企业,其购买碳排放配额后,生产成本会随之上升。当前,绿色消费尚未成为主流消费理念,当产品进入终端市场时,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是产品价格,而非企业的绿色投入,故会出现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有偿购买碳交易配额的企业,其产品价格会升高,在缺少类似机制对超额排放温室气体的中小企业进行规制的情况下,购买碳交易配额的企业会处于竞争劣势。当然,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节约碳排放配额的企业,其在减少碳排放的过程中,势必会增加改进技术或者使用清洁能源的成本,交易碳配额取得的收益通常难以抵消其额外的绿色投入。
2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建议
2.1 加强顶层设计
与前期试点相比,参与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数量巨大,初步估算约有1万家,而且涉及行业众多,该机制更为复杂。因此,在全国碳排放市场构建方面,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1)建议完善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的同时,还要出台与其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及相关标准,使碳排放交易相关法律政策形成多层级、相配套的体系。对外要重点处理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衔接问题,使相关制度设计适应巴黎气候大会后全球碳市场发展的新形势,特别要与中国国际减排承诺相适应;对内要处理好地方政府特别是试点省市相关政策与全国碳排放交易政策的衔接问题,避免出现脱节或冲突问题。
(2)建议加强与碳排放交易运行密切相关的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尽快建成国家、地方、企业三级碳排放合算、报告与核查体系,最好依托现有试点建设全国碳排放交易注册登记体系,强化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及真实性,确保整个交易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运行。
(3)需要创新支撑碳排放交易的财税、投资、价格、金融等政策,推动碳排放交易与财税金融政策的融合,重点加强碳金融市场建设。
2.2 打造自由开放的交易市场
建设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一方面需要推动已经试点的区域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向全国性交易市场过渡,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尚未试点的区域尽快建立相关市场。与前期试点不同的是,国家碳排放交易市场打破了行政区域限制,排放配额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配。按照《“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根据国家确定的配额分配方案对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企业开展配额分配。 因此,企业除了与本辖区内单位交易配额外,也会进行跨区域交易。而这都有赖于开放自由的交易市场。在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建成之前,建议7个试点省市打破行政区域限制,率先启动跨区域交易工作,实现配额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积累相关经验,为全国碳市场建设做好准备。
2.3 加强相关制度的协调
不管碳排放交易,还是用能权交易或节能量交易,其目标都是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及温室气体排放。基于三种交易制度的特性,建议进行必要的融合与协调。鉴于用能权作为节能量交易的前置条件,而且两者的属性及交易规则基本类似,完全可以将两者进行合并,统一为用能权交易。在此基础上,妥善处理碳排放交易与用能权交易的关系。用能权侧重于能源使用量,企业在配额内用能免费,超配额则需要付费。此外,鼓励用能单位使用可再生能源,其自产自用的可再生能源不计入其综合能源消费量。而碳排放交易则侧重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排放的温室气体则主要产生于化石能源使用,与用能权交易类似,企业的额外排放配额都需要付费。节能必然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两者存在一定联系。为减轻企业负担,基于两者的内在联系,建议在企业履约的过程中,用能指标与碳排放配额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抵用。
2.4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为营造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消费环境,需要建立完善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将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内化,同时对正外部性行为进行补偿。一方面,加强对纳入交易体系的企业进行财税政策支持,给予参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特别是通过技术改进和使用新能源而节约碳配额的企业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税收减免等经济激励,补偿其相应的绿色投入。另一方面,对于未纳入交易体系的其他企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制度,比如碳税等,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内化,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
3 征收碳税的必要性
除碳排放权交易之外,国外也广泛运用碳税去应对气候变化,并取得积极成效。在国家全面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同时,也计划启动碳税立法相关工作。将碳税作为碳排放交易的必要补充,可以克服碳排放交易存在的相关问题,更好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3.1 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缺点
碳排放交易具有诸多优点,但是也有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主要如下:
(1)总量难以确定。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是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但是,当我国经济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企业普遍经营困难,不少企业已经关闭、停产或减产,确定合理的减排总量目标存在一定的技术难题。
(2)可能有失公平。在初始阶段,配额往往免费分配给排放者,而购买配额者则需要付费,可能会存在权利配置不均的问题。
(3)可能导致集中排放。那些呈区域性分布的治理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在购买到配额后,该区域内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会激增,从而出现集中排放问题。
(4)存在技术难度。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往往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信息公开、交易结算等制度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制度的构建往往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撑,但现有技术却很难达到要求。
(5)推动技术进步能力不足。在排放权交易体制中,配额出售方的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买方也是必不可少的交易主体,他们的治理技术通常比较落后,在配额成本低于治理成本的情况下,买方改进治理技术的意愿不大。
3.2 碳税是碳排放交易的必要补充
在国际上,加拿大、美国等国都在同时运用碳税及排放权交易两种制度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两种制度的互补性也在实践中得以体现,主要如下:
(1)覆盖面。碳税可以规制到所有消费化石燃料的单位和个人,其覆盖面较宽。比较而言,排放权交易的主体相对单一,多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人往往被排除在外。
(2)稳定性。碳税比较稳定,它对能源产品价格的影响可以预期。与之不同,在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由于存在供需关系问题,排放指标的交易价格会经常波动,缺乏可预期性。
(3)经济性。在现有的税收征管体制下,依靠税务机关和环保机关的合作,就能保证碳税的顺利征收,所花费的额外成本相对较少。而排放权交易则涉及到排放总量核算、配额分配、交易平台建设、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等,额外花费较多。
(4)公益性。碳税作为中立性税收,税收所得往往以相关税收减免或补贴等方式返还给纳税人,公益性较强。而排放权交易所得往往作为企业的利润,不会在社会上进行再次分配。
(5)环保性。排放权交易的基础是总量控制,所要实现的环保效果比较明确。然而,碳税征收的基础是一个抽象的宏观引导,所要达到的环保效果相对模糊。
(6)利他性。在碳税征收中,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义务人征税,纳税人之间不存在互助关系,利他性不明显。比较而言,在排放权交易中,原始配额的持有者,通常是潜在的排放权交易方,买卖双方都能在交易中受益,通过配额转让,卖方获得了经济利益,而买方则减少了污染治理成本。
(7)权力寻租。碳税的实施以税务机关为主导,会存在权力寻租问题。排放权交易以市场为主导,通常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
(8)接受程度。征收碳税,直接增加了化石燃料的价格,在税负较重的现状下,民众对征收碳税的热情不高。比较而言,排放权交易对相关产品价格的影响比较“模糊”,民众对该制度的认可度相对较高。
简言之,在我国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同时,通过开征碳税,可以弥补碳排放交易存在的一些不足,更好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4 碳税和排放权的制度协调
由于碳税和排放权交易都是基于市场的管制手段,其管制机理具有一定的类似性,若两者都被用于管制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很可能出现管制重合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两种制度的协调问题进行探讨。
在对该问题回答之前,需要对两个关键性问题进行说明:一是调控的主体范围。碳税具有普适性,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只要购买了化石燃料,都负有缴税义务。从国外碳税立法实践来看,碳税的调控范围较大,涉及到最为广泛的市场经济主体。比较而言,排放权交易的主体则较为单一。排放权交易的主体主要为企业,当然也包括一些政府及事业单位,但个人被排除在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参与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往往是一些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或能源消耗量较多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往往被排除在外。例如,在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交易主体主要是火电厂、水泥厂、炼油厂、石灰厂等高耗能企业;在我国,参与排放权交易的企业也主要是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等行业的重点耗能企业。二是管制的温室气体范围。碳税为二氧化碳排放税的简称,其主要调控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与之相比,排放权交易所管制到的温室气体类型则较为广泛。欧盟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已经管制到了二氧化碳和氧化亚氮等多种温室气体。我国的试点,虽然大多数省市仅对二氧化碳进行管制,但也有个别省市将多种温室气体都纳入交易体系。
若我国同时适用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制度,建议按照以下思路协调两者的关系:一是基本定位。在二氧化碳排放领域,所有的个人排放者都可以运用碳税加以管制。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区分情况,依据其年均能源消耗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划分,对于低于一定标准的企业,可以用碳税加以规制;高于该标准的企业,则可以用排放权交易制度加以管制。二是实施方式。碳税对于市场的成熟程度要求不高,只要设计好碳税的实体性要素和程序性要素,就可以适用碳税。而排放权交易涉及到配额分配、温室气体核算、排放监测、统计和审核等环节,不仅技术要求高,而且对交易市场的成熟度有要求,全面征收并非易事。目前,国家已经计划全面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据估算纳入交易的企业数量在1万家左右。但在交易机制成熟之前,广大的中小企业还很难纳入交易体系,会出现管制真空问题,而这部分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碳税进行管制。三是衔接方式。开征碳税后,使用化石能源并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和个人都应是纳税主体,同时应设定一个除外条款,即: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免征碳税。当然,随着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被纳入交易体系,对于进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企业,应当采取免征碳税的方式进行处理,避免出现管制竞合问题,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负担。当然,为了降低制度设计对于企业的负面影响,可以给予企业一定的选择自由,除了重点耗能企业外,在某一个耗能区间段或二氧化碳排放范围内的企业,可以让其选择加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或是缴纳碳税。
[1] 高常水,姜宝林,段志成.全球碳市场发展态势下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探析[J].中国煤炭, 2015(10)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6年度报告[R].2016
[3] 张国丰,刘全文.基于产权理论的低碳经济政策研究[J].中国煤炭,2010(1)
[4] 湖北碳市场交易额近70亿居中国首位[EB/OL].[2017-01- 21]http://news.cnhubei.com/xw/jj/201701/t3777389.shtml.
[5] 潘家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挑战与市场拓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8)
[6] 李传轩,肖磊等.气候变化与环境法理论与实践[M].法律出版社,2011
[7] 毛涛.碳税立法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张大鹏)
On the perfe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and the necessity of carbon tax
Mao Ta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C., Haidian, Beijing 100846, China)
In term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have adopted carbon tax and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Both of them have been proved to be effective. As a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our country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positi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example, start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during 12th Five-Year .Summarizing the previous pilot experie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s well as discussing the coordinati on of carbon tax and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and innovation measures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carbon tax,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greenhouse gas
毛涛.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与征收碳税的必要性[J].中国煤炭,2017,43(3): 5-9. Mao Tao. On the perfe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and the necessity of carbon tax[J].China Coal,2017,43(3): 5-9.
TD-9
A
毛涛(1983-),男,河南省南阳市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全球能源资源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兼任河北大学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资源能源环境法律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