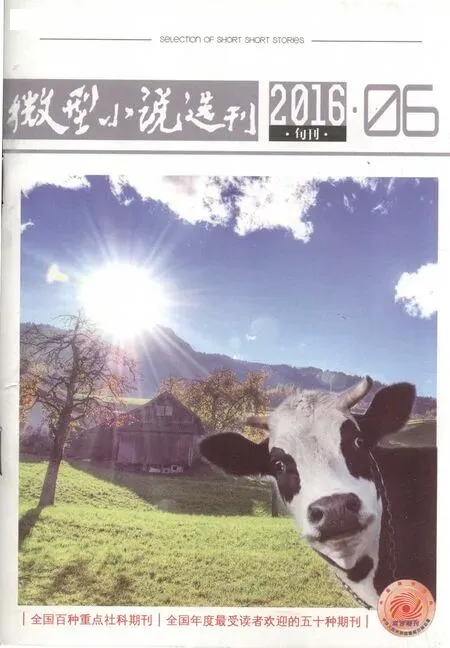渴
□何 竞
渴
□何 竞

夜色如墨,眼皮睁开或不睁开仿佛都没有区别,唐薇在枕头上放慢呼吸,伸手从儿子肚皮下拽出手机,儿子和老公,一左一右在她身旁快乐地打呼,其实不用看,她也知道这时是凌晨三点,最尴尬的时刻。
再早一点醒来,可以借口说自己是吃货,饿得胃空空,要到冰箱翻找一通;再晚些,可以平躺在床上,听门外运垃圾的车、洒水车、送奶车,一辆接一辆的车开过来,发出清新快活的呼吸,提醒她新的一天即将到来。当然也可以高高兴兴做个瑜伽吧!反正,什么都好过凌晨三点醒来。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唐薇不管睡前吃安眠药,还是跑步,这个时间都会准点醒来,她觉得渴,若静下心听,能听见嗓子眼冒白烟的那种嗞嗞声。平躺着,干渴感更甚,唐薇舔了舔上唇,夸张地想到自己嘴唇也许已经龟裂如干旱的土地了,她轻手轻脚下床,到厨房倒了满满一杯水,咕咚咕咚喝下去。
那种渴,一刻钟之后再度袭来。唐薇知道自己是无法上床安睡了,就算她现在去睡,过不了多久也会被膀胱的紧胀感催逼着再度起身。她索性蜷在沙发上,翻出手机,她和费思的微信聊天记录,只剩那么一条了,翻来覆去看,她都能背下来,其实那不是费思的话,是人家秦观的《鹊桥仙》。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这是费思想和唐薇说的话,她却拼了命想把这话从脑海里抹掉。如果记忆可以用橡皮擦擦掉该多好,那么唐薇便不会记得那场相遇。
一个多月前他们一起在外地参加行业大会,他是系统里数一数二的少壮领导,被人团团围住巴结谄媚的红人,她只是几年前在他手下短暂共过事的小角色,她甚至拿不准他是否还记得她的名字。但他不但记住了,他们还在无聊的晚宴后偷偷溜出来喝了一杯。不但喝了酒,他还送她回酒店,而且不到五分钟,她连换洗衣服还没找出来时,他已敲开了她的房门。
那晚,说不准是谁主动,唐薇不愿承认,但又无从否认,她像是盛开的花朵,又像是野性难驯的小猫,他也不再是西装革履的外表下那个谦逊有礼的人,总之,他们仿佛在对方身上找到另一个自己。
唐薇是从那天起,开始得一种怪病,每天凌晨三点,都被梦中的渴催促着转醒,两岁儿子在说梦话,老公鼾声高高低低,她缩在沙发上,将身体抱成团,奇怪自己内心竟没有恨。以前听人讲女人红杏出墙,她会认真地恨那个不洁的女人,现在,怎么连恨自己的力气都省了?
费思的短信和电话记录,她都删了,像一个手起刀落的侠客,来一个,砍一个,绝无丝毫留情。但没想到,他会突然再出现,在她加班的夜晚。
其实,并不太晚,时钟刚过九点,费思就这么大剌剌地空降到他升调前曾待过的单位。唐薇吓得有点呆了,他想做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他是这里的明星吗?还敢直接送上门来!费思脸上依旧挂着官方的微笑,他对唐薇轻轻说:“辛苦了。”
虽然办公室只有唐薇一个人,她依旧心惊肉跳,绝望感袭上来,附带了阵阵干渴,她慌忙去取桌上的水杯时,不小心碰翻,文件全都遭了殃。费思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她。
这个人!她不由得怒从心中起,他难不成还想要挟她?就算和他有过“一次相逢”又怎样?又不代表她身上烙了他的印记,今生今世都要受他摆布!
想得委屈丛生,唐薇眼睛瞪圆了,费思却温和提议:“我们出去散散步,怎样?”
唐薇稀里糊涂地跟在费思身后。他们一前一后,唐薇勾着头走在费思的影子里,脑子纷乱地看他和门卫打招呼,听他打电话让司机先回去。
“我不是坏人。”费思放慢了步子,等待唐薇跟上来,她却故意慢半拍,关闭耳朵。
“那天之后,我想了很多,是我对不起你。”费思也低了头,他拿脚尖去碾树下的落叶,声音发冷,“想要把你放下的,但试过了,做不到,想你,就像身在沙漠的人,想念一杯清水。”
她怔了一下,他竟这么说?他有什么理由这么说?她眼泪都快激出来了,他懂什么叫渴吗?已经一个月了,她每晚三点起床,抱着膝盖坐到七点,老公在床上快乐地打呼,一直没发现她眼睛下两块青黑,她在等待什么?她简直不敢问自己。
费思鼓了很大的勇气拖住唐薇的手,在一棵叶子泛黄的梧桐树下。她这才记起来,他胃不好,但成功男人哪能没有一个酒精考验的胃呢?于是,他就常常喝中药,说话的语调也染了一点中药的清苦味道。他涩涩地说:“人一辈子可能总要犯点错吧,是我渴,我认了。”
唐薇的眼泪越来越多地聚集在眼眶,她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让它落下来,然后告诉面前这个男人,其实,她也渴。
(原载《小说月刊》2015年第11期 湖北韩玉乐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