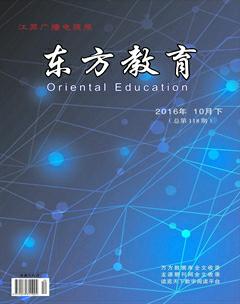语言哲学对非存在物存在问题的解释初探
张涛
摘要:西方哲学史中关于非存在物是否存在的问题从柏拉图以来争论就个体词所指物与事物共相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现代哲学在语言途径讨论非存在物是否存在的思考体现了语言哲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语言哲学;非存在物;共相;
西方哲学史中关于非存在物是否存在的问题从柏拉图以来争论就个体词所指物与事物共相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主张非存在物存在的思想始于主张共相的存在。经院哲学中唯名论和唯实论争论的焦点产生了著名的波菲利问题,即为:共相究竟是独立存在还是只存在于心灵之中?如果它独立存在,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果它是无形的,它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独立存在还是存在于可感事物之中并与之一致?
分析哲学的鼻祖费雷格对于语言哲学的重大贡献是区分了个体词的意义和指称。他认为“符号、符号的涵义和符号的意谓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是如此:相应于符号有确定的涵义;相应于这种涵义有某一意谓;对于一个意谓对象有一个符号。相同的涵义在不同的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对于共相是否存在的问题,费雷格区分概念与对象。他把句子的组成部分分为专名和谓词。专名表示对象,谓词表示概念和关系,是对对象的表述。这次的谓词不是传统语法中的谓词,而是逻辑结构的谓词。谓词或概念表示一个结构或一个有待填充的函数,填写上专名时就得到一个真值为真或假的句子。这里的共相不再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体,而是被转化为概念、谓词、一个结构或函数关系。费雷格用这种方式通过逻辑结构的转化回避了共相是否存在的问题。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缘起于虚拟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即自然语言中的句子主语是否都表示逻辑命题的主项。罗素将个体描述性词组分成两类:专名和限定摹状词。后者描述某一特定事物某方面的特征并对该对象是独一无二的。摹状词不是专名,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符号,不代表命题主项。它的逻辑作用与谓词相同,仅表示某种性质。限定摹状词不再是主词,而被转换成为谓词。从而消除了自然语言的主词是否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困惑,重构了精密化的逻辑语言。不管摹状词的所指物是否实际存在,专名与摹状词的逻辑地位根本不同。限定摹状词虽然可以被用作命题主词,但更适合被用作谓词或转换为谓词。专名作为主词时其指称物的存在已经不言而喻的蕴含于其中。当在自然语言中使用某个专名时就已经表达了专名所指物的存在。摹状词理论将容易被误认为是类似于专名的句子主项的非存在物限定摹状词转换到谓词的位置上,避免了将限定摹状词误认为是句子的逻辑主词而赋予其实际存在的错误。无论其所指物是否实际存在,限定摹状词仅表示事物的某种性质,而性质不能推论出主词是否存在。即使将存在放置在谓词的位置上,也不能赋予主词以实在性。因为存在不是某种性质,只有专名的所指物才具有存在物的必然性。专名蕴含的是存在,摹状词则只蕴含不知是否存在的某种事物或性质。
分析哲学家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则将专名和限定摹状词做出了明确区分。他认为专名只有指称,限定摹状词不足以承担专名的意义。无论所指物实际存在或非存在的限定摹状词都无法保证像专名所指物的必然存在。限定摹状词无法满足模态逻辑所要求的必然性,它不是专名意义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表述存在物的摹状词无法确定与所指物的必然联系,表述非存在物的限定摹状词更无法做到。专名蕴含所指物的必然存在,存在是所有一切可能性的集合。而摹状词不管所指物是否存在,只能说明某种属性,与对象的存在并无必然联系。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从模态逻辑角度是必然和偶然的区分。摹状词作为对象的偶然符号无法保证有实在性的存在物的存在,更无法保证非存在物的存在。限定摹状词只能是对所指物的某一方面性质的描述,而所指物并不一定存在。专名与所指物的固定联系则是由历史中形成的因果链条得到保证的,所以指称实际存在的对象。克里普克的区分做法说明专名指称某个对象并不取决于这个对象是否符合某些特征或这个专名的使用者是否相信这个对象具有这些特征,而只取决于这个对象本身的存在和人们使用这个名称对这个对象的命名活动。专名借助于某些与这个名字有关的历史事实去指称某个对象。指称虚拟事物的个体摹状词看似专名,但缺乏历史中的因果链条或者命名活动,因而只能描述人们在想象中赋予的某些有限的属性特征。
分析哲学家蒯因对分析哲学的重要贡献是重新恢复了分析哲学中本体论的地位,主张重新建立一种明确的标准或规范来检验语言陈述中的本体论承诺问题。蒯因认为存在的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什么事物存在和我们说什么事物存在。针对非存在物问题,蒯因认为当使用一个语词就认为承诺了其所指对象的存在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根源于意义与命名的混淆,把被命名的对象与词的意义混淆起来,认为为了使词有意义,其所指物必须存在。只要根据摹状词理论把这个词改成一个摹状词短语就可将其消解。据此蒯因指出“我们能够有意义的在语句中使用单独语词而无需预先假设有这些语词所要命名的对象。”这里蒯因所说的语词是非存在物的摹状词而不是专名。对于属性及共相的非存在物是否存在的问题,传统形而上学认为属性的存在比具体的存在更普遍。但蒯因指出,这种本体论的承诺可以不为真。共相的意义不是具有某种抽象的东西。蒯因指出“我们能够使用一般语词(例如谓词)而无需承认它们是抽象的东西的名字。”他认为名词和谓词的使用都不能承担关于非存在物的个别实体和共相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可以承担本体论承诺的只有现代逻辑中的“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在命题中量词是被用来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变项则涵盖一个可能的值域,变项的值是被带入命题置换变项的事物。因此,在语言中我们无法证明非存在物是否具有本体意义的存在,表述本体论承诺的唯一途径是把个别事物用量词归类。
总的来说,在语言中讨论非存在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必须明确意义与所指、存在与个别属性这两个方面的区分。表述个别属性的符号是限定摹状词,它只强调意义而与对象的存在并无必然联系;表述存在的符号是专名,它强调所指却可以没有意义或个别属性。个体的非存在物由于缺乏在使用中的历史因果链条而只有人们赋予它的想象中的意义因而没有所指,只是表述个别属性的限定摹状词,不是指示存在的专名。非存在物的共相同样只表述个别属性而不表示必然存在,两者都可以根据其意义转化为谓词而不必有实在性。将符号的指称物是否存在的问题转化为对于有限的个别意义或属性的探讨,从而将非存在物是否存在的问题消解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基本解决思路。
参考文献:
[1] Frege.Die Grundlagen der Arthmeti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 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M],2001。
[3] 涂纪亮,陈波.《蒯因著作集》第四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