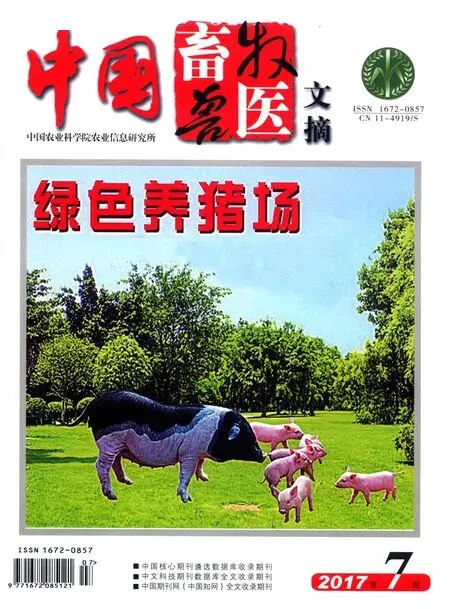关于完善我国动物防疫法律体系的几点思考
张绍军 陈向武 李卫华
关于完善我国动物防疫法律体系的几点思考
张绍军 陈向武 李卫华
完善的动物卫生法律体系是顺利开展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保障。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动物防疫法》)为核心,以《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法规为支撑,以《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等为配套的兽医法律体系,对于确保养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动物源性产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立法制度设计的适度超前性,《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规章经过近9年的运行,一些立法、执法等方面问题也日益凸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动物防疫工作的需要,因此建议及时修改补充完善,确保各项动物防疫工作顺利运行。
1 当前我国兽医法律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兽医法律体系建设既存在立法空白方面的问题,也包括现有制度运行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
1.1 配套规章不健全
1.1.1 《动物防疫法》授权制定配套法规的工作尚需加大力度。为了确保法律的可操作性,《动物防疫法》以“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或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的表述方式,授权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或商(会)国务院其他部门制定相关配套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这种授权类规定在《动物防疫法》中有近40处[1]。新《动物防疫法》施行之后,农业部组织制修订了《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10余部。从数量看还不足授权制定总数的1/6。一些需求迫切的规章至今未能出台,如《官方兽医管理办法》,制约了官方兽医队伍的发展。在实施《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的过程中,更需要制定系列配套规章,为实现《规划》的阶段性目标和总体目标提供立法支持。
1.1.2 现行的配套法规尚需尽快修订。《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颁布实施至今,动物检疫管理体制、疫情报告渠道、养殖场所选址布局、执业兽医资格准入管理制度、动物诊疗活动管理等不少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为确保相关法律制度的顺利实施,需要及时启动相关配套规章的立法后评估以及修订工作。
1.1.3 重大动物疫病根除净化缺乏法律依据。2012年,国务院在《规划》中提出了根除净化重大动物疫病的策略。但现行《动物防疫法》设计的法律制度绝大多数是为了适应动物疫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不完全适用动物疫病的根除与净化。从现行立法层面分析:一是法律规范没有疫病控制状态的规定,比如如何界定根除或净化的标准;二是强制免疫只有进入而没有退出机制;三是缺少动物疫病根除净化措施的法律规定。
1.1.4 尚未出台专门的《兽医法》。从人、事、物三方面综合立法或分别立法是确保兽医工作顺利运行的“三驾马车”,缺一不可。目前,多数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均制定了规范管理兽医人员的专门法律法规,对于促进兽医队伍发展、确保动物防疫工作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现行《动物防疫法》仅对官方兽医、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等3类兽医人员管理作了原则性规定。《动物防疫法》规定原则性强,操作性不够;配套的《官方兽医管理办法》仍未出台,现行的《执业兽医管理办法》《乡村兽医管理办法》中的一些制度设计从近几年的运行情况看也亟待完善,另外,受法律层次限制,配套规章处罚力度不够大,这都制约了我国兽医队伍的健康发展。
1.2 法律制度不完善
1.2.1 动物防疫主体责任没有有效落实。《动物防疫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和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养殖者是强制免疫法定责任主体。由于我国中小规模和散养仍占主体地位,受传统思维和工作模式影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府部门承担了散养动物养殖者的免疫责任,加之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滞后,致使养殖者本应当承担的强制免疫法定义务没有履行。
1.2.2 动物疫情尚不能及时如实报告。由于重大动物疫情的灾害属性不明确和疫病防控归责和扑杀补偿机制不合理,导致出现了地方政府不愿报、兽医系统不敢报、业主不想报的现象。同时,尽管《动物防疫法》规定,发现动物疫情可向兽医系统三个单位报告,但是由于没有突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疫情报告的主渠道作用,反而在事实上弱化了疫情报告体系的建设[2]。
1.2.3 检疫监管制度尚需健全完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动物检疫依法实施已有五十多年,其性质也历经了从技术措施、技术行政行为到行政许可的多次变革。但从实际情况看,动物检疫特别是产地检疫的技术含量却始终鲜有增长,官方兽医往往是通过查验免疫档案和肉眼观察后即出具检疫证明,有时候还存在隔山开证、只出证不检疫等问题,《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虽有“农业部规定的实验室检验符合要求”的规定,但在产地检疫过程中真正施行实验室检测的则为数极少。“以检促防”“以监促检”的实际效果并未真正显现。
1.2.4 法律责任部分需要调整。201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将“生产、销售检疫不合格,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病死或死因不明等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行为;或者在动物及动物产品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规定,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兽药等,足以造成他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列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司法解释主要涉及《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四)(五)款的禁止性规定。对于已经入刑的行为,不能再适用行政处罚的方式实施,需要及时修改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动物防疫法》与其他法律法规针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也有所差异,需要进一步协调。
2 有关思考
2.1 构建合理的动物卫生法律体系框架
我国兽医法律体系框架,可以围绕“人”(兽医人员)、“事”(疫病防治、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物”(兽医药品、兽医生物制品、兽医器械)这三个方面,构建兽医人员管理、兽医行为管理和兽医药品药械管理等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兽医法律体系,分别制定兽医法、动物卫生法、兽医药品法等。
2.2 构建兽医法律体系模式
借鉴国外大陆立法体系和英美立法体系经验,结合我国兽医立法体制实际,在人事物等方面平行立法。在此基础上,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依次相生,形成“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程或标准”等多层次的树状模式[3]。
2.3 制定中长期立法规划
首先,以《规划》提出的指导思想、防治目标和总体策略为指导,围绕疫病防控重点任务,确立兽医法律立法的中长期规划。其次,制定近期立法计划,在开展动物防疫法立法的评估基础上,着手修订《动物防疫法》,完善《动物防疫法》配套规章及相关规范制订,研究起草《兽医法》。再次,制订年度立法计划,优先着手解决近期《动物防疫法》授权立法的制修订问题。
2.4 建立相对固定的专家组织
在农业部层面组织立法、执法监督、动物疫病预防控制、行政管理、科研院所等方面的专家成立立法专家委员会,建立相对固定的专家组织,并按照动物防疫、检疫等实施分组管理,建立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为动物卫生立法建立良好的专家资源。专家组可以深入开展立法调研和评估,以及多形式、多层次的调研评估活动,提高法律规范的可行性、科学性、适用性和操作性。
摘自《中国动物检疫》2017年第34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