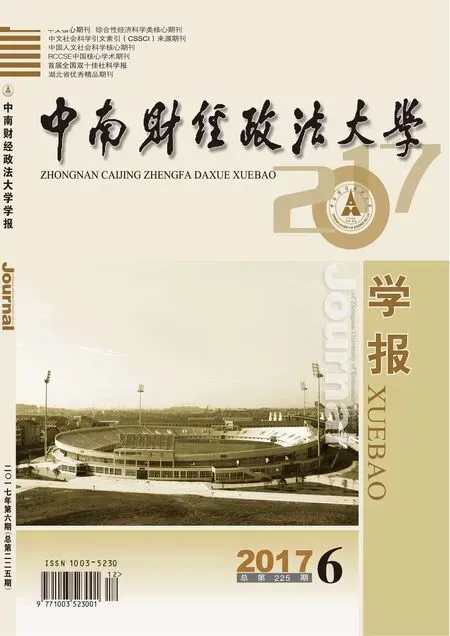产业结构转换研究述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产业结构转换研究述评
谢伟丽石军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产业结构转换长期受学术界关注,在产业结构转换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解释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本文首先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维度归纳了驱动产业结构转换的重要因素,需求侧驱动强调消费结构变化、需求收入弹性和消费外部性等引致的收入效应会驱动产业结构转换,供给侧驱动强调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引发的替代效应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转换。进一步地,本文系统考察了产业结构转换的动态过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转换的国际关联与国际差异,并归纳了产业结构转换的测度方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评价产业结构转换研究的关键问题、寻求理论模型拓展的未来方向、探讨产业结构转换的多重驱动机制、深化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等提供了文献基础。
产业结构转换;需求侧驱动;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
一、引言
世界大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产业间产出、就业和消费结构的显著转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结构转换(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1]。自库兹涅茨(Kuznets)将结构转换归纳为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①以来,产业间的结构转换就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而如何通过产业结构转换使经济稳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早期的学者如库滋涅茨(Kuznets)和钱纳里(Chenery)对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2][3][4][5],这奠定了“结构主义学派”的基本分析框架。近些年来许多文献更侧重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产业结构转换的驱动因素,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典型事实,丰富了结构转换的研究视野。不过,新近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日趋复杂,但对产业结构转换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出现了一些分歧,这说明学术界对产业结构转换的研究依然缺乏一致的结论。比如,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征从总体上被概括为两种不同的事实,即库滋涅茨(Kuznets)事实和卡尔多(Kaldor)事实。Kuznets事实体现在大多数经济体可观测的产业就业率变化的过程[2],Kaldor事实反映的是一些发达经济体过去几十年中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即一种增长率、利率、资本产出比率和劳动份额不随时间变化的状态[6](P177—222)。但是,关于哪一种事实是现代经济近乎合理的长期增长经验,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学者力图拓展一些理论框架来调和这两种事实,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的见解。比如,Duarte和 Restuccia将劳动力随时间在产业间的重新分配看作结构转换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的特征是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持续上升,以及工业部门就业先上升后下降[7]。显然,针对产业结构转换的研究,无论从理论探索角度还是从实践比较角度,都远未达成一致的共识。因此,及时对产业结构转换近年来的研究进行较系统的回顾、梳理和分析,对于厘清未来研究工作的逻辑思路和推动后续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从需求侧探讨产业结构转换的驱动因素;第三部分则从供给侧归纳产业结构转换的驱动因素;第四部分论述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第五部分通过国际贸易和国别差异两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换进行国际比较;第六部分则集中对结构转换的测量方法进行评述;第七部分为总结评论和提出研究展望。
二、产业结构转换的需求侧驱动机制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转换的需求驱动机制强调“恩格尔定律”等非位似偏好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恩格尔法则下,技术进步会提高收入水平,促使需求结构发生转变,即消费者偏好从农产品转向制造品[8]。结构转换的需求侧驱动力的研究主要基于“收入效应”视角展开,以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结构变化、需求收入弹性和消费外部性等对行业间要素分配的影响。这里的“收入效应”与微观经济学中收入效应的涵义不同,是指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会因产品间的收入弹性差异而发生改变,进而从需求端推动结构转换。现有研究遵循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效应源于消费偏好的非位似性,偏好的非位似性随收入变化而体现。自考虑偏好的非位似性和运用非位似效用函数分析消费结构变化与收入效应以来,对结构转换需求驱动力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采用Stone-Geary效用函数,如Kongsamut等(Kongsamut、 Rebelo和Xie,以下简称KRX)、Laitner、Echevarria、Rogerson通过引入Stone-Geary偏好描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恩格尔定律。这类文献认为,因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增长快于需求弹性较小的行业,从而导致生产要素从低增长部门向高增长部门流动,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1][8][9][10]。另一类是基于需求等级产生的非齐序效用函数,如Foellmi和Zweimüller、Buera 和Kaboski等学者引入序列消费偏好揭示结构变化的原因。此类文献认为,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新产品会被创造和生产,进而形成新兴行业,消费者对现有产品的偏好低于新产品,从而促使新行业快速扩张,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产品种类的增多,单位新产品对经济的影响亦日渐减弱,结构变化也逐渐趋于平缓[11][12][13]。
限于篇幅,本文首先重点归纳和总结KRX、Foellmi和Zweimüller、李尚骜和龚六堂、Alonso-Carrera和Raurich等文献中对需求驱动机制的说明[1][11][14][15],以梳理相关文献从需求侧对Kuznets事实和Kaldor事实进行解释的理论演进过程。这几篇文献是近年来有关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引用较多的文章,尤其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改进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具体而言,KRX在三部门模型中引入了最低维持/禀赋性消费,消费者具有Stone-Geary偏好②,揭示了各部门消费对总消费的贡献强度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且由于效用函数的非位似性,促使产业结构随收入的提高而发生变化[1]。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最早探讨了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中的Kaldor事实同时出现需要满足的条件,即偏好参数和初始技术参数存在特定关联这样一个“刀刃条件”,我们可称之为Kongsamut- Rebelo-Xie条件(以下简称KRX条件)。只有满足KRX条件时,伴随着结构变化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包容Kaldor事实的“扩展平衡增长路径”,即各行业增长率存在差异但经济总量增长率不变的路径[1]。李尚骜和龚六堂在KRX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内生偏好视角,构建了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并引入非位似偏好,假设农业和服务业内部存在不同的偏好结构,将内部偏好结构的变化看作经济代理人自主决定的一种内生化行为[14]。在这一假设条件下,农业和服务业部门内部的偏好结构由经济代理人所决定,即经济代理人受各种影响因素驱动决定农业部门维持生存消费和服务部门自我提供服务的大小,而农业和服务业部门内部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会引起这两部门实际利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差异,进而推动生产结构变化,同时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变化体现了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4]。
与KRX相似的是,Foellmi和Zweimüller也认为产业结构变化是由各部门需求收入弹性不同所驱动的,但是其运用的具体模型和研究视角又有所不同。他们基于非线性恩格尔曲线驱动结构变化的理论模型,重点分析就业的动态变化和总需求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结构转换的动力源于居民越来越富有所引起的消费结构变化[11]。类似地,他们也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三部门模型,产品类型的假设与Kongsamut等基本一致。在序列偏好的假设下,随着收入的增加,新产品被持续引入市场,这些新产品最初都是高收入弹性的非必需品,并随时间的推移成为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品,故恩格尔曲线的非线性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周期推动了结构变化[11]。Foellmi和Zweimüller指出,产业结构的转换可以通过就业率刻画,即随着消费需求的变化,农业就业率单调递减、服务业就业率单调递增、制造业就业率呈“倒U型”趋势[11]。与其他研究非位似偏好和非线性恩格尔曲线对结构变化影响的文献不同的是,这篇文献的一个边际贡献是指出需求引致的结构变化可以包容Kaldor事实,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
如上文所述,KRX基于需求侧提出了同时包容Kuznets事实和Kaldor事实的KRX条件,显然,这一件是比较苛刻的。是否存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条件能够说明Kuznets事实和Kaldor事实则成为近期文献关注的主题之一。如Alonso-Carrera和Raurich借助于多部门外生增长模型,认为非位似偏好驱动了产业结构变化[15]。他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各部门要素的占比(资本占比和就业占比)纳入函数中,假定各部门技术进步率相同,效用函数中同样引入了维持/禀赋性消费,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各部门消费因维持/禀赋消费参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各部门就业份额和消费份额会发生变化,从而驱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③[15]。他们得出的产业结构转换的需求驱动机制与KRX极为相似,但与KRX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在非刀刃条件下也可以同时存在。其中的关键在于两者总量最低消费的值不相同,KRX的结论是必须在总量最低消费值等于0的刀刃条件下才能实现,而Alonso-Carrera和Raurich将加总最低消费需求占GDP的比值设定为最低消费需求的水平,发现只要最低消费需求的初始水平足够小,结构变化和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就能够同时出现[15]。他们采用美国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当最低消费需求的初始值是GDP的25%时,经济中的均衡是最优的[15]。
上述从需求侧探讨结构转换动力机制的文献基于收入效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引入非位似偏好,他们的重要区别在于对消费偏好的设定,即模型中对部门消费加总的假设不同。事实上,除了各部门需求的收入弹性差异,其他需求因素也可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如Hori等基于消费外部性的角度提出了结构转换的一种驱动机制,认为结构变化是由非齐序偏好和各部门不平衡生产率增长共同导致的[16]。他们从消费外部性的影响程度出发,假设消费外部性对个体的消费偏好存在较大影响,借助于一个简单的多部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内生增长模型,发现特定商品的消费外部性可能是结构变化的一个来源[16]。换言之,当商品消费外部性的程度不同时,每个部门的增长率也不相同。这与此前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所不同,比如KRX、Alonso-Carrera和Raurich的模型在加总部门消费时,消费者决策主要考虑个人消费对效用的影响,并不考虑个人消费对各部门消费的外部性影响[1][15]。
三、产业结构转换的供给侧驱动机制
产业结构转换的另一类动力机制来自供给侧,供给侧的驱动机制侧重于从生产结构方面重点分析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供给侧驱动力也可称为替代效应或相对价格效应,即随着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各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因部门间生产技术方面的差异与资本深化水平会发生变化,进而从供给端驱动产业结构转换[17][18]( P188—218)[19][20]。概括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早期的学者重点考察技术进步差异对结构转换的影响。如Baumol最早从供给侧强调部门间生产率增长差异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影响,他认为部门间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源于生产率差异[17]。其次,鉴于KRX从需求侧解释结构变化和经济总量平衡增长的研究,近期的研究也逐渐从供给角度将结构转换与Kaldor事实融合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中,考虑相对价格效应对结构转换的影响。如Meckl借助基本的研发驱动增长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率引致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一般均衡增长路线上,宏观变量的增长率不变,部门最终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率是变化的,最后的结果是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和结构变化同时发生[21]。再次,考虑到金融体系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探讨金融发展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流动而影响产业结构转换也变得较为重要。Lin等认为一国金融体系与其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相匹配,才能够有效发挥金融的作用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22]。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换的供给驱动机制加以说明。
(一)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
不少学者探讨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影响。Ngai 和Pissarides构建了一个部门间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对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19]。该模型的主要特点是假设部门间全要素生产率(TFP)即技术进步存在外生差异,并把结构转换归因于部门间技术进步率的不同,揭示了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劳动力由高技术进步率部门向低技术进步率部门转移,并最终收敛于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与生产率增长速度最低的部门[19]。他们虽然利用理论模型说明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研究结论也大致符合Kuznets和Kaldor典型事实,但这一结论仍不够严谨。Acemoglu 和Guerrieri在Ngai 和Pissarides的研究基础之上,从资本深化的角度分析能够实现部门间非平衡增长与Kaldor事实同时存在的条件[20]。他们修改了生产函数的假设条件,借助于非平衡增长的两部门模型,运用不变替代弹性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设技术进步外生和各部门要素产出弹性不同,认为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是部门间要素密集程度的不同和资本的不断深化,资本深化趋于增加资本密集程度较高部门的产出,但同时导致资本和劳动要素从该部门转移进而在部门间重新配置,最终所有要素将收敛于某一个部门,经济也由多部门收敛于单部门,从长期上实现总量的平衡增长,符合Kaldor事实[20]。
借鉴Acemoglu 和Guerrieri的理论模型,陈体标构建了包含最终部门和多个中间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假设经济中只有一种消费品,由中间产品以不变替代弹性函数所生产,而中间产品按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生产[23]。他的理论模型不考虑资本深化,并得出了比Ngai和Pissarides更为具体的结论:由于中间部门的技术增长率存在差异和多种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具有替代性,使得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间流动,进而导致中间部门的产出份额发生变化,而中间部门产出份额的变动方向取决于中间产品间替代弹性的大小。依据不同的替代弹性,该模型能同时包容Kuznets和Kaldor两种事实[23]。进一步地,Alvarez-Cuadrado等认为部门间要素产出弹性差异能够影响产业结构,并且各部门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同也会引起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分配的不同,这主要是他们考虑了不同部门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差异影响资本和劳动分配的机制[24]。与Ngai 和Pissarides、Acemoglu 和Guerrieri不同的是,该研究基于各部门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差异假设,采用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分析部门和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24]。上述文献中的模型均假设代表性家庭具有不变的跨期替代偏好,采用了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从供给侧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说明,并能够解释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但是,他们提出的经济总量平衡增长由多个假设条件所限制,且因为理论模型最终均收敛于单一部门,故上述结论并不能很好地包容多部门的平衡增长。
(二)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换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金融体系发展导致的投资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第二,金融体系可通过激发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进步和影响资本积累,并基于替代效应作用于产业结构转换。具体而言,现有关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文献多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金融体系对产业结构转换的供给驱动。Chava等认为金融机构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从而推动科技创新和形成资本积累,使得长期内经济保持增长和带动产业结构变迁[25]。相似地,Brown等采用16个欧洲企业在1995~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对融资约束与R&D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能够影响企业的研发投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的改善能够激发技术创新、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自由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活动,从而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换[26]。其他学者如Sasidharan等也认为金融发展改善了企业的融资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持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进而对结构变化产生影响[27]。易信和刘凤良在Ngai和Pissarides、Acemoglu 和Guerrieri的研究基础之上,将金融中介部门引入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进而拓展为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他们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该理论模型能包容Kuznets和Kaldor事实,且发现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与“结构”效应驱动产业结构转换和促进经济增长[28]。
综合产业结构转换的需求和供给驱动机制而言,需求和供给是紧密相联的,需求侧对结构转换的影响离不开供给侧的推动,如KRX、Alonso-Carrera和Raurich、Hori等也考察了各部门技术进步率不同对结构变化的影响[1][15][16]。这也引发如下的问题:单独从供给或需求方面研究结构转换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能否在一个模型中同时考虑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事实上,Matsuyama就曾考虑过非位似偏好和部门间不平衡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推动[29]。后来的研究中也不断有学者明确提出需求和供给因素均能影响产业结构转换,诸如Boppart综合考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来揭示产业结构转换的成因和过程[30],Herrendorf等通过对比需求和供给侧因素在模型中的影响机制以寻求产业结构变化的合理解释[31]。其中,Boppart指出,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共同决定结构转换,并且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能够包容Kaldor 事实,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Non-Gorman偏好的模型,假定收入不平等能够影响总量需求结构,并采用美国数据对结构变化、支出增长和相对价格的动态变化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替代效应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大致相同[30]。Boppart对偏好的设定与Foellmi 和Zweimülle提出的序列消费偏好相似,同样基于非线性恩格尔曲线的经验事实。不同的是,该模型中引入与价格无关的广义效用函数,强调了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而研究相对价格效应[30]。Herrendorf等运用部门消费支出比重数据,分析美国居民在1947~2007年间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偏好选择,指出相对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都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31]。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最终消费支出中,收入效应是消费支出比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消费增加值中,相对价格效应是其变化的主要动力[31]。由这些研究结论可知,产业结构转换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或者是要素价格扭曲等因素,都能够影响产业结构转换过程。因此,供给侧的改革也不能脱离需求因素,供给和需求如何形成良好的互动并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积极效应,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产业结构转换过程
尽管大量的理论文献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内生驱动机制已经做了许多研究,但是更多的经验研究还是具体考察三次产业的动态变化过程。Caselli和Coleman、Dekle和Vandenbroucke等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动态变化视角来研究结构转换过程,他们并不关注理论模型中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而是重点考察在供给或需求因素驱动下的结构转换如何引导三次产业在数量、比重和地位等方面的交替变化,并透过产业变化更为深入了解结构转换[32][33]。徐朝阳基于Acemoglu 和Guerrieri的两部门模型,引入双层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构建了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三部门模型,刻画了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上升和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化过程,该过程受各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和产出增长速度的影响,体现为生产要素由产出增长慢的部门向产出增长快的部门流动[34]。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本文对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从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农业
农业是产业结构转换的初始部门。Caselli和 Coleman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关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下降的结构转换现象: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得教育和培训成本不断降低,从而造成大量劳动力从非技能的农业部门转移至需要技能的非农业部门,导致农业部门产出和就业率下降[32]。他们认为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缺乏和技术进步是促使结构转换的主要原因,还提出美国在结构转换的初始阶段,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换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20世纪的区域融合,并运用美国1880~1990年的数据从价格和数量上对此进行了解释[32]。近期也有学者依据结构转换中农业变化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转换。如Cao和Birchenall运用两部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包括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非位似效用函数,采用中国1991~2009年微观企业数据对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校准,研究发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产出和就业流向非农业部门的主要原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初是通过将劳动力重新分配到非农业部门来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出现了人力和实物资本集聚[35]。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后结构转换的还有Dekle和Vandenbroucke,他们采用中国1978~2003年的相关数据,对资源从农业部门重新配置到非农业部门的转换活动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率分别呈下降、“倒U型”和上升趋势[33]。与Caselli 和Coleman、Cao 和Birchenall不同的是,Dekle 和Vandenbroucke考虑了国有规模这一因素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影响,他们指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结构转换除了受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还受企业国有特征和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强调了资源在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再分配[33]。
(二)工业和服务业
工业和服务业的动态变化是产业结构转换的重要标志,Buera 和Kaboski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起进行了研究[12][13]。他们运用31个发达国家样本数据,经分析发现制造业的名义增加值份额呈“驼峰型”变化[12]。他们重视以制造业兴起为主的经济结构长期变化,分析经济发展中从传统的小规模家庭手工业到大规模制造业的转变过程,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将生产单位规模的作用引入高增长的现代技术和停滞的传统生存技术两种不同的模型中,分析代表性家庭、制造业和服务业三种生产规模单位的结构变化,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部门间的生产规模差异又引起产业结构变化,进而促进工业化和市场化[12]。通过观察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Buera 和Kaboski发现美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1950年的60%上升至2000年的80%,其中技术密集型服务份额增加了25%,低技术水平服务的份额反而有所下降[13]。他们探讨了技术密集度在产业结构变化中的作用,发现服务业的增长是消费向技术密集度更强的产出活动转变所刺激的,即当生产力上升时,需求转向技术密集更强的产出,提高了服务业市场化相对于家庭生产的重要性,有助于服务业的迅速发展[13]。同时,该文献也指出虽然非位似偏好引起的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服务业的兴起,从而引发了结构转换,但是这一过程也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作用[13]。
此外,还有学者考察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Moro,他并不关注产业结构转换的驱动机制,而是基于工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的视角,分析二者所产生的结构转换效应对GDP波动的影响[36]。具体而言,他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探讨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结构转换对GDP波动性下降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美国在1960~1983年和1984~2005年这两个阶段GDP增长下降的过程中,结构转换效应占28%。换而言之,服务部门规模的扩大会挤占工业技术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GDP增长的下降主要源于工业技术冲击,服务业比重的上升给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远远小于工业比重下降对经济的负向冲击效应,这意味着服务业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外部性作用弱于工业[36]。
五、产业结构转换的国际比较
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仅研究单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显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国的产业结构转换如何处理与国际环境的关联、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何异同等问题更值得关注。近期考察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转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国际贸易与各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关系;另一类是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进行比较分析。
(一)产业结构转换与国际贸易
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加深,国际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分析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产业结构转换成为一种趋势。周辰亮和丁剑平基于开放经济下的三部门模型,考察了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影响,认为部门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是推动结构转换的重要因素之一[37]。Kuralbayeva和Stefanski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的两部门模型,假设制造品参与国际贸易,而非制造品不参与国际贸易,旨在分析因原材料出口产生的暴利而引起的劳动力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的流动过程[38]。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贸易如何通过供给或需求因素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转换?产业变化趋势如何?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Frankel 和 Romer指出一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它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就会越高,贸易开放度通过提高生产率作用于结构转换,它能够引导资源从低生产率行业转向高生产率行业,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变化[39]。Dessy等借助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贸易开放度可通过两种直接效应(降低内销品的相对价格和提高农业生产投入的需求)促使农业部门扩大,从供给侧(如技术进步)推动经济体的结构转换[40]。进一步地,Teignier对美国(1890~2007)、英国(1800~1900)和韩国(1963~2007)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国际贸易作用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对美国、英国和韩国的产业结构转换都具有积极的驱动作用[41]。鉴于韩国在20世纪后期的突出表现,一些学者关注其产业结构转换与国际贸易的关系,Betts等构建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的三部门模型分析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结构转换的影响,运用韩国和OECD国家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研究显示:就韩国而言,虽然封闭经济模型中各部门的非位似偏好和生产率差异是导致其农业增加值和就业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但却不能很好地说明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份额的增加,而引入贸易的两国模型则能够较好地解释这一问题[42]。因而,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贸易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消费需求推动结构变化。
(二)产业结构转换的国别差异
上文提到学者们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考虑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换,如Betts研究中涉及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主要关注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转换的作用,并没有对收入水平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进行比较说明[42]。而国家间不同的发展程度与结构特征具有高度一致的关系,如杨天宇和刘贺贺同时考虑非位似偏好、部门间生产率差异、劳动力流动壁垒因素,构筑了一个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揭示了1978~2004年间中国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指出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中国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印度,而印度产业结构转换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工业,加大了其与中国总劳动生产率的差距[43]。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换路径进行归纳和总结。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转换的路径有所差异。基于库滋涅茨和钱纳里关于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Bah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阶段中三次产业比重和人均GDP的关系为切入点,研究了它们的产业结构转换路径,并借助于多项式函数检验各国产业产出份额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两组不同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44]。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路径与库滋涅茨事实一致,随着经济发展,资源依次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流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不同,没有遵循统一的路径[44]。该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路径出发,提供了研究产业结构转换的新视角,但文章主要关注中国等发展初期的产业结构转换,2000年以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点并没有在文中体现,也没有充分阐述理论基础。
其次,探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产业结构转换路径存在差异的原因。不少文献从供给角度研究富国和穷国之间技术进步率的差距问题,具体说明部门间生产率差异的大小。Bah运用三部门模型,借助于美国、韩国、巴西和喀麦隆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选取部门就业率和人均GDP对部门TFP进行了测算[45]。他发现,相对于美国,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生产率比制造业低,这些国家将较多的劳动力分配到了服务业[45]。不同的是,Herrendorf和Valentinyi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体分析发展中国家食品、生产消费、服务业、设备和建筑5个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与美国相比,发展中国家食物、建筑、设备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大于经济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制造业和消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基本与经济总量持平,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小于经济总量,其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是由相对价格的不同导致的[46]。他们从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经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不同,与传统意义上的两部门或三部门模型不同,但因生产函数数据限制,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和政策的重要性。
最后,世界各国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也是跨国分析的重要部分。Dabla-Norris等运用168个国家在1970~2010年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际增加值数据对结构转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分别对全样本和分区域(发达经济体、新兴与低收入国家群体、按国家所属州)产业比重变化趋势的显著差异进行描述和分析[47]。他们采用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后发现,国家间产业比重的差异大多来源于国家特征,如实际人均GDP、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47]。相似地,Buera和Kaboski对30个国家的工业、服务业、农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各产业实际人均产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比重呈下降趋势,制造业比重呈“倒U型”变化,服务业先缓慢上升,随着制造业比重下降而迅速上升[12]。
六、产业结构转换的测度方法
在经验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准确而合理的测度产业结构转换,合适的测量方法有助于考察产业间的动态变化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一般而言,衡量产业层面经济活动常用的指标包括就业、增加值和最终消费支出份额3种。依据视角的不同及数据的可得性,这几种产业结构转换的衡量方法和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根据不同衡量指标的属性,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对上述3种测度方法进行说明。
(一)生产角度
产业的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均属于生产领域。库滋涅茨通过收集不同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具体数据,借助于理论模型和统计方法,归纳出样本国家三次产业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的变化规律[2]。Buera和Kaboski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借助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数据,检验人均GDP与不同产业增加值份额之间的关系,以测度结构转换的产业变化趋势[12][13]。Buera和Kaboski发现美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稳步上升[13]。类似的还有Bah、Dabla-Norris等运用产业就业份额或增加值份额通过简单回归分析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结构转换[44][45][47]。这一类测度方法操作简单,数据也易于获得,能够观察到产业显著的变化趋势,故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这种测度方法并不能量化产业结构转换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判别不了结构转换效应的优劣。不同的是,Moro并没有局限于通过产业增加值份额或就业份额分析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而是重点考察了美国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结构转换对其GDP波动的影响,采用校准法模拟了产业结构转换的效应[36]。
(二)消费角度
采用消费领域的最终消费支出份额指标测度结构转换与生产领域的两个指标的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对制造业的测度。产业消费支出份额的数据获得难于生产领域的测度指标,不易于操作,故这种方法的应用范围并不广泛。Boppart利用美国二战后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数据,对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结构转换进行经验分析[30]。Herrendorf等在考察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机制时,基于效用函数,运用三次产业的最终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投入产出关系,从而揭示伴随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对产业结构转换的驱动[31]。
事实上,无论是生产领域的就业份额和增加值比重,还是消费领域的消费支出份额,都不能够完全测度结构变化。在现有文献中通常采用这些指标开展基础的经验研究,再结合理论模型,采用校准或数值模拟等方法,深入分析产业结构转换。因此,在研究中测度产业结构转换并不能仅从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判断,仍需要结合理论模型,寻求变量间的内在联系,方能更好地从理论和实证上理解结构转换。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自引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增长以来,产结构转换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本文主要对2000年以来关于结构转换研究的相对前沿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分别从驱动机制、变化过程、国际贸易、国别差异、测度方法等方面对相关文献加以评述和总结。事实上,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主题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无论是产业间的动态变化,还是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转换的作用,或者是不同国家产业结构转换的差异,都是围绕经济增长中由供给和需求因素驱动的结构转换展开的。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阐释了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机制以及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了供需驱动下的结构转换在三次产业中的具体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揭示开放经济环境下贸易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影响,同时考虑发展程度与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归纳产业结构转换的测度方法,以期为结构转换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虽然现有文献围绕产业结构转换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在有些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完善,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从理论模型着手,遵循供给或需求两条路线寻求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但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型可以解释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与结构变化;其次,供给和需求因素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协同效应一直被忽略,这方面的研究仍存在明显的不足;进一步地,产业结构转换过程的研究多局限于三次产业的动态变化,鲜有文献观察产业间的动态变化对经济产生的结构效应;再次,关于贸易对产业结构转换的研究还不成熟,缺乏一个比较合适的开放经济模型分析贸易的作用;最后,由于涉及国家较多、国家间的异质性、数据难以获得等原因,产业结构转换的跨国比较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约束,时间基本都在2010年以前,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向进一步探讨产业结构转换的作用机制和新趋势:
(1)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仍需进一步完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变化,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理论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现有经济增长研究中引用最多的理论模型,大多数学者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对生产函数(供给)和效用函数(需求)假设条件的不断改进,从理论上分析结构变化的驱动机制,寻求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而现有研究中,具有产业结构变化的多部门增长模型所描述的平衡增长是在苛刻的约束条件下的单一平衡状态,并没有准确预测多部门的平衡增长,故增长模型仍需不断改进方能更好地解释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机制,并探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据前文分析,产业结构转换并不仅仅受单一因素的影响,它是多种因素(如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虽然已有学者考虑相对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对结构变化的协同作用,但理论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特别地,考察多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深入了解产业结构转换的具体作用机制。
(3)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有待于深入研究。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再工业化”战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实施,如美国、德国、英国、中国等,工业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但就目前而言,“服务业主导论”似乎在理论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现有文献中关于工业和服务业互动关系的研究比较匮乏,没有形成广泛的理论基础和进行深入的经验分析。因此,明确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机制有利于深刻理解产业结构转换,更有助于分析产业结构转换与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4)结构转换研究中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个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产业结构转换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开放经济环境下,各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已有研究表明贸易对其产业结构转换有重要作用,而竞争优势是经济发展理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故应注重思考产业结构转换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虽然结构变化与比较优势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学者从竞争优势的视角分析产业结构转换。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基于国际竞争优势视角,探寻产业结构转换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既具有理论价值又能够完善现有研究成果。
研究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转换对中国经济实践具有现实意义。中低端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开始回落,需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和经济下行的压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稳定经济增长,重视供给侧结构改革”,强调这是适应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必然要求。此后,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和各界关注的热点。而需求侧改革则逐渐淡化,甚至有观点认为需求侧改革已不再有效。其实不然,供给和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供给侧改革强调通过资源有效配置来提高生产质量和经济效益,解决供给问题本质上也是在刺激和创造新的需求,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因而,解决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复杂问题,必须供需双管齐下,既要解决供给侧存在的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问题,还应尽快摆脱需求不足的困境,通过积极有效的产业结构转换,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同发展,扩大有效供给和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这些典型特征主要包括6个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产量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很高,这是最显著的特征;生产率快速增长;经济结构迅速转变;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开始走向世界,瓜分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尽管有扩散到全世界的倾向,但实际的扩散却是有限的,只局限于全世界1/3的人口范围内。
②在Stone-Geary偏好中,农产品是必需品,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制造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趋近于1,服务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
③该研究没有考虑供给侧因素对结构变化的影响,而是将其设为一给定的因素。
[1] Kongsamut,P.,Rebelo,S.,Xie,D.Beyond Balanced Growth[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1,68(4):869—882.
[2] Kuznets,S.Modern Economic Growth:Findings and Reflection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63(3):247—258.
[3] Kuznets,S.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57,5(S4):1—111.
[4] Chenery,H.B.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0,50(4):624—654.
[5] Chenery,H.B.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65(2):310—316.
[6] Kaldor,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C]//The Theory of Capital.Palgrave Macmillan UK,1961.
[7] Duarte,M.,Restuccia,D.The Role of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ggregate Productivit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125(1):129—173.
[8] Laitner,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0,67(3):545—561.
[9] Echevarria,C.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7,38(2):431—452.
[10] Rogerson,R.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 Outcom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2):235—259.
[11] Foellmi,R.,Zweimüller,J.Structural Change,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8,55(7):1317—1328.
[12] Buera,F.J,Kaboski,J.P.Scale and the Origins of Structural Change[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12,147(2):684—712.
[13] Buera,F.J,Kaboski,J.P.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6):2540—2569.
[14] 李尚骜,龚六堂.非一致性偏好、内生偏好结构与经济结构变迁[J].经济研究,2012,47(7):35—47.
[15] Alonso-carrera,J.,Raurich,X.Demand-Based Structural Change and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5,46(2):359—374.
[16] Hori,T.,Ikefuji,M.,Mino,K.Conformism and Structural Change[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15,56(3):939—961.
[17] Baumol,W.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415—426.
[18] Kravis,I.B.,Heston,A.,Summers,R.The Share of Services in Economic Growth[C]// Global Econometrics:Essays in Honor of Lawrence R.Klein,The MIT Press,1983.
[19] Ngai,L.R.,Pissarides,C.A.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1):429—443.
[20] Acemoglu,D.,Guerrieri,V.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3):467—498.
[21] Meckl,J.Structural Change and Generalized Balance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s,2002,77(3):241—4266.
[22] Lin,J.Y.,Sun,X.,Jiang,Y.Endowment,Industrial Structure,and Appropriate Financial Structure: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2013,16(2):109—122.
[23] 陈体标.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7,(04):1053—1074.
[24] Alvarez-Cuadrado,F.,Van Long,N.,Poschke,M.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Structural Change and Growth[J].Theoretical Economics,2017,12(3):1229—1266.
[25] Chava,S.,Oettl,A.,Subramanian,A.,et al.Banking De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109(3):759—774.
[26] Brown,J.R.,Martinsson,G.,Petersen,B.C.Do Financing Constraints Matter for R&D?[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2,56(8):1512—1529.
[27] Sasidharan,S.,Lukose,P.J.J.,Komera,S.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vestments in R&D: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 Firms[J].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5,(55):28—39.
[28] 易信,刘凤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15,(10):24—39,90.
[29] Matsuyama,K.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Comparative Advantage,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92,58(2):317—334.
[30] Boppart,T.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Kaldor Facts in a Growth Model with Relative Price Effects and Non-Gorman Preferences[J].Econometrica,2014,82(6):2167—2196.
[31] Herrendorf,B.,Rogerson,R.,Valentinyi,A.Two Perspectives on Preference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7):2752—2789.
[32] Caselli,F.,Coleman II,W.J.The U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A Reinterpret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109(3):584—616.
[33] Dekle,R.,Vandenbroucke,G.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12,36(1):119—135.
[34] 徐朝阳.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倒U型”产业结构变迁[J].世界经济,2010,33(12):67—88.
[35] Cao,K.H.,Birchenall,J.A.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Structur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 in Post-Reform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3,104:165—180.
[36] Moro,A.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and the Decline in the US GDP Volatility[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12,15(3):402—415.
[37] 周辰亮,丁剑平.开放经济下的结构转型:一个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J].世界经济,2007,(6):27—34.
[38] Kuralbayeva,K.,Stefanski,R.Windfall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pecializ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90(2):273—301.
[39] Frankel,J.A.,Romer,D.Does trade Cause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3):379—399.
[40] Dessy,S.,Mbiekop,F.,Pallage,S.On the Mechanics of Trade-induce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0,32(1):251—264.
[41] Teignier,M.The Role of Trade i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Z].SSRN Working Paper No.1984729,2009.
[42] Betts,C.et al..Trade,Reform,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Z].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No.49540,2013.
[43] 杨天宇,刘贺贺.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印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J].世界经济,2012,35(5):62—80.
[44] Bah,E.H.M.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Z].Proceedings of the German 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ference,Frankfurt a.M.No.42,2009.
[45] Bah,E.H.A Three-Sector Model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Z].Dynamics,Economic Growth,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onference Papers No.c014,2009.
[46] Herrendorf,B.,Valentinyi,A.Which Sectors Make Poor Countries so Unproductive?[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2,10(2):323—341.
[47] Dabla-Norris,E.,Thomas A.H.,Garcia-Verdu,R.,et al.Benchmark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cross the World[Z].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ashington DC,Working Paper No.13/176,2013.
(责任编辑:陈敦贤)
F264
A
1003-5230(2017)06-0041-11
2017-09-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金融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及其效应测度研究”(13CJY06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工业发展、结构转换与出口质量”(2016Y1050)。
谢伟丽(1990— ),女,安徽淮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石军伟(1977— ),男,河南汤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