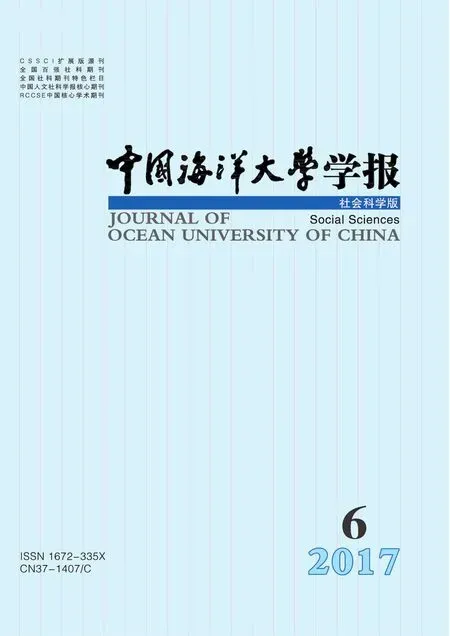唐代“涉外”婚姻制度考思*
崔彩贤 付常辉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2.天津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2)
唐代“涉外”婚姻制度考思*
崔彩贤1付常辉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2.天津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2)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和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扩大,面临的涉外问题也更加频繁和复杂。涉外婚姻家庭领域是国际私法最为复杂的一个分支,《法律适用法》对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做了最基本的原则性规定。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梳理了唐代涉外婚姻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探究其基本理论,分析其基本内容和重要特质,对其积极性和局限性作出评价,并总结了唐代涉外婚姻制度对当代的启示,为进一步完善涉外婚姻法律适用的规定提供一定的借鉴思路。
唐代;“涉外”婚姻;化外人制度
婚姻是一种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种族、时代、地域以及宗教等背景,自奴隶制社会起,我国婚姻由成立到解除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度,由习惯到成文的礼再到法律规范,日臻完善。我国当代法律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尤其是婚姻家庭领域,古代的婚姻伦理、家庭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在当代婚姻法律中体现明显,因为婚姻家庭观念作为公序良俗的一方面虽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长远来看,其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唐代法律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制的集大成者,表现出盛世之下法律的成熟性、多样性、包容性,是中华法系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古代中国的“外国人”不仅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其他国家的人,还包括其他民族、其他法域的人。如,在已有“外国人”这一名词的唐朝,法律中依然以“谓藩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的“化外人”来制定有关“教化”以外的人的法律。[1]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文所指唐代的“涉外”包括与唐相对的其他主权国家以及位于唐国内但当时的法律、礼仪制度不能直接适用的少数民族区域。
一、研究缘起
(一)开放创新的时代背景
唐代是中国几千年文明运转更替中一个典型的朝代,特殊的历史时代造就了唐代法律制度开放创新的制度特色和时代背景。“涉外”婚姻制度不是唐代“首创”,但无疑是最具典型意义和影响较大的涉外制度之一。
1、“丝绸之路”拓展了唐代统治者的经济视野
唐代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之后中国封建历史上又一个统一稳定的朝代,民族关系较为融洽,国力昌盛,经济极度繁荣。以交通为例,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网络,大运河的开通更是使南北几大流域相通,两京的船只北达幽州、南抵两广,国内的产品可通过陆运和河运互通有无。与此同时,伴随着唐代开明、开放的政策和统治者开阔的经济视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远射和拓展,成为唐代和外国沟通的桥梁,唐代时长安等几大重要城市外国人云集,有“身处长安,如在异域”之说。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观念的进步,增强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心,为涉外婚姻的发展以及涉外婚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物质基础。
2、多元文化的普纳成就了中原民族的融合态势
自开国之君高祖李渊开始,唐代制定了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国内的儒、释、道文化和谐互补,且与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其他西域宗教多元并存。而且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民族融合的趋势不断加强,原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先后进入中原,与黄河流域的汉人不断融合,华夏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普通汉人对于异族、对于外国人的排斥性也逐渐降低,为涉外婚姻的发展以及涉外婚姻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3、开明的政治制度孕育催生了成熟的法律制度
唐代基本继承了北朝和隋的法律制度,并在建国初的几个时期不断完善,从《武德律》、《贞观律》到《永徽律疏》(《唐律疏议》),唐代的法律制度达到了顶峰,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中也首次出现了“化外人”制度以及涉外婚姻制度。唐代中央平等对待各少数民族,坚持夷夏平等,为唐代涉外婚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和政治基础。
(二)当代学术研究的附属性和间接性
学术界关于唐代婚姻制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付永聚、[2]姜晓强、[3]张嫣娟等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唐代涉外婚姻进行了分类;[4]高树异、[5]吴美菊和黎嫦娟等学者对涉外婚姻中的“外国人”进行了界定和分析;[6]郑显文和田廷柱梳理了外国人来唐的优惠政策、类型和生活状况;[7][8]管辉和张伯晋围绕《唐律疏议》原文解析了唐代法律制度对于涉外婚姻的态度,[9][10]比较了唐不同时期官方对于涉外婚姻的态度及原因;费超介绍了李唐皇室的“涉外”婚姻(和亲),并指出对当时社会涉外婚姻制度的重大影响。[11]
一方面,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框架的提出和倡议,已经有大约60多个国家加入到该战略框架之中,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完善和实践操作。国内开明的政治和多民族融合统一的政策,国际上开阔的经济卓识和远见以及开放的对外政策,当代中国出现了与唐代相似而又更进步创新的时代背景和特色。另一方面,理论上对唐代涉外婚姻制度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且与唐代法律制度的联系较弱,大多是研究唐代婚姻制度或者涉外民事制度的附属产品,理论研究表现出附属性和间接性特征。本文对唐代涉外婚姻制度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发掘与思考。
二、唐代涉外婚姻制度的基本类型和重要特征
(一)基本类型
按照涉外婚姻关系成立地域标准,唐代涉外婚姻可分为和亲型、边塞型以及内地型。
1、和亲型。政治和亲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鲜见,中国比较有影响的有春秋时期的秦晋之好、西汉时的昭君出塞,唐代延续了政治和亲的传统,且在数量上多于前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和亲作为涉外婚姻的一种典型形式,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大多婚姻不过是实现政治诉求的一种手段。唐代,汉族与其他国家或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范围和数量都在增加。据史籍记载,唐朝的正式和亲有23次,其中中唐前期有16次,此外,唐公主和宗室女也有嫁给在唐供职的少数民族将领的。参与和亲的唐朝公主包括高祖十九女中的七位,太宗二十一女中的八位,涉及的国家或少数民族政权包括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吐谷浑、奚等。
2、边塞型。和当代相同,唐国境内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的边境地区,由于与他国边境贸易或日常交往密切,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边塞型涉外婚姻。其最大的特点是涉外婚姻关系成立的自发性。结婚男女之间虽属不同国家,但语言、生活习惯等却极为相似。为了更好地管理边疆地区,唐政府在周边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设立羁縻州,依当地习俗而治,有别于一般州县,类似于现在的自治区,当然,羁縻州内并非都为少数民族。依据民族和睦的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甚至通婚现象相当普遍。据《旧唐书·王愕传》,在岭南地区“广人与夷人杂处”,据《新唐书·卢钧传》,同样在岭南地区“蕃撩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另据《唐定兴等户残卷》,在敦煌地区,胡汉通婚同样非常普遍,记载的12户中就有13对胡汉婚姻。所以,受当时民族和睦政策的鼓励,唐时边塞涉外婚姻大量存在,国家法律对此类涉外婚姻有宏观的指导,主要表现为禁止性规定(后文详细阐述),但婚姻具体事务的协调主要依据当地的习俗。
3、内地型。唐代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与周边少数民族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通过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等通道与遥远的域外各国保持着经济文化等交流,各国的使者、商人、僧侣云集于唐,“万国衣冠冕旒”“朝气氤氲”,且有众多外国人长期定居于此,与唐人结婚生子,存在着大量的内地型涉外婚。《资治通鉴》记载,“先是回绘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或衣华服,诱娶妻妾”,[12]“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12]除长安外,广州、洛阳、扬州等繁华城市,也生活着大量的外国人,他们依靠经营饮食业、珠宝业等,赚取了财富,与唐人生儿育女,组成了众多的混血家庭。唐代内地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这既包括在唐不同国家外国人的婚姻、同一国家外国人的婚姻以及他国人与唐人的婚姻,有的国家婚姻成立条件与形式还有特殊的风俗习惯或者宗教要求。
(二)重要特征
1、身份层级明显。唐时无论身份地位的高低,与外国人通婚皆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与从边疆地区而来的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婚姻成立的形式。上层的涉外婚姻多为与周边国家或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政治和亲或者宗室、大臣子女参与的政治型联姻,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下层的涉外婚姻多为与塞外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和来唐学习、经商的外国人的普通婚姻或者边塞婚姻。
2、涉外婚姻常态化。唐时外国人与唐人或者在唐外国人之间成立的婚姻数量难以考证,且由于当时对外国人统称为“胡”“夷”“蕃”等,普通的涉外婚姻所涉及的具体国家也难以确定,但可以从外国人在华工作生活等资料中推测出相关的信息。唐代时对外交往颇为活跃,与上一个大一统的秦汉时期相比,不仅陆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拓展,而且海上丝绸之路也快速发展,据《唐六典》卷4《尚书礼》记载,在盛唐时期,约有三百余个国家和唐交往,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的国家也有七十余国。唐无疑是公元7-9世纪东亚以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外国人前来学习、经商、生活,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处理涉外法律关系规范的朝代,即“化外人”制度。所以,基于唐代对外交往国家与来唐人口的巨大基数,我们足以推断出唐代涉外婚姻的数量之多与涉及的国家之广,涉外婚姻关系的成立已经步入常态化。
3、胡男汉女型较多。唐时受交通工具、自然环境以及他国风俗习惯的限制,来唐的外国人多为青壮年男性,部分留在唐朝的便与当地女性结为夫妻,所以才有了《资治通鉴》中的“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之说,而非“皆有丈夫和孩子”。来唐的外国女性相对较少,但绝非没有,李白在《杂曲歌词·少年行三首》中有“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其中的胡姬便是在唐外国女性,这些胡姬一般年轻貌美,若遇唐代风流少年,通婚自然不可避免,婚姻形式可能多种多样,这些胡姬就是唐代少数胡女汉男型婚姻的主要参与者。
三、唐代涉外婚姻制度的重点内容与关键特质
(一)唐代涉外婚姻制度的重点内容
1、“化外人”制度
《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其中,“化外人”是我国古代的法律术语,“化”即教化,所谓的“化外人”指中国的礼仪和法制所不能控制区域的人,即所谓的“外国人”,广义上的“化外人”应当包括与唐相对的其他主权国家的人和位于唐国内但当时的法律、礼仪制度不能直接适用的少数民族。《唐律疏议》中关于“化外人”的条款,是我国关于在华外国人适用法律的最早规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冲突规范。本条款是“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的结合,如果化外人是同类,则依据其属人法—“各依本俗法”;如果是异类,则适用唐的法律—“以法律论”。该冲突规范虽没有对涉外婚姻做直接的规定,但婚姻自主权作为人身权利的一种,根据“化外人”制度应当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理解为如果同一民族或者同一国家的“化外人”通婚,则按照他们本民族或者本国家的风俗和法律执行,具有法律适用的“属人性”;如果不是同一民族或同一国家的人结婚,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化外人之间通婚或者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化外人与唐人通婚,则按照“属地性”原则,适用唐的习惯和国内法。总之,依据“化外人”制度,在唐外国人的婚姻自主权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
著名的“化外人相犯”条的规定:“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向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多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本俗法”,表明唐朝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兼采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古代中国法制民刑合一,“化外人相犯”条也适用外国人在唐朝因婚姻关系产生的纠纷。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与唐朝不同,婚姻方面《隋书·西域志》记载着西域人“妻其姊妹”、“兄弟同妻”,这些西域的婚俗与唐朝的同姓不婚、伦理道德是相矛盾的。为了尽量避免矛盾的发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体现统治者的广阔胸怀,唐朝政府采取了尊重他国风俗习惯的宽容原则。[13]
2、“不得还蕃”制度
《唐律疏议》卷8卫禁篇“越度缘边关塞”条和《唐会要》卷100中都提到了一条规范:“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唐代直接关于涉外婚姻的法律规范。前文已提到“蕃”是唐时对外国人以及未归化的少数民族的统称之一,通过此条可以推断唐法律并不禁止本国女性出嫁于外国人,只是这些女性不能被带回蕃国罢了。所以,唐时外国人和本国人的婚姻权只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并未被剥夺,仍然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在以严格强调夷夏之辨甚至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是非常进步的。
《唐律疏议》卷8卫禁篇中的另一条款:“中国人不得越边塞与异族人通婚,违者,流二千里,婚姻未成,则减三等处罚”,与前述条款殊途同归。本条款指中国人无论男女不得越过边境与他国人通婚,是限制中国人的流失,本质上并未禁止与他国人通婚,与前述条款的立法目的是一致的。
唐朝政府在原则上对于异族通婚是禁止的,如与化外人“共为婚姻者,流两千里……未成者,减三等”。不过,唐朝政府对于异族通婚采取了默许的政策,《唐律疏议》规定“蕃人”可以“娶得汉妇女为妻妾”,这说明唐朝允许在华的外国人与唐朝的女子通婚,这有利于外来人员稳定地留在唐朝,从而促进唐文化的繁荣。但又有限制性的规定“不得将还蕃内”,即不得将所娶的妻妾带回其本国,“若将还蕃内,以违敕科之”。这样规定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唐人将其所知的国家情报泄露给外国人,另一方面也防止唐朝人口流失,保证国内人口的增长。
3、“不得私与为婚”制度
《唐律疏议》卷8卫禁篇规定“国内官人、百姓不得私与入朝蕃客为婚”,本条是指唐无论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私自与来唐的蕃客通婚。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蕃客”的特殊身份,这些人往往带着一定的政治使命而来,或敌或友,都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所以对这些群体做了特别限制;其二是不得“私”与为婚,即未经一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通婚,也许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本条并未绝对禁止蕃客与唐人通婚,而且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婚姻成立重要条件的唐代,此条款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朝的涉外婚姻是在官府的干涉下进行的,蕃汉通婚的实现要得到官府的许可,不允许他们“私作婚姻”。据《册府元龟》“互市”云:“开成元年六月……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又举取蕃客钱,以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14]官府控制蕃汉通婚一是有利于保护唐人的权利,二是防止通婚使得后代人种变异,危及唐朝的正统血统。
(二)唐代涉外婚姻制度的关键特质
1、标榜了夷夏平等的观念
周时,已经有纳“夷狄”之女为妻的事例:“是以周纳狄后,富辰谓之祸阶,晋升戎女,卜人以为不吉”,[15]表明先秦时期与外国人通婚是祸端,是不吉利的,此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是比较低的。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尤为强调夷夏之辨,其影响之大从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可见一斑。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渗入我国法制的骨髓,我国封建时代法制又有“外儒内法”之说。而唐却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它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归化的北方少数民族影响较大,且李唐皇室本身就有少数民族血统,此时的夷夏观念开始淡化,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自古以来,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若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12]结合“化外人”制度,唐代无论从政策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主张夷夏平等的,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婚姻领域,所以唐代的涉外婚姻才会出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和亲之多,甚于前朝,胡汉通婚,蔚然成风。
2、注重于当时的农耕经济
唐代仍是典型的小农社会,采取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虽然曲辕犁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出现,但劳动力仍是最大的农业成本。无论“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还是“中国人不得越边塞与异族人通婚”,其目的皆是为了防止人口或者潜在人口的流失,从而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流失。所以,唐代的婚姻政策还是服务于小农经济的,属于农业经济的产物。
3、服务于唐政权的管控安全
《唐律疏议》关于涉外婚姻制度的相关规范体现了抑制人口流失、提高军事实力的思想,此外,仅有的三条规定,即“中国人不得越边塞与异族人通婚”、“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和“国内官人、百姓不得私与入朝蕃客为婚”皆规定在调整国防安全的卫禁篇,而非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户婚篇。所以,从立法目的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将涉外婚姻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与其说立法者关注的是涉外婚姻关系的成立,倒不如说更关注涉外婚姻关系成立的后果。
4、体现了政权管控及律令制定与实施的极度相关性
唐朝后期,由于政府没有制定专门的涉外婚姻法律,而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又是复杂多样的,“化外人”制度已不能独立解决相关问题。某些地方官员为了维护本辖区的社会稳定,制定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涉外婚姻政策与制度。一些沿边地区政府为减少涉外争讼,下令禁止胡汉通婚,如《新唐书》卷182《卢钧传》记载,卢钧任岭南节度使时,“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地舍,吏或扰之,则相挺为乱。钧下令蕃华不通婚,禁名田产,阖部肃一无敢犯。”虽然短期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实质上却是唐后期政权衰落导致的法制退步的一种表现。
四、唐代涉外婚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直接因素
1、人口因素。我国封建时代以农耕经济为主,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唐时筒车和曲辕犁出现,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但人仍然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同时经过战乱,唐初人口稀少,政府比较注重人口数量的增加。涉外婚姻制度的设计首先防止了劳动力或者潜在的劳动力外流,使农业生产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同时也鼓励涉外通婚和生育,提高人口的增长率。唐代的发展,经历了从隋朝的废墟上重建,一路向上直至唐玄宗时候达到顶峰,又经安史之乱逐渐衰落的过程。唐代人口的变化,与整个唐代的发展基本保持一致,也有一个由少至多又衰减的曲线,呈现出马鞍形。
2、税收因素。唐初处于战后的恢复期,百废待兴,经济低迷,国家的赋税收入较低,农业能缴纳的赋税有限,商业也是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涉外婚姻法律的制定要同等地保护在唐外国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既要高效地解决纠纷,也使外国商人安心开展商业活动,从而提高了唐政府的赋税收入。
3、军事因素。在冷兵器时代的唐,人不仅是经济上的生产力,更是军事上的战斗力。经过连年战乱,唐初人口明显减少,抑制人口流失对于农业经济具有重要性的同时,同样,人作为军事上的主要战斗主体更不能流失,否则会对唐政权形成潜在的安全威胁。因此,唐政权在允许涉外通婚的同时也规定了一定的禁止和限制条件,以保证国家安全。
4、外交因素。和亲由于其目的的特殊性,不受一般国内法律的调整,但其与政治的联系最为密切。当各国间需要互相拉拢关系、安抚对方、寻求和平时,和亲会相应变得频繁;当政治目的不能实现之时,和亲的意义同时也就丧失,和亲的数量自然就会减少。
(二)间接因素
1、李唐皇室血脉因素。“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事实证明,在世界历史上,一国统治者的性格、气质、生活背景等会极大的影响国家管控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唐在这点体现尤为明显。李唐皇族是带有明显“胡化”基因的统治者,正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16]是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结果。鲁迅也曾有言:“唐室大有胡气。”[17]李唐皇族体内充满了北方原少数民族的血液,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匈奴人,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是鲜卑人,也就是说李渊有二分之一的汉族血统,李世民只有四分之一的汉族血统,李治则仅有八分之一的汉族血统,唐代的其他皇帝、皇子、公主等出自胡母者更是大量存在。皇室血缘上“胡”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代的政策和制度。同时,唐之前王朝隋直接继承于北周的鲜卑族政权,更是充满“胡气”,因此唐政权对待婚姻、对待外民族实施开明和开放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也许正是李唐皇族自身的胡人血统,才使太宗皇帝语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进而在政策的制定上坚持“夷夏平等”,保护在唐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化外人”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2、社会文化教化因素。唐代涉外婚姻制度的各种影响因素其实是相互联系的,最终作用于社会,会对普通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进而形成涉外婚姻关系成立的群众基础。首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唐代的汉族其实是以汉族为父系,以鲜卑等族为母系的新汉族,胡人开放、不重礼法的性格对该时期的汉人影响较大,普通群众不介意与归化的少数民族通婚,也不介意与来自更远的地方甚至长相有明显差异的外国人结婚,此为唐代涉外婚姻大量存在的群众基础;其次,历经战乱动荡,李唐皇室深知调整好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既然皇帝不分夷夏“独爱如一”,百姓参与涉外婚姻也就更无后顾之忧;而且,随着唐代的对外开放与快速发展,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习俗等信息在唐广泛传播,与汉族文明相互交融,使民众的视野更加开阔,民众对待涉外婚姻自然持积极态度;最后,唐代社会存在大量的外国人,禁止其与汉人通婚不仅会产生社会隐患,而且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所说:“唐代异族入处内地者甚多,安能禁其婚娶,此势所不行也。”[18]
五、唐代涉外婚姻制度的简单评价
唐代的涉外婚姻制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自身的积极性和局限性。
(一)积极性
1、立法理念开放。坚持开明的的民族政策,坚持夷夏平等。唐代的涉外婚姻制度保障了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平等的婚姻权利,打破了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在十分强调“夷夏之辨”的传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在立法和法律实践上确为巨大的进步。魏晋南北朝之时,婚姻十分重视门当户对,盛行所谓门第婚,在这一婚姻制度下,士族与庶族之间是绝对不允许通婚的。及至唐朝,此种风俗仍有很大影响,“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19]世家大族甚至仍然坚持“男女婚嫁,不杂他姓”,[20]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述:“自隋唐而上……家有谱系……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21]
2、注重保障人权。通过法律保障人权,维护婚姻选择自主权。涉外婚姻权利作为一种与人身密切相关的权利,其得到保障不仅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还有利于安抚普通群众,保障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关注国家安全。以发展的眼光制定法律,将涉外婚姻政策纳入国家经济和军事发展的长期规划之中。唐代的涉外婚姻制度,既可以有效地防止人口外流,还可以增加新生人口的数量,进而促进生产力和军事实力的提升,维护国家安全。
4、重视制度创新。唐代的涉外婚姻制度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从人员和血统上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着人们对其他民族的看法,而且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文化,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另外,政治和亲能有效地起到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为国家的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局限性
1、立法技术不成熟。如“化外人”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未区分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也未区分民事关系与刑事关系,而是根据法律关系主体的国籍直接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以致法律的适用性降低。冲突规范的连接点应该是多样的,如国籍、住所地、物之所在地、行为地、最密切联系地等。
2、法律规范修正不及时。涉外婚姻制度没有与社会同步发展,随着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综合国力的提升,《唐律疏议》关于涉外婚姻仅有的三个条款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需要更为完善具体的法律制度。
3、法律政策执行不到位。安史之乱后,唐代地方政权壮大,藩镇林立,地方政府在贯彻法律方面存在懈怠之心,有的为了一时的安宁而禁止涉外婚姻,从长远来看,消极作用是大于积极作用的。
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孕育不同的法律制度,总的来说,唐代的涉外婚姻制度体现了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在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不能以现代苛刻的标准去要求当时的立法者,但应当看到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以史为镜。
六、唐代涉外婚姻制度的当代启示
唐代的法律制度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对涉外婚姻制度的规范虽然较少,但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国现在的的状态和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我国当代涉外法律尤其是涉外婚姻法律的完善可以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适应开放潮流,做好应对问题的准备。当今中国存在着大量的涉外婚姻,《法律适用法》调整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相对比较完善,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涉外婚姻的数量会持续增长,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大量涉外婚姻纠纷的准备,继续完善相关法律,保障人权,平等地尊重和保护涉外婚姻当事人的婚姻权利。
其次,完善法律解释,树立创新思维,灵活执行法律。涉外婚姻的立法要正确处理法律与宗教、法律与习惯的关系,尊重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此举不仅能体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包容的态度,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需要。如《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二条“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这里的“结婚手续”便不能单纯理解为在国家机关办理的登记手续,应当扩大解释为“结婚的形式”,因为某些国家只需要举行宗教婚礼不需要办理专门手续即可成立婚姻。
最后,制定立法规划,坚持发展眼光,始终维护国家利益。涉外婚姻制度不能同国家利益相冲突,我们要坚持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要处理好涉外婚姻制度规范的范围,既要保证涉外婚姻的成立和解除有法可依,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其选择婚姻成立或解除的形式和程序,更要坚守国家的安全底线,维护我国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随着国家的崛起,我们的涉外法律制度在探索中不断前行。外国人已不再是蛮夷,也不是鬼子,而是互利共赢的伙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外国人在中国的婚姻关系方面的法律权益也将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
[1]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付永聚.唐代的涉外婚姻[J].人文杂志,1994,(3):97,99.
[3] 姜晓强.唐代婚姻制度及婚姻类型探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8.
[4] 张嫣娟.唐代婚姻制度的践行与妇女社会地位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2.
[5] 高树异.唐宋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J].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z1):138-146.
[6] 吴美菊,黎嫦娟.唐代涉外事件处理的法律原则[J].兰台世界,2014,(35):99-100.
[7] 郑显文.唐代涉外民事法律初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4-29.
[8] 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J].社会科学战线,1993,(1):190-193.
[9] 管辉.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
[10] 张伯晋.唐代婚姻法制与婚俗矛盾关系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11] 费超.唐代婚姻制度与礼俗的时代特色[D].烟台:烟台大学,2013.
[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 周宁.唐朝涉外法律制度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14]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5] (唐)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6] 黎靖德,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 鲁迅.鲁迅书信集(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8]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9]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1] (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OntheInternationalMarriageSysteminTangDynasty
Cui Caixian1Fu Changhui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2. Law School,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increased, and the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complicated.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marriage and family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branch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e most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law applicable to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Wit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digs in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riage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explores its basic theory, analyzes its basic content and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evaluates its positives and limitations, and summarizes the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times, and forms useful experien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provisions in law applicable to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Tang Dynasty; international marriage; foreigner system
周延云
2017-01-22
崔彩贤(1971- ),女,陕西合阳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法学、社会学研究。
D913.9
A
1672-335X(2017)06-00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