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灾害应对实效性再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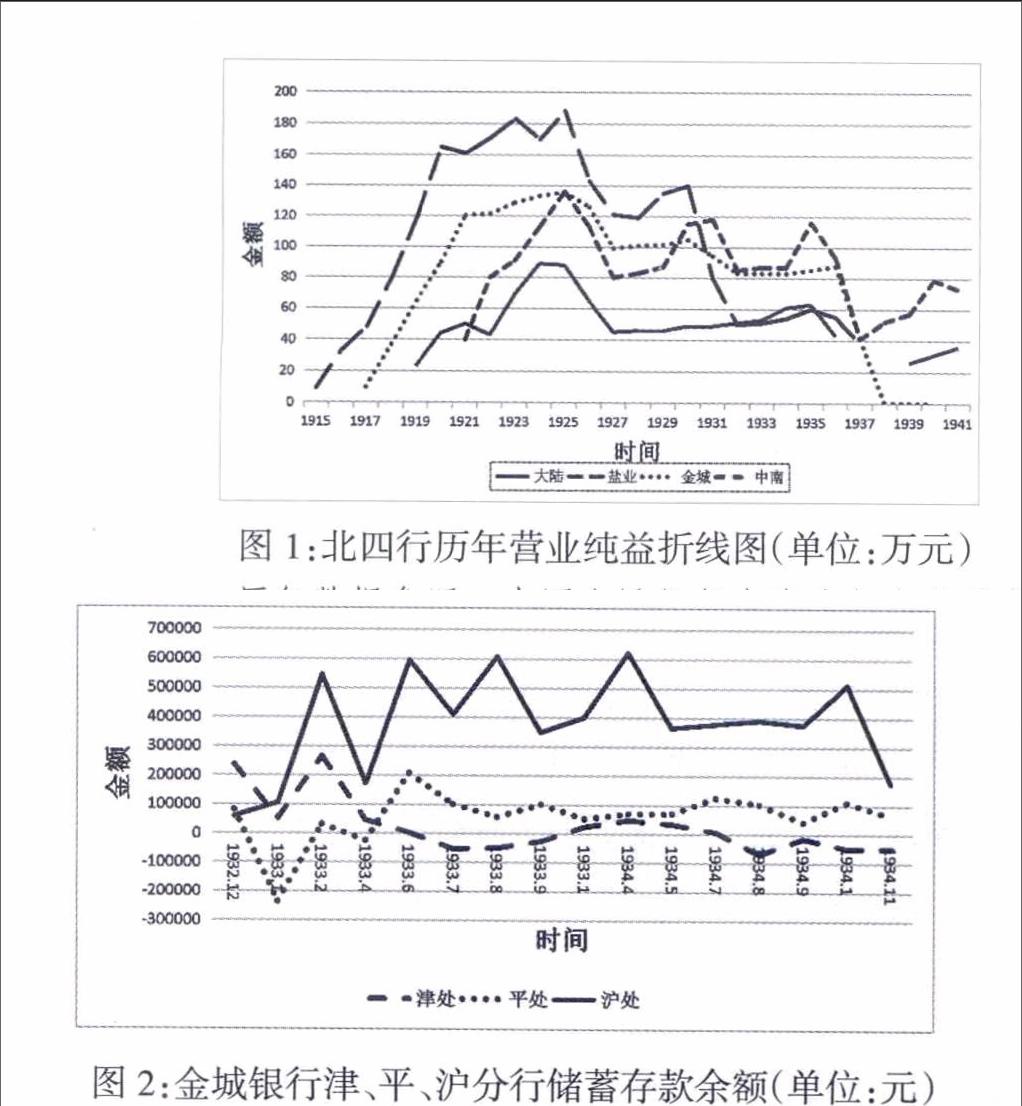
摘 要?演唐朝前期,唐中央在灾害应对的实效性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加之将繁冗复杂的救助制度纳入唐的日常政务系统,由此导致了救助时效的滞后与拖延,使得赈济效果受到影响,但这种中央政务的拖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社会自我救助力量的增长。再加上有关唐前期灾害赈济的文献呈现出以虚代实的特点,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两者间的巨大反差,影响了我们对于唐前期灾害应对实效性的判断。
关键词?演唐前期,灾害应对,日常政务,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演K24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22-0023-07
古代社会的灾害应对一直是影响王朝政务走向的关键,在唐代荒政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上,①前辈学者多在应灾的整体效果、不同灾害的应对方案与各区域的应灾方法等方面展开研究,②其中,对记载灾害的文献的静态勾描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在灾害应对实效性环节的考察问题上较为薄弱,③由此忽略了受灾民众的施救效果与被救程度及影响灾害应对实效的诸多因素等。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安史之乱前的唐代中央赈灾政令为中心,以灾害应对的实效性为切入点,聚焦唐前期灾害应对的制度规定层面与实际运行情况之间的差异,并分析灾害文献的构成特点与赈济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剖析灾害应对在唐代政务运行系统中的独特模式,以求教于方家。
唐前期,唐廷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灾害应对奏报制度,并在实际的政务运行上呈现出较为繁复的过程。依据《唐律疏议》载:
其应损免者,皆主司合言。主司谓里正以上。里正需言于县,县申州,州申省,多者奏闻。④
再者,北宋《天圣令》中保留了唐代的《赋役令》:
诸田有水旱虫霜为灾处,据见营田,州县检实,具帐申省。①
综合上述两段文献,我们可以探知唐代实行的是基层政权单位逐级上报灾情的政务运行方式。首先,由主管乡里的官员“里正”向县一级政权单位汇报,县级官员进行“州县审核”,即对“里正”上报的行政文书进行检查核对。然后,县申州,州申省,行政层级逐步递增至中央政府。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地方的政令文书渐次达到唐廷中央。如高宗总章二年(669年):
冀州大都督府奏,自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以上,坏屋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区,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②
咸亨四年(673年)九月:
婺州暴雨,山水泛涨,溺死者五千人,漂损居宅六百家,诏令赈之。③
高宗总章二年,冀州灾情汇报到唐中央,经过了州县检实、逐级上报的过程,文献保留“冀州大都督奏”则显示“州申省”的运行过程。都督一般兼任治所州刺史,④这是一则典型的以州刺史为代表的地方长吏上报唐廷其所治州县受灾状况的具体实例。《唐会要》载:
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⑤
作为纳入国史文本的地方灾情史料,上级行政单位的逐层审核可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高宗时代两次重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在传世文献中得以记载,而这些具体数据也折射出地方政务运行的成果。
尽管唐前期灾情的申报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州县检实”与“具帐申省”两项程序与其他地方事务申报别无二致,由此可知灾害应对被统治阶层看作一种普通的政务问题。在灾害发生后,地方官员的第一要务是统计灾害程度与受灾人数,然后再依据相关程序制定具体的赈灾措施,这种固定化的处理是以牺牲时间为代价换取应对本身的合理性,便暴露了时效性的问题。据《新唐书》载,上元三年(676年)八月,“青州大风,海溢,漂居人五千余家;齐、淄等七州大水”。⑥而青州“至上都二千四百五里”,⑦如若按照“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⑧的普通行程计算,即使长途奔袭,昼夜不息,由青州至京都,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自然灾害的紧迫性,要求信息传递的速度是越快越好。在唐代初年,便设有专门应对紧急事务的“飞驿”。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辽东,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并许之(发表奏事,自兹始也)”。⑨这种由飞驿传递的文书一般都是涉及军事情报的紧急政令,但重大的灾情奏报是否也被纳入其中,从现存史籍中尚难见到明确记载。韩愈在《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中有“街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之语。⑩当然,“日驰三百”要比“马日七十里”快速得多,但韩愈所处的是河北藩镇叛乱之际,虽不能由此草率地判定唐代的文书传递速度可以达到“日驰三百”,但这种紧急情况下的公文传递速度仍可以为灾害救助公文的传达提供一参考标准,毕竟二者都具有紧急性和特殊性。不仅如此,唐代的赦令文书的传递同样具有特殊性,根据规定,可以“赦书日行五百里”。?輥?輯?訛比较赦书与灾情上奏文书的性质,笔者暂且折中推测自然灾害这一紧急状况下,唐代的灾情奏报的传递速度以每天三百里为一大致标准,而不以日常文书“马日行七十里”为依据,那么,从青州到长安最快为八天时间。由此可见,申报的过程消耗了一周多的时间,加之从中央接到灾情奏报到最终采取救灾措施,这一制度层面的程序规定又加剧了时间的消耗,送往迎来,时间乘倍。而灾害还在不断蔓延,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恶劣影响,如农作物生长受挫、粮食短缺、瘟疫疾病等,不断地威胁着地方社会的稳定与民众的生产生活。
从上述文书的灾情奏报程序来看,唐廷对地方社会实行的是高度控制,并未因灾害的特殊性而采取新的应对举措,由此导致了政务运行的时效性存在较大问题。当我们把视角指向“国家”层面时,唐廷面对地方的灾情申报又是如何决断与应对的呢?史载,永泰二年(766年)四月十五日制称:
周有六卿,分掌国柄,各率其属,以宣王化。今之尚书省,即六官之位也……其尚书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请。勅到省,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详定闻奏,然后施行。①
地方的行政文书先申至尚书省,经尚书省六部中的某司为某事申奏“上”于门下省,经过门下省读、省、审,再上报皇帝,最后行下执行。②唐前期整个政务系统处于完整的律令体系支配下,有其时间限制与法律依据:
凡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之程限:一日受,二日报。(其事速及送囚徒,随至即付。)小事五日,(谓不需检覆者。)中事十日,(谓须检覆前案及有所勘问者)……小事判勾经三人已下者给一日,四人已上给二日……内外诸司咸率此。③
这种对上奏时间的规定可以提高政务应对的时效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务运行的整体效率,而对于重大自然灾害,又增加了一个步骤,即“中事十日(谓须检覆前案及有所勘问者)”,通常由皇帝派大臣进行覆检。例如,唐太宗贞观元年七月:
关东、河南、陇右及缘边诸州,霜害秋稼。九月辛酉,诏曰:“……可命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征等,分往诸州驰驿,捡行其苗稼不熟之处,使知损耗多少户口,乏粮之家存问。若为之计,必当细勘,速以奏闻!待使人还京,量行赈济”。④
通过这段史料,可探知以下问题。
首先,时间截点问题。七月发生灾害,九月才颁布应对政令。在这场霜害中,唐廷并未因灾害的特殊性而迅速应对。上文所引的制度规定“其事速及送囚徒,随至即付”,其对时效性的要求无法在相隔两个月后的诏书中得以体现。
其次,前揭文献的最后,“若为之计,必当细勘,速以奏闻!待使人还京,量行赈济”,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唐廷对灾情应对规定的统一运行程序,即不管灾害的地域范围与损害程度,中央均要派遣使臣检覆具体的受灾实态,等到这些情况上报到中央后,最后商议赈贷、蠲免、赈济等一系列救助措施。又如贞观二十二年正月:
诏建州去秋蝗,以义仓赈贷。二月诏泉州去秋蝗及海水泛滥,开义仓赈贷。⑤
建州去年秋天遭蝗灾,而中央颁布了赈贷诏令却是来年正月,可见时间性方面严重滞后,受灾民众根本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又如永徽元年(650年),“夔、绛、雍、同等州蝗”。⑥而唐中央颁布救灾诏令却是第二年:
二年春正月戊戌,诏曰:“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己,载深忧惕。今献岁肇春,东作方始,粮廪或空,事资赈给。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存问,务尽哀矜之旨,副朕乃眷之心。⑦
唐高宗在诏令中使用了许多关心民众疾苦的话语,极力要塑造仁君形象。而他赈济的是去年受蝗灾民,其标榜的帝王形象与真正给予受灾民众的实际救助很难契合。诏令文书程式化的背后到底是采取了应有的应对举措还是延迟赈济,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不应被简单的文字表述所遮蔽。
总之,唐前期中央应对地方自然灾害所的救助过程需要一个复杂的程序,这一繁琐制度由州县审核、具帐申省和中央讨论、诏书颁布组成,充分体现出唐廷政务运行系统的完整性。由于统计资料、逐级申报与检覆前案等繁杂程序在救助申报中消耗了大量时间,且并未在短时段内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这种程序性的繁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灾害救助的行为,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灾后重建与救助的困难。
唐前期,唐廷在灾情应对上实行与普通政务相同的处理程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灾害应对时效性的发挥。无论是等待中央的赈济诏令还是中央派遣的使节救灾,均不是灾害救助最佳的时效性表现。
在自然灾害这一特殊环境下,需要的是快速、高效的处理方法和措施。因此,地方社会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与便捷,他们打破了传统政务运行的繁杂程序,对灾后百姓进行了较为及时的救助。高宗上元初,员半千为武陟尉“时属旱歉,劝县令开仓赈恤贫馁,县令不从。俄县令上府,半千悉发仓粟,以给百姓”。①《新唐书·李皋传》记录了李皋擅自开仓赈济的事例:
上元初旱歉,皋禄不足养,请补外,不许,乃故抵轻法,贬温州长史,俄摄州事。州大饥,发官廪数十万石赈饿者,僚史叩庭请先以闻,皋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可俟命后发哉?苟杀我而活众,其利大矣!”既贷,乃自劾,优诏开许,就进少府监。②
《新唐书·韩思复传》亦载:
思复调梁府仓曹参军,会大旱,辄开仓赈民。州苛责,对曰:“人穷则滥,不如因而活之,无趣为盗贼。”州不能诎。③
玄宗开元年间,《张之辅墓志》记载其在沧州任上:
属濒海水灾,连□(注:原文缺)粟贵。人负子,舟乘城。公以奏报历时,幼艾蒙袂。请以一身之罪,庶解万人之悬,乃开仓救之。④
《全唐文》则保留了开元年间齐州刺史裴耀卿在任上修筑河堤的事迹:
河堤坏决,诸郡有闻,皆俟诏到,莫敢兴役,害既滋甚,功无已时。公以为执事诿上者,非至公之法也;便文自营者,非尽忠之计也。亦既成奏,因而发卒,播告厥指,率吁于人。荷锸者襁属,负畚者靡至,从公于迈,祁祁如云。公俯临决河,躬自护作,雨不张盖,尘不振衣,馈不致鲜,寝不处馆,蔬食以同其烹饪,野次以同其燥湿。板筑竞劝,鼛鼓弗胜,克巩而成,匪亟而速。以浃辰之役,兴百倍之利,澹灾革弊,人到于今赖焉。⑤
综合上述文献,以员半千、李皋、韩思复、张之辅和裴耀卿为代表的地方长吏并没有按照唐廷确立的应对秩序进行灾害救助,而是在治所直接开展赈济活动,这一行为使得整个救灾程式发生转变,地方的政务运行与中央王朝的制度规定出现了不一致的状况。不言而喻,中央政府的赈济政令抵达地方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严重,在律令体系完整健全的唐代社会中,地方长吏断然不敢违抗中央政府的规定。
地方上的因时自救显示出一定的时效性,这为过于严密的灾害应对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运行模式历经唐前期几代帝王,最终在玄宗朝得以改造,其实质也是对以往灾害应对制度的否定。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诏令:
以检校尚书右丞相皇甫翼充河南淮南道宣慰使、检校尚书吏部侍郎刘彤充江东江西道宣慰使、尚书兵部侍郎李镇充山南道宣慰使。制曰:去年江南淮南有微遭旱处,河南数州亦有水损百姓等,皇甫翼等咸谓能贤,式将朕命,其间乏绝应须赈贷,便量事处置,回日奏闻。⑥
开元二十二年又颁布了诏令:
晋州地震,谪见后土。朕每克念,何以甄兹。仲尼云:“某祷久矣”,而精意以告,或道神明。徐国公萧嵩,地在辅弼,朝之端右,欲重将命,暂为此行。宜往秦州,致祭山川,凡缘所损百姓间事,皆委嵩随事处置。⑦
从玄宗时期的“便量事处置,回日奏闻”与“皆委嵩随事处置”,比之太宗时期“必当细勘,速以奏闻!待使人还京,量行赈济”的政令方式来看,唐朝的灾害救助方式已发生了变化,虽仍采取奏报的方式,但在应对处理上具有了较大的灵活性。在实际执行中的具体方式与制度上的灾害应对之间出现了变化,从最初的高度控制到委派使臣“量事赈济”,取消了使臣再报中央请求赈济这一环节,提高了一定的时效,加快了灾后救助的步伐。最终,在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诏令:
承前有遭损之州,皆待奏报,然始赈给。近年亦分命使臣与州县相知处置,尚虑道路悠远, 往复淹滞,以此恤人,何救悬绝?自今以后,若有损处,应须赈给,宜令州县长官与采访使勘会,量事给讫奏闻。朕当重遣使臣宣慰、按覆。①
自此,唐朝形成了州县长吏与使臣派遣共同应对灾情的处理方式。
综而述之,唐代灾害救助方式经历了以京官充任地方宣慰使量事处置,到命京官随事处置,再到颁布诏令由地方州县长官与采访使商议后量事赈济的过程,反映了唐权力不断下放、逐步制度化的发展态势。由“尚虑道路悠远,往复淹滞,以此恤人”到“州县长官与采访使勘会,量事给讫奏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央王朝与地方力量之间的微妙变化趋势,反映了州县地方的自主权力的增长。
在唐前期,灾害赈济的方式颇多,诸如“赈贷”“蠲免赋税”“调粟济民”“物资赈济”等等,又有义仓、常平仓等专门的赈灾机构的设立。在传世文献中,更是保留了大量有关唐朝的赈济文书。留给笔者的疑问是,唐前期制定的救助地方灾情的各项政策与措施是否能够在具体的实际救助中取得较好的效果呢?②赈济文书能否得到切实的执行?受灾民众凭借朝廷的力量能否从灾难中尽快回归至正常的生产生活?
首先,唐朝前期的主要赈济机构是义仓,诸如“赈给”“赈贷”等都是由义仓承担物资供给。《唐六典》载:
凡义仓之粟唯荒年给粮,不得杂用。若有不熟之处,随须给贷及种子,皆申尚书省奏闻。③
据前辈学人统计,该机构有67次的赈济记录。④那么,这些文献记载的背后是真实的救灾景象,还是虚实结合的叙述范式?
神龙元年(705年)六月,河南、河北十七州大水,中央“遣中郎一人巡行赈给”。神龙二年六月,又“遣使赈贷河北遭水之家”。同年十二月,“以河北诸州遭水,人多阻饥,令侍中苏瓌存抚赈给”。⑤唐廷应对此次河南、河北大水的举措为“赈给”,即“遣使巡行赈给”。但对“赈给”的总数额、每户灾民可领取的数额、赈济的过程与具体措施,等等,均没有记录在案。然而,唐廷一次次的遣使赈济其结果依然是“人多阻饥”。从最终结果来看,赈济效果是不理想的。接着,我们再分析一则有明确赈济数据的史料。开元十五年八月制曰:
河北州县,水灾尤甚,言念蒸人,何以自给。朕当宁兴想,有劳旰昃,在予之责,用轸于怀。宜令所司量支东都租米二十万石赈给。十二月,以河北饥甚,转江淮租米百万余石赈给之。⑥
这份制书详细保留了唐廷赈济河北州县的米石数。如按河北道全部州县受灾算,受灾人数大概在三十余万众,⑦一户约六口,每口可以获得0.6石米,每户可获3.6石米,按照唐代成丁一日二升的标准,⑧推算六口之家至少应有三个成丁,其他三人所食租米折合1.5个成丁的标准,将上述数据进行推演可知,唐廷赈济的二十万石粮食最多可以维持河北受灾民众两个月的生计,持续到十月份。然而从十月到十二月这个相对短时段中,河北的水灾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出现了“十二月以河北饥甚,转江淮租米百万余石赈给之”的状况。两月之间,唐中央政府可能没有采取新的救灾措施,二十万石租米难以帮助受灾百姓度过四个月的危难期,也同时证明了河北水灾所造成的潜在影响很难使百姓尽快恢复生产与生活,才会出现“河北饥甚”的恶劣情景。
再者,除义仓赈济外,还有“移民就粟”的救助举措。唐初规定:“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①由此州去彼州还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到他州就食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人员死亡、救助不及时等诸多情况,是否会由迁移而衍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问题。唐高宗总章二年七月,“剑南益、泸、嶲、陵、邛、雅、绵、翼、维、始、简、资、荣、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大旱,百姓乏绝,总三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户,遣司珍大夫路励行存问赈贷,许其往荆、襄州就谷,九月括州暴雨大风,海水泛涨,溢坏永嘉、安固二县城郭及庐舍六千余家,漂溺人畜遣使赈给”。②剑南十九州发生旱灾后,唐廷一方面派司珍大夫路励行存问、放贷,另一方面,“许其往荆、襄等州就谷”。③在安土重迁的古代人民心中,遇灾流离他处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中央有财力支持而救济有方、民众尚能存活的话,普通百姓一般是不愿抛家弃产、转徙他乡的。又如唐高宗咸亨元年,“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④江南租米成为关中旱灾的主要依托,要横跨南北来调粮赈济,这种远路途、大规模的调运行动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由此必然会影响救灾的及时性,影响灾后应对的实效性。同时也从另一侧面显示出唐朝的义仓、常平仓等救灾机构的形式化。因此,在自然灾害面前,中央的实际赈济是很难及时、高效的使受灾民众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政令文书的程式化表达与对民众的实效性赈济难以相互契合。
应对灾害的措施除“赈济”与“移民就粟”外,还有“蠲免”。唐代有完整的因灾蠲免令文:
诸田有水旱虫霜为灾处,据见营田州县检实,具帐申省,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分已上免租调,七已上课役具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折来年,经两年后,不在折限。其应免者,通计麦田为分数。⑤
如开元五年二月,河南、河北受灾,诏:“河南、河北遭涝及蝗虫,无出今年租。”⑥随后五月,再次发布诏令:
河南、河北去年不熟,今春亢旱,全无麦苗。虽令赈给,未能周赡,所在饥弊,特异非常。……其有不收麦处,更量赈恤。⑦
“蠲免”与“赈恤”是唐廷应对河南、河北灾害的重要举措。从诏令中可知此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否则也不会全部免租,并给予赈济。但是,从实效性层面来看,这些赈济救助举措的效果似乎并不十分有效,就连唐中央政府都承认“虽令赈济,未能周赡”。而此时的唐代社会是处于开元盛世的上升期,中央权力相对集中,国力是较为雄厚的,但对地方的赈灾救助仍然是“未能周赡”,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政务的程序性报送所造成的时间延误,还是实际的赈灾举措不得力?这些是无法从简略的文字史料中找到答案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何种原因,均是与唐朝中央的行政应对息息相关。面对大规模和连续性的灾害,只有合理的灾害应对制度及有效运行,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实效性,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有关唐前期灾害赈济的史料繁多,但无法从“开仓赈济”的字面表达去判断与衡量当时的实际救助情况与救助效果,这种格式化的政令文书也很难判定救助效果的好坏,但透过这些简略的文字史料,还是能从某些细节处窥探灾后救助的具体情况。如天宝十二载(753年)正月,“河东及河淮间诸郡去载微有涝损,已令给粮;每道各令御史一人往宣抚,应有不支持者,与所繇计会,随事赈给,如当郡无食及不充,听取比郡者分付,务令胜致,以副朕怀”。⑧从此段文献可知,天宝十一年涝损,十二年时唐廷仍要派御史进行“宣抚”,文本本身的意义或许能更加彰显统治阶层的“仁政”行为,但反向思考却折射出赈济的实际效果问题,很可能是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救助,下句“如当郡无食及不充,听取比郡者分付”便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唐帝国对灾害救助实效性的隐忧,假使当地仓廪充裕,为何还要调取它郡分付?由此可见,唐廷还是无法及时高效地解决灾害救助期间的粮食问题。
另外,“弥灾”也是灾后应对的一种方式,以期从精神层面来安抚民众。这种“弥灾”通常是由皇帝以“减膳食”“避正殿”的方式来进行。如乾封二年(667年),“正月丁丑,以去冬至于是月无雨雪,避正殿,减膳,亲录囚徒”。①又如玄宗开元三年五月戊申,遇旱灾,诏曰:
司牧生人,爱之如子,眷兹灾旱,倍切忧勤。将理政不明邪?冤囚有滞邪?疠疵道长邪?阴阳气隔邪?何崇朝密云,布未洽也?载加寅畏,弗敢荒宁,诚不动天,叹深罪己。思从避减,以塞愆尤,俾月离有期,星退何远。朕今避正殿,减常膳,仍令诸司长官,各言时政得失,以辅朕之不逮。天下见禁囚徒中,或以痛自诬者,各令长官,审加详覆。疑有冤滥,随事案理。仍告于社稷,备展诚祈。诸州旱处,有山川能兴云致雨者,亦委州县官长,速加祷祀。②
“弥灾”是历代帝王应对灾害的必备措施,对于唐代的统治者也并不特殊,但“弥灾”基本是从精神上来安抚民众,很难对实际的赈济效用有所裨益。首先,“因灾虑囚”与“避正殿”对于古代帝王而言,是带有很浓厚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因素,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力的稳定,应对灾害最根本目的仍是维护王权自身的合法性。其次,帝王的“减膳”并不意味着统治阶层减少了对普通民众的搜刮,即使皇帝“减膳”,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救济灾民,对于大范围受灾状况来说,也无异于杯水车薪,依然无法改变受灾民众的实际生存状态。
总之,唐前期在灾害应对上虽有“赈济”“蠲免”“移民就粟”与“弥灾”等多种举措,但无论是何种应对措施,在史料中均采用了较为模糊的表述,可以说这种表述成为了唐前期中央官方灾害应对政令文书的主体表达范式,呈现出以虚代实的记载特点。虽然我们不能以文献记载的缺环来草率地认为赈济效果不佳,但一些文献的细节中还是能透视出某些救灾情境与效果,可看出唐前期的灾害救助是不及时、不全面的,故而我们对唐前期灾害应对的实效性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加之在行政程序上将灾害应对作为一般性政务来处理,实行繁冗复杂的救助程序,未能注重灾情的紧急性和及时性,错失了最佳救治时间,最终影响了灾害救助的实际效果。尽管在唐玄宗时期对这种处理程序做出了调整与突破,给予地方上便宜行事之权,甚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力量的增长,但从文献记载的细节来看,其救助效果是不理想的。尽管文献记载采取了以虚代实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两者间的巨大反差,影响了我们对于唐前期灾害应对实效性的判断,但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们仍窥探到一丝真实。
【作者简介】 李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历史教学·高校版2016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