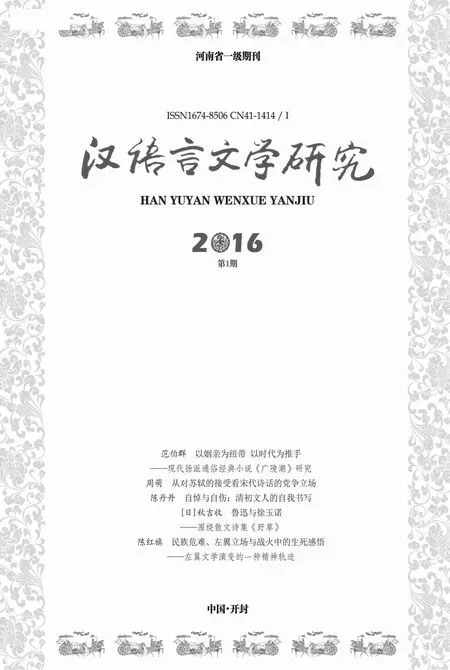莫泊桑《项链》中的反讽与悲观主义*
孙彩霞
莫泊桑《项链》中的反讽与悲观主义*
孙彩霞
摘要:在短篇名作《项链》中,围绕玛蒂尔德的“梦想-实现-突转-发现”,莫泊桑安排了三次对比,并形成两个典型的反讽情境。这样的精心安排使得《项链》成为深刻的反讽文本,并最终指向贵族留给世人的美丽幻梦和人类形而上意义上的荒诞困境,也隐含着莫泊桑对贵族家世的无奈怀想和对人类生活的悲观认知。
关键词:《项链》;反讽;贵族;人类生活
*本文为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经典阐释与文学文化比较”(项目编号2015-CXO-02)与201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项链》是莫泊桑最富盛名的短篇小说,研究者对它的主题历来争议不断。最典型的是“爱慕虚荣说”,认为作者通过玛蒂尔德的悲剧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①参阅莫泊桑著,郝运、王振孙译:《羊脂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译本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其次是“合理欲望说”,认为作品揭示了玛蒂尔德欲望的合理性,对其寄予了同情;②如M·雅洪托娃等提出:“它说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同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见【苏】M·雅洪托娃、【苏】M·契尔涅维奇、【苏】A·史泰因著,郭家申译:《法国文学简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53页。再次是“褒扬美质说”,认为玛蒂尔德善良单纯、重义轻利;③参阅齐剑英:《〈项链〉女主人公形象的文本解读》,《理论界》2005年第10期。最后是“美质毁灭说”,即作品表现了美的被亵渎和被毁灭。④参阅逯漓:《〈项链〉的“是”与“不是”》,《名作欣赏》2007年第5期。这些分歧实际源于对作品的侧重点不同:若重视玛蒂尔德舞会之前对生活抱着美丽梦想的情节,会讨论其欲望是“爱慕虚荣”,还是“合理欲望”;若重视舞会之后玛蒂尔德和丈夫备尝艰辛偿还欠债,会讨论是褒扬“美质”,还是慨叹“美被毁灭”。这些研究都很有见地。相比之下,系统的研究尤为珍贵。有学者从命运的不合理性、偶然性、荒诞性、辩证性等方面论证,认为作品既有讽刺虚荣心的局部主题,也有感叹人生命运的整体主题,这种观点全面而深刻。⑤参阅胡山林:《〈项链〉主题新解》,《名作欣赏》2007年第5期。还有学者提出,玛蒂尔德具有两面性,莫泊桑用突发事件将其隐性品质激发出来,在舞会等描写中有讽喻的意味;⑥参阅孙绍振:《一个人物的两个自我——读〈项链〉》,《语文建设》2008年第6期。还有学者提出作品表现了小人物对命运的抗争。综上可知,目前的研究还远未达成一致。
本文希望重点研究贯穿整个《项链》的反讽,认为围绕玛蒂尔德的“梦想-实现-突转-发现”,莫泊桑安排了三次对比,并形成两个典型的反讽情境。仔细分析这些反讽手法,我们会发现,它最终指向的是贵族留给世人的美丽幻梦和人类形而上意义上的荒诞困境。选择“项链”来结构整个作品,也许正如莫泊桑推崇的哲学家叔本华所说:“向往豪华、好奇等等,难以消灭的内在欲求,也是表示中断自然的顺序,最后仍是不免一场空幻。——居则琼楼玉宇,宴则通宵达旦的达官巨贾的生活,毕竟也不能超脱生存本来的贫弱。冷然静思,珠玉、宝石、舞会、盛宴,又能带给我们什么?”①【德】叔本华著,陈晓南译:《叔本华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这样的反讽和悲观主义亦可以从莫泊桑的其他作品中得到印证,也许其深层原因正是莫泊桑对贵族家世的无奈怀想和对人类生活的悲观认知。
一、第一次对比:不切实际的梦想与现实
小说的第一部分突出了玛蒂尔德的梦想与现实的对比,为第一个反讽情境设置了基础。
虽然“面庞儿好,丰韵也好,但被造化安排错了,生长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她没有陪嫁财产,没有可以指望得到的遗产,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男子来结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②【法】莫泊桑著,郝运、赵少侯译:《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页。本文所引《项链》均出自该版本,以下不再一一标注。她自感应该过高贵富足的生活,但现实不如人愿。虽然她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因为女子原就没有什么一定的阶层或种族,她们的美丽、她们的娇艳、她们的丰韵就可以作为她们的出身和门第。”——但她却真的没了机会,只好任人把她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
既有可能,又真的没了可能。在这样的遗憾中,玛蒂尔德是痛苦的。但她并没绝望,梦想还会时常浮现,让她既痛苦又迷醉。梦想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体现在住所、仆佣、社交、饮食等各个方面。
梦想中的生活典雅、闲适而浪漫:住所宽广雅致,接待室“四壁蒙着东方绸、青铜高脚灯照着、静悄悄的”,大客厅“四壁蒙着古老丝绸”,内客厅有“陈设着珍贵古玩的精致家具”,“精致小巧、香气扑鼻”;每天的日子从容悠闲,甚至在接待室服侍的男仆也“被暖气管闷人的热度催起了睡意,在宽大的靠背椅里昏然睡去”;社交生活优雅、风情,“午后五点钟跟最亲密的男友娓娓清谈”,那些高贵的男友是“所有的妇人垂涎不已、渴盼青睐、多方拉拢的知名之士”;饮食异常考究,“精美的筵席、发亮的银餐具和挂在四壁的壁毯,上面织着古代人物和仙境森林中的异鸟珍禽”,佳肴“盛在名贵盘碟里”,她“一边吃着粉红色的鲈鱼肉和松鸡的翅膀,一边带着莫测高深的微笑听着男友低诉绵绵情话”。她是社交界的中心,“讨男子们的喜欢,惹女人们的欣羡,风流动人,到处受欢迎”……
可是现实却一片灰暗,没有任何光彩:生活贫寒拮据,“住室是那样简陋,壁上毫无装饰,椅凳是那么破旧”;只有一个“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人”替她料理家务;日子沉闷枯燥,她“从来也不出门做客”,更不会有风雅动人的社交;每天坐在“三天未洗桌布的圆桌旁”吃着最平常的饭菜,汤盆里的炖肉都会引起丈夫的惊叹;“她没有漂亮的衣装,没有珠宝首饰,总之什么也没有”,当然也不会有风流倜傥的男士爱慕她,向她轻诉情话……
玛蒂尔德古典、精巧、华丽、优雅、甜蜜的梦境与寒伧、黯然、破旧、粗陋、平板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其实,在反讽情境中,自视甚高者不切实际的梦想正是反讽的基础,玛蒂尔德的梦想也是如此。克尔凯郭尔曾说:“有的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无所不知,面对这种愚蠢行为,真正的反讽是随声附和,对这一切智慧惊叹不已,吹捧喝彩,从而鼓励此人越来越狂妄荒诞,越来越高地往上爬,尽管反讽者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这一切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面对空乏无聊的热情,真正的反讽不以响彻云霄的欢呼、颂歌为足,而是争先恐后、更进一步,尽管反讽者知道这种热情是世界上最大的愚蠢。”③【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著,汤晨溪译:《论反讽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莫泊桑在小说一开始即突出了玛蒂尔德的梦想。随着情节进展,我们会看到,梦想越是美丽,对梦想的渴盼越是持久,最终的反讽效果越是强烈。起初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正是后来反讽情境的基础。
二、第二次对比:绚烂一夜与深渊十年
命运突然垂顾了她,让她终于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丈夫带回了一张教育部长的请帖。从伤心、忧虑没有美丽的衣裙和首饰,到丈夫为她订做了衣裙,好友借给了她钻石项链。万事俱备,玛蒂尔德参加了晚会。
这是她一生中最光彩绚烂的夜晚:本来生活孤寂,“从来也不出门做客”,压抑的梦想男友倾诉绵绵情话。现在,她的女性魅力充分展露:“她比所有的女人都美丽,又漂亮又妩媚,面上总带着微笑,快活得几乎发狂。所有的男子都盯着她,打听她的姓名,求人给介绍。”她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她已经陶醉在欢乐之中,什么也不想,只是兴奋地、发狂地跳舞。她的美丽战胜了一切,她的成功充满了光辉,所有这些人都对自己殷勤献媚、阿谀赞扬、垂涎欲滴,妇人心中认为最甜美的胜利已完完全全握在手中,她便在这一片幸福的云中舞着。”她完全沉醉在梦想实现的幸福里。
但是,陶醉于梦想实现的荣光正是反讽得以实现的重要一环,它与此前的梦想及以后的灾难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反讽情境:“梦想-实现-突转”。梦想的实现越是辉煌,以后的反讽效果越是强烈。“如果我们把反讽看作一个从属性的环节,那么它就是能看透生存中的乖戾、谬误以及虚荣的锐利眼光。……它并不摧毁虚荣,不像正义摧毁罪恶那样,它也不像戏剧那样具有和解的因素,它强化虚荣,使虚荣者更虚荣,使疯狂者更疯狂。”①【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著,汤晨溪译:《论反讽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21页。莫泊桑特别渲染了玛蒂尔德虚荣心满足时的幸福感,她被这一夜的荣光笼罩,浑然不知命运已将她作为嘲讽的对象。
晚会结束,她仍迷恋其中。丈夫为她披上的“平日穿的家常衣服”没有让她觉得温暖,却提醒她必须回到现实中来,她不情愿地意识到“那一种寒伧气和漂亮的舞装是非常不相称的”;坐着旧马车回家,冻得浑身哆嗦,她的梦想本应到此为止,但是她站在了大镜子前,希望“再一次看看笼罩在光荣中的自己”。就在这时,她发现项链丢了!
这样,情节的“突转”与“梦想-实现”结合起来,恰好形成了第一个反讽情境。
亚里士多德为“突转”(peripeteia)下的定义是:“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突转”是悲剧可以摹仿的、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重要事件,而且比完整的事件更能引起震动,“此类事件若是发生得出人意外,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或较好地]取得上述效果。如此发生的事件比自然或偶尔发生的事件更能使人惊异,因为即便是出于意外之事,只要看起来是受动机驱使的,亦能激起极强烈的惊异之情……所以,此类情节一定是出色的”。③同上,第82页。
《项链》出色地安排了“梦想-实现-突转”的反讽情境,以显在的借项链、丢项链为中心,将玛蒂尔德隐性的梦想与现实对比,梦想越美丽,现实越令人难耐;现实越痛苦,梦想的实现越魅惑;梦想的实现越绚烂,丢失项链的打击越巨大;情节的突转越剧烈,对人物的反讽效果越显著。小说的布局是一连串巧妙地导向结局的匠心组合,事件朝着高潮和结局发展,它满足了开端所引起的好奇,也为下一次反讽奠定下基础。
玛蒂尔德的生活一下子跌进了深渊。由此,作者又设置了第二次对比,即梦想实现的绚烂一夜和偿还欠债的深渊十年相对比。对比再次集中在几个方面,玛蒂尔德不是对现实中的住所、仆佣、社交和饮食不满吗?不是有着美丽的梦想吗?现在,就连她本来拥有的也给她剥夺掉:
本来,她厌恨住室简陋、椅凳破旧。现在,“搬了家,租了一间紧挨屋顶的顶楼”;本来,她苦恼没有安逸和排场。现在,“辞退了女仆”,“家庭里的笨重活,厨房里的腻人的工作,她都尝到了个中的滋味。碗碟锅盆都得自己洗刷,在油腻的盆上和锅子底儿上她磨坏了她那玫瑰色的手指甲。脏衣服、衬衫、抹布也都得自己洗了晾在一根绳上。每天早上她必须把垃圾搬到街上,并且把水提到楼上,每上一层楼都要停一停喘喘气”;本来,每天坐在圆桌旁,听着丈夫的惊叹她都厌烦。现在,“她穿得和一个平常老百姓的女人一样,手里挎着篮子上水果店,上杂货店,上猪肉店,对价钱是百般争论,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保护她那一点可怜的钱,这就难免挨骂”;本来,“从来不出门做客”,怀抱着古典雅致的梦想,伤心“没有漂亮的衣装,没有珠宝首饰”。现在,“她变成了穷苦家庭里的敢做敢当的妇人,又坚强,又粗暴。头发从不梳光,裙子歪系着,两手通红,高嗓门说话,大盆水洗地板”。
现在,她是沉在生活的底层了。不再有梦想,只是一天天地不修边幅、勤苦劳作、拼命节俭、攒钱还钱。她安心于寒伧、黯然、粗陋、平凡的现实了,她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十年前的梦想越是优雅、甜蜜,那一夜梦想的实现越是绚烂辉煌,眼下的生活越是极大的讽刺。然而,莫泊桑没有就此收笔。
三、第三次对比:忍受磨难的英雄与命运捉弄的玩偶
为偿还债务,玛蒂尔德艰苦生活了十年。十年之后,当她已经变成一个坚定的妇人,“劳累了一星期,要消遣一下”的时候,却被生活“消遣”了。她突然发现项链是假的!这是作品出现的第二次情节的“突转”,而且和“发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小说的第二个反讽情境。
“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发现”“也可以和无生命物和偶然发生之事联系在一起;此外,还可发现某人是否做过某事。”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突转”和“发现”是“悲剧中的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②同上,第64页。它们常常造成主人公凄绝荒诞的命运,引发怜悯和恐惧。
这样看来,《项链》中的“突转”和“发现”既能造成主人公不幸的命运,引起怜悯和恐惧,也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只是莫泊桑的侧重点不同。
不管在玛蒂尔德借项链时福雷斯蒂埃太太那么爽快地一口答应显得多么可疑,也不管买项链时商人说只卖出过盒子多么不正常,还是还项链时福雷斯蒂埃太太看都没看就收下了项链多么令人匪夷所思,其实,所有这些“伏笔”都不是作者强调的重点。项链的真假已经不重要,因为伤害是真的。假的珠宝可以赔偿,但青春岁月和期许却一去不复返。这样沉重、无奈的反讽是一般灾难所不能相比的。有评论者认为,玛蒂尔德通过十年磨难变成了生活踏实的女人。似乎是她付出十年艰辛,终于了然生活的真理,是痛苦成全了她。其实不然,生活本身的荒诞和变幻莫测才是作者要说的。
十年前,当找不到项链时,她“一下子英勇地拿定了主意”,赔偿项链,还债;十年来,她艰苦生活,恪守道义,选择做忍受磨难的英雄。但真相显现,却让十年的勇敢和努力一下子成了徒劳,她变成了命运捉弄的玩偶。生活露出了它荒诞和残忍的真面目:在你以为达到目的时,却发现根本就没有目的;在你以为赢得了胜利时,却发现根本没有对手;在你经受了痛苦后才知道,一切痛苦都是白费。在忍受磨难的徒劳中,原来的“英勇”饱含了反讽。她原本可以不必失去现实中拥有的一切,不必付出十年的艰辛,现在她坚韧、痛苦的抗争都成了无意义、无价值。
反观玛蒂尔德的遭遇,在一次次对比中——表象与真实的对比、愿望与结果的对比,在一次次突转中,终于形成了典型的反讽情境。并且,“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照越强烈,反讽越鲜明”③【英】D·C·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受嘲弄者多少明确地表示依恋未来,而始料不及的事态变化使他的计划、企盼、希求、忧虑或者热望发生逆转或遭到挫折。他最终能够获得他曾经盼望的东西,但为时已经太晚;他抛弃了他后来发现实属不可或缺的东西;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在不知不觉中采取了恰好引导他远离目的的步骤;他为了避免某事发生而采取的手段,证明恰恰是使某事发生的手段”。④同上,第98页。
这是一种特殊的反讽:“命运的讽刺”(cosmic irony or the irony of fate),即“上帝、命运与宇宙作用被描绘成故意左右时事的主宰,他们造成主人公不切实际的愿望,继而加以百般戏弄”。①【美】M·H·艾布拉姆斯著,朱金鹏、朱荔译:《欧美文学术语辞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玛蒂尔德对其处境深怀不满,产生美丽的梦想,为反讽设下基础;梦想的力量一直累积,推动她不断向前,终于有了舞会上的辉煌;就在这时情节突转,项链丢失,她要为那一夜的光彩付出艰辛;十年熬尽,真相显露,原来艰辛乃是徒劳,坚韧早被戏弄。这是怀有希望、恐惧、期待和允诺的人,与邪恶而又不可更易的命运之间的斗争,而人最终失败。通过“梦想-实现-突转-发现”的情节安排,《项链》表现了典型的“命运的讽刺”,玛蒂尔德的遭遇乃是“捉弄人的力量(而非人力)——无论是上帝、魔鬼,还是人格化的命运、人生或运气——操纵的结果”②【英】D·C·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她最终成为命运摆布的玩偶。
四、反讽意旨:从贵族的美丽梦幻到人类的总体讽刺
从根本上说,文学乃是隐喻的系统。莫泊桑也认为,小说家“以一种本人所特有的、而又是从他深刻慎重的观察中综合得出来的方式来观看宇宙、万物、事件和人”,“他的目的决不是给我们述说一个故事,娱乐我们或者感动我们,而是要强迫我们来思索、来理解蕴含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③【法】莫泊桑:《“小说”》,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264页。《项链》正是莫泊桑借助“充满个性的人世假象”展示其对人类生活整体思考的结果,故事只是用来隐藏“自我”的面具,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面具,辨认出莫泊桑隐藏的“自我”。④莫泊桑曾说:“要使得读者在我们用来隐藏‘自我’的各种面具下不能把这‘自我’辨认出来,这才是巧妙的手法。”参阅【法】莫泊桑:《“小说”》,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一)贵族迷梦的破灭
反讽的高深之处在于它指涉的是某种普遍的现实,即“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⑤【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著,汤晨溪译:《论反讽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玛蒂尔德的故事也是如此。
玛蒂尔德的一切悲喜剧都源于最初那不切实际的梦想,晚会之所以让玛蒂尔德“狂热”“兴奋”“沉迷”,并为此付出十年艰辛,正因为那是她梦想的唯一一次实现。可那梦想绝不是普通妇人能有的梦想,而只能是贵族留下的美丽梦幻。
玛蒂尔德向往的生活是古典、华丽、优雅的:接待室、大客厅、内客厅不是随意地装饰,而是四壁蒙着古老丝绸;家具上不是随意摆放实用的东西,而是陈设着珍贵的古玩;室内不是灯火明亮,而是雅致的青铜高脚灯发出幽静的光;男仆不是忙碌慌乱,而是悠闲地服侍;饮食不是吃饱吃好,而是要有精美的筵席、发亮的银餐具;谈话不为交流,而要风雅迷人……她的梦想有很高的文化含量和精神诉求,审美修养也不是一个只拥有金钱的妇人能够设想的,她的梦想应该是像贵族妇女一样生活。
但通观整个作品的情节设置,她的生活遭际又不啻是对这种贵族梦想的极大讽刺。因为贵族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复有迷人的光彩,它留给世人的只能是残光碎影的魅惑。正如《女人的一生》表现了贵族和贵族文化是如何一步步破落衰败的,《项链》也是一部幻想破灭的小说,它指向的也正是贵族迷梦的破灭。
这一思想除了与19世纪末法国贵族的没落有关,也与莫泊桑本人的家世相连。莫泊桑出生于托尔维伊尔市一户没落贵族家庭,全名亨利-勒内-阿尔贝-居伊·德·莫泊桑(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他名字中的“德”(de)字表示他出生在贵族家庭,其实能标志他的贵族血统的也只有这个“德”字了。在他祖父时期,这个贵族家庭就和封建制度一样趋于没落。莫泊桑的父亲更是生活放荡、嗜赌成性。这个家庭虽然衣食无忧,但昔日贵族的荣光已经一去不复返。
莫泊桑生活在资产者和贵族地主激烈冲突的时代。当他回望贵族家世,尽管充满无奈的怀想,却不得不承认贵族没有力量抵挡现实的争斗;当他面对现实,却又清醒地看到,整个社会充满了资产者的实利主义、掠夺成性和腐朽寄生。莫泊桑既痛恨资产者咄咄逼人的进击,同情贵族阶级面临的挤压,又无奈地承认这是生活的必然。对生活的认识越深刻,越是陷入更深重的悲观、无助,他说:“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是可怕地凡庸和胆怯。或许,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目光如豆和残酷不仁。”人们被“丑恶的偏见、比罪行本身还更令人厌恶的关于名誉的口是心非的理解、堆积如山的伪善感情、装模作样的体面、可恨的功名心所压迫,俘虏和毁损”。①【苏】但尼林著,夜澄译:《莫泊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7页。
(二)形而上意义上的总体反讽
反讽“蕴藏着一种先天性,……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对存在的总体从反讽的角度予以观察”。②【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著,汤晨溪译:《论反讽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莫泊桑对贵族生活的无助感深化为在形而上意义上对人类的总体思考,正如他感叹的:“如果她没有丢失那串项链,今天又该是什么样子?谁知道?谁知道?生活够多么古怪!多么变化莫测!只需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就能把你断送或者把你拯救出来!”可见,莫泊桑既通过玛蒂尔德个人讽刺了贵族迷梦,又通过这一个体指向全人类。她的故事中正隐含了人类思想的无力、生活现象的不可认知、人的痛苦的挣扎,以及一切希望和努力的徒劳等悲剧性主题,并最终指向整个人类悲剧性的存在状态。
从本源上说,人类存在即含有反讽的成分,因为从理性角度看,人类生活有着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一方面是“地道的或原始的反讽者”上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超越凡俗,独揽一切,永不泯灭,无拘无束”;另一方面是人,他“深陷在时间和事务之中,盲目行动,临事应付,生命短暂,不得自由——而且自信得竟不知道这即是他的窘境”。③【英】D·C·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作者借助玛蒂尔德的“梦想-实现-突转-发现”最终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存在和现象,而是针对整个人类存在。正如但尼林所说:“这种孤独的人深信,他来到世界上只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快活和享受;他以自己的整个生命冲向这种幸福。但是莫泊桑指明,对于这种人说来,幸福是悲剧性地不可企及的,不但由于类如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偏见和虚伪的小市民道德的不相干的阻碍,而且还因为人本身是脆弱的,渺不足道的,不能了解幸福在哪里以及怎样才算幸福,以致把它忽略过去,不能成为幸福的小心翼翼的保全者,而他的命运仍旧只是往后的悔恨,一生徒劳无益地消逝了的痛苦的认识和逼近的老年。”④【苏】但尼林著,夜澄译:《莫泊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1-12页。在这个意义上,莫泊桑超越了玛蒂尔德,和她的感觉拉开了距离,他超然如神灵一般,怜悯地、不时又带着轻蔑地展示整个人类的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项链》展示了没有反讽者的反讽:生活充满隐秘的奸诈和狠毒,设下圈套和陷阱,人们就处身于这样可笑又可悲的境地,热情和梦想蒙蔽了理智,造成可怕的灾难。
这种认识源于莫泊桑对整个生活的悲观主义态度。在哲学上,他深受叔本华的影响,认为叔本华是“人间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梦想破坏者”,人生活在一个空虚的、失去意义的世界里,受到迟钝的本能的支配,被痛苦和贫困压垮,显得平庸、自私、狭隘;同时,人是孤立的,不被别人所了解。⑤参阅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而“生活是由最相异,最意外,最相矛盾,最不调和的事物组成的;它是粗糙的,没有次序,没有联贯,充满了不可理解的变故……”⑥【法】莫泊桑:《“小说”》,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
然而,《项链》在形而上意义的隐秘的嘲讽中又包含着莫泊桑对现世的深刻的悲悯,这种悲悯是对于世界在本质上即为矛盾、唯有爱恨交织的态度方可把握其矛盾整体的事实的认可。就像罗莎丽所说的:“您瞧,人生从来不象意想中那么好,也不象意想中那么坏。”①【法】莫泊桑著,盛澄华、张冠尧译:《一生漂亮朋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莫泊桑对人类的悲悯,既是受福楼拜教育时所接受的深刻的社会怀疑主义的发展,又是他关于人类一切努力徒劳无功的意志沮丧的观念愈来愈深刻而尖锐的表现,是由他对社会现实的深恶痛绝、而同时又意识到跟现存事物秩序的斗争中自己的无能为力所决定的。因此,莫泊桑在《项链》中的态度,既是对人类苦难的充满热忱和敏感的描写,又充满了怜悯和同情。
结语
莫泊桑在许多作品中设计了反讽,《项链》尤为突出,这是莫泊桑充满伤感的作品,也显示着他思想的高深与艺术的复杂。莫泊桑早期创作中明朗的思想在末期愈来愈屈从于惊动不安的情绪,他在周围主要是见到否定性的现象:残酷、畸形、盲目的谋杀、各种各样的折磨和恐怖、惊心动魄的发现……在1889年的短篇小说《催眠女巫》里,莫泊桑对受苦受难的人发出哀叹:“噢,不幸的,不幸的,不幸的人,我体验到他们的一切痛苦,由于他们的死亡而痛不欲生……我经历到他们的一切苦难,在差不多一小时之间忍受到他们一切的折磨。我知道促使他们达到这样结局的一切的不幸,因为我熟悉生活的一切卑鄙的欺骗,而谁也没有像我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这些。”②【苏】但尼林著,夜澄译:《莫泊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51-52页。“生活的一切卑鄙的欺骗”,这也许是对《项链》最好的注脚,而《项链》中对人类荒诞困境的刻画、对人类生存中偶然性的强调、对人的失望无助感的诉说,又隐含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意绪,同他的文学导师福楼拜一样,启发着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③莫泊桑当时已经注意到象征主义的创作。参阅莫泊桑:《“小说”》,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责任编辑郑慧霞】
作者简介:孙彩霞,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