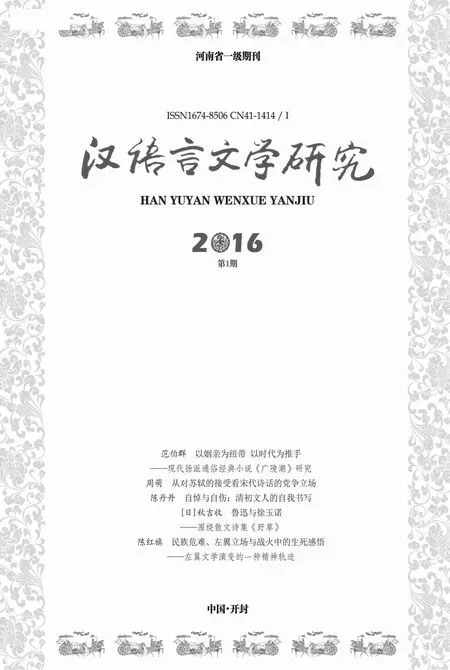1930年代东京左翼文坛内中国大陆与台湾作家的文学交往*——以张文环佚文《台湾的创作问题》为分析中心
马泰祥
1930年代东京左翼文坛内中国大陆与台湾作家的文学交往*——以张文环佚文《台湾的创作问题》为分析中心
马泰祥
摘要:作为日据时代台湾顶尖作家的张文环,曾在1930年代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机关杂志《杂文》的文学建设活动。他的《台湾的创作问题》一文长期湮没无闻,在这篇评论里作者详尽地提出了自己对“台湾文学”现状及其发展方向的分析和构想。通过细读这篇佚文,可以得知在左联东京分盟的左翼文学建设大业中,不仅有旅日中国留学生的辛勤笔耕,还融入了适时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作家的思考;同时这篇佚文的存在亦展示出在1930年代日本东京左翼文学运动中,祖国大陆和台湾作家之间的文学联系与交往的深广度可能比既有论述的规模更大。
关键词:张文环;杜宣;左联东京分盟;东京左翼文坛;文学交往
《张文环全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收入《台湾的创作问题》。较早注意到这篇文章的,是台湾清华大学台文所的柳书琴教授。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机关杂志《杂文》第1期,1935年5月,第23-24页。她在专著中曾提及这篇文章:
1935年5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简称左联东京支盟)机关志《杂文》创刊号出版。该号目录上明载《台湾文坛之创作问题》一篇,作者为张文环。不过翻阅该志各期均未见此篇,也没有其他署名张文环的文稿。换言之,这篇评论应是有目无文的。②柳书琴:《荆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96-297页。此书为柳教授2001年台湾清华大学博士毕业论文出版物,书中《张文环创作年表》载入《张文环全集》。柳教授专著中将此文的题目列为《台湾文坛之创作问题》,与《杂文》原刊上的题目稍有不同,有可能《杂文》在编辑中资料编排或有阙漏,题目发生了误植。柳教授还推测张文环彼时或未及交稿,因而“有目无文”。是故《台湾的创作问题》一文终未能编入《张文环全集》。如今通过检视《杂文》原始刊物而发现了文章全貌,或可得出结论:此文应为《张文环全集》的集外未刊佚文。
一
《杂文》这份刊物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对193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左翼文坛却有一定影响。在1935年5月15日创刊后,该杂志在日本东京编辑、印刷,再运回上海发行。因为受众广、影响大,在刊行三期后被日本方面禁止发行(一说为国民党上海官方所禁)。③被日本当局查禁说见林林:《“左联”东京分盟及其三个刊物——回顾文学路上的脚印》,《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第162页。被上海官方查禁说见魏猛克:《“左联”往事漫忆》,朱日夫等整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从第四期开始,根据郭沫若的提议改名为《质文》,继续发行至1936年11月而终刊,共刊行八期。对于这份刊物的研究和理解,大多从中国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力量聚合入手,如郭沫若与鲁迅此时因为同在《杂文》第三期刊出作品而再次产生互动,双方均有意以此作为消弭意气之争、实现新阶段“左翼联合”的重要契机。据魏猛克回忆:在第三期杂志出刊后,“鲁迅来信表示要与郭沫若加紧团结,消除隔阂,共同对敌,更主张左翼文艺界都应大力加强团结”,“郭沫若看了这信后,很为感动。他俩的革命友谊,促进了左翼文艺队伍的团结”。①魏猛克:《“左联”往事漫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第161页。于是,东京“左联”分盟对于国内左翼文艺运动的配合情况,是《杂文》这份刊物通过文艺创作的刊载所呈现出的最重要的文学特色。
彼时“左联”东京分盟除《杂文》外,还有《诗歌》《东流》两份刊物,刊物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三份刊物的同时存在,无疑表明了彼时东京艺文活动的自由度相当可观,且其时旅日知识分子对左翼文学活动的参与兴致及认同度也颇高。日本学者小谷一郎在考察《东流》的创办情况时指出,“除东京左联成员以外,广大旅日中国留学生也参与了《东流》杂志的创办。也就是说,《东流》杂志并非仅仅是依靠东京左联成员来维持的,它得到了周围众多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支持。其后创办的杂志《杂文》、《质文》、《诗歌》也应属于同样的情形”。②[日]小谷一郎:《论东京左联重建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艺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第61页。实际上,《杂文》第一期中《台湾的创作问题》的登载,还提醒我们注意:在“左联”东京分盟的左翼文学建设大业中,不仅有旅日中国留学生的辛勤笔耕,而且还融入了其时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作家的思考。
二
对于张文环这位台湾作家而言,这篇佚文的发现也很有意义。张文环(1909-1978)为日据台湾时期最为重要的新文学作家之一,1931年进入日本东洋大学文科就读后,次年他就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台湾文化社”,并在1933年东京成立的“台湾艺术研究会”中,列位为重要成员,参与文艺刊物《福尔摩沙》(『フォルモサ』,1933-1934)。1937年返台以后,他的文学活动还包括主编《风月报》日文版(1938)、创立启文社发行《台湾文学》(1941-1943)、作为战时台湾代表赴东京参加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2)等等。在日据台湾文学史上,张文环素以小说中浓郁的乡村风情以及丰富的民俗色彩而著称,小说《论语与鸡》《阉鸡》和《夜猿》等,已是日据台湾的文学经典。而他那乡村优位性的书写思路,展示出其现实主义“消极抵抗”的美学风格,“这种都市与乡村对立的思考方式,放在殖民地社会的脉络来考察,颇具有消极批判的意味。因为,都市代表日本人价值观念的渗透,而乡村则是台湾人的精神堡垒”。③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91页。此外,自创作伊始,张文环就采用日语创作,台湾光复后遇到转用中文创作的“瓶颈期”致使文学活动骤减,直到1970年代才重操日文,写作长篇小说《在地上爬的人》。与其丰富的小说创作相比,张文环的随笔创作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在《全集》中的两卷“随笔卷”中,有关文学的专论也并不多见,作家1937年返台之前旅日期间的文艺评论尤为鲜见。根据《张文环全集》可知,此阶段张文环的文学评论,除了杂志《编辑后记》以外,只有刊载于《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三号的《说自己的坏话》、第二卷第五号的短文《道歉》以及《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三号的《明信片》三篇而已。《台湾的创作问题》作为张文环在东京时期为数不多的、论述主题相对集中的一篇文艺评论,如将其与作家其他阶段文学评论文章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勾勒出张文环创作初期文学理路的建设过程,亦可发现张文环如何以“左翼联合”的国际化视野来看待台湾文学在日据时代的区域特性。
《台湾的创作问题》约900字左右,从正文结尾“因为超过了编者被指定的字数”的论说可以看出,这篇文字是应《杂文》编辑的邀请专门撰写的。这与刊物编辑林林当时“和与祖国分离的台湾文艺青年合作,我们的刊物登了张文环的《台湾创作问题》(《杂文》第一期),吴昆煌的《现在的台湾诗坛》(《诗歌》第四期),台湾朋友又选择较好的作品译为日文,送到日本文学杂志刊登”①林林:《“左联”东京分盟及其三个刊物——回顾文学路上的脚印》,《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第166页。此处作者记述稍有误,文中张文环评论的标题应为《台湾的创作问题》,台湾作家“吴昆煌”应为“吴坤煌”之误。的相关回忆是吻合的。这份文稿经谁邀约而诞生,由于资料的不足,目前难以定论。根据柳书琴早前的判断,她认为台湾作家吴坤煌很可能是联系“左联”东京分盟成员与旅日台湾作家之间文学活动的关键人物。吴坤煌与中国诗人雷石榆同为日本普罗诗人组织“前奏社”机关志《诗精神》同人,“在以日本作家为主的集团中,他们极可能是唯一的台湾人或中国人”,②柳书琴:《荆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第315页。因此或惺惺相惜。雷石榆身为《诗歌》的主编(1935年),使得他有可能出面为《杂文》约稿。另可引起注意者:在1935年期间雷石榆陆续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大陆文坛及诗坛的概观性评论,如在《诗精神》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中国詩壇の近状」(《中国诗坛的近况》,1935年1月)、东京《文学案内》发表的「中国文壇現狀論」(《论中国文坛现状》,1935年10月)等等,这些评论的题目及内容在在透露出雷石榆对中国大陆文坛从宏观角度进行的点检与反思。是故,他极有可能从“台湾文坛的创作现状”这个宏观方面来命题,请求吴坤煌及其台湾文学同人撰文来向大陆文坛介绍台湾文学的近况。最终,张文环接受了这个文学任务,以日文原稿书写了一篇文艺论文,由杜宣翻译成中文后刊载在《杂文》创刊号上。
具体到《台湾的创作问题》这份文本,张文环在有限的篇幅内详尽地提出了自己关于“台湾文学”现状以及发展方向的分析和构想。其立论的关键点,在彼时日据台湾文学创作的语言-文字问题。众所周知,日据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历经殖民宗主国语言同化的强力作用,而产生了一种特异的文学语言更迭现象:从1930年代开始,日语文学创作逐渐取代汉文文学创作,占据文坛主流地位。1937年以后,日语创作的绝对优势扩大:除通俗文艺圈外,日语几乎成为文坛唯一的创作语言。固然,日语创作显示出殖民地文化烙印,但是“它反映出的民族性的精神倾向和表达方式仍然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③倪婷婷:《中国现当代作家外语创作的归属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它们当然是中国文学遗产中较具地域特性与时代印记的一部分。彼时的台湾作家,特别是自创作初期以来就采用日语作为唯一书写语言的作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语言-文化选择的,张文环这篇论文提供了现场式的文学报导。作者指出文学运动在台湾的文化意义在于打破了“文学的对封建时代的不关心”,以及提点文化界觉悟到“一般文化研究之必要”,文学创作因此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对于台湾文学运动新建设的关键,张文环指出“这就关联到了我们的文字的大问题来了”:究竟是用日文创作,还是用汉文创作。自1919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教育令》,开始推行日文教育;1933年更开始施行《国语普及十年计划》(所谓“国语”即日语),以求日语日常化的实现;到了1937年,台湾日语理解者率从1930年的8.47%,一跃升至1937年的37.8%,进入1940年代后,更是突破51%。④[日]藤井省三著,张季琳译:《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46页。此一事实表明了日语在实际上已渐次成为台湾文化界占据主流的强势语言。加之日语“公学校教育”、日语文学读书市场的生成等软性文学生产方式的规约,日语已成为1930年代步入台湾文坛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首选文学创作语言。此时开始文学创作的台湾作家,无论是意识形态光谱偏向左翼的杨逵、吕赫若,还是较为倚重艺术感觉表现的巫永福、翁闹,其文学创作语言都是日语,张文环亦不例外。而张文环思考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深知在此时日语写作趋势化的大潮中,不弃用汉文写作的深层意义:“若是要把我们的真正生活描写出来的话,那就非用汉文不可,否则的话,则对于我们的生活感情和种种的风俗的细微描写是表现不出来的”。母语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张文环在殖民地语言困境下,被迫用日语来进行的思考,因此弥足珍贵。
在语言-文字问题之上的,乃是台湾文学的定位问题。在日据台湾同期,适时的台湾文学创作都被列为日本的“外地文学”。这种指称源自1940年代日人岛田谨二对法国殖民地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他将这些观念和方法挪移到台湾文学场域之中,认为“台湾文学作为日本文学之一翼,其外地文学——特别作为南方外地文学来前进才有其意义。和内地风土、人和社会都不同的地方——那里必然会产生和内地不同而有特色的文学。表现其特异的文学名之为外地文学”。①[日]岛田谨二:《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文艺台湾》第2卷第2号,第13页。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3册,台南:“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06页。他的种种论述将台湾本土生发的文学强行与日本内地的文学进行捆绑,认为其“该视为本国文学史研究的延长线之一”。而透过《台湾的创作问题》一文可以发现,早在1930年代中期,张文环已经试图为台湾文学进行定位。他反问,“究竟日本文坛能够收容我们的作者吗”?答案是“这件事对我们是不可能的”。是故,结合台湾文学场域中1930年代仍存有的日语与中文创作并存的文学结构,他重新为台湾文学定位:“因此,我们在不能无视作者生活的限度内,我们不得不着目于日本文坛和中国文坛之间来开展台湾文学的计划不可”。从以台湾的文学创作实绩来沟通、系连中日文坛而不是简单划分文学从属权这个角度,张文环获得了对台湾文学区域特性的体认。固然,这一思路来源于1930年代东京左翼文艺运动下“国际联合主义”的时代风潮,但同时可以发现,张文环从台湾殖民地文学这种特性出发,以“文学沟通”的文化视域间接抵抗着“日本文学归属”话语论述的侵蚀。有论者即指出,“虽然语言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但沟通终究超越语言的范畴,涵盖了较为完整的文化境界,而这也是作家寄望透过作品来承载、传递的文化信息”。②[新加坡]伊斯迈·达立著,李勤岸译:《后殖民文学的语言》,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04页。张文环试图传递的文化信息,正在于如何从语言并存的多样化角度入手而超越语言本身的中介层面,将台湾作家的生存处境、思维趋势以及文化抉择,透过跨区域的交流而获得大陆左翼文坛的理解。虽然作家同时认识到,“延入中国文坛的这件事,在我们现在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容易被考虑的”,但以“文学沟通”的细大不捐,作家坚信终究可以觅得台湾文学之归途。
三
1926年8月,台湾新文学先驱者张我军造访鲁迅,在交谈中张我军提及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文学联系的泥阻不畅:“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鲁迅在事后的回忆中自述“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也只能表示“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③鲁迅:《而已集·写在〈劳动问题〉之前》,《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台湾新文学改革运动诚然是祖国大陆文学革命的延伸,④杨若萍:《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1652-1949)》,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但是日据台湾因为殖民地特性,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学联系,也不能不受到殖民宗主国的严苛桎梏。因此二者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台湾新文学作家与大陆新文学作家之间相互影响来实现。比如鲁迅、胡适、郁达夫、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在台湾本岛文学报刊的登载,大陆作家对台湾文化圈的访问和对谈,以及台湾新文学作家如张我军等在大陆的文艺活动种种软性互动来加以实现。二者之间直接对话的机会非常难得,而在1930年代的日本东京,较别处而言相对宽松的艺文环境、远离中国大陆“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境,使得在这里聚集的跨区域左翼知识分子有了能够沉淀思绪、进行相互对话的文学空间,来自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左翼作家也及时抓住了这一时代契机进行文学经验上的交流。身处东京,对于远离大陆左翼文学第一线的旅日大陆作家以及远离台湾本岛的旅日台湾作家而言,他们之间的联合尤其具有深意。在进入1930年代中后期以后,台湾文坛的日文创作已经开始逐渐占据主流,适时的台湾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日语创作及其定位,张文环的这篇佚文《台湾的创作问题》解答了这个疑惑。通过分析这篇篇幅有限却意蕴无穷的文论,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旅日大陆留学生与旅日台湾留学生之间在左翼文学的大纛下产生互动、联合的真实图景。在先行研究中,中国大陆与台湾留学生之间的互动情况,几乎都以雷石榆一人为焦点而展开,使得雷石榆获得了1930年代“参加这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大陆人”①张丽敏:《雷石榆人生之路》,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的称号。如今这个说法似乎可以挑战一下了,比如,在《台湾文艺》上曾发表作品的魏晋,他与吴坤煌以外的其他台湾作家是否有交游;《台湾的创作问题》的译者杜宣,和张文环是否有直接联系,这些都可以随后再进行讨论。通过对这篇佚文的考察,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在日本东京左翼文学运动中大陆和台湾作家之间的联系,可能比既有论述的深广度还要大。
附录:
台湾的创作问题
张文环(台湾)
虽然是落后的台湾精神文化运动,近一二年来却很盛旺的在发展着,但是这是像失了练习场的运动会一样,被建立了的计划,到中途若不把方针改变,终于会衰落的。对于这事情的起先是怎样我们暂且不谈,然而目前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拿出来来看一下的。
台湾的文学运动是被挟在政治经济运动的胁下而登场的。我想这不就是台湾文学的出发点吗?但是它的出发点的动机也和它能力一样的失败了。然而对于从前文学的对封建时代的不关心是被打破了,对于一般文化研究之必要也觉悟到了。而开始有对于苦痛生活中的种种烦闷所发泄出来的作品。至于到达了怎样一层结果那是还没有的。不过,我们是有了这样一个过程而已,至于这过程中对于我们的态度和方法,这就关联到了我们的文字的大问题来了。这就发生了这样个问题,是用日文创作呢?抑或是用汉文创作呢?若是要把我们的真正生活描写出来的话,那就非用汉文不可,否则的话,则对于我们的生活感情和种种的风俗的细微描写是表现不出来的。但是我们要努力用汉文的话,那么读者们也非读汉文不可。但现在台湾的青年们是多半没有汉文读的。从老年,中年,少年,以至于幼年各阶层一想的话,那么汉文和日文都成了必要的了。因此不用日文是不可能的问题也必然的发生了,那么用日文创作是怎样地被盛入台湾文学之中呢?假若我们要说明这一点的话,那非连络到文字的问题不可,不能读日本文的人他是会读汉文的,不会读汉文的人他是会读日本文的。因此,我们在不能无视作者生活的限度内,我们不得不着目于日本文坛和中国文坛之间来开展台湾文学的计划不可。但是究竟日本文坛能够收容我们的作者吗?这样的日本文坛闯入者从经济的地或者从日本文坛宏大处看起来,这件事对我们是不可能的。至于来延入中国文坛的这件事,在我们现在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容易被考虑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坚实的文化团体是非常必要的事,要之,这是要通过团体的力量,像中野重治氏说的一样,汉文的作品用日文翻译出来,日文的作品用汉文翻译起来这样来供给各读者层,产生这种供给的机关不就是我们当前先决的问题吗?——因为超过了编者被指定的字数,其余的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杜宣译)
【责任编辑郑慧霞】
作者简介:马泰祥,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据时期台湾文学。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台湾文学场域中语言转换现象的文化考察研究》(2015BS1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期间曾得到杜宣先生之女桂未明女史以及台湾清华大学台文所柳书琴教授的指点,特此致谢。